- +1
寫作大賽獲獎者談|余同友:為什么要記住一場多年前的海難?
編者按:2019年7月19日,首屆“澎湃·鏡相”寫作大賽頒獎典禮落下帷幕。本次大賽于2019年1月23日啟動,由澎湃新聞主辦,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今日頭條聯合主辦,旨在挖掘極具價值的時代標本,培育優秀寫作者,并長期孵化紀實類佳作。學術評審、業界評審兩輪匿名制交叉打分,最終決選出“鏡相”特等獎1名,一等獎2名,二等獎3名,三等獎4名,優勝獎、提名獎若干。
“鏡相”欄目將陸續刊出對大賽前十名獲獎者的訪談,挖掘他們創作背后的故事,探討對非虛構寫作的理解和展望。今天的訪談來自特等獎得主余同友,他的獲獎作品是:《村里有座廟——對1990年安徽東至“1·24海難”民間記憶的打撈》。
文|薛雍樂(澎湃新聞)

在首屆澎湃新聞“鏡相”寫作大賽中,憑借《村里有座廟》獲得特等獎的余同友三次重返事發地,采訪幸存者、遇難者家屬及救援人員,打撈起這段被遺忘的往事,還原出逝者鮮活的面貌和生者綿長的回憶。終審評委評價稱,本文“題材厚重深邃,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同時,文字冷靜克制,沒有絲毫的過度渲染……細節充沛,立意深遠”。
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余同友表示,每一個平凡的個體都值得被記錄,自己有責任用文字為那些逝去的生命立一座紀念碑。他也從職業作家的角度,對加強非虛構的沉淀和文學性提出了建議。

為生命豎一座文字紀念碑
澎湃新聞: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專業背景和寫作經歷。
余同友:我出生于70年代,學的是財務管理,跟寫作沒什么關系,后來在機關做公務員,再到當地報社做了十年的編輯和記者,2009年調到安徽省作家協會,屬于半個專業作家。我從小就有一個寫作夢,在學校里就開始寫了,一開始寫詩歌、散文,后來開始寫小說。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會想寫“一·二四”海難?
余同友:這起事件發生在1990年1月,我當時在老家的一個鄉鎮做實習生,離事發地點大概有七八十公里。那時資訊很不發達,外面知道這起事件的人很少,但慢慢就口口相傳,等傳到我這里的時候,已經是夏天了。
后來過了幾年,我到市里的報社上班,碰到縣里的人,在偶然閑談間聽他們說了,我才第一次知道那時竟然死了那么多人,很震驚也很疑惑,就一直惦念著。我特別關注這個題材,可能跟個人經歷有關。我少年的時候,母親就死于一場意外事故,所以,對死亡的理解、對逝者的惦念,我可能比別人體會得更深。
雖然我很想寫,但采訪難度非常大,一開始沒打算自己寫。大概從十年前開始,我就把這個選題不斷推薦給其他寫作的朋友。可能他們覺得有難度吧,我前后問了兩三個人,他們都沒寫。
2017年,有一家我認識的文學類雜志開設了一個非虛構欄目,我跟編輯吃飯的時候又聊到這件事。對方說:那就你寫吧。我就準備試試,專門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去了事發地。
寫成非虛構是定下來了,但怎么寫我心里沒有底,一直寫了三稿,幾乎都是推倒重來。我寫中短篇小說的時候,從來沒有為一個故事寫過三稿。第一稿,我是以尋找真相的視角去寫,寫得很不滿意。第二稿我把自己的情感帶進去寫,發現也不行。最后一稿才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想過把它寫成小說,為什么要把它寫成非虛構?
余同友:我覺得這不適合寫成小說,或者說,我不知道怎么將它作為素材寫成一個小說。這起事件對我的沖擊太大了,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在于為遇難者立一座文字的紀念碑。標題是《村里有座廟》,我就想用文字來搭建一座廟,來表達對這起事件的關切。
澎湃新聞:您是怎么找到那些受訪者的?三次尋訪您分別做了什么?
余同友:找人其實費了一番功夫,畢竟事情過去了將近30年,對地方上來說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所以我把困難預估得比較充分。好在我有一些當地的文友,所以一開始是通過他們來聯系。但行政層面是繞不開的,后來我找到縣里以前的一位宣傳部領導,他參與了整個善后過程,在那里待了20多天。我就請他帶我去了。
當時的幸存者和遇難者家屬,有的現在都不在當地了。2017年我第一次開車去,在縣里的各個鄉鎮一共跑了三天,只要有線索,我們就趕過去。我們是通過村委會去采訪的,一開始我沒把意圖說得太明白,只是跟當事人聊天,慢慢說服了他們,被他們接受了。
第二第三次我都是單獨去的。第二次是想去核實一些細節,包括到現場江堤上尋訪當時立的一塊碑。我完稿后給了那家文學期刊,他們不太敢發,另一家文學期刊也想要,最后還是沒發。今年初我剛好看到澎湃的非虛構大賽,就想試試。
所以在2019年初,我第三次去了當地,為修改稿件找了一點感覺,沒有進行采訪,就是走走,感受一下村莊、田野的氣氛。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用什么技巧,讓受訪者盡可能多說一點?
余同友:他們的傷痛在表面上已經看不出來了,但隨著交談的深入,巨大的傷痛其實一直都存在,就像人身上的傷口一樣,看上去愈合了,可一遇到天氣變化就會疼痛。我想,到特定的那個日子,每一戶當年出事的人家肯定都會很傷感,那種陰影想完全去除干凈是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采訪選在一個村民組長的家里,就是文章里失去弟弟的張華柏。因為是中午,說著說著,一些吃飯的左鄰右舍就聚過來了,一旦打開了話匣子,他們就愿意說了。
其實還有好多人有線索,但他們不愿接受采訪,也有些是我不忍心去采訪。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有一個老太太的媳婦和女兒當年在船上,都沒有了,老太太后來過得很辛苦也很貧困。她聽我們大家說話時一直沒開口,就在那里流淚。我想問她的時候,村民組長把我拉出來,讓我不要問她,因為她太苦了。后來就算了。
澎湃新聞:您除了實地尋訪之外,做了哪些案頭工作?
余同友:可供參考的幾乎沒有,我查了一些報紙和檔案,所能查到的資料基本上都在文中呈現出來了。我找了一本當地出的《東至文史》,但也就是短短的幾十個字。還有一份不公開的政府紀要,我是托朋友幫忙找的。
澎湃新聞:您如何彌補歷史信息的殘缺,又如何還原無法親眼看到的情景?
余同友:我找到了逝者的親屬、親歷的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員、當時的縣長,從各個階層建立一條證據鏈,一環一環來互相彌補,力求從整體上還原當時的情境,不能光從片面去調查。
在很多地方,我直接引用了當地人的方言。像他們說“看一看”,不是說“看”,而是“望一望”,還有“把肝都哭出來了”等等,我覺得一般人也能理解,所以就直接引用了原話。我還寫了一位找不到兒子的中年女子,她在除夕夜很痛苦,一直在哭,母親跟她說:你鍋上也哭鍋下也哭,哭壞了怎么搞?“鍋”指的是鄉村里面的鍋灶,上面炒菜,下面燒柴火,我也拿來引用了。
在還原場景方面,我基本沒有想象,大都是根據受訪者的說法,除了個別地方會渲染一下氣氛。比如我寫霧像“炸裂”開來,這是文學化的語言,跟事實也不矛盾。我總體是尊重采訪得來的原始素材的,因為我覺得受訪者說得比我描繪得更好,有些東西是想象不出來的。
將心比心杜絕獵奇寫法
澎湃新聞:災難是很痛苦的,我們為什么要記住它們?對于過往的災難,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態度?
余同友:這是一種使命。1995年日本發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那里的紀念碑上有一段碑文,我覺得可以很好地表達我的想法:“1995年1月17日5時46分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震災奪去了生命、工作、團聚、街景、回憶。人類是多么渺小,我們甚至無法預知一秒鐘之后將要發生的一切。震災留給了我們溫情、關愛、互助、友人,這個燈火,連接著被奪去生命的每一位逝者和我們的追思。”
這么多人的生命半途夭折了,如果沒有一點記錄,我覺得那是對生命的冷漠和不尊重。有一家媒體開設了名叫“逝者”的小欄目,讓普通人寫他們逝去的親戚朋友,我經常會讀,因為它表達了對平凡生命的關切。
當然,我們也不能每天都沉浸在悲痛當中,但有一些經驗和教訓可以汲取。事件中的人可能是無辜的,該記錄的還是要記錄,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澎湃新聞:您在創作手記里面寫道,決定不從獵奇的角度去寫,而是如實地記錄,這兩種寫法的區別在哪里?
余同友:我覺得,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抱有獵奇的態度,哪怕是寫游記,對于相對欠發達或落后的地區,如果作為闖入者去寫,我覺得非常不妥當。寫作首先應該懷著真誠的心態,將心比心——如果別人向我獵奇,我會很難受,所以我作為一個作者,肯定不能抱著獵奇的態度。
在這篇文章里,其實有人給我講了很傳奇的一個細節。船要開的時候,有兩個人打起架來,就離船上岸了,我寫到這里就中止了。但其實有人告訴我說,那兩個人起初在打架,看到船開走了、沉沒了,覺得逃過一劫,就抱頭痛哭,后來結為兄弟。我想,一來找不到當時的人求證,二來這不太可能是真的,因為那時大霧滿天,他倆怎么能看到快到對岸的那艘船沉沒的情況?如果我這樣寫了,肯定會吸引眼球,但我還是放棄了,不能寫,這是一個態度問題。
澎湃新聞:您在采寫過程中,還有沒有什么印象特別深刻的一些細節?
余同友:還有一些細節我沒寫進去,比如陪我第一次去采訪的那位領導說,當時工作隊進駐到村里,睡在一個閑置的倉庫里。倉庫里有很多老鼠,他的腳就被老鼠咬了,當時也不能請假,回去后腳上一直流著黑水,還住院了,黑水流了大概半個月才治好。這些細節跟主題沒關系,或者不夠精煉,所以我都刪掉了。
澎湃新聞:您采寫中最大的難點又是什么?
余同友:難點是很難進一步挖掘。我采訪的幸存者、受難者家屬總數不是很多,如果要寫得更深入一點,還得多找一些人去采訪。但確實有人不愿接受采訪,也有人是我不忍心去問。比如有逝者留下來的后代,現在在大學里讀書,我找到了其中一個的聯系方式,但考慮到是學生,我始終沒敢采訪,怕年輕人受不了。如果我找到更多聯系人、做更多采訪,估計會寫得更好、呈現的面貌會更豐富一點。
非虛構應重視沉淀和陌生化
澎湃新聞:您之前接觸過哪些非虛構作品,有沒有對您影響比較大的?
余同友:像美國彼得·海斯勒寫的《江城》、《尋路中國》、《奇石》,我都看過,他給我們打開了非虛構的思路。后來我也讀了得諾貝爾獎的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些作品,還有卡波特的經典著作《冷血》等等。
國內的紀實文學我認可的主要有幾部,一部是錢鋼寫的《唐山大地震》,還有以前劉心武講足球的《五一九長鏡頭》,時間比較久遠了。媒體方面,像南香紅、李海鵬的作品,我基本都讀過。還有國內這幾年比較新的平臺,澎湃鏡相我是很早就關注了。
但影響我這篇文章寫作的,可能沒有哪一部具體的作品。我當時找到了馬爾克斯《一個海難幸存者的故事》,但沒有讀,怕讀了會對自己有干擾。
澎湃新聞:您自己之前有沒有寫過其他非虛構或紀實作品?
余同友:寫得不多,今年3月我和幾個同事一起出了一本書,40多萬字,標題是《一條大河波浪寬:1949-2019中國治淮全紀實》,講的是淮河治理。我們寫的時候想偏重文學性,也做了一些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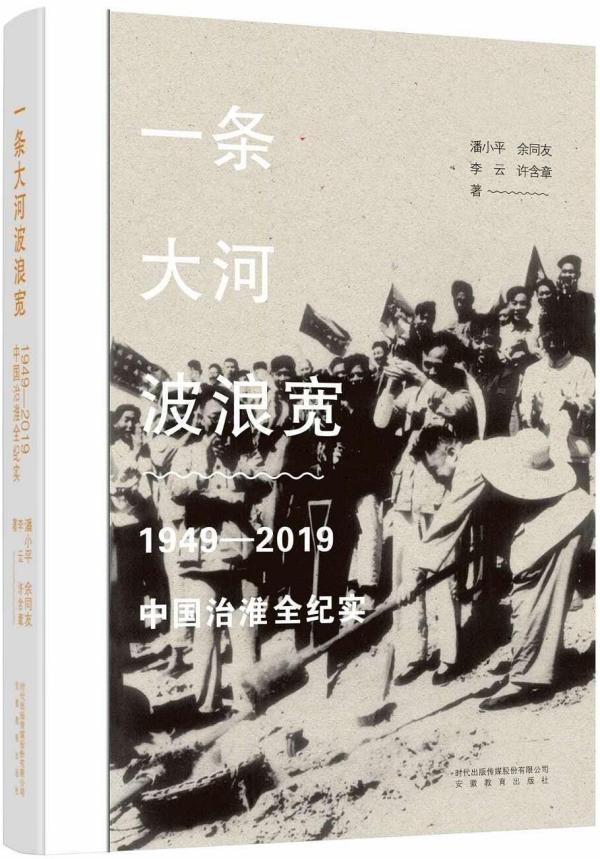
余同友:虛構和非虛構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想抵達社會生活的深處。當然它們也很不同,通俗一點說,虛構就是以假話來推演現實,非虛構是以真實來求證現實。比如寫青蛙的鳴叫,小說可以虛構出一個池塘,青蛙在池塘里鳴叫,但非虛構必須得真有池塘才能這么寫。
我覺得虛構和非虛構彼此會相互促進。舉個例子,去年我在寫淮河治理的書,沿著淮河四個省走了很長時間,有一天來到淮河邊的一座村莊,因為國家治淮,全村都搬走十幾年了,但還有一對老夫婦在堅守。其實國家也給他們安排了房子,他們不愿去住,就兩個人在那里,沒有水電,自己買了太陽能的發電板、打水井生活。
后來,我依據這個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叫《臺上》(因為淮河邊的莊子叫莊臺),發在今年第五期的《安徽文學》,最近被《小說月報》選載了。我幾乎完全是按照人物原型來寫的,如果稍微變一下,就是一篇非虛構。
所以這兩者相輔相成,虛構可以表達出某些非虛構無法表達的東西,而非虛構會讓作家走出象牙塔,迫使他們去采訪,更接地氣。
澎湃新聞:許多文學雜志也刊登長篇散文,這和非虛構有什么區別?
余同友:我的理解是,非虛構和散文有時邊界很模糊,但還是兩個不同的文體。相對散文來說,非虛構可能更注重新聞性,或者說是當下性。比如有些散文寫很久遠的事情,看上去是真實的,但和當下聯系得不太緊密。
非虛構的話題也需要是公共性的,或者呈現出一個開放性的姿態,讓大家都可以參與討論。散文可以只是寫給一個人看的,但非虛構如果只寫給一個人看,恐怕不太合適。
澎湃新聞:文學界和新聞界的非虛構,側重點會不一樣嗎,如何取長補短?
余同友:我覺得確實應該取長補短。文學界這邊的缺陷是,作者缺乏豐沛的生活經驗和去現場的自覺性,容易懸在空中,落不了地。而新聞界的非虛構作品可能新聞性很強,但文學性不夠,或者說是沉淀得不夠。
打個比方,我覺得尤其是我們很多國內平臺推的非虛構,很多只滿足于照相式的寫作,好像到了現場后,“啪啪啪”拍了很多照片就發出來了,沒有沉淀。我覺得,好的非虛構不應該是照相式的寫作,而是整個身心都融入進去。在情感上不要一味獵奇,不是只關注流量和新聞性。
還有一個是表達上的問題。我們很多非虛構作者在表達手法上比較單一,缺乏結構和語言上的追求,從文學上來說沒有達到“陌生化”的效果。唱歌是說話的陌生化,跳舞是走路的陌生化,那就是藝術。我們的非虛構在這方面可能還有所欠缺。在文學性方面,李娟獲得《人民文學》非虛構獎的《羊道》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我有一個觀點不知道是否正確:一篇好的非虛構,現在能看,10年、20年、30年以后還能看,這恐怕就是衡量非虛構優劣的最大的一個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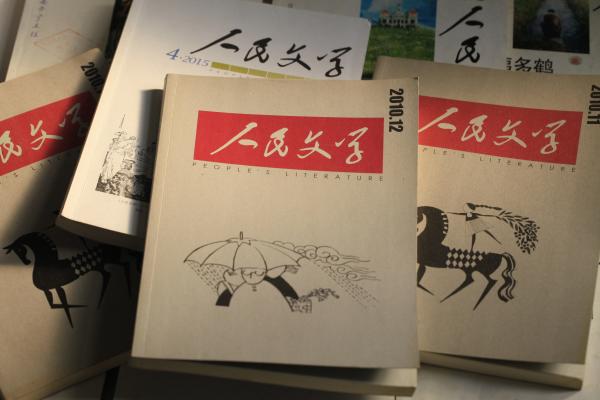
澎湃新聞:對于業余作者,您有什么建議?
余同友:一是肯定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二是要深挖。比方說,我有一個朋友提前退休了,回到山里種了兩畝田,親身種水稻。每天待在那兒,看他是怎么播種、怎么管理農田的?稻秧每天又是怎么生長的?如果一點一點如實記錄得特別到位,是不是就是一篇很好的非虛構?我覺得還是要從自己身邊最有生活的地方、最熟悉的領域去寫。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關注到其他一些參賽作品,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
余同友:有一篇印象很深刻的是講電信詐騙的《電話那頭的克蘇魯》。《小廠之春》也不錯,很有時代氣息。
澎湃新聞:您將來是否會繼續去寫非虛構,有沒有特別想寫的話題?
余同友:估計不會很多,但還是會嘗試寫一些。我已經有一些題材想寫了,但還沒有采訪。其中一個是動物保護,長江江豚據說現在總數已經比大熊貓還少了,種群生存非常艱難,我可能會對這方面有所關注。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