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那些隱藏在身邊的心理變態者,大腦中在發生什么?
我們的理解里只有殺人犯,異己,脫離于社會之外的人才算精神變態。但畢生都致力于這方面研究的犯罪心理學博士羅伯托·黑爾認為,要看出誰是精神變態者,你無需眾里尋他千百度,這種人可以遠在天邊,也可以近在眼前,他可以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也或者是你的伴侶。
在和他人的社會交往中,有幾樁事情是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我們自以為彼此看世界的方式大體相同,某些基本的事實大家都明白,說的話,你理解的意思和我理解的意思是一樣的。我們還一廂情愿的認為大家的是非觀都差不多。

羅伯托黑爾教授是位犯罪心理學家,PCL-R(病態人格檢測表)——心理上判定一個人是否是心理變態者---就是由他發明的。多少年來,他一直在監獄以內和以外的地方研究有變態行為的人,和他們一起來面對這個問題。“我們身邊完全可能有這種人,他們的情感相當的不連貫,在他們眼里,其它人就只是個可以毫無顧忌的操縱和摧毀的物品,六十年前我開始研究時就感到吃驚,現在還是這樣。”黑爾博士說。

說到底,黑爾的測試也很簡單:一張表上列有20項標準,每一項分三個等級打分,(測試者覺得自己根本不是這樣)打0分,(測試者覺得有部分符合的)打1,(測試者覺得完全符合)打2。
整張表格看下來是:巧舌如簧和表面很富魅力,自我價值感極端膨脹,撒謊成性,很狡猾/有控制欲,沒有愧疚感,情感很少,冷酷無情缺少同情心,不愿意為行為負責,總覺得很無聊,過著寄生蟲一樣的生活,缺乏現實性的長遠目標,沖動,不負責任,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很早就顯示出行為上的問題,少年犯罪,犯罪本事多樣,有假釋期犯事,假釋被取消的歷史,結過多次婚,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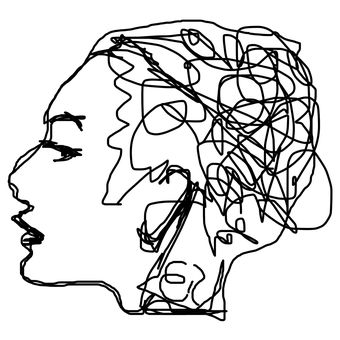
然而心理變態是一種障礙呢還是一種不同的存在方式方法呢?你只要讀過上面這個列表,都會發現自己知道的人就有幾項相符呢。平均來說,沒有過刑事犯罪記錄的人可以打到5分。“這也是要分情況的,”黑爾說,“有些人,在這個等級比度上有一部分的分打得高,高到你可以把他或她列為心理變態,但又沒有高到足以引起問題的程度。
很多時候他就是我們的朋友,有他們在身邊很有意思,他們可能會時不時地利用我們一下,但通常的情況下,不太為人所察覺,而且他們也能替自己開脫。”就象我們把自閉癥當作是光譜一樣——被診斷成心理變態的人,也會悄無聲息地墨跡于正常的人群里。
我們的理解中殺手,罪犯,脫離社會的人才是心理變態者,例如31歲的英國女人喬安娜·丹尼希2013年就殺了3個男人,之前一年,她被診斷出有變態性人格障礙。還有美國的連環殺手,殺了至少是30個人的泰德·邦迪,他就這么說自己“我就是你看到過的那個最冷血的王八蛋,我就是喜歡殺人。”

黑爾說這樣的隨機抽查并不合理(“10%的財務總監都心理變態”這肯定是胡說。)但我們也容易看出,要是想在商界混得出人頭地,沒有道德上的顧忌,不顧惜別人的的死活,肯定是對事業大有幫助的。
“同情心有兩種”,加洲大學神經學家,《精神病的內心世界:跟神經學家親歷大腦的黑暗面》一書的作者詹姆士·法隆說,“一是認知上的同情,就是你有知道別人現在在想什么的能力,再一個是情感上的共情,就是一種悲其悲,樂其樂。”
自閉癥的人可以是很個同情心的——他們能感知到別人的痛苦---但對象笑容呀,皺眉呀這樣告訴我們對方在想什么的,一般人輕易就讀懂的線索,他們則不大能識別。心理變態者則是反的: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但他們自己沒這份感情。
“這就給某些個心理變態者很大的優勢,因為他們知道你的想法,可他們不在乎,所以他們能利用你的這個感情反過來對付你。”(心理變態的人特別擅長于看到人的弱處。2008年的一項調查就讓參加者來記住些虛擬人物,結果那些心理變態測試上得分很高的人能很準的識別出不開心,不成功的女性來,但對其它特征倒是記不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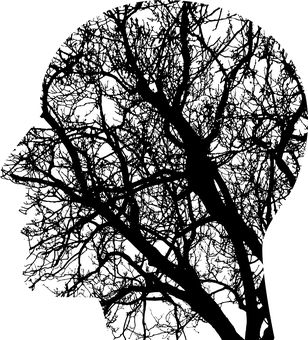
他描述了一個很大的從人的腦前部開始的圓環型物質,其中包括與人的情感,沖動控制,和同情心這些情感相聯的海馬旁回、杏仁體和其它其它區域。在特定的情況下,正常人的核磁共振成像上,這些地方會亮些,但到心理變態者這里,這塊區域就暗些了。
“我看到一個極端不正常的圖像,當時想這人肯定和正常人有很大偏差。看起來就象我一直在研究的殺人犯似的”。法隆說。他怕萬一這個圖像是放錯了群組里,就解開了匿名密碼。密碼一解開,發現那是他自己的腦掃描圖。“我簡直是魂都嚇倒了”,法隆說,“后來呢我一些心理學家朋友研究了我的行為,他們說我事實上可能是一種邊緣型的精神變態者。”
和法隆講話,你會覺得很怪;一個小時他幾乎說話不帶停下來喘氣的,而我在這一小時里也就問了他三個問題。他講給我聽他是如何經常性的讓自己的家人置身危險當中,讓自己的弟弟接觸致命的馬爾堡病毒,明曉得非洲的郊外有獅子出沒還帶自己的兒子去釣鱒魚。
年青的時候,“面對權威機構——比如說因為偷了車,自制了炸彈,去放了火——被警察給抓住了,我是臉不改色,心不跳的,有什么可緊張的。”可是此人是個相當成功的人士,一路發奮圖強做得人上人。他告訴我的事,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難以啟齒:妻子說自己嫁的人一面是有趣,有愛,隨遇而安的好人,一面是自己不喜歡的,有很陰暗人性的人。
他很可親,有趣,除了有點以自我為中心。可我還是不由自主的想到黑爾的那個PCL-R:長得好皮囊,缺乏情感的深度,極度膨脹的自我價值感。“湯姆,你看我現在不象個什么,”他說——現年他66歲了——“可是長大那會兒,我可是帥著呢,有6英尺高,180磅,體格健壯,人聰明,有趣,很招人喜歡的。”(順便要說的一點是,黑爾博士警告那些非專業人士不要用他的測試方法來給人妄下評論。)
“心理變態者的確是認為自己要比別人理性,而且不認為這是個缺點,”黑爾說,“我遇見過一個罪犯,是個實打實的心理變態者,他就說“我的問題吧,心理醫生就說我是用腦多,用心少。”你說我該怎么做?兩眼深情淚?”另一個,當問及說你為什么搶人東西,還把人給捅了,他回答說“唉喲,你現實點吧,你就在醫院呆了幾個月,我這兒到是要死爛在監牢里呢。我要真殺他,一下子就割他喉嚨。這才是我;我這還是手下留情了呢。”
然而,正如黑爾指出的,在我們來談論不是罪犯,可能人生還挺成功的人時,就不容易把這樣的行徑算做是失常了。“你說我走到政界,經濟界,或是學術界的高層,把那些做得最成功的人找出來,說“你看看,我覺得你吧腦子有問題”,這太難了。”我有個病人就說自己的問題是,他呢是只貓,這周圍的世界滿是老鼠。要是你來比比貓和耗子的腦電波活動,你就會發現它們相當的不同。
這種看世界的方式,黑爾說,從進化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很多先人會視做很成功,而且如今這方法也很有效;由于善于操控人,一個心理變態者“能象一個教會或是文化組織似的被一個群體接納,說“你想的,就是我想的”,當然這人事實是只假裝是耗子的貓,接著一下子所有的錢都沒了。

所以心理變態者對自己的狀況往往是接納的,“醫治他們”就變得很復雜。“你說有多少心理變態者會到心理醫生那兒來治自己的心理問題,還不是等到坐牢了?不坐牢,他們不會到看心理醫生這一步。”黑爾說,到個監獄的呢,往往是強迫去參加談話治療,共情培訓,或是和受害人家屬去談話——但因為心理變態者是沒有共情之心的,所以這種方法不行。“你要做的就是對他說,“看,改變是為你自己好,否則你要在監牢里坐上一陣子的。”
黑爾博士的這個用意英國的司法部似乎是已經明白了:人格障礙型犯人指導法則中,司法部就說明“由于心理變態程度很高的人可能對治療有相當的抵觸性,所以要想心理干預發揮最大作用的話,要把重點放要其自身利益上---犯罪者想從生活里得到什么---和他們一起培養起對社會有利而不是有害的,能實現自身目標的技能。”
如果有人的腦子里就沒有我們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道德感,很明顯他們也不會在這些方面做出任何改進,所做的不會多于一個色盲的人開始看顏色,看來看去都一樣。那么從哪里開始沒有了道德責任的概念了呢?“一直以來,我們的司法體系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證明這話是錯的。”
神經學科學家,《躲在我們大腦里的陌生人》一書的作者戴維·伊格曼說。他建議說:“法律要考慮的不是犯罪行為值不值得得譴責,它要應對的是再犯的概率是多少,相應地該判多長刑期。能從改造好的就去改造,可能成為長期危險人物的刑就要判長點。哪類罪犯還會有再犯的危險,對這種罪犯的用的十進制計算法中,已經包括進了黑爾博士的PCL-R標準。“人生保險公司做的就是這種事,到保險精算表,他們會問“你估摸著還能活幾年?沒有哪個人會假裝說自己知道什么時候會死。但他們可以這么估估,這就帶來了一個極為高效的保險制度。”
伊格曼說,這里面所說的并不象科幻電影《少數派報告》里的一個情節:可能會犯罪的人在實施之前都被關起來了。“原因說給你聽,”他說,“就是人群中很多人心理很變態—比例約為1%,但他們不會都會成罪犯。事實上這些人中很多憑借自己的巧舌如簧,個人魅力,有能操縱別人的本事,他們很成功。他們成了CEO,職業運動員,士兵。別人敬重他們,說他有勇氣,敢直言,有征服前進路上的障礙的意志力。只是心理有變態,并不等于說這個人會發作,會犯罪。”
在英美法系里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你不能假設對方會犯罪,而來懲罰他。而且,伊格曼說,這種狀況將來無論是出于哲學,道德的原因,還是出于實際的考慮都不會改變。《少數派報道》里的這個情節只是個臆想。“即使你知道這個人的人格類型他的方方面面,你也無法預料他下面會做什么事。因為生活太復雜,犯罪又是概念性的東西。只有到人犯了罪,到這個人越過了社會的界限,這才有更多的統計功效來告訴我們,這些人接下來還會做什么。可是在這之前,你什么也不知道。”

“你知道孩子會用放大鏡來燒螞蟻,他們覺得好玩。“黑爾說,“你把這個移植到一個成年的心理變態人身上去,想想他這么對人。你會覺得毛骨悚然的。”談到一個階段時,羅森建議我去和另一個出名的,自稱是心理變態的女性去談談,我沒有。這建議太讓人心悸,就象他讓我去和個死人說話似的。
原文標題:psychopaths: how can you spot one?
原文鏈接:https://www.telegraph.co.uk/books/non-fiction/spot-psychopath/
原文作者:Tom Chivers
譯者:sinno123
譯文來源:譯言網(yeeyan.org)
基于創作共同協議(BY-NC)在譯言整合發布
本譯文僅用于學習和交流目的。圖片源自網絡,版權歸作者所有,非商業轉載請注明譯者、出處,并保留文章在譯言的完整鏈接。商業合作請聯系editor@yeeyan.com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