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徐秀麗:從劉燕瑾、王林夫婦情感經歷看八路軍婚戀紀律與自由
1945年8月,王林正在晉察冀邊區總部所在地阜平上黨校,對整風、學習情緒倦怠。組長批評他們生產情緒高于學習情緒,王林則贊成“不是生產情緒高了,而是學習情緒不夠高”的說法。好在本來為期一年的學習因抗戰勝利突然中斷。他們是在8月11日晚間獲知日本投降消息的,整個邊府立即沸騰了,人們笑鬧狂喊,點起漆黑夜晚最能代表狂歡心情的火把,有人從校部搬出一大捆燒火用的蘆子,惹得工友追出。人們說都勝利了,還在乎這個,整個點著在場中跑圈,后又拆開鬧。校部宣布馬上進行甄別與鑒定,一周內結束。王林則擔心“這一周我看也要趕不上時代了”。
在這樣飛揚的心情中,已經36歲的王林又一次痛感非馬上解決“老婆問題”不可。他既幻想不久的將來“到北京演真的李自成”時尋找往日戀人或者另覓良緣,又處處留意身邊的鄉村少女,還再次動了追求火線劇社名演員劉燕瑾的念頭。他一向欣賞劉的藝術才華而不喜歡其外表,但這年9月的相見,卻驚訝地發現劉“特別漂亮”。不過劉并未接受他的追求。
王林雖是火線劇社的首任社長,是該社許多上演劇目的劇本創作者,他卻不知道,劉燕瑾正在焦急地等待她的戀人凌風(即后來的名導演凌子風)歸來。即使他自己,恐怕也并沒有準備好一場認真的戀愛。

一
劉燕瑾1923年出生于北京,1938年到冀中參加火線劇社。1941年,根據地掀起排演中外經典戲劇的熱潮,火線劇社準備上演曹禺的《日出》。但火線劇社平日所演多是反映時事宣傳抗日的小戲,對排演《日出》這類“大戲”沒有經驗,所幸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西戰團)此時正在晉察冀根據地活動,劇社便請來“剛從上海出來見過大世面”的凌風當導演。18歲的劉燕瑾出演“顧八奶奶”,無疑給凌風留下美好印象——凌晚年仍說劉是冀中“最漂亮的女演員”。
據王林、劉燕瑾的長子王端陽推測,劉凌二人最晚重逢于1943年1月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召開期間的阜平。3月,凌向劉表達了愛情;不久,劉也墜入愛河。1944年3月8日,因“西戰團”即將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也就是回延安,凌風突然表示要帶劉燕瑾一起走。稍作猶豫之后,劉答應了他。這天晚上,她“興奮得全睡不著。月亮把屋里照得非常亮,我看著窗格的花影慢慢的斜過去,斜過去”。但她知道,她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她是一個黨員,必須絕對服從組織。
劉燕瑾性格活潑,演技精湛,是一個帶有明星光芒的女演員,追求者眾多。但實際上,凌風是她真正的初戀,是“第一個自發的主動的自然的戀愛”。她忐忑不安,言行舉止緊張而鹵莽。凌風表白后的第二天:
滿懷著極大的不安,忐忑的走到了家中,我的臉一進村就燒得通紅了,像有一件什么事情將要臨頭,我也不知我是興奮還是恐懼。但是到了家各處全是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大家全背糧去了,我只有等待著,等著他們回來。
黃昏了,人們也全零星的走了回來,但是卻沒有人找我談,指導員,社長,全像往常一樣,只有我這心里頭像有一條花毛蟲在爬,在爬。小鬼從門外急促的進來了,我馬上從炕上跳到地下,心撲撲的跳個不停,原來他是找的別人,我只好又暫時的安靜下去。
天快黑了,我實在再也等待不住,一股勁的跑到了社部。當我一進院子,我立著了,我到底干什么來呢?我怎樣講呢?這些事先我全沒有想到,現在當然也沒機會來準備了。鼓了鼓氣大膽的喊出了一聲指導員。他出來了,和往常一樣,我不能抑制自己了,我說出了我的話。他沒有回答,因為他不知道有這一回事。沒法,我只好又回去。
當天晚上凌風的到來使情況更為惡化。既沒有經過組織手續,劇社也沒有接到通知,他卻貿然提出了帶走劉燕瑾的要求。事情自然辦不成。凌非常堅決,說一定要經過組織把劉調走。但劉燕瑾沒有那么樂觀。“西戰團”與火線劇社性質不同,又不屬于一個組織系統,再說,劇社人員本來就調動不易,她又是臺柱子。
劉燕瑾在忐忑不安中等待著進一步的消息。3月10日,劇社開始整風,她心不在焉。她參加學習,但她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別人的發言一句也聽不見。學習文件,很好,很合適,正好可以掩飾她的不安情緒。她的眼睛順著行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心卻飛到了“西戰團”,“陪伴著他們行軍,陪伴著他們談笑,陪伴著垂頭喪氣精神痛苦的凌風”。她下地勞動,低頭干活不休息。手掌磨起了泡,泡又磨破了,也不感覺得奇怪,更不感覺到痛。她像一個呆子似的跟著別人亂跑,沒有思維,也沒有靈感,劇社熱烈的整風、學習、生產,對她沒有絲毫刺激。她的一顆心都在凌風身上。
在深深的焦慮中,她炸著膽子又找了指導員。他很不滿意,嚴厲批評了她,最后指導員說他也沒有辦法,只有等待組織上的決定。
不用等多久,13日,組織上就告訴她“不能走”。組織的理由有兩條,第一,劉是黨員,凌是群眾;第二,火線劇社屬于軍隊,“西戰團”是群眾團體。劉知道這是她無法抗拒的,她深深感嘆:“組織紀律呀,打破了那迷人的噩夢!”
深陷于熱戀中劉燕瑾無法自拔,感覺“天是黑的,地是黑的,交流的空氣也是黑的”。她總覺得凌風會給她留下一封信,哪怕是幾個字,寫明了他的去處,可以使她安了心,從而作長期的等待。她并未等到這封信,但她還是決定等。“雖然我也知道這是一種可能很小的希望,我也曾受遍人們的諷刺、謾罵,可是我的心卻無時不飛向那有他住著的遙遠的地方,任何人的力量全拉不回了我的心,任何人的愛都使我難于接受。”
“西戰團”于4月初離開晉察冀邊區返回延安,劉燕瑾一直留意著這個團體的信息。6月1日,她終于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又哭又笑,向大家報告:“西戰團到延安了,在中央大禮堂演出《把眼光放遠一點》”!《把眼光放遠一點》正是冀中的劇啊,劉燕瑾飾演“二老婆”,很是入戲。
9月份,劉燕瑾的戰友中有多人(包括火線劇社的兩人)調往延安,她按捺不住,向組織提出了要求,并給凌風寫了信。結果又一次陷于絕望的孤獨里,感嘆“月圓人不團圓”。
12月,她在整風運動中“總結清算了我從歷史發展以來的一切男女關系,從思想上從具體事實上來找出它的根源、危害及結果”。她說她在幾次戀愛中都違反了政治原則,因為對象全是非黨員;她說她有高度的強烈的“自信心”,黨不可教育的人,自信可以培養,黨了解的落后分子,自信可以由自己的手來改造成為進步的;她甚至不可思議地把自己貶低為與敵人的“桃色間諜”類似的角色,認為“因為自己的一種輕浮的風騷的調情的作風、風度,擾亂了周圍的男人,激動了他們情緒的不安與混亂”。
但即使這樣“觸及靈魂”的批判與懺悔,仍不能使她忘記凌風。1945年3月8日如期而至,看到“紀念三八大會”幾個字,她感到“血液忽的一家伙沖到了腦頂”。她想起三百六十五天以前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刮著大風沙的白日,尤其是起了上弦月的半陰的夜晚,她感覺“這悠長的歲月是用痛苦和悲哀充實起來的,這悠長的歲月是用眼淚所洗過的日子”。她強抑住心中的銳痛,全身心投入新劇的排練中。她剛獲得根據地紅色文藝代表作品之一《王秀鸞》的主角,體驗生活,賣力勞動,外觀已成為強壯能干的農婦,熟人直接叫她“王秀鸞”。她想讓這樣的強行壓抑習慣成自然,好讓心中的痛不那么尖銳。但周圍的人們已經聽不到過去無處不在的“大劉的笑”了。她則說自己“嚴肅了,對于過去一切的小資產階級羅曼蒂克的幻想,一切不合實際的念頭都應該置之高閣”。
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下,王林覺得“還是追一下大劉為上策”。中間人傳來劉燕瑾的回話,說對王林別的沒有挑,就是嫌體力體格不是她所理想的,惟恐將來的夫婦生活不濟。與此相關的即年齡問題。王林大她14歲,年齡和體能的差異是無可改變的事實,她如此回答,自然是不留余地。她關注著延安文藝工作者的動向。有人說延安的文藝工作隊已經出發,不久將到華北各解放區,并說凌風也會到冀中來。劉燕瑾在殷殷期盼的同時,又懷著強烈的不安:如果他真的回來了,可是卻帶來了另外一個她,她該怎么辦?
10月,劉燕瑾在固安的街上看見許多從遙遠地方來的旅客,穿著破舊,精神疲倦。她在大街上不斷問來人,從拼湊起來的隱隱約約的零星信息中確認他們是從延安和其他根據地來的,目標是東北。她希望不久會有那么一天,在相似的一群旅人中能看見她的朋友的歸來。她從10月等到11月,“等待一個最大幸福的來臨”。
11月10日,她終于等來了凌風的消息。這個消息卻讓她萬箭穿心。
凌風在延安已經結婚!劉燕瑾竭力壓抑住自己的情緒,當眼淚涌上眼圈的時候,一個轉身又把它逼回去,嘴上說道“結就結吧!誰能管著誰呢?再說相隔這樣遠,我們又沒海誓山盟過……”。她跟著劇社在霸縣上汽車,又到新鎮上船,一路沉默,直到在船艙里躺下,用大衣蒙住全身,才哭了出來。
1946年3月8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劉燕瑾又一次記下了這場戀情帶給自己的“悲哀與不幸”。
給她最后的打擊來自凌風夫妻的一張合照。照片中的兩個人甜蜜地微笑著,劉燕瑾深受刺激,“感覺他們在向我示威,在向我炫耀,是一個勝利者對于他的頹敗的對手的驕傲的微笑啊,是一個對于戰敗者的鄙視而諷刺的微笑啊……”
她可能聽說過,凌風的婚姻是“組織”安排,她沒想到照片中的兩人竟如此親密。
受到“甜蜜暴擊”的這一天,是1946年8月10日,兩個月前,劉燕瑾已經與王林確定戀愛關系。8月24日,王劉二人成婚。
劉燕瑾與凌風的愛情不能圓滿,確實有“組織”的原因,如果“組織”同意兩人共赴延安,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局。但是,“組織”并不是導致他們關系變質的主因。如果曾經愛得癡狂的凌風如劉燕瑾一樣選擇等待,只需一年多,他們便可重逢。當然他們并不能預知需要等待多久,但無論如何,他等待的時間過于短暫了。時間和距離,從來都是深情的敵人,只不過戰爭年代的人們行事更加倉促而已。從根本上說,劉凌這段感情,不是敗于“組織”,而是敗于亙古而然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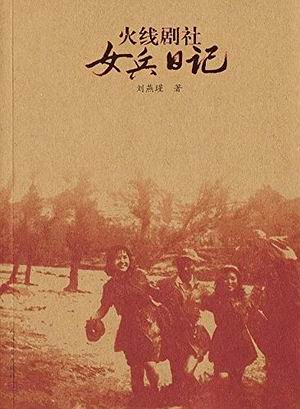
總有一些人,他們的婚戀過程特別曲折。不是因為他們輕忽這件事,恰恰相反,他們把婚戀看得太重、在人生中的意義太大,所以患得患失,難以成就;不是因為他們周圍缺乏適當的對象,而是因為他們一直不能確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對女性的欣賞趣味幼稚而固執,情商也往往低到難以正確判斷對方的感受和想法。這樣的人,現實生活中被稱為“直男”。王林正是一個典型的“直男”。
“二八五團”(各根據地有大致類似的婚姻條件規定,28歲、5年黨齡、團級干部即“二八五團”較有代表性)的組織紀律完全無法約束王林。他出生于1909年,革命資歷深厚:1931年入黨,曾擔任青島大學黨支部書記——抗戰時期冀中區重要領導之一黃敬就是他在此時介紹入黨的;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到東北軍學兵隊做地下工作,親身經歷了西安事變;1938年在冀中參加抗日戰爭,曾任冀中文建會副主任、火線劇社第一任社長、冀中文協主任等職,是冀中文化界的重要領導。
王林在文學創作上有相當高的成就:20世紀30年代初參加左翼文藝活動,出版小說《幽僻的村莊》受到沈從文賞識;抗日戰爭時期,他寫下了大量小說和戲劇作品,其中長篇小說《腹地》是他在日寇掃蕩的嚴酷環境下寫下的壯美詩史;他還主持了多項重大文化活動——如影響很大的“冀中一日”征文。他與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黨委書記黃敬、政治委員程子華、政治部主任孫志遠等均交情甚篤。呂正操說他們幾人相聚,總是談笑風生,別有情致。呂還說他為人開朗,富有風趣,能接近群眾,婦孺多識其名;王林長年累月走鄉串戶,熟悉地方風土,所知掌故最多,有冀中活字典、活地圖之稱。這樣的經歷、這樣的個性、這樣的工作環境和性質,都為他尋找理想伴侶提供了便利,但是,雖然其情史豐富而坎坷,其實在劉燕瑾之前,王林似乎還沒有經歷過一段真正投入而穩定的感情。
王林所夢想的女子,是“驕傲而美麗”。他不怕女人驕傲,只怕她們的驕傲僅只是外表的,一時的。至于“美麗”,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完美主義者,對任何一點“不完美”——如嘴稍大,單眼皮之類都會介意。他最愛黃眼珠的姑娘——感覺好像有法蘭西少女的詩和幻想!他最討厭胖——胖子給他的印象永遠不佳!
王林的情感經歷頗為曲折。戰前,他在北平有女友“仲英”,戰爭期間始終未通消息,他在日記中提及這位女友是在抗戰勝利之后有可能再回北京的情形之下,可見他們并不具有牢固的感情基礎;抗戰初期追慕過較長時間的對象UL(王林日記中的代號,有些可以還原真名,但似乎沒有必要還原),是一二0師戰斗劇社的演員,并不在身邊。1940年6月UL與王絕交,他隨即轉向H(可能即是“黃眼珠”的HS),覺得“她確實動人,她確實刺激了我這寂寞苦悶的心!”還說這是他唯一的春天,過了這春天,難見另一春天!但這段感情同樣未得善終。1942年,因對LE失望,轉而追求P(兩人早有通信)。1943年初,經過兩年多時斷時續的通信交往,終于與P相見。傳說中P極美,見面后卻覺失望,以為不夠美,但另一方面也認可P的美。不過P拒絕了王林的追求。抗戰勝利,王林“光棍子心情亂飛”,更加亂了方寸。他一方面想象與“仲英”重逢的可能,或者“堅持一下”到大城市討老婆,另一方面對身邊的農村少女動情,先追求小嫣(或寫成小然),再追求小馨(或寫成小欣),仍然碰壁。
上述諸人中,只有LE對王林頗為主動,他們的關系也得到王林朋友孫犁等的認可。其他諸人大致屬于王林一廂情愿。身材苗條、唇紅齒白、神情高傲常常是低齡少女的特征,尤其是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下,具有這些特質的女孩更為低齡化。如追求過幾年的UL,王林說“她太幼,但身段與鼻子,真是我幻想中的人物”。后期的兩位農村少女都只有17歲。這種與實際頗為脫節的擇偶觀,害得他長期無法結束令其萬分煎熬的單身生活。他的朋友對他“找對象”這件事有個評論,說他好像到電影院看電影,起初找個座,覺得不好。又找一個,還不好。后來才覺得以前找到的好,回去,可是已經被別人占了。最后只好坐個加凳。加凳不好,后來連加凳也沒有了,只好立在太平門處看。這確是知人之言。王林認為這個比喻對他而言是深刻的,同時也是最辛酸的。
其實,如果僅僅追求外表,也不至于如此為難。他周圍有些“速成”婚姻的例子。他的朋友史立德就“乘機觀變,因勢利導”,婚姻速戰速決。某女士對史有好感,但又猶豫不決。史要她表白態度,她說:“讓我們的關系自然發展下去不好嗎?”史要她說痛快話,愛不愛他?她說:“事實的表現不很清楚的嗎?”史要訂婚,“何必這么急呢?”“我是這樣急,急得等不得了!”“等我考慮考慮。”“考慮多久?”“三個月!”“不行!”“三天?”“不行!立刻答復!”“那么依著你!”“啊!這可是從你自己嘴里說出來的!”有位婦女干部舊歷年剛結了婚,年后王林問她何政委是什么地方人,她說是陜西的,山西的?鬧不甚清。王問其夫念“我”字是什么音,她苦笑著說:誰知道呢,我對他也沒有什么印象!但王林是一個在根據地少見的具有純粹文藝氣質的人,外表只是他追求的表層,他的深層次追求,是藝術上的才華和共鳴。
從王林日記可見,他隨時隨地記錄山川風景,故事人物,著意積累創作素材。作為有“冀中莫里哀”之稱的戲劇家,他對周圍人物尤其體察細致。他的日記中有從水塘中竄出追著他們要通行證的光屁股“中國新主人翁”,有魅力型群眾領袖韓老祥、“大眼侯”等,有識字測驗得第一但亂用新名詞的老太婆,有筋肉緊張地努力學文化的老馬伕……他對環境有著詩意的感受和描寫能力。1940年5月4日五四紀念大會時,他和朋友躺在井臺上的海棠樹蔭中,時而張林出來,他拉著提琴,聲調纏綿。王林說“晉東南最叫我永要回憶的是海棠花和提琴”。說時一陣風過來,樹上的白蕊紛紛而下。他具有藝術家的欣賞情趣,戰爭倥傯之間,仍然喜歡讀經典名作,喜歡讀充滿美感的沈從文、朱光潛等人的作品。他說,“接受遺產,讀古典作品,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愉快的。莫里哀時代距離這昝那么遠,地域國度又大不相同,然而仍能叫讀者感到栩栩如生。古典作品真乃人類性靈永恒不滅之光也。”他在戰斗環境中讀《大公報》上的文藝舊文,如沈從文的《湘行散記》,感覺別有情趣。沈從文是他在青島大學讀書時的老師,《湘行散記》寫于1934年,文筆自然淳樸,流麗迷人,呈現的“湘西世界”憂傷而美麗,是有名的美文。他還自承受梁實秋的影響很不小,“由梁而朱光潛,于是資產階級一套唯心論的藝術論,接受得真不少——當然其中未必都是反動的一部分,好的遺產也有。然而藝術與政治,非政治觀點,人性觀點,藝術自由觀點卻是直接從他們(那)兒學來的”。雖用的是批判的語調,欣賞和接受都是真實的。
更為重要的是,王林是一位具有獨立思考意識和能力的真正的藝術家,具有環境和時代無法徹底化除的獨立見解。1939年9月1日,他與梁斌談起小說和劇本創作問題。他說:凡是主題和思想先行的作品,都必然走上宿命論的結局,因為故事有預定的框架,人物只能成為抽象思想的符號。“這雖然也可能是寫實的,然而是宿命論的唯物論。”相反,如果以人物性格為主體展開故事,則可展示人的能動性,這樣的創作符合“辯證唯物論”。總之,成功的小說和戲劇是人物性格決定故事的發展,而不是故事決定人物。這是對文學本質相當深刻的理解。他專注創作,不愿做其他工作;他設想即使在勝利之后,也選擇像肖洛霍夫那樣隱居鄉間寫作,而不是擔任什么領導職務。他在敵寇的殘酷掃蕩中堅持不離冀中,以近距離觀察和感受戰爭,記錄下中華民族的偉大抗爭。他在地道口和“堡壘戶”土坑上寫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長篇小說《腹地》。根據地的文藝創作崇尚宣傳動員功能,多短平快作品,寫長篇不但不被倡導,且受批評和質疑。1940年,王林在太行山上寫下長篇小說《平原上》,即受到批評。批評者說“寫長篇不能配合政治現實,等你寫完了,時代也早過去了。并且在寫時,也妨礙了最迫切的應時文章”。認為長篇可以等勝利之后作為戰后回憶從容寫作。但王林不這么想。他從不懷疑中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將屬于中華民族,卻不敢幻想自己能在戰火中幸存,所以“不能不早些把時代的光和音收在文字上!”
在對婚戀對象的選擇上,王林固然屬于“外貌協會”,但經過外貌這道門檻的攔截之后,立即便是對藝術氣質和藝術潛質的考量。抗戰勝利后他曾傾心過的兩位鄉村姑娘小嫣(小然)和小馨(小欣)——連名字都被他詩化了,他顯然是“聽音取字”,所以會有不同寫法,而這兩位姑娘更可能叫“小燕”和“小杏”——令他心動,但對小嫣,他在認識當天即趕去她的村莊,“再研究一下她在藝術上有何發展前途,是否藝術的低能兒?看她的身段、表情、體態、眉眼,至少能在話劇上發展。是否能在音樂上更有特長,今天即可研究出來。總之,她的聲音也是圓潤透明柔和的”;小馨是小學教師,這令王林滿意,他迫不及待地讓她讀小說,學英語,練寫作,并說她在藝術上一定會有成就。可見,長相美麗是他擇偶的第一個條件,但并不意味著是最重要的條件。
王林“打光棍三十多年,永遠夢想著像小說中似的有一個傳奇般的戀愛”。但他的兩條擇偶標準,在彼時彼地,即使滿意一條也難。他的長期單身,簡直是“咎由自取”。王林對私生活嚴格自律,鄙棄“杯水主義”,這個表面上“頂快活”的中年人,內心卻騷動得厲害,有時難以自制。1944年最后一夜,有老婆的團圓去了,王林“對明月發誓:出校后第一要搞老婆,打光棍太無價值”;“在這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打光棍簡直是可恥!簡直是懦夫!簡直是無用之輩,可恥!”
劉燕瑾和王林,這兩個似乎不會選擇對方的人,卻在各自與別人來來回回擦肩又錯過之后認定對方,并很快結為夫婦。
三
王林是火線劇社的社長,劉燕瑾是該社主要演員,他們當然很早便相識共事。但他們一直沒有走進對方的心里。于劉燕瑾,這個活潑的女孩身邊圍繞著追求者,1944年后又因與凌風的戀情而遍體鱗傷,年長的領導王林不會是她的理想良人。于王林,他非常欣賞劉燕瑾的藝術才華,曾幾度動過追求劉燕瑾的念頭,但劉體態的“胖”(他在日記中有時稱她為“胖劉”)卻是他最為討厭的女性外表特征,所以一直未下定決心。
劉燕瑾人稱“大劉”,劇社同事編派的歌謠中描寫她“大劉胖,頭發薄”。她有個外號叫“二胖”,因為她有“兩個凸出的松馳的甚至下垂的乳房”。劉本人雖為此而悲哀和悲觀過,一度認為這是她生平中最大的遺憾。但當她提高覺悟后,認為從小資產階級觀點看來,這固然是一個不可彌補的缺陷,但是如果站在勞動階級的觀點看來,那么會更實際,因此便不以為意。在扮演王秀鸞期間,因賣力參加體力勞動,她比以前更粗壯了,體重比上年增加十斤,老百姓夸她“身大力不虧”。
劉燕瑾的“胖”是王林特別討厭的,但她的藝術才華又對他構成無法忽略的吸引,因此,從王林一面說,難免陷于“天人交戰”。
1944年5月22日,王林日記中說“劉燕瑾在《兩方便》中的動作,飾老婆,動作極有節奏”。他應該動了追求的念頭——其實此時劉燕瑾正陷于對凌風的刻骨相思中——但一方面害怕她將來更要胖,認為不如到新民主主義農村中找新民主主義少女更有趣,天真、單純和樸實,另一方面又認為劉燕瑾這個天才也是很稀少的,失此機會,或將成終身遺恨。9月14日又看劉燕瑾演戲,說“劉燕瑾表演術真是好,風趣橫生,我就是怕‘戰勝’不了”。演出前,他溜到后臺在熟人叢中與劉燕瑾亂談了幾句。16日夜晚,經過熟思,王林準備“對她下決心了”,說她忠厚而富于熱情,“過去老討厭她的胖是沒有道理的”。他打算給她寫信,要她幫忙抄個《前線》中的插曲,借以拉攏關系。
但從后來的日記可知,王林并未真正“下決心”,更沒有行動。
1945年9月,在抗戰勝利的喜悅中,王林與火線劇社諸人重逢。這一次,他感覺“大劉顯得特別漂亮”,很后悔上一年有機會接近而自己則冷冷如也。王林雖又一次說不清自己到底是希望一個能上臺的好演員,還是一個貌美性柔能給他抄抄文章的姑娘,但最終,“才華”壓倒“美貌”,他決定“還是追一下大劉為上策”。不料遭到了拒絕。
王劉二人,彼此都不是對方的首選,都帶有“退而求其次”的無可奈何。對劉燕瑾而言,凌風沒有選擇她,她只好另外選擇,老干部王林是文藝內行,為人正派,性格幽默,是個不錯的婚姻對象;對王林而言,他無法求得兩全其美,最后舍表求里,折服于劉燕瑾的藝術才華。從后果看,這是一樁旗鼓相當相濡以沫的成功婚姻。王林后來的文名并不彰顯,與他在冀中的地位和實力不相稱,更有甚者,他“像寫遺囑那樣”寫成的《腹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部被批判的長篇小說,因其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根據地民眾生活——包括“暴露黑暗”,被扣上“自然主義”的帽子。三十多年間,他不斷地修改《腹地》,直到改得面目全非,而這時,時移世易,他的作品又一次與時代背道而馳。1985年王林身后面世的《腹地》新版讓他的兒子“無法卒讀”,而讀完1949年老版后卻受到極大震撼。這是文學史上一個帶有悲劇性的故事,王林這位被評論者認為是“冀中抗戰文學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也被籠罩上了一層悲劇色調。
劉燕瑾顯然是個好妻子,她也是個好演員——王林的藝術眼光不容置疑,在判斷劉燕瑾藝術才華方面同樣完全正確。她是冀中女演員中最出色的一位,而且藝術生命悠長,解放后出演過話劇《葉爾紹夫兄弟》《同甘共苦》,歌劇《白毛女》,電影《葡萄熟了的時候》《昆侖山上一棵草》《平原游擊隊》《活著》等,曾與于蘭、郭蘭英、葛優、鞏俐等明星配戲。王劉夫婦還養育了兩個富有藝術才華而且境界超越的兒子。
戰爭年代,青年云集,若對婚戀毫無規制,便難以形成嚴格紀律,無法凝聚強大戰斗力。革命隊伍中的婚戀,確實極大地受制于“組織”,組織不同意,肯定結不成婚。但從本文幾位主人公的經歷看,“組織”的作用也并非漫無邊際。至少同樣難以抗拒的還有人性:分離,移情別戀,感情的厚度不足以支撐長期等待,等等。
俗語云:“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里挑一。”王劉二人最終選擇了“靈魂伴侶”,攜手共赴人生旅途。應該為他們慶幸。
參考文獻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王林:《王林文集》第5卷“抗戰日記”》,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
王端陽:《母親劉燕瑾和凌子風》,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附錄。
王端陽:《父親王林和他的<腹地>》,《名作欣賞》2016年第31期。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