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的母親是個農民
文|魚見缸

準確的說,我的母親是個蠶農,除了一般農民的種田鋤地,她每年還養4-6萬只左右的蠶寶寶。
一
母親是家里的小女兒,上面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還有個弟弟。外公的毛筆字寫的不錯,因此據說還做過教書先生。但令母親終身引為恨事的是,外公不重視女孩的教育,在應該上學的年紀,家里讓她去照顧大哥的女兒,而大人就可以出去勞動掙更多工分。自始至終,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我父親比她年長6歲,住在河的對岸。當時賣船得了一筆錢,他就去買了一臺空調大小的春雷牌收音機。每天,聲響放到最大,放歌。通過這種方式,父親贏得了母親的芳心。
這是記憶里他們和我開玩笑時講的版本。成年以后,大伯母跟我講了另一個版本:母親原本訂了一門親事,在西邊的另一個鎮,男方條件不錯;但某次,母親聽說男方喜歡打牌,因此果斷拒絕了這門親事,選擇了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那時快30歲了,在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30歲還沒結婚是很危險的年紀,有淪為光棍的可能。之所以這么晚還沒結婚,是因為我的奶奶很早就去世了,沒有人想著替這個家中最小的兒子張羅婚事。而父親本人其貌不揚,沉默寡言;母親說,她就是看中父親勤勞踏實。
我還記得老家的樣子。前面一排三間房子,右間是我家,不到20平米,還分成了前后兩間,前面是廚房,后面是臥室;左間是大伯家;中間的大廳,兩家共用。后排矮房還有茅廁、豬舍、羊棚、兔棚,然后就是一個天藍色的房間,是我們的蠶房。

我喜歡這個天藍色的房間,不養蠶的時候,經常帶小伙伴進去玩。后來,母親告訴我,這是他倆的婚房。結婚前,這個房間是我二伯的臥室,他剛剛搬出去不久;簡單的刷上天藍色,就做了婚房。
24歲的本命年,母親就在那個天藍色的蠶房里生下了我。不知是否因為接生我的關系,接產婆的兒子后來做了廠長,成了我們村首富。
他們很拼命的干活,希望早日從這低矮的房子里搬走,造一座樓房。養蠶,插秧,雙搶,打谷子,收油菜籽,種杭白菊。
有一年,兩個人在桑樹林里套種榨菜,肩挑一兩百斤的羊糞,來回數趟;4月,榨菜豐收,收了一萬多斤;再連夜去菜葉、削皮、腌漬。3、4歲的我也參與其中,卻差點把自己左手食指切斷,疤痕現在仍清晰可見。
那一年的榨菜價格奇低無比,賣完以后,連肥料錢都付不起。
還有一年,母親把家里寶貴的一塊地用來種杭白菊。4月種下,5月壓條,6月除草,7、8月防澇,秋天采收。每天晚上都要蒸菊花,然后攤在竹匾上晾曬。那個秋天陰雨無常,菊花始終干不透。為了防止霉變,母親跑到大姨家里,和她一起買煤球、建灶臺來烘干。同樣的,成袋成袋的菊花被販子運走,售價卻沒能抵過煤球。
可能是被溺愛的緣故,我割羊草的速度和重量遠遠差于同村小伙伴。放學后,大家背著竹筐去野地里找草,手里拎一把鐮刀。其他人把草壓的很實,又重又滿;我呢,故意把草弄的蓬松,這樣看起來和他們差不多,背著又不累。
母親就開始認真的擔心我以后能不能自食其力。有一年暑假,她非常罕見嚴肅的把我逼到秧田里,讓我必須學會插秧。我呢,內心惶恐是不是小腿上有螞蝗趴著吸血。“鄉下人連種田都不會,以后誰來養你?”
直到她看見我上學成績還可以,開始有了另外一個想都不敢想的想法:離開農村。她對我說,不要做鄉下人,要做城里人。
二
接生婆的兒子那時剛剛把羊毛衫廠開出來,母親就去廠里做了紡織工人。但是,她仍然堅持養蠶。常常,半個小時的午飯時間,匆匆跑回來切桑葉、喂桑葉,自己扒拉幾口冷飯又去上班。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算最早的“半農半X”?
羊毛衫廠是沒有周末的,也沒有五一假期,最多過年放幾天。晚上工作到11點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算最早的、也是最極致的“996”?
星星小學就在羊毛衫廠邊上,我們那時發明了一樣很變態的游戲:放學以后,去翻工廠的工業垃圾,并從中挖掘潛在玩具的可能。有一種橫機上的帶鉤銀針,頗受歡迎。
除了翻垃圾,我還拿著搪瓷飯盆等在工廠門口。母親會把工廠補貼的加班晚餐省下來,然后倒給我,讓我帶回家去吃,她則回去繼續加班至深夜11點。我特別喜歡吃這種加班晚餐。
父親那時脾氣變得格外火爆,他先在窯廠燒磚,后來在建筑工地做搬運工,偶爾會給我帶幾個爛蘋果。有一回,他在村廣播里聽到印染廠招工的消息,就去應了聘。
印染廠是兩班倒,24小時工作制。今天早上出門,要到明天早上回來,白天睡覺,晚上工作。我和小伙伴正嬉鬧著,房間里就發出父親咆哮的怒罵聲。后來演變成,他只要一見到我和小伙伴在一起,就勒令回家。
許多個暑假,他們兩人都在上班,就會把蠶托付給我。我就連哄帶騙的叫上村里幾個小跟班,幫我一起把桑葉喂了。窗簾拉著,屋子里漆黑一片,只聽見“沙沙沙”、如大雨般的、蠶吃桑葉的聲音。
三
當我在星星小學上到四年級的時候,母親終于實現了搬家的愿望:他們造了一座兩層、130平米/層的樓房。
我在新房子的某塊磚頭上用粉筆寫了自己的目標:上屠甸中學、桐高、北大。堂哥們發現了我的狂言妄語,一頓奚落嘲笑。
屠甸鎮有兩所中學,一所叫屠甸中學,是給鎮上孩子的;一所叫紅旗中學,是給村里孩子的。為此,母親特意去向小學陳老師打聽,怎樣可以上屠甸中學,因為他的女兒陳亞楠早先從村小轉到了屠甸鎮小上學。陳老師說,農村戶口要上鎮上,要交轉校費。
因為剛造了新房子,家里一貧如洗、還欠了外債,母親就斷了讓我去上鎮小的念頭,我從星星小學畢業后自然就去了紅旗中學。
紅旗中學,據我的老師說,是全市最差的初中。果然,我的同學到了初二就紛紛輟學,去紡織廠上班了;有不少去了接生婆兒子的廠。
而我,居然鬼使神差的從最差的紅旗中學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桐高。母親說,廠里人都很羨慕她。

高考的時候我發揮失常,自然沒考上北大,上了吉林大學。高考結束的那天,大雨磅礴,我早有預感自己考砸了,沒有回家,徑直鉆進了網吧。
也不知凌晨幾點,我不敢回家,就去了鎮上賓館打算開房睡覺。賓館嫌我沒有身份證,讓我去派出所開證明。派出所警察直接開警車把我送回了家。
我站在家里的曬場,喊母親開門,月光如洗,照在一地的桑條、蠶沙上面。
母親非但沒有怪我,還驕傲的逢人就說,兒子要去遙遠的東北上大學了。
四
許多年以后,我瞞著母親,只身來到千島湖租了20畝桑園開始養蠶。

前幾年,一到養蠶季,我就試圖跟著母親偷師,問這問那。但不到3個問題,她就劈頭蓋臉怒斥:“你學這個干什么!?有什么用!?讀了大學,老不干正經事!”
實際上,我來千島湖的目的很簡單——自己能夠真正主導一次養蠶。
五一節前,我在公號上發布養蠶活動公告。不到一天時間,就有40多人表示興趣。最后建了一個60多人的“養蠶群”。
第一個來的是鄭阿姨。從上海過來,頭天早上就出發,原本3、4個小時的路程,高鐵沒票,花了24小時,第二天早上才到農場。
鄭阿姨說她有養蠶的情節。她的外公以前在無錫是養蠶人,她的媽媽小時候也養蠶,15歲考上大學后離開無錫。但是,她媽媽特別喜歡養蠶,在她小的時候,每年到了養蠶季就要騎著自行車去上海近郊摘桑葉。因為沒有冰箱,桑葉取回后就用濕毛巾蓋著,留著備用。

無錫現在已經沒人養蠶了。去年,我還特別去拜訪了改建為公園的無錫蠶種場,上世紀初的民國建筑,輝煌而別致。我的母親與鄭阿姨同輩,卻隔了兩代,與她的外公一樣是蠶農。鄭阿姨的媽媽是他們家第一代大學生,考上大學,離開無錫后,一去不復返,養蠶是個念想;我也是我們家第一代大學生,卻又折返回來,繼續養蠶。
可見這件事,隔了兩代,終究是要做。逃是逃不掉的。
許多人問我,為什么會有這么大勇氣?實際上,我從來都是個膽小鬼。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我的勇氣來自于身為柔弱養蠶人的反抗。
放眼世界,或者是奢侈品牌,或者是設計師品牌,或者是紡織廠老板,或者是工匠大師,或者是貿易商,居然就真的沒有一個養蠶人自己的絲綢品牌。
我們的愿景很明確: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由蠶農成立、以蠶農為靈感的絲綢品牌。
5月是很特別的時間,12日是母親節,20日是母親生我的日子;整個5月,春蠶從一粒小小的卵,變成白胖的蠶寶寶,吐絲結繭。
母親不讓我養蠶是為了我好;我要養蠶則是為了更長久的延續她的血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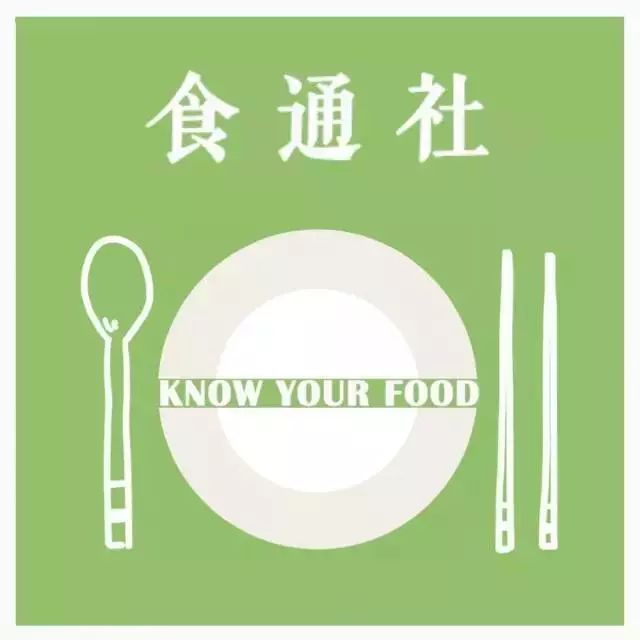
您還可以在微博、豆瓣、知乎找到“食通社”,轉載、投稿和聯系請加食通君微信小號或發郵件至info@foodthink.cn。
公平|公正|美味|健康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梅和魚”:meiheyu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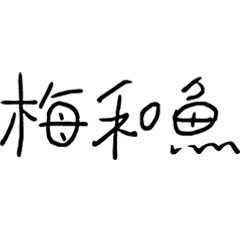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