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美國陷阱》:美國司法的長臂原則如何瓦解他國商業巨頭
近幾年,美國在外交與國際貿易中的不少做法,讓世人對美國司法中的“長臂原則”有了深切體會。例如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影響到了許多跨國公司在伊朗的商業布局。由于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定,并且表示要制裁和伊朗有經貿往來的外國公司,無論是歐洲的飛機制造商空客或者汽車制造商雷諾都不得不從剛剛復蘇的伊朗市場撤出。

另一被經常使用的“治外法權”則是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FCPA)。FCPA的立意很好,是為了禁止美國企業和與美國有經貿往來的企業直接或者間接(通過代理商)向海外政府公務人員行賄。但是在實操層面,只要一家企業與美國有一絲關聯,比如在美國證交所上市,使用美元交易,都能成為美國司法部援引FCPA展開調查的理由。而在2008年之后,這種利用“長臂原則”針對海外(非美國)跨國公司調查的案例越來越多,其選擇性執法和頻出的天價罰單(上億美元以上),讓不了解美國司法制度的外國人不得不開始揣測,美國的“長臂原則”,除了秀肌肉之外,是不是還隱藏著其他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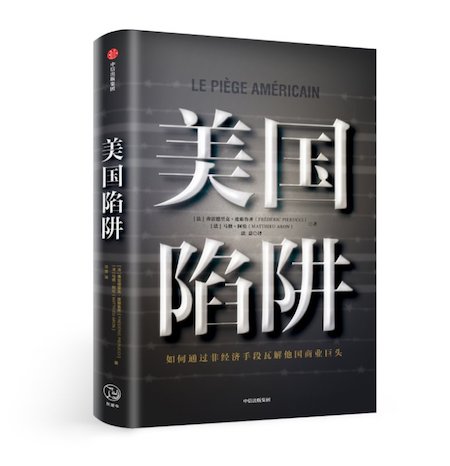
法國人皮耶魯齊的新書《美國陷阱》用他個人的親身經歷分析了美國司法的長臂原則,也給日益全球化的中國企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警示。2013年,時任法國工業集團企業阿爾斯通全球鍋爐業務負責人的皮耶魯齊在美國出差時被捕,航班剛剛抵達紐約機場,他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探員帶走,開始了與美國司法體系長達五年的博弈,并且入獄服刑接近兩年。
FBI帶走皮耶魯齊的原因就是懷疑他觸犯了FCPA,因為他在2003年參與了爭取印尼一個1.18億美元鍋爐合同競標的中間人談判,而事后證明中間人曾經向印尼有關議員行賄。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皮耶魯齊還不是阿爾斯通核心管理層成員,FBI希望以抓捕他為突破口,深入調查阿爾斯通全球業務中涉嫌的各種行賄問題。
《美國陷阱》的記述凸顯了皮耶魯齊所理解的美國司法的長臂原則——選擇性執法以及司法背后可能代表的商業利益裹挾。作為親身經歷者,皮耶魯齊對美國的司法制度給出了細致的觀察,尤其對司法機構用輕罪指控或者減刑來壓迫和利誘嫌犯揭發或者做污點證人的做法,有比較深刻的批評。他因為應訴和服刑,輾轉了美國的多家監獄,也因此對美國監獄系統,尤其是外包給盈利機構經營的監獄系統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全景式的揭露,其中就包括對經濟罪嫌犯及未決嫌犯缺乏足夠的保護。
但是,恰恰因為皮耶魯齊的親歷者身份,書中也充滿了他個人的怨憤,一些評述失之客觀。比如,他認為的美國司法部“構陷”他的利益驅動——幫助通用電氣壓垮阿爾斯通,收購阿爾斯通的明星產業——就不夠客觀。因為事實上,GE的這一并購被證明是GE前任CEO伊梅爾特任內最大的敗筆,因為當時伊美爾特根本沒有預測到到鍋爐行業的整體衰落。
盡管如此,皮耶魯齊的這本書仍然提出了兩點重要的觀察,值得各國企業警醒。
第一,美國司法的長臂原則的確有重點打擊非美國的跨國公司的味道,對此一方面可以陰謀論地揣測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盛頓的游說能力大大強于海外跨國公司,另一方面也凸顯了美國司法部有通過訴訟讓跨國公司就范、收取大量罰金的動力。
按照《美國陷阱》中的統計數據,截止2014年,司法部海外反腐調查案件中,只有30%的涉及外國(非美國)公司,但是這些公司貢獻了67%的罰款總額。而罰款超過一億美元的26個案例中,21個是外資公司,包括西門子(8億美元)、道達爾(3.98億美元)和戴姆勒(1.85億美元)這樣的歐洲巨型企業。相反,美國企業的游說似乎有效地多,司法部從沒有在美國石油企業,比如美孚這樣的巨頭,或者國防企業,比如通用動力等巨鱷身上挑出任何毛病。按照皮耶魯齊的說法,這些領域和阿爾斯通所在的裝備行業一樣,都充斥著海外交易利用中間人行賄的潛規則,美國公司真能免俗?
值得注意的是,FCPA法案早在1977年就已通過,但在最初的30年并沒有多少判例,但是2008年后開始有爆炸式增長。可以揣測的是,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司法部通過FCPA案件給出巨額罰單的確可以補貼政府不足的預算。當然,由于美元清算體系在紐約,紐約的檢查官處于“屬地管理”的地位,也很愿意調查跨國公司這樣的“大魚”,因為一則可以揚名,二則可以帶來巨額罰款,兩者都會成為他們在政壇上進階的資本。
第二,博弈美國的司法流程,即使在歐洲人看來也不容易應對。首先,美國司法機構一開始會選擇和嫌疑犯做交易,尤其是像皮耶魯齊這樣的小魚蝦,因為他們的目標是釣大魚。FBI第一次抓捕皮耶魯齊時的談話就是希望發展他做臥底。而在被調查企業內部發展臥底,搜集更多證據,是司法部常用的做法。阿爾斯通就有一位被美國司法部“策反”的臥底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門,成為與調查人員全方位合作的眼線。可惜,皮耶魯齊對此根本不了解。如果以事后阿爾斯通對他的態度來評判,選擇合作可能可以使他避免深陷牢獄之災。當皮耶魯齊選擇不合作,寄希望于律師的辯護之后,美國司法機構采用第二招,狂轟濫炸,用海量的文件來拖垮當事人。在美國,查閱卷宗、對案件進行復核鑒定、尋找有利于被告的證詞,這些步驟的費用都必須由被告人支付。因此狂轟濫炸的策略,比如檢方提出幾百萬份文件,就可能壓垮大多數被告人,因為看完這些文件需要律師付出大量時間,律師費也會貴得驚人。
最終,皮耶魯齊雖然并不認為自己有罪——他只是阿爾斯通隱秘雇傭中間人流程中的一環,而按照歐洲人的理解,如果企業高管只是按章辦事,沒有中飽私囊,那么即使企業被判觸犯海外反壟斷法,不應該由個人來承擔責任——仍然不得不選擇認輕罪,并因為審判所在地美國康涅狄格州從未審理過FCPA案件,法官希望樹立一個典型而被“重判”了30個月監禁。
對于我們而言,《美國陷阱》一書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提醒中國跨國企業,必須直面全球化過程中的法律風險。一方面中國跨國企業需要進一步認清美國的 “治外法權”可能給企業以及企業的高管帶來的新風險;另一方面,中國的跨國公司也非常有必要進行 “普法”教育,因為在短期內美國司法體系的“長臂原則”不會改變,只有了解不同的司法實踐,致力于合規,才能對企業和企業的高管真正給予有效的保護。而美國對海外反腐法的更為嚴格的執行,在全球基本已經成為大趨勢,許多發達國家都已經簽署了OECD反腐敗條約,這些都值得中國立法者去思考。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