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54年:羅馬教廷為何如此奇特?
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節目,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54年。
這是咱們節目開播以來的第55期。過去,我們都會播報一句,這是大宋多少年,大遼多少年。但今年,這個環節就免了。因為這一年咱們要說的,是一件歐洲的事。
請注意,這可是11世紀。世界上沒有哪個文明像我們中國人這樣愛記錄歷史,所以,這時候世界上絕大部分地方的歷史面目還是一片模糊。歐洲也一樣,我們以前就說過,這個階段歐洲的可信歷史記載并不多。
整個11世紀,如果說歐洲有什么一定要關注的大事件,那今年發生的這件事一定排在前三名。這件事就是:基督教東西教會的大分裂。
這一次的教會大分裂,其實和當初羅馬帝國的分裂一樣,分裂成了東邊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會,和西邊羅馬的天主教會。

1054年7月16號,西邊的羅馬教會派人千里迢迢趕到君士坦丁堡,闖進圣索菲婭大教堂,把一張紙拍在人家教堂的祭壇上,說你們都是基督教的異端,是魔鬼,是撒旦,我們宣布,你們被開除出基督教會了。
那東邊的教會能干嗎?很快,東邊的教會也召開宗教會議:把那張紙拿來,就是羅馬教會拍在我們祭壇上的那張紙,拿來燒了,同時宣布,我們也把你們開除出基督教會了,你們的教皇,還有把這張紙送來的幾個人,也開除。當時的話說的是:“教皇的使者及其隨從人員像野豬一樣來到圣城,玷污了真理”。
什么事兒啊?鬧成這樣?你要非說具體的事兒,那都非常小。比如,舉行圣餐的時候,用的那個面餅,應該是用發酵過的呢?還是沒發酵過的呢?東邊教會說了,必須得是發酵過的啊,因為發酵過的才有生命啊,沒發酵的餅就是死面。西邊說,不對不對,耶穌最后的晚餐,吃的就是沒發酵的餅啊。
能擺上臺面吵的事兒,都是這類事兒。當然也有一些理論上的分歧,比如圣靈是來自圣父,還是來自圣父和圣子。你懂的,兩口子鬧到要離婚的地步,能擺在桌面上的沖突,往往都是這樣的雞毛蒜皮。但是作為旁觀者,我們心里也得清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背后的矛盾一定是積累很久了。
你想,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在政治上的徹底分裂是在公元395年,現在是1054年,已經600多年了。羅馬教廷用的是拉丁文,東正教會用的是希臘文。兩邊從政治到語言到教義,早就不是一回事了。能拖到1054年才正式分裂,已經是看在耶穌的面子上,盡力維持的結果了。
順便說一句,這兩個教會后來和解了。不過是直到1965年雙方才宣布:得了,我們互相都不開除對方了。這就相當于兩兄弟的家族比鄰而居,在北宋時候鬧了矛盾,氣哼哼地過了快一千年,到我們這一代才開始能互相串門。
我們今天不去分析,他們互相之間為什么會鬧矛盾,誰對誰錯,那是基督教內部的問題,跟我們關系不大。這次東西教會大分裂,是一個契機:它讓我們有機會觀察羅馬教廷,到底是怎樣一個存在?
我們這代人,一提起基督教會,往往想起的就是羅馬教廷。羅馬教廷干的一些事,具備的一些特征,我們想當然地都算在了基督教的頭上。
但是有了1054年東西兩個教會的分裂,我們可以對照一看:誒?羅馬教廷跟他東邊的那個兄弟很不一樣啊。不僅如此,東邊那個兄弟和世界上其他的宗教組織其實更像。而羅馬教廷怎么越看越奇怪呢?
是的,今天我們就拿東正教會當個鏡子,我們來看看,西邊的羅馬教廷有什么奇怪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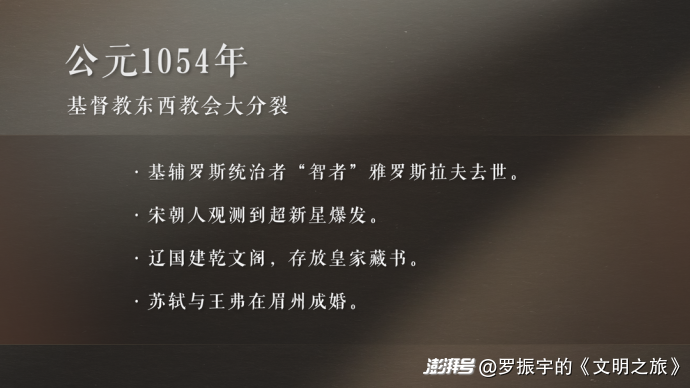
奇怪的羅馬教廷
要說羅馬教會的奇怪之處,咱們得先回到一個起點:什么是教會?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宗教信徒的群眾組織嘛。
那你就說一個正常的民間群眾組織應該什么樣?又沒有軍隊、又不掌握暴力,純粹靠著信眾的共同信仰維持著。跟我們大學里的興趣小組比,強點兒,也有限。
我們身邊的佛教寺廟,或者是現在美國的那些基督教會,差不多就是這樣:大家也就是在業余時間、周末聚在一起聽聽講座、唱唱歌,或者做點義工,也沒什么強制性,想來就來、想走就走。這才是我們心中正常的一個宗教組織的形象。
你可能說,這只是剛開始。如果信仰的力量足夠強,一個教會在高度組織化之后,是可能擁有很強實力的啊。
是的。確實可能。但是接下來呢?要么它干脆謀求擁有暴力和軍隊,最后變成一個政權。比如說現在很多伊斯蘭國家,還有中國晚清的太平天國。基督教自己也有一個例子,16世紀的加爾文教派在日內瓦建立的一個神權共和國。這也就是所謂的政教合一,宗教領袖直接變成國家領袖。
還有第二種情況:一個宗教組織,那么有影響力,世俗政權就不放心了,要么迫害他,要么收服他。基督教早期遭遇的就是迫害。不止是尼祿這樣的暴君要迫害,賢能君主也一樣。比如說,羅馬帝國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就是寫過《沉思錄》的那位。即使是在他的統治時期,基督徒在監獄里也是關得滿坑滿谷。那個關基督徒的牢房能擁擠到什么程度?據說很多人是在牢房里因為缺氧活活憋死的。
迫害也消滅不了,那就收服。基督教的東邊那一支,東正教就是這樣。拜占庭的皇帝說了,你在我這兒傳教,那我來問你:誰才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啊?皇帝才是。誰來主持最重要的宗教儀式啊?皇帝來主持。誰來決定東正教的最高首領牧首的人選啊?皇帝來決定。回答正確!那你這個宗教領袖就可以有一些地位嘛,但是必須要聽話哦。
又過了幾百年,拜占庭帝國滅亡了,東正教一路往北,到俄羅斯發展,那就得聽俄國沙皇的。后來俄國出了一位曠世雄主——彼得大帝,想來想去還是不放心,干脆把牧首這個崗位給廢了,設立了一個東正教事務管理局,直接用國家機關來控制東正教。
你看,一個宗教組織,要么你給別人當家,要么別人來當你的家,反正一山不容二虎。這才是正常的邏輯。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走中間路線呢?一個宗教組織,既沒有暴力和軍隊,也不想管理世俗事務,但還想獨立存在,還要有強大的影響力,還想能和各種國王、皇帝、手里有刀有槍的人掰掰腕子,甚至騎在他們頭上。有這個可能嗎?
見證奇跡的時刻來了。世界上還真就有這樣的教會,那就是:基督教在歐洲西邊的這一支,羅馬教廷。沒有槍,沒有炮,手里就拿著一本《圣經》,居然就能縱橫歐洲幾百年。你說奇怪不奇怪?
羅馬教廷的奇怪之處主要有兩點,一個是組織很奇怪,一個是領袖很奇怪。我們先說組織。
正常的宗教組織應該是什么樣?大家因為共同信仰走到一起來,而信仰這個東西,往往一人腦子里有一個想法,所以,宗教組織特別容易分裂。就像一個線下興趣小組,往往玩著玩著就分開玩了,沒有那么強的凝聚力。所以,正常的宗教組織都是網絡狀的,而不是金字塔狀的。教區和教區之間的聯系,是靠溝通、靠商量、靠契約,沒有辦法靠命令、靠紀律、靠制裁。
美國現在的新教就是這樣,雖然大家都用同一本《圣經》,但是小教派林立,誰也不服誰。基督教歷史上的東正教也是這樣,它其實只是一個分散的聯盟,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雖然號稱是“平等中的第一”,但是不好意思,那是大家給你面子,你召集個會議,協調個關系還行,還真就沒有什么對下面教會的管轄權。這也符合中國人的常識,比如中國佛教的各大寺院,大家都是十方叢林,登封少林寺和洛陽白馬寺的方丈,見面也只能客客氣氣,互相誰能管得著誰呢?
但是你回頭看看羅馬教廷:其他宗教組織都可以稱之為“教會”,而唯獨羅馬教會被稱作“教廷”,朝廷的那個廷。是的,它的組織化、集權化的程度跟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是差不多的。羅馬教廷從上到下是一個結構緊密的金字塔組織。最頂上是說一不二的教皇,下面分成各個教區,教區里有主教。一層一層,體系嚴密。有點像軍隊里面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的建制一樣。
你想想看,這是一個多古怪的局面:信眾一進教堂,神父就跟他們聊人人平等;信眾一走,教堂門一關,神父馬上進入了等級社會,在羅馬教廷體系內居然是官大一級壓死人。一個宗教組織怎么會演化成這樣?很奇怪。
還有一點,就是這個體系頂端上的宗教領袖,教皇,也很奇怪。
正常的宗教領袖什么樣?這個都不用看別人,你看早期的基督教領袖就行了。
基督教剛起家的時候,和其他宗教組織差不多:耶穌帶著自己的十二個學生,所謂“十二使徒”嘛,里面有幾個是打魚的漁夫,有稅務局的小公務員,有無業游民,這些三教九流的人,四處巡游傳教。他們講的,都是仁慈、寬恕、“要愛你們的仇敵”“有人打你的右臉你就把左臉也伸過去讓他打”這一套。
后來他們影響力越來越大,就招來了迫害。耶穌是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他的十二使徒中,除了一個約翰,剩下十一個人都因為各種各樣的迫害死于非命。就拿耶穌的大弟子彼得來說:你要是去看西方教堂的壁畫和雕像,手里面拿著一把大鑰匙的就是他。因為據說是耶穌說的,我把天堂大門的鑰匙交給彼得看管。這位彼得,最后也是慘死在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迫害中。他臨死的時候說,你們要把我釘死在十字架上啊?但那是耶穌的死法,我不配,你們把我倒過來釘死吧。你看,基督徒的反抗精神通常是用這種方式體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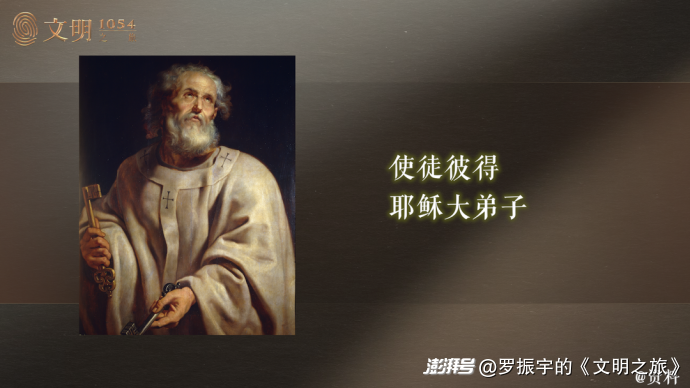
這個彼得是誰啊?就是后來追認的第一任教皇啊。現在到羅馬教廷所在地梵蒂岡去旅游,看到的那個大教堂,叫圣彼得大教堂,就是用第一任教皇彼得來命名的。據說彼得的遺骸就埋在它下面。
教皇的英文是Pope,這個詞更準確、更學術的中文翻譯,應該是教宗。(只不過,一般人更熟悉教皇,我在節目里就這么稱呼了。)Pope這個詞,它的拉丁文詞源就是 papa,意思就是“父親”。對啊,一個宗教領袖是靠精神力量來引領人的。不像父親一樣慈愛,怎么行呢?
其實,在基督教內部,教皇形象的底色一直是這樣的。我舉個近點兒的例子。
話說在民國的時候,山西大學有一位前輩老教授,歷史學家,叫閻宗臨,他就曾經近距離接觸過羅馬教皇。那是在抗日戰爭前夕,閻先生正在歐洲讀博士。他不是因為家里有錢才出國留學的,他是勤工儉學,在國外工廠里打工,靠自己發奮圖強,考上了瑞士的博士。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經常去梵蒂岡的圖書館查資料,被圖書館的一位老神父注意到了。老神父就和當時的教皇庇護十一世說,有個中國來的學生,每天坐在圖書館,非常用功地讀書。教皇一聽,也挺有興趣,就把閻先生請過來聊天,還對他的學業很關心。后來閻先生離開梵蒂岡,回到瑞士結婚。教皇聽說了這件事,還主動打電報,送上了祝福。
你看,這才符合我們心中對一個宗教領袖的正常印象嘛。有威望、人品好、滿腹經綸、內心虔誠、以德服人。遇到迫害,就以身殉道,只留精神在人間。
好了,你再回頭想想,教皇給我們一般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發動十字軍東征、迫害科學家、用宗教裁判所把人燒死、在整個歐洲和各種國王對剛。這些事情里面的是非曲直咱們暫且放在一邊,至少這個羅馬教皇肯定是一個強有力的形象,這和那個慈眉善目的,灑向人間都是愛的“Papa”慈父,不沾邊啊。這兩個形象的反差怎么這么大呢?
在理論上,教皇的權力有多大呢?《天主教法典》里是這么表述的:“由于此職務,他在普世教會內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職權,且得經常自由行使之。”你看,這詞兒用的:最高的、而且是完全的、還是直接的,還是自由行使的。說白了,這是一種完全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的皇帝,那么大權力,還要被什么天命、祖制、民心、諫官制約著。教皇,理論上除了上帝,誰的臉色都可以不看。

那教皇和世俗政權的那些國王和皇帝,誰的權力更大呢?羅馬教廷歷史上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寫的,叫《教皇如是說》,一共是27條,挑幾條給你看:
“他的使節——即使教階較低——在宗教會議上高于所有的主教,并有權做出廢黜主教的判決。”
“在各種事情當中,我們也不能與被他開除教籍的人同居一室。”
“他的頭銜是世界上唯一的。”
“他能廢黜皇帝。”
“任何人都不能撤銷他的任何判決,所有人中唯有他一人能撤銷這種判決。”
“他自己不受任何人審判。”
“羅馬教會從未犯錯誤,也永不犯錯誤,《圣經》作證。”
你可能會說,這是教皇自己寫的,一廂情愿吧?還真不是。我們現在講的是1054年的教會大分裂。再過21年,到了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寫下了這份文件。再過兩年,1077年,就發生了歐洲歷史上那個著名的事件: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得罪了教皇,被教皇絕罰了,就是不承認他是基督教徒了。
結果怎么樣?亨利四世連夜趕路,跑到教皇家門口,你想,那可是1月啊,天寒地凍啊,他就這么帶著自己的老婆孩子,在大雪地里光著腳站了三天三夜,請教皇原諒。
一個人如果手里沒有暴力和軍隊,他怎么可能擁有這么大的權勢呢?你不覺得奇怪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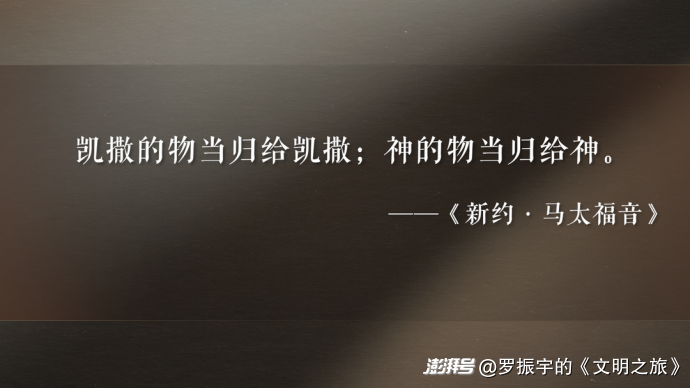
奇特的歷史機緣
早年間到歐洲旅游的時候,有一句順口溜,叫“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停車看廟”。廟是什么?就是教堂啊。確實,歐洲古跡的精華往往都是各式各樣的教堂: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還有圣彼得大教堂,等等。尤其是這個羅馬的圣彼得大教堂,你要是去旅游,天哪,能看見多少藝術珍品啊,貝爾尼尼的雕塑、拉斐爾的畫作、還有附近西斯廷教堂的米開朗基羅的穹頂畫,幾乎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都有藝術品。但那又何止是藝術品啊,那就是錢啊。
是的,過去1000多年,從各地籌集的海量金錢,都被沉淀在歐洲這些大大小小的教堂建筑和藝術品當中了。《中世紀》的作者李筠就說,我作為游客,一邊逛一邊想,這背后可絕不僅僅是宗教信仰,一定還有一個龐大的、井然有序的、高效的組織在一直運轉,才會有這么澎湃的、持續的財富積累。這個組織,當然就是羅馬教廷。而且前面說了,它手頭沒有暴力,不以槍桿子為基礎,居然也能夠有這樣的力量,真是一個奇跡,而且是在全世界任何文明中都沒有出現過的奇跡。那怎么解釋這個奇跡呢?
李筠老師的這本書里提供了兩個原因:一個偶然的時機和一些偶然出現的人。先說時機問題。
羅馬教會是在什么時候掌權的?是在西羅馬帝國崩潰的時候。
中華文明雖然也經歷過亂世,就是那種一點秩序也沒有的時候:五代十國時期,大概持續了半個世紀左右;從西晉八王之亂到五胡入華時期,這個比較長,大概一個半世紀。這也就是頂了天的長度了。
可是歐洲的那個亂世呢?那可就長嘍。西羅馬帝國雖然是公元476年才正式結束的,但是自從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破羅馬,在城里面燒殺搶掠3天,歐洲西部的秩序其實就已經崩潰了,各種蠻族小國,各種莊園林立,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1世紀初,才形成了那種很粗糙的封建秩序。歐洲的這個黑暗亂世,你算算,那可是600年啊。
黑暗的中世紀,這個詞我們經常用,但是到底黑暗成什么樣子?是蠻族來了,成天燒殺搶劫嗎?不會的。要是那么殺600年,什么都剩不下了。
黑暗時代,破壞力最大的其實不是戰爭,而是秩序的消失。對啊,蠻族來了,他們也是人,他們最大的特點不是愛打仗,而是文明程度低,沒有治理復雜社會的經驗。所以,法律體系首先崩潰了。
如果你是當時的羅馬人,你會發現,自己和別人的利益沖突,沒有人出面調解了,那行了,生意就不能做了。遠距離的貿易就只能停了,各個地方的交流就被阻斷了。再然后呢?城市化就崩潰了。對啊,城市的運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協作網絡,得有水源吧?得有復雜的服務業吧?這個時候都沒有了,城里又沒有糧食,你待在這兒干啥呢?等著餓死嗎?所以有土地的貴族往鄉下跑,這里有吃的,人聚集起來,還稍微安全點。
一般的市民也往這里跑,附近的農民也跑來投靠。一個個自給自足,經濟水平很低的小莊園就遍地開花地長出來了。羅馬、米蘭這樣的大城市就“幽靈化”了,成了空殼,基礎設施、引水渠、公共浴池迅速地被廢棄,街道上雜草叢生。到了這一步,社會的崩潰就不可逆了,因為合作方式解體了嘛,就算還有什么國王,他也很難再收的上來稅,提供公共品。

再接下來,就是貨幣消失、藝術消失、技術大退步、糧食產量下降、人口下降。再接下來,時間一長,真正的悲劇來了:文化大斷層。幾代人不讀書,什么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誰啊?不熟。是魔鬼嗎?到了這一步,歐洲的天可真就黑了。文明要在徹底的黑暗中再次啟動,可就難嘍。
但是慢著,就在這幾百年的沉沉黑暗中,有一個地方,還有亮光,哪里?羅馬教會。
在我們一般的印象里,歐洲中世紀的黑暗,不就是羅馬教會造成的嗎?他怎么反倒成了保留亮光的地方?
歐洲的情況我們比較隔膜,所以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中國古代也遇到了一個類似的亂世,那保留文明火種最后的地方會是在哪里?也可能就是寺院啊。強盜燒殺一個村莊和燒殺一個寺院,哪個可能性低一點?當然是寺院。寺院里畢竟有菩薩,即使是強盜,心里多少也有點忌憚。《西廂記》的故事不就是發生在唐朝后期,鶯鶯小姐和老夫人為躲避兵亂,住在普救寺里,這才有了和張生的奇遇嗎?

歐洲的情況差不多。修道院里,沒啥財產,教士在里面苦修,沒什么可搶的。但是,教士有文化啊,基督教的教義講仁愛和寬恕啊,在亂世中對人心是有撫慰作用的,老百姓很信他們。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有軍隊、有權力的人,你會不會保護修道院和這些教士,為己所用?好歹降低一點治理成本嘛,好歹能讓這些有文化的教士給自己幫點忙嘛,那怕能幫自己看看信也是好的啊。當時的那幫蠻族的國王是真不認識字啊。
有一個很著名的傳說,公元453年和455年,一個叫利奧的基督教領袖兩次赤手空拳去跟蠻族人談判,說不要毀滅羅馬城好不好?第一次對方居然答應了。第二次雖然只是部分成功,但是這種勇氣還是讓人佩服。那你說,這人在民間的聲望能不高嗎?當時的西羅馬帝國的皇帝能不高看他一眼嗎?對啊,皇帝手下的那些將軍,根本信不著,文官系統也都崩潰了。突然冒出來這么個教士,又有文化、又有勇氣,別忘了,他還有遍及國內的基督教的組織網絡,但他唯獨沒有軍隊,沒有野心,但是還有擔當,愿意幫忙。你說天下哪兒找這樣的人去?
你就想中國古代的一個場景:我是一個軍閥,附近廟里的有個老和尚,人品好,有聲望,還經常能挺身而出幫我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什么少林寺、白馬寺的方丈跟他還是師兄弟,可以幫他打聽全國各地的消息,這和尚還認字,你說,我是不是該八抬大轎把他請來,給我當軍師啊?
羅馬皇帝又不傻,能不支持這位利奧嗎?利奧是誰啊?其實他就是基督教會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有權力的教皇,利奧一世。羅馬皇帝說,快,我看你們基督教這個主教那個主教的,都不如這個主教靠譜,以后,這個利奧一世就是你們教會里面的皇帝。教皇制就這么建立起來了。
權力就是這樣,很多情況下,拿到權力,并不是靠野心和計謀,而是在緊急情況下被心甘情愿地授予和讓渡過來的。基督教會就是在羅馬帝國的危難時刻,靠主動的擔當,拿到了信任,拿到了權力。
如果你生活在那個時代,你會發現,時代的中流砥柱,這個時候已經不是羅馬帝國的朝廷了,而是這個新崛起的羅馬教廷了。教廷有文化、有聲望、有網絡,他們反而更值得信賴。更重要的是,從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宣布寬容基督教,這個組織已經和帝國共存了一百多年了。羅馬帝國怎么靠法律、行政命令和等級化權力,管理那么廣大疆域和那么龐大人口,基督教會也一直在學習啊,這個時候他也學得個七七八八了。所以,西羅馬帝國崩潰的時候,只有基督教會能繼承帝國的衣缽,成為權力真空時期的主心骨,甚至承擔一些社會管理職能。
這么一捋,你應該明白了,羅馬教廷的底色,是一個宗教群眾組織,但他為什么能夠成為一個結構緊密的金字塔組織呢?這是非常偶然的歷史機緣的結果。你看,同樣是基督教,羅馬帝國東部的局面就沒有過那么長期的混亂,所以,東邊的基督教會就一直被皇權壓制,也就沒有崛起的機會。
當然,羅馬教廷的崛起,教皇權力的取得,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間有很多重要節點,
不像我剛才說的這么簡單,學術界還有不少爭論,但是毫無疑問,它是偶然和幸運的歷史機緣。
羅馬教會的另一個幸運在于,它的歷史上不斷出現雄才大略的教皇。
利奧一世之后一百多年,這個時候的西歐已經一片糜爛了,羅馬教會又有了一位了不起的教皇,那就是公元590年登基的大格列高利。有人說他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教皇。所以,他的名字前面加了個Grand,偉大的意思,大格列高利。為啥?因為這個時候已經沒有羅馬皇帝可以依靠了,教會得獨自肩挑這個爛攤子。
美國歷史學家雪萊的《基督教會史》,里面有這一么一段描寫:
早在公元590年,羅?就處在掙扎之中。這座城市先是遭受悲慘的洪?和殘暴的戰爭的蹂躪,后?受到?情蔓延的瘟疫的重擊。?們已經茍延殘喘了,接踵??的是?死病爆發,?批?迅速死去。??上??地堆滿?體。?們快發瘋了。羅?成為?座廢墟,教宗帕拉糾?世(Pelagius II)本?在痛苦的叫喊聲中去世。
圣彼得?教堂有六個?沒有教宗秉政。當教會領袖選出?位名叫格列?利的修?時,他拒絕就職,甚?逃出羅?城,藏在?林?,后被發現并拖回羅?。在通告君?坦丁堡之后,教會官員于公元590年9?3?封他為圣彼得的繼承?。——雪萊:《基督教會史》,p.165
對,大格列高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洪水、戰爭、黑死病、連前任教皇都死于瘟疫的黑暗時刻,這個50歲的大叔,被強行推上了教皇的位子。既然跑都跑不掉,那就好好干。他上任后,就帶領教會的人,處理瘟疫,招兵買馬跟蠻族人干,拿出財產解決羅馬城的糧食短缺問題,救濟老百姓,重新修建羅馬城的基礎設施,等等,當然,還有傳教。
你看,羅馬教廷還是我們印象里那個又反科學、又反進步的宗教組織嗎?
恰恰相反,這本書里有一個形容,說這位教皇大格列高利,是“撿起了被粉碎的世界的碎片”。所以格列高利死了之后,他的墓志銘上用了一個詞,叫“神的執政官”。對,可不是一個只管宗教事務的神職人員哦,是執政官。本來,人間的事不歸我羅馬教會管,是歸羅馬帝國管。但是現在人間完蛋了,羅馬帝國沒了,所以從大格列高利開始,羅馬教會就必須站出來,替上帝把這個世界管起來。既然現在我羅馬教會得管理整個西歐的秩序,那我就必須建立一個在全歐洲從上到下的、有組織力的系統,否則,世界就會落到那些野蠻、好戰的草臺班子手里面。這本書里還有這么一句話,“中世紀教皇的特權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格列高利通過這個多事時代維系下來的實干政府。”教廷作為教會的核心、教會作為西方的引領者在他手中算是穩住了。
當然,還不只是他,江山代有才人出:又過了400多年,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又出了格列高利七世,就是逼著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在門口雪地里光腳站了三天三夜的那位教皇,還有后來13世紀初期的登上了教皇權力頂峰的英諾森三世,等等。這都是雄才大略的人。你要是看這些人的傳記,會發現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意志極其堅定,在看似沒有可能的地方,他們覺得可以再試試;在別人覺得必須要退讓的地方,他們直視對方的眼睛,來啊,互相對撞啊,堅持不退。

就拿我們剛才聊到的四位教皇來說——
第一位利奧一世,讓大家覺得,哦,亂世中,羅馬教會居然是一股可靠的力量,來,可以把更多的權力給到這股力量;
第二位大格列高利,讓大家覺得,真是有擔當啊,羅馬教會才是這塵世間的擎天柱,是文明賡續的燈塔;
第三位格列高利七世,讓大家覺得,教皇雖然沒有任何兵馬,但就是可以凌駕在世俗君主的頭上,創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先例;
第四位英諾森三世,讓大家覺得,教皇是歐洲所有力量中最無所不在的、最關鍵的那根杠桿,他和誰站在一起,誰就可以贏。
你看,教皇的權力基礎,不是暴力,而是這種上千年積累出來的先例、故事、獨特的政治生態位,以及各種各樣的精神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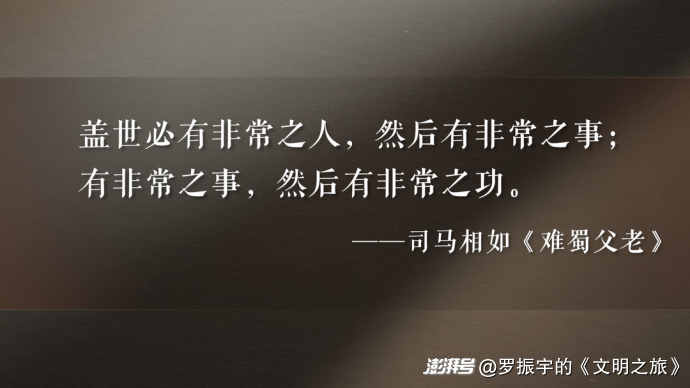
文明的演化論
好了,說到這里,我們可以回答一開始提出來的那個問題了:為什么西方可以發育出如此奇怪的、在全人類歷史上都絕無僅有的羅馬教廷?
答案可能是兩個字,偶然:偶然出現的帝國崩潰的歷史情境,以及偶然冒出來的雄才大略的領袖人物。
千萬別看不起“偶然”這兩個字,它好像什么都沒有解釋,但其實,偶然是生物演化、物種創新的最重要的動力。文明和大自然里的物種一樣,總是在產生各種各樣偶然的基因突變。換成歷史學的詞匯,這個突變,就是所謂的奇特的歷史機緣。
請注意,在剛才這段話里,觀察文明的發展,我用了一個新視角:演化論的視角。這和過去的很多思維習慣是有區別的。
過去,很多人都覺得,西方文明牛啊,所以人家從根兒上就是對的。其他文明如果不是那樣,那就是其他文明走了岔道。所以,過去我們經常問問題的方式是:西方文明是這樣,那么,我們中華文明為什么沒有這樣?好像是理應如此,而我們沒有做到。人家有了蒸汽機,我們也有水排和風箱啊,為什么我們就沒有把它們加起來變成蒸汽機呢?我們哪里錯了呢?這就是所謂的“李約瑟之問”嘛。
但是,今天這期節目,我們通過看西方基督教會這一個例子,試圖給你一個反過來的視角:為什么所有的文明都是這樣,而唯獨西方文明會變成那樣?在文明演化的過程中,他們到底經歷了什么樣的突變?
你換到這個角度一想,很多問題就不用糾結了。人類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里,就像是在不同的環境中獨立演化的許多物種,依托各自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發展路徑,篩選和積累了大量獨特的文明意義上的基因突變,比如生活方式,宗教傳統,思維模式,技術路線等等等等,最終形成了五花八門的文明形態。在這個意義上,文明形態沒有對錯高低,只要能生存下來的就是成功者——和地球生物物種的生存邏輯一樣。
但是別忘了,人類是可以交流的。等哥倫布發現美洲,世界各地的文明重新擺脫了獨立狀態,又一次開始深度交流和融合,人類世界開始進入高速變化的時代。而在這個過程里,各個文明所攜帶的獨特的基因突變會融合,產生一種文明意義上的“雜種優勢”。誰能和更多文明保持充分的交流和融合,誰能在自己體內引入更多樣的文明突變,誰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就能提高。這個過程有點像農業科學家把一些作物的種子發射到太空中,承受宇宙射線的照射,讓它發生各種變異,然后再返回到地球上,根據結果來篩選,然后再通過雜交,來優化整個物種的性狀。
簡單一句話,人類文明每一個部分,經歷的歷史機緣,積累的有益突變,最后都不是自個兒的,而是都會成為所有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誰帶來的不重要,最后都是大家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文明發展,是不是比我們爭論,西方好還是東方好,誰該向誰看齊,要好得多?
說得更直接一點:人類文明的其他分支,如果演化出來什么好的特性,我們應該是高興還是沮喪。長期來看,當然應該是高興。因為我們不用付那么慘痛的代價,比如像西羅馬帝國那樣經歷幾百年的黑暗亂世,我們就可以拿到在正常環境下不可能變異出來的文明基因,然后為我所用。這是多好的一件事?他人承擔代價,而我只須拿來。
最后,我們來看看西方基督教會的這次突變,會引發什么?
羅馬教廷的奇特崛起,會帶來西方社會獨特的政教二元結構。用《中世紀》這本書的話來說,“政教二元化使得講政治的道理變得非常重要,武力消滅不掉各種對手又得和他們長期斗爭,嘴仗就得一直打。為了比誰更有理,各種政治法律理論層出不窮,講權利、講法治、講制衡、講道義,花樣繁多、高論迭出。教皇革命使西方真正成為西方,西方從此走上了一條被自己的政教二元結構約束的獨特道路。”
你看,崩潰的羅馬帝國,激活了奇特的羅馬教廷,而奇特的羅馬教廷,又會進一步激活一個不一樣的西方社會。一個奇妙的鏈式反應開始了。這個話題,我們要留到公元1096年,就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那期再講,那剛好是第三季《文明之旅》的第一期。距離你看到的這期節目,還有42期。42期節目之后,我們將會把目光再移回到歐洲。請耐心等待。
公元1055年,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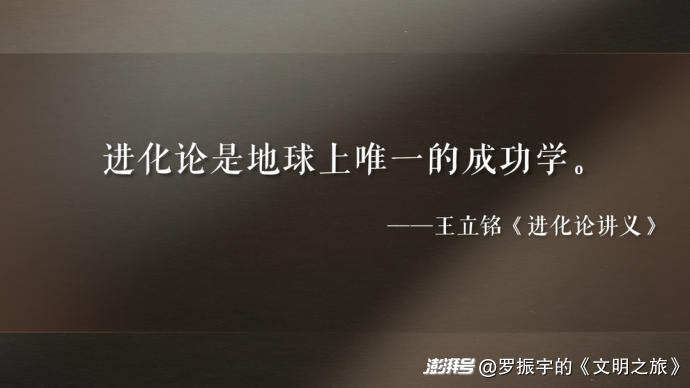
致敬
本期節目的最后,我想致敬生物學家王立銘。做1054年這期東西教會大分裂的主題,當然要讀大量的歷史研究著作,但給我最大啟發的,卻是這本王立銘老師的《進化論講義》,給你念書里的一段吧——
面對復雜的真實世界,進化論指出了一條完全相反的改造路徑。它告訴我們,復雜系統能夠自發形成,復雜問題總能自己找到解決方案。哪怕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們需要的無非是清晰的邊界條件、持續的進化推力,以及足夠的耐心。
它用生命現象證明了這條路徑的巨大力量,同時也告訴我們這條路徑有一些難以避免的麻煩,比如強烈的路徑依賴、無可逃避的僵化和死亡,需要我們保持警惕。
總有人問我,《文明》這個節目,是不是主打中國歷史,但通過這期節目,我想告訴你的是,我們這個節目的思想資源,絕不僅限于歷史研究,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甚至包括生物學,都是我們的靠山。人類文明每一個部分經歷的歷史機緣,積累的有益突變,都是財富啊,我可不會給自己劃定什么邊界,一邊學習,一邊輸出,不知老之將至,多快樂啊。
參考文獻
(英) 米瑞·茹賓、(美)沃特·西蒙斯編著:《劍橋基督教史(第四卷):西歐基督教(約1100—約1500)》,楊華明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
(美)哈羅德·J.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第一卷),賀衛方等譯,法律出版社,2018年。
(英)埃蒙·達菲:《圣徒與罪人——一部教宗史》,龍秀清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
(美)胡斯托·岡薩雷斯:《基督教史(上下冊):初期教會到宗教改革前夕》,趙城藝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
(英)沃爾特·厄爾曼:《中世紀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
(美)布魯斯·L. 雪萊:《基督教會史》,劉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德)畢爾麥爾等編著:《中世紀教會史》,(奧)雷立柏譯,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英)愛德華·伯曼:《宗教裁判所——異端之錘》,何開松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俄)C.H.布爾加科夫:《東正教——教會學說概要》,徐鳳林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
(英)約翰?麥克曼勒斯主編:《牛津基督教史(插圖本)》,張景龍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美)威利斯頓?沃爾克:《基督教會史》,孫善玲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李隆國:《從羅馬帝國到神圣的羅馬帝國:3—9世紀的歐洲政治與政治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
李筠:《中世紀:權力、信仰和現代世界的孕育》,岳麓書社,2023年。
王立銘:《王立銘進化論講義》,新星出版社,2023年。
陳志強:《拜占庭文明》,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
閻守誠:《閻宗臨傳》,三晉出版社,2014年。
王亞平:《西歐中世紀社會中的基督教教會》,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樂峰:《東正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李騰:《秩序重構下的11—12世紀歐洲政教之爭》,《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
張日元:《試析1054年教會大分裂之因》,《歷史教學問題》,2020年第5期。
李騰:《禮儀分歧與政治博弈的糾葛——重回1054年大分裂的歷史現場》,《基督教學術》,第二十輯,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
趙林:《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的盛衰轉化——從東西方教會大分裂到西方教會大分裂》,《學習與探索》,2015年第6期。
楊宏偉:《中世紀早期基督教會對世俗武力的規范》,《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Chadwick, Henry. East and West: The Making of a Rift in the Church From Apostolic Times Until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Whalen, Brett. "Rethinking the Schism of 1054: Authority, Heresy, and the Latin Rite." Traditio , vol. 62, 2007, pp. 1-24.
Saint Gregory the Great Collection , Aetern Press, 2016.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