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紀念沈渭濱︱沈渭濱先生與新修《清史》
2025年4月12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召開紀念沈渭濱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談會,本次座談會也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科創建100周年紀念活動之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參加座談會的部分發言稿和提交座談會的交流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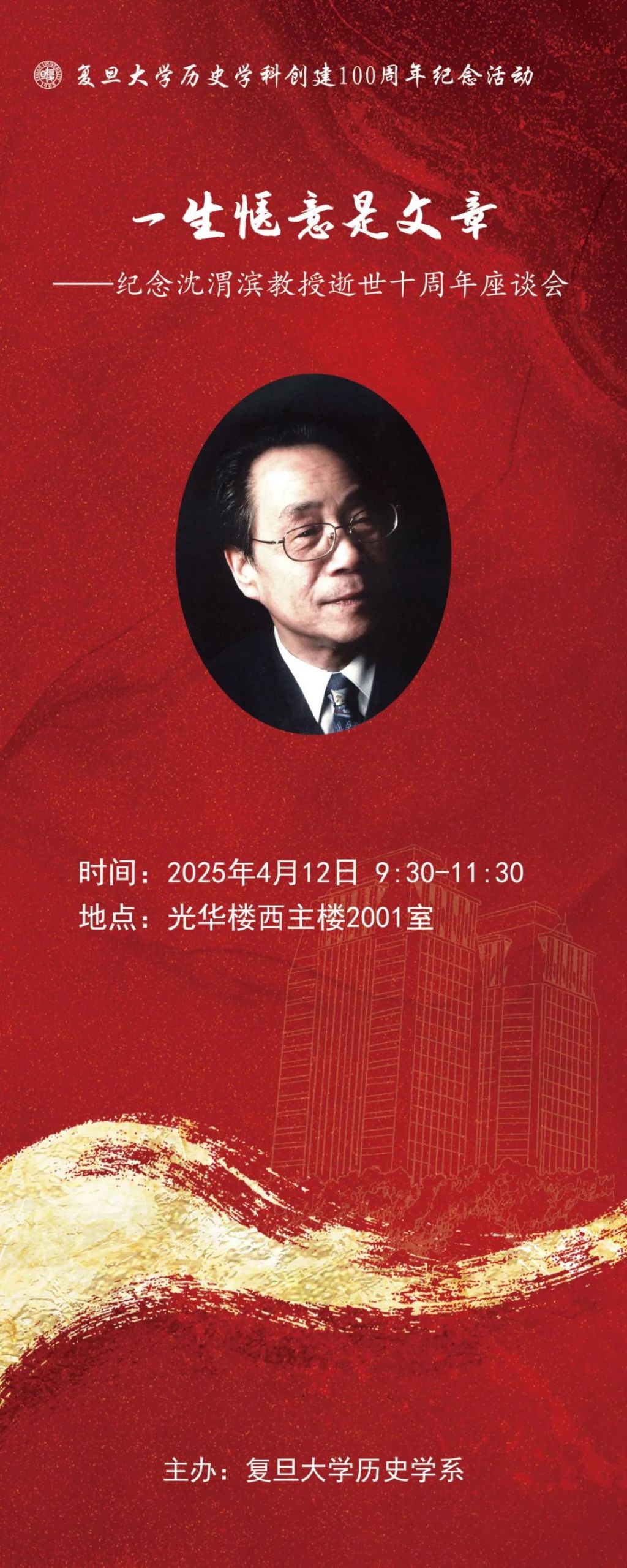
一生愜意是文章——紀念沈渭濱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談會
2006年2月19日,先生開始撰寫新修《清史》“傳記·光緒朝(上)”人物傳記,第一個為崇厚,“以《清代人物傳稿》所載該傳為超越對象”,一個上午“僅得三百余字”。2月24日,“上午仍寫崇厚,字斟句酌,極費神思,知正史人物傳寫作之不易。昔清史傳記作者,俱桐城派大家,今之作者不能望其項背,將來書稿質量真難得保證也”。3月1日,“仍寫崇厚,多日來僅得千余字,反復修改,至今未成篇,頗焦急”。3月11日,“仍寫崇厚,至傍晚僅得五百余字,可嘆”。3月22日,“崇厚傳寫竟,約三千二百余字,此文……前后約一月始完成。寫得極為艱難,蓋首次寫清史人物傳,要求高,無經驗故也”。開始撰稿以來,雖不斷有各種事務摻雜其間,耽誤時日甚多,但與先生平日寫論文胸有成竹“一氣呵成”差異極大,對傳主角色的整體把握反復思量,遣詞造句力求準確精當,如此精心撰稿,“崇厚傳”上交后被列入樣稿選編,成為傳記撰寫樣本。
作為“會通型”中國近代史史家,先生對新修《清史》的編纂有全局性的思考,發表《清史編纂體裁體例之我見》;對“通紀”的撰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持“傳記·光緒朝(上)”項目,具體實踐“傳記”撰寫,自然有更深刻的體念與感受。
一、“清史編纂體裁體例”的思考與建議
2003年3月中旬,清史編委會致電先生,邀請出席4月6日在上海舉行的南方各省市“清史編纂體裁體例學術座談會”。由此,他開始思考清史“編纂體裁體例”,以為“纂修清史一事,本為循盛世修志、隔代修史傳統。民初所修僅是《清史稿》而已,稿非史,且《清史稿》錯訛甚多,必須重修。故當前重修清史,并非置《清史稿》而不顧,另編與廿四史體裁迥異之新史,應在《清史稿》基礎上經改良、考訂后編纂出一部與廿四史大體相當即以紀、傳、表、志為主要體裁之清史”。以此為基礎,他撰寫《清史纂修體裁體例之我見》,到4月2日夜十點殺青,約一萬一千字,“寫竟心頭為之一寬”。文章后發表在《復旦學報》當年第4期。
先生以為新修清史指導思想,“其大要應是實事求是、排除意識形態成見,正確厘清史實、不求處處發現規律,不臧否人物、不評騭史事,文字簡潔、務去陳言。簡言之,以保存史料、講清史實為指歸”。對于這一“指導思想”,在文章中僅就“評騭史事、臧否人物”有所申述,“眾人修史,評騭議論焉能一致,褒貶臧否出諸誰口?所議所評,隨星轉斗移往往會今是而昨非,焉能保證經得起時間檢驗?”在日記中對發現“歷史規律”更有申論:
傳統正史,本意在存史實,序教化,求資治而不在尋規律、窺趨勢,作詮釋演變因果之探求,此皆號稱歷史學家之為者也。故任何一部正史,均不具今人所謂研究性(學術性)專著之功能,今人完全不必因其大勢難貫而苛求之,何況以目前現有之水平,誰能保證敘述演進大勢詮釋內在聯系經得住歷史檢驗?
“紀”是全書之綱,在《清史稿》“本紀”外,先生建議增加“別紀”記述南明諸王及太平天國洪秀全等。如此“既可破除以清皇朝為正統之觀念,又示新纂《清史》不僅為皇朝史,而且為清代史”。具體撰寫過程中,以編年為線索,吸收“本末體”寫法,即先賢所謂“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避免“大事不貫、支離破碎”。若使用得當,“定可超邁前人,獨樹一幟于二十四史之林”。
“志”“記朝章國典及國計民生攸關之事”,清代制度變遷損益較前朝劇烈,故應“破舊立新,因事設置”,在《清史稿》16篇基礎上新增憲政、學校、湖泊、租界、民族、宗教等六志。新設各“志”有的分割原有相關“志”內容擴充而成(如《憲政志》以《清史稿·選舉志》中“新選舉”為基礎,設考察憲政、預備立憲、咨議局、自治團體、資政院、國會請愿、皇族內閣等篇目),有的完全是因應新事務而新設(如《租界志》),有的補充《清史稿》缺陷(如《民族志》《宗教志》)。當然,原有各志內容也非一成不變,如《天文志》需以現代天文學知識撰寫,《食貨志》增加農業、手工業、機器工業等,“加上原有各目,合成有清一代經濟專史”。
表“以系時事,而以大事年表列入,以補傳記大事不貫之缺憾,另附地圖及相關圖片”。先生設計的新修清史刪去《清史稿》10表中的《皇子世表》《公主表》,新增《清代人口統計》《清代田地田賦統計》《清代關稅、厘金歷年收入統計》《清代歷年財政收支統計》《鴉片進口歷年統計》《歷年所設商埠、租界、租借地表》《歷年所訂中外約章表》《歷年所借外債統計表》等8表。另外,《清代大事年表》作為全書附錄,不列入“表”部。
《清史稿》人物傳記以“分類相從”編排,在15類中(其中大多數人物被聚為一類,未擬目,先生定名為“臣僚”)“最易招物議者為‘循吏’和‘忠義’”,都屬于“臣僚”,“析出另立,既體現編者以清王朝為正統別忠奸之價值觀,又反映編者以維護清王朝長治久安為確定臣僚良善與否之標準”,因而先生建議廢除此兩目,統編入“臣僚”中。原“儒林”“文苑”“雖術有專攻,但細分并無必要”,合并為“文儒”。同時將“臣僚”改稱“政事”,因需增加南明王朝、太平天國、革命黨和立憲人物,他們均非“臣僚”。這樣,列傳分設后妃、諸王、政事、文儒、疇人、遺逸、藝術、孝義、烈女、土司、藩部、屬國等12類。
新修清史既然是二十四史續編,“則其文體宜用簡易文言為好”,一可“省篇幅”,二“可與前史相銜接”,“尤其與使用資料之文體相一致”,以免現代漢語史書“敘事之語體與資料文體上”的不一致,全書控制在70冊二千萬字上下。
當然,這僅僅是先生對新修清史體裁體例的總體思考與建議,屬一家之言。新修清史最終分為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五個部分,其中“通紀”屬于本紀的變體,有先生所言“求歷史發展規律”的期許與欲求。對此,他曾在“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通紀編寫專題討論會”“通紀大綱研討會”兩次會議上有進一步論說。“通紀編寫專題討論會”發言最終整理為《清史纂修與太平天國的歷史地位——對〈清史·通記〉纂修的幾點意見》,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先生以為“《通紀》是新纂清史中不同于以往二十四史中的創新體裁”,“無成例可按”。現有提綱將太平天國置于清史框架,避免寫成太平天國專史,“體現了新編清史不同于以往王朝史的特點,肯定了農民戰爭的歷史地位”,但從提綱看,“太平天國成了這一卷的主體”。太平天國雖是一個政權,但無論如何僅僅屬于清王朝統治下的“武裝割據”,不能成為這一時期通紀的主體。也就是說,太平天國可以成為“本卷核心內容之一”,但“不應該因此而將清王朝的鎮壓、應對及統治體制的變化等諸多歷史事實輕描淡寫, 作為非核心內容帶過”。
“通紀大綱研討會”上先生兩次發言,第一次說:
余初表示不贊成通紀體裁,現讀大綱感覺基本以時序為經,以史事為維,以政治史為主線,旁及社會、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實為通史之通,基本可以,但需調整,如太平天國、辛亥革命二篇,不以清王朝為主體,太像近代史,似不妥。至于如何使通紀作為志、傳、典、表各部銜接,可作專題之通,如典章制度之通、學術文化之通、興亡治亂之通等等,也可以皇朝各代設卷,避免因設篇引起交叉混亂。
第二次發言認為“通紀”之“通”,“其要求有兩點,一為以大事敘其趨勢,一為以思辨論其義理”。現有大綱“敘其趨勢已基本符合要求,以思辨論其義理,以‘洋務運動篇’為好,晚清其他各篇似開局不夠大氣,思辨不足”。
當然,因新修清史變“本紀”為“通紀”,皇帝進入“列傳”,先生在具體寫作光緒傳時對這一變化也有思考:
新編《清史》,廢帝王本紀,將其列于傳記,以示改革,竊以為不妥。本紀為史志正體,源遠流長……紀傳體例不同,書法各有規則,廢紀入傳,寫作頗難。光緒傳之遲遲不能歇手,與此不無關系……又新編《清史》有“通紀”,亦為以往正史所無,屬創新一例……其實“通紀”一如清代史,屬通史之體,原不應列入分部編纂組合而成之正史史體。通紀以觀點、思想、史觀為串線,自不免有所品評分析,難免隨時間轉移而有偏差,則與正史之“述而不作”相背,又與新編《清史》之其他體例不合,焉能匯為一書?
二、主持“傳記·光緒朝(上)”項目
先生雖對新編清史編纂體裁體例有所議論,但并沒有參與這一“隔代修史”“大業”意愿。2004年2月,前輩中央民族大學郭毅生先生來電邀請參加“清史考異”項目,先生以“不參加清史之初衷告”(他私下曾對楊國強老師說,“余已望七,何必與朝陽旭日者爭此短長”)。但考慮到郭系前輩,“師友之命不可卻,答應為考異稍盡綿力”,允諾推薦學者參與,并擬定了考異選題供郭先生參考。后來也曾參與不少相關評審工作,如評審傳記標書,審讀傳記樣稿(認為相較《清史稿》《清史列傳》,“內容過簡,主次欠妥,時間模糊,文字不統一,兩書中可用者不采,長編中可用資料不入正文”),為某“表”寫出共7頁“蠅頭小楷”評審意見等等。
對于是否承擔“傳記·光緒朝(上)”項目,先生也很躊躇,曾分析得失,若承擔“任務頗重,壓力亦大,曠日費時,成功難料。且手中兩書,勢難完成。若改易他人……當可安排自如,無精神負擔也。利弊得失,似以后者為好”。當時,他正承擔復旦大學“金秋計劃”《道光十九年》和出版社約稿《細說慈禧》的撰寫,同時正思考相關“三民主義”多篇論文(后發表三篇,影響甚大,皆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經多方考慮后,他最終還是決定擔任項目主持人,并于2005年5月立項。
作為項目負責人,首要任務是組織項目組。項目組成員的構成(他們是否尊崇學術、是否認真負責、盡心盡力)對項目能否順利完成具有極端重要性,先生對此深有體會,其間甘苦實在是一言難盡。他曾告知好友張一文(張負責“兵志”項目,2007年啟動),項目的完成“主要在慎選團隊成員”。當一位成員突然提出退出時,先生始而驚愕,最終只得“允其所請,何人取代,矛盾彷徨兼而有之,夜不成眠哉,苦也”。第二天電話王立誠老師,“竟一口答應,喜出望外,如獲救星”。項目組最終由謝世誠、戴鞍鋼、王立誠、廖大偉和我(2009年中途加入)組成,其中謝世誠教授“最下功夫”,特別是他完成自己任務之外,臨時負責另外9人,完成了122人中34人傳記的撰寫,因此一再被先生感激,“余清史團隊中,以世誠最為認真、誠樸,深為欽佩”。
組成項目組后,請各組員提出各負責部分名單,對“傳記組”擬定名單與人物等級予以調整。最終經討論,在傳記組設計的119人(含附傳1人)基礎上,新增附傳3人,即馮子材附王孝祺、蘇元春附馬盛治、何啟附胡禮垣。王孝祺、馬盛治《清史稿》有附傳,且在中法戰爭中均有戰績;胡禮垣在西學介紹中,與何啟多有合作,雖資料太少,難以單獨成傳,可列為附傳。人物等級方面,共有15人變動,先生向傳記組的報告中對每個人物的等級變動都有詳細的理由,如光緒帝原定丙級,“此人歷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維新等諸大事,比之同治帝乃至咸豐帝,多有作為。雖戊戌政變后被幽禁,但帝位未廢,號令仍以上諭發出,且《清史稿》‘本紀’分上下兩篇……若以丙級立傳,區區三千字勢難寫明此人經歷”,建議升為乙級。原定丁日昌乙級、沈葆楨丙級,丁日昌“歷事與沈葆楨相比,似覺稍簡,以其地位與沈氏相較,則遠不如沈”,“建議兩人等級對調”。禮親王世鐸與奕譞同為丙級,世鐸“雖居軍機大臣十三年,但……一生碌碌無為,地位遠在奕譞之下”,在《清史稿》中僅為代善附傳,建議降為丁級。此外,張曜、吳長慶、文煜由丁級升為丙級,曾紀澤由乙級降為丙級,載齡、許庚身、徐用儀、吳贊成、汪鳴鑾、倪文蔚、徐邦道等由丙級降為丁級。
考慮到項目組成員多是中國近代史學者,對晚清史缺乏深入研究,對所撰寫晚清人物缺乏了解,先生約請部分成員勘查《清史稿·傳記》、沈云龍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三編、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1-5冊)、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上下)、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1-20冊)、戴逸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1-10卷)、《清碑傳合集》1-5冊、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恒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下卷)等,尋找相關人物年譜、文集、日記等,編成122人基本資料索引,列出書目、頁碼等,于2005年9月打印分發。有此資料基礎,成員對所撰人物有概貌性的了解與理解,基本克服了項目啟動初期對傳主資料生疏、無從措手的困難。編制索引過程中,先生某天早上刷牙,發覺右面頰、右邊嘴舌有麻木感,“疑有面癱之嫌”,“估計近二月來為寫論文、接手清史、普查人物,太過勞累所致”,提醒自己“年屆七旬,應以節勞為好”。
相比這些基礎性工作,對撰稿質量的把控、督促成員按期交稿更為重要。項目正式啟動之初,就召開組會,分析討論“傳記組”提供的樣稿,要求資料長編“必得錄自原始資料,正確翔實”,正文“注意制度上不得有硬傷,必須有注釋,年月日絕對正確,措辭正確,不做評論”。項目組首批提交11篇傳記僅5篇審查通過,先生所寫崇厚傳作為樣稿入選《傳記選編》,他仔細閱讀發現“選編稿”與原稿有幾處修改,“細讀之,體悟改稿本意益深,為今后寫、改均有裨益”。得到審查意見后召開組會,“就傳記組對崇厚一稿修改處逐句解析”,并將修改稿復印分發,作為成員寫稿、改稿參考,約定修改稿及后續稿件提交時間。
此后,催稿與撰稿質量成為先生“日常”的不安與憂慮。2006年12月21日,“團隊無人按約交稿,為此事常心緒不寧”。第二批交稿經審查僅兩篇“尚可”,2007年1月20日召開組會,傳達北京意見,“總體情況不好,頗為憂慮”。4月9日,向團隊成員催稿,結果不理想,“距北京要求太遠,憂甚”。5月23日,“吾組上交傳文率據中下水平”。5月30日,“近日為清史傳記交付數量不足,質量又差,頗多憂慮,血壓升高,自在情理之中”。最終因交稿不及時,第三期經費被停付。對于項目進展如此緩慢,先生慚愧不已,“余一生辦事從不爽約,重諾如命,不意在清史寫作中,陷此泥潭,愧疚良深”;“清史傳記一事,遲遲不能完成,令余愧疚不已。半世認真負責之譽,毀于此,痛心之極,大有何必當初之嘆”。當然,面對北京的一再催促,他也有另一角度的思考,“北京方面交稿時間鐵定,然團隊人員自身任務繁重,無空為清史寫作,即使交卷亦質量欠佳,只求進度顯然不合理,真擔憂此書質量”;“北京只扣進度,不解決作者時間,質量何能保證”;“北京只見進度,又不創造條件,文稿質量堪憂焉”。這種催稿、交稿、質量要求的“心緒不寧”“憂慮”一直持續。2009年9月,傳記組到上海召開項目組會議,約定各人交稿時間,“戲稱軍令狀”,“群情振奮,可謂快事,余以往憂慮消失大半,初稿完成可期矣”。但組員大多并沒有踐諾,先生陷入繼續催稿狀態,直到翌年年中初稿大部完成轉入修改階段,才得以緩解。
作為項目主持人,先生也參加“傳記組”工作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2005年10月福建會議,談及原來的中國近代史專家轉入清史領域后,學術觀念要有所轉變,史料掌握也要有新的開始,并提出傳記標準:第一,不可有硬傷,必須準確;第二,主要事跡不能遺漏;第三,人物特點寫清寫確;第四,文字雅馴。2008年4月傳記組工作會議,先生就進度、資料、經費三點發言,其中指出“進度應以寫作初稿為第一要義”,資料“不應過分注重事事均要由原始資料而來,應對前人研究成果予以重視”。先生就光緒帝等級調整報告曾稱:“因新編《清史》有《通紀》,將來光緒傳如何與之銜接,是一大難點。其傳文寫什么?全寫還是重點寫,哪些寫,哪些不寫,均是問題。其實,十代皇帝傳均有此問題,建議傳記組開專題討論會統一規范。”2008年7月,“皇帝傳”會議在大連召開,先生與會提交光緒帝大綱,聽報告后“頗有啟發”,專家談及清史各組溝通不夠,將來相互矛盾重復等難以處理,“頗為中的”。
三、撰寫慈禧太后、光緒帝等17人傳記
項目組最初分工時,先生承擔皇帝載湉,王公奕譞、世鐸,部院大臣皁保、丁日昌、吳贊誠、周家楣、延煦、鄧承修、賀壽慈、祁世長、崇厚、沈秉成、崇綺、張佩綸、汪鳴鑾,督撫沈葆楨、張樹聲、劉長佑,軍事將領吳長慶共20人傳記撰寫。具體撰稿過程中,奕譞傳由臺灣學者王明燦(其博士論文《奕譞研究》)撰寫,張佩綸、沈葆楨由姜鳴師兄負責,劉長佑由謝世誠教授擔任,最終先生撰寫了項目組16人傳記。項目進行過程中,發現無論是“光緒朝(上)”還是“光緒朝(下)”都沒有“慈禧太后”,傳記組最終委托先生項目結束后撰寫。
具體撰稿過程中,先生為準確定位傳主與遣詞造句的準確,極費思量,推倒重來也屢見不鮮。2006年3月26日開始寫第二個人物鄧承修。29日全天傾力貫注,“至晚飯前,僅得六百余字,字斟句酌,頗不易也”。到4月10日,至夜已得約四千余字,“仍有談判邊界未寫,估計需五千余字,超過丙條多矣。益體會《清史稿》之取舍了得,新編清史難能及此,可謂堪憂者也”。翌日,大體寫就,“都四千余字,擬明日刪修之”。12日全日修改,“至傍晚始擱筆”。15日繼續修改,“改定后不計注釋,約三千六百余字,仍超過丙條三千字規定。益見《清史稿》鄧傳撰寫者概述精到,其將鄧之參劾統寫,不分時間,而突出其修約活動,輕重得宜,真大家手筆也”。21日謄抄完畢,正文約3300字。至此,鄧承修傳記完成。從3月26日到4月21日,丙條鄧承修傳記耗費時日也近一月之久。第二年還根據新修長編繼續修改,最終字數約3100字。
丁日昌傳記的寫作,更因資料與定位、如何剪裁與措辭極耗時間與精力。2009年5月21日開始寫,到6月10日,幾乎天天寫,因長編缺丁日昌“撫吳奏稿內容”無法撰文而擱筆。11月5日重啟,長編“質量頗差,缺漏不少”。11月12日,讀已寫之丁日昌傳,“覺過細過繁,決定推倒重寫”。12月16日繼續,因丁日昌“撫蘇一節,事多人雜,難以選擇概括、梳理得宜,連日寫而又改,改而又寫,毫無進展,煩躁不已,寫至四時半,仍在原處徘徊”。直到12月24日,“撫蘇部分,總算理順”,由此“漸覺順手”。2010年1月9日,丁日昌傳終于完成約3400字,超過丙條規定字數,“已無可再刪,乃定稿”。此傳重新開始撰稿以來,也前后費時超過二月,“反復多次,至今可謂心緒一寬”。與丁日昌傳撰寫同樣遷延時間極長的還有皁保傳。2008年5月14日開始寫,6月4日全天“僅得五六百字”,“進度甚慢”“憂甚”。11月18日繼續寫,“精力無法集中,蓋喘咳自上周四起,晝夜不止,難以成眠”。直到12月11日,才寫成約二千字傳稿,“此傳曠日持久,至此完成,心為之一寬”。為進一步完善,此后查閱翁同龢日記中相關皁保的資料。
當然,也有撰稿較為順利而暢達的,祁世長傳稿雖“資料不全,其中法和議時奏折難以確定時間,故行文反復重寫,極費周折”,但僅十天就完成。崇綺傳寫10天,汪鳴鑾傳費時5天,賀壽慈傳最短4天告成。即使如此,先生對傳記撰寫的不易還是時刻保持警惕,并一直持極為謹慎的態度。沈秉成傳成稿約1800字,“以區區之篇幅,前后一周寫竟,足見清史傳記寫作之不易也”。撰寫過程中,先生對資料的全面性要求極高。我為先生所做世鐸資料長編資料僅《清實錄》一種,他看后頗失望,囑咐我“勿專錄《清實錄》為滿足,應擴大搜索面如日記、方志、文集、書信等”。無奈之余他自行尋找《翁同龢日記》中相關資料,撰稿中對世鐸有新認識:“昔以為世鐸無多內容可寫,不意此公立言頗多,寫至光緒五年已近千二百字,若寫至其謝世,丁條二千字將大為超額。”對一些疑點與傳聞,先生予以充分查考辯證,不輕易下筆。“為查證平定朝鮮壬午兵變后,吳長慶、張樹聲與李鴻章矛盾,瀏覽劉厚生著《張謇傳》、苑書義著《李鴻章傳》、謝世誠著《李鴻章評傳》、雷頤著《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諸書,不得確證”。最終以《張謇日記》為基礎,表述為“長慶奉北洋大臣李鴻章命,回天津述職。‘李相欲以慶軍屬馬建忠’,長慶知忌,遂有辭意,經勸乃罷”。
相比上述人物而言,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傳記的撰稿更為繁復。2009年3月28日開始寫光緒傳,“至下午四時半擱筆,得六百余字”。30日“為明了其入學后所學課程,查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年至九年各卷,費時費神,幾及一上午”。4月2日,“頭暈目眩,精力不濟,遂擱筆”。讀《清代人物傳稿》中祁龍威、楊國楨、龔書鐸、苑書義諸教授所撰晚清人物傳,“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頗有所悟”。此后因其他事務,斷斷續續,8月8日全日寫光緒傳,“反復甚多,進展不大,郁悶異常,帝王傳記之難寫,深有體會”。此后因寫其他人傳記等停止。翌年3月23日再次拾起,“改寫已成千余字之光緒傳”。此后連續“作戰”,5月6日通讀光緒傳已寫部分,“字數竟超過八千字,則全傳當在萬字以上,太長,需刪削,擬寫完后再改”。5月16日,初稿終于撰成,近九千字,遠超規定字數,“已無力削減,蓋邊寫邊刪,無從再改矣”。5月22日,修改謄清光緒傳,約7500字,“仍嫌過長,已無可再刪矣。留待高手為之”。
先生對慈禧很早就有研究興趣,幾十年來斷斷續續搜羅史料,并有全局性思考,2007年出版階段性研究成果《晚清女主——細說慈禧》。傳記組委托他撰寫慈禧傳,可謂選擇得人,他自己也曾以為“非余莫屬”。接受任務后,他開始熟悉資料,為正式撰寫做準備,如2010年6月28日,讀《清史稿》同治、光緒“本紀”,“為寫慈禧傳留一印象”;2012年2月7日,為撰寫慈禧重讀相關史料、論著。2012年9月2日,開始正式撰稿。其間,“因頭緒紛繁,寫了又改,改而再寫,至今進度緩慢,焦慮日甚”;稿件“冗長、繁瑣,雖反復精簡,曠日持久,進如蝸牛,然仍未能如意。蓋帝后傳應如何寫,未有把握也”。后因評審通紀第七卷撰稿中斷,直到第二年3月5日,讀以前所寫慈禧傳,“覺冗長繁瑣”,由此進入慈禧傳繼續撰寫狀態。到3月9日,將以前所寫16頁刪削完成至11頁。第二天從同治之死入手新寫,但“查資料、理頭緒,一時竟無從下手”。其后撰稿仍然非常不順利,“連日均在光緒初年史事剪裁布局上徘徊反復,曠日費神,無所進展,甚悶”;“徘徊于光緒十二年,無大進展,甚郁悶”。到6月24日,寫到戊戌政變,已超過二萬字,“此傳曠日費時,查史料,核注釋,思措辭,辨字句,在在頗費斟酌,每天僅寫五六百字。進度遲緩,費心勞神,甘苦自知”。7月8日,全稿終于完成,約三萬字,“自知字數太多,僅是長編,將來供傳記組刪改”。自3月5日第二次全身心投入撰稿到7月8日完成,也已超過4個月,習慣居然成自然了,“因習慣于整天寫慈禧傳,一旦歇手,竟手足無措,茫然若失”。先生撰稿投入程度可以想見。
四、結項及評審通紀第七卷
自2010年7月開始,根據傳記組的要求,先生開始修改各成員撰稿,大多數稿件修改很順利,但也有些傳記問題不少。如衛汝貴定位不準確,需要重寫;馬盛治“傳文過簡”,比《清史稿》篇幅還少,“若干經歷缺失,建議重寫或增補”;靈桂傳字數過少,“履歷太細碎,事功言論不具載,刪繁就簡外,增加事功立言,力圖改變原稿臉譜式書法,修改進度緩慢”。全力改稿的同時,應出版社增訂《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身體警報頻傳,但他并不在意。“年老體衰,疾病成堆,高血壓、糖尿病、前列腺肥大、內外痔、便秘叢集一身,全憑意志力硬撐,一旦轉為惡疾,恐難保無可藥救。目前務必集中全力,完成清史工程,以踐諾言”;“近來耳鳴乏力,頭暈眼花……本擬延醫調理,奈因清史改稿近于百米沖刺,自著忙于修訂,既無心又無力它顧,只得聽之任之,挨到明年兩者脫手再說”。最終病魔不期而至,2011年10月9日,到上海大學延長路校區演講,出現步履不穩、略微顫抖,后在瑞金醫院確診為“急性腦梗,輕度偏癱”,由此入院治療,停止一切學術活動。
患病以后,先生奉行封筆、封鏡、封講三封原則,但終日無所事事,“極感無聊,為活而活,實在毫無意義且極不習慣”。對于這種“學人而不治學”,“每日以散步、吃藥、打針為主,不敢讀書、筆耕”的生活,“心猶未甘”,決定從2012年2月開始“從整理舊稿入手,恢復寫作、讀書、思考”生活。繼續修改傳稿,何如璋傳“資料不豐富,但行文甚好”;王韜傳“資料豐富,然行文過于細碎繁瑣”,“為之增刪修潤”。同時開始撰寫結項報告。8月,結項報告修改完成,清史項目“終于接近收尾,此中甘苦,非局外人可知”,除項目組成員外,更對傳記組學術聯絡人馬忠文在寫稿、組稿、審稿、統稿中“竭誠相助,全力扶持”感謝不盡。11月24日召開項目組會議,“終以公正、公平、公開圓滿結束,向各位致謝,宣布項目組到此結束”。
項目結束后,除繼續撰稿慈禧傳外,先生還接受通紀組委托評審楊國強老師主持的通紀第七卷。對此評審工作,先生起始就向通紀組提出其工作原則:“只能糾正明顯筆誤及提出某處修改意見,不能改正正文。一是作者以思辨統貫全卷,且文風獨特,別人改動,既牽一發動全身,將傷及全卷思想體系及文風。自己已年老體衰,交稿時間緊迫,力所不逮,只能提出意見供作者自改”。2012年12月3日開始評閱,到翌年2月26日完成,“歷時三月之艱辛,總算完成,渾身一輕”。其間,有充分的贊賞,也有恰如其分的建議:“敘法國侵越,中法交涉,頗條例清晰,說理有度”;“覲見禮儀之爭,縱論英使馬嘎爾尼至咸同年間中外糾結,堪稱通達,派外使節以郭嵩燾為議論重點亦屬得當,若能將清廷由此與西方溝通,由夷務而為洋務之觀念轉變稍為申說,則更深刻”;“新疆及臺灣建省”“說理透徹,過程清楚,為它書所不見,堪稱獨識。然對劉銘傳在臺之經營稍加申述,更能知建省系實有基礎”;“述清流之輿論興起有獨到識見,但若進而指出清流中張佩綸、陳寶琛等不僅熟諳洋務,且與李鴻章私相交接。所謂分化,僅屬政見不同,敢于直聲而已,并非反洋務自強之需耳”;等等。最終提交了長達29頁的“審讀隨記”和4000字左右的評審鑒定書,“自詡如吾之認真者恐不多哉也”。評審得到了清史編委會的一致好評。
清史項目進行過程中,先生曾發愿得此機會認真讀書,“近年雜事太多,靜不下心來讀書。惟有產出,長此以往,良可嗟嘆。擬利用寫清史人物傳之際,認真讀書,俾得長進”。更計劃項目結束后,“靜心讀書,先從史部入手,每讀一史作札記,若天假以壽,再讀子書,不求專,惟求通達,冀提高識見,以明事理”。可見先生對學術無止境的追求與本其一生的“通達”愿景,惜乎老天未能給予他更長的時日與更多的機會。
2005年3月12日,先生剛剛應許擔任清史項目主持人,卻不斷接到師友噩耗,當日在日記哀悼“故舊漸見遠行,豈不痛哉!新年噩耗不斷,極為掃興”,更有期許與愿望,“希望老天假吾十年,完成清史傳記再走,當可了卻心愿,無憾矣”。可謂一語成讖,為清史勞心勞力、費盡心血,因而極大損傷身體的先生,真的在十年后的2015年4月18日“走”了!十年后閱讀先生日記中相關新修清史的記載,思量他對新修清史的貢獻,再次感念他對學術的純粹追求、過早離去未能完成《慈禧大傳》與《陳旭麓先生傳》等學術計劃的遺憾,能不痛哉!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