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魚翅與花椒》:被川菜迷住的英國姑娘,寫了本中國美食書
我們中間有幾個膽子比較大的,比如從海參崴來的薩沙和帕夏,會熱情地跟他打招呼,想跟他聊天,或者講個笑話,一心想讓他笑一笑,但他還是一張冰塊臉,完全面無表情,不動聲色,只是和往常一樣問道:「啥子面?」
——「魚翅與花椒」
這是英國女作家扶霞·鄧洛普書中的成都擔擔面老板——謝老板。
謝老板在四川大學外面開了一家面館,玻璃櫥柜里的紅油、花椒面兒、蔥花、醬油、醋、鹽和胡椒,引誘著往來的好吃嘴。一口擔擔面下肚,可謂是「非常有效的醒神藥,簡直救命」。
1992年,從事亞太地區新聞報道助理編輯的扶霞來到中國,本意是研究少數民族歷史,卻在途徑成都時愛上川菜。她留在四川大學學習,并成為當年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第一位外國學徒。

我通過漢語老師認識了一位研究烹飪史的學者,人很好,邀請我出去吃火鍋,然后點了一大盤很貴的豬腦花,說是專門給我吃。他用小漏勺把腦花放進咕嘟冒泡的湯底,煮熟了倒進我的味碟中。
——「魚翅與花椒」
初來中國時,扶霞和大多數老外一樣,對「狂野」的中國菜敬而遠之。而這一次,每當扶霞想「調虎離山」地處理掉腦花時,對方總會往她碗里再添加一點,幾個回合下來,扶霞敗下陣來。
她心一橫、眼一閉,張口就吃了,「那口感像奶凍,柔軟綿密,又很有豐富的層次,真是危險的誘惑」。


川菜大廚十分擅長組合多種基本味,創造出勾人魂魄的復合味。……先是用適量的紅油喚醒味蕾,再用麻酥酥的花椒調動唇舌,辣辣的甜味是對味覺的愛撫親吻,干炒的辣椒也在對你放電,酸甜味又使你得到安撫,再來一口滋補的濃湯,真是過山車般驚險刺激的體驗啊。
——「魚翅與花椒」
扶霞最喜歡的一道川菜是魚香茄子,她在書中第一章末尾就迫不及待分享了魚香茄子的食譜,「如果一生只能選擇吃一道菜,那一定是魚香茄子」。
魚香味是川菜中非常經典的復合味,調位方法來自于傳統川菜中的魚類料理,咸、甜、酸、辣,蔥姜蒜的香味充分融合,多層次、多方位地調動和刺激味覺,「稱得上是世界上最不可抵抗的復合味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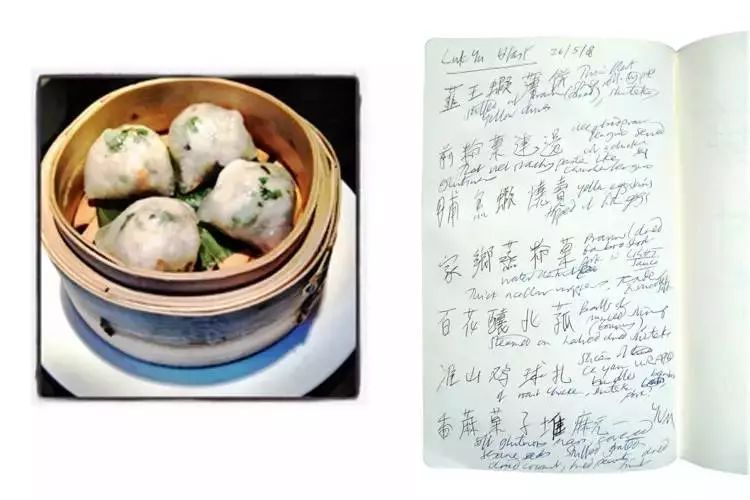
九十年代中期的成都接近了扶霞多年的夙愿:回歸到烹飪的基本,沒有捷徑,無法偷懶。小街巷中的人家還在使用幾百年歷史的方法來儲存食物,晌晴天氣時,家家戶戶在細細彎彎的繩子上掛滿青菜葉,曬到半干才能取下來,揉進鹽和香料,放進密封罐子里發酵。窗欞上整整齊齊地晾著陳皮,皺巴巴、硬邦邦的,深吸一口氣仍有提神的桔子香味。

太平上街是她特別喜歡的街,順著錦江南岸延伸,當最后一座房子快要拆完的時候,她偷了一塊寫有街名的門牌,如今掛在倫敦的公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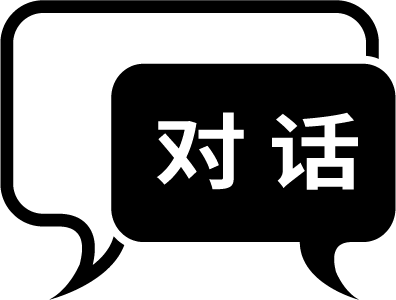
答:魚翅和花椒都是中國人會吃的、很特別的東西,魚翅很珍貴,但對西方人來說卻很詭異,花椒在當年也是沒什么人知道的四川香料,用這兩種食物來表達我在中國與眾不同的餐飲體驗。這里要申明我沒有宣傳吃魚翅的意思,書中有部分內容是將飲食對大自然的影響,這只是一個話題,而不是讓大家去吃魚翅。
問:你在書中也提到了中餐和西餐文化中存在很多誤解,你如何理解這種跨文化交流?
答: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人對西餐了解很少。我曾碰到一個年輕的廚師,他當時用很隨意的語氣說「不喜歡西餐」,我有點驚訝他居然吃過,結果他說「我吃過一次肯德基,簡直太難吃了」。
旅居中國多年,我的口味已經發生了變化。跨文化交流必然是好事,當你在另一種文化中待太久,它就會改變你,最大的影響就是你很難客觀或單純地看待世界了,它會讓你從其他角度看問題,而不是偏執地認為自己是對的。
問:你在后記中寫到一只菜蟲,與中餐文化接觸多年,飲食習慣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答:我喜歡中餐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國人特別智慧,你們懂得如何根據時令節氣,吃得健康,西餐很難做到這一點。所以現在我更愿意吃中餐,甚至在吃西餐的時候都會情不自禁地批判:肉太多蔬菜太少,怎么連湯都沒有,太上火了!
問:這本書在海外影響力如何?是否糾正了既有陳見?
答:這本書在英國和美國都得了獎,評價還行。這本書可能修正了某些偏見,但我覺得更多的是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大家有很多機會接觸不同飲食文化,減少了誤會。

何雨珈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