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澎湃思想周報|美國科技巨頭共謀反移民行動;法國生態農運史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政府實施一系列針對移民的措施,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開始陷入緊張情緒。據《紐約時報》今年3月的報道稱,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對來自43個國家的公民實施旅行限制。越來越多的移民開始擔心自己將受到不斷變化的簽證政策和反移民言論的影響。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5日,美國紐約市,抗議者集會要求廢除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并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自特朗普上任以來,便承諾進行大規模驅逐,并著手準備相關的基礎設施:包括確保關塔那摩灣的拘留能力,甚至考慮讓薩爾瓦多接收一些被逐出美國的人員;在數據方面,允許政府獲取大量個人數據,并與私營公司簽訂合同,以支持大規模抓捕。最近幾周,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下稱ICE)甚至開始逮捕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及合法工作簽證的居民。面對公眾的憤怒,特朗普總統卻誓言這僅僅是個開始。
而這一次,美國的科技公司積極為政府提供工具,以實現這一目標。
《國家》雜志作者辛西婭·羅德里格斯(Cinthya Rodriguez)寫道,關于移民的爭論自特朗普第一次競選起,就從未停歇。一方認為,移民是美國的核心組成部分,公民權利同樣不可侵犯。他們擁有憲法的支持,以及為國家運作貢獻力量的家庭和工人。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將盡可能多的移民定罪、監視、拘留并驅逐,無視公民自由和法律程序。盡管特朗普政府試圖削減其他政府職能,卻不斷向驅逐移民的基礎設施投入更多資金和資源,其中包括擴大與科技公司的合作。
對于這一切,少數族裔社區并不感到意外——在特朗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拉美裔社區組織Mijente就發起過#別為ICE提供科技支援(#NoTechForICE)的運動,以應對政府與科技巨頭日益緊密的合作。該組織曾發布報告,揭露亞馬遜、律商聯訊(LexisNexis)和在大數據分析領域的技術公司帕蘭泰爾(Palantir)如何通過銷售軟件、服務和數據,為ICE提供恐嚇移民社區的手段;并揭露了ICE如何利用生物識別技術和地理定位技術追蹤目標。
紐約市立大學傳播學教授尤利西斯·阿里·梅吉亞斯(Ulises Ali Mejias)在《半島電視臺》撰文表示,這些數據公司提供幾乎所有人的詳細檔案,包括人口統計數據、消費習慣、地理位置、健康狀況、教育背景、保險記錄和財務數據——你的手機、汽車,甚至智能手表,都可能成為數據來源。此外,政府還大規模收集移民的DNA數據。該計劃始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并在拜登政府的支持下繼續推進。官方的說法是,這些數據有助于未來調查移民犯罪,盡管官方統計數據顯示,移民的犯罪率實際上低于美國本土出生的公民。
梅吉亞斯寫道:如今,這些公司、投資者與聯邦政府之間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硅谷并不為之感到羞愧。在1月的總統就職典禮上,谷歌、特斯拉和亞馬遜的高管們紛紛站在特朗普一邊。這些科技巨頭已然成為寡頭,他們的企業準備從特朗普政府的行動中獲取巨額利潤。這些科技寡頭不再僅僅滿足于驅逐移民,而是積極提供技術支持,以推動一場涉及所有人的殘酷政治。
從這些科技巨頭近期的動向中,人們或許能察覺到其傾向。羅德里格斯寫道:谷歌最近刪除了其AI原則中“不設計或部署可能造成整體傷害的技術”的承諾。以踐踏勞工權利著稱的前亞馬遜高管大衛·基林(David Keeling),如今被特朗普政府提名負責全國范圍內的工人安全監管。亞馬遜旗下的Whole Foods正在加速特朗普政府解散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NLRB)的進程。帕蘭泰爾一半的收入來自政府合同,并且最近贏得了新的聯邦合同。SpaceX 和 Starlink 已成為美國國內外監視系統的關鍵部分。數據經紀公司繞過庇護城市的保護措施和《第四修正案》(旨在禁止無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狀的發出有相當理由的支持),向ICE出售敏感的個人信息,無需法庭許可。律商聯訊繼續與ICE合作,制定全國范圍的目標名單,為后者突襲和逮捕移民提供幫助。作為回應,人們在特斯拉工廠、展廳和經銷商門口抗議,呼吁企業問責,同時聯邦工人和普通民眾也紛紛加入。在美國多地,也開展抵制特斯拉運動,該運動號召特斯拉車主出售他們的汽車,并拋售特斯拉的股票。
梅吉亞斯提示:在向政府出售數據之外,科技公司開始有意識地讓仇恨言論在公共領域合法化,試圖讓新的移民政策獲得主流認可,從而減少法律挑戰的可能性。這些公司正在操控“言論自由”的定義,以服務于特朗普政府的目標。“移民是骯臟、惡心的垃圾。” 根據最近泄露的一份文件,Meta公司宣布在Facebook和Instagram平臺上將不再將這種言論標記為仇恨言論。這一政策調整發布于特朗普就職前幾天,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對此的解釋是,將此類言論歸類為仇恨言論“脫離主流話語”。這種對“主流”言論界定的改變,是為特朗普的新移民政策鋪平道路的一部分,同時也凸顯了那些掌控數據的公司,與掌控邊境的政府之間的互惠互利關系。
在文章結尾,梅吉亞斯強調:當“言論自由”被強權者單方面利用時,它可以成為一種審查手段,也可以變成壓迫與破壞的武器。Meta和X等公司積極推動仇恨言論,助長了針對弱勢群體的暴力行為。面對這一問題,單靠培養媒體素養、打擊社交媒體上的虛假信息是不夠的。在這個“后真相”、“后閱讀”的時代,大家都明白,獲得最多點贊和分享的敘事就是“現實”——至少對那些人來說就是如此。而掌控算法的人,顯然不會輕易放棄這種權力。
然而,梅吉亞斯也指出:將即將發生的災難歸咎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最簡單的做法。事實上,民主黨長期以來也支持放松監管和私有化的自由主義政策,正是這些政策促成了如今“科技寡頭階級”(broligarch class)的崛起。在一個由全球最富有的人操控的“科技-獨裁”國家(klepto-fascist state)面前,反抗將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些科技巨頭正是通過數據掠奪建立了他們的帝國,而人工智能只會加劇這種掠奪。人們必須拒絕殖民主義的核心謊言——即“強權即公理”。
對于這一系列問題,兩位作者分別作出了呼吁。梅吉亞斯認為:移民的福祉,也包括我們所有人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共同奪回對數據的掌控權,決定哪些數據被收集,以及如何使用這些數據。羅德里格斯則提醒人們:任何針對最脆弱群體的迫害,最終都會蔓延到那些看似不受影響的人身上。在阻止他們之前,所有人的隱私和自由都處于危險之中。
法國農業生態運動的歷史與挑戰
政治領域中使用的術語常常依賴于籠統的概括:“生態主義者”“農民”“城市人口”“決策”“消費者”等等。這些簡化通常為既得利益集團及其代理人服務。例如,法國占主導地位的農業工會FNSEA一直在捍衛農業世界的統一性——但是在其自身權威下。然而,過度簡化現實、擠壓掉所有細微差別、隱藏少數派運動和那些產生社會創新和試驗新模式的邊緣領域,這總是危險的。在平穩航行時,這些新事物可能會造成干擾,但當船開始傾斜時,它們可能會成為救命稻草。因此,在全球食品系統已經開始出現“漏水”、工業文明在其自身破壞力量的重壓下“溺水”的時候,重新審視那些代表性不足且常常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生態農民”的歷史和現狀是很有價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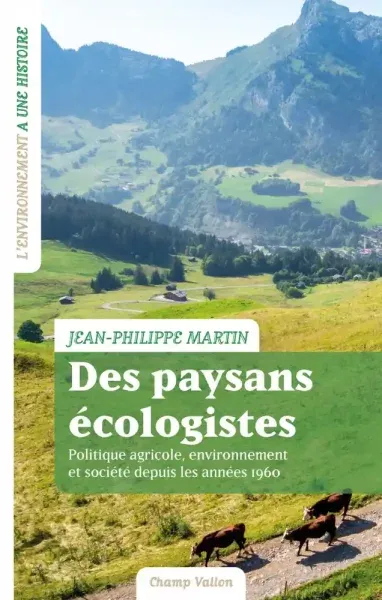
《生態農民:1960年代以來的農業政策、環境與社會》
讓-菲利普·馬丁的《生態農民:1960年代以來的農業政策、環境與社會》(Des paysans écologistes. Politique agricole, environnement et société depuis les années 1960,Paris, Champ Vallon, 2023)是一部追溯法國生態農業運動發展歷程的著作。作為歷史學家和農民聯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研究專家,馬丁在書中將研究視野擴展至法國農業運動的全景,既包括主流農業組織,也涵蓋了各種少數派生態農業倡議。
這部著作詳細梳理了兩種早期對工業化農業的批判性運動:一是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并在1960年代通過“自然與進步”(Nature et Progrès)組織在法國發展的有機農業運動;二是源于工會主義傳統、特別在法國西部地區發展的工人-農民運動,后者強調農業的經濟性與自主性。
第一種有機農業及其先驅——生物動力農業(biodynamic agriculture),接受了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德國、瑞士、英國(1945年成立社會協會)和法國發展起來,尤其是1964年創建了“自然與進步”組織,該組織匯集了醫生、農民和消費者。
這一運動強調健康和生態問題,但并不忽視社會問題。它由保守甚至反動的成員組成,同時又有傾向社會主義的成員。后者在法國催生了全國有機農業聯合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agriculture biologique,成立于1978年,歸功于幾個運動的統一以及1981年法國政府——特別是農業部長皮埃爾·梅尼埃[Pierre Méhaignerie]——的認可,這導致了法國和歐洲“生物”或“有機”標簽的創建)。
在工業化農業占據霸權的時期,有機農業提供了一個社會經濟框架,用于保存和發展后來被“重新發現”的替代性農藝和獸醫實踐以及各種社會和商業實踐,特別是與“消費者-行動者”的直接聯系。事實上,有機農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消費者愿意為其產品多付一點錢,預兆著所有工會提出的一項要求:需要真正有利可圖的價格。
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化農業一方面大聲要求提高價格并譴責消費者的矛盾行為,另一方面又毫不猶豫地因為高價格而貶低有機農業。誠然,在前一種情況下,重點是支付“生產成本”(農藥、化肥、設備和銀行債務),而在后一種情況下,重要的是保護環境和健康。差異立即顯而易見。套用帕斯卡的話:農業企業這一邊是真理,另一邊則是謬誤。
第二種生態農業運動興起于工會主義內部,特別是在法國西部,這個地區在畜牧業中有著相互技術援助的強烈傳統,并且以小型、勞動密集型農業為特征,與以谷物為主的東北部地區形成對比。
在飼料革命之后,當草地栽培取代永久性草原時,畜牧業經歷了玉米飼料革命及其衍生物:雜交種子、化肥、植物保護產品、收割機、青貯飼料收割機、食品補充劑和大豆——簡而言之,一系列進口的“生產要素”剝奪了生產者的自主權,使他們依賴于農工業綜合體(agro-industrial complex),同時將他們的地位降低為分包商和臨時工人。與農民之名相反,他們越來越像無產階級。
正是為了反對這些趨勢,在技術領域,像CEDAPA這樣的組織成立了。CEDAPA受到農業科學家、活動家安德烈·波雄(André Pochon)的影響。同時,出現了一種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批評,強調工人而非農民的權利。這一運動由伯納德·蘭伯特(Bernard Lambert)領導,他在政治上靠近自我管理運動(self-management movement),后于1981年作為社會黨人當選為議會議員。
這些運動要求農業“更加經濟和自主”,這引自雅克·波利(Jacques Poly)1978年報告的標題,當時他是國家農業研究所(INRA)的主任。這些不同的運動于1987年聯合起來,形成了“農民聯盟”,賦予“農民”一種政治意義,并將其帶入公共話語,作為全國農業經營者聯合會(FNSEA)推廣的農場主模式的替代方案。在這一趨勢中更為低調的參與者是與共產黨有聯系的MODEF(法國家庭農場保衛運動組織)。
馬丁著重描述了20世紀80至90年代生態理念如何在農民群體中逐漸扎根,以及瘋牛病危機、轉基因生物爭議、水污染和氣候變化等問題如何促使農業界重新思考其與環境的關系。
“經濟且自主的方法”對環境的危害要小得多。然而,該運動的社會議程與其生態關切(這些常被視為“城市”議題)之間的接近則需要時間。到了70年代末期,在放棄工業主義的農學家勒內·杜蒙(René Dumont)1974年總統競選活動之后,蘭伯特認識到解決生態問題的重要性,但該運動提出的社會批評被許多小生產者所接受,這些小生產者由于缺乏土地,加強了工業化生產,特別是通過養豬和家禽養殖。因此,生態問題在農民聯盟內部引起了分歧。它通過推廣農業生態學(agroecology,一種生態和社會關切的結合)逐漸加入了生態運動。生態關切也蔓延到了主導工會,其成員轉向有機農業。隨著1991年新工會“農村協調組織”(Coordination rurale)的出現,全國農業經營者聯合會(FNSEA)失去了一些代表性權重。即使FNSEA試圖接受有機農業,特別是在它控制的專業組織中,它優先考慮了一種不同的方法:“合理”(reasoned)農業。
這些努力很快受到兩個新擔憂的威脅:大型食肉動物特別是狼和熊的回歸(要么是由于土地荒廢,要么是因為它們被有意重新引入),以及動物產品消費的減少(彈性素食主義/素食主義/純素主義三件套)。大型掠食者的回歸可能會影響農業生產和畜牧業,而動物產品消費的減少則可能影響相關產業的經濟效益。
這兩種趨勢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因為相當數量的“農民”是靠在不適合工業化的牧場上進行廣泛畜牧業而生存的。純素主義和大型食肉動物因此成為廣泛畜牧業的威脅,而廣泛畜牧業依賴于高山草地和從事這種畜牧業的農民。
這場爭論揭示了追求生態社會的內在張力,這使得有必要解決多重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優先事項:生物多樣性、自然性、能源、土壤保護、水資源和景觀。這些矛盾只能通過妥協來解決。這些緊張關系重新激發了一種對立的“城市老鼠”(被認為是“無根的生態學家”)和“鄉村老鼠”(被認為是“有根的當地人”)的敘事。雖然這種沖突常常可能是殘酷的,但它并不本質上排除妥協的可能性。
女性在專業中的角色日益增長也是一個反映整個社會的趨勢。這對于應對農業的代際更新這一巨大挑戰至關重要——這是一個真正的頭痛問題,因為在農場如此資本化的時代,個人繼承已經變得不可能。對此有三種解決方案:按照農民聯盟的建議拆分這些農場;按照“土地聯系”(Terre de Liens)所倡導的,讓它們的資本還有勞動力共有化(mutualization);以及如全國農業經營者聯合會(FNSEA)自1960年以來在實踐中所做的那樣,接受有限責任公司模式和基于公司的農業。最終的選擇將取決于實施哪些公共政策。
農業工程師馬修·卡拉姆(Matthieu Calame)在3月20日刊發的書評中,對馬丁關于“生態農民自己成就自己”的論點提出了不同意見。他指出,馬丁的核心論點存在矛盾:一方面說生態農民“自己成就自己”(made themselves),另一方面又承認他們“享受支持”(enjoyed support,指享受生態組織和城市消費者的支持,這些消費者購買有機和本地產品,并接受社區支持農業)。他不認同馬丁試圖將生態農業“農業化”(agriculturalize)的防御策略,認為這種策略沒有必要。他反駁了農業產業化是內源性過程的觀點,指出農業產業化同樣是受外部刺激的結果,而非農村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
卡拉姆認為生態農民的優勢不太在于他們的本土性——即“自己成就了自己”——而在于他們為農業與社會之間的新契約鋪平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是“享受”支持:他們與城市運動談判,與之分享價值觀和目標,商定了一種互惠互利的交流條款,他們希望這種交流有朝一日能成為常態。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