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傅光明《〈紅樓夢〉之謎——劉世德學術講演錄》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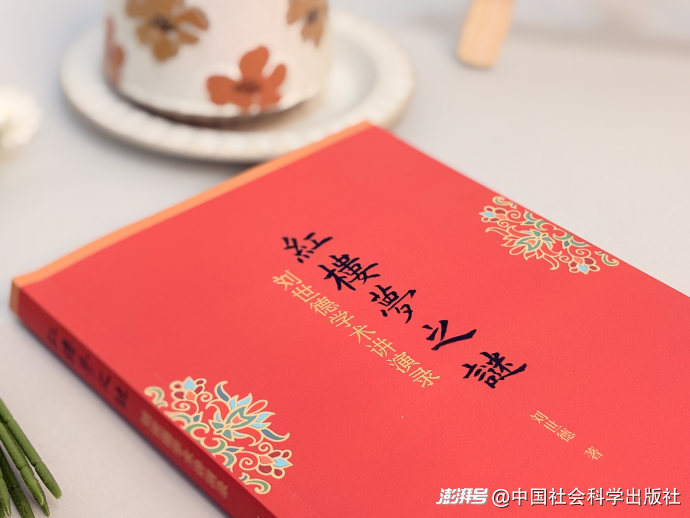
《紅樓夢》之謎:劉世德學術講演錄
劉世德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ISBN:9787522745657
近年來的“紅學”熱,帶動了“讀紅”“研紅”者數量的激增。無法否認,這是客觀效果的現實存在,但同時,也令眾多的“讀紅”甚至“研紅”者感到“紅”亂如麻般的困惑,有的已在未知覺間陷入迷局。這么說,好像是標榜在迷局中我自獨醒似的。事實上,任何一個《紅樓夢》的讀者,都可以是一個解謎者。不過,如何劃定學術解謎與胡亂猜謎之間的界限,又是個頗費唇舌的事。《紅樓夢》本身留下的謎畢竟太多了,導致解謎的視角多也屬順理成章,且解謎者多能自圓其說,以致有誰給挑個刺兒出來,便會媒體左右,網絡上下,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如此,在“紅學”的江流里,似乎很難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了。
在“研紅”的學者中,劉世德先生是方法、路徑與眾不同的一位,他從版本學的角度,以版本為切入點,不是單純做版本之間的對勘,而是以此來探索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過程和藝術構思。這當然須以扎實、嚴謹、深湛的考據功夫作底子,非常人所能為也。
近年來,常見報道說某某破譯、揭秘了“紅樓”密碼,喜歡弄噱頭的媒體便趁勢把“草根紅學”與“主流紅學”對立起來,動輒就說某某的大作問世,即意味著“主流紅學的全面破產”。好像主流紅學家們早已經跑馬圈地,霸道得眼里根本容不下嚼草根的;而“草根”又非要擺出跟“主流紅學”對簿公堂的架勢,看你還敢強龍壓地頭蛇。
在劉先生眼里,其實不僅“紅學”,任何一門學問都分兩個層面,一是大眾的,一是學術的,正好比學者與明星,本屬兩類物種,各有場域,倒不必非人為弄成隔絕甚至對立。現在的許多情形,是運用簡單邏輯把大眾與學術攪得水火不容,好像一提學術就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大眾只能悄然而悲,肅然而恐;而一說大眾,學界又嗤之以鼻,以為其只會拿三腳貓功夫混飯吃,大可不必理會。于是,學者與明星的混搭橫空出世,卻也常弄到一種尷尬境地,學界似乎矜持得對明星并不感冒,而明星卻暈乎得亂了方寸,攀比出場費的高下暫且不說,有的竟會演算出自我認定為明星加學者等于“部省級文化名人”的荒唐公式。
劉先生是冷板凳坐得幾十年的大學者,但只要走近他,會發現他自甘寂寞的學術研究,不僅不會“冷”得拒你千里,且會從中自然流溢出一種濃郁的親和力。劉先生是有真功夫,有真學識的大學者,從不故弄玄虛,從不石破天驚。我想,這樣的能力來自他天賦的學術才華。
想想能在近幾年的時間里,通過邀請劉先生來文學館做學術演講,得以走近他和他的學術世界,實在是一份幸運。而帶給我這一緣分的,是我的好友、《文學遺產》的竺青兄。當時請竺青兄幫忙策劃,請學者們來文學館“品讀《水滸傳》”,并請劉先生講《〈水滸傳〉的作者與版本》。
劉先生是我所欽佩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才華、學術功力,及其由此而產生的那份強烈的學術自信,深深感染著我。他的治學精神,研究方法,使我獲益多多。還記得當我問劉先生是否愿意在文學館已經講過兩輪《紅樓夢》之后再講“紅”時(前兩輪講“紅”,劉先生剛好不在北京),劉先生微笑著說:“我講‘紅’不用準備。”
他開始只準備講四個題目,講起來發現有的題目內容得兩講才容得下,便給我發來郵件,“申請”增加一講。如此往來,最后一直增到七講。再加上最近講的“介紹一部新發現的《紅樓夢》殘抄本”,剛好以8講“《紅樓夢》之謎”單獨成集。
劉先生所講,多源自其學術著作《〈紅樓夢〉版本探微》。竺青兄言,此書可以傳世。我便向劉先生討要,看后,以為然。同時,劉先生還一口氣送了我他寫的《紅學探索——劉世德論紅樓夢》和《曹雪芹祖籍辨證》。讀罷,更由心底發出兩個字:一為“嘆”,二曰“服”。
說心里話,我雖然也忝列學界小有時日,做著令許多人羨慕的學術研究,但通過與劉先生的交往,才發現自己對學術二字,真是無從談起呢!比如,在劉先生演講“《紅樓夢》后40回作者是誰?”之前,甭說別人,我都在心底問,難道這還有什么講頭兒嗎?誰不知道《紅樓夢》后40回的作者是高鶚,書上不白紙黑字印著?不是高鶚,那會是誰?你要說不是高鶚,得以理服人嘛。劉先生不緊不慢、有條有理地以堅實的考據功夫,一條一條地舉證,有內證,有外證,使聽者,也包括我,不僅不覺枯燥,而且被帶入了一種情境,會覺得離真實越來越近了,直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實證的學問,不見得沒有索隱出來的故事好聽、有趣。大眾不就愛聽個“故事”嗎?單以劉先生為例,他以如此深厚、令人嘆服的版本功力,隨時隨地以文本為依據,實證地破謎、解疑,沒有空穴來風,沒有捕風捉影,而是透過一個個的細節線索,縝密地考稽曹雪芹的創作過程和藝術構思的變化,探索曹雪芹可能的寫作方式。
劉先生以他令人嘆佩的學術功力,每次都給聽者帶來學術驚喜。還是拿《紅樓夢》來說事兒,對于普通讀者,最熟悉的莫過于以悲劇收場的寶黛釵的愛情故事,特別是那些當年看過徐玉蘭、王文娟主演的越劇電影《紅樓夢》的受眾,以為這就是《紅樓夢》的全部。而且,有人根本搞不清,也不想搞清那么多復雜的人物關系(像劉先生講到的“迎春問題”,從不同的版本看,竟有七種說法),而愿意干脆把寶玉和元、迎、探、惜四姐妹,都一股腦看成賈政和王夫人的親生兒女。這樣人物關系和故事情節都簡單了。我小時候,腦子里灌的就是母親以越劇《紅樓夢》為藍本講的故事。到我讀原著時,才發現里邊的人物關系怎么這么亂!根本理不清,想想頭都大。慢慢地,又發現《紅樓夢》還有那么多復雜的版本問題,真乃中國古代小說中之唯一奇觀。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劉先生講到的每一個問題,都是一般的《紅樓夢》讀者所忽略的,并非不經意間地忽略,而是根本就注意不到。每次聽劉先生演講之前,我也常在云里霧里,覺得這個題目有那么多可說嗎?每次聽到最后,又都是云開月朗。
比如,劉先生講的“兩個賈琮”問題。一般讀者能有多少人會對賈琮留下印象?賈琮何許人?他跟邢夫人什么關系?他是賈赦和邢夫人的兒子,還是賈府的族人?劉先生以福爾摩斯式的“偵探”,結論出: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紅樓夢》80回,實際上是由初稿和改稿兩種成分組成的。在初稿中,賈琮不過是一般的族人。到了改稿,賈琮變成了賈璉的弟弟。由賈琮問題看出,標志著賈府敗落的“抄檢大觀園”故事,是組成曹雪芹初稿的重要內容之一。換言之,《紅樓夢》的素材包括兩個主要的部分:一個是賈府這個封建貴族大家庭的腐敗、沒落,一個是我們一般讀者都熟知的寶黛釵三個人的愛情、婚姻悲劇。是兩者的合流,形成了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紅樓夢》的樣子。
劉先生的學術自信,是建立在學術嚴謹之上。讀《紅學探索——劉世德論紅樓夢》時,見書中收錄了一封致馮其庸先生的信《關于曹良臣的幾個問題》,信寫得干脆利落,沒有寒暄,一上來就直陳馮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考證曹良臣的籍貫問題、歸葬地點和他的兒子問題,結論甚有說服力”。然后筆鋒一轉,便說在某處結論上資料還需“有所補充和修正”。再然后,就把自己以前讀《明太祖實錄》時抄下的相關記載附于后,有14條之多。再再然后,不動聲色地說“上述材料,惟有第四條曾被大著征引。其余均在遺漏之列”。最后,劉先生又將自己從這些材料中得出的幾點事實表述出來。不溫不火,不急不躁,考而有據,嚴謹扎實,真一派大學者的學養風范。
何以能如此呢?在劉先生看來,“一個美好的推測,如果它不時地存在著被駁斥和被推翻的危險,那么,它還有什么必要向讀者們鄭重其事地提出和推薦呢?一個美好的推測,如果它不時地存在著被駁斥和被推翻的危險,那么,它還有什么理由要苦苦地堅持和不斷地重復呢?”
所以,他在從事曹雪芹祖籍問題的研究時,始終“努力以客觀的證據為出發點、支撐點,并以帶有濃烈的主觀色彩的推測為忌”。他非常清楚,在沒有可資利用的原始材料的情形下,任何主觀的推測都帶有冒險性。他說:“你企圖讓大家接受你的結論,然而你的結論賴以存在的前提卻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你立論的基礎既然是薄弱的,對大家來說,你的結論自然也就缺乏最起碼的說服力了。如果從一開始起跑點就錯了,又怎么能夠方向正確地、順利地、迅速地到達終點呢?”言簡意賅,耐人尋味。
劉先生強調要有實證,他以為:“在考據中,在對同時存在的多種可能性進行抉擇時,如果只選取其中的一種可能性,而排斥其他的多種可能性,那就必須以另外的證據為支柱。否則,嚴肅的考據工作就有可能變成一場隨心所欲的游戲了。……我認為,一個公開提出的結論之站得住與否,最起碼的檢驗的條件就是看它是否經受得起來自別人的任何有理由的反問。”
“在學術研究工作中,做考據,立新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證據。而證據是不能自封的。它必須是客觀存在的,并經得起嚴格的檢驗。沒有證據,考據就與兒戲無異,考據家也就淪為強詞奪理的舌辯之徒。沒有證據,新說就變成了臆說,并喪失了最起碼的說服力。
“證據可以是多種的、多方面的。但以正面的、直接的證據為主,其他的都屬于次要的、輔助性的證據。證據都以確鑿可靠為前提。否則,將是軟弱無力的、無助于解決疑難問題的。
“在立新說時,除了用正面的、直接的證據加以論證之外,還應當注意排斥反證。反證存在,就說明新說的結論有著或大或小的缺陷。如缺陷過于重大,則會造成新的結論有被推翻的危險。”
鄧紹基先生在為劉先生所著《曹雪芹祖籍辨證》所寫序中說,劉先生的論文“注重實證,論析嚴密,即使有假設推論,也建筑在對文獻材料作綜合研究的基礎之上,萬一材料不足,有的假設推論也注重情理邏輯,而不作無根無稽的和強詞奪理的所謂‘推考’”。
跟隨劉先生讀過研究生、現在同樣是知名學者的石昌渝先生,對劉先生身上體現出的“由鄭振鐸、何其芳所倡導的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學風”深有感觸,那就是“不盲從,不隨大流,不尚空論,老老實實從大量可靠的材料中尋求事實的真相和文學發展的規律。這種學風看似平常,真正實踐起來絕非容易,它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在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下,更需要多一些的學術定性”。時下慣于拿故事戲說學術的浮躁學風,與此相差霄壤,利欲熏心者當警醒。在學術的付出上,一分功力帶來一分收獲,任何的假冒偽劣,都不會有學術生命力。
劉先生的“紅樓夢之謎”,好似為由繁復的《紅樓夢》版本問題而探索目迷五色的“紅學”,打開了一扇窗戶,透過它,《紅樓夢》中的眾多謎團不再“不見其處”,而是變得清晰了一些。“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我想,這正是劉先生的學術貢獻,他的“版本學”為研讀曹雪芹的創作過程和藝術構思,為研讀其他明清小說,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性。讀者盡可以充分享受由劉先生的版本研究所帶來的閱讀快感。“研紅”對劉先生來說,是精微之處見功夫;“讀紅”對讀者來說,是精微之處見滋味。簡單一句話,劉先生的《紅樓夢》版本研究,無疑有助于讀者更清晰地“讀紅”“解紅”。
劉先生第一次蒞臨文學館講“水滸”的那天,是2003年10月11日,大雨。到2007年10月14日講《紅樓夢》的“眉盦藏本”,幾乎整整四年的時間里,他一共在文學館做過16場學術演講,并由此成為在文學館演講場次最多的學者。我不揣冒昧,戲稱他為文學館的“演講冠軍”。現在來看,這16場演講像事先分割好了似的,講《紅樓夢》8場,講其他幾部明清小說(先后依次講的是《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游記》《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恰好也是8講。這便是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兩部學術演講錄的源與緣。[1]
劉先生不計尊幼,囑晚學作序。唐突學步,聊以代之。
2007年10月12日于中國現代文學館
[1]編者按,另一部學術演講錄即《明清小說:劉世德學術演講錄》,線裝書局,2007。

劉世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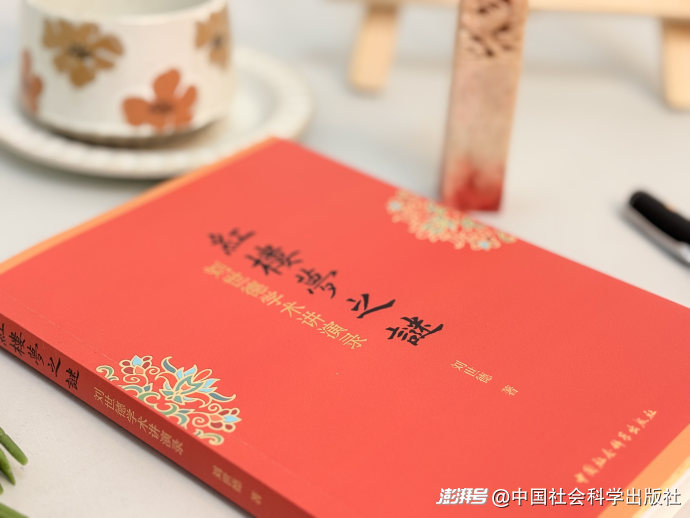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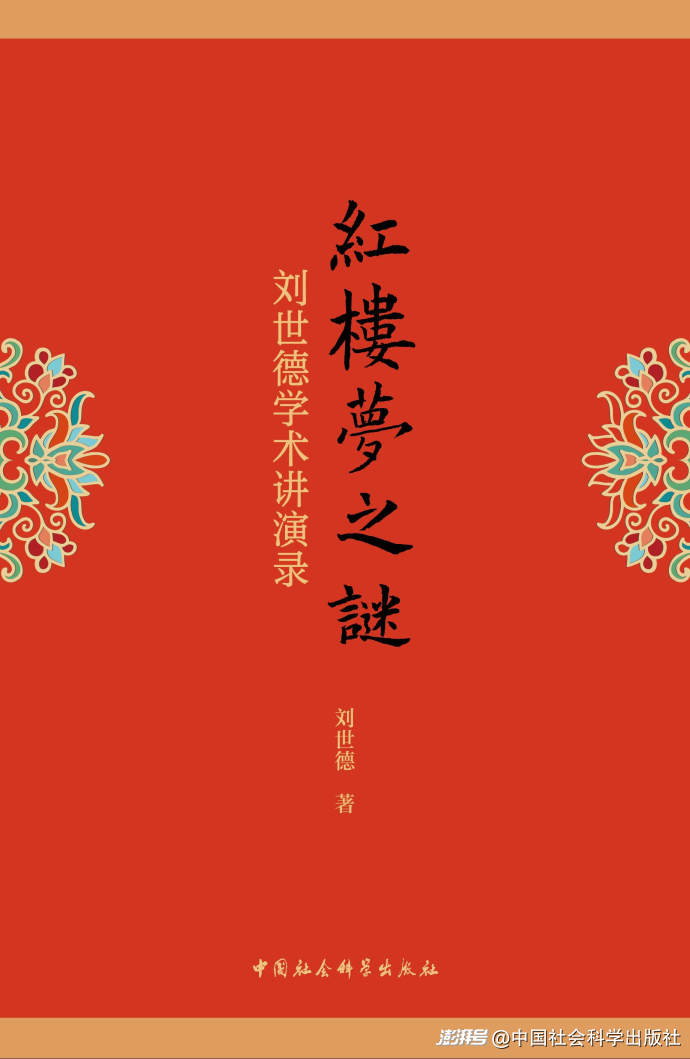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