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塞斯·洛克曼談種植園經(jīng)濟(jì)與美國資本主義

塞斯·洛克曼(章靜繪)
塞斯·洛克曼(Seth Rockman),現(xiàn)任教于美國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的布朗大學(xué)歷史系,研究領(lǐng)域聚焦于美國獨(dú)立戰(zhàn)爭至南北戰(zhàn)爭期間的社會(huì)史與勞工史,尤其關(guān)注奴隸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其研究興趣更著眼于兩種制度在美國歷史中的互動(dòng)與協(xié)同作用。
塞斯·洛克曼的第一本書《艱難度日:早期巴爾的摩的雇傭勞動(dòng)、奴隸制與生存》(Scraping By: Wage Labor, Slavery, and Survival in Early Baltimore)聚焦于美國快速發(fā)展的城市之一——巴爾的摩,探討了黑人與白人、奴隸與自由人、男性與女性等不同群體的生存策略。在這本書中,他深入分析了種族和法律鏡框是如何塑造勞動(dòng)市場,以及勞動(dòng)市場如何反過來影響勞動(dòng)者的機(jī)遇與困境。而在其近期出版的新著《種植園專用商品:一部美國奴隸制的物質(zhì)史》(Plantation Goods: A Material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中,他研究了新英格蘭的工業(yè)革命,以及該地區(qū)生產(chǎn)的商品如何被運(yùn)往南方種植園使用。這些“種植園專用商品”包括帽子、鋤頭、鐵鍬、鞋靴和紡織品等。通過追蹤這些商品從制造地到使用地的流動(dòng)過程,塞斯·洛克曼試圖揭示工廠工人與種植園勞工之間的聯(lián)系,并由此構(gòu)建一種新的美國歷史敘事——不再將奴隸制與資本主義視為對立的兩極,并由此展現(xiàn)它們?nèi)绾蜗嗷ソ豢棥f(xié)同發(f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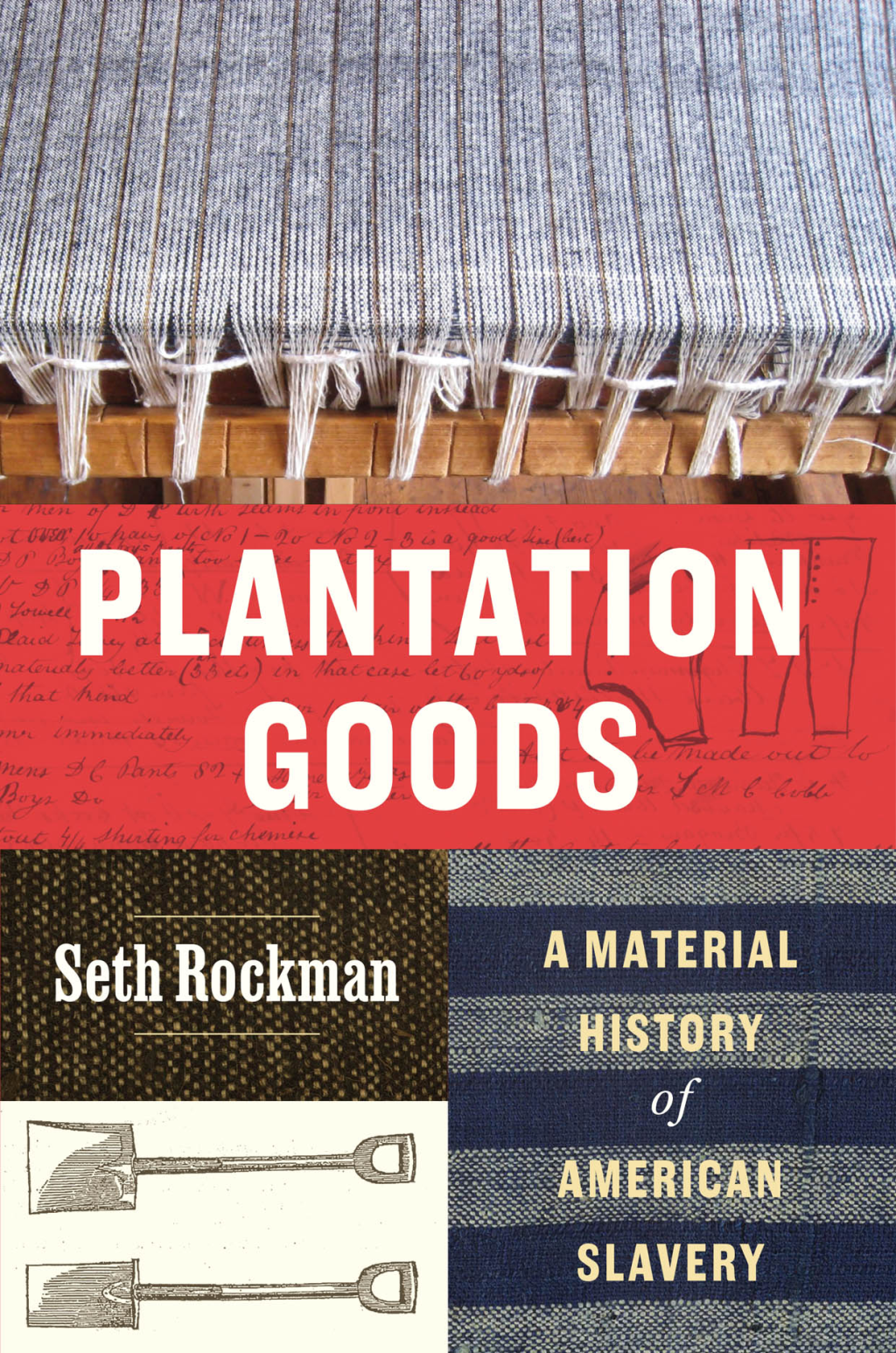
《種植園專用商品:一部美國奴隸制的物質(zhì)史》( Plantation Goods: A Material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
在撰寫《種植園專用商品》之前,您曾出版了《艱難度日》,并與哈佛大學(xué)斯文·貝克特教授一起合編了《奴隸制的資本主義:美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新歷史》(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是什么契機(jī)促使您投身于奴隸制、資本主義與勞工史這一研究領(lǐng)域?
塞斯·洛克曼: 在我學(xué)習(xí)美國歷史的初期,我有一個(gè)印象深刻的經(jīng)歷,那就是閱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傳——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對于那些不太熟悉他的人來說,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出生于十九世紀(jì)初的馬里蘭州東部,一出生便是奴隸。然而,在他青少年時(shí)期,由于鄉(xiāng)村缺乏適合他的農(nóng)業(yè)工作,他被送往巴爾的摩——這座快速發(fā)展的海港城市。在那里,他可以通過從事造船、卸貨等工作賺取工資。然而,作為奴隸,這些工資并不屬于他,而是屬于擁有他的奴隸主。我對奴隸掙工資這一現(xiàn)象非常好奇,因?yàn)樵谖铱磥恚錆M了矛盾。
此外,道格拉斯在自述中提到的另一件事也讓我深受觸動(dòng)。他講到,自己在巴爾的摩學(xué)習(xí)閱讀時(shí),竟然發(fā)現(xiàn)了比自己更貧困、生活更悲慘的群體——那些雖然饑餓卻懂得閱讀的愛爾蘭兒童。道格拉斯用面包賄賂這些孩子,以換取閱讀課程。這一細(xì)節(jié)令我感到十分震驚:怎么會(huì)有比奴隸還貧困的人存在于城市中?難道奴隸不應(yīng)該是處境最為困頓的人嗎?這一發(fā)現(xiàn)引發(fā)了我對種族與階級(jí)關(guān)系的深刻思考,也讓我開始質(zhì)疑:在動(dòng)態(tài)的市場環(huán)境中,奴隸制為何能夠存在并蓬勃發(fā)展?正是這些問題,推動(dòng)了我今后的學(xué)術(shù)研究方向。
在閱讀《種植園專用商品》時(shí),我被您巧妙地以“種植園專用商品”為核心,探討奴隸制、資本主義與勞動(dòng)關(guān)系交匯點(diǎn)的方式深深震撼。同時(shí),您在研究中對種族、階級(jí)乃至性別動(dòng)態(tài)的深入挖掘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能否先簡要介紹一下學(xué)界圍繞奴隸制與資本主義關(guān)系的歷史性爭論及其演變?此外,我也很期待聽聽您希望通過這部作品在既有史學(xué)研究中做出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
塞斯·洛克曼: 在西方史學(xué)界,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于1944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奴隸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威廉姆斯的研究聚焦于十八世紀(jì)的大英帝國,并提出了一個(gè)極具影響力的論點(diǎn):資本主義的興起源于加勒比殖民地,在那里奴隸被迫種植甘蔗,甘蔗生產(chǎn)創(chuàng)造了巨額財(cái)富,而這些財(cái)富又被英國資本家投資于工廠,推動(dòng)了英國從十八世紀(jì)的重商經(jīng)濟(jì)向十九世紀(jì)的工業(yè)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一旦英國確立了工業(yè)基礎(chǔ),奴隸制便失去了經(jīng)濟(jì)上的必要性,因此英國能夠“負(fù)擔(dān)得起”廢除奴隸制所需的代價(jià)。換句話說,奴隸制催生了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最終促使了奴隸制的廢除。過去七十年來,學(xué)者們圍繞威廉姆斯這一論點(diǎn)展開了廣泛討論,試圖深入理解英國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
然而,美國并沒有像《資本主義與奴隸制》那樣的著作來解釋自身的歷史。相反,我們對資本主義與奴隸制關(guān)系的理解,主要是通過美國內(nèi)戰(zhàn)(1861–1865)這一事件來進(jìn)行的。內(nèi)戰(zhàn)的傳統(tǒng)敘事通常是這樣的:工業(yè)化的北方與以奴隸制為基礎(chǔ)的南方發(fā)生戰(zhàn)爭,最終北方獲勝,這似乎被視為奴隸制在經(jīng)濟(jì)上無足輕重的“證據(jù)”——如果奴隸制真那么重要,為什么它沒有幫助南方贏得戰(zhàn)爭?因此,許多美國學(xué)者和公眾形成了一種錯(cuò)誤的觀念,即奴隸制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而不是相互交織的。
在過去二十年里,美國大學(xué)的許多學(xué)者開始重新思考奴隸制與資本主義的關(guān)系,認(rèn)為二者是共生的(symbiotic),而非對立的(antagonistic)。這一研究體現(xiàn)在多個(gè)方面。例如,通過賬簿研究,學(xué)者們發(fā)現(xiàn)許多先進(jìn)的會(huì)計(jì)技術(shù)首先在美國南方的種植園中應(yīng)用,而非在北方的工廠;研究還表明,工廠的標(biāo)準(zhǔn)化管理和時(shí)間規(guī)制模式在南方的大型種植園中比在新英格蘭的工廠更為常見;此外,資本流動(dòng)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九世紀(jì),許多投資者更傾向于將資本投入奴隸制種植園,而非工業(yè)工廠,因?yàn)榉N植園的經(jīng)濟(jì)回報(bào)不僅更為確定,而且全球市場對奴隸種植的棉花和甘蔗的需求也在穩(wěn)步增長。
隨著這些學(xué)術(shù)成果的積累,美國史學(xué)界逐漸形成新的共識(shí):奴隸制與資本主義并非二元對立,而是緊密交織的。這一觀點(diǎn)不再將奴隸制簡單地視為封建主義的遺留,也不認(rèn)為資本主義的興起必然意味著奴隸制的終結(jié)。相反,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完全能夠?qū)⑴`制納入自身的體系,而非將其排斥在外。據(jù)我觀察,這一觀點(diǎn)已成為美國史學(xué)界的主流看法。
然而,一些經(jīng)過經(jīng)濟(jì)學(xué)訓(xùn)練的學(xué)者并不接受這一觀點(diǎn)。他們試圖證明奴隸制并未對美國GDP(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做出關(guān)鍵貢獻(xiàn),并主張如果美國更早廢除奴隸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會(huì)更加高效、更加繁榮。但在我看來,這些論點(diǎn)并不具備說服力,因?yàn)樗鼈兓诘氖羌僭O(shè)性推測(“如果當(dāng)時(shí)……”),而非對歷史現(xiàn)實(shí)的深入研究。歷史的事實(shí)是:美國最富有的人選擇投資種植園和奴隸,并因此變得更富有;南方的種植園成為金融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關(guān)鍵場所;奴隸種植的棉花,是美國乃至英國工業(yè)革命的關(guān)鍵原料。美國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正是在奴隸制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奴隸制在美國經(jīng)濟(jì)騰飛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在十九世紀(jì)初的幾十年里。
去年我曾讀過尤金·吉諾維斯(Eugene Genovese)的《奴隸制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南方奴隸制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他在書中提出了一個(gè)有影響力的觀點(diǎn):奴隸制主要是一種地區(qū)性的制度,并沒有產(chǎn)生顯著的全國性影響。雖然他承認(rèn)奴隸制是有利可圖的,但他認(rèn)為奴隸制是一種深度融合的社會(huì)系統(tǒng)和文明,使南方形成了一種與北方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根本不同的經(jīng)濟(jì)模式。您認(rèn)為他的觀點(diǎn)更傾向于您之前提到的內(nèi)戰(zhàn)敘事嗎?
塞斯·羅克曼:在我看來,這個(gè)問題的答案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美國學(xué)術(shù)界的運(yùn)用密切相關(guān)。吉諾維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尤其是在他職業(yè)生涯開始的階段,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之一。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吉諾維斯堅(jiān)信存在著不同的生產(chǎn)方式。這些生產(chǎn)方式是根本不兼容的,并且它們會(huì)按照預(yù)定的階段進(jìn)展,封建體制會(huì)被資本主義體制取代,資本主義會(huì)轉(zhuǎn)變?yōu)樯鐣?huì)主義。因此,如果從這個(gè)起點(diǎn)開始看待歷史,認(rèn)為主要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南方,關(guān)注于向世界市場銷售商品,處于一個(gè)與以工廠和工資勞動(dòng)為主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截然不同的生產(chǎn)方式,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這不僅僅是因?yàn)轳R克思主義在美國學(xué)界的式微,而是一批堅(jiān)守該傳統(tǒng)的學(xué)者開始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美國歷史。這一轉(zhuǎn)向尤其體現(xiàn)在非裔學(xué)者的理論創(chuàng)新中。以塞德里克·羅賓遜(Cedric J. Robinson)1983年出版的《黑人馬克思主義:黑人激進(jìn)傳統(tǒng)的形成》(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為例,該著作并未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而是主張必須將非洲及非洲裔群體五百年的獨(dú)特歷史經(jīng)驗(yàn)納入其理論框架。羅賓遜的洞見催生出一個(gè)新穎的分析視角: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jì)邏輯不應(yīng)僅以曼徹斯特工廠為分析原型,而應(yīng)將販奴船——那些橫渡大西洋、載滿被標(biāo)價(jià)的人體——視為同等重要的研究場域。這種范式轉(zhuǎn)移使學(xué)者得以在堅(jiān)持階級(jí)分析的同時(shí),摒棄“工業(yè)資本主義為最高生產(chǎn)形態(tài)”的預(yù)設(shè)。在此基礎(chǔ)上,學(xué)界逐漸突破尤金·吉諾維斯(Eugene Genovese)等前輩對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論”的執(zhí)著,轉(zhuǎn)而關(guān)注資本主義如何通過人口商品化機(jī)制吸納奴隸制,而非將其視為前現(xiàn)代殘余。

塞德里克·羅賓遜(Cedric J. Robinson)
所以,這更像是是拓寬了資本主義的概念,而不僅僅專注于其制度下的生產(chǎn)模式,或者嚴(yán)格遵循社會(huì)進(jìn)化的固定階段,如封建主義 → 奴隸制 → 資本主義,對么?
塞斯·洛克曼: 完全正確。
您提到有些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不認(rèn)同奴隸制是一個(gè)有效的經(jīng)濟(jì)體系。然而,我記得在閱讀《苦難的時(shí)代:美國奴隸制經(jīng)濟(jì)學(xué)》(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時(shí),羅伯特·威廉·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和斯坦利·L.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在其定量分析的基礎(chǔ)上,論證了奴隸制作為一種制度是高效的。那么,您認(rèn)為為什么許多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仍然對他們的結(jié)論持懷疑態(tài)度?
塞斯·洛克曼: 你提到了1974年出版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書。這本書由兩位經(jīng)濟(jì)史學(xué)家撰寫,他們使用定量分析來論證奴隸制作為生產(chǎn)商品的一種極其有效的機(jī)制。在美國,從南北戰(zhàn)爭時(shí)期開始,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認(rèn)為奴隸制是低效的、落后的,并且可以通過機(jī)械化或其他技術(shù)創(chuàng)新輕易取代,從而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然而,當(dāng)福格爾和恩格曼在1970年代出版這本書時(shí),許多人質(zhì)疑道:“等等,如果你們說奴隸制是高效的,那你們是不是在說奴隸制是正當(dāng)?shù)模俊彼麄兓貞?yīng)道:“不,不,不,我們絕不是在說奴隸制是正當(dāng)?shù)模〗^對不是!”他們的論點(diǎn)是:奴隸制是一種極為高效的機(jī)制——它既能強(qiáng)制勞動(dòng)力投入,又能為全球市場規(guī)模化生產(chǎn)商品。南方奴隸主選擇奴隸制而非工資制度或其他激勵(lì)性報(bào)酬體系,實(shí)際上是基于經(jīng)濟(jì)理性的決策。
不出所料,人們開始質(zhì)疑:“等一下,暴力?暴力怎么能被視為理性的經(jīng)濟(jì)選擇?這可不好。”而《苦難的時(shí)代:美國奴隸制經(jīng)濟(jì)學(xué)》引發(fā)了大量批評,尤其是來自那些秉持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libertarian economics)——特別是那些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致力于市場自由能夠最大化人類自由的觀點(diǎn)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這一觀點(diǎn)幾乎成了美國及西方世界經(jīng)濟(jì)學(xué)者的主流共識(shí),尤其是在冷戰(zhàn)時(shí)期。因此,當(dāng)福格爾和恩格曼提出“市場并不必然促進(jìn)自由,市場也可能剝奪自由”時(shí),這對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術(shù)思潮造成了極大的挑戰(zhàn)。因此,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花費(fèi)大量時(shí)間來爭論《苦難的時(shí)代:美國奴隸制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觀點(diǎn),并通過其他定量分析方法重新評估奴隸制在商品生產(chǎn)中的效率。
但與此同時(shí),歷史學(xué)家對這場辯論興趣不大,他們在當(dāng)時(shí)基本上沒有繼續(xù)深入討論此事,直到2000年代史學(xué)界重新開始關(guān)注奴隸制與資本主義的關(guān)系。當(dāng)時(shí),盡管歷史學(xué)家對《苦難的時(shí)代:美國奴隸制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方法持批判態(tài)度,但福格爾和恩格曼所收集的數(shù)據(jù)仍然被證明極具價(jià)值。不過,歷史學(xué)家們在運(yùn)用這些數(shù)據(jù)時(shí),會(huì)給予不同的解讀。他們更傾向于強(qiáng)調(diào)奴隸制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和道德上的可憎制度。相比之下,經(jīng)濟(jì)史學(xué)家通常不會(huì)對奴隸制進(jìn)行道德評判,但也鮮少關(guān)注被奴役者的人性維度。
比如,當(dāng)福格爾和恩格曼在分析種植園賬簿時(shí),他們量化了奴隸每日平均被鞭打的次數(shù)。這種量化分析本身便再現(xiàn)了奴隸制的非人化本質(zhì)——正如種植園主當(dāng)年將人體創(chuàng)傷轉(zhuǎn)化為賬簿數(shù)字,當(dāng)代學(xué)者的統(tǒng)計(jì)實(shí)踐亦在方法論層面延續(xù)了將人類簡化為可計(jì)算單位的暴力邏輯。因此,許多歷史學(xué)家選擇不延續(xù)福格爾和恩格曼的研究方法,而是傾向于采用更多定性研究,即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經(jīng)歷、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和奴隸制的道德后果,而非單純的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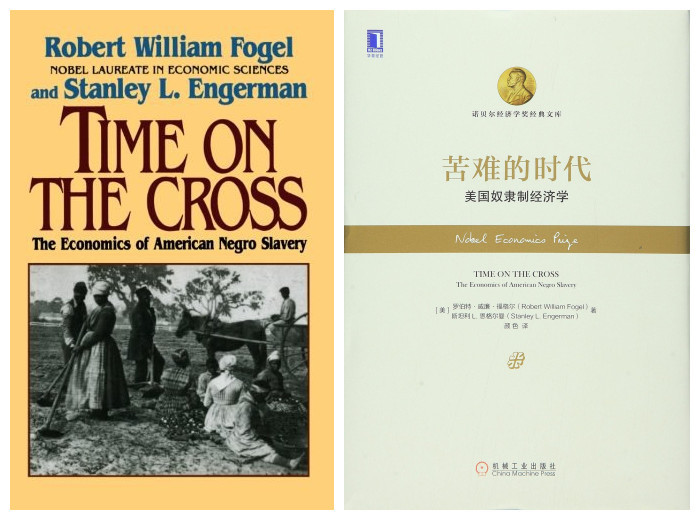
《苦難的時(shí)代:美國奴隸制經(jīng)濟(jì)學(xué)》(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您提到當(dāng)代美國學(xué)界已基本達(dá)成一種共識(shí):即奴隸制與資本主義在美國歷史中是相互依存的。同時(shí),您使用了“共謀”(complicity)這個(gè)概念來描述工業(yè)化的北方與農(nóng)業(yè)化的南方之間的關(guān)系。那么,在您的研究中,“共謀”意味著什么?您如何定義這一術(shù)語?此外,您提到“共謀”應(yīng)該被視為一種既定的歷史狀態(tài),這對您的研究具有何種方法論上的意義?
塞斯洛克曼:“共謀”(complicity)這個(gè)概念在過去七十五至一百年里,已經(jīng)成為西方世界中一個(gè)重要的討論話題。它的某些含義或許可以追溯到二戰(zhàn)時(shí)期,特別是關(guān)于誰是納粹的合作者(collaborators)。例如,在二戰(zhàn)期間,人們開始反思——誰選擇袖手旁觀?誰對反人類罪行視而不見?誰為了賺取微薄的利潤或避免遭到納粹政權(quán)的干涉而選擇沉默? 這些討論使“共謀”概念逐漸發(fā)展,并在二十世紀(jì)和二十一世紀(jì)被廣泛應(yīng)用,以要求人們對自己的政治和經(jīng)濟(jì)決策負(fù)責(zé)。例如:當(dāng)我給汽車加油時(shí),我是否在全球變暖中扮演了“共謀者”的角色? 因?yàn)槲以谥L化石燃料的燃燒。當(dāng)我購買某個(gè)品牌的衣服,而這個(gè)品牌的服裝供應(yīng)鏈涉及孟加拉國的血汗工廠時(shí),我是否共謀于那些遠(yuǎn)在世界另一端、拿著極低工資的童工的苦難?當(dāng)我使用iPhone時(shí),我是否共謀于中西非礦工的困境? 因?yàn)樗麄冊跇O端惡劣的條件下開采制造電池所需的稀土礦物。這些問題與我們今天的全球消費(fèi)模式密切相關(guān),它們讓我們思考:當(dāng)我們消費(fèi)某種商品時(shí),在供應(yīng)鏈的另一端,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我感興趣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將這種“共謀”概念歷史化(historicize)。但我們是第一代提出這些問題的人嗎? 答案當(dāng)然是否定的。例如,在十八世紀(jì)九十年代的英國,廢奴主義者就開始對奴隸制和奴隸貿(mào)易展開激烈抗議。他們向英國公眾宣傳:“每當(dāng)你把一勺糖放進(jìn)茶里,你就等于在飲用非洲奴隸的鮮血;你就等同于食人族;你和在巴巴多斯或牙買加揮舞皮鞭鞭打奴隸的種植園主,并無區(qū)別。”換句話說,他們將普通消費(fèi)者與奴隸制的暴行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指責(zé)英國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默許并助長了奴隸制。
到了十九世紀(jì)的美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提出類似的問題:北方如何投資于南方的奴隸制?北方如何從奴隸種植的棉花中獲利?北方人如何一邊譴責(zé)奴隸制為“道德上的邪惡”,一邊又靠奴隸制賺取巨額財(cái)富?這些歷史問題,正是我想要在書中深入探討的內(nèi)容。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個(gè)基本前提是:“共謀”并非一種例外狀態(tài),而是一種常態(tài)。尤其是在全球貿(mào)易高度一體化的世界中,我們的日常行為幾乎都在無形中將我們與那些我們無法看見的遙遠(yuǎn)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當(dāng)我穿上這雙襪子時(shí),它們的生產(chǎn)地是否重要?當(dāng)我在超市買一個(gè)檸檬時(shí),這是否讓我與一個(gè)遠(yuǎn)在異國的柑橘種植工人產(chǎn)生聯(lián)系?當(dāng)我給汽車加油時(shí),這是否讓我與沙特阿拉伯的女性生活現(xiàn)狀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
因此,我并不只是想簡單地找到“共謀”的證據(jù),然后寫一本書說:“看,北方和南方其實(shí)同樣罪惡。”抑或是“看,那些自詡‘道德高尚’的人其實(shí)也是偽善的。”對我來說,這并不是歷史學(xué)家的任務(wù)。歷史學(xué)家的任務(wù)是理解人們在過去的世界中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并如何做出決策的。如果我們把“共謀”看作是一種常態(tài),而非例外,如果我們承認(rèn)沒有人能夠做到完全潔身自好,也沒有人能完全避免以某種方式參與到世界上的壓迫體系之中,那么,我們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歷史上的人們?nèi)绾卧谝粋€(gè)“共謀”無處不在的世界中做出選擇。這正是我在這本書中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當(dāng)您提到“共謀”這一概念如何影響您研究的思維框架時(shí),我想到了書中的兩句話。第一句來自第四章《工資奴隸》(“Wage Slaves”),您寫道:“幾乎沒有證據(jù)表明,工廠工人認(rèn)為自己在奴役制度中扮演了‘共謀者’的角色,更不用說認(rèn)為自己是奴隸制的受益者了。”(149頁) 而在結(jié)論部分,您又寫道:“講述這些復(fù)雜歷史的目的,并不是要塑造一個(gè)沒有英雄的歷史,而是要展現(xiàn)一個(gè)充滿普通男女的歷史——他們在這個(gè)由復(fù)雜的道德糾葛和大量自欺與短視機(jī)會(huì)構(gòu)成的世界中摸索前行,既不比我們更高尚,也不比我們更邪惡。”(357頁) 這句話讓我深有共鳴。正如您所說,歷史學(xué)家的職責(zé)不僅僅是用廉價(jià)的道德主義去評判過去的人,而是去揭示世界的相互聯(lián)系,并理解個(gè)體如何在其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做出決策。
塞斯·洛克曼:隨著對這一問題思考的深入,我愈發(fā)確信:歷史中的行動(dòng)者并不比我們更高尚,而我們也不比前人更優(yōu)越。
您在新作中巧妙地運(yùn)用物質(zhì)史(materi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通過追蹤鋤頭、鞋靴等種植園日常用品的流通網(wǎng)絡(luò),將奴隸制、資本主義與勞動(dòng)關(guān)系的多重歷史維度有機(jī)串聯(lián)。能否請您談?wù)劊菏鞘裁磫l(fā)您選擇種植園專用商品作為分析這些主題的關(guān)鍵切入點(diǎn)?
塞斯·洛克曼: 其中一個(gè)重要原因是,我想找到一個(gè)講述好故事的方法。而要講好一個(gè)故事,我們需要建立不同事件和人物之間的聯(lián)系,需要一個(gè)能夠?qū)⑾嗑嗌踹h(yuǎn)但屬于同一體系的人們連接在一起的機(jī)制,即便他們自己未必意識(shí)到自己身處同一體系之中。在這一點(diǎn)上,我受到了地理學(xué)領(lǐng)域的一些學(xué)者的影響,過去幾十年,他們提出了一種研究全球供應(yīng)鏈的方法,稱為“跟蹤物品”(follow the things)。這個(gè)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我們追蹤今天世界上任何一種大規(guī)模生產(chǎn)的商品——無論是冷凍蝦、橡膠球,還是一件運(yùn)動(dòng)衫——并將供應(yīng)鏈上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都與具體的個(gè)人聯(lián)系起來,比如在農(nóng)田里勞作的工人、在工廠里工作的工人、在倉庫里整理貨物的工人,甚至是駕駛卡車運(yùn)送這些商品的司機(jī),我們就能夠講述幾乎所有關(guān)于人類經(jīng)驗(yàn)的故事。與此同時(shí),我們也能夠認(rèn)識(shí)到這些人雖然處于同一個(gè)供應(yīng)鏈中,但他們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卻是多種多樣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而那個(gè)商品(比如冷凍蝦或運(yùn)動(dòng)衫)在運(yùn)輸過程中可能保持不變,但它所承載的人類故事卻是多層次的、相互交織的。這一點(diǎn)深深啟發(fā)了我,使我想到,這或許也是將新英格蘭的工人生活與奴隸制南方聯(lián)系起來的理想方法。
在書中,我選擇了一組非常普通的商品:種植園專用商品(plantation goods),包括帽子、鋤頭、鐵鍬、鞋靴和紡織品。這些商品在北方制造,最終被運(yùn)往南方種植園使用。我試圖追蹤這些商品的流動(dòng)軌跡,從最初的制造商,到商人和中間商,再到最終的消費(fèi)者。書中首先關(guān)注新英格蘭的企業(yè)家——他們認(rèn)為,如果能制造出一把堅(jiān)不可摧的鋤頭,或者一種完美的羊毛布料,他們就能賺取巨額財(cái)富。接下來,我聚焦于工人群體,即那些真正制造這些商品的人。然后,我討論了中間商,包括負(fù)責(zé)銷售和運(yùn)輸這些商品的商人及廣告商。隨后,我關(guān)注奴隸主,他們是這些商品的第一批消費(fèi)者——畢竟,正是他們購買了這些物品,用來裝備自己的種植園。最后,我來到奴隸這一群體,他們是這些商品的最終使用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也會(huì)根據(jù)自身需求來決定如何使用這些商品。因此在這個(gè)意義上,“跟蹤商品” 的方法,使我能夠講述一段仍然以人為核心的歷史故事。
您提到,“跟蹤物品”(follow the things)的方法深刻影響了您的研究,同時(shí)您在導(dǎo)論中也提到聚焦“物品的社會(huì)生命”(the social lives of objects)。這一方法是否對您的書籍結(jié)構(gòu)和行文方式產(chǎn)生了影響?我注意到,您的著作分為三個(gè)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于生產(chǎn),探討了新英格蘭的企業(yè)家與工廠工人;第二部分關(guān)注流通,研究了經(jīng)營種植園商品的中間商;第三部分則圍繞消費(fèi),首先分析奴隸主作為主要消費(fèi)者的角色,隨后延伸至被奴役者的消費(fèi)行為。您能否進(jìn)一步闡述,這一研究方法是如何塑造您的書籍結(jié)構(gòu)的?
塞斯·洛克曼: 是的,您準(zhǔn)確地描述了這本書的結(jié)構(gòu)。在構(gòu)思這本書的早期階段,我曾考慮是否要按照商品類別來組織章節(jié),比如:一章討論農(nóng)具;一章討論鞋類(footwear);一章討論紡織品(textiles)。但是后來我意識(shí)到,這樣的寫作方式會(huì)使書變得非常無聊。如果我采用這樣的結(jié)構(gòu),那么書中的物品本身會(huì)比人更受關(guān)注。而且,這種結(jié)構(gòu)最終可能會(huì)導(dǎo)致我在不同章節(jié)中重復(fù)講述相同的故事,因?yàn)橐浑p鞋所揭示的歷史,可能與一把鐵鍬或一把斧頭所揭示的故事十分相似。
因此,我決定不寫一本單純探討物品本身的書,而是聚焦于不同群體的人們,分析他們?nèi)绾闻c這些商品發(fā)生關(guān)系,以及他們的經(jīng)歷如何彼此不同。這樣一來,書中的物品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實(shí)體,而是變成了一個(gè)媒介,連接起那些曾經(jīng)生活在相同經(jīng)濟(jì)體系但卻彼此陌生的人們。換句話說,這本書關(guān)注的是“人與物品的交匯點(diǎn)”,而非物品本身。
此外,您書中精心設(shè)計(jì)的“插曲”(Interlude)章節(jié)令我印象深刻。這些獨(dú)立成篇的物件敘事充滿戲劇張力,既為全書注入情感共鳴,又深化了主題表達(dá)。您在構(gòu)思這些插曲時(shí),希望它們承擔(dān)怎樣的敘事功能?
塞斯·洛克曼: 這本書的一個(gè)獨(dú)特之處在于,我設(shè)計(jì)了三個(gè)簡短的“插曲”章節(jié)(每篇篇幅不長,大約三到五頁),每篇集中講述一件具體物品的故事。這些插曲既為讀者提供暫時(shí)抽離主線內(nèi)容的閱讀間隙,更重要的是要引發(fā)讀者思考:為奴隸制種植園生產(chǎn)物品的歷史,如何在公共記憶中被呈現(xiàn)或被遺忘。
我希望通過插曲部分討論這些問題:哪些歷史遺存了下來?我們能在博物館找到哪些物品?公眾記憶如何圍繞這些商品形成,或者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記憶是如何被抹去的? 例如,在其中一個(gè)插曲中,我探討了一只1838年的褐色工鞋——它曾在十九世紀(jì)末芝加哥世界博覽會(huì)上展出,在當(dāng)代卻被塵封于馬薩諸塞州北布魯克菲爾德歷史協(xié)會(huì)的檔案庫。在二十世紀(jì),這雙鞋的歷史意義被逐漸淡化,以至于如今仍然有很多當(dāng)?shù)氐木用穸疾恢溃麄兯幼〉牡胤皆?jīng)是美國奴隸工鞋制造中心。而恰恰是通過這些插曲,我希望能夠?qū)⑦^去與當(dāng)下聯(lián)系起來。

訪談中提到的1838年的褐色工鞋
我特別欣賞您通過插曲章節(jié)將歷史與當(dāng)下勾連的努力——比如您書中重點(diǎn)呈現(xiàn)的鞋靴等實(shí)物,使抽象概念變得鮮活可感。不過關(guān)于您研究的史料來源,您在導(dǎo)言中提到研究面臨實(shí)際困難:由于種植園相關(guān)實(shí)物遺存稀少,聚焦物質(zhì)文化研究頗具挑戰(zhàn)。能否具體談?wù)勀侨绾瓮黄剖妨暇窒薜模吭谘芯窟^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難與意外發(fā)現(xiàn)?這些經(jīng)歷又如何影響了最終的研究路徑?
塞斯·洛克曼: 確實(shí),與考古學(xué)家可以研究大量出土陶器不同,奴隸制時(shí)期的實(shí)物遺存非常稀少。大多數(shù)專門生產(chǎn)給種植園使用的商品本質(zhì)上是消耗品,它們在使用過程中就已經(jīng)被磨損、廢棄、遺失,因此很難被找到。這些物品既沒有被博物館精心保存,也沒有成為家庭傳承的遺物。因此,我們很難找到直接可考的奴隸鞋、奴隸衣物或奴隸使用的工具。
因此,盡管我想要研究種植園專用商品,但卻苦于實(shí)物遺存稀少。但研究中我最大的意外發(fā)現(xiàn)是:生產(chǎn)這些商品的北方企業(yè)在羅德島(我的居住地)、哈佛商學(xué)院以及眾多小型地方歷史協(xié)會(huì)和博物館中,保存著海量檔案資料。對于研究美國南方奴隸制的學(xué)者來說,“應(yīng)該去羅德島或馬薩諸塞州找資料”這種想法似乎不合常理——誰會(huì)認(rèn)為美國北方檔案館里存有講述南方歷史的證據(jù)?但這些商業(yè)檔案確實(shí)蘊(yùn)藏著大量奴隸制相關(guān)材料:奴隸主的來信、南方商人的函件、旅行推銷員的報(bào)告、公司代理人的備忘錄以及律師的法律文書。這些信件當(dāng)年被寄回生產(chǎn)種植園商品的工廠后,歸檔保存了數(shù)百年。正是這些記錄,使我得以發(fā)現(xiàn)種植園生活的新維度,并通過其他史料難以傳達(dá)的方式,“聆聽”被奴役者的聲音。舉個(gè)例子:在這些檔案中,我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奴隸主給北方制造商的信件,其中內(nèi)容大概是:“我和我的奴隸談過,他們說去年的布料質(zhì)量不佳。他們希望布料能夠編織得更緊密,顏色更深一點(diǎn),并且需要更多羊毛填充。”雖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直接得到了奴隸們的第一手口述歷史,但這樣的信件確實(shí)讓我們看到——奴隸對于他們所穿的衣物是有需求和偏好的。這些材料使我們能夠進(jìn)一步挖掘種植園勞工的社會(huì)史和勞動(dòng)史。
我注意到您在第三、第四章中將種植園勞動(dòng)與工廠工資勞動(dòng)進(jìn)行對比分析。您為何選擇將這兩種勞動(dòng)形態(tài)并置研究?這種比較對理解北方工業(yè)化時(shí)期種族、階級(jí)和性別因素的復(fù)雜互動(dòng)有何啟示?
塞斯·洛克曼: 種植園商品制造業(yè)的發(fā)展極為不均衡。它并未經(jīng)歷高度技術(shù)革新,也沒有依賴蒸汽動(dòng)力。相反,它通常由低技術(shù)、低技能工人完成,他們的工作方式與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幾乎沒有什么不同。有些工作發(fā)生在工廠中,但許多生產(chǎn)仍然是在家庭內(nèi)部完成的。例如:新英格蘭的女性和女孩通常在家中從事“外包手工業(yè)”(outwork)。商人會(huì)送來五十磅紗線,并告訴她們:“兩周后我會(huì)回來,到時(shí)候你們要用家里的織布機(jī)織出五十磅布料,作為回報(bào),我會(huì)用商店的信用點(diǎn)數(shù)支付你們,你們可以用這些點(diǎn)數(shù)購買生活用品。”對許多新英格蘭家庭而言,這種制造種植園商品的工作,并不需要離開家進(jìn)入工廠,也不涉及嚴(yán)格意義上的雇傭勞動(dòng),而是被融入到他們原本的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模式中。因此,許多農(nóng)民家庭的女性和女孩能夠通過這項(xiàng)工作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但她們的生產(chǎn)方式仍然屬于傳統(tǒng)的家庭勞動(dòng)體系。
但在本書第四章中,我希望聚焦于參與制造種植園專用商品的男性群體,他們的經(jīng)歷有所不同。盡管這些工人確實(shí)進(jìn)入工廠空間并以工資勞動(dòng)為生(即使他們從事的工作仍是低技術(shù)含量且非自動(dòng)化的),但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對“靠工資維生的男性是否算真正公民”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他們對自身身份有著不同期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發(fā)現(xiàn)許多工人一方面制造奴隸使用的工具(如斧頭),另一方面又在爭取自身權(quán)益,比如參加罷工,甚至舉著寫著“我們不是奴隸”(We are not slaves)的標(biāo)語。我對這種政治意識(shí)的矛盾感到非常好奇:這些制造奴隸用具的人,如何在社會(huì)認(rèn)同上將自己與奴隸區(qū)分開來? 這正是我在本書第四章想要探討的重要問題。
您在書中揭示了種植園商品具有多重意涵——同一件物品在制造商、中間商、奴隸主與奴隸手中呈現(xiàn)截然不同的功能與象征意義。我覺得這種動(dòng)態(tài)關(guān)系非常發(fā)人深省,尤其是您借鑒了“可供性理論”(affordance theory)等跨學(xué)科理論。您能否進(jìn)一步闡述這一動(dòng)態(tài)關(guān)系,并討論這些理論框架如何塑造了您的分析?
塞斯·洛克曼: 同一物品在不同語境中具有不同意義。在我們眼中,斧頭或許處處相似,但其象征意涵卻千差萬別。對于康涅狄格州的工人來說,制作一把斧頭每天能賺一點(diǎn)五美元,因此斧頭代表著勞動(dòng)的艱辛;對于旅行中的斧頭推銷員來說,斧頭象征著財(cái)富,他希望通過銷售它們發(fā)家致富;對于奴隸主而言,斧頭可能象征著恐懼,因?yàn)樗麄儠?huì)擔(dān)心奴隸用它作為武器反抗;對于被迫砍伐樹木的奴隸來說,斧頭是必需的生產(chǎn)工具,如何揮舞它才能在成百上千次砍伐中保護(hù)自己的脊椎不受傷害,是他們每天必須考慮的問題。
我試圖在研究中保持這種意義的多重可能性——物品的意義隨著持有者身份而流轉(zhuǎn)。但更關(guān)鍵的是,這些物品切實(shí)塑造著人類生存境遇:布料的透氣性直接影響奴隸的生存狀況,鞋底的靜音性決定著奴隸們夜間秘密集會(huì)的風(fēng)險(xiǎn),斧柄的力學(xué)設(shè)計(jì)左右著勞動(dòng)強(qiáng)度與效率。無論是奴隸、奴隸主、制造商,還是工廠工人,每個(gè)人對這些商品都有不同的期待和需求。因此,我希望在書中同時(shí)呈現(xiàn)這些不同的角度,讓讀者理解商品不僅僅是物品,更是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媒介。
您在書中也討論了被奴役者如何在這樣一個(gè)壟斷市場中同時(shí)扮演生產(chǎn)者與消費(fèi)者的雙重角色,以及他們?nèi)绾卧趹?zhàn)前南方被當(dāng)作貨幣或信用工具使用。這些多重身份揭示了當(dāng)時(shí)經(jīng)濟(jì)體系的哪些本質(zhì)特征?
塞斯·洛克曼: 十九世紀(jì)的美國缺乏穩(wěn)定的國家貨幣體系,跨區(qū)域支付面臨巨大挑戰(zhàn)。 由于南方種植園主通常以信用交易的方式購買商品,他們往往承諾在六到八個(gè)月后的下一次收獲季節(jié)償還債務(wù)。但如果棉花價(jià)格下跌,他們可能無法支付賬單。當(dāng)他們無力償還債務(wù)時(shí),他們就需要出售資產(chǎn)來籌集資金。那么,什么資產(chǎn)最容易出售?當(dāng)然是奴隸。實(shí)際上,在許多情況下,奴隸主通過出售奴隸來償還欠北方制造商的債務(wù)。這說明了一個(gè)關(guān)鍵事實(shí)——奴隸被視為一種可流通的商品,其變現(xiàn)能力成為跨地區(qū)商業(yè)交易的最終支撐。有學(xué)者也曾指出,這一時(shí)期美國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并非金本位或銀本位,而是“奴隸本位”。
您在本書中除了解釋南北方之間共謀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外,您在第八章《商業(yè)脫嵌》(“Commercial Emancipation”)中還探討了南方奴隸主試圖擺脫北方制造業(yè)控制的努力,例如建立自己的紡織產(chǎn)業(yè)和種植園商品制造業(yè)。我想請問下,這種動(dòng)態(tài)關(guān)系如何與您的主要研究問題相呼應(yīng)?
塞斯·洛克曼: 南方奴隸主常常認(rèn)為北方制造商是種植園農(nóng)業(yè)的受益者。他們相信北方是靠南方致富的。當(dāng)北方活動(dòng)家開始將奴隸制譴責(zé)為道德罪惡時(shí),南方奴隸主變得更加惱怒。因此,他們試圖宣布經(jīng)濟(jì)獨(dú)立,并宣稱要自主生產(chǎn)商品。每當(dāng)棉花價(jià)格下跌時(shí),這些雄心便會(huì)付諸實(shí)踐。但一旦棉價(jià)回升,奴隸主便停止設(shè)想建造工廠,轉(zhuǎn)而又回去種植棉花。他們抱怨連連,但比起經(jīng)濟(jì)多樣化,他們更熱衷于追逐利潤。正如一位滿懷抱負(fù)的南方制造商哀嘆的那樣:大多數(shù)奴隸主寧愿購買最激進(jìn)的廢奴主義者制造的工具——只要價(jià)格足夠低廉!





- 澎湃新聞微博
- 澎湃新聞公眾號(hào)

- 澎湃新聞抖音號(hào)
- IP SHANGHAI
- SIXTH TONE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