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知識、權力與民族性——讀《憂郁的牢籠》
第四太陽紀元,終末。
水很冷。
由于缺少日光照耀,最柔軟的事物也長出了尖牙,撕咬著化身成美西螈的死神修洛特爾幼嫩的皮膚。
死神恨恨地擺擺淺粉色的尾巴。為了躲避那個蒙著鳥臉的瘋子,他已經逃入過玉米地、藏身在龍舌蘭間,依靠變身的天賦化成身旁的作物。但是羽蛇神似乎總能看穿他的偽裝,誓要完成殺戮,用所有神祇的生命獻祭。
跟他不一樣,修洛特爾不想輕率地死。他不想把自己的消失當作交換未來希望的籌碼。在神的世界里這是可恥的,因為此間諸神應該重義輕利、蔑視死亡。但死神想從這個故事里跑走,跑進一個不需要死掉的故事里。
“他媽的,這張傻臉只會微笑”。風刃切開水面,切下他的頭顱時,修洛特爾還在想著這件事。
********************
蝙蝠與死神
作為沒有在學術機構供職的研究者,我常常與學界同好笑稱自己是一只野生知識分子、拉封丹寓言里溜出的蝙蝠:非鳥非鼠,享有著職業學者沒有的閱讀自由與悠然視角,也需要更多的自我證明,才能在學術共同體中得到應有的尊重。墨西哥歷史學家恩里克·克勞澤嚴肅地否定了我的玩笑:對他而言,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從事不受任何組織資助的研究,并通過文章積極參與國家事務,體現的是一種重要的獨立性。
對于已經獲得學術成就和公共影響力的學者而言,這種獨立性不僅珍貴,也值得尊敬;但對于更大范圍的知識分子群體而言,身份依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族群性格、身份認知與不同范圍的知識分子群體,往往呈現出相互建構的循環過程:知識分子探究、描述與總結人群文化特性,而他們的思想產品又在更長的時間線和更廣闊的空間范圍內塑造著面對的人群。這種身份的詛咒在一代代知識分子的灌溉中逐漸壯大成為一個群體的文化圖騰,繼而又影響著更多后來者。
此類圖騰標記了學派、社會群體,甚至擴大到民族國家或更大范圍。當我們透過經過翻譯乃至轉譯的學術作品去了解他者時,這些圖騰就成為路標和燈塔,將探索者帶到被苦心打造的意象之境中,去接受一套套典型敘事。
“我們血管里印第安人的血越多,死亡的吸引力就越大”;“墨西哥人對死亡的漠視,由其對生命的漠視而來”……這些“蔑視死亡的墨西哥人”說辭就構成了這樣一種典型敘事。然而修洛特爾逃避求生的傳說與思想界賦予的“民族性”之間,產生了一絲微妙的縫隙。很難判斷這個縫隙,與羅赫爾·巴爾特拉找到的社會學縫隙有多大程度的重合;但能夠確定,在這里,歷史文本、神話表現與相關學術論述沒有做到真實對應。
在傳說中,修洛特爾最終化為了一只美西螈。而“美西螈”和它背后的一系列意象,就像是一面矗立在特諾奇蒂特蘭古城上的圖騰大纛,標記著墨西哥人應當具備的形象。而對它的討論,正是羅赫爾·巴爾特拉在《憂郁的牢籠:墨西哥人的身份與異變》中的核心主題。
********************
1984年2月,巴黎植物園。
胡里奧·科塔薩爾隔著透明玻璃幕墻,和水族箱里面的美西螈對視。
雖然那張面孔只會呆板地微笑,但科塔薩爾知道自己對面的其實是阿方索·雷耶斯。
因為哲學家金色的雙眸在對他傳遞著信息:
“我的頭顱是印第安人的,可腦灰質卻來自歐洲。我是一只混血兩棲動物。
“而你也是一只混血兩棲動物。”
等科塔薩爾緩過神來,對面竟變成了一張長滿胡須的熟悉面孔——自己居然被換入了水族箱中。
“不要緊,你在外面吧,”科塔薩爾心道,“外面是一個更大的牢籠。”
********************
從美西螈開始
我欣賞羅赫爾·巴爾特拉的探討,更喜歡的是他對議題的選擇。“民族性”是任何當代文化思想群體都無比鐘愛的議題,存在著跨越學科的廣泛視角以及其他議題無可比擬的現實性。總結陳述如《菊與刀》,群像訪談如《大分裂》,以及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本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中的多部佳作,成為了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重要倚仗,也反哺了對當代國際事務中一些現象的解釋。
拉丁美洲由于其知識群體的復雜背景,這方面的研究則更為具體而豐富。曾經有學者列出書單,建議將《憂郁的牢籠》與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薩穆埃爾·拉莫斯(Samuel Ramos)有關民族性的著作合并閱讀,以便更好地了解“墨西哥民族性”和“墨西哥學者對于民族性的態度”。
但是這部書的出發點,與《孤獨的迷宮》和《面具與烏托邦》迥然不同,甚至在某些問題上持相反的意見與批判的態度。我更愿意相信巴爾特拉在墨西哥版序言中所表示的,一位左派知識分子對“民族性”敘事(或更直接地說,霸權敘事)的祛魅和解構的探索:
有關“墨西哥性”的意象并不是大眾意識的反映(將這種意識假設為一種單一、同質化的實體存在,是值得懷疑的)。另一方面,雖然這些想法是由知識精英提煉出來的,但我不會只把它們當作意識形態表達來處理,而主要將其歸作霸權文化所制造的神話。
不同于內容排布與論述中的浪漫主義,以整書而言,巴爾特拉在嚴肅而謹慎地面對著這一問題:墨西哥民族性的建構者們是誰,或者說他們應當是誰?如果這些詮釋者確實具有天然合法性,他們的論述就一定是符合實際的嗎?
美西螈就在這一刻出現了。和科塔薩爾一起,展開了一場對拉美文學讀者而言熟悉又陌生的魔幻對話。從美西螈阿方索·雷耶斯開口講話開始,科塔薩爾的小說原著被巴氏借用,呈現出了全書第一次異變,也給我初始的翻譯工作增加了許多難度和樂趣。在兩位杰出的駐法記者幫助下,我復原了巴黎大清真寺附近的地形地貌,將這場虛擬的跨物種對談還原到巴爾特拉期待的“真實”之中。
從美西螈開始的外延探索,帶來了這部作品的第二個特點——堪稱獨特的內容排布。作為墨西哥人類學與社會學界久負盛名的知識分子,巴爾特拉已經擺脫了學者寫作的一貫模式,轉向了富于文學創造性的學理表達。他在奇數章引入了十數個有關美西螈的文學作品、民族神話與博物掌故,在偶數章展開對于墨西哥“民族性敘事”的研究與批判。這種陰陽嵌合的表述方式,讓這部作品在嚴肅討論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種結構上的音樂性。這也使得翻譯的過程變成了一場場在不同場合進行的、風格迥異卻又存在連續性的對話,從美西螈開始,至現代社會中的墨西哥人而止。
********************
20世紀,墨西哥城一家烏有的咖啡店。
“您相信,”埃米利奧·烏蘭加扶了扶眼鏡,“墨西哥人由于自卑被判斷為無能;而我的判斷則完全相反,是由于無能而呈現出自卑。”
對面的薩穆埃爾·拉莫斯有些不快:“請注意,‘無能’源于自身,而‘自卑’來自外在世界的評判,從而扭曲了價值觀。我們在墨西哥人身上看到的正是這種價值的紊亂,就像你的想法,是不是在無意識中回避‘自卑’呢?”
“與其說自卑,不如說孤獨。”奧克塔維奧·帕斯放下裝著歐洽塔的杯子,“感到孤獨不是感到低劣,而是感到不同。”
“親愛的詩人,您錯了,”拉莫斯強調,“您在墨西哥人面具的背后找到了孤獨,可如果您觀察得更仔細,會發現這種孤獨并非自愿的決定。”
********************
赤誠打造的牢籠
與拉美大陸上大多數國家類似,墨西哥擁有大量世界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學者表達政治意見的比例和頻率都非常可觀。如果再將容留流亡知識分子與革命者的傳統計算在內,墨西哥可稱為這一領域的代表(也包括巴爾特拉本人,其雙親均為加泰羅尼亞流亡者)。從這一部書內,我們就可以讀到數十位對墨西哥民族性議題闡述過意見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呈現了豐富廣闊的思想來源。
但同時在本書的視域下,墨西哥政治權力的掌控者、墨西哥知識群體、普通墨西哥民眾在這種敘事中也存在著災難性的歷史性割裂。如今,在墨西哥城古城區的北端有一座享有盛譽的“三文化廣場”,在一座廣場的范圍內可以同時遇見前哥倫布時期的原住民文化、殖民時期文化以及現代墨西哥文化遺跡,完美地詮釋了這個混血國家的文化基因。思想界的顯學普遍認為這三個時期的文化在當代得到充分融合,形成了當代墨西哥的民族文化。
顯然巴爾特拉并不完全認同這種觀點,這與我在墨所見所學可作印證:三種文化的印記并不能像光線一樣均勻地投射到每個墨西哥人的觀念中。盡管在很多意義上,由于知識分子的苦心經營,墨西哥平民往往被灌輸自己擁有或應該擁有怎樣的民族性格、優點與劣根性,但日常生活表現中,常常觀察不到那些虛無縹緲的民族性格普遍存在的證據。
在巴氏的論述中,民族性格的探討轉變為民族主義敘事的牢籠,是一個漫長的充斥著權力的陰謀、或傲慢或真誠的詮釋,帶給作為接受者的墨西哥民眾品類豐富、口氣篤定、有各路權威背書的洗腦套餐。為此,他在書中設計了一次核心知識分子的咖啡館對談(本書第十章),探討墨西哥人的形象、墨西哥人的共性與個性,以及“墨西哥人的哲學”存在的可能性和可能意義。在其中,他也借著旅墨西班牙哲學家何塞·高斯(José Gaos)之口,講出了這件事的荒謬性:
不存在“一種”墨西哥人,而只存在地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意義上不同的墨西哥人——高原或海邊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克里奧爾人或梅斯蒂索人;殖民地時期的、墨西哥獨立時期的、墨西哥革命時期的或與我們同時代的人;流浪漢、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農民……所以“墨西哥人的哲學”并非在發展其他哲學,如果有的話,也是任意選取的某些墨西哥人的哲學……
這種質疑,在哲學上無疑是根本性的。高斯的話語可以當作結論,而對該結論的論證,以及對于其影響的研判,貫穿了整個《憂郁的牢籠》。對于詮釋合法性的問題,書中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客觀而言,巴爾特拉與他的墨西哥同儕權利平等;但同樣的思想土壤與相似的使命感,給他們帶來的是相異甚至相反的理念。
在翻譯涉及幾十位墨西哥學者的相關論述時,也讓我回憶起多年來涉及墨西哥民族性議題的閱讀。在本土性意識之外,墨西哥知識分子身份背景與學術背景國際化程度極高,也讓他們在這個老問題上總能引入新學派、新理論,像是秀美聰慧的牡丹鸚鵡,極力收集外來所有的羽毛、亮片和鮮花嫩枝,打造最美麗的窩巢。
在巴氏的梳理下可以見到,研究者固然并非都是善意的(混雜著人種學的歧視與殖民主義的傲慢)。但仍然有許多當代文化人心懷赤誠,盡力對墨西哥性中“原始的天堂”、自卑與憂郁等問題進行觀察評述以期啟迪國民,但卻終究鑄成一座圍困民族火焰的思想牢籠。
********************
流浪漢坎丁弗拉斯從后門進入,攪亂了思想者們的沙龍。
正在發言的是安東尼奧·卡索:“似乎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之間存在著某種深刻的聯系,在兩族混血之后,優點各自保留,缺點卻合而為一。”
邋遢的流浪漢嘿嘿笑了:“您幾位要感謝墨西哥人的毫無價值,不然‘墨西哥性’早就被白人們搶光了。”
導師巴斯孔塞洛斯緊皺眉頭:“怎么沒有優點?我們混血而生,是宇宙的種族,是代表未來的種族,將會建立光輝燦爛的混合文明!”
坎丁弗拉斯聳聳肩:“在我這兒,所有的想法都值得被尊重,無論是小主意還是蠢想法。”
最莊重的墨西哥人和最戲謔的墨西哥人對視無言。最終,墻角的西班牙人打破了沉默。奧爾特加·伊·加塞特說道:
“也許墨西哥性一直在流動,而不是一種定論。墨西哥人是墨西哥居民和墨西哥環境的聚合。如果沒有置身其中,墨西哥性也無從尋蹤。”
坎丁弗拉斯浮夸地點頭:“這才是關鍵。要是你們聽不懂,我也不會向你們解釋,那是那些‘明白人’的任務。如果他們真的如自己想的,真正了解這個問題。”
********************
隱秘的枷鎖,自由的夜燕
墨西哥知識群體,尤其是近代墨西哥知識群體,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群有知識的普通墨西哥人”,這一現象也并非孤例。由于殖民歷史的存在,墨西哥人雖在人種上實現了“宇宙種族化”,形成了中國讀者印象中的“現代墨西哥人”群體,但財富、知識和社會資源的不平衡,也對知識分子的出身背景造成了自然篩選。
這就是我談及的,三文化的印記并不像自然光線一樣普照墨西哥,定義者(知識群體)與被定義者(普通民眾)也并非完全對標。巴爾特拉的擔憂,一部分也自此而來。巴爾特拉對于“野蠻”“憂郁”和墨西哥政治權力的研究,自上世紀70年代至今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延續性。這幾項元素的結合,也成為了貫穿作者這部代表作的主線。
坎丁弗拉斯式的廢話文學,無論是其他學者眼里的批判與解構,或是巴氏判斷中將政治蠱惑的合法化,都指向了相似的方向:威權。威權者是民族性敘事中不顯露名字的參與者,也是最有力量的參與者。一種成形的民族主義敘事,無論是鄉村的伊甸園還是城市的流浪漢,乃至本書中的美西螈范式,都可以被引導和轉變成一種掩蓋現實問題的政治文化——這次呈現的是“革命民族主義”。
“墨西哥人被驅逐出了民族文化”,墨西哥知識界打造出了供權力驅使的文化弗蘭肯斯坦。巴爾特拉的視角與論證充滿了破壞力,試圖將思想界前人與同時代人精心建筑的理論大廈一擊而潰。民族性和民族哲學研究依然散發著迷人魅力,但在《憂郁的牢籠》加持之下,也隱隱透出危險的氣息。
這種嘗試是否是有價值的?作為譯者,在與作者漫長的筆談中,我得到了自己的結論。如果可以暫時擱置墨西哥知識界對于民族性的論述孰高孰低,對于一個“墨西哥人”而言,或許打破樊籠、不歸屬任何定義,真正像蝙蝠一樣在黑夜中自由飛翔,才能遠離修洛特爾的隱喻,靠近克察爾科亞特爾的傳說。
(本文系《憂郁的牢籠:墨西哥人的身份與異變》一書“譯后記”,本次刊發時又做了補充、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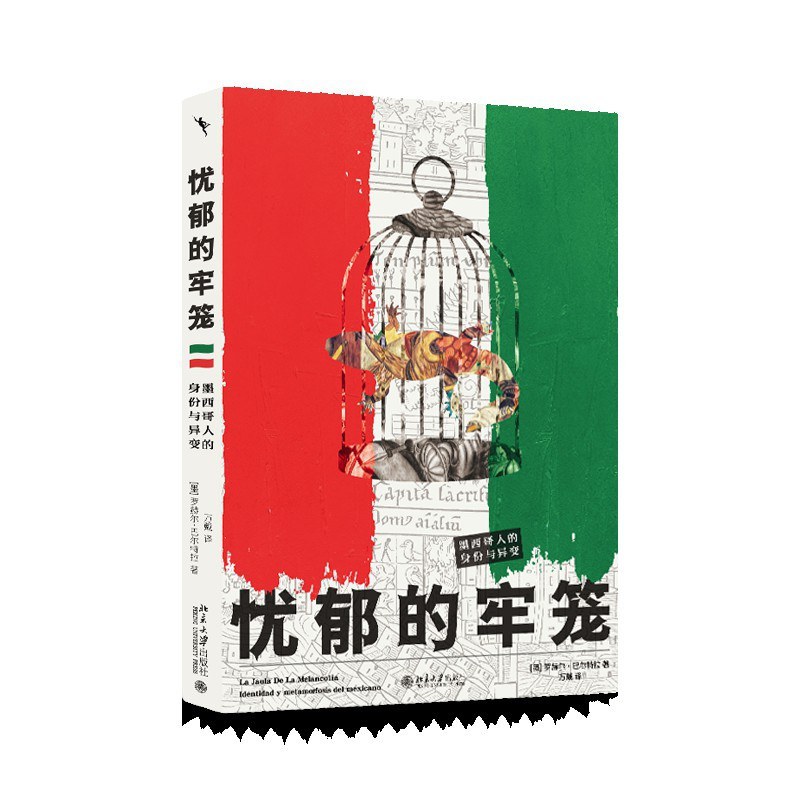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