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安德魯·阿伯特談閱讀、知識和社會學的未來

安德魯·阿伯特(章靜繪)
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他1982年獲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在羅格斯大學任教一段時間后,1993 年返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執教,歷任芝加哥大學學院社會科學部長、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2000年至2016 年,阿伯特任《美國社會學期刊》主編。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職業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主要著作包括《職業系統》《學系與學科》《學科的混沌》《攸關時間》《過程社會學》等。阿伯特多本著作的譯者、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周憶粟對他做了專訪。在這篇訪談中,阿伯特對自己的學生時代和職業生涯做了回顧,并談及了對閱讀、知識和社會學的未來的看法。
您在高中時候曾經想成為一名科學家,大學時候學習的是“歷史與文學”專業。是什么促使您選擇了社會學?您在芝加哥大學發現社會學是偶然的嗎?
安德魯·阿伯特:我十幾歲的時候已經很不安分了,對很多事情產生了興趣。我選擇社會學,是因為1960年代讓我開始思考很多棘手的社會問題,比如越南戰爭、種族歧視、宗教信仰是怎么受到社會影響的,等等。社會學能讓我用各種方式來研究這些問題,而不需要固定在某一種方法上。
當然,這里也有些巧合。在大學第一年,我主修的是“1750-1850年的英國歷史與文學”。主要是因為我就讀的學校有一個復雜的規定,導致我沒法選“社會研究”專業。但很快我就對社會科學產生了興趣。其實我早該換專業的,只是那時候哈佛沒有社會學系,只有一個叫“社會關系”的專業,這個專業人很多,課程也比較輕松,但沒什么太大的意義。一直到我應征入伍在軍隊里申請研究生的時候,我才下定決心申請社會學專業。
您的第一個職位是在羅格斯大學。是什么促使您在1993年回到芝大?是因為受到了“芝加哥學派”的召喚,還是單純地做了一個合理且時機正確的職業選擇?
安德魯·阿伯特:我在1988年出版了《職業系統》(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16年)后,幾所大學都對聘請我表現出了興趣。我最后選擇了芝加哥大學,主要是因為學術、工作和家庭的原因。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的研究早就受到了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在準備我的畢業論文開題時,我廣泛閱讀了芝加哥學派的作品,對它們非常熟悉,也覺得這和我的智識興趣很契合。
到了芝加哥之后,一些機緣巧合和自己的選擇讓我逐漸明確地與芝加哥學派聯系起來。我在1992年的美國社會學學會索羅金講座中探討了芝加哥學派在理論上的重要性,還著手寫了系里和《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中譯亦稱《美國社會學雜志》)的歷史。到1990年代末,我已經成為系主任和《美國社會學期刊》的主編。所以,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已經成了芝加哥學派的一部分了。
在諸多與您相關的書中,有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多樣化的社會想象力》(Varieties of Social Imagination,中譯本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一本主要針對非歐洲或北美社會研究者的作品評論合集,由您假托為芭芭拉?塞拉倫特(Barbara Celarent)寫成,并將之編訂成一本書。中國讀者在《大學教育與知識的未來》(三聯書店,2023年)中讀到了此書中的三個章節:塞拉倫特對瞿同祖、陳達、費孝通著作的書評。芭芭拉和安德魯有什么不一樣?
安德魯·阿伯特:芭芭拉的寫作風格和我的《學科的混沌》以及《攸關時間》(二書已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類書有明顯的不同。后兩本書的寫作帶有辯論性,因為作者安德魯都參與了某些特定的學術爭論。而芭芭拉的風格更為冷靜和審慎。她喜歡的作家會大力推薦,而對那些她不欣賞的,她只是選擇不提,而不是像我那樣直接批評。她要比我成熟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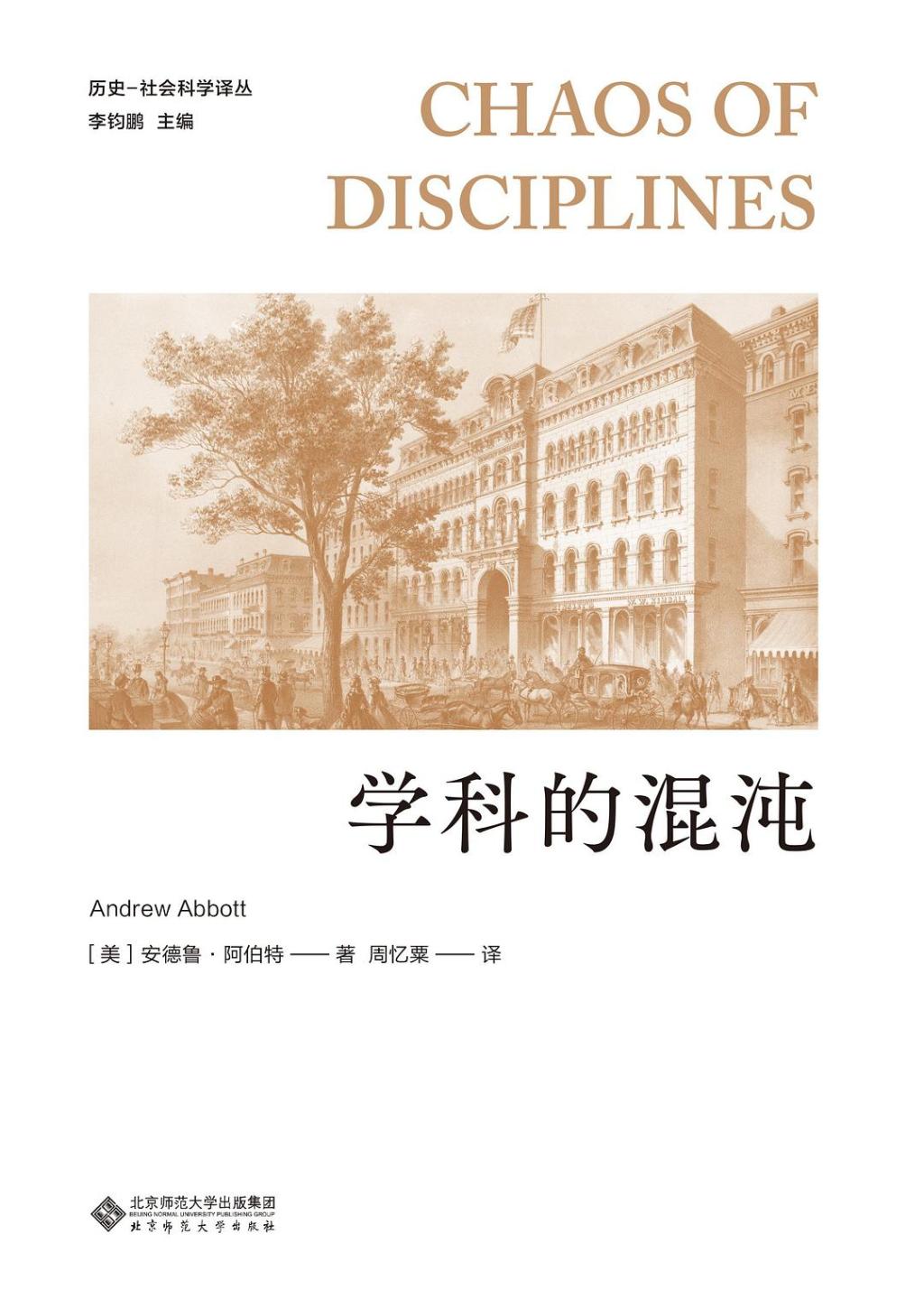
《學科的混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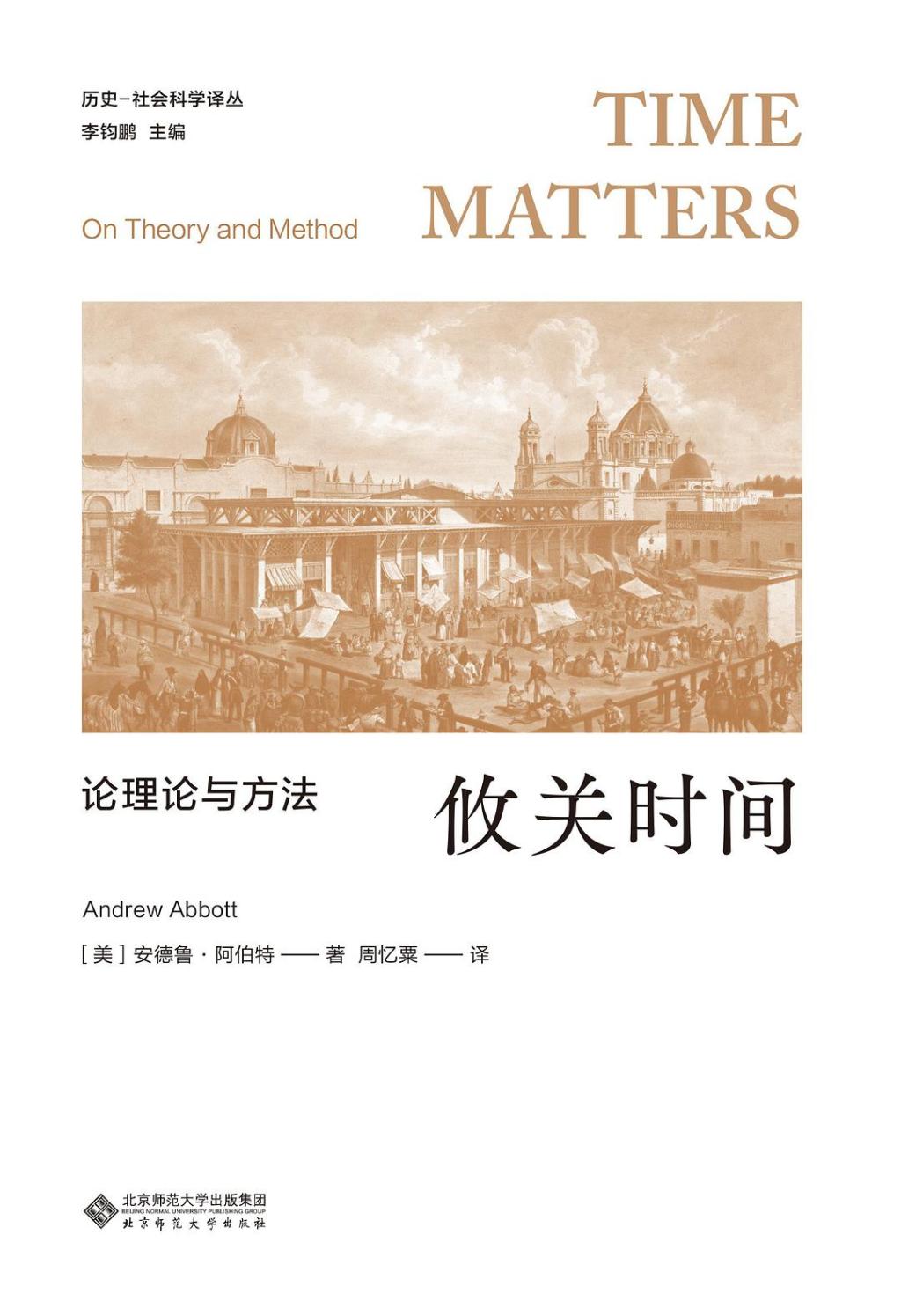
《攸關時間》,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今年要在中國出版的《探索之道》(Methods of Discovery,上海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在您的諸多著作中受眾最廣,銷量也很好。但我自己在教學中,聽學生表示這本書看似簡單,實際上由于其中涉及的知識廣度,很難一下子理解。您為何寫作《探索之道》一書?在寫完此書后,您都收到了來自學生和同行們的哪些反饋?
安德魯·阿伯特:除了聽到一些關于把這本書用在教學上的個人反饋外,我幾乎沒收到什么對《探索之道》的直接評論。說實話,這本書賣得還不錯,但真正讓我吃驚的是,它在Google Scholar上竟然有一千四百八十次引用(Web of Science上有三百八十四次)。我從沒想過這本書會被引用,它本來只是一本寫給學生用的教材。
讓我更意外的是,學生們居然會對書里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風格感到驚訝。我對很多不同的東西感興趣,我也以為別人和我一樣。豐富的多樣性本身就是一種樂趣,這也是我成為社會學家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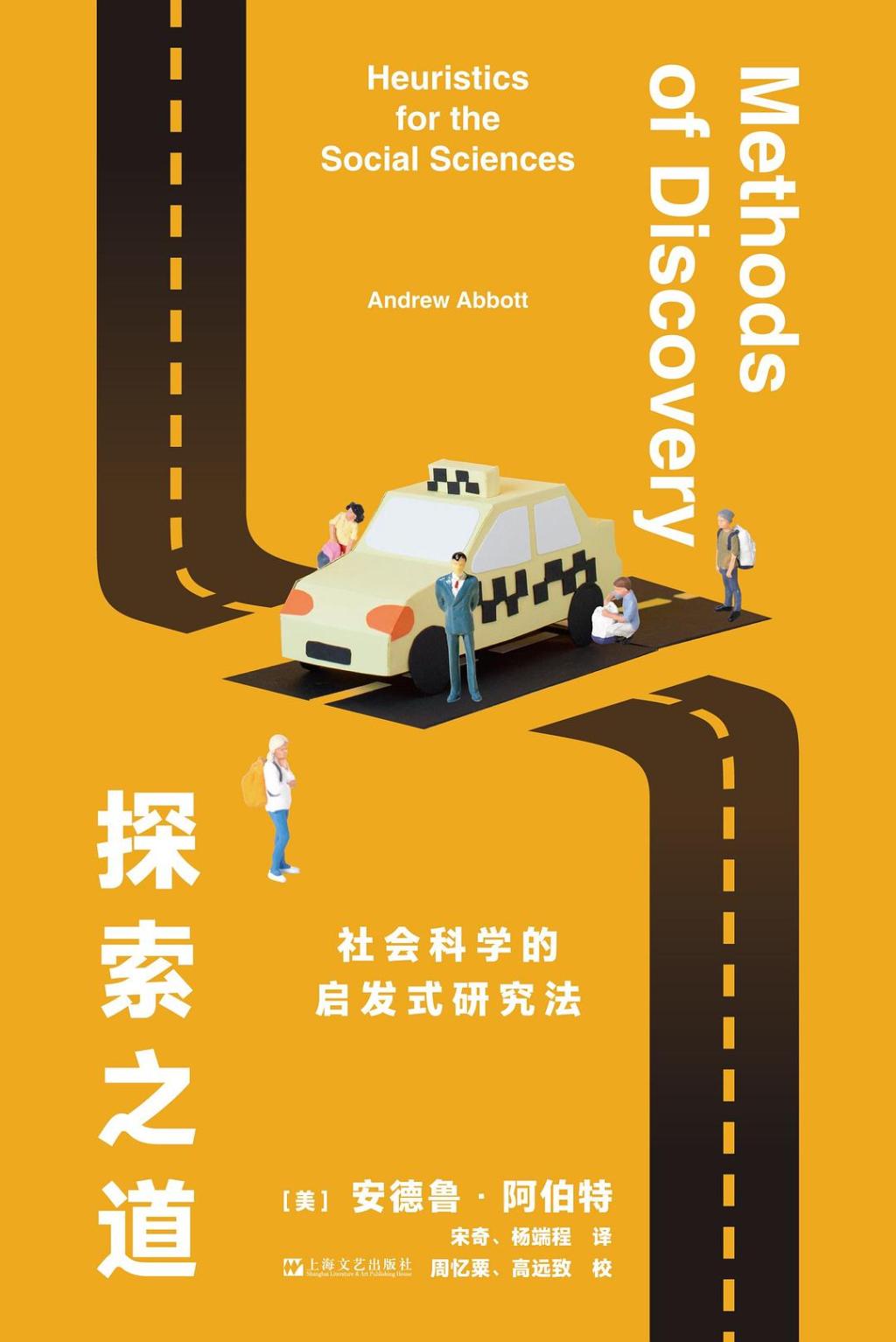
《探索之道》,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3月即出
《探索之道》的宗旨,用中國俗語說就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但是對大部分中國社會學本科(甚至碩士)的學生而言,恐怕打魚遠比燒魚難,“發現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用您的話說,一個puzzle)可能要遠遠難于對一個題目進行分析、論證、搜集整理數據材料……您能結合《探索之道》談談,作為一個社會學的入門者,如何“尋找謎題”嗎?
安德魯·阿伯特:想想伊本·赫勒敦。他在《歷史緒論》(Muqaddimah)里說過,別急著做簡單總結!如果我覺得可以用一句話教會人捕魚,我早就只寫一句了;如果用一段話就能教年輕人怎么找到一個謎題,我也只會寫一段話。
我后來寫的《數字論文》(Digital Paper;中譯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里也談到了謎題。在《探索之道》出版后的十年里,我在教學中開始強調兩個關于謎題的重點:第一,謎題必須是“為什么”的問題,而不是“怎么發生”的問題;第二,謎題必須有兩個真實的備選答案。
我做的這些教學上的變化,其實是因為學生變了。隨著美國的學生們越來越傾向于持有強烈的政治立場,許多人不自覺地把研究重新定義為一種尋找數據來證實自己既有觀點的過程。作為一名資深教師,我明顯觀察到了這種逐漸走向政治化研究的趨勢,盡管學生們自己往往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我不得不調整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們避免將學術研究異化為純粹的政治工具。
一些《探索之道》的讀者告訴我,這本給本科生的書,是為了啟發他們提出好的社會學問題的入門作品;但實際上,由于本科生的閱讀量不大,反而會比較難以理解本書中的很多內容。用您自己在《專業知識的未來》(中譯載《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十二輯)中的話來說,他們的頭腦中欠缺那些“小鉤子”,讓他們可以把新讀到的內容和先前的知識聯系起來。您如何建議他們使用這本書?
安德魯·阿伯特:面對學生閱讀能力持續衰退的現狀,我們似乎還未找到明確的解決方案。但這種衰退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要扭轉這一趨勢,就必須設法讓學生擺脫對社交媒體的依賴。然而,就普通學生群體而言,這個目標恐怕難以實現。因此,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培養一個規模較小的知識分子群體,使他們精通“圖書-閱讀者技術”(book-reader technology),并建立起有效閱讀所需的廣博知識儲備。
[采訪者注:book-reader technology是阿伯特理論化(圖書館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時提出的說法。在標準社會科學研究中,數據被研究者引出(elicit,可以是主動的如問卷和訪談,也可以是被動的如人口普查),然后通過一套概念和測量標準被轉化為分析對象。在圖書館研究中,數據來自先前別人所做的研究,通過“閱讀和瀏覽”這兩種關聯性算法(association algorithms)被研究者從文中提取。在這個過程中,結合讀者自身的知識,生成輸出,即某種理解。讀者們可以把這個與“網站-瀏覽者”技術做一個對比。在瀏覽網站的時候,我們碰到的超鏈接是預先嵌入在頁面里面的,所以所有的讀者都會被引導到同樣的特定頁面。但是在圖書閱讀時,超鏈接是在閱讀過程中動態生成的,取決于讀者的知識和文本的潛在含義相結合的程度。很顯然,這依賴于讀者已有知識的豐富程度。相關見解系統性地收錄于《數字論文》一書,以及《傳統的未來:關于圖書館研究的一項計算理論》(2008)一文中。]
讀過您著作的讀者往往都被您廣博的知識面吸引,您在很多場合也表示自己更愿意成為一個“通才”,但今天的學術訓練和學院文化都在整體上把學生往專才的道路上推進。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安德魯·阿伯特:的確,今天的學術文化把學者們推向了越來越窄的專業化方向。一些研究和交流的技術也是如此,尤其是現在的引用和審稿系統,已經不再是為了鼓勵優秀研究,而是變成了一種管理工具,因此它正在迅速破壞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中的知識。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有點像藏傳佛教徒清掃沙壇城的儀式。二十世紀的知識體系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創造了龐大的知識量。這些領域大多是非累積性的(比如,誰能說《紅樓夢》有最終的唯一解讀呢?)。所以我們需要時不時地抹去那些已經積累的知識,重新開始。畢竟,啟蒙的意義在于創造知識,而不是擁有知識。微觀專業化和那些沒有意義的引用,都是在破壞社會科學的知識創造過程。
因此,我們也可以把“通才”看作是一條通往新知識的道路。不過這種通才式學科研究最終可能也會變得程式化、專業化,屆時我們可能又需要重新“破壞”一次。
總之,可以說我的這種研究風格,其實是因為我一直在反對那些過度專業化的東西,這才賦予了它意義。
使您成為通才的一大要點是廣泛的閱讀。您曾經說過,“研究生階段讀的書塑造了你是誰”(You are what you read in graduate school),從您學生的記述中,我們知道您除了藏書豐富、閱讀廣博之外,還每學期都組織“隨機讀書小組”:若干名各個階段的學生,每周挑一個主題,各自闡釋,然后找一本書,大家坐下來一起讀,然后討論。閱讀的重要性雖然被廣泛提及,但在專才導向及技術化導向的學術生產體制下,很多學者都不再讀書了(他們只讀論文)。在您自己的學術工作以及智識生活中,閱讀扮演怎樣的角色?
安德魯·阿伯特: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我一直都在讀書。我大多數時候讀的是虛構作品。我通常會在睡覺前花一個小時看小說或文學作品。而且我在周五的“隨機閱讀”小組里讀到的書,常常會吸引我的注意,讓我去借出來認真讀。在教學期間,我也會讀(或者重讀)課程的材料。我還經常讀學生的論文章節和草稿——我許多最好的想法,都是在把我的理論應用到這些論文中時產生的。
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我已經不再讀別人的理論書了,因為我忙著寫自己的東西,而且要確保它們前后連貫。不過,我常常讀或者重讀一些實證研究的專著。比如,去年我讀了幾本關于互聯網行為的民族志研究。有時候我也會為暑期選個主題,然后集中讀很多相關的書。兩年前我選的是“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去年則是“古代(西方)歷史”。
總之,我的桌子上總是堆滿了我計劃要讀的書。大概有一半會被我實際讀完。
所以您認為“讀者-書籍技術”(book-reader technology)不會被 AI 的熱潮取代,對嗎?為什么?
安德魯·阿伯特:嗯,我大約十五年前在一篇文章里討論過的“讀者-書籍技術”會繼續存在。至于它將來會如何與AI以及由AI帶來的各種知識形式相結合,這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個話題太復雜了,在這里沒法深入探討。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我們正走向一場關于知識本質的大型哲學討論。AI的基礎是完全接受“真理符合論”,也就是說,認為每個知識點都可以有一個“最優、最終的表述”。
但顯然,這種模式并不適用于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對人文社科,我們需要不同的關于知識理想的標準。而由于大多數開發AI的人都是自然科學家,他們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夠深入,所以還需要時間來理解這些學科跟自然科學,比如分子科學,完全不同的知識系統。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音量可能很大。
即便如此,對我們現在的人文和社會科學中的知識觀念提出挑戰,其實是件好事。因為這些領域很久沒出現什么偉大的新思想了,確實需要被好好攪動一下。
接著上一個知識觀的問題。您在哈佛大學的時候就通過費正清先生與中國相遇,也閱讀過大量中國文學和歷史,您覺得中西方在教育和對知識的理解上有怎樣的不同?
安德魯·阿伯特:我上的第一門與中國相關的大學課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十七年的時候,那是1966年秋天。當時中國發生了很多令人驚訝的事情,但費正清先生還是主要從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來講解中國。第一學期他講到十九世紀早期,第二學期講的是從十九世紀到當代。不過第一學期課程進展很快,快速掃過了長時間段的歷史。
之后,我的閱讀讓我不時回到中國。所以我依次讀了《紅樓夢》《儒林外史》《西游記》《水滸傳》和《金瓶梅》(當然是英文版)。它們都是1970年代末的老版本,要么是通過德文轉譯的,要么是不完整的譯本。我在羅格斯大學的頭幾個月里,晚上沒什么事干,就把這些中國經典都看完了。
1991年我回到芝加哥時,隔壁辦公室的白威廉教授(William Parish)是位中國研究專家,不久之后我們又請了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所以我們經常討論中國。不過真正讓我開始更多研究中國的契機是2000年之后大量中國研究生的涌入,以及白教授2006年的退休。自此我開始參與很多中國學生的論文答辯,后來幾乎每個中國學生的研究都會參與,所以我需要更多了解中國社會。
但學生的研究讓我又回去重讀了費正清和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四十年后,我終于把這些內容都弄明白了。在余國藩教授(Anthony C. Yu)的指導下,我重新開始閱讀中國古典小說。他是第一個把《西游記》完整翻譯成英文的人。我們一起吃了很多次愉快的午餐,爭論《紅樓夢》里的各種觀點。在他的鼓勵下,我在2016年去中國之前把所有重要的中國古典小說又讀了一遍。遺憾的是,我的同事和老師在2015年去世了。
在過去二十年里,我也讀了一些現代中國小說——比如莫言、張愛玲、韓少功、曾樸、魯迅和丁玲等人的作品。奇怪的是,最讓我感動的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雖然它講述的是一個和我完全不同的世界,但丁玲對那個世界的描寫非常有力量。
更具體一點,您覺得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培養方面的不同,可以從您自己帶過的那么多學生引開說說嗎?
安德魯·阿伯特:我在教中國學生的過程中學到了很多。我每年教一門本科的社會科學“核心課程”,在這門課里,我能接觸到很多中國學生和華裔學生。在研究生階段,我也和本系及社會科學碩士項目的中國學生有很多交流。大多數(但不是全部)中國學生都來自中美兩國的名校,所以他們并不是一個隨機的樣本。這些學生在智識上訓練有素,有自制力,學習動力十足,而且他們是一群很有意思的年輕人。
他們和美國學生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他們更習慣對我表現出尊重,無論是對我的年齡還是身份,他們表達得都很自然。其次,中國學生在人際交往上很有一套。對美國人來說,這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因為中國學生通常顯得非常友好和禮貌,但同時他們可能會有自己的思考,與導師或老師的想法不太一致。這種能力自然是源于中國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復雜性和壓力。
第三個不同是,中國家長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比美國家長要大得多。美國的孩子有時只會在遇到麻煩時才想到找父母幫忙,而中國家長總是積極參與孩子的生活,孩子做任何重要決定時幾乎都會考慮到父母的意見。
第四個不同點是,美國學生——尤其是在像芝加哥這樣頂尖大學的學生,特別是經濟學以外的社會科學專業學生——現在的政治傾向很強,甚至讓人有點不安。這也影響了他們從老師那里學習的態度,他們往往自以為能夠判斷老師的政治立場,但其實并沒有什么證據。而中國學生的政治觀念可能同樣很強,但他們身處的是另一個環境,一般也不會談論政治。因此對美國老師而言,這讓他們看起來比美國學生更愿意接受不同的觀念。
當然,這些差異也和我自身有關,而不僅僅是學生間的區別。中國學生讓我想起了自己年輕時的樣子,而我也變成了我曾經想象中的那類教授,可能像費正清先生一樣。但美國年輕人的風氣已經改變了,所以我與大部分美國學生的思想越來越脫節,只有少數能與我產生共鳴。有智識方面興趣的學生從一開始就會覺得我有意思,而那些高度政治化的學生和準備沖向商學院的學生則往往覺得我很奇怪,甚至覺得我不合時宜。
您最近讀的中國小說是?這本作品哪里吸引了您?
安德魯·阿伯特:我最近讀了兩本中文小說——《孽海花》和《牡丹亭》。前年,我在周五下午和學生的“隨機閱讀”小組中讀到一本關于上海的書,里面提到了《孽海花》。不過遺憾的是,這本小說沒有英譯,所以我讀了的是法語譯本。我當時還不知道這本書是“隱射小說”(roman à clef)。看完后覺得它的基調——幻滅、憤世嫉俗——很特別,也挺有意思的。
我讀的是全本《牡丹亭》。這本書我已經想讀很多年了,因為它在《紅樓夢》里提到過。我覺得《牡丹亭》確實很打動人,不過它把極致的浪漫主義和顯白的粗俗語言混合在一起,感覺非常奇特(好像有些版本里刪掉了粗俗的部分),這種風格確實是一種挑戰,表現了不同社會世界的交融。
縱觀這些年來,攻讀社會學博士(PhD)學位的學生群體特征發生了哪些變化?研究生導師制度如何演變?社會學就業市場又經歷了怎樣的轉變?您認為這些變化會對社會學這一專業學科產生什么影響?
安德魯·阿伯特:這個問題涉及范圍極廣,需要充分的歷史背景才能作答。從1890年到1970年,美國學術界基本上呈指數級增長,其間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現過中斷。從基礎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當時的學術界呈現出年輕化特征:大量的研究生、數量適中的富有活力的中年教師,以及相對較小規模的資深學術帶頭人群體。在這種人口結構下,創新相對容易,因為許多研究課題都未被規模較小的早期(資深)學者群體所涉及。理論與實證研究之間保持著合理的關系,這實際上是因為數量眾多的年輕學者在應用數量較少的資深學者提出的理論。當時并不存在數十種相互競爭的理論體系和術語體系,而僅有少數幾個重要的思想流派,這些流派通常與主導院系的學術泰斗相關聯。直到1960年代早期,社會學和大多數學科一樣,約百分之五十的博士學位來自十五所院校。這個學科不僅規模小,而且高度集中。
1975年之后,美國高等教育停止擴張,學術界轉向了純粹的替代性人口結構(pure replacement demography),即一位學者離開才能有一位新學者進入。因此,教師隊伍的年齡分布變得更加平坦:年輕學者減少,資深學者增多。但我們并未相應調整對學術生涯的認知模式。結果是,提出宏大理論的人太多(因為資深學者相對更多),而閱讀這些理論的人太少(因為研究生和助理教授相對更少)。同時,龐大的學術體系迅速消耗著可供論文寫作和實證研究的選題;只有通過不斷創新實證方法(以及平靜地忽視大量“過時”的研究和“無關”的數據),我們才能回避這個明顯的事實:我們已經對大多數課題進行過數十次研究。
誠然,這個體系頂層的人口結構變化較小。現在仍然存在十到十五個主導性院系,這與1955年以及1975年的情況相似。雖然它們在博士生培養方面的主導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系統內其他地方也在培養博士,但這些博士很難在頂尖院系中競爭職位,因為這些院系主要從自己的圈子內招聘。這些機構的規模和身份認知在數十年間基本保持不變。
但大多數博士的就業市場并不在這個精英層面。因此,1975年后的新人口結構產生了重大影響。由于高等教育停止指數式增長,于是出現了買方市場,這種局面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壓力并帶來了激烈的競爭。競爭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更關注表象而非實質。第一個此類變化出現在1970年代末,當時在定量研究項目中擔任助手的研究生,從前只在論文致謝中提及,開始被列為作者(勞動分工并未改變,僅僅是標注方式改變)。接著,求職者的推薦信從真實評估優缺點轉變為營銷文件,變成了充斥溢美之詞的交響樂,一些同事將他們的每個學生都描述為多年來最優秀的。我不確切知道推薦信何時開始轉變為純粹的溢美之詞,但如今這些信幾乎難以區分,也幾乎毫無價值。
與此同時,學科規模的擴大本身也產生了不同類型的影響。1975年社會學的主導教授們都是在1950年代獲得博士學位的人。當時整個學科僅有約四千人,精英核心群體來自大約五所主要院系。現在學科規模達到一萬四千人,精英核心來自更廣泛的院校。此外,該領域的多范式特征削弱了招聘院系有效評估跨領域論文的能力。
這一切的結果是,純粹的發表數量(作為主要的價值衡量標準)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迫使研究生在專業發展的更早階段就開始發表文章,這比1950年代、1970年代甚至1990年代的社會學家都要早得多。已發表的論文成為衡量學術研究進展的唯一有效指標。
總的來說,社會學變得更具競爭性、更專業化、更程序化。其發表系統現在主要是一個教師評估系統,而不是信息交流系統。這個系統(及其競爭程度)還因知識的商品化而進一步加劇: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es)、統計軟件、個人電腦、搜索算法、世界圖書聯合目錄(Worldcat),當然還有現在的人工智能。這些都使更多人能夠寫出更多東西,而現在沒有人有時間去閱讀。事實上,社會學和其他領域的“知識爆炸”在很大程度上實際是平庸的爆炸。
更令人擔憂的是,多種因素降低了學術就業相對于商業就業的吸引力,至少目前如此。這些因素清單很長,無需一一列舉。但一個與1970年代結果不同的地方在于,除了經濟學以外,現在每一代大學畢業生中的頂尖人才不再選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就業。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許多優秀學生選擇了學術這條道路。但這種情況在1980年代隨著高等教育擴張結束而導致的第一次學術就業市場崩潰而終結。1990年代和2000年代出現短暫復蘇,部分原因在于上一代的退休潮。但2010年代,多種因素導致衰退重啟。現在很明顯,在美國本科生中,除經濟學外的社會科學并未吸引到應有比例的優秀人才。在美國,這種效應可能因這些領域(尤其是社會學)的大部分被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不平等研究”所主導而被進一步放大。
這些重大變化不可避免地改變了社會學的研究生教育以及學科的公眾形象。這些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被大量來自國外的優秀學生所抵消(在我指導過的博士生中,有四成來自美國以外)。但我個人認為,就吸引本土人才而言,美國的社會學學科正面臨困境。
但是,這種遠離學術職業選擇的轉變影響著所有學科,而不僅僅是社會學。我不清楚相較于其他學科的衰退進程,社會學處于什么位置。而且,導致這種衰退的許多力量遠遠超出了學術界的范疇。但這些問題已經遠離了本次訪談的原本主旨,因此我先談這些。
您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這本刊物的主編長達十六年。 您如何看待社會學期刊對學科的意義?您曾將這本刊物劃分為四個時刻,可否簡要介紹一下?
安德魯·阿伯特:《美國社會學期刊》是社會學領域最古老、最著名的期刊。不幸的是,現在它像其他現代期刊一樣,更多是為了學者推進自己職業生涯,而不是為了學術生活。它未來會怎樣,我說不準。這本期刊的悠久歷史可以很容易地總結出來。基本上,《美國社會學期刊》從一本“應用宗教”的期刊,逐步轉變為頂尖的學術刊物(具體可參見《學系與學科》一書,中譯本125-128頁)。但在我之前談到的1970年代美國大學擴張停滯后,它就被“生涯取向”束縛住了。當時美國的學術體系像龐氏騙局一樣大規模崩潰。之后會發生什么,我也無法預測。
作為有特定學術口味偏好的學者的您,與作為行業內最為重要的學術期刊的主編的您,這二者的角色如何平衡?
安德魯·阿伯特:我在學者和編輯這兩個角色之間找到了良好的平衡。秉持絕對公正是我的一個優勢,而且我也充分認識到,在我擔任主編期間,不可能親自審讀全部六千篇投稿文章。因此,作為編輯,我的工作重點是確保遴選優秀的審稿人,并認真對待他們的評審意見。我選擇依靠同事們的專業判斷,通過規范的評審流程——而不是依賴個人判斷——來保證期刊的學術品質。正因如此,我從未感受到個人目標與期刊宗旨之間存在任何沖突。事實上,期刊也確實發表過一些文章,這些文章雖然得到審稿人和同事們的高度評價,但在我個人看來可能是有誤的、無益的,或者是浪費時間的。期刊就是該這樣運作——它是《美國社會學期刊》,而不是“阿伯特社會學期刊”(采訪者注,兩者縮寫都是AJS)。
作為一本“美國”刊物,《美國社會學期刊》是否需要兼容并包外國社會學、國際社會學的旨趣?
安德魯·阿伯特:所有期刊都有自己的風格,不同國家的社會學也有自己的風格。我本來想把《美國社會學期刊》擴展到全球,但我的歐洲朋友和同事讓我意識到,很多人并不喜歡AJS文章的標準格式。我覺得很難調和這些差異。所以,我讓期刊的風格保持不變,主要考慮美國的論文,國際文章符合這種風格的就發表。另外我還開啟了芭芭拉?塞拉倫特項目。這個項目最后在我的網站上獲得了將近一百萬次點擊(https://home.uchicago.edu/~aabbott/barbara.html),我覺得這個策略還是有些智慧的。
年輕學者苦發表久矣,這是中西皆然的問題。對那些苦于頂級刊物發表的學者、學子,您作為這本刊物的主編有什么建議?
安德魯·阿伯特:不管是否發表,我對年輕學者的唯一建議就是:寫好作品(Write good work)。這是學者唯一能做的事。你無法避免期刊評審中的隨機性,也無法賄賂審稿人,也不能用AI(至少現在不能)來生成真正有吸引力的想法——AI的問題是,它沒有生成深層次新意的能力。它最終依賴于“平均想法”和“想法延續性”的概念;算法總是為了優化某些東西,而優化就需要依賴許多前提條件。所以,并沒有什么捷徑可以進入頂尖期刊。況且,如果你想通過作弊來獲得地位(或者財富?),還有很多比做社會學家更有效、更賺錢的方法。我們之所以成為學者,是因為我們關心把事情做好,把論點說清楚,而不是想著發財和權力。所以,盡力而為寫出好論文,論文自然會在學術的世界里照顧好你。
作為一位將時間和社會過程當作自己核心興趣的學者,過去二十年里,您認為自己在學術上以及個人生活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
安德魯·阿伯特:過去二十年來,我得過兩次癌癥,失去了父母和兄長,看著兒子長大成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但我仍然對智識問題著迷,到目前為止,上天對我的頭腦還是很眷顧的。最大的變化是,我現在覺得自己的作品不是寫給當下的社會學界乃至學術界的,而是為那些將來可能有機會看到并會為之興奮的讀者而寫。我相信,這些人不會很多,但我希望至少會有一些感興趣的人……
您如何看待當今社會學面臨的挑戰?
安德魯·阿伯特:八年前,我接受過一批美國年輕社會學家采訪,而他們從未真正提出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他們更關注眼前的實際問題:“期刊審稿公平嗎?”“有什么新的發表途徑嗎?”“您如何看待就業市場?”
面對這種情況,我告訴他們,作為即將成為社會學守護者的一代人,他們需要有更遠大的抱負。他們應該思考這些更為關鍵的問題:社會學是否能夠繼續存在下去?學科體系和大學是否能以當前的形式延續?面對全面數字化的浪潮,社會學該如何應對?哪些知識課題值得投入畢生精力去研究?我們可以就其中幾個問題展開討論。
智識生活能否在大學里存續?
安德魯·阿伯特:如前所述,1970年代學術擴張的終結導致了學術人才的買方市場,競爭迫使所有學術衡量標準(包括發表、作者署名等)貶值,其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無關緊要的發表。這種泛濫幾乎摧毀了學術交流體系,使其淪為評估考核的工具。
1970年以前,普通教授一生中可能只發表一兩篇作品。這并非因為他們愚鈍、懶惰或缺乏訓練,而是因為他們只在真正想要發表時才會發表。如今,教授們必須不斷寫作以滿足上級要求,支持他們所在大學在毫無意義的排名中攀升。由于隨之而來的發表泛濫,實際上沒有人在認真閱讀。人們都在瀏覽、摘取、復制。互聯網助長了對材料的極其膚淺的接觸,僅僅尋找對自己當前項目有用的特定片段。對任何在學術界工作了至少二十年的人來說,這種行為(過度發表和新的“閱讀”方式)顯然由新自由主義管理模式驅動,而該模式正在或多或少地摧毀大學中傳統的智識生活形式。在科學領域,情況已然發生,許多學科在我看來正在迅速退化為單純的工程學。
社會學能從中幸存下來恰恰因為我們不重要。在我看來,整個知識體系必須改變,否則真正的智識主義將在大學中消亡。未來的關鍵不在于像《社會學科學》(采訪者注:Sociological Science是一本新形式的刊物:沒有版面字數限制、開放獲取,完全電子化)等新期刊是否為《美國社會學雜志》樹立了榜樣。真正的問題在于:是否還會有任何刊物能夠容納非機械性的學術產出,而不是僅僅出于人事考核需要的寫作;出版由那些專注于思考和反思,只在真正有寫作沖動時才愿意動筆的學者的作品。二十世紀的知識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功,即便當時個人的發表率遠遠低于今天。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新體系能夠取得相近的成就。
我們現有的數據類型能否繼續存在?
安德魯·阿伯特:眾所周知,選舉民意調查如今經常無法準確預測選舉結果。究其原因,似乎是因為當前大多數民調都依賴于自主參與式網絡調查(opt-in online surveys)。顯然,這種調查并不具有樣本代表性,事實上,許多調查由政黨出于策略考慮而自行制作。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學術社會學領域:付費招募的調查答卷者群體能否構成高質量社會學研究的合理數據庫?從互聯網上抓取海量的明顯不具代表性的數據,除了反映這個范圍未知群體的特征之外,是否能產生真正有意義的結果?IP地址樣本是否等同于人群樣本?
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所有形式的在線反饋數據都可能且正在被經濟和政治利益所操縱。同時,計算機算法與廉價呼叫中心(這些中心雇傭著亟需工作的人員)的結合,正在耗盡公眾參與調查的最后一點點意愿。我們正面臨著大量的“數據”泛濫,這些數據在上世紀中葉的社會學家眼中可能會被視為毫無價值的垃圾。但這很可能很快就會成為研究者唯一負擔得起的數據來源。因為電話營銷人員的騷擾已經嚴重損害了電話調查的回應率,而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調查成本則高得驚人。
我們還能再次獲得“具有代表性”的數據嗎?我們是否應該認定這些新型數據具有代表性,只是代表著不同的事物?對于那些“作為透明度的一部分而公開可用”的行政數據(administrative data)又該如何看待?這些數據是否可信,還是像我們看到的某些公司采取雙重會計準則一樣——“透明”的會計記錄全是謊言?這些問題以及許多相關問題都將是下一代社會學家必須應對的挑戰。事實上,互聯網讓社會群體的整個概念都變得可疑,在機器人(bots)盛行的時代,人們很難理解任何社會群體的“真實”范圍,甚至不知道這種范圍是否真的重要。
能否談談您對計算技術的看法?
安德魯·阿伯特:在我看來,這一切意味著,在社會學的未來發展中,對計算機科學和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的扎實掌握與統計學基礎同等重要。這里所說的掌握,是指對該領域的真正精通,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表面的操作層面。社會統計學主要是由嚴謹的數學家們開創的。同樣,社會學中嚴肅的計算工作也需要在這一領域接受過基礎訓練的人才。
同時,正如我們在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領域已經看到的那樣,計算技術也會產生大量質量欠佳的研究。因此,新一代社會學家必須為計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建立質量標準,區分其優劣。建立良好的統計標準花了整整三十年,但僅僅十年后,這些標準就被統計軟件削弱了,這些軟件使“假設檢驗”(hypothesis testing)在智識上失去了意義。計算社會學可能會重蹈覆轍。
在質性研究方面,我并不認為田野筆記的索引程序能比仔細的多次閱讀和深入思考帶來任何額外價值。而且顯然,絕大多數可視化呈現都具有誤導性,甚至更糟。
因此,計算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但它已經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此,在新的知識世界中,我們必須理解并從哲學角度批判計算主義所基于的算法:馬爾可夫鏈蒙特卡羅方法(Monte Carlo Markov Chain)、模擬退火(simulated annealing)等類似技術。再次強調,在我看來,社會學將需要通才而非專才。
在您看來,社會學的全球化應該如何推進?
安德魯·阿伯特:我在《多樣化的社會想象力》一書中已經探討過這個話題。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思想傳統與西方有著顯著差異。雖然在非西方世界中,確實有許多人采用西方規范分析來開展本土批判和政治工作,但更多的人完全不接受西方的規范本體論(normative ontologies)。這些人可能堅信等級制度的合理性,或社會支配的正當性,或其他十幾種為各派別的西方社會科學家所不能接受的觀念。因此,社會學的全球化可能朝兩個方向發展:要么將西方理念強加于世界,要么嘗試從非西方社會的思想中汲取養分,展望一個真正多元的未來。
僅僅思考這些“跨文化”問題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就能讓我們意識到它們需要研究者投入畢生精力。我之所以能夠列舉這些問題,僅僅因為我年事已高,已經盡己所能處理了我那個時代迫切的知識問題,并在《多樣化的社會想象力》、我的馬克·布洛赫講座(中文版收錄于《社會科學的未來》,2023年,商務印書館)以及其他場合提出了以上的問題。在這些著作中,我至少提出了這些議題。接下來的探索,我將留給我的學生和讀者們。
當然,從短期來看,日常生活仍將繼續。在我之后的幾代人中,有人會抓住機遇,有人會錯失良機,有人會經歷起起落落。其中一些人最終會進入精英院系,一些人會在普通院系工作,一些人會在四年制學院任教,一些人會在圖書館工作,還有一些人會進入私營部門、非營利部門等。無論如何,大多數人都能在各自的崗位上找到豐富而令人滿意的人生。個人的成就感更多源于性格和其他個人因素,而非職業成功。
當然,我說這些話可能顯得輕巧,因為就職業而言,我的運氣遠超我應得的。確實,能夠擁有我現在的職位是很美妙的事情,它帶來了回報、自由以及大多令人愉快的“責任”。但成就系統的運作方式是:實現了夢想就意味著你會有更多的夢想。
我們之所以繼續前進,并非為了成就。而是為了明天的有趣想法,周四的頓悟,或周五那個憂心忡忡的學生。我們做這些事,是因為維護真正的智識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未來會有其他人將其傳承下去。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培養和滋養后來者。
可否向中國讀者推薦一本您最近讀過的非社會學著作,并談談推薦的原因?
安德魯·阿伯特:給出理性選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是列出目前放在我床頭書柜的三本書。我推薦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在那里”:一、朱塞佩·托馬西·迪·蘭佩杜薩的《豹》;二、清少納言的《枕草子》;三、但丁的《神曲》。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