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夜讀丨為什么我們對溝通缺乏耐心
我媽做的家常小菜很受歡迎,正好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物色本土風味食品,我便想給她搭個橋。才說完基本情況,我媽的焦慮幾乎要從電話里溢出來了:“哎呀,短時間里我批量做不出來啊。”
我說這才哪到哪,你現在完全不必擔心。她又說了幾輪車轱轆話,我便開始失去耐心:“都說了現在只需要選幾個樣品給人評估,你到底在糾結什么?現在誰要你量產了?”眼瞅著自己的嗓門逐漸飆高,我趕緊掛了電話。最近我們沒怎么聯系,我原本還想趁機跟她嘮嘮家常的。
更早之前,跟朋友約飯,定好了時間和地點。臨近碰頭,她又拋過來幾個選項,說這些看起來也很不錯,問要不要改一下。我把最初定好的那家店發過去,說這就是“打死不改版本”。雖然在微信上看起來這是個蠻輕松的調侃,但實際上我心里已經滿是不耐煩。
前述種種,并不能簡單歸結為“把壞脾氣都留給了親近的人”。我的情況似乎比這更嚴重,因為我在溝通中越來越沒有耐心。我對這種不耐煩常后知后覺,也表示懺悔,但并未真正改變。
好像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面對和處理,通關的唯一秘訣就是提高效率。但凡讓人多廢幾句話的事,都能讓我大動肝火。
我盡量要求他人和自己用最簡短清晰的方式表達,最好能簡化成公式。就像奧卡姆剃刀定律:如無必要,勿增實體。這在工作上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成效也往往喜人。比如,我們的工作團隊曾把工作流程梳理出流水線,并制作成共享表單,所有人每天的事項與銜接都一覽無余,由此省去了很多冗長又低效的會議。
但放到別的事兒上,過度追求溝通效率反而顯得蠻不講理。比如,有人找我傾訴,說現在的老板、同事如何如何“搞人心態”。聽了兩分鐘后,我直接打斷她,說這事兒你已經講了半年了,我這里有個工作機會,你要么投個簡歷試試?她猶豫了一下,突然崩潰:“我難道不知道要怎么解決嗎?不!我就是想要你提供點情緒價值!”
有次朋友們聚餐,席間有人發起心理測試,我被測出來本質上是只機器狗——波士頓動力公司生產的那種四足機器人,工具屬性十足,卻毫無人性。講真,滿桌都是形形色色的人類,就我一臺機器,剛開始我對這個獨特設定沾沾自喜。但隨著自己喪失耐心的次數增多,我發現身為人類卻顯得高度機器化,實則是件挺危險的事。
把各種事物一概視為任務,只想迅速提供解決方案并通過,這確實能提高效率,但長此以往,對他人和生活的感知,就變得麻木。回想起來,我甚至已經很久沒有發自內心地覺得愉悅欣喜了。
生活原本粗糲,有人只想迅速把活兒干了,有人會站那里看會兒云,看風吹動樹影婆娑,看人來人往。這些事無關目的,浪費時間,但恰恰是它們給生活增添了質感,給人帶來滿足和確幸。
詩人M·索萊達·卡瓦列羅寫道:
你晚上十點十四分給我打電話。我想:
他最好是被綁架了或者被槍擊了或者……
出來吧,你笑著。你站在
草坪上拿著一袋狗屎和一條狗鏈。
你說看看月亮吧。然后我就看了。
這是藏在生活褶皺里的、輕盈的浪漫。就像好好和親友說話,說點廢話,更能從中體驗親密關系的羈絆。我應該察覺到我媽面對新鮮事物的惶恐,耐心為她解答,甚至我們還能就此聊會天,我被她需要,她亦有依靠。
可惜,在那個瞬間,以及其他無數瞬間,我都在“機器狗模式”,忘了切回“人類模式”。
麥克尤恩在小說《我這樣的機器》里,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算力強大的機器人亞當和同伙們努力適應人類生活,卻在面對人類的情感和倫理問題時陷入崩潰。用流程和公式去搞定一切,是機器的強項,而在此之外,那些感性的、渙散的、消耗人耐心的,恰恰是人類生命的質地,也是我們始終難以被機器輕易取代的部分。
我現在希望能像接到任務一樣,把自己盡快切換成“人類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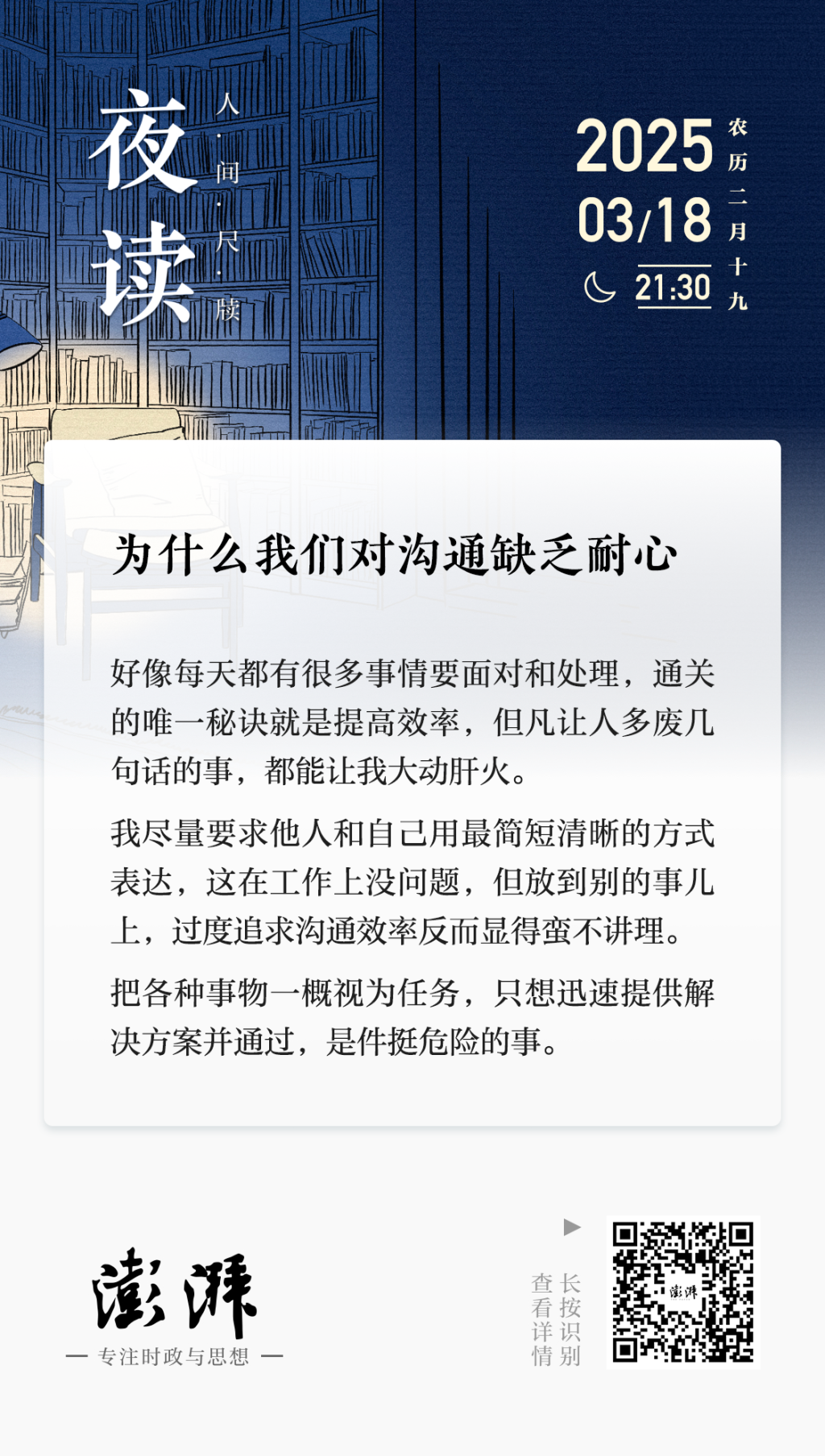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