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沒有地理大發現,就沒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
白銀流入與一條鞭法
很多人忽略了一點:地理大發現除了發現美洲以外,其實也對東亞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6世紀以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先后來到南亞和東亞,深度參與了東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洋貿易。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和美洲銀礦的開采完全改變了世界的白銀供給結構。它對中國的直接影響,就是充分滿足了中國商品經濟對白銀的巨量需求。
根據估算,從嘉靖二十九年(1550)到順治元年(1644),大約就是明代最后的一百年,中國約有90%的白銀是從海外進口的。這個數字相當于全世界白銀產量的25%—50%。

2024年3月9日,杭州,浙江省博物館,明朝銀錠。
無論用什么標準去看待,它都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以至于當時的商人和航海家送給中國一個“白銀地窖”的稱號。或者正如有些歷史學家說的,中國像是個“白銀吸塵器”。換句話說,中國成了全球白銀循環的終點,白銀來到這里之后,就再也走不了了。
為什么中國能成為全球白銀循環的終點?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擁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尤其是能夠生產歐洲人欣賞的那些商品,比如絲綢、瓷器和香料。歷史學家K.N.喬杜里指出,1500—1750年間,中國擁有亞洲最先進和最復雜的經濟形態,中國之所以能夠吸收如此大量的白銀,主要是因為在生產成本上具有相對優勢。而一旦經濟活動開始活躍,“畫地為牢”的編戶制就會暴露出巨大的劣勢:極大地限制民眾的人身自由,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軍戶體制面對這種社會現實的沖擊,其命運只能是瓦解,“洪武體制”也就隨之被顛覆掉了。
以白銀流入為標識的社會經濟底層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其后果當然也會反映在上層制度設計與政策實施中。這個制度轉向在明代政治史中也非常有名,它就是以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為代表的稅制改革。
什么是一條鞭法?其實這個制度本身并不新鮮,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過。從先秦時代開始,統治階層就以徭役這種制度來驅使百姓貢獻免費勞動力。徭役指的是強制的義務勞動,在和平時期包括修建城防、轉運物資、協防治安、為宮室皇族提供義務勞動等等,在戰爭時期就是服兵役。
徭役制度誕生的年代對應的是奴隸制盛行的年代,東西方概莫能外,這也可以理解。但是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社會財富的積累,這套制度給民間生產帶來了很多破壞。代入古代百姓想一想,如果一年中有兩三個月不能從事本職工作,而是要給政府義務勞動,耽誤賺錢不說,關鍵是這份苦實在吃不得。所以,歷朝歷代也都有變通辦法,簡單概括就是“贖買”。我通過種種名目,出錢來抵義務勞動,政府拿了我的錢,轉雇其他沒錢但愿意出力氣的人來抵掉。
相比用編戶的手段把民眾變成“畫地為牢”的“國家農奴”,用錢來抵消繁重的義務勞動,也可以說是經濟繁榮造成的“正增長秩序”為社會帶來的進步。因此,許多朝代都在制度上予以認可,搞賦役合一。
明朝初年面臨的是七百年來的財富積累被輸送出去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局面,貨幣高度短缺。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維系對蒙古的戰爭動員能力,建立了相當嚴酷的“洪武體制”。這套體制在朝代初期是管用的。一方面,戰亂年代,民眾生活極其凄苦。“洪武體制”盡管嚴苛,但和平總比動蕩要好得多;另一方面,朱元璋、朱棣兩代皇帝都是難得的帥才,是擊敗了蒙古鐵騎的優秀軍事領袖。他們殺伐征戰的個人超凡魅力可以對被編戶的底層民眾形成震懾。
然而社會穩定后,經濟活動開始活躍,“畫地為牢”的編戶制極大限制了民眾的人身自由,自然就會出現脫離軍籍的狀況。而一旦出現這一局面,“洪武體制”的戰時動員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從洪武帝到嘉靖朝,差不多過了一百五十年,這套體系已經積重難返。嘉靖朝北方有韃靼,南方有倭寇,中央財政捉襟見肘。負責軍國實務的地方官僚們,不得不把中國歷史上反復實施過的妥協辦法,也就是贖買徭役的制度又重新找出來,也就是一條鞭法。
很多人以為張居正是一條鞭法的首創者,其實并不是這樣。這個辦法是嘉靖年間在抗倭一線作戰的實踐中慢慢總結出來的。像一開始處理倭事的張經、后來的浙直總督胡宗憲,都發現了這個辦法的可行性:浙江、福建沿海民間因為從事海上走私,各家積蓄的白銀不少。這些人本來就旨在掙錢,不愿意當兵,如果要強征他們,他們說不定就地加入倭寇,所以不如“化非法為合法”:你出十二兩銀子,免了兵役,我另找人當兵。此舉一施,兩難自解。當然,這也不是張經和胡宗憲他們多么天賦異稟,而是他們又一次采用了這個國度歷史上曾被人反復發現、證明有效的實踐操作辦法而已。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張居正個人的功績。因為作為有明一代最優秀的政治家之一,他從實踐中無師自通地領悟了“正增長秩序”,同時提供了改造財政體系的這套系統改革方案。

張居正像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駕崩。首輔徐階召張居正一同撰寫《嘉靖遺詔》,勸裕王上位,改元隆慶,張居正真正躋身帝國最高決策層。他上任后對財政體系的改革,其實始于“開關”。
有明一代的開關,實際上是兩個方向的開放:向北對蒙古陸路貿易的開放和向南對海洋貿易的開放。張居正親身促成了前者,入內閣期間經歷了后者。
大明對蒙古的開關實際上緣于一個偶然事件。蒙古俺答汗看上了受鄂爾多斯部落禮聘的三娘子,作為補償,他把自己孫子把漢那吉的妻子嫁到鄂爾多斯部落。把漢那吉感覺受到侮辱,于隆慶四年(1570)一怒之下投奔了明朝。張居正得知此事,立刻派人將把漢那吉控制起來,并以此人為餌與俺答汗和談,實現了明與蒙古之間的長期和平。這為大明解除了西北邊境面臨的持續壓力。
而大明對東南沿海的開關,則緣于“海禁”政策的無法維系。我們都知道,明初朱元璋因對海盜深惡痛絕而下達“片板不許入海”的禁令。但隨著日本銀礦的開采和東洋貿易的繁榮,海洋貿易蘊藏的巨大利益反而吸引許多沿海民眾以身犯險。這就等于說,良民因“海禁”變成了海盜。就拿明代有名的倭患來說,最早的倭寇確實是日本武士,可后來真正稱霸一方的,如宋素卿、汪直,乃至后來的鄭芝龍等人,他們多數倒是中國人,只不過常常在日本設有據點而已。到嘉靖年間,來自日本的“真倭”在室町幕府和戚繼光的打擊下基本被消滅了,而來自中國的“假倭”在事實上成了主流。
在這種情形下,一些務實的地方官員和沿海世家大族開始上書朝廷,請求廢止“海禁”。道理很簡單,在白銀流入的大環境下,從事貿易的利潤百倍千倍于捕魚撈蝦,“海禁”政策擋住了沿海百姓的生路,他們當然會視你為仇讎。
嘉靖皇帝在位期間,剛愎自用,刻薄寡恩,始終沒有廢除“海禁”。隆慶帝即位后,廣開視聽,察納雅言,故而正式廢止“海禁”政策,于福建漳州月港開放海禁,準許與東洋及西洋的貿易,是為“隆慶開關”。時在內閣的張居正也是制定政策的參與者之一。
隆慶開關雖然名義上只允許在漳州一地貿易,但它的風向標意義是重大的。這代表大明王朝不再把海外貿易視為完全非法的舉措,而是可以承認它的存在。其實當時除了漳州之外,還有一片地域名義上雖未開關,事實上卻可以無阻礙地自由貿易,這片地區就是澳門。
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后,葡萄牙人向國庫繳納一定數額的租金,以獲取自治權,但被明朝海道獨吞,澳門就這樣莫名其妙成了葡萄牙人的自治領。此地一年兩次舉辦高級交易會,吸引了大批海商參與,也成為明代重要的對外貿易窗口。
漳州月港的開關和葡萄牙人入駐澳門,為白銀加速流入明朝提供了便利的窗口。而白銀越加速流入,越是會加速“洪武體制”的瓦解。“洪武體制”的瓦解,對解放民眾負擔來說,其實是一件好事。而到了萬歷年間,由于皇帝年幼,張居正獨攬了大明帝國的最高權力。他決定利用自己的位置,做一些最簡單的實事。
首先是全國范圍內推行一條鞭法。嘉靖年間,一條鞭法已經在浙江廣泛實施了。那時候張居正還在翰林院,沒有什么權力。當然,他本人肯定是很熟悉一條鞭法優點的。因為胡宗憲平倭期間,有位屬下叫作譚綸,還有位部將叫作戚繼光,這兩個人都近距離實操過用一條鞭法籌備軍費,后來也都成了張居正的好朋友。所以,張居正對他們的經驗不可能不重視。
當然,身在高位,他要做的不僅僅是把一條鞭法推行下去,而是要以它為基礎,打造一套合理的系統。我們前面反復講過,一條鞭法的實質是一種妥協。王朝建立之初的僵化體制無法維系,因此必須承認民眾“贖買”徭役義務的辦法是合理的,這樣才能完成社會動員。
但這本質上還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雖然究其本質原因,是“洪武體制”有問題在先,但若官府僅僅是做出妥協,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將此作為權宜之計予以認可,都還是不夠的。因為國家的根本政策,不能不體現公平正義。
赤貧的“洪武體制”下,所有人都被畫地為牢圈禁起來,所有人都似暴力機器的農奴,這也是一種平等。但隨著白銀的流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妥協”的過程中,他們用借名、代持、收買、偽造等種種手段,把自己的徭役責任轉嫁到了窮人頭上,這自然會造成巨大的不公平。
嘉靖朝一些地方官員在主持實務的過程中,已經認識到了這種弊病。例如,廣東巡撫戴璟在承認“民壯及均平銀兩計田算銀”的基礎上,還要求“各縣人民并不許置買香山等縣田土寄莊”,目的是“以抑勢豪兼并之勢,以杜奸頑慣賴之害,以阻里排影射之風”。簡單說,就是官府不允許逃避徭役的富者成為一方豪強,不允許這種社會不公長期存在。
既要修正妥協帶來的不公,又不能回到普遍赤貧的“洪武體制”,這樣的系統該如何設計呢?它的最底層邏輯是什么呢?張居正找到的答案,是數據。“社會不公”并不是一個空泛的道德概念,它一定會表現為實質物質財富上觸目驚心的差異。一小撮人田連阡陌,多數人卻無立錐之地甚至要賣妻鬻子,這怎么都是說不過去的。
搞辯經沒有意義,直接公布財產數據才有說服力。萬歷八年(1580),張居正以首輔之尊,向全國推行《清丈條例》,下令在全國丈量土地。他引用了“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來形容此舉的艱難和他準備破釜沉舟的勇氣。
的確,古往今來,多少利益的爭奪、權力的博弈、陰謀的施展,其實總逃不過一個底層邏輯:數據。如果你有真實且清晰的數據,哪個環節誰動了手腳,就一目了然了。而如果你沒有這個數據,那么無論如何樹立道德的大旗,歸根結底還是解決不了碩鼠上下其手的問題。
在一切均以強制和暴力為出發點的“洪武體制”下,所有施政效果在本質上都是不能數據化的。——官府能靠里甲制度強迫一個人服勞役,但官府無法監督這個人在勞作時消耗了自己體力的5%還是10%。官府可以要求一個人工作八小時,但不能確保他這八小時沒有渾水摸魚。
這就是暴力體制相對于貨幣經濟體制最大的弱點:只要貨幣這個信用媒介的基礎是牢靠的,那就一定可以把所有效果數據化。每個人應該繳納多少賦稅,每個官員是否盡心盡責地把它們收上來,一切都無法抵賴。
浪漫一點說,張居正改革的意義正在于此。他知道“洪武體制”事實上已經無法維系,采取“贖買”是財政改革的唯一出路。但關鍵問題在于,不能讓改革成為造就新的不公正的借口,而要實現這一點的硬邏輯,就是數據。
令我們敬佩的是,他真的做成了——當然,僅限于他那個年代的政治環境和技術條件,但這足以名垂千古。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反復論述過張居正改革的成就和偉大之處,我就不需要再畫蛇添足了,只列舉如下幾個事實:
張居正身后,萬歷一朝遭遇著名的“三大征”,即萬歷二十年(1592)蒙古降將哱拜叛亂導致的“寧夏之役”、萬歷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日本太閣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導致的“朝鮮之役”和萬歷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596—1600)楊應龍叛亂引發的“播州之役”。歷史學家公認,萬歷皇帝雖久不上朝,導致行政機構運行紊亂,卻依然能夠指揮有度,先后贏得三場戰爭的勝利,其基礎正是張居正厲行改革后為大明國庫留下的財富。
明亡之后,清兵入關而代之。嗣后雍正皇帝推行攤丁入畝,用的還是萬歷八年張居正推行清丈法收集到的數據。換句話說,這套數據的可靠性得到了清朝的承認,正所謂“一時之功,百世之利”。
“脫鉤”與帝國的衰落
張居正能夠進行一條鞭法改革,乃至于大明王朝后期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其實都跟兩件事有關:第一,大航海時代的展開,明朝社會加入世界貿易大循環;第二,得益于廉價勞動力而形成的制造業中心吸引了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但是,全球化讓世界變得如連通器一般:一處水位高則處處水位高,一處水位低則處處水位低。因為全球化繁榮而獲得的收益,也會因為全球化的退潮而失去。
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有幾個處在全球化關鍵環節上的帝國都出現了各種政治危機。例如,在全球白銀循環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自16世紀下半葉起,開始卷入各種地緣政治沖突。比如,原屬哈布斯堡王朝的荷蘭地區因為信奉新教,與虔誠的天主教徒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發生沖突。當地起義不絕,導致腓力二世的軍費激增。從1571年到1580年,盡管王室收入因為西屬美洲的鑄幣稅增長了一倍(以西班牙貨幣單位計,五年財政收入從390萬杜卡特增加到800萬杜卡特),但由于戰爭花錢太多,國王還是不得不于1575年宣布破產。
荷蘭信奉新教,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宗教戰爭本來就是一場敵方不死不休的矛盾。要命的是,荷蘭人“海上馬車夫”這個稱號不是白叫的。在那個年代,這批船上人在航海家、商人、海軍和海盜之間是可以自由切換身份的,所以“海上馬車夫”也有獠牙。自西班牙與荷蘭開戰以來,荷蘭人就利用航海優勢對西班牙的航路進行了封鎖。其中對東亞白銀貿易影響最大的是對兩個港口的封鎖:一個是果阿,一個是馬六甲。這兩個港口恰好一個通往印度,一個通往中國,都是當時勞動力最廉價、產品最豐富的地方,因而也是白銀最大的流向地。
盡管這些戰場遠離歐洲和亞洲的文明中心,是毫無疑問的邊緣地帶,但是可不要小瞧這些航路貿易的重要性。當時東西洋之間貿易利潤十分豐厚,到了一艘船的貨物足可以用“富可敵國”來形容的程度。例如,1603年,荷蘭船長雅各布·范·黑姆斯克爾克虜獲了一艘葡萄牙貨船卡特琳娜號,其商品價值220萬荷蘭盾,相當于當時英格蘭一年的財政收入。
1628年,荷蘭船長皮特·海因虜獲了四艘西班牙大帆船,貨物價值達到了驚人的1150萬荷蘭盾,五倍于卡特琳娜號的收獲。此船的收入為荷蘭軍隊提供了八個月的軍費,讓他們贏得了一場重要戰爭。海因歸國之后,被荷蘭人視為民族英雄。這些案例說明的是,西班牙帝國因宗教原因在歐洲掀起的戰爭,卻在他們事先未曾預料的地方,也就是南亞和東南亞,打擊了貿易線路,因而也就打擊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不是唯一起火的地方,第二重打擊來自日本幕府。17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東亞的存在感其實很強,他們帶來的白銀和武器,引起了許多地方政權的興趣,日本各地的大名也不例外。然而,當時日本主政的德川幕府對此感到十分緊張,害怕大名通過海外貿易積累巨量的財富和兵力,挑戰幕府霸權。因此,從17世紀開始,日本幕府開始以傳教為由,限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與日本展開貿易,此即著名的“鎖國政策”。“鎖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當時整個東亞的白銀貿易。
而對于大明王朝來說,還存在著第三重打擊,也就是經濟規律本身的漲消。我們前面介紹過,東亞白銀貿易的根本動因是中國的白銀短缺。日本和美洲的白銀開采當然緩解了這個問題,但是日本和歐洲商人歷經千辛萬苦來到這里不是做善事的,而是為了賺錢。在中國最缺乏白銀的時代,最賺錢的生意還不是直接拿白銀換瓷器和絲綢,而是直接拿白銀換黃金。相對于白銀在元代的大量流失,中國保留的黃金相對多一些,這就形成了一個套利空間:商人們把海外的白銀運進中國,換成黃金,再到別的地方賣出去。
比如,隆慶二年(1568),中國的金銀兌換比是1︰6,西班牙的金銀兌換比則超過1︰12。也就是說,如果有辦法從西班牙帶白銀到中國,換成黃金帶回去,利潤就能達到100%。但是,隨著套利生意規模的擴大,大量白銀涌入中國,高銀價是不可能一直持續的。到天啟七年(1627)以后,中國的金銀兌換比已經漲到1︰10到1︰13,而西班牙的比例則在1︰13到1︰15之間。套利空間縮小,白銀流入中國的勢頭就衰減了。
在地緣政治和經濟規律的雙重打擊下,東亞白銀貿易的規模在17世紀上半葉開始大規模下跌。17世紀20年代,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從23噸下降到18噸,到17世紀40年代則下降到10噸左右。
以上因素,使得大明王朝在張居正時代享受到的全球化紅利不復存在了。大明王朝晚期,其金銀兌換比上漲到了與西班牙接近的地步,這個數字不代表白銀短缺得到了滿足。因為白銀循環的過程就像婚禮上的香檳塔一樣,水必須先灌滿上層的杯子,才會流向下層。
當外貿水流充足的時候,最先從外貿中掙到銀子的一批人就是海盜與外貿商,其次是與他們打交道的國內商人,然后是受益于白銀輸入的政府機關,最后才是被減輕了束縛的老百姓。然而,當外貿的流水被從源頭上關閉了,最先遭遇貨幣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崇禎十一年(1638),一千枚(一貫)銅錢能兌換0.9兩銀子,到清順治三年(1646)就只能兌換0.17兩了。
老百姓一銀難求,然而一條鞭法的規定又是交稅必須交白銀。當年利民便民的措施,莫名其妙地給民眾挖了坑。世間已無張居正。這一次沒有位高者理順治理過程中的細節,也沒有百年一遇的改革家來給大明王朝續命了。
明末思想家顧炎武記錄了官府強征白銀導致民眾家破人亡的慘狀。他說,自古以來,即使像禹湯這樣的盛世,也難避免老百姓在饑荒年份賣妻鬻兒。然而,像我大明這樣豐收年份老百姓也被迫賣掉妻子孩子的,則真是唐宋以來所未曾有的。
顧炎武說自己走過關中岐下這些地方,年歲是好的,糧食是豐收的,然而官府來征糧的時候,賣老婆孩子的村民竟然形成了集市一樣的規模,“謂之人市”。原因是什么呢?——“有谷而無銀!”銀子短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外貿的商船不來了!
張居正厲行改革的舉措,遇上了白銀循環的終結,竟然造成了這樣的局面,這恐怕是他萬萬沒想到的。當然,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竟然有人認為,隆慶開關造成的大量白銀內流,是大明最后亡國的原因之一。且不說市場經濟的大潮到底能不能擋住,如果不開關大明會是什么下場,難道“洪武體制”本身就是正義的嗎?難道大明把老百姓當農奴一樣畫地為牢,讓他們世世代代為軍為匠為民為灶就是正義的,就不會滅亡嗎?正所謂寧在一思進,莫在一思停。古往今來,沒有哪個國家不經受外界環境的變化和突發的挑戰。如果不反思一個政權為什么只能保守“祖宗之法”,做不到應變有方、進退有據,反倒怪外貿的輸入,那可真是舍本逐末、緣木求魚了。
接下來的故事眾所周知。崇禎元年(1628),高迎祥反;三年(1630),張獻忠反;四年(1631),李自成反。八年(1635),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老回回、過天星、九條龍等十三家首領會于滎陽,同年高迎祥攻破明中都鳳陽。十四年(1641)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十七年(1644),張獻忠破重慶、成都,李自成破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盡于景山。
輝煌燦爛的大明,號稱全球“白銀地窖”的大明,結局竟是如此慘淡。當然,白銀循環連接的另外一個主角,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沒有好到哪里去。
白銀循環的衰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收入下降。在16世紀的最后五年里,西班牙王室平均年收入2640萬杜卡特,但是到1620年,腓力二世的兒子腓力三世在位的最后一年,王室年收入竟然萎縮到40萬杜卡特,而當時與荷蘭的戰爭仍在持續,每年要花費400萬左右杜卡特。腓力四世即位后,王室在1625年宣布破產,兩年后再度宣布破產。到這時,很多銀行家已經完全不想把錢借給日不落帝國的國王了。
財政破產的直接結果就是司機因為沒油,已經開不動車了。不僅荷蘭這臺車出了問題,加泰羅尼亞和葡萄牙這兩臺后花園里的車也熄火了。17世紀40年代,以上兩個地區先后發生叛亂,而為了撲滅家門口的災難,國王不得不在1648年跟荷蘭等其他交戰國簽訂和約,八十年戰爭結束。戰后,荷蘭獲得獨立,瑞典獲得大量賠償金,法國獲得大片領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滿盤皆輸,從興盛走向衰落。
從17世紀全球化退潮的角度看,白銀循環的衰落竟使東西方兩大帝國同時崩潰,而這兩大帝國的精英對此又全無認知。無怪乎有句話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如果視野天生受到局限,不能跳出一國一社會之外,真正站在太空高度俯瞰地球,那么即便是再聰慧的頭腦、再高級的政治家,所思所想也不過是南轅北轍,不可能真正直面一個社會存在的問題,并解決問題。
那場“脫鉤”,所有人都是無意為之,所有人都是無心受過。
(本文選摘自《世界之中》,張笑宇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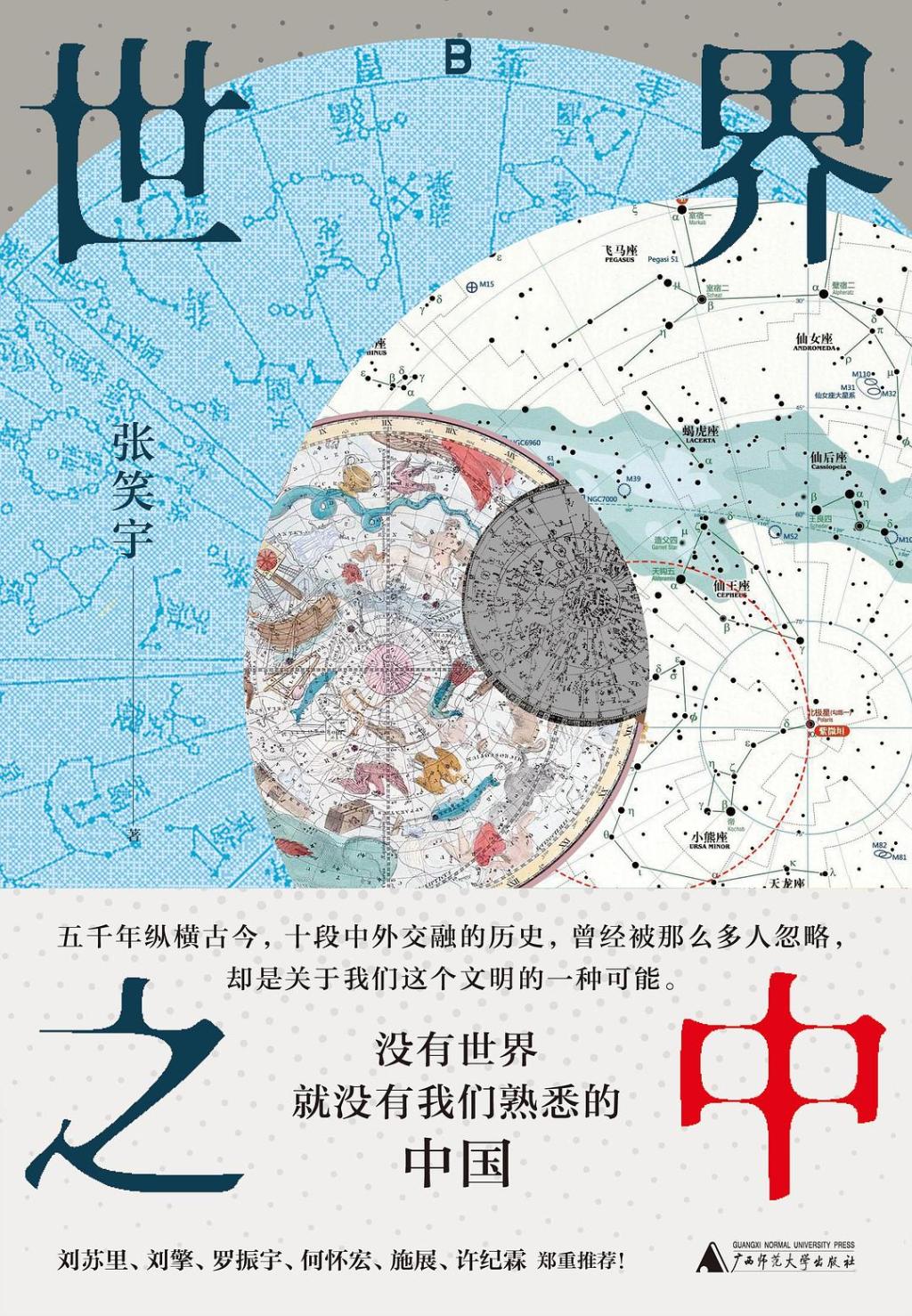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