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龔萬瑩《島嶼的厝》:探索城鄉二元敘事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中國新文學自魯迅的《故鄉》起,便構建起一系列關于故鄉的書寫譜系。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便是敘述者回鄉后遭遇的故鄉與情感、回憶與現實之間的錯位與失落。在龔萬瑩《島嶼的厝》中,雖然敘事者多為沒有離鄉的本地居民,但是故鄉主題所攜帶的挽歌情調,卻無差別地彌漫在每篇小說中。即使是開篇幾部以兒童視角展開的作品,在表層的幻想書寫下仍潛藏著傷感的情感內核。對這一情感現象,雷蒙威廉斯對于童年與鄉村的闡釋頗具啟發性:它“常常被轉化為關乎鄉村往昔的幻覺:連綿不斷的、無窮無盡向后退去的‘童年時代的快樂’”。(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也就是說,童年視角不僅是開篇幾部作品的敘述視角,更是貫穿所有敘事者情感結構的關鍵詞。他們對島嶼故鄉的情感與童年經歷強相關,如同芒果樹見證并承載了阿禾與她媽媽的童年幻想,每一代人對島嶼的愛戀都無法擺脫在此度過的童年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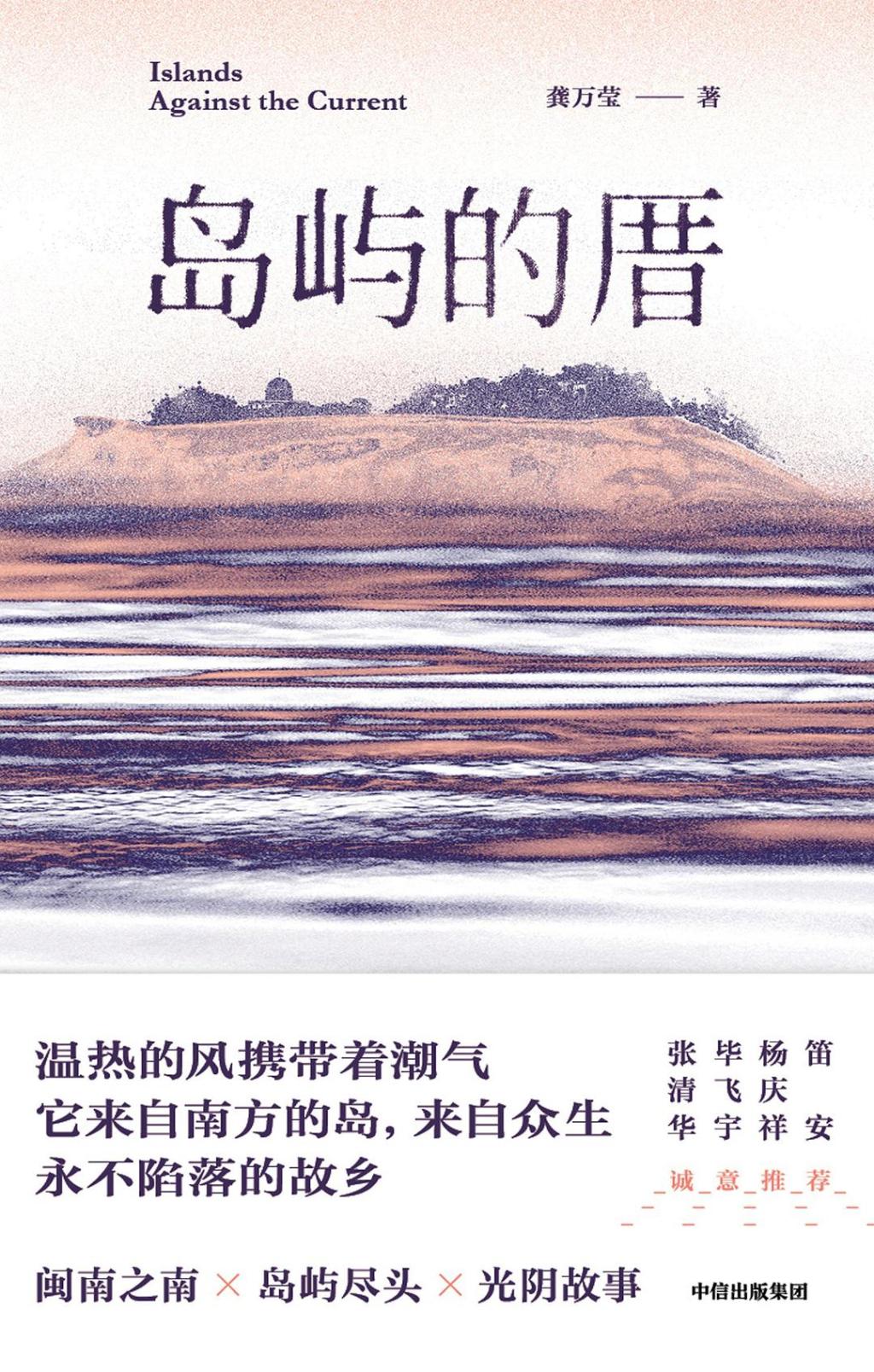
《島嶼的厝》書封
因此在《島嶼的厝》中,故鄉與童年不僅同構且互相指涉。解讀這座島嶼必須依據每個居民的成長經歷,不同年齡段的敘述者在島嶼度過的時間都構成了這座島嶼空間形象的一部分。在這種處理方式下,這部小說雖然從不同人物的具體經歷著眼講述,但實際敘述焦點凝縮在以鼓浪嶼為原型的這座島嶼本身,構建的是關于整座島嶼的情感印象。
在閱讀中,讀者可以輕易辨識出作者對島嶼隱含的深沉愛戀。但是,作者并不因此回避講述島嶼與童年中“煞風景”的一面。政治與經濟等現實因素填充在每個敘述縫隙,外來商品如曲奇、巧克力等成為阿禾一代小孩子珍貴的饕餮回憶,而下崗潮的線索也貫穿在阿禾、月兔的媽媽們的遭遇中。《大厝雨暝》與《浮夢芒果樹》中,阿禾童年的趣事中穿插著漏水的大厝和蟲蟻繁多的芒果樹,童言稚語中將尷尬的家庭經濟狀況勾勒了出來。種種冰冷、堅硬的現實存在于每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島嶼居民們都共同分享著某種相似的生活境況。這樣的主題稍微處理不慎便有流入尖銳批判或悲情哀悼的風險,但龔萬瑩卻將之圓融地納進了細密而溫暖的故事之網中,不回避也不放大現實冷硬的一面,用特有的細膩彌合了愛、回憶與真實性之間的裂隙。
這部小說集的特質不僅在于不回避現實,還在于其往往以情感的面目呈現和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阿禾一家關于是否將大厝租出去和是否砍樹的分歧本身牽涉眾多因素的考量,但這些爭執是通過阿禾的只言片語呈現的。在阿禾的轉述下(也正是以轉述的形式才能實現),經濟問題轉變為情感問題,幼年的阿禾無法也無需作出這道困難的選擇,她的童言稚語和奇思妙想可以輕飄飄地掠過這個問題,而不會在文本結構層面造成敘述不充分的缺陷。這種處理方式也與小說散文化的敘述方式十分契合,大量自由間接引語將人物心理與生活場景無縫銜接,場景經常是人物的幻想或情緒的投射,因而每篇小說的實質結構是情感而非情節,帶給讀者的也是對整座小島的氛圍式印象。
在龔萬瑩的自述中,她反復提到島嶼不可避免的消失和她強烈的“保存”沖動,“那時,我帶著膠片機,咔嚓咔嚓滿島拍照,留下島的圖片標本。在夢里,我看見島嶼滅沒,反復驚醒……那時的我突然意識到,那個似乎永在的故鄉,其實是會消失的。”(龔萬瑩:《后記:島嶼回潮》)小說固然是虛構的藝術,不可以作者親身經歷簡單貼附解讀,但這份后記也為闡釋小說中的挽歌情調提供了注解。因為這些情緒已然成為小說創作時的心理背景,故而隱含作者在大多時候總是處于“在而不屬于”的姿態,無法避免以“離鄉者”的情感介入“本地人”的故事。當然,龔萬瑩的創作是自我克制的,即使“島嶼受潮”的恐懼不時浮現,它也并不會迅速轉譯為對都市現代文明的認同。作者以情感為錨點,試圖阻止的正是某種單一“視角”和判斷,她盡量以人物情感的幽微來塑造復雜化的地方經驗,暫時懸置對都市與島嶼、現代與傳統等二元結構的判斷。

龔萬瑩
當然,對許多當代地方書寫而言,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參照系。但若是未經省思地將自我釘牢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結構中,地方書寫難免流俗于自我奇觀化,這是對刻板城鄉二元對立認知的固化與重復,也是對具有“他者性”的地方經驗與情感的漠視與浪費。在此意義上,《島嶼的厝》中大量真實可感的細節都在阻撓對于二元認知的想象。以普通話與方言的拉鋸為例,《大厝雨暝》中阿嬤面對外地游客與老師家訪時會自覺切換閩南方言與普通話,自由穿梭于兩種語言之間,不僅用當地人揶揄的智慧消弭了兩種語言之間權力不對等的尖銳感,也擾亂了既往對于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刻板區分。在寫作的形式層面,方言詞匯以注釋的形式標識出意義,彰顯出某種因“地方性”而需要被標注出來的“用力”,它們內嵌在以普通話的思維和句式統攝的全文中,與內容共同構成了雙重的“在而不屬于”的效果。
在這座島嶼中,出島看似是個天經地義而無需道義禮法論證的事情,就連作為島嶼標志的座鐘歌曲也以出島為題,懷戀與向往的都是彼岸他處。“離開”的欲念似乎從島嶼誕生之時便涌動在這里,仿若地方書寫中某種遺傳性的宿命。但《島嶼的厝》以島嶼內外的辯證法提供了更為復雜的選擇,探索了另一種書寫的可能。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