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寫“中國文學史”的新嘗試——張隆溪的“中國自主意識”
當前“重寫”的呼聲響徹世界,而“重寫中國文學史”是“重寫文明史”運動的一個側影。它是文明互鑒觀念所催生的理論、話語和學科自主創新的最新實踐,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推出了很多重要論著或調研報告,對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和借鑒意義。其中,張隆溪的《中國文學史》以自己的獨特方式,面向英語讀者講述了中國文學的數千年故事,搭建了文化交流的雙向橋梁,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群產生了共鳴影響。2024年,作為回譯的《中國文學史》中譯版,經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從其熱銷狀況能看出,本土文化讀者群特別是大眾讀者也是喜愛這本書的。這里主要談談這本書在“重寫”浪潮中的自主性和自主意識問題。
張隆溪的《中國文學史》在重構中國文學敘事的過程中,體現出鮮明的“中國自主意識”。這種自主性并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以全球視野為底色,通過跨文化對話、理論反思與歷史重釋,彰顯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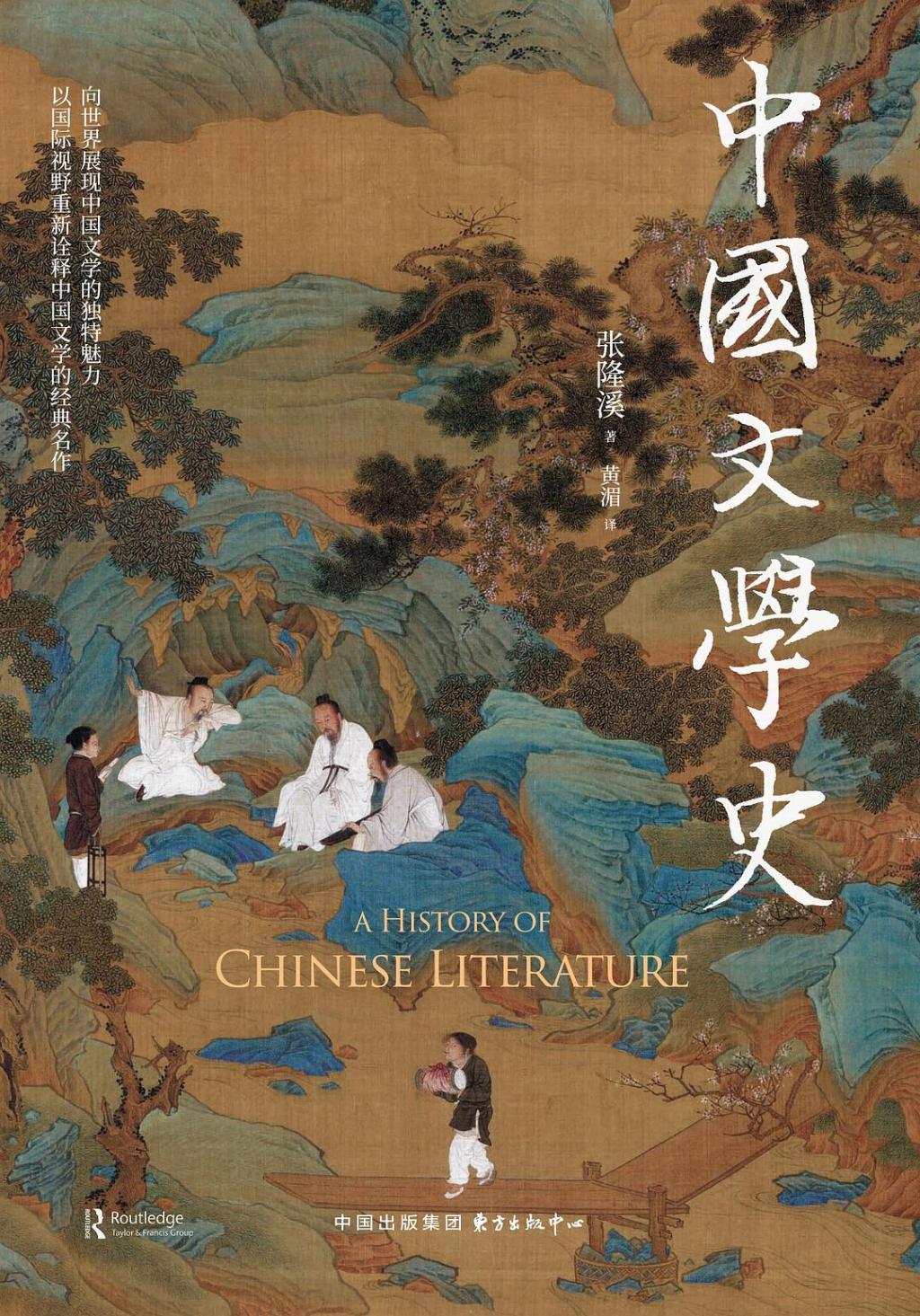
一、雙語文化互文的全球傳播策略
張隆溪的寫作初衷是推動中國文學經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其核心策略是主動向外輸出中國文學價值,而非被動接受西方視角的審視。他選擇以英文撰寫此書,正是基于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現實考量,試圖通過翻譯讓中國文學突破本土語言的局限,進入全球流通領域。而作為“回譯”的中譯本,書中保留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文,形成“雙語并讀”體例,既服務于海外讀者的認知習慣,也為中國讀者提供對照視角,從而在雙向翻譯中強化中國文學的普世性與獨特性。書中所涉及的古代和現代文學作品的英譯文,其質量是經得起仔細推敲和靜心品鑒的,它們注重譯出這些文學作品的中國審美神韻,而非簡單地換一套外語的馬甲,向英語讀者最大程度地傳達了中國文學的原初形象和精神底蘊。
這一策略的自主性體現在:不同于傳統漢學研究的“他者化”視角,張隆溪主動掌握敘事話語權,以中國學者身份直接向世界闡釋中國文學,而非等待西方學者“發現”。正如他借唐玄宗《題梵書》詩自喻“鶴立蛇行域外傳”,即通過外語媒介傳播中國文學,但內在肌理仍然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深層邏輯。而《中國文學史》的中譯本,旨在向中國大眾讀者展示中國文學史如何進行全球傳播的“張隆溪范式”。這種范式既不同于俄國王西里、英國翟理斯、日本古城占吉、德國施寒微等早期漢學家的“中國文學史”,也不同于21世紀以來美國孫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編的兩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德國顧彬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美國梅維恒主編的八卷本《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歐美漢學家的編撰視角和立場總體上反映出比較明顯的“歐洲中心論”意識,在進行中國文學研究和書寫時,站在西方價值立場、知識傳統、思維方法和評價標準來編纂中國文學史,體現鮮明的“歐美優越感”。而歐美漢學家的這種寫法深深影響了中國本土學者的書寫模式,幾乎成為歷史共謀的思維套路。
近期的漢學家也深感其弊端,試圖調整為以中國視角看待中國問題,但難免不切實際地夸飾中國文學和思想文化,這實際是變相的失真寫作;即使是努力克服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偏見,卻受西方學術訓練所固存的文化心理慣習而仍隱伏著“漢學主義”特征。而“漢學主義”本身包含著東方人作為弱勢群體的卑微、憤恨和扭曲,又殘存和糾纏著“東方主義”的潛在迷戀。
張隆溪身為中國學者,但深耕中外比較文學,其國際化思維方式早已形成習慣。張隆溪范式,就是體察英語讀者對中國文學的實際接受情況,以世界文學視野,推介以作品為主體內容的最基礎的中國文學演繹史,呈現他眼中的中國文學精髓。這種范式,不再是文化二元對立,不再是闡釋接受的單維迎合。將英文版回譯成中文版,其中一個作用是,讓中國讀者群知曉,英語國家那些零基礎的普通讀者群目前具有怎樣的接受水準和心態,設身換位領略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接受特征,以期喚起全球文化傳播意識。張隆溪重寫中國文學史所體現的自主意識,最明顯的就是這種“雙語文化互文”的傳播策略,中譯本采用作品選文的雙語對照,正是對文化交融的內在邏輯與雙向互動的追求。
二、跨文化對話和文明互鑒中的主體性建構
在闡釋中國文學時,張隆溪固然兼顧了英語讀者的文化接受習慣,但并未簡單套用西方理論,而是通過中西思想的“意向互補”,在對話中凸顯中國文學的獨立價值。例如第一章《先秦時代與中國文化傳統基礎文本》,講述《淮南子》對倉頡造字引發的“天雨粟,鬼夜哭”神異事件,引了東漢高誘注的解釋。張隆溪認為,高誘注里提到的“錐刀”代稱文書案牘一類的工作,《淮南子》的言論與注釋“顯然是出自道家觀點,以自然之本樸高于文明之巧偽和虛驕,而在這種情況下,口說之言自然也優于書寫之文字了”。關于口語和文字的優劣問題,他認為中西方哲學都有貶低書寫文字的傾向,并舉《斐德若篇》的相關表述為例,說明柏拉圖同樣對書寫文字不屑一顧。柏拉圖說寫作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只不過是智慧的表象,即作偽,“而這正是道家之所以擯棄書面文字的原因,即書寫文字導致巧詐和虛偽,失去質真與素樸”。此章針對這個問題補加腳注,認為德里達所批判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與老莊的“道”論頗似。他讓中國原創的“道”與西方的“邏各斯”形成跨文化對話。當然,他并不認為兩者相契無間。從書中對儒家和道家等先秦基礎文本的論析來看,中國文學中的“道”更強調自然與生命的流動,而非邏各斯的理性中心主義。這種比較并非依附西方框架,而是通過差異凸顯中國思想的獨特性。
漢字構成的表意文字系統,如甲骨文、青銅銘文,是漢字書寫的最初形式;漢字系統是全世界最古老而持續使用的書寫系統,具有異常強大的凝聚力,使得當代讀者依然可以閱讀兩千多年前的古籍,甚至深遠地影響了東亞的“中華文化圈”。該書將“道”作為貫穿中國文學的核心哲學概念,與西方“邏各斯”形成對話,并以“道”統攝文學史脈絡,堅持了漢字書寫系統對于中國文學的根基性作用。比如分析中國詩歌概念的生成過程,聲音、音樂和文字的聯系由緊到松,從口耳相傳到最終以書面形式固定下來,《詩經》就這么成為經典文本。該書進行大量文本解讀時,更是滲透了中國傳統思想在中國文學史中的潛移默化,引導中外大眾讀者去感受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緊密聯系,品察中國文學獨特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同中存異,這顯然在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中秉持了一種中國自主意識。
張隆溪在文明互鑒的同時,講究文學史敘事的雙向文化互動,打破單一區域線性描述的歷史觀,讓中國文學與異文化形成內在呼應地交融。比如對佛教經典早期漢譯情況,花了不少筆墨敘述《四十二章經》傳入中國的情況,穿插安世高、支婁迦讖的漢譯佛經活動。表面上看,敘述佛經漢傳過程,似乎游離了中國文學的發展主線,但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不無關系,講述魏晉以后的中國文學精神,必然涉及佛教思想因素的考察。還有日本遣唐使的文學活動,也是從文明互鑒和文化交流的視角,讓文學史的敘事打破“文化中心論”,既展現中國文學的開放性和輻射性,又強調其對外來文化的轉化能力。張隆溪在不同章節描述了阿倍仲麻呂(晁衡)與王維、李白以文學為媒介的交往情誼。可以說,該書提供了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學文獻,揭示唐代文學如何通過對外交流強化自身的主體性,而非單向接受外來影響或單向輸出文化的形象。
三、作為普及性讀本在重寫浪潮中體現自主編撰特色
梳理國內較有權威性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可以發現,基本的學科知識體系在形式上已然建立。大致包括:一是文學史的起源和發展,從先秦文學直到近代文學等幾大時段劃分,再續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下級學科劃分也由此形成。二是文學流派和代表作品,涵蓋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以及各時代典型的文學集團。三是文學創作理論和批評方法,如《文心雕龍》《歷代詩話》等內容。四是文學思潮和文學思想,如唐宋的士人文化、明清文學的理學元素、建安文學、唐宋派等。五是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塑造經典作家作品如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等。六是文學史與社會歷史的關系闡釋,如文學作品對社會歷史的反映和影響等。七是主流文學樣式與通俗文學兼顧。八是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動態,如文學史的編纂方法、文學史研究的新動向等。流行教材大體上形成這樣的編寫范式,只是各有側重點和若干特點。不過,汗牛充棟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均隱含著源自亞里士多德形式與質料的“二分法”固習,其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兩大版塊闡釋模式的痕跡較為顯著,這使得分析、描述、詮釋、歸納中國文學時呈現出單調意味。在重寫中國文學史的浪潮中,不少學者也在思考新的書寫模式。
張隆溪的《中國文學史》體現了在編撰理念上的自主意識。它在篩選作家和作品方面參考了章培恒、駱玉明和袁行霈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而在切入點方面則考慮了歐美漢學家從中國語言文字和先秦文化思想根基入手的習慣,從而確定了從文字到文化再到文學文本的講述模式,由此潛伏著中國文學如何主動參與世界文學書寫的意圖。相較于國內主流文學史的翔實的考據,張隆溪有意弱化社會背景的鋪陳,轉而聚焦經典作品的跨文化闡釋,努力平衡文學史材料的簡化與深化之關系。例如以“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概括唐詩與宋詩的差異,既借用席勒美學概念,又融入對中國詩學內在脈絡的把握。又如在講述唐代文學的生成特點時,他特意指出,在唐代的詩歌與各種文學形式中,經常出現“碧眼胡僧”及其他舶來形象,“他們那些有別于中土的風俗和生活方式、音樂、舞蹈與文化特征,都在這樣開放包容的中國文化上留下了印記,令其更為豐富多彩”。再如對元代戲劇《趙氏孤兒》的評析,著重以此為例來強調中國文學通過傳教士的翻譯進入全球視野的主動性;從全球文化交流的角度,梳理《趙氏孤兒》由馬若瑟、梅塔斯塔奧、伏爾泰、墨菲到儒蓮和芬頓數個世紀的歐洲傳播簡史,顯現其重要的文化交流意義。如果說張隆溪《中國文學史》英文版是讓英語讀者領略中國文學的世界性,那么中譯本則是讓中國大眾讀者能夠管窺中國文學的世界身影。這種寫法在中國學者以往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中是不太明顯的,而這正是本書的“重寫”價值所在。
再者,在詮釋作品過程中,張隆溪以自己的閱讀感受和經驗來評析作品的審美特點和思想價值,堅持做出自主判斷。例如對王安石《明妃曲》中“意態由來畫不成”的贊譽,聚焦其突破傳統倫理敘事的藝術創新,回避了南宋以降的夷夏之辨爭議的討論,實際是淡化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泛濫導向,回歸文學性與審美價值的評判。再如對晚明李贄及其作品的評述,重心放在具有普泛意義的自由精神上,把李贄與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相提并論,褒揚一種共同的為理想為信念而勇于獻身的自由精神。對《紅樓夢》的解讀,側重揭示曹雪芹對生活與想象、夢幻及現實關系的自覺敘述,認為紅樓的夢幻世界是曹雪芹對記憶與優雅的詩意呈現;把握小說里面的預言讖語構成的命運主題這個邏輯線索,認為小說展示女兒國里美丑愛恨的社會全景。夢幻和命運,是世界文學史中很重要的文學主題,由此聯想到霍克斯、閔福德的英譯本流傳情況,提示中國文學的世界屬性。這種自主判斷意識,上例只是略舉幾片花瓣,讀者自可發現更多有意思的論斷。
總而言之,張隆溪的《中國文學史》在中國文學史重寫浪潮中體現了較強的文化自信心,其文學史敘事格局宏闊,將數千年中國文學的文化根基、精神底蘊和審美品質展示出“世界文學”屬性。毫無疑問,作為面向中外大眾讀者的普及性讀本,其所持的跨文明對話的書寫視角、重寫文學史的自主立場,以及對中外文學交流的重視,都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為重寫中國文學史提供了一種新的嘗試。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