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莫尼克·威蒂格的《奧波波納克斯》與“所有人的童年”
【編者按】
法國(guó)作家、哲學(xué)家莫尼克·威蒂格(1935-2003)是法國(guó)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的先驅(qū),以《奧波波納克斯》獲“美第奇獎(jiǎng)”,創(chuàng)造了獨(dú)特的敘事方式挑戰(zhàn)傳統(tǒng)性別觀念。本文系《奧波波納克斯》(張璐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5年3月版)的中文版導(dǎo)讀,由威蒂格研究者卡特琳·埃卡爾諾與法國(guó)里昂大學(xué)副教授亞尼克·舍瓦利埃撰寫(xiě)。有刪節(jié)。澎湃新聞經(jīng)明室授權(quán)刊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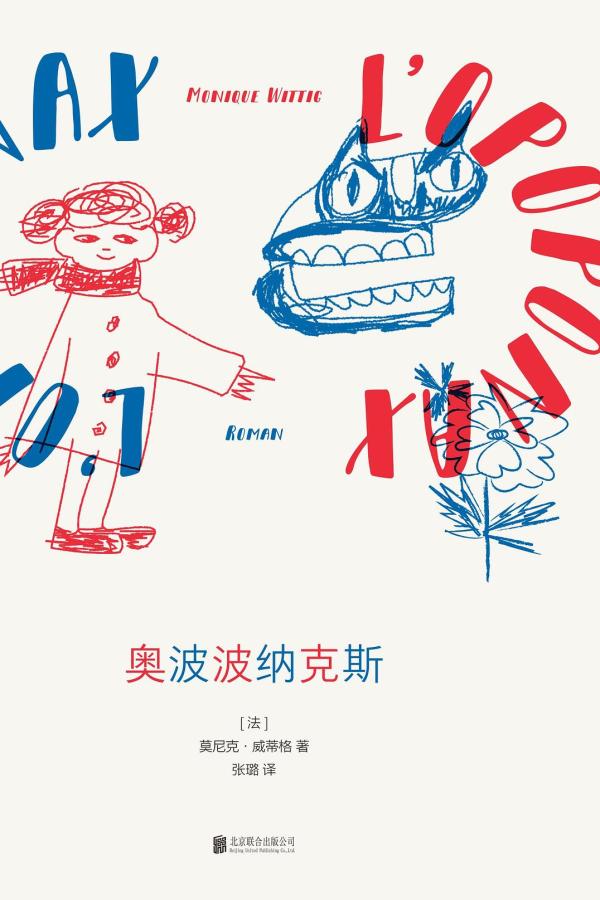
《奧波波納克斯》書(shū)封
與許多同時(shí)代的作家一樣,莫尼克·威蒂格(1935—2003)很少談?wù)撟约骸K钕矚g做的事是實(shí)驗(yàn)新的寫(xiě)作形式,以此跳脫出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的類(lèi)別范疇。1964年第一版《奧波波納克斯》的封面上印著“小說(shuō)”,它也的確作為虛構(gòu)作品獲得了“美第奇獎(jiǎng)”(這是法國(guó)最權(quán)威的文學(xué)獎(jiǎng)項(xiàng)之一,嘉獎(jiǎng)最具智慧、美感,最能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把“美第奇獎(jiǎng)”頒給威蒂格的正是當(dāng)時(shí)最重要的一批作家:娜塔麗·薩洛特、瑪格麗特·杜拉斯、克洛德·西蒙等,他們都是“新小說(shuō)”的代表人物,和他們一樣,威蒂格的作品也在午夜出版社出版(午夜出版社也出版了塞繆爾·貝克特的作品)。
威蒂格與“新小說(shuō)”派的關(guān)系可見(jiàn)一斑。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新小說(shuō)”派一直主導(dǎo)著法國(guó)文化界。也正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新小說(shuō)作家的美學(xué)和文學(xué)傾向開(kāi)始發(fā)生轉(zhuǎn)變:在此之前,他們與自傳體的寫(xiě)作形式一直保持著距離,從80年代起,雖然他們依舊堅(jiān)持自己一貫的美學(xué)和寫(xiě)作原則,但個(gè)人生活開(kāi)始成為他們的寫(xiě)作題材,如娜塔麗·薩洛特的《童年》、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情人》(獲1984年龔古爾文學(xué)獎(jiǎng))、阿蘭·羅伯-格里耶的《重現(xiàn)的鏡子》。午夜出版社也借著這股回歸“傳記”的風(fēng)潮在1984年再版了《奧波波納克斯》,讓這本在二十年前作為小說(shuō)和虛構(gòu)作品來(lái)閱讀和接受的作品,得以作為自傳再次進(jìn)入大眾視野。
一部代替自傳的小說(shuō)?
然而,在《奧波波納克斯》中,讀者卻幾乎找不到關(guān)于莫尼克·威蒂格童年經(jīng)歷的確切信息。1935年,莫尼克·威蒂格在離法德邊境線不遠(yuǎn)的阿爾薩斯出生。四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阿爾薩斯被納粹德國(guó)占領(lǐng),威蒂格一家只得逃離家鄉(xiāng),來(lái)到位于法國(guó)南部“自由區(qū)”的小城羅德茲(洛澤爾省)。這種當(dāng)時(shí)許多法國(guó)兒童都擁有的逃亡經(jīng)歷沒(méi)有在威蒂格的第一部小說(shuō)中留下任何痕跡。書(shū)中僅僅提到孩子們?cè)凇胺e滿了水的彈坑”中玩耍,那是戰(zhàn)爭(zhēng)轟炸的遺跡,以及“烤餅的香味”,那是法國(guó)南部特有的地方美食。作者對(duì)風(fēng)景的描寫(xiě),尤其是讓卡特琳·勒格朗興趣盎然的眾多樹(shù)木、花卉、禾草,都不足以成為事件發(fā)生地點(diǎn)的判斷依據(jù),畢竟作者最常提及的植物在法國(guó)各地都能見(jiàn)到。威蒂格寫(xiě)作中的一切似乎都在抹去地域特色,而地域特色卻在20世紀(jì)40年代的法國(guó)尤為突出。總之,《奧波波納克斯》可以發(fā)生在法國(guó)的任何一個(gè)鄉(xiāng)村。
同樣地,威蒂格也沒(méi)有在卡特琳·勒格朗和她同伴們的故事中打下任何歷史時(shí)期的烙印,書(shū)中沒(méi)有提到德國(guó)占領(lǐng)法國(guó),沒(méi)有提到隨著德軍不斷推進(jìn),大批法國(guó)人背井離鄉(xiāng),除了一處非常隱晦的數(shù)數(shù)暗示:“一起數(shù)數(shù)。七十一,七十二。嬤嬤是比利時(shí)人。”。
因此,威蒂格在《奧波波納克斯》中講述的是一個(gè)共同的童年,所有人的童年,或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幾乎所有人的童年。
“所有人的童年”(瑪麗·麥卡錫)
在20世紀(jì)60年代,法國(guó)大部分人口已經(jīng)生活在城市中,城市聚集著工廠和其他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場(chǎng)所,但是家家戶戶依然保留著關(guān)于祖輩務(wù)農(nóng)的記憶,他們生活在鄉(xiāng)村,與卡特琳·勒格朗以及她的同伴們一樣,他們的生活圍繞著季節(jié)更迭、田間勞作以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周期展開(kāi)(比如收割完麥子便會(huì)迎來(lái)采摘葡萄的季節(jié))。《奧波波納克斯》的第一批讀者對(duì)于這種對(duì)鄉(xiāng)間生活的懷念依然可以感同身受,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大眾對(duì)它的喜愛(ài),因?yàn)橥高^(guò)威蒂格細(xì)膩的描寫(xiě),他們?cè)跁?shū)中看到了田野間的游戲、漫步,以及童年日常生活的一切,哪怕讀者本人未必親身經(jīng)歷,父母和祖父母也一定把這些回憶傳遞給了他們。
同樣,大多數(shù)讀者也未必?fù)碛袝?shū)中描寫(xiě)的校園經(jīng)歷。卡特琳·勒格朗就讀的學(xué)校是由天主教修女授課的“私立”學(xué)校,而大多數(shù)讀者上的學(xué)校則是國(guó)家創(chuàng)辦的“公立”學(xué)校。但是威蒂格從來(lái)沒(méi)有強(qiáng)調(diào)私立學(xué)校的特別之處,反而極力突出兩個(gè)教育系統(tǒng)在課程、課外活動(dòng)等方面的相似之處(尤其是在“外出教學(xué)”中,教師組織學(xué)生走出課堂,教孩子們識(shí)物,教授他們植物、地質(zhì)、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等方面的知識(shí))。
至于大篇幅的宗教儀式(彌撒、朝圣、游行),1964年的讀者對(duì)它們并不陌生。直到20世紀(jì)50年代,宗教活動(dòng)在法國(guó)依然盛行,人們即使不是每個(gè)星期日都去教堂,也會(huì)在重大節(jié)日(圣誕節(jié)、復(fù)活節(jié))頻繁前往。然而,如今宗教活動(dòng)在法國(guó)已經(jīng)十分少見(jiàn),今天的法國(guó)讀者面對(duì)書(shū)中大篇幅的儀式描寫(xiě)也會(huì)感到驚訝和困惑。再加上威蒂格所寫(xiě)的宗教儀式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huì)議(1964年)推行改革之前的天主教儀式:彌撒用拉丁語(yǔ)吟誦,神父背對(duì)信徒主持儀式,圣體顯供架、香燭等儀式器具必須彰顯教會(huì)實(shí)力。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huì)議的改革旨在使崇拜儀式現(xiàn)代化,拉近信徒與教會(huì)的關(guān)系,改革后,彌撒用法語(yǔ)吟誦,神父面對(duì)信徒,流程也得到了簡(jiǎn)化。所以今天的法國(guó)讀者其實(shí)與中國(guó)讀者一樣,也會(huì)對(duì)神秘的宗教信仰和儀式感到費(fèi)解。這也正是威蒂格的天才之處,她通過(guò)一個(gè)小女孩的視角將天主教的禮儀和儀式展現(xiàn)在讀者眼前,而小女孩自己也無(wú)法理解這些禮儀和儀式的意義,在彌撒中,她百無(wú)聊賴,卻發(fā)現(xiàn)了另一樣重要的東西——愛(ài)。杜拉斯也在文章中提到天主教儀式的晦澀以及孩子們對(duì)它的厭倦:“一個(gè)主教死了。他的死會(huì)造成或帶來(lái)什么?在隆重、奢華的主教葬禮中,在中殿的陰影下,在一切引人注目之物的陰影中,在一切之下,小女孩的一綹頭發(fā)被她旁邊的小女孩看到了。多美啊。[……]經(jīng)過(guò)的天主教修女們盲目地見(jiàn)證了她們并不知曉的另一種耀眼的至福。”
從個(gè)人視角到普遍視角
雖然卡特琳·勒格朗的童年扎根于20世紀(jì)四五十年代的法國(guó),但威蒂格努力淡化了時(shí)間和空間對(duì)小說(shuō)的限定,而是選擇突出童年經(jīng)歷的共性。80年代,威蒂格在評(píng)論朱娜·巴恩斯的寫(xiě)作時(shí)提到,《奧波波納克斯》的寫(xiě)作不在于描述一種“個(gè)人視角”(即喜歡同班同學(xué)的法國(guó)小女孩卡特琳·勒格朗的視角),而在于構(gòu)建一種可以容納所有讀者的“普遍視角”。這種將視角普遍化的成功嘗試引起了“美第奇獎(jiǎng)”評(píng)審委員會(huì)的關(guān)注,也正是因?yàn)樽x者能在《奧波波納克斯》中找回自己的童年回憶,才使得今天的法國(guó)讀者對(duì)它情有獨(dú)鐘。
為了將視角普遍化,威蒂格采用了一種簡(jiǎn)單的手段,但是它給文本帶來(lái)了極其精巧、復(fù)雜的風(fēng)格特征。一般而言,小說(shuō)通常由第三人稱書(shū)寫(xiě)[借助用于描述他人的人稱代詞“il”(他)或“elle”(她)],而自傳一般用第一人稱書(shū)寫(xiě)[借助人稱代詞“je”(我)],但威蒂格選擇了一個(gè)特殊的代詞——“on”。這個(gè)法語(yǔ)人稱代詞功能特殊,只在極少的語(yǔ)言中存在,它是一個(gè)第三人稱代詞,卻能指代說(shuō)話者(等同于“je”)。它既是“je”,也是“il/elle”,是一種可以同時(shí)提及說(shuō)話者(第一人稱)和被指涉對(duì)象(第三人稱)的語(yǔ)言形式。“on”的使用讓《奧波波納克斯》既不屬于小說(shuō)體裁,也不屬于自傳體裁。
不同于第三人稱代詞“il/elle”,“on”既可以指代女性,也可以指代男性,這是它的另一個(gè)優(yōu)勢(shì)。威蒂格利用“on”的這一特性構(gòu)建了一個(gè)性別身份還未經(jīng)社會(huì)構(gòu)建的兒童人物:卡特琳·勒格朗只是單純地認(rèn)為自己是一個(gè)人,她正在接受的教育也尚未將她完全限制在小女孩的身份之中。而“on”也讓《奧波波納克斯》的讀者,無(wú)論男女,都能代入其中。
克洛德·西蒙也對(duì)“on”帶來(lái)的獨(dú)特閱讀體驗(yàn)贊賞有加:
閱讀這些文字的時(shí)候,我不是在閱讀一段歷史或故事,它在忠實(shí)而有趣地訴說(shuō)可能發(fā)生在一個(gè)小女孩身上的事情,而是通過(guò)她的眼睛、嘴巴、雙手和皮膚去看,去呼吸,去咀嚼,去感受。
“on”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新穎、奇特的視角,讓我們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孩提時(shí)代的感覺(jué),或者說(shuō)學(xué)習(xí)成長(zhǎng)的感覺(jué)。《奧波波納克斯》沒(méi)有講述故事,而是呈現(xiàn)了那個(gè)叫卡特琳·勒格朗的小女孩所感知到的一切,沒(méi)有敘述主體來(lái)組織她的感知,區(qū)分故事與現(xiàn)實(shí),將事件放置在空間或時(shí)間之中。毫無(wú)征兆地,地理課緊接著彌撒,田間散步緊接著課間休息,摘豌豆緊接著背寓言。經(jīng)歷過(guò)的場(chǎng)景、觀察到的事實(shí)、聽(tīng)到的故事、孩提的恐懼以及青春期的遐想接踵而至,它們交織在字里行間,展現(xiàn)出孩童對(duì)宇宙強(qiáng)烈的探究欲和記錄知識(shí)的激情。這就是瑪麗·麥卡錫所說(shuō)的“所有人的童年”,也是瑪格麗特·杜拉斯所謂的“我們都寫(xiě)過(guò)這本書(shū)”。誠(chéng)然,讀者無(wú)法與一個(gè)缺乏外表與性格描述的人物產(chǎn)生身份認(rèn)同,但《奧波波納克斯》通過(guò)人物的成長(zhǎng)節(jié)奏、“純粹的描述材料”讓讀者仿佛置身于故事中,化身為卡特琳·勒格朗。
學(xué)習(xí)讀寫(xiě)
卡特琳·勒格朗的活動(dòng)和學(xué)習(xí)讓我們意識(shí)到她在長(zhǎng)大,年級(jí)在上升。她學(xué)習(xí)寫(xiě)字,先用“黑色的鉛筆”在本子上吃力地畫(huà)出“m、l、b”,接著寫(xiě)出單詞、句子,比如“萊昂學(xué)功課”,最后鉛筆換成了令人討厭的蘸水鋼筆:“食指總是滑到蘸滿墨水的筆頭上。本子上有紫色的手指印……”她也在學(xué)習(xí)讀書(shū):“你高聲朗讀完整的句子。磨坊里的磨坊主磨玉米。磨坊主的丈夫拉來(lái)綿羊。綿羊吃磨坊主磨的玉米。”
從其他材料中借來(lái)的引文、語(yǔ)句貫穿全書(shū)。首先,學(xué)生們高聲拼讀句子,隨著年級(jí)的升高,句中的詞匯也越來(lái)越復(fù)雜。在第二章中,井里發(fā)現(xiàn)的寶藏取代了磨坊主和她的磨坊:“對(duì)——這——個(gè)——窮——人——家——來(lái)——說(shuō)——是——一——筆——意——外——之——財(cái)”。
在第四章中,卡特琳·勒格朗登上了一個(gè)嶄新的臺(tái)階。假期里,她和表兄弟在看各自的書(shū)。當(dāng)樊尚·帕爾姆因?yàn)椤鞍⒌揽舜L(zhǎng)在追威士忌泡——泡——泡時(shí)變成了一只小鳥(niǎo)嘰——嘰——嘰”(《丁丁歷險(xiǎn)記》之《月球探險(xiǎn)》)而哈哈大笑時(shí),卡特琳·勒格朗則在背誦課本上的《薩朗波》(福樓拜)片段:“鬢角的珠串垂到嘴角,粉色的嘴巴像半開(kāi)的石榴。胸前的一組寶石……”
接下來(lái)到了高中時(shí)期。為了記住《阿利斯坎》武功歌的片段,卡特琳·勒格朗和同學(xué)們一整天都在背誦古文:“德拉姆王指髯為誓/吾當(dāng)以五馬分尸……余知其髯不能守信”。她們閱讀拉丁語(yǔ)的維吉爾,她們學(xué)習(xí)詩(shī)人,卡特琳·勒格朗從龐大的詩(shī)詞庫(kù)里摘出零散的詩(shī)句,將它們散落到自己的文本中,比如馬萊伯的“鄉(xiāng)村已在我面前展開(kāi)”。她把查理一世的詩(shī)句“思想中除我以外之一切禁錮我”和蘭波的詩(shī)句“潔白的奧菲莉亞像一朵大百合花漂浮著”寫(xiě)在給瓦萊麗·博爾熱的植物標(biāo)本集上。
卡特琳·勒格朗引用的詩(shī)句越來(lái)越多,越來(lái)越復(fù)雜。她將《阿利斯坎》武功歌的古法語(yǔ)詩(shī)文作為第五章的開(kāi)篇,而波德萊爾《旅行的邀約》中的三個(gè)詩(shī)節(jié)(而非疊句)則貫穿最后一章。從“你說(shuō),我的孩子/我的姐妹/想想多甜美/去那兒一起生活/悠然相愛(ài)/相愛(ài)至死/在像你一樣的國(guó)度里”開(kāi)始,到最后一頁(yè)的“你說(shuō),落日的余暉/給田野、運(yùn)河與城市/灑下風(fēng)信子/與金黃的色彩/在溫暖的柔光中/世界在沉睡”。全書(shū)最后一句則借用了文藝復(fù)興詩(shī)人莫里斯·塞夫的愛(ài)情詩(shī):“你說(shuō),我曾愛(ài)她之深我仍活于她身。”
在最后一章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你說(shuō)”(on dit)代表后面的內(nèi)容是一句引語(yǔ),它們也讓這一章成為全書(shū)最模糊的一部分。你說(shuō)現(xiàn)在是九月,你說(shuō)現(xiàn)在在下雨,你說(shuō)瓦萊麗·博爾熱的嘴唇像佩涅洛佩的一樣閃耀……誰(shuí)在說(shuō)話?是思緒還是夢(mèng)境?誰(shuí)在引用波德萊爾和塞夫的詩(shī)句?或許是卡特琳·勒格朗,但也可以是任何人,每個(gè)人,甚至是作者本人。全書(shū)最后一句的人稱和時(shí)態(tài)讓它脫離了那個(gè)已經(jīng)成長(zhǎng)為少女的小女孩的故事,而隱隱勾勒出作者本人的形象。不過(guò),既然引用詩(shī)文是少女卡特琳·勒格朗鐘愛(ài)的消遣方式,而且這些抒情詩(shī)也與她和瓦萊麗·博爾熱的情愫相互呼應(yīng),即便是最后一句,莫尼克·威蒂格依然與卡特琳·勒格朗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奧波波納克斯》是自傳體文本的第三人稱變體,威蒂格對(duì)文體的探索也延續(xù)到了她的第二部史詩(shī)小說(shuō)《女游擊隊(duì)員》(Les Guérillères)中。
一種寫(xiě)作的到來(lái)
《奧波波納克斯》是一種寫(xiě)作的到來(lái),是與作者本人經(jīng)歷極其相似的寫(xiě)作實(shí)踐。首先,威蒂格與卡特琳·勒格朗的寫(xiě)作都與前人的文本密不可分,威蒂格在《文學(xué)工地》(Le Chantier littéraire)中說(shuō),“與作家首先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的是浩大的古代與現(xiàn)代作品庫(kù)”,卡特琳·勒格朗,抑或是莫尼克·威蒂格本人,都喜歡裁剪、挑選、拼湊他人的文本,從孩童時(shí)代起便把閱讀與寫(xiě)作結(jié)合起來(lái),把讀到的段落背誦下來(lái),以便日后使用。其次,威蒂格與卡特琳·勒格朗進(jìn)行的都是一種實(shí)踐性的寫(xiě)作。在《文學(xué)工地》中,威蒂格將作家比作那些在工作室或工地上處理具體問(wèn)題的工匠、建造者。而卡特琳·勒格朗的寫(xiě)作活動(dòng)更像是DIY:她先試著畫(huà)出奧波波納克斯的模樣,再用文字對(duì)它進(jìn)行描述;她在頁(yè)腳寫(xiě)字;她自己制作書(shū),做植物標(biāo)本集……她目不轉(zhuǎn)睛地注視著妹妹韋羅妮克·勒格朗以及后來(lái)瓦萊麗·博爾熱在地上畫(huà)的形狀和字母。最后,卡特琳·勒格朗為了博得瓦萊麗·博爾熱的注意和愛(ài)而寫(xiě)作,這讓人聯(lián)想起作者本人自青春期起就將寫(xiě)作與女性之間的情愫緊密相連……
威蒂格在寫(xiě)作生涯中不斷追尋普遍性,而這一切都始于《奧波波納克斯》——一個(gè)關(guān)于法國(guó)童年的故事。威蒂格以極少的文學(xué)手段,慷慨地為讀者提供了找回童年的機(jī)會(huì)。卡特琳·勒格朗是她,但同時(shí)也是我們這些閱讀《奧波波納克斯》的人,無(wú)論是男是女,無(wú)論出生在20世紀(jì)還是21世紀(jì),出生在法國(guó)還是中國(guó)。這部驚人的小說(shuō)講述的是我們每一個(gè)人的故事。我們無(wú)比欣喜地得知,在中文譯本的幫助下,卡特琳·勒格朗也變成了中國(guó)人。





- 澎湃新聞微博
- 澎湃新聞公眾號(hào)

- 澎湃新聞抖音號(hào)
- IP SHANGHAI
- SIXTH TONE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