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從“神經癥”到“美國病”:成為美國大眾現象的瘋癲
與各地一樣,在美國,最早被旅居法國的外國人稱為“神經癥”(neuroses)亞臨床形式的瘋癲,比有明顯臨床癥狀的瘋癲常見得多,后者的病患會被關起來。正是密歇根精神病院的院長E.H.范·德烏森博士在1867—1868年度報告的補充說明中,將法國神經癥歸入“神經衰弱癥”(neurasthenia)大類。1869年4月,他在《美國瘋癲病雜志》發表了名為《對一種最終導致瘋癲病的神經衰弱癥的觀察》文章。他在文中解釋了自己選擇的名字:“神經衰弱癥是一個古老的術語,取自醫學詞匯,之所以使用它,只是因為它似乎比任何其他術語都能更直接地呈現這種疾病的特征,而且可能比常用的術語‘神經虛弱’(nervous prostration)更明確。”“我們的觀察使我們想到,”范·德烏森寫道:
有一種神經系統的疾病,上面[在標題中]給出的術語很好地抓住了其基本特征,在該疾病的發展過程中,它的基本特征非常穩定,因此將它視為一種獨特的疾病形式是合理的……在其誘因中,過度的腦力勞動名列第一,尤其是當病人同時伴有焦慮和營養缺乏。它也可以由其他原因造成:壓抑的情緒、悲傷、家庭糾紛、長期焦慮和經濟上的窘迫……其主要癥狀是全身不適、營養不良和消化不良;肌肉無力,面容表情改變;子宮移位及其帶來的不良反應,以及神經衰弱性頭痛、大腦缺血,同時伴有感覺過敏、易怒、精神抑郁、智力受損、憂郁癥和躁狂癥的傾向。

“神經衰弱”是很容易被識別出來的,盡管醫學的專業術語在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出版后,迅速代替了早期《美國瘋癲癥雜志》的普通用語,并成為了一種寫作范式。《物種起源》一書的出版大大提高了美國科學的權威,同時加速了美國精神心理學從先前效仿的英國和法國的模式,向所謂“更科學”(至少在語言上)的德國模式的轉變。“神經癥”作為一種診斷比它多用了許多年。在許多情況下,它被稱為“歇斯底里癥”。今天,我們稱之為“雙相譜系疾病”——包括精神抑郁、循環性精神失調、廣泛性焦慮障礙,等等。范·德烏森博士寫道:“它發生了……在那些身居要職的人身上,那些職位對個人的神經能量要求很高。它們讓人累死累活,而且得不到所需要的大量睡眠。”在密歇根州,女性尤其受到了它的影響,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中下階層女性。范·德烏森寫道:
我們一些小農場主妻子的婚姻生活在早期似乎特別容易導致這種情況。她經常是從一個可以享受必要的社交和智力娛樂的家庭,搬遷到一個與世隔絕的農舍。在那里,她每天都要從事非常單調的家務勞動。她的新家,如果它算得上是個家,由于嚴格的功利主義,沒有一樣可以令人感到愉快的東西:花園里看不到一朵綻放的花;也許她有書,但沒有時間去讀……農活的緊迫性,使得人們每頓飯都匆匆忙忙,根本沒有交談的時間。隨著夜幕的降臨,干了一天活的農民疲憊不堪,往往習慣于很早就上床睡覺,讓妻子用針線活打發漫長而寂寞的夜晚。打理莊稼和各種各樣的農場活計讓她丈夫的生活足夠豐富多樣、充滿樂趣,但她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如果她還要獨自照顧一兩個病懨懨的孩子時,既令人疲憊,又令人沮喪,其嚴重程度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許多申請住院治療的女性病人都是來自這個階層。
這段描述不乏對女性的同情。然而,它的邏輯是錯誤的。例如,如果一個農民的妻子必須照料小孩,為什么她的日常生活會變得更加壓抑?她丈夫辛勤工作、種植莊稼、干農場里的各種活時會感覺豐富多彩、饒有趣味,難道照料孩子不會讓她有同樣的感覺嗎?不,農婦們神經衰弱的根源不是農場生活的艱辛。相反,真正的原因是她們想象自己本可以過上一種不同的、更加體面的生活,但錯誤的選擇讓她們與之失之交臂。這正是為辛克萊·劉易斯贏得了諾貝爾獎的小說《老百姓》(Main Street)中的卡羅爾·肯尼科特(Carol Kennicott)所面臨的問題——這本書被稱為“美國中產階級思想的精彩日記”——在范迪森在《美國瘋癲病雜志》發表“觀察”一文的半個世紀之后,該小說問世。在該故事中,卡羅爾嫁給了歌斐爾草原——明尼蘇達州一個小鎮里的社區——的一位醫生后,搬到了這里生活,她對新生活完全不能適應,而她的丈夫和大多數居民一樣,對那里很滿意。卡羅爾又是如何處理自己的不適應呢?她認為,歌斐爾草原不利于人們居住,需要改革。這個問題持續成為“美國中產階級的思想問題”(而卡羅爾的“解決方案”,也將持續成為其解決方案)。事實上,范·德烏森認識到,并不是只有農民的妻子才容易患“神經虛弱癥”。“現今的溫室式的教育制度,”他寫道,“以及許多商業企業及職業活動的輕率、浮躁、投機的特點,非常容易讓人們患上這種精神疾病。”
后來,在1869年,喬治·米勒·比爾德也把明顯普遍存在的“神經虛弱”或“神經衰竭”(nervous exhaustion)稱為“神經衰弱”(neurasthenia)(asthenia在德國是一個特別常見的詞匯,雖然它起源于蘇格蘭)。比爾德的文章發表在《波士頓醫學和外科雜志》上,也許,該雜志比《美國瘋癲病雜志》更受歡迎,至少在一些紳士們看來是這樣的。被診斷患有“神經衰弱”的威廉·詹姆斯幫助普及了這個概念,他把神經衰弱稱為“美國炎”。這個詞是從一位名叫安妮·佩森·卡爾(Annie Payson Call)的作家那里借來的,1891年她出版了《休息帶來的力量》(Power Through Repose)一書。詹姆斯對該書給予了好評,因為他認為這本書顯然有助于減輕精神緊張,而精神緊張是這種全國性疾病的原因。佩森·卡爾寫道:“極度的精神緊張似乎是美國人特有的,以至于一位德國醫生來到這個國家行醫……最后他宣布自己發現了一種新的疾病,他稱之為‘美國炎’。……我們患上了各種各樣的‘美國炎’。”在詹姆斯的案例中,他的病情似乎比其他病患更為嚴重,抑郁癥讓他產生了自殺的想法。不過這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認為這很正常,“我認為,凡是受過教育的人”,他指出,“都不可能從未動過自殺的念頭”——他認為,即使是異常復雜的神經衰弱,也只是人們生命過程中的正常發展階段,和我們今天所談的“青少年焦慮癥”如出一轍。雖然他的狀況非常糟糕,但他的神經衰弱始終沒有發展到臨床精神疾病的程度,然而他的直系親屬中,并非每個人都那么幸運。
喬治·米勒·比爾德認為,這個對美國影響尤其大的問題涉及的范圍太廣了,值得他為自己之前的著作《美國人的精神緊張:原因和后果》(1881年)再寫一本幾百頁長的《增補》,在它的序言中他告訴讀者:
美國出現了一些新型疾病,英國直到最近才知道這些病,或者之前對其知之甚少。這是神經系統的一類功能性疾病,現在開始在文明世界中隨處可見,似乎它們首先在美國生根,并從那里將它們的種子四處散播。
這些疾病都是現代才有的,發源于美國;在過去,任何時代、國家、文明在鼎盛時期,都不曾出現過這樣的疾病,無論是希臘,羅馬,西班牙,還是荷蘭,都不曾有過。在現代社會學的所有事件中,功能性神經疾病在美國北部的興起和發展是最驚人、最復雜和最引人深思的;破解它的謎題,揭示它的奇妙[原文如此]現象,追溯這些疾病的源頭,展望它們未來的發展,就是在解決社會學本身的問題……
美國這個新世界的每一項貢獻都規模宏大,同西歐國家微不足道的倉庫貢獻的任何東西相比,美國貢獻的東西即使不一定更好,也永遠是更大的。此外,美國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因此,當這個年輕的泱泱大國終于有了自己的疾病時,這不僅僅是“美國病”——而是全美國人的病。
在他的《觀察》一文中,范·德烏森博士指出:“在精神病理學中,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神經衰弱的人最早出現的明顯的病態心理癥狀是猜疑。誠然,在此之前這些人會易怒,或者脾氣和性格會產生其他的變化——總是有嚴重的癥狀……但是,如前所述,第一個明顯的病態情緒是猜疑。如果病人是一個有著深厚宗教感情的人,對他來說只有宗教是唯一的、偉大的、最重要的事,那么他就會猜疑上帝的承諾,對個人與教會、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產生病態的看法——總之,這就是所謂的‘宗教憂郁’。如果賺錢盈利和擁有廣闊的土地是某個人人生的偉大目標,那么,對貧困的擔憂會時時折磨著他。他未來似乎只能進貧民收容所,貧窮將是他的宿命。地契里滿是錯誤,他的筆記是偽造的,連金銀似乎都一文不值。如果夫妻關系特別親密、恩愛,就會經受嫉妒的折磨。在幾個典型的病例中,病態的感覺始終存在。”16世紀的英國人說話直截了當,他們將這些特別敏感的人(disaffection)(或不適應社會的人)稱為“不適分子”(malcontents)。“美國的神經衰弱者在他們的社會中感到不舒服;他們無法為自己找到合適的位置;一切都很可疑,因為他們不確定自己的身份。”范·德烏森博士認為,如果不通過改變他們的環境和職業來緩解“以前的擔憂和焦慮”,并由專門的“衛生和醫療機構”來保護他們,這些神經敏感的人肯定會發展成“確診的憂郁癥或躁狂癥患者”,即臨床上的精神病人。然而,在開放、多元和寬容的美國,大多數患者能夠成功地自我治療。這種自我治療一貫采取下述形式:如果不是狂熱,他們也至少會熱情地投身于一些事業,這些事業并非是致力于其中的那些人的興趣所在。它們的吸引力在于可以提供一個批判美國社會的窗口,從而證明這些人對美國社會的不滿和不適是有道理的。
19世紀40年代,美國北方各州發生了一場大眾運動,它被精神病界認為是一種集體瘋癲。它是一場宗教運作,因其核心教義的創始者是米勒先生,被命名為“米勒主義”,米勒先生預言世界即將毀滅。《美國瘋癲病雜志》1845年1月發表了一篇關于這場運動的文章。“我們不打算撰寫[其教義的]歷史,”文中寫道,“也不打算證明它只不過是一個以前經常流行的妄想的再次流行,它對社區造成了巨大傷害。眾所周知,它最近的傳播帶來了不幸的結果,因為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報道了它所導致的自殺和瘋癲案例。”例如,紐約州北部的一家報紙寫道:“我們的證券報中滿是對米勒式的妄想最駭人聽聞的描述。我們聽說過自殺、瘋癲和各種各樣的愚蠢行為。”波士頓的一份報紙報道說:“該市的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因為受這種可怕的妄想的影響,上周被送到精神病院。這名男子割破了自己的喉嚨,但在切斷大血管之前被人阻止。另一名男子因同樣的原因割斷了自己的喉嚨,導致他當場死亡。”康涅狄格州、費城和巴爾的摩也有類似的報道。尤蒂卡(Utica Asylum)精神病院涌入了大量“參加該教的布道后精神錯亂”的病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康復了。但有些人被認為無法治愈,一直瘋癲。根據1844年北部各州精神病院的報告,只有三所醫院收治了32名因信奉米勒主義而瘋癲的患者。在《美國瘋癲病雜志》的一位作者看來:“黃熱病或霍亂的流行對國家帶來的危害遠遠不如這種教義潛在的危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所報道的自殺事件和精神病院收治的病人只是冰山一角:“成千上萬的人雖然尚未精神錯亂,但他們的健康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以致他們永遠也沒有能力去履行生活中的職責;尤其是女性。許多人的神經系統幾個月來一直處于興奮和驚恐的狀態,他們受到了沖擊,這將使他們容易患上各種各樣令人痛苦的神經疾病和瘋癲,也將使他們的后代容易患同樣的疾病。”未受影響的人通常認為這種妄想“只屬于世界的黑暗時代,或者只在文盲和無知的人群中傳播”。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信奉米勒主義的不乏“聰明善良的人”。事實上,《美國瘋癲病雜志》宣稱:“我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教義的倡導者和信徒是真誠和虔誠的人。我們完全不認為他們有任何惡意。事實上,這種道德流行病似乎總是在蔓延……‘它的傳播沒有得到任何腐化社會的邪惡東西的幫助,也不依賴于任何關乎世俗利益的想法’。”
很明顯,比起今天那些對異見者口誅筆伐的評判者,早期的美國精神病學家對那些信奉他們認為是錯誤甚至危險的信仰的人更仁慈——他們更尊重美國人民。在《美國瘋癲病雜志》看來,米勒主義是一種疾病,一種流行病或傳染性偏執狂,把信奉這一學說的責任推給它的受害者是愚蠢的,這同把感染肺結核都歸咎為病人自己的過錯無異。
1845年,米勒主義顯然已經衰落,《美國瘋癲病雜志》寫道:“目前,我們可以認為這種學說已經消亡,可能不會很快復活。”但是,它預測,“肯定會有其他類似的流行病”。文中建議說:
如果我們不能采取措施來防止其他同樣有害的妄想四處傳播,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是否還有更好的辦法來對付它。這種妄想的流行會為其他妄想鋪平道路。因此,我們必須期待他們,期待那些對社會還有良好愿望的人,去努力防止這些妄想對人們造成廣泛的傷害。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與已經受米勒主義傷害的人交談沒有任何好處——
與那些已經被它影響的人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事實上,通過觀察一名患有嚴重妄想癥的信徒,我們的看法得到了證實。他們是偏執狂,越是與他們講道理,他們的注意力就越是集中在他們妄想的主題上,他們病態的信仰就越是強烈。我們認為,人們為了揭露米勒先生的猜測和預言的謬誤所進行的布道和印制的傳單并沒有多大用處。
相反,他們提出了以下建議,特別是針對家長的建議:
不要去聆聽任何新的、荒謬的和令人興奮的教義,遠離那些你會影響到的人。這不需要也不會阻礙你獲得新道理和新知識,因為在這個國家這些東西會在第一時間出版。如果你愿意的話,可以讀讀它們,但不要親自去看和聽——去擴大觀眾和聽眾的人群,因為正如前文所說,這些病癥主要是通過接觸傳染和模仿來傳播的。
讓人們偏好閱讀,是個明智的想法(它鼓勵人們理性地思考問題,與此相比,其他傳遞信息的方式可能會將這些問題包裹在情緒中,模糊人的感知,阻礙理性思考)。除了這一條外,這個建議很可能本質上是錯誤的。米勒主義的流行不太可能是由于接觸傳染。更確切地說,它說明信奉該學說的人之前就已經存在神經衰弱的狀況。這種情況在19世紀40年代的先進歐洲國家已經非常普遍,如英國和法國;它在美國的傳播速度也一定很快,因為這里明確以自由為導向,且很快就讓人們明白了民族主義的隱含之意。事實上,正如我們所見,在短短幾十年內,它將成為“美國病”。顯然,在19世紀40年代,米勒主義讓許多人感覺解脫,它幫助人們明白了令他們感到不快的經歷(解釋了他們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為什么這樣的感覺合乎情理),從而引導他們,提供他們生活中缺乏的某種形式的結構。在美國歷史進程中,這種對治療的普遍需求會持續存在并不斷增加。
不管《美國瘋癲病雜志》的這位早期撰稿者對集體瘋癲的傳染性的判斷是對還是錯,他預測到即使米勒主義衰落了,美國的瘋癲也不會終結,這一點是正確的。類似的運動將震撼美國人口的各個組成部分。其核心的思想或教義通常是妄想(即與客觀現實沒有任何聯系的純粹幻想的產物),但在后來的病例中,這種“病態的信仰”將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當然,在美國,政治和宗教相互貫通:政治從很早就成為了美國的宗教,而傳統宗教則根據美國的民族主義被重新詮釋,這使得兩者很容易結合在一起,也很難對二者進行區分。由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特別適應他們的文化環境,這種相互貫通在精神病院病人的作品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我們今天從收集這些數據的第一刻起就能診斷出他們是否為精神病患者。然而,盡管它們的關系錯綜復雜,經過思考我們可以發現政治領域的影響超過宗教領域。這些精神分裂患者的絮言,以一種詭秘的方式,反映了他們周圍文化的整體變遷。那些患有輕度的、普遍的、全美國都有的精神疾病的人,即神經衰弱患者,代表了整體上的美國文化。
正如我們在賈維斯關于瘋癲原因的討論中所看到的,早期的美國精神病學家注意到在社會意識中,政治超越了宗教,它的興起會擾亂人民的意識。《美國瘋癲病雜志》提到它時,平靜淡然,似乎這件事不言自明,不需要解釋。例如,布里格姆博士1849年4月以編輯的身份寫道:“所有轟轟烈烈的熱潮的受害者最終都住進了精神病院。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路德宗教改革,都導致了瘋癲的增加。”紐約附近布盧明代爾精神病院的已故醫生麥克唐納博士說道:“作者自己的經歷證明,反共濟會熱潮、支持杰克遜的熱潮、反杰克遜運動、金融熱潮、廢奴運動、投機熱潮,都給精神病院提供了病人。”布里格姆不認為這些“熱潮”有多大區別,他發表的社論文章是一項有關“賺錢狂潮”研究的序言,但他提到的大多數“熱潮”顯然是政治性的。
隨后,德國宣布出現了一種新形式的明顯的政治瘋癲。一位名叫M.格羅戴克(M. Groddeck)的作者在其題目為《民主病:新型瘋癲病》的醫學博士論文中指出,這是“民主疾病”,其“民主帶來的新時代的瘋癲病毒最近在整個歐洲大陸國家中傳播的速度,與霍亂穩重、文雅的行進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瘋癲病雜志》的一位編輯1851年評論道:“它在所有歐洲國家的首都幾乎同時擴散,但我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想過要對它進行醫治。”從這一反應來看,雖然他并不認為對民主瘋癲病的診斷令人震驚,但他不確定這種疾病是否嚴重到需要對其進行精神病學的干預。在我所關注的瘋癲病發展的早期階段,《美國瘋癲病雜志》中的大部分“道德流行病”或“集體偏執狂”的例子都來自歐洲。歐洲離我們很遠,而在美國,到1851年,還沒任何政治“熱潮”能達到“傳染性偏執狂”的程度,這可能是暴風雨前的平靜,因為這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對平等的崇拜甚至超越了對上帝的種種闡釋,它對于平等是如此寬容,因此肯定也難逃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顯然是民主——“道德流行病”的魔爪。
2005年6月,《華盛頓郵報》宣布,根據最新數據,“美國有望在精神疾病方面排名全球第一”。這一“令人愉快”的聲明的基礎,是哈佛大學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羅納德·凱斯勒主持進行的著名的全國共病調查復測,本書前文已經多次提到這一研究。據《華盛頓郵報》記者稱:“該研究集中于四大類精神疾病:焦慮癥(如恐慌癥和創傷后應激障礙),情緒障礙(如重度抑郁癥和雙相情感障礙),沖動控制障礙(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和藥物濫用。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候符合這種疾病的標準。”這位記者援引凱斯勒的話說:“因為精神分裂癥、自閉癥和其他一些嚴重且相對常見的疾病沒有被包括在內,所以實際患病率更高一些。”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每兩個美國人中至少有一個是“神經衰弱者”。當然,我們不再用這個完全過時的名字來稱呼這一全國性的疾病。盡管“神經衰弱”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分類》(ICD)中仍然是一個診斷類別,但我們自己的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其前身是美國瘋癲病醫療機構負責人協會——的《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DSM)不再使用這個術語。我們現在用一種更科學的方式來描述這種廣泛傳播的疾病,將其稱為焦慮癥、沖動控制障礙以及輕度抑郁癥,有時這么稱呼確實更為科學。與精神分裂癥和躁郁癥相比,威廉·詹姆斯所認為的“美國炎”癥狀更為輕微。精神病院關注的是一種輕度的瘋癲——影響愛德華·賈維斯的那種持續的不適,即在一個開放、多變、競爭激烈、選擇越來越多的社會中,人們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天,太多的美國年輕人都在受到這種疾病的困擾(《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精神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輕人的疾病。”一半被診斷為精神障礙的人14歲便會顯示出這種疾病的跡象,四分之三的人在24歲開始出現這種疾病的征兆),因此它被認為是正常現象,被認為是一個麻煩但不可避免的發展階段,如婦女的月經或更年期。這不是一種會導致將主觀和客觀現實相混淆的嚴重精神疾病,只是一種精神上的不適,無論人們對它的感受有多么深刻。“美國炎”這個詞合適嗎?——不過,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只有一半的美國人,即不超過1.6億人,患有這種疾病。也許稱之為“美國病”(一些俄羅斯精神病學家習慣于這么稱呼它)有點夸張?畢竟,統計數據無論如何都不會完全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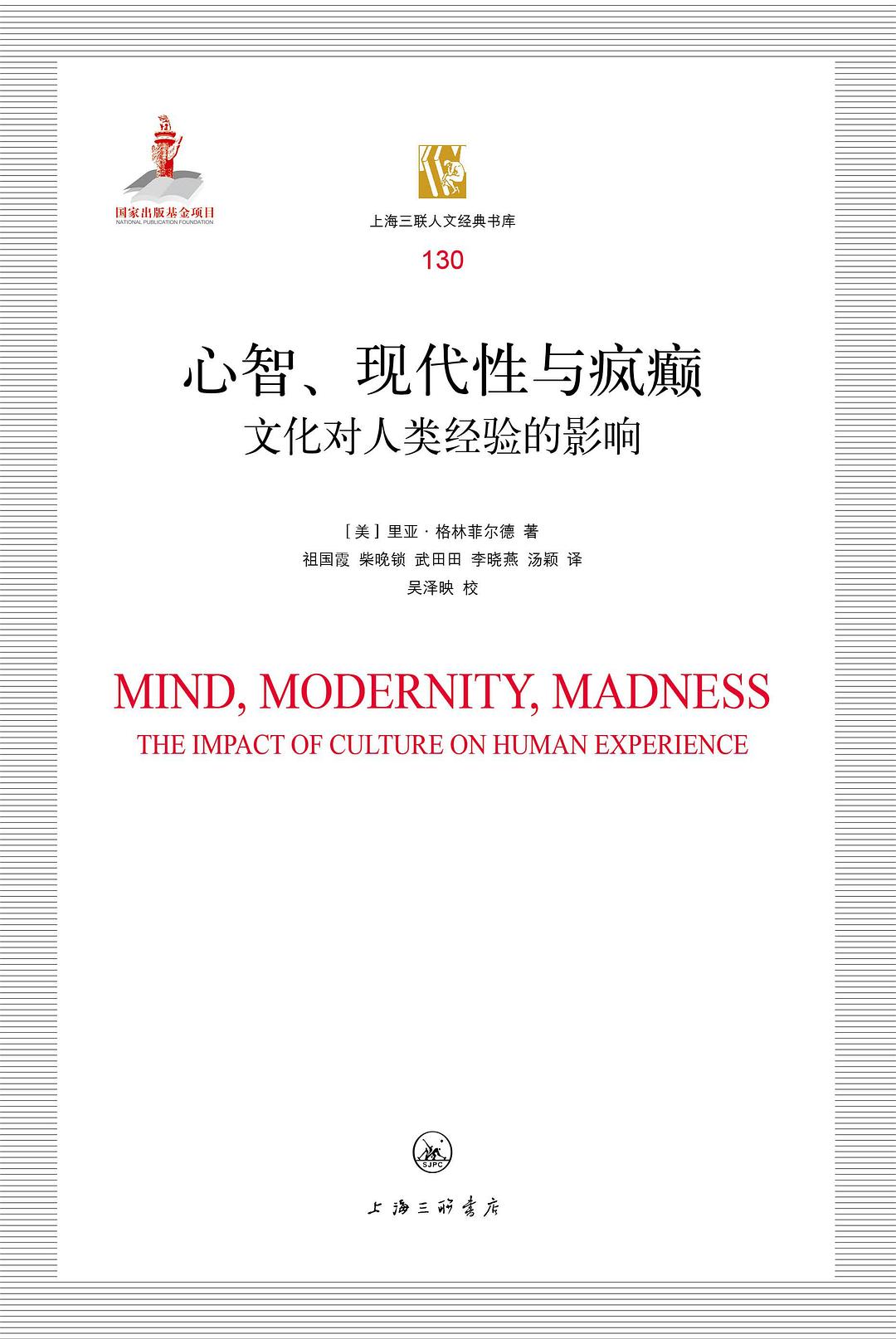
《心智、現代性與瘋癲:文化對人類經驗的影響》,[美] 里亞·格林菲爾德 著,祖國霞、柴晚鎖、武田田、李曉燕、湯穎 譯,吳澤映 校,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1月出版
(本文選摘自《心智、現代性與瘋癲:文化對人類經驗的影響》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