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金光耀 王建朗︱我們的學業和人生導師——《余子道文集》序

從左至右:王建朗、余子道、金光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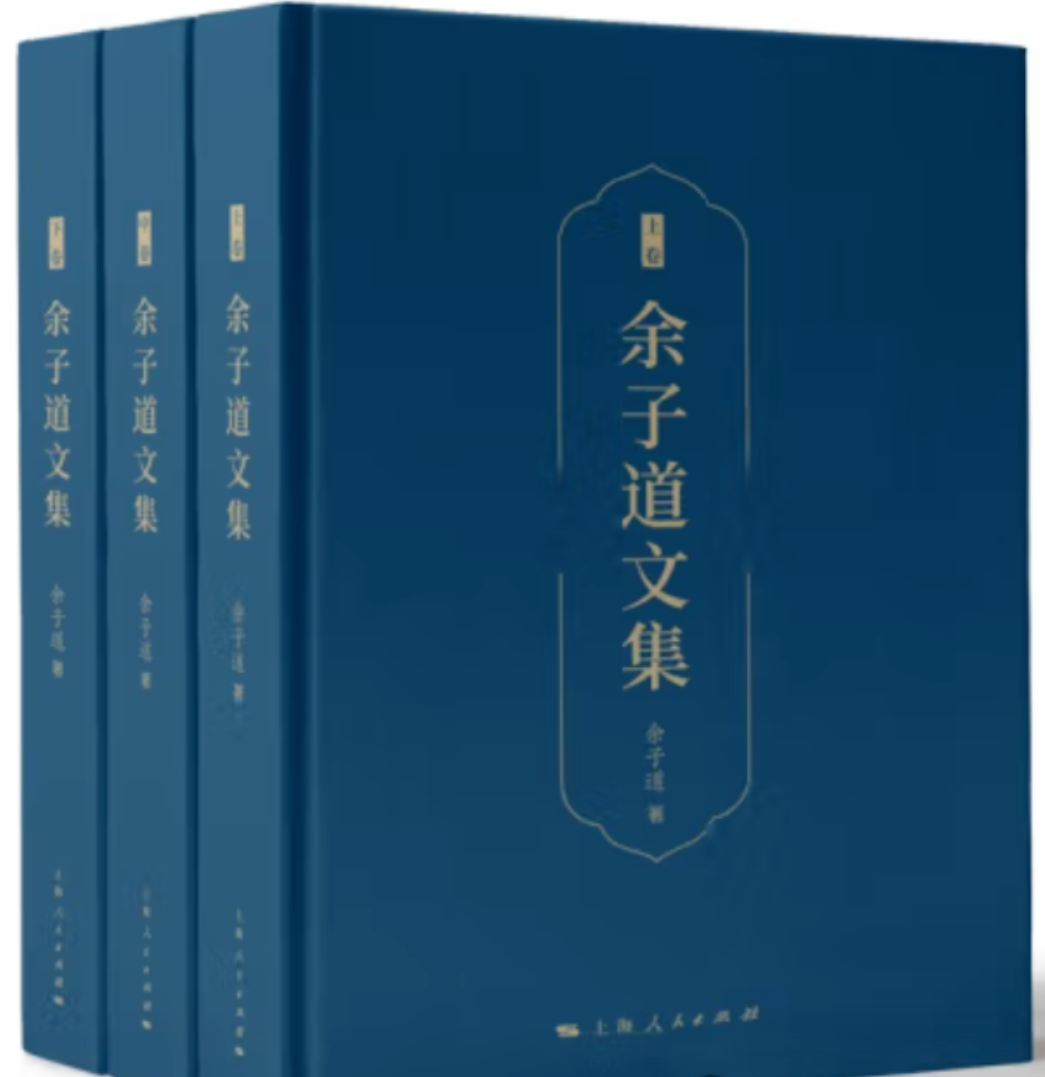
《余子道文集》,余子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
匯集了余子道老師近百篇文章的文集歷經多年選編終于要付梓出版了,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余師希望我們為文集寫一個序言。初聞此言,作為學生的我們感到頗有些為難。序言通常是由師長或者平輩朋友來寫,晚輩學生似乎是不合適寫序的。但對于94歲高齡仍在伏案寫作的余師,不要說前輩,即使平輩中合適寫序的人也無法來寫了。我們是余師最早的碩士研究生,已年屆古稀或已過古稀。這樣一想,學生為老師寫序似乎并無什么不妥,而是理所當然地報答師恩的一種方式。
我們是1983年投入余師門下的。那時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學科分近代史和現代史兩個教研室,我們是中國現代史第一屆研究生。在第一學期中國近代史的課程后,余師在第二學期給我們開了中國現代史專題和馬列經典作家論現代中國兩門課。后一門課是閱讀和討論經典作家論現代中國和世界的原著,其中有列寧論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文章。前一門課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按專題講授現代史。這門課主要由余師講授,但五四運動這個專題他請了新聞系的李龍牧教授,并特別強調李龍牧教授對此問題有精深的研究。在讀期間,余師還請民國史專家李新教授來給我們講了幾次專題課。我們的中國近現代史基礎就是通過這些課程打下的。
余師的中國現代史專題課雖是實行學位制度后給首屆碩士研究生開設的,但講課內容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準備和積累,那就是他在1962年開設的中國現代政治史專題的本科生專門化課程。那時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以1919年為界。復旦歷史系的中國近代史課是由胡繩武和金沖及兩位先生于1953年開創并講授的,中國現代史課開設稍晚。1956年胡繩武先生將余子道老師從中國革命史教研組調入歷史系承擔中國現代史課程,成為這門課程的開創者。
余師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首批考入復旦大學的本科生,先讀商學院國際貿易系,后在國文課老師陳子展先生鼓勵下轉讀新聞系。1952年8月,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因國家建設需要與四年級學生一同畢業,所有學生除三個人外全部去了北京新華社。余師是留校的三人之一,被安排在剛成立不久的新民主主義論教研組,是復旦大學第一批專任政治理論課教師。一個月后,余師就與其他五名年輕助教走上講臺講授《新民主主義論》這門課。按復旦傳統,助教是不能獨立上主課的,只能上輔導課,所以六大助教上講臺授課成為當時校園中的一件大事。上了兩個學期的課后,余師被復旦選派到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進修。這個研究班是根據中宣部和高教部指示開辦的,任務是培養全國高校的政治課教師。余師在研究班的中國革命史組,主講教師是何干之,還有李新和彭明。因此,余師是共和國培養的第一代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者,研究班的學習使他明確了畢生的研究方面。兩年研究班學習結束后,余師回到復旦,不久就調入歷史系,開始了他在復旦歷史系幾十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
余師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與教學是同時進行,相輔相成的。收在文集中時間最早的一篇論文《孫中山與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1956年發表的,正是余師調入歷史系開始講授中國現代史那年。文集中時間最晚的論文是2021年發表的《九一八事變與亞太地區國際關系的重大變動》。兩篇論文前后時間跨度65年,余師學術創作時間之長,學術生命之旺盛,令學生感佩和敬仰!
從文集最后所附余師論著目錄的論文發表時間來看,“文革”前發表5篇,1979年至1991年退休發表33篇,退休后至2023年發表101篇。這組數據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余師這一代學者所經歷的時代和余師在學術道路上艱辛求索的足跡。“文革”前,隨著學術界的政治批判不斷升級,正常的學術研究越來越難以開展,尤其在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段,學術討論的余地不多。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現代史研究成果寥寥是學界的普遍現象。對余師來說,相比一般的教學研究人員,還多了一份辛勞,他是校園里“雙肩挑”的中層干部。來到歷史系后,他參與黨總支的工作,1959年后更是長期擔任系黨總支書記。在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的年代,這一職務占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更難于安心從事學術研究。論著目錄中“文革”期間沒有一篇論文,但有一本合著的《日本軍國主義史》。這一時期,余師負責集體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的工作,“文革”結束后這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他造成了很大壓力。上世紀八十年代,余師發表了多篇軍事史和抗戰史的論文,有的還引發了海峽兩岸學者的學術爭鳴,進入了學術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這種現象在余師那一代學者中十分普遍,原因就在于時代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在同代學者中更為突出的是,1991年退休后,余師老當益壯,心無旁騖地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之中,迎來學術創作的又一個高峰期。其實,這一時期超過一百篇的論文還不足以說明余師對學術研究尤其是抗戰史研究所做的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上海市宣傳主管部門找到余師,希望余師為上海紀念抗戰勝利出點主意做些事情。抗戰研究尤其是上海的兩次淞滬抗戰是余師花費了很大精力研究的領域。余師不僅為上海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做了許多實事,更是抓住這一機遇,切切實實推進上海抗戰史的研究。余師主編的《淞滬抗戰史料叢書》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出版,此后又陸續出版該叢書續編1—4編,整套叢書共65卷,為上海抗戰史研究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史料基礎。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也在余師親力親為的指導下成為一個受到專業人士好評和普通觀眾喜愛的博物館。
余師從事學術研究時間超過一個花甲,研究時段主要集中于以往所稱的中國現代史,即從五四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的歷史,研究領域涉及甚廣,按文集的編排共有八個方面。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戰史是文集的第一個專題,也是余師研究初期最下功夫的領域。余師進入人大研究班進修時,《毛澤東選集》前三卷剛出版不久,《毛選》為他們這一代學者學習和理解中國近現代史提供了基本框架、理論觀點和敘事方式,他們也將學習《毛選》作為提升自身理論和專業素養的基本功,因此在認真學習《毛選》的基礎上闡釋毛澤東思想成為這一代學者普遍熱心的課題。余師在毛澤東思想中專注于軍事思想,與其早年參加革命的經歷相關。1949年春,余師離開就讀的杭州新群高中,到諸暨參加浙東人民解放軍,然后隨部隊進駐寧波參加接管,成為軍管會公安部工作人員。在我們看來,這段參加軍事斗爭的經歷雖然短暫,卻是余師研究軍事史的重要動因。余師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著眼于闡明其對革命戰爭的成功指導及其是中共軍隊勝利的根本保證。而在同時代學者中更顯出自己特點的是,從哲學層面來討論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余師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興趣還進一步延伸至民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蔡鍔、蔣百里和楊杰等,對他們幾部軍事名著中的戰爭觀念、軍事理論、國防戰略、建軍方針等進行梳理和分析,闡發他們在中國現代軍事史上的意義。因此,余師對軍事思想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而是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中國現代軍事思想的面貌,這是對學界的一個貢獻。
抗日戰爭史研究是余師著力深耕的主要領域,他在抗戰史研究的諸多方面都做出了創新性的貢獻。余師在國內較早提出中國“十四年抗戰”這一歷史概念。1991年,他在《抗日戰爭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局部抗戰綜論》一文,系統梳理了中國局部抗戰的發展過程,闡述了局部抗戰和全國抗戰的關系,指出這兩個階段的抗戰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十四年抗戰史。中國的局部抗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他提出“應給局部抗戰應有的地位”。
余師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戰略研究亦多有貢獻。長久以來,學界較多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略,而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戰略缺少研究。改革開放之初,余師即注意到這一問題,深入研究了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略——“持久消耗戰略”,指出這一戰略在全面抗戰爆發前便已提出,它是集守勢消耗與攻勢消耗于一體的持久消耗。這是大陸學界較早做出的有關國民政府抗日戰略的客觀的科學的研究。對于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的戰略作戰方向,余師也提出了他的獨到見解。臺灣學界長期流行的觀點認為,蔣介石發起淞滬會戰的意圖是引誘日軍改變戰略作戰方向,即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這一改變奠定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基礎。余師是第一個對此提出質疑的大陸學者,他以翔實的研究指出華東成為主戰場是在多種因素作用下在會戰中逐漸形成的,會戰之始便有改變戰略作戰方向說法是事后之美化,是“近乎理想化的推測”,缺乏史實根據。這一質疑引發了一場兩岸學者參與的學術爭鳴,推動了對正面戰場戰略研究的深入。
余師對抗戰時期的若干重大戰役和重大事件進行了具體研究,其中,對淞滬抗戰的戰略戰術、作戰過程及上海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著力尤深,先后發表了數十篇多有創見的重要論文,洋洋灑灑百萬言之多的《上海抗戰史》也即將脫稿。余師可當之無愧地稱為上海抗戰史研究第一人。
對抗戰時期汪偽政權史的研究,是余師有關抗戰研究的另一重要領域。余師與復旦歷史系諸位老師組成的汪偽政權研究團隊是公認的這一領域最強有力的研究團隊。他們先后出版了《汪偽政權全史》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影響的專著和論文,復旦大學因此成為汪偽政權研究的學術重鎮。
前面提到,余師是一個在大學校園中“雙肩挑”的中層干部,教學科研之外,還擔負著黨政管理工作,因此對歷史系和學校工作有切身的了解和感受,而他又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幾十年后仍清晰地記得許多珍貴的歷史細節。文集中列有一個專題,記敘了余師眼中的復旦往事。蔡尚思和周予同是復旦歷史系兩位卓有聲望的教授,余師記敘了與他們的密切交往。其中對于周予同先生在皖北參加土改的回憶,不僅是關于周予同生平的重要資料,也是高校師生參加土改的第一手記錄,對研究這段歷史具有很高的價值。王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十年間復旦大學黨政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集中寫王零與復旦師資隊伍建設的一篇,記敘了復旦培養骨干教師、青年教師的情況,其中“青老年掛鉤”、“預備教師”等做法不僅是復旦校史乃至高等教育史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對今天的高校管理者也有現實意義。1979年余師負責學校黨委宣傳部時,代表學校與校學生會主辦的《大學生》雜志有直接聯系。這本雜志當年在全國高校和社會上影響很大,但只刊印了短短的兩期。余師對此的回憶是改革開放初期復旦校園內領導作風開明學生思想開放的生動寫照。文集中這一專題的文章只收入6篇,其實余師寫的相關文章不止這些。而在他記憶中還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來不及寫出來或講出來,或者已經講出來了還在整理之中。
收集在這部文集中時間最晚的一篇文章是2021年的,那一年余師正好90周歲,但那遠不是他的封筆之作。鮐背之年的余師還在愉快地工作著。這些天一部一百多萬字的由他主編的《上海抗戰史》書稿在他的案頭,正進行著最后的修改定稿,要在2025年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時刊行。從立志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算起,余師的研究已超過了70年,而且還在延續。這為我們學生輩樹立了終身學習的榜樣。
余師不僅是我們的學業導師,也是我們的人生導師。他的正直、他的豁達、他的與人為善,他在順境與逆境中的堅持等高貴品格,潛移默化地熏陶著我們。這是我們在學業之外的另一寶貴收獲,它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為人為學。這份師恩,我們未曾有機會鄭重表達,借此做序之機,我們在這里向余師表達深深的景仰和由衷的感謝。
祝余師健康長壽,學術之樹常青!
(本文系《余子道文集》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