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考試制度讓嚴格的教育要求與家庭溫暖之間很難取得平衡
每隔一周的星期六,我會給參與我研究的一些孩子上英語課。在這一天,我把孩子們分成了不同時間段的兩個小組。我用心制訂課程計劃,讓孩子們更多地參與游戲,盡量減少正式的教學。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成為孩子們的又一個學習負擔,所以我盡量讓大家共度的時光有趣起來。
有一個叫艾比的9歲孩子很喜歡我的活動,她兩個小組都參加了。她來的時候總是表現得很積極,所以當她在7月的一個星期六表現得情緒不佳的時候,我很驚訝。她一到就開始抱怨自己很累,說除了我的課之外她還有兩門英語課要上,還有一大堆暑假作業要做。我試著讓她高興起來,說道:“如果你現在做完了作業,到了8月就可以玩了。”她反駁道:“8月我會有更多事要做!”
幾個月后的一個周末,在中秋節的晚餐后,我去看望艾比和她的父母,這才對她抱怨的原因有了更多了解。艾比的父母一直在解釋說,盡管夫妻二人在育兒上相互協作,但在特長班這個問題上兩人持有不同看法。艾比的媽媽說道:“她爸爸覺得沒必要去上那么多特長班。但我感覺,孩子之所以今天這么優秀,和上這些特長班有關系。”
艾比估摸著,在她9年的人生中,她肯定至少已經上了12種不同的課程。她嘗試為我列出這些課程,不過馬上就把手往空中一甩,說:“我自己都記不清了!”
隨后艾比的爸爸開口了:“我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我覺得在學習特長方面,就像專家說的,要按孩子的興趣來,不要強行給他們增加負擔。專家說孩子的天真單純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創造一個輕松的環境,對她的身心健康有益,就已經很好了。可能她也沒辦法一下子吸收這么多特長班的內容。”
艾比的媽媽為自己辯護說,這些課程就是根據艾比的興趣來選的。她讓我問艾比之前那個周末發生了什么。看來艾比還記得那天的情形,她知道我說的是哪個周末。
“你那天怎么了?”媽媽要艾比說。
“那天的前一天是星期五,對嗎?星期五晚上我去上了英語課。第二天早上我去上了書法班!然后下午我去上了你的課!”
媽媽很驚訝地問她:“你把去關老師那兒當成上課?”
“對。我確實把它當成上課!”
“但你不是說你很喜歡關老師教的嗎?”
“對啊!但關老師教的單詞我必須全都背下來!我一回家你就考我!我答不上來你就罵我!你會說,”艾比開始模仿媽媽,“‘哎呀!她都不收費了,你還不當回事!我再也不讓你去了。’”
這番話自然讓艾比的媽媽頗為尷尬,房間里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但這一刻也很能說明問題。我其實一直因為自己也成了孩子們的課外班負擔而深感內疚,但同時,我也確實為了讓家長開心時不時地教孩子們一些新單詞。我完全不知道艾比會在家被考這些單詞。

艾比的媽媽趙海華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女性,她相信與女兒保持友誼很重要。她試著遵循專家的建議來提升女兒的主體性。例如,她曾給我講過她把女兒從“小飯桌”小組里接走的故事(“小飯桌”是有人照看的孩子們的午餐小組,是學校老師為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支付額外費用的忙碌父母開設的)。“小飯桌”的老師總是抱怨其他孩子模仿艾比的一舉一動。如果她吃了兩碗飯,其他孩子也會吃兩碗飯。趙海華說,艾比的老師普遍不喜歡艾比有個性這件事。盡管趙海華無法消弭學校文化與女兒個性之間的沖突,但她至少能把艾比從“小飯桌”接走,保護她的個性不被“磨平”。
趙海華總是自豪地談起自己與女兒的親密無間和母女情深,然而,中國考試制度的邏輯妨礙了她成為友好家長的努力。要想在嚴格的教育體制提出的要求與營造家庭“溫暖”(用趙海華的話來說)之間取得平衡總是很棘手的問題。
盡管改革倡導者和政策制定者力圖改變應試教育體制,但考試的地位依然穩固,每個人的未來就取決于高考和中考的表現。考試在中國兒童及家庭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縱然中國的中產父母想按照專家建議去做,但隨著孩子年齡增長、越來越臨近關鍵的入學考試,確保學業生存的壓力變得越來越大。
以市為單位的中考決定了學生在國家規定的九年義務教育之后能否繼續就讀高中,以及就讀什么樣的高中(普通高中還是職業技術高中)。全國性的高考決定了學生最終將進入什么樣的學院或大學(學術型還是職業技術型,“211”還是非“211”高校),以及選擇什么樣的專業。鑒于這兩場考試事關重大,家長們認為就讀合適的初中極其重要,因為這是學生準備中考的階段,而中考之后則是學生準備高考的階段。爭取進入一所好名聲的學校不只是執迷于社會地位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出于實際考量——確保有效的教學方法以及(對一部分人而言)確保孩子能有一定的生活質量。既然所有學生都參加同樣的標準化入學考試,那么那些過度依賴復習課、布置大量家庭作業卻又沒有高升學率的學校便不受青睞。相比之下,在聲譽好的學校,有能力的老師會用聰明的方法緩和學習強度。
在昆明,我結識的大多數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云南大學附屬初中,該校的高中升學率每年都排名第一。這所初中聲譽極佳,以至于人們常開玩笑說,云南大學才是這所初中的附屬學校。作為一所民辦學校,它向非大學教職工家庭每年收取7000元人民幣,三年下來的教育費用共21000元。該校的入學選拔考試由語文和數學兩個科目組成。根據《義務教育法》,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兒童都有權接受免費教育,在所在地的學校免試入學。但昆明的許多家長愿意“擇校”,即在指定片區外找學校上。雖然21000元對普通的雙薪家庭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但家長們都爭著把孩子送進云大附中。我結識的一個家庭決定不把女兒送去這所學校(盡管她被錄取了),原因是每天的通勤時間太長。他們最后對這個決定頗為后悔,因為女兒如今淹沒在海量的作業中,而且通過云大附中的入學選拔考試也實屬不易。
學生通過在校學習做好準備參加標準化入學考試,這些考試強度很高,要在三天時間里測試學生三年來的多學科知識積累。學生必須學習掌握和死記硬背下來的材料(無論是幾千年的史實和數字,還是無窮無盡的數學題——它們有些可能會出現在考試中,有些則不會)之多,對不在這個體制里長大的人來說簡直難以想象。很常見的情況是,學校會用整個學期的時間來復習而不上新課,因為學生有太多內容要記憶。
當代考試制度植根于唐朝開始的帝國官員選拔制度——科舉。這是一種全帝國范圍內實行的標準化、擇優錄取的政府官員選拔機制。沒有什么比金榜題名、晉升士紳階層更榮耀的事了。參加科舉的考生必須背下四十多萬字的內容才能掌握包括儒家經典在內的諸門課程,同時他們也會求助神靈并使用占卜手段來應對壓力(艾爾曼[Benjamin Elman] 1991)(2000)。時至今日,訴諸迷信依然常見,足以體現標準化考試帶來的焦慮和不確定:父母會在當地寺廟敬神,還會用“聰”和“算”的同音字食材(即蔥和蒜)做飯。同時,學生會避免攝入任何不吉利同音字的食物或飲品,他們甚至會避免理發,以免“從頭開始”。我認識的一個女生還會穿紅內衣來求好運,這是她媽媽的主意。
高考出了名的折磨人,它是一種將學生推向人類忍耐極限的制度(任柯安 2011)。中考同樣會帶來焦慮,因為不同于高考(理論上一個人可以多次參加高考,直到考出滿意的分數),學生只能參加一次中考。以2007年為例,中考一共包含六個科目:語文、物理、數學、政治/思想品德、英語和化學。總分是660分,根據預測,昆明重點高中的分數線在600分左右。參加考試后,考生需要在不知道自己分數的情況下,根據模擬測試的結果和往年各高中的分數線(分數線每年都會按照報考總人數和整體成績的不同發生變化)進行估分,填報志愿。因此,入學考試都包含填報志愿這一額外工作,它需要有權衡各種因素和預測結果的能力。理想狀態下,填報的志愿應與模擬考成績相匹配,因為那些你可能考得上但在志愿中排名靠后的學校,可能不會接收你。
就中考而言,考試成績高于學校分數線的可以作為公費生入學。而低于學校分數線10分的可以選擇以擇校生的身份入學,實際名額視指標而定。和在劃定片區外上初中一樣,擇校生上高中的費用也很高。(這樣的學生有時也稱為自費生。)我沒能核實到具體的費用,但我多次聽到和讀到,擇校生需要為低于分數線的每一分支付1萬元。
擇校現象很普遍,這首先是因為人們對優質教育意愿強烈。好學校設置了很高的錄取分數線,要求未通過的學生支付額外費用。其次,即使在同一個城市,學校之間的教學質量也參差不齊,所以盡管就讀劃片之外的學校要支付高昂費用,大家還是爭著送孩子去更好的學校。這第二個因素與高收入社區還是低收入社區關系不大,而與中國的具體教育政策有關。好學校能將擇校帶來的收入投入其發展之中,與其他收入一道,服務于改善基礎設施、招募一流教學人員,以完成學校知名度和地位的再生產。學校的發展又反過來強化了學校的教育資源,讓高收費和低錄取率更顯合情合理。
支持擇校的人認為這是一種亟須的市場機制,能讓籌資渠道多樣化,公眾和個人皆從中受益。他們認為,擇校現象只不過反映了大眾對優質學校教育的渴望,這種渴望通過市場體制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滿足,同時也彌補了國家資金的不足(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工作委員會 2005)。擇校的批評者則指出,擇校違反了教育公平原則,加劇了學校之間既存的差距,助長了腐敗,還給民眾帶來了過重的經濟負擔(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工作委員會2005;楊東平[2004]2006)。由于往往需要支付擇校費才能把孩子送進理想的學校,家庭因而倍感壓力,不得不利用手頭的一切資源。由于入學考試成績與要不要支付數萬元額外費用直接相關,學生因而心理壓力倍增,必須刻苦學習。由于評估學校和老師根據的是學生的升學率,提供教育因而變成了狹隘的“應試教育”。
以應試為中心的教育體制帶來的一個意外后果在于,學校和老師傾向于關注有前途的學生,而“歧視”其他學生——不公正地對待他們,讓他們留堂、停課,開除他們(Man Qimin[1996]1997)。這類歧視現象在享有盛名的精英重點中學尤為突出,不過它早在小學就開始了。我常聽到這樣的故事:有孩子被施壓或被要求離開學校,有家長因孩子與小學主科老師有矛盾而將孩子轉校。對學生而言,一種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就是老師不再關注他們了,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教師承受的壓力和面臨的競爭。在昆明,從小學到中學,班級規模都相當龐大。老師要引導足足50-70名學生邁向成功,這讓老師也感到負擔沉重,對學生的越軌行為沒什么耐心。
我之所以強調擇校問題,是因為在家長看來,正是擇校這一中國應試教育的具體表現,成為他們面臨的最緊迫的道德問題和實際問題。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過上好日子,這意味著確保他們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成為受人尊敬的人。為了能讓孩子找到好工作,家長必須確保他們踏上通向好大學的道路、取得有分量的學位。為了讓孩子踏上正確的道路,家長必須通過補習班和日常監督來提高孩子的應試能力,同時想辦法負擔進入好學校的費用。如果孩子與老師發生沖突或產生誤解,家長必須要么幫孩子重獲老師的好感,要么尋找新學校,因為在普通家長看來,與老師的關系好壞能決定學業的成敗。
放眼全球,焦慮是中產的內在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須通過教育成就來確保中產身份地位(克雷默-薩德利克[Tamar Kremer-Sadlik]和古鐵雷斯[Kris Gutiérrez] 2013)。和美國中產階級母親一樣(盡管課堂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國中產母親也積極干預和學校有關的不利狀況(拉魯 2011)。在中國,考進好學校的熱潮也與艾利森·皮尤在加州灣區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發現的“鋪路消費”(Pathway Consumption)相類似。“鋪路消費”是為了創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軌跡的機會,以及確保“舒適”的學習環境(2009)。因此,從比較視角來看,中國中產父母的強烈焦慮并不是完全獨有的現象。全球經濟鼓勵個體“將自己視為可資管理和發展的人力資本投資組合”(安德訓 2013),并期望個體和家庭能吸收系統性矛盾的“沖擊”(15)。各國的就業市場十分不穩定,畢業生失業的陰影籠罩著許多國家。通過對教育投入金錢和精力來投資人力資本的做法雖然不能保證回報,但至少是中產家庭掌控之內的事。
本文摘自《不確定的愛: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后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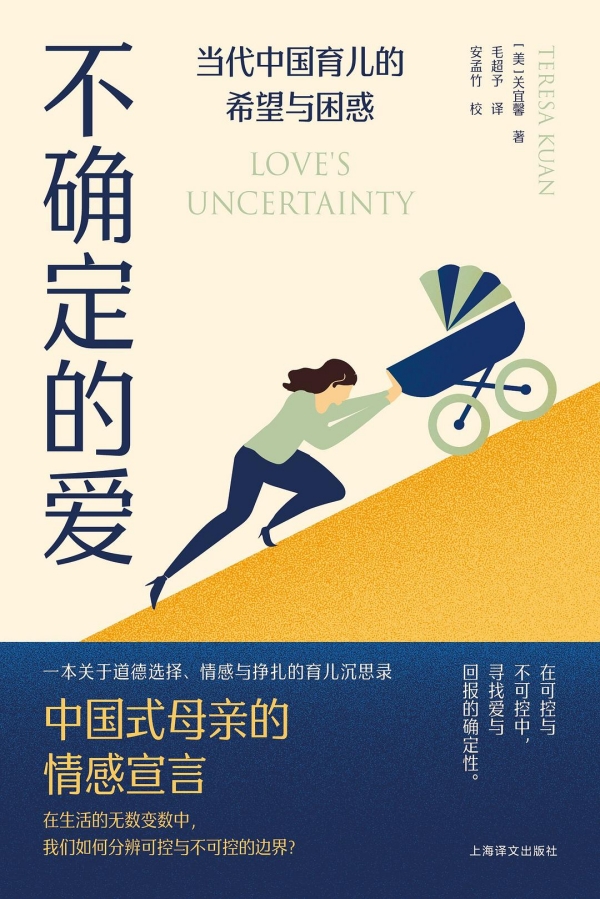
《不確定的愛: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美】關宜馨/著 毛超予/譯 安孟竹/校,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1月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