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必須優(yōu)秀”與“活著就好”之間:我們如何接住這一代崩潰的青少年?|翻翻書·送書

“我”在一家大醫(yī)院的精神科病房見到小珍時,她正因“壓力太大”接受治療。
作為母親,陳佳玲對女兒小珍的愛毋庸置疑。但也正是這份愛讓她不愿看到女兒在殘酷的社會競爭中落敗。于是,小珍的日程表被五花八門的課外輔導班填滿。然而,隨著女兒精神痛苦加劇并最終開始住院服藥,陷入深刻自我反思的陳佳玲又不得不掉頭去呵護女兒脆弱的心靈。沉重的城市生活壓力、嚴格的學校紀律以及激烈的社會競爭體系共同造就了這樣一對充滿矛盾的母女關系。
這個故事并非個例。在現實生活中,陳佳玲像是21世紀初中國城市父母的縮影,折射出中國式育兒正在經歷的集體性陣痛。對小珍這一代人來說,從中學到大學,每一個暫時安全的彼岸都變成了新一輪競賽的起點。社會生存的壓力與痛苦也不斷從成年人的生活向兒童的世界下沉。快樂的童年與有保障的未來之間似乎變得越發(fā)不可兼容。
當“教育競賽”的宏大敘事投影在孩子書桌的臺燈下,那些在補習班與游樂場之間走鋼索的父母,到底該如何尋得平衡?“虎媽”“雞娃”“內卷”“躺平”等現象背后,被教育內卷所異化的親子關系又是否有另一條出路?
人類學學者關宜馨決定推開一扇觀察之窗。在春城昆明的市井煙火里,這位人類學者通過多年的田野調查,與這座城市中的十多戶中產家庭結成了超越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關系的長期友誼,她走進課堂、家庭與心理咨詢室,見證了普通中國父母的育兒困境,并最終推出了《不確定的愛》這本書。
在《不確定的愛》一書中,關宜馨通過一系列真實的故事,探討了當代中國城市中產父母在育兒上的希望與困惑,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在生活無數的意外事件中,辨識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可以控制的。
第四十期「翻翻書·寫寫字」的征集就為大家?guī)磉@部教育民族志方面的著作《不確定的愛》,讓我們在二十年外界環(huán)境變化背景下,去看普通中國家庭中的變與不變。
以下內容摘自《不確定的愛》,編輯過程中略有刪減,經出品方授權發(fā)布。
(參與贈書活動可直接滑至底部,2月24日當天我們會選出3名讀者,請留意公眾號文章的回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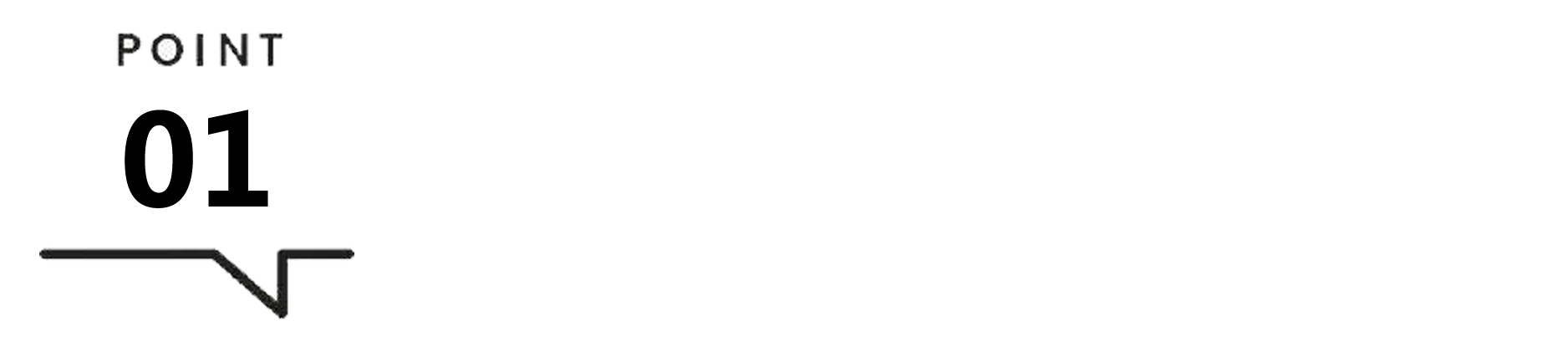
普通人的養(yǎng)育兵法
2004年,我讀初中,離升學考試還有兩年,正是人生中最無憂無慮的時光。每天最期待的是下午最后一節(jié)課的下課鈴,鈴聲一響,無論講臺上的老師還在說什么,心就飛出了教室外,飛向街邊的小吃和報刊亭里的《歌迷大世界》、音像店里的周杰倫和蔡依林。我就讀的中學位于一條商業(yè)街的中央,老師和家長們總憂心這樣的環(huán)境“太過復雜”;精力旺盛的中學生們卻只想著,放學后能把丑丑的校服塞進書包在街上游蕩。
彼時的我們對全球化、市場經濟時代的生存壓力還懵然無知,提前焦慮起來的總是父母。雖然全國教育系統(tǒng)都在倡導“減負”,但擋不住教培機構遍地開花;周六日、寒暑假,平時一起玩的朋友們漸漸有了另外的去處,奧數班、英語班、鋼琴班、游泳班……下學期再見,有人在開化學課之前就背好了元素周期表,有人已經會在英語作文里用虛擬語態(tài),一點一滴地走在了大家前面。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媽的閱讀興趣好像也發(fā)生了變化,家里的書櫥開始擺放各種“養(yǎng)育秘籍”,其中就包括當年聲名大噪的《哈佛女孩劉亦婷》。與如今劍指“清北復交、哈耶牛劍”的海淀媽媽們不同,當年在我生活的東部小城,像我媽一樣的母親們懷揣的是從前科學育兒的時代走來的惴惴不安。報紙雜志上鋪天蓋地的親子寓言讓她們意識到,“不打不成器”再也不是通用的教養(yǎng)法則,今天的“好媽媽”要謙卑地學習如何與我們這代獨生子女相處。然而她們也明白,自己經歷的那個“畢業(yè)包分配”的時代已成歷史,成長于千禧年的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優(yōu)勝劣汰”的社會。身為家長的責任感無法讓她們對下一代“放任自流”。
2004年也是本書作者關宜馨來到西南的省會城市昆明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的第一年。在那里,她發(fā)現了一個時至今日依然困擾著中國都市家庭的悖謬:在一個充滿不安全感的社會里,快樂的童年與有保障的未來之間似乎變得越發(fā)不可兼容。讓她看見這種悖謬的不只是“痛苦的孩子”,還有常常陷入情感掙扎的母親。
陳佳玲就是這樣一位母親。她愛女兒小珍,不希望女兒在可預見的殘酷競爭中落敗,但只能以另一種“殘酷”的方式去鞭策年幼的孩子。她用五花八門的課外輔導塞滿小珍的日程表,用嚴格的監(jiān)管為女兒的人生把關。但隨著小珍精神痛苦的加劇、開始住院服藥,陷入深刻自我反思的陳佳玲又不得不掉頭回去呵護女兒脆弱的心靈。陳佳玲充滿矛盾的形象是21世紀初中國城市父母的縮影,她的進退失據也折射出中國教育改革藍圖的內在張力。
現代國家的兒童養(yǎng)育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私人問題,中國亦不例外。早在中國現代化的肇始之端,知識分子們就認定“教育”這件事攸關民族生死存亡。但好的教育究竟意味著什么?問題的答案也在百年來隨著戰(zhàn)爭、革命和經濟模式的轉型而不斷變化。1980年代,關于“現代化”的大討論成為執(zhí)政者與知識界共同的關切,“人的現代化”便是其中一個核心論題。用人類學的術語講,所謂“人的現代化”,指向的是一項主體性塑造的工程。隨著中國越發(fā)卷入世界經濟體系,這項工程有了更加明確的指向——即培養(yǎng)未來能夠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高素質”勞動力。教育改革的倡導者們期待,下一代人口的素質的提升,能夠助力國家的發(fā)展模式從依賴廉價勞動力向“知識經濟”轉型。
這樣的宏觀政治議程如何與家庭教育的日常聯(lián)結起來?關宜馨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2000年代初的大眾傳媒和出版市場。在當年占據暢銷書排行榜的流行育兒指南里,死記硬背、照本宣科的中式教育常常被斥為“填鴨”,鼓勵孩子盡可能發(fā)揮想象力的美式課堂則被構建為理想的他者。有跨國生活經驗的專家們指出,美國的教育看似混亂松散、缺少指導,卻構成了孕育“創(chuàng)造力”的土壤,后者正是21世紀人才的核心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課堂、家庭與市場,兒童有待開發(fā)的生命潛能與改革時代亟需釋放的經濟潛能形成了某種呼應:如果在市場經濟之下,政府應該通過減少行政干預、提供制度支持促進民間經濟活力的釋放,那么教育者和家長們該如何為促進孩子的潛能開發(fā)培育合適的苗床?
當童年開始成為一個人力資本積累的“預備階段”,中國式家長、中國式養(yǎng)育,也開始遭受全面檢討。坊間流傳的育兒故事總是發(fā)人深省:工薪家庭出身的殘障女孩周婷為何能遠赴美國求學,達成讓普通人艷羨的成就?品學兼優(yōu)的徐力何以做出“錘子殺母”的暴行、承受半生牢獄之災?這些或鼓舞人心、或觸目驚心的故事為千禧年的家長們留下了養(yǎng)育的醒世恒言,也為困擾著整個民族發(fā)展的教育之問提供了間接的診斷——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孩子的天資、品性,而是父母有沒有給他們提供合宜的成長空間。如果國家的現代化工程依賴于高素質的下一代,那么這一人口治理的目標,最終要靠中國家長們對“養(yǎng)育方式”的改造來實現。這些蘊藏著社會轉型寓言的育兒故事提醒人們看到,所謂兒童主體性的培育,實際上是靠家長主體性的重塑實現的。
隨著中國父母對養(yǎng)育方式的改造被納入到世紀之交“民族振興”的敘事之中,作為養(yǎng)育者和照料者,他們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調和這一工程的內在矛盾。這個尷尬的位置給中國家長們帶來了新的困境。他們當然想遵循教育專家的建議、對表現不佳的孩子也施以“賞識”和“耐心”,讓他們在陽光樂觀的氛圍中成長,然而殘酷的競爭規(guī)則面前,他們卻也時常徘徊不定、情難自禁。家庭里,深陷情感沖突的總是母親——身兼家庭內外“雙重負擔”的她們被養(yǎng)育文本刻畫成情緒化的存在。但真正讓她們左右為難的是現實中的“不可通約之善”(incommensurable goods):她們清楚對孩子“發(fā)火”會讓他們備受打擊,可小事上的放縱(完不成作業(yè))有可能釀成大的危機(被老師放棄、同學排斥),甚至讓他們面臨被教育篩選淘汰的風險。這樣的內在情感沖突不只是性別化育兒分工的副產品,它也在道德的層面提醒著我們,在中國做個好母親遠非輕而易舉之事,而是一場隨時隨地需要權衡、掙扎、選擇的斗爭。
誠然,孩子的成長充滿了不確定性,漫漫人生的幸福終究非家長可以一力確保。但為孩子的未來而奮斗的養(yǎng)育投入,對家長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第一人稱問題”——縱使前路變幻莫測,作為父母,究竟什么是我可以控制的?
千禧年的家長們跨越階層的養(yǎng)育共識是竭力為孩子“創(chuàng)造條件”。這樣的“條件”可以是花錢送孩子進鋼琴班、舞蹈班,陪著孩子學《新概念英語》,也可以是為了躲避不良同儕環(huán)境的影響而搬家,動用人脈幫孩子發(fā)表作文以博得老師的好感。在一個推崇競爭的社會,“淘汰”、“失敗”是懸在每個孩子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與其說家長們“創(chuàng)造條件”是為了確保孩子“出人頭地”,倒不如說他們的種種舉動是出于一種中國家長內心尤其強烈的緊張與不安。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他們普遍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經歷過“條件”的匱乏,深知手上有牌可打、心中才能安定的道理。畢竟在一條險象環(huán)生的賽道上,一次貌似微小的機會錯失就可能產生難以逆轉的影響,即便他們明白,自己創(chuàng)造的種種“條件”孩子未必能利用起來,但盡力而為只是為了避免可能的遺憾,這是他們至少可以做到的,也是他們至多能夠達成的。
關宜馨書中描繪的媽媽們是我們最熟悉的那種母親。她們有著最瑣碎的考量、最尋常的糾結,她們對孩子的關切有時甚至顯得過于現實、功利,甚至連彼時流行的肥皂劇也不遺余力地展現她們的“庸俗”。與阿德里·庫斯羅(Adrie Kusserow)筆下努力在極為不平等的世界里給孩子營造“平等”體驗的精英父母不同,中國母親們甚至會毫不遮掩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丑陋現實攤開來給孩子看。她們也羨慕作者口中不必在意經濟保障、追求內心認定的意義感的“美式”生活,但這對她們的孩子而言終究是不切實際的奢侈。在龐大的人口規(guī)模與有限的社會資源之間,在過剩的學歷和難以持續(xù)吸收白領勞動力的就業(yè)市場之間,中國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并沒有什么懈怠的余地。流行文化總是不懈地制造各種浪漫的泡沫,當年風靡大街小巷的趙寶剛式青春劇里,心懷理想的年輕人最終總能讓保守的父母屈服妥協(xié),而現實生活中的母親們卻深知,如果她們今天不做些什么,未來威脅到孩子發(fā)展的就是他們將要面對的社會本身。
或許在“投入”這個層面上,關宜馨書中描寫的家長們,和全世界的中產階級父母并沒什么不同,在物質上他們很少對孩子吝嗇,既愿意為了學區(qū)房、營養(yǎng)品、課外輔導、特長培訓花錢,也愿意盡力滿足孩子在追星和零食方面的消費。盡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中產家庭為確保孩子競爭優(yōu)勢的金錢投入要么被赤裸裸地賦予“拜物教”的含義,要么被輕易地斥為“溺愛”獨生子女的表現,但在關宜馨眼中,這樣的付出更接近于艾利森·皮尤(Allison Pugh)所說的“尊嚴經濟”——與其說這一切是在幫孩子進行兒童版本的地位競爭,倒不如說是怕他們在他人面前感到自卑。“拜物教”里固然凝結著“價值注入”的維度,但也蘊含著不容忽視的道德考量;“創(chuàng)造條件”的行動固然包含著功利的企圖,但也映射出普通人如何在難以抵擋的社會歷史洪流中“掌握主動”。
(安孟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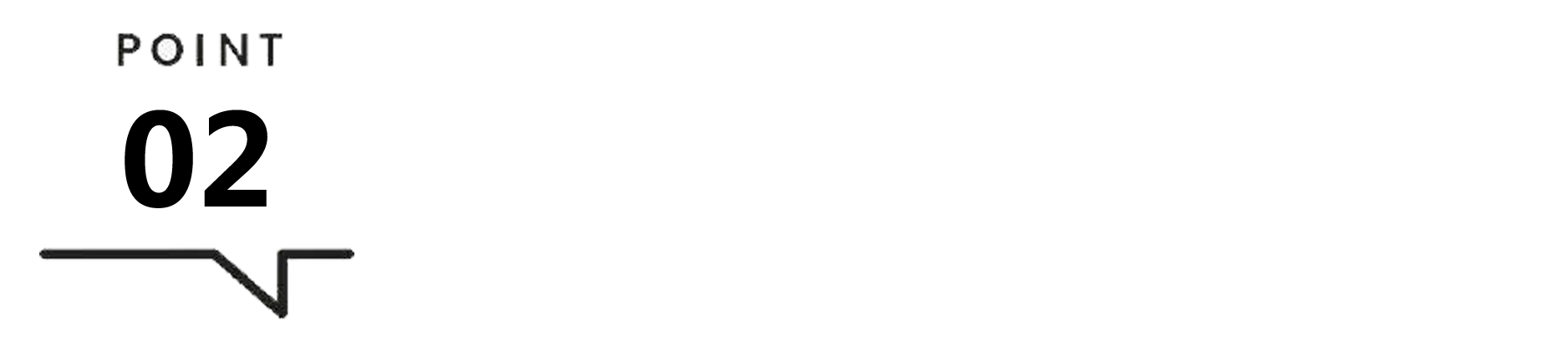
考試制度
每隔一周的星期六,我會給參與我研究的一些孩子上英語課。在這一天,我把孩子們分成了不同時間段的兩個小組。我用心制訂課程計劃,讓孩子們更多地參與游戲,盡量減少正式的教學。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成為孩子們的又一個學習負擔,所以我盡量讓大家共度的時光有趣起來。
有一個叫艾比的9歲孩子很喜歡我的活動,她兩個小組都參加了。她來的時候總是表現得很積極,所以當她在7月的一個星期六表現得情緒不佳的時候,我很驚訝。她一到就開始抱怨自己很累,說除了我的課之外她還有兩門英語課要上,還有一大堆暑假作業(yè)要做。我試著讓她高興起來,說道:“如果你現在做完了作業(yè),到了8月就可以玩了。”她反駁道:“8月我會有更多事要做!”
幾個月后的一個周末,在中秋節(jié)的晚餐后,我去看望艾比和她的父母,這才對她抱怨的原因有了更多了解。艾比的父母一直在解釋說,盡管夫妻二人在育兒上相互協(xié)作,但在特長班這個問題上兩人持有不同看法。艾比的媽媽說道:“她爸爸覺得沒必要去上那么多特長班。但我感覺,孩子之所以今天這么優(yōu)秀,和上這些特長班有關系。”
艾比估摸著,在她9年的人生中,她肯定至少已經上了12種不同的課程。她嘗試為我列出這些課程,不過馬上就把手往空中一甩,說:“我自己都記不清了!”
隨后艾比的爸爸開口了:“我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我覺得在學習特長方面,就像專家說的,要按孩子的興趣來,不要強行給他們增加負擔。專家說孩子的天真單純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創(chuàng)造一個輕松的環(huán)境,對她的身心健康有益,就已經很好了。可能她也沒辦法一下子吸收這么多特長班的內容。”
艾比的媽媽為自己辯護說,這些課程就是根據艾比的興趣來選的。她讓我問艾比之前那個周末發(fā)生了什么。看來艾比還記得那天的情形,她知道我說的是哪個周末。
“你那天怎么了?”媽媽要艾比說。
“那天的前一天是星期五,對嗎?星期五晚上我去上了英語課。第二天早上我去上了書法班!然后下午我去上了你的課!”
媽媽很驚訝地問她:“你把去關老師那兒當成上課?”
“對。我確實把它當成上課!”
“但你不是說你很喜歡關老師教的嗎?”
“對啊! 但關老師教的單詞我必須全都背下來!我一回家你就考我!我答不上來你就罵我!你會說,”艾比開始模仿媽媽,“‘哎呀! 她都不收費了,你還不當回事!我再也不讓你去了。’”
這番話自然讓艾比的媽媽頗為尷尬,房間里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但這一刻也很能說明問題。我其實一直因為自己也成了孩子們的課外班負擔而深感內疚,但同時,我也確實為了讓家長開心時不時地教孩子們一些新單詞。我完全不知道艾比會在家被考這些單詞。
艾比的媽媽趙海華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yè)女性,她相信與女兒保持友誼很重要。她試著遵循專家的建議來提升女兒的主體性。例如,她曾給我講過她把女兒從“小飯桌”小組里接走的故事(“小飯桌”是有人照看的孩子們的午餐小組,是學校老師為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支付額外費用的忙碌父母開設的)。“小飯桌”的老師總是抱怨其他孩子模仿艾比的一舉一動。如果她吃了兩碗飯,其他孩子也會吃兩碗飯。趙海華說,艾比的老師普遍不喜歡艾比有個性這件事。盡管趙海華無法消弭學校文化與女兒個性之間的沖突,但她至少能把艾比從“小飯桌”接走,保護她的個性不被“磨平”。
趙海華總是自豪地談起自己與女兒的親密無間和母女情深,然而,中國考試制度的邏輯妨礙了她成為友好家長的努力。要想在嚴格的教育體制提出的要求與營造家庭“溫暖”(用趙海華的話來說)之間取得平衡總是很棘手的問題。
盡管改革倡導者和政策制定者力圖改變應試教育體制,但考試的地位依然穩(wěn)固,每個人的未來就取決于高考和中考的表現。考試在中國兒童及家庭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縱然中國的中產父母想按照專家建議去做,但隨著孩子年齡增長、越來越臨近關鍵的入學考試,確保學業(yè)生存的壓力變得越來越大。
以市為單位的中考決定了學生在國家規(guī)定的九年義務教育之后能否繼續(xù)就讀高中,以及就讀什么樣的高中(普通高中還是職業(yè)技術高中)。全國性的高考決定了學生最終將進入什么樣的學院或大學(學術型還是職業(yè)技術型,“211”還是非“211”高校),以及選擇什么樣的專業(yè)。鑒于這兩場考試事關重大,家長們認為就讀合適的初中極其重要,因為這是學生準備中考的階段,而中考之后則是學生準備高考的階段。爭取進入一所好名聲的學校不只是執(zhí)迷于社會地位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出于實際考量——確保有效的教學方法以及(對一部分人而言)確保孩子能有一定的生活質量。既然所有學生都參加同樣的標準化入學考試,那么那些過度依賴復習課、布置大量家庭作業(yè)卻又沒有高升學率的學校便不受青睞。相比之下,在聲譽好的學校,有能力的老師會用聰明的方法緩和學習強度。
在昆明,我結識的大多數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云南大學附屬初中,該校的高中升學率每年都排名第一。這所初中聲譽極佳,以至于人們常開玩笑說,云南大學才是這所初中的附屬學校。作為一所民辦學校,它向非大學教職工家庭每年收取7000元人民幣,三年下來的教育費用共21000元。該校的入學選拔考試由語文和數學兩個科目組成。[1]根據《義務教育法》,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兒童都有權接受免費教育,在所在地的學校免試入學。但昆明的許多家長愿意“擇校”,即在指定片區(qū)外找學校上。雖然21000元對普通的雙薪家庭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但家長們都爭著把孩子送進云大附中。我結識的一個家庭決定不把女兒送去這所學校(盡管她被錄取了),原因是每天的通勤時間太長。他們最后對這個決定頗為后悔,因為女兒如今淹沒在海量的作業(yè)中,而且通過云大附中的入學選拔考試也實屬不易。
學生通過在校學習做好準備參加標準化入學考試,這些考試強度很高,要在三天時間里測試學生三年來的多學科知識積累。學生必須學習掌握和死記硬背下來的材料(無論是幾千年的史實和數字,還是無窮無盡的數學題——它們有些可能會出現在考試中,有些則不會)之多,對不在這個體制里長大的人來說簡直難以想象。很常見的情況是,學校會用整個學期的時間來復習而不上新課,因為學生有太多內容要記憶。
當代考試制度植根于唐朝開始的帝國官員選拔制度——科舉。這是一種全帝國范圍內實行的標準化、擇優(yōu)錄取的政府官員選拔機制。沒有什么比金榜題名、晉升士紳階層更榮耀的事了。參加科舉的考生必須背下四十多萬字的內容才能掌握包括儒家經典在內的諸門課程,同時他們也會求助神靈并使用占卜手段來應對壓力(艾爾曼[Benjamin Elman] 1991)16(2000)。時至今日,訴諸迷信依然常見,足以體現標準化考試帶來的焦慮和不確定:父母會在當地寺廟敬神,還會用“聰”和“算”的同音字食材(即蔥和蒜)做飯。同時,學生會避免攝入任何不吉利同音字的食物或飲品,他們甚至會避免理發(fā),以免“從頭開始”。我認識的一個女生還會穿紅內衣來求好運,這是她媽媽的主意。
高考出了名的折磨人,它是一種將學生推向人類忍耐極限的制度(任柯安 2011)。中考同樣會帶來焦慮,因為不同于高考(理論上一個人可以多次參加高考,直到考出滿意的分數),學生只能參加一次中考。以2007年為例,中考一共包含六個科目:語文、物理、數學、政治/思想品德、英語和化學。總分是660分,根據預測,昆明重點高中的分數線在600分左右。參加考試后,考生需要在不知道自己分數的情況下,根據模擬測試的結果和往年各高中的分數線(分數線每年都會按照報考總人數和整體成績的不同發(fā)生變化)進行估分,填報志愿。因此,入學考試都包含填報志愿這一額外工作,它需要有權衡各種因素和預測結果的能力。理想狀態(tài)下,填報的志愿應與模擬考成績相匹配,因為那些你可能考得上但在志愿中排名靠后的學校,可能不會接收你。
就中考而言,考試成績高于學校分數線的可以作為公費生入學。而低于學校分數線10分的可以選擇以擇校生的身份入學,實際名額視指標而定。和在劃定片區(qū)外上初中一樣,擇校生上高中的費用也很高。(這樣的學生有時也稱為自費生。)我沒能核實到具體的費用,但我多次聽到和讀到,擇校生需要為低于分數線的每一分支付1萬元。
擇校現象很普遍,這首先是因為人們對優(yōu)質教育意愿強烈。好學校設置了很高的錄取分數線,要求未通過的學生支付額外費用。其次,即使在同一個城市,學校之間的教學質量也參差不齊,所以盡管就讀劃片之外的學校要支付高昂費用,大家還是爭著送孩子去更好的學校。這第二個因素與高收入社區(qū)還是低收入社區(qū)關系不大,而與中國的具體教育政策有關。[2]好學校能將擇校帶來的收入投入其發(fā)展之中,與其他收入一道,服務于改善基礎設施、招募一流教學人員,以完成學校知名度和地位的再生產。學校的發(fā)展又反過來強化了學校的教育資源,讓高收費和低錄取率更顯合情合理。
支持擇校的人認為這是一種亟須的市場機制,能讓籌資渠道多樣化,公眾和個人皆從中受益。他們認為,擇校現象只不過反映了大眾對優(yōu)質學校教育的渴望,這種渴望通過市場體制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滿足,同時也彌補了國家資金的不足(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wèi)工作委員會 2005)。擇校的批評者則指出,擇校違反了教育公平原則,加劇了學校之間既存的差距,助長了腐敗,還給民眾帶來了過重的經濟負擔(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wèi)工作委員會2005;楊東平[2004]2006)。由于往往需要支付擇校費才能把孩子送進理想的學校,家庭因而倍感壓力,不得不利用手頭的一切資源。由于入學考試成績與要不要支付數萬元額外費用直接相關,學生因而心理壓力倍增,必須刻苦學習。由于評估學校和老師根據的是學生的升學率,提供教育因而變成了狹隘的“應試教育”。
以應試為中心的教育體制帶來的一個意外后果在于,學校和老師傾向于關注有前途的學生,而“歧視”其他學生——不公正地對待他們,讓他們留堂、停課,開除他們(Man Qimin[1996]1997)。這類歧視現象在享有盛名的精英重點中學尤為突出,不過它早在小學就開始了。我常聽到這樣的故事:有孩子被施壓或被要求離開學校,有家長因孩子與小學主科老師有矛盾而將孩子轉校。對學生而言,一種可能發(fā)生的最壞情況就是老師不再關注他們了,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教師承受的壓力和面臨的競爭。在昆明,從小學到中學,班級規(guī)模都相當龐大。老師要引導足足50—70名學生邁向成功,這讓老師也感到負擔沉重,對學生的越軌行為沒什么耐心。
我之所以強調擇校問題,是因為在家長看來,正是擇校這一中國應試教育的具體表現,成為他們面臨的最緊迫的道德問題和實際問題。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過上好日子,這意味著確保他們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成為受人尊敬的人。為了能讓孩子找到好工作,家長必須確保他們踏上通向好大學的道路、取得有分量的學位。為了讓孩子踏上正確的道路,家長必須通過補習班和日常監(jiān)督來提高孩子的應試能力,同時想辦法負擔進入好學校的費用。如果孩子與老師發(fā)生沖突或產生誤解,家長必須要么幫孩子重獲老師的好感,要么尋找新學校,因為在普通家長看來,與老師的關系好壞能決定學業(yè)的成敗。
放眼全球,焦慮是中產階級的內在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須通過教育成就來確保中產階級身份地位(克雷默—薩德利克[Tamar Kremer-Sadlik]和古鐵雷斯[Kris Gutiérrez] 2013)137—138。和美國中產階級母親一樣(盡管課堂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國中產母親也積極干預和學校有關的不利狀況(拉魯 2011)。在中國,考進好學校的熱潮也與艾利森·皮尤在加州灣區(qū)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發(fā)現的“鋪路消費”(Pathway Consumption)相類似。“鋪路消費”是為了創(chuàng)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軌跡的機會,以及確保“舒適”的學習環(huán)境(2009)177—214。因此,從比較視角來看,中國中產父母的強烈焦慮并不是完全獨有的現象。全球經濟鼓勵個體“將自己視為可資管理和發(fā)展的人力資本投資組合”(安德訓2013)13,并期望個體和家庭能吸收系統(tǒng)性矛盾的“沖擊”(15)。各國的就業(yè)市場十分不穩(wěn)定,畢業(yè)生失業(yè)的陰影籠罩著許多國家。通過對教育投入金錢和精力來投資人力資本的做法雖然不能保證回報,但至少是中產家庭掌控之內的事。
[1] 這是2000年代中期的數字。
[2] 中國學校之間的差別植根于“重點學校”政策,這一政策按照更大范圍的國家計劃將國家支持導向指定的“重點”學校(楊東平 2006)。
▼ 第四十期書目:《不確定的愛: 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

《不確定的愛: 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
[美]關宜馨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1月出品
★ 一本關于道德選擇、情感與掙扎的育兒沉思錄。《不確定的愛》呼應了這兩年引發(fā)關注的“虎媽”“雞娃”“內卷”“躺平”等現象,分析了二十年來普通中國家庭在外界環(huán)境變化背景下的變與不變。
★ 中國式母親的情感宣言,辨識育兒的可控與不可控。作者提供了對“母職”困境的深刻洞察。中國式母親,在生活無數的變數中,尋找愛與回報的確定性。
★ 民族志的寫作手法,關注個體經驗,兼具在場感、故事性與學術性。《不確定的愛》對當代中國育兒實踐的觀察,與90后以及00后的成長經歷高度重合,如書中對“減負”“素質教育”“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強勢甚至歇斯底里的母親與甩手的父親”等現象的討論,給人強烈的似曾相識之感。
▼ 書籍簡介
《不確定的愛》是一本教育民族志方面的著作,關宜馨在書中探討了當代中國城市中產父母在育兒上的希望與困惑。將長期的民族志研究和對流行的育兒指南、電視劇以及官方文件的分析相結合,關宜馨見證了普通中國父母的困境,他們在有限資源的現實中努力調和“好父母”的新定義。
關宜馨與昆明的十多戶中產家庭結成了超越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關系的長期友誼,在與這些父母、學校的老師等相關人員的交談和來往中,關宜馨以人類學學者特有的對敘述和細節(jié)的敏銳,將田野調查、民族志研究與學術規(guī)范相結合,對當代中國城市中產父母雄心勃勃的育兒方式以及他們身處其中的希望與焦慮提供了一種理論性的解釋,揭示了在當前中國教育體制下城市中產父母所處的道德困境,以及在急劇變化的現代化進程中家庭這一最基礎單位內部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經歷。
將這些父母的經歷置于國家努力提高“人口質量”的歷史背景下,《不確定的愛》揭示了經濟變革如何在人類最私密的經歷中表現出來。本書提供了一種對道德能動性的本質的思考,探討人們如何在生活無數的意外事件中,辨識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可以控制的。
▼ 作者簡介
關宜馨(Teresa Kuan),本科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人類學,博士畢業(yè)于南加州大學,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人類學、醫(yī)療人類學、兒童研究、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心理觀念等。
▼ 如何參加共讀?
希望你
1. 關注教育、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話題,具有獨立的判斷和思考能力
2. 有表達的欲望,能用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3. 尊重彼此的時間,遵守我們的約定
你需要做
1. 前往“湃客工坊”微信公眾號,在文章評論區(qū)告訴我們?yōu)槭裁聪胱x《不確定的愛》,包括但不限于你對相關議題的了解及興趣。截止時間為2月24日12時。
2. 2月24日當天我們會選出3名讀者,請留意公眾號文章的回復,并及時添加“湃客小助手”微信,發(fā)送地址和聯(lián)系方式,我們會第一時間郵寄圖書。
3. 在10天內(從收到書當日起計)把書讀完,發(fā)回800-1000字的評論。你的文字,將有機會在澎湃新聞客戶端及“湃客工坊”微信公眾號上發(fā)布。如果你成為當期的圖書推薦人,我們將邀請你加入“湃客讀者”微信群,讓你與來自各行各業(yè)的喜歡閱讀、享受思考、愿意表達的讀者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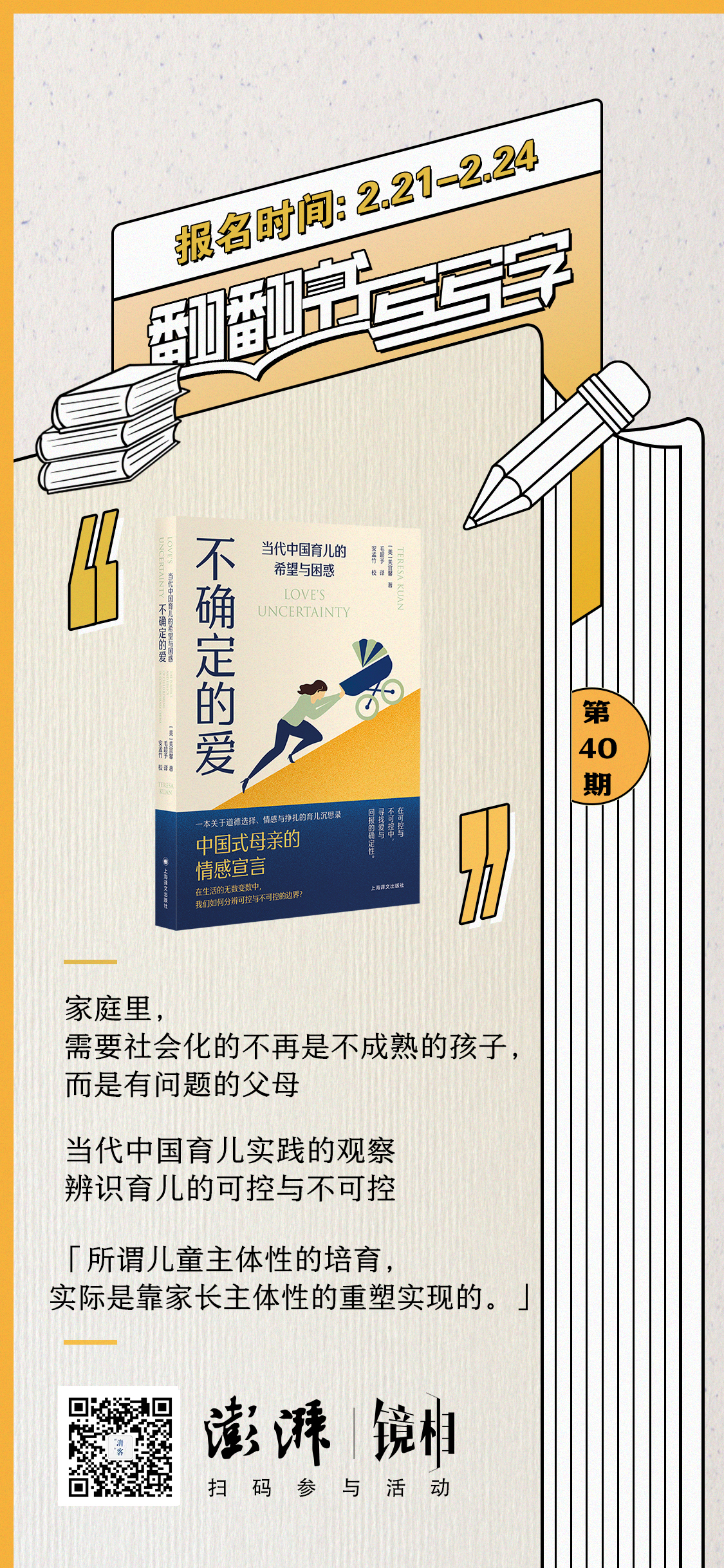
策劃/編輯:吳筱慧
實習編輯:張耀英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