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寒假書單丨胡簫白:從周邊看明代中國
通觀現下的大陸與西方學界,邊疆史都是頗為搶眼、引人注目的學術熱點。即以近年來的熱門史學思潮為例,從“何為中國”到“從周邊看中國”,再及強調跨地域互動的全球史,一波波學術熱潮都在邊疆史范疇留下余溫,推動領域聚焦議題的持續更新。至于西方學界的情形,自不待言——一批清史學者對清代中國廣袤邊關地帶的關注,引起了遷延日久的學術爭鳴與碰撞。在這樣的邏輯下,作為一個從立國之初便承受著巨大邊防壓力、最終亦因邊關失守而走向衰亡的王朝,明代中國的邊疆問題獲得了學者的持久關注,也不是令人意外之事。本文擇取筆者在2024年末或因工作緣故、或由興趣使然而集中閱讀的數部關乎明朝邊疆史的學術作品,進行天馬行空式的關聯和碎碎念風格的點評,權且作為對近年來明代邊疆史研究,尤其是海外學界相關學術演進情形的一次管窺。
竇德士著,陳佳臻譯:《長城之外:北境與大明邊防:1368-1644》,天地出版社,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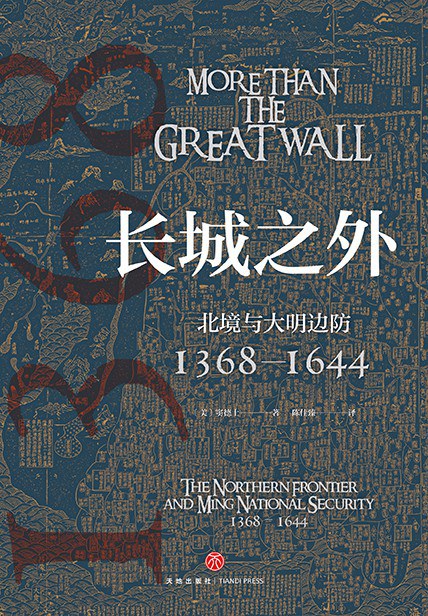
談及明代的邊疆與邊防,恐怕大多數讀者的第一反應都是明蒙對抗與明長城的修筑。誠然,不論是明初自洪永時代便開始醞釀、爾后在土木之變集中爆發的邊防矛盾,還是明代中后期與“南倭”并行的“北虜”問題,甚至于最終壓垮明朝的西北民變與滿洲崛起,北境危機伴隨有明一代始終。正因為此,明代北部邊疆史吸引著無數學人的目光。但也恰恰是由于關涉史實的繁復駁雜、所涉史料的龐大體量,少有學者敢于在一部專著中處理整個斷代的北境邊防議題。在這個意義上,縱然本書作者對于史料的處理多少存在誤讀和簡化,我們也應該對其以八十高齡挑戰學術高山的勇氣致以敬意。
《長城之外》的作者竇德士(John W. Dardess),生于1937年,于2020年去世,是美國老一輩明史研究者中的代表人物。近年來,隨著《嘉靖帝的四季》《長城之外》等書的譯介,竇德士之名逐步為大陸學界所知。被萬明教授稱作“美國明史研究的開拓者”的范德(Edward L. Farmer)與竇德士年齡相仿并仍健在,相比之下,竇德士或更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竇德士的學術關注與其職業履歷一樣豐富:他先后求學于喬治城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并長時間任教于堪薩斯大學。在將學術目光投向明代北境邊防之前,他亦曾關注過明初專制體制、明中期宮廷政治、明末黨爭、明代江西地方社會,以及元代后期的政治思想史,可謂涉獵廣泛。而《長城之外》的英文原著More than the Great Wall: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Ming National Security, 1368-1644于2019年出版,是作者離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
筆者在此處并不打算系統介紹《長城之外》的學術旨趣、觀點抑或得失,因為此項工作已在崔繼來兄的詳密書評中得到了很好的完成(《從細節深處透視大明邊防——讀〈長城之外〉》,《澎湃新聞》2024年5月21日)。質言之,本書循時間線索梳理了明朝歷代對蒙活動大事記,并以邊防政策為綱,將明代北境邊防分為了以戰爭為主軸的洪武到宣德時期、以防御為特征的正統到隆慶前期,以及從和談到崩解的隆慶中期以至明末。本書對非專業讀者并不算友好,因為讀者很容易被巨量的細節淹沒,而這其實是作者有意為之:在“序言”中,作者便直言明代可以在近三百年中相對成功地守御近三千公里長的北境防線,其答案“當然無法簡單地在軍事史、政治史、經濟史、火器發展史或長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從一連串經年累月的事件敘述中去總結,從一系列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涉及為遲滯對中原永無止息的襲擾,消除事關存亡威脅的戰事、謀略、決策、行動的史實中去發現”。以此,要想理解大明的邊防演進,便只能將之全盤呈現。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作者的敘述是一本完完全全的流水賬。在鋪陳史事的間隙中,總有作者精辟而謹慎的點評與概述。用心的讀者,當不難在這些夾敘夾議中體味到作者的深厚功力。
在這里,筆者更希望將《長城之外》放在西方世界的長城研究脈絡里進行討論,以期檢審英文學界近年來的學術范式轉換。關于明清時代直至二十世紀初西人對長城的認知,趙現海已有專文討論,茲不贅言(《近代以來西方世界關于長城形象的演變、記述與研究:一項“長城文化史”的考察》,《暨南學報》2015年第12期)。二十世紀上半葉,以拉鐵摩爾和威廉·蓋洛為代表的探險家留下了眾多關于長城的游記和影像材料,通過記錄歷史現場的方式為西方讀者展現了真實而立體的長城形象。二十世紀后半期,近乎今日我們所熟知的科學意義上的長城研究數量日增。如林霨(Arthur Waldron)于1990年出版的《長城:從歷史到神話》(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便是新世代長城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林霨一方面以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關注了明代長城的修筑過程,并將之與明代中期的“收套/棄套”戰略結合而進行討論,另一方面則考察了作為文化符號的長城在近代中國被政治化的過程:長城與中華民族精神逐步綁定,且被知識分子不斷進行文化建構,直至最終形塑了層次多元的長城神話。林霨這部分的書寫顯見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史風潮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讓讀者品出了些許“歷史三調”的味道。
林霨以后的西方學者多就長城的象征意義展開文化研究維度的討論。如藍詩玲(Julia Lovell)2006年出版的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 – 2000 AD 便對東西方之間圍繞長城所代表的“偉大民族象征”與“文化孤立主義”之截然二分進行反思。藍氏認為,長城兩千年的龐雜歷史已然確認了這座偉大建筑文化意義的靈活多變,它因之并非文明和野蠻的界限,而是對歷史流動性和相對性的預示。與藍氏觀念異曲同工,2010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羅鵬(Carlos Rojas)專著The Great Wall: A Cultural History同樣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對長城的象征意義展開討論。羅鵬尤其關注長城傳說,認為隱含在這些傳說中的“儒家思想的儀式和隱喻”是理解長城的重要思想基礎。而別出心裁的是,羅鵬特別關注了一系列“長城文本”中蘊含的女性力量的流動,認為長城并不僅僅是父權家長制所蘊含的威權與武力的象征,諸如“宣太后和義渠王”“昭君出塞”和“孟姜女哭長城”等女性傳說也指向了長城象征的靈動與脆弱,而恰恰也就是此種不確定性使得“長城”的象征意義得以不斷發展和豐富。
循著這樣一種學術脈絡,可以認為竇德士的《長城之外》算是回到了林霨研究的實證主義發端。誠然,在竇氏1992年對林霨專著進行的書評中,他便已經盛贊林霨對明代長城歷史的研究了——而在《長城之外》中,也幾乎不見竇氏對長城文化符號意義的解讀,這可以看作是老派學者對傳統史學路徑的回歸。相較而言,年輕學人則在“全球史”的范式風潮下將長城研究帶入了新境。如匹茲堡大學的克里斯托弗·鄂可森(Christopher Eirkson)便在其博士論文“Ideas of Empire in Early Ming China: The Legacy of the Mongol Empire in Chinese Imperial Visions, 1368-1500”中將明代中國的“建墻”行為放置在廣大的時空語境中進行考察。鄂可森認為“建墻”不僅僅是明代中國所獨有的現象,而且在其時歐亞大陸各處廣泛存在。如沙俄帝國便在不斷向南擴張的過程中與草原游牧民族發生摩擦,因之開始建墻以應對具備高機動性的游牧者。在與草原世界互動的維度上,明代中國在諸多方面都與其他歐亞政權具備可比性。例如正統皇帝被游牧民族擄走并囚禁之事,其實在歐亞大陸西端的奧斯曼帝國同樣發生過。1402年,奧斯曼帝國蘇丹巴耶濟德一世被帖木兒大軍在戰爭中俘獲并囚禁,此一史事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奧斯曼帝國政體在之后的發展方向。近日筆者在收聽播客的時候,得知羅新教授亦將進行關乎長城的旅行寫作,他不僅僅走訪了明長城沿線的很多村寨,還對伊朗長城、不列顛半島的哈德良長城等有身體力行的感受和體驗。筆者以為,比較史學的框架或許可以成為深化理解明代中國北部邊防與長城文化的可行路徑。
David M. Robinson, 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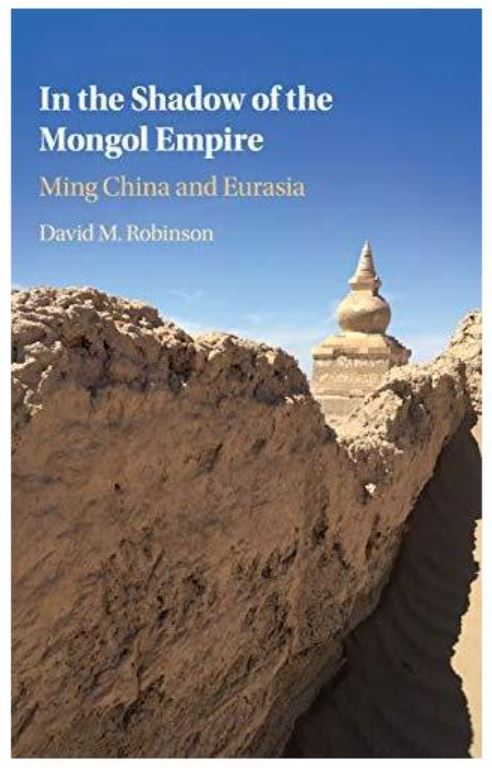
與《長城之外》的關注點相似,美國柯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亞洲研究暨歷史學講席教授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的近著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暫譯名:《在蒙古帝國的陰影下:明代中國與歐亞世界》,下文簡稱《在蒙古帝國的陰影下》)也處理了明朝與其草原強鄰的關系,并將時間聚焦于洪武時代。對于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魯大維之名當不陌生,其著作如《帝國的暮光》《神武軍容耀天威》等近年來被批量譯介,最新翻譯出版的《稱雄天下:早期明王朝與歐亞大陸盟友》亦頗受好評。事實上,《稱雄天下》與《在蒙古帝國的陰影下》本為姊妹篇,學術聚焦一以貫之,且以后者為上篇。又據卜正民(Timothy Brook)透露,在投稿給劍橋大學出版社時,兩書甚至本為一更大部頭的作品。惟出版社從篇幅、出版和市場角度考慮,要求作者將之拆分為兩本。因此,若可將兩書對讀,便更容易把握作者近年來所謂“將明代前期歷史放在元明易代的語境中深化理解”的倡導。
《在蒙古帝國的陰影下》的核心議題,是朱元璋如何在一個滿溢著蒙古時代政治文化遺產的歐亞大陸強化自己的權威及宣稱明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魯大維認為,蒙古時代在歐亞大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留下烙印,存在感與顯示度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在這個邏輯下,蒙古時代的影響力有多大,朱元璋的壓力就有多大。作為一個非黃金家族成員、沒有娶到黃金家族女子、沒有在元朝行政體系中扮演過任何角色的小人物,朱元璋如何向全世界證明他自己,這是魯大維想通過此書回答的問題。
筆者關于此書的詳盡書評將在一份專業期刊發表,此處僅做節略式的概括并談一談大體感想。《在蒙古帝國的陰影下》共分四個部分,其中第二、第三個部分是此書的核心章節。在這兩部分中,魯大維分別討論了朱元璋向國內臣民及歐亞大陸其他政權表達他理解元明鼎革的方式,并通過種種策略的文本敘述來達到他強調自身合法性的目的。為了概括明廷對蒙元時代的敘述策略,魯大維提出了“成吉思家系敘事”(Chinggisid narrative)的概念,并以“敘事”一詞所蘊含的“具有目的性的觀點敘說”之意來提煉明初朝廷對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乃至整個蒙古帝國與時代的評述策略。在魯大維看來,朱元璋時代的“成吉思家系敘事”絕非很多人認為的平面的、程式化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是值得細細拆解的、能夠反映洪武朝政治文化的文本凝聚。如情感態度激烈的“反蒙古”言論,顯然是將國內臣民視作主要聽眾。而大元國運已失、明代元興實屬水到渠成的自然之選這樣的敘事,則主要是說給北元朝廷、尤其是身處明初疆域東南西北邊地的那些搖擺者聽的。與軍事行動相比,這樣的“宣傳戰”對于明朝開疆拓土、穩定邊防而言同樣重要。
如果說該書的第二部分主要呈現的是明初“成吉思家系敘事”的國內版本,那么第三部分則凸顯的是此一政治文化的外向輸出。例如《給大汗的信》這一章便考察了朱元璋在二十余年間向妥歡帖睦爾、愛猷識里達臘、脫古思帖木兒所發出的十余封信件。在這些信中,朱元璋不厭其煩地敘述了為何元運已失、為何他能夠代元而立,以及為何這幾位大汗應該接受甚至擁抱這樣的變化。值得說明的是,魯大維在這一部分中對大量敕諭進行了全文英譯,為日后學者的翻譯工作與中英對讀提供了重要參考素材(竇德士專書亦對大量明實錄節段進行了翻譯,或可給需要英譯相關文段的學者提供不少便利)。除此之外,魯大維在分析具體文本內容時亦尤其注意明初朝廷對漢文與蒙古文、波斯文之間的翻譯問題的處理。即便從文本的角度出發,亦可推見明廷和后蒙古時代歐亞大陸諸多政權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蒙古帝國的陰影下》的結論部分對全書中的很多觀察進行了系統化的概述和提煉。魯大維認為,朱元璋之所以面對各類聽眾不厭其煩地敘說蒙古帝國的崛起、榮耀與衰微,是因為這樣的表述擁有廣大的應用場域:明初的“成吉思家系敘事”不僅可以合法化朝廷對于權力的掌握、提醒人們元朝興復的無望,還對那些尚持觀望態度的豪強輸出著“附明即得生、附元即滅亡”的道理。蒙古時代是歐亞大陸諸多政權的“起點”,所以“成吉思家系敘事”是一種切合跨地域語境的、大家都能聽懂的政治宣傳。而這種敘述的底色則是“規勸”。在魯大維看來,既有研究對于朱元璋與洪武朝的專制主義特質矚目甚多,往往將其理解為殺伐決斷的絕對權威,這當然是其尤為鮮明的一面;但與此同時,論者可能較少看到他反復調整語匯、用一種規勸式的口吻進行政治表達的面向。在這個維度下,朱元璋的“成吉思家系敘事”展示出的更多是耐心、容忍與堅持,并且貫穿了洪武朝始終——這直接指向了朱元璋頗為看重卻無可奈何的一個要素,亦即在十四世紀幾乎可以被視作全球的歐亞大陸,對于如何處理蒙元帝國的政治文化遺產,是不分種族、宗教、文化的各地統治者共同思考的難題。《在蒙古帝國的陰影下》聚焦于元末明初的數十年,切面不可謂大,然關懷亦不可謂小。
卜正民為魯大維這本書的姐妹篇撰寫了書評,并發表于業內頂尖刊物《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在這篇書評中他對魯大維之研究不吝贊美之辭,認為這兩本書是“很多年未有的關乎中國王權統治的最有分量的研究”。卜正民認為,包括他在內的一代明史學者仍致力于觀察明朝與世界的聯系,尤其是借由晚明中國考察白銀全球化將世界各地勾連在一起的形式。而新一代的明史學者則受到近年來學術范式的促動,更傾向于將元以降的中國放置在歐亞大陸的時空框架下進行考察。毫無疑問,魯大維的一系列研究便是此一思潮轉換的標志性成果。以此,我們不妨進而思考:如果明朝的前一百五十年尚在因應蒙古時代的影響,而后一個半世紀則與海洋世界發生了愈深愈廣的聯系,那么這樣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理解這樣的轉變,又可以如何刺激我們去反思明代中國,反思這個朝代在元朝與清朝之間的位置,以及更廣泛時空中的角色呢?
Sixiang Wang, Boundless Winds of Empire: Rhetoric and Ritual in Early Choso?n Diplomacy with Mi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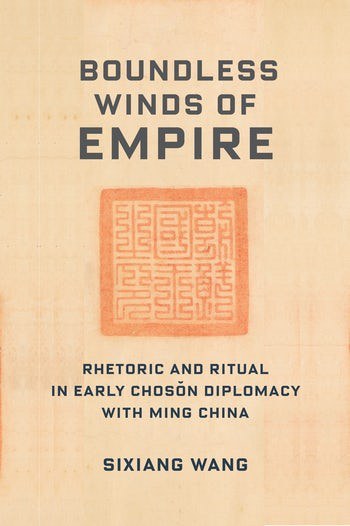
十余年前,葛兆光先生發出“從周邊看中國”的學術倡議,認為研究中國歷史需要多幾面鏡子,過去的歷史學家往往以西方作為參照,卻忽略了朝鮮、越南、日本這些從屬于漢字文化圈的“周邊”的鏡鑒作用。約略于同時,張伯偉先生站在文學領域的立場上亦強調需要加強對域外漢籍的重視。一時之間,文史領域雙雙開始對傳統意義上東亞世界的“中心”與“外緣”角色進行反思,對學者的研究多有刺激。
王思翔的近著Boundless Winds of Empire: Rhetoric and Ritual in Early Choso?n Diplomacy with Ming China(作者本人建議譯名:《皇風無垠:明鮮外交中的修辭與禮儀》)或許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進行理解——當然,筆者并不是說王思翔本人的觀點受到了大陸學界的啟發,中英文學界的問題意識本就不同,呈現出相似的關懷,或許更多是“形似神異”的巧合。但雙方共同展現的,則是對既有范式下對東亞世界區域格局僵化處理的不滿,以及對跨地域聯系、互動及相互影響的強調。
《皇風無垠》的作者王思翔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在加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前,其人先于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后又次第于斯坦福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博士后職位。而拜賓大學緣所賜,筆者也算是忝入王思翔的同學行列。如果筆者的記憶沒有產生偏差的話,王思翔的父母都是安徽人,因此其自小便是漢語、英語的雙母語使用者,這從《皇風無垠》對大量詩詞的精彩翻譯、深入詮析中便可窺見一斑——有過相關文本處理經驗的朋友都知道,翻譯詩歌的門道有多深。而作者因為研究的關系,韓語的聽說讀寫能力亦俱佳,因之能夠對跨區域歷史研究駕輕就熟。
用作者自己的話說,《皇風無垠》聚焦的是“修辭與禮儀”在朝鮮王朝(1392-1910年)與明帝國(1368-1644年)長達兩個半世紀復雜互動中扮演的角色,亦即文字與書寫是如何在東亞外交中發揮作用的。通過靈活的修辭策略,朝鮮一方面在“事大”的邏輯下保持對明忠誠,另一方面也沒有放棄對自主權益的強調。全書第一部分(1-2章)介紹了朝鮮與明朝溝通之初利用各種手段抹平雙方之間張力的努力。十四世紀后期東北亞的地緣政治格局千頭萬緒,半島政權與蒙古勢力藕斷絲連,而李成桂取代高麗建國,在明朝方面看來亦有先斬后奏之嫌。因此朝鮮需要利用諸種外交手段來重新獲得明朝信任,從而穩定區域局勢。全書第二、三部分(3-7章)是專著的核心內容,檢審了朝鮮士人對包括儒家思想和文學創作等文化行為的調用,并考察此類行徑幫助朝鮮在與明交互過程中尋得“臣服”與“獨立”之間平衡的方式和邏輯。如朝鮮使節堅持將朝鮮,即“東國”,納入古之圣賢所倡導之文明場域,這樣便可以在樹立朝鮮文化權威的同時,一定程度上驅散明廷對朝鮮半島投射的復辟主義陰影;而在對具體外交實踐中的禮儀進行分析時,王思翔也力圖呈現明鮮雙方是如何就繁復禮儀的文化內涵進行協商甚或較勁的——在這個意義上,外交禮儀便不僅僅是符號化的形式主義,更是暗流涌動的權利博弈場域。甚或在軍事協作的過程中,明、鮮軍隊之間的抵牾如何與政治文化場域中雙方高下分明的階序關系自洽,亦是此部分的關注主題。而在全書的第四部分(8-10章)中,王思翔則重點關注《皇華集》,通過分析朝鮮文士與明廷使臣的唱酬之作中展現出的修辭策略,作者論述了朝鮮朝廷和明朝統治者如何共同打造明朝的所謂“帝國意識形態”。以此,在東亞區域格局的邏輯里,明、鮮關系的意識形態基礎便不僅僅是儒家思想所定義的政治原則的簡單衍生,亦非明朝世界觀的自然延伸,而是產生于朝鮮王朝與明帝國之間有關文化與政治傳承的復雜互動。
《皇風無垠》在西方中國學的學術脈絡中所處位置如何?筆者以為,是書應當放在關乎“朝貢體系”討論的延長線上進行理解。上世紀六十年代,費正清學派提出用“朝貢體系”的概念理解古代東亞區域秩序。此后的數十年中,歷史學家對于此一框架多有批評,認為“朝貢體系”的敘述存在相當的局限性,以至于衛思韓(John Wills Jr)一度將“朝貢體系”比作一艘沉船,說它沒有任何值得打撈的價值。而即便“朝貢體系”的相關討論存在扁平化解讀或文化沙文主義等多方面的偏頗,學界一時半會兒也尋不到合適的替代概念,以至于柯嬌燕認為“朝貢體系”已然獲得了永生。相較而言,在歷史學家對朝貢體系大加批判之際,西方學界的政治學家們卻對此框架欣賞有加,尤其認為朝貢體系提供了一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后西方國際關系的東方世界對應物。眾多政治學家在2015年的《當代中國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和2017年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組織了兩期特刊,后者的特刊主題甚至直接叫“朝貢體系萬歲!東亞國際關系研究的展望”(“Long Live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Future of Studying East Asian Foreign Relations”),可見相關討論的熱度。
近年來,關乎“朝貢體系”的討論在歷史學界似乎有回暖之勢,但仍以批評為主。如卜正民領銜編輯的《天命:成吉思汗以來的亞洲國際關系》(Sacred Mandates: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Chinggis Khan)便提出藏傳佛教在后蒙古時代東亞世界的國際關系中亦發揮了重要的潤滑劑角色,基于儒家倫理的朝貢體系并非統攝性的外交準則。如若聚焦到明代,雖然很多學者曾經將明代中國視作中國歷朝歷代中實踐朝貢體系最完備徹底的王朝,但根據Felix Kuhn的最新研究,作為外交工具的朝貢體系僅僅是明廷維系與外界關系的政治、文化、經濟、軍事手段中的一環而已(“Much more than Tribute: The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s of the Ming Empire”)。
近世中國與朝鮮的關系是近年來英文學界反思朝貢體系的典范場域。2018年,宋念申出版專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討論一直以來較為穩定的中朝邊境是如何在十九世紀后期開始被流民、戰爭、地緣政治、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等要素擾動,而中朝圖門江邊界的劃界,則指向了以朝貢體系為準則的傳統東亞秩序最終的“現代轉向”。同年,王元崇亦出版專著《重塑中國》(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聚焦清代的中朝關系。不滿于既有研究中“朝貢體系”的解釋力度,王元崇提倡以回歸歷史語境的“宗藩關系”概念討論清代“中華帝國”所強調的區域秩序,并希冀以朝鮮為鏡,考察清代中國如何形塑和表述自身的政體性質和與世界交往的邏輯。在這個意義上,《皇風無垠》幾乎可看作《重塑中國》所涉議題的“明代版本”——所不同者,在于王元崇通過關注清朝與朝鮮的互動來理解清代中國的帝國形塑,而王思翔則經由考察明朝與朝鮮的往來去檢審朝鮮方面的政權建構理路。在他看來,僵硬的“朝貢關系”框架無法全面概括明朝與朝鮮的關系,朝鮮方面在雙邊關系中并不失語,而是在動態的外交實踐中靈活調整自己的身段,通過遣詞造句的外交辭令、文學創作及儀式展演盡力維護自身利益,一方面不開罪天朝上國的華夏中心主義邏輯,另一方面也在此過程中完善了屬于半島的政權形態和處事邏輯。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