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皇權、閣權和宦權:明代權力機構是如何運作的?
《明代國家權力機構及運行機制》與《澄清吏治:明代的文官考核與官僚政治》是近年出版的兩部明代政治史的新書,此前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劃、舉辦學術沙龍,邀請兩位作者對談明代政治中的皇權、閣權與宦權,本次學術沙龍由宋晨希主持。本文系部分發言的文字整理稿,內容經發言者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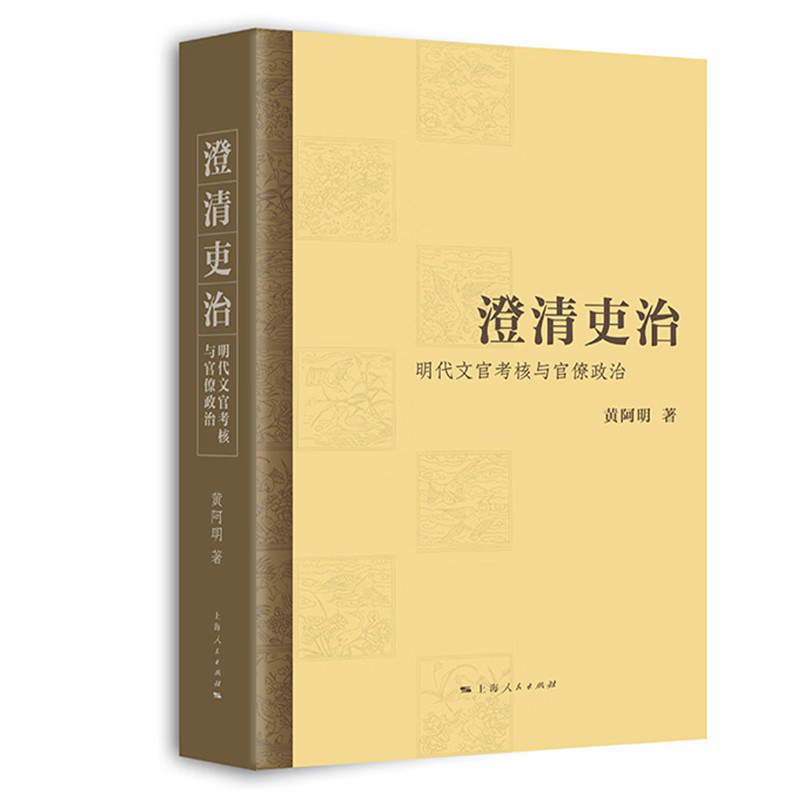
《澄清吏治:明代的文官考核與官僚政治》,黃阿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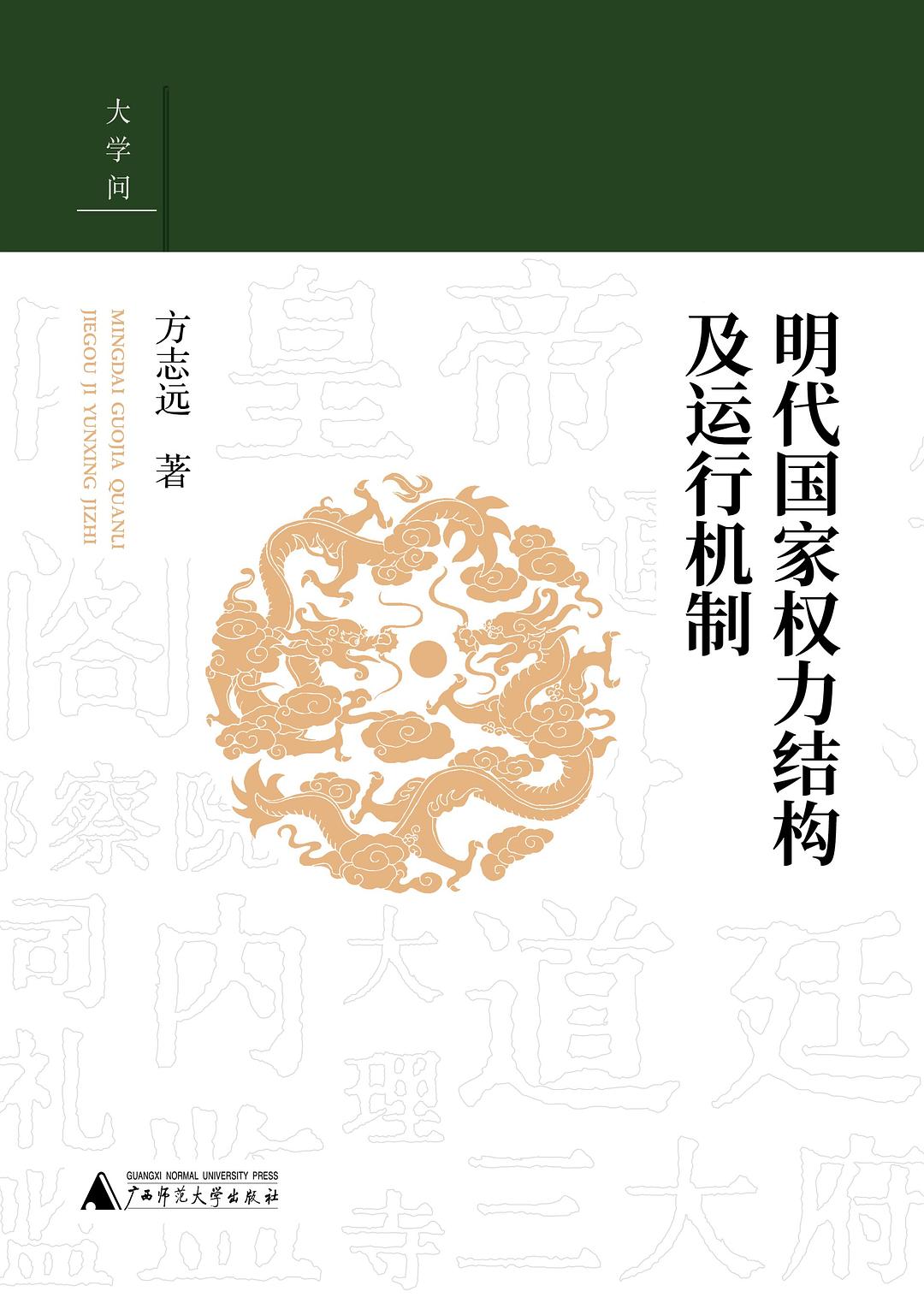
《明代國家權力機構及運行機制》,方志遠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
兩種觀點:明代的專制與數目字管理
宋晨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想起嚴耕望先生曾經回憶說,錢穆先生跟他們講:歷史學有兩只腳,一只腳是歷史地理,一只腳是制度。兩位老師的著作對于明史的一些觀點或者觀念起到了廓清的作用。以兩種非常主流的觀點來講,第一種觀點是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里談到明代的制度其實是走向了獨裁,他甚至用政治惡化這樣的說法來評價明清時期的制度。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就是朱元璋廢除宰相制,所以,很多上一輩的歷史學者對明代的政治制度的評價是非常低的。第二種觀點來自黃仁宇,他認為明代是缺乏數目字管理的。首先請方老師談談您的看法。
方志遠:黃仁宇先生毫無疑問是我們的前輩學者,我認為他的《萬歷十五年》開發/開拓了我們這一代大陸學者的史商。他離開中國很多年,往往是用美國的標準來看待中國的歷史,所以不斷地說數目字。我對《萬歷十五年》的評價很高,但是我比較討厭他說的數目字,因為中國人的管理就像我們現在說的中醫和西醫——中醫是讓你稀里糊涂地活,西醫是讓你明明白白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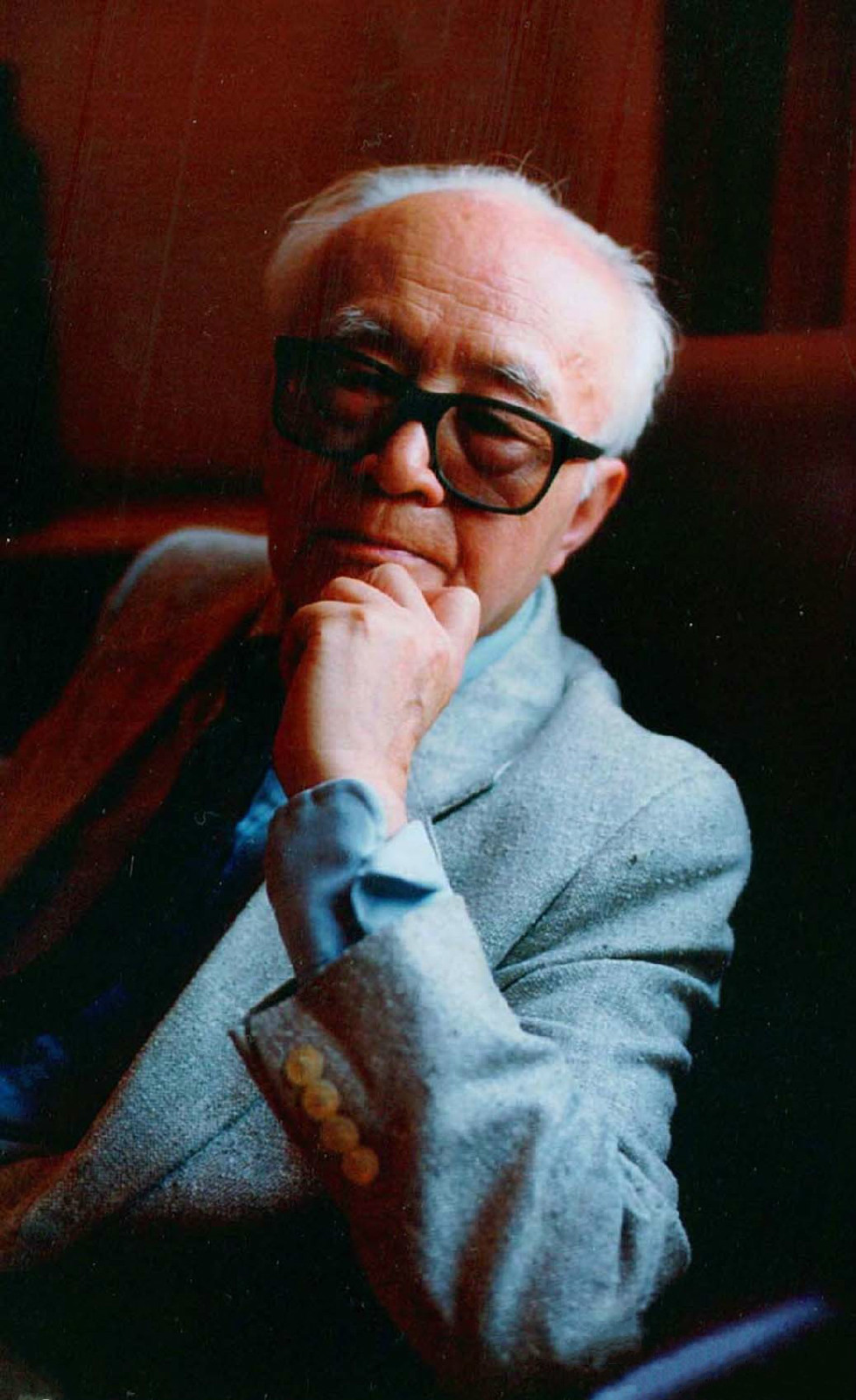
黃仁宇
黃仁宇先生希望把整個中國都用數字進行管理,實際上這已經是現代國家的管理了。但是中國古代一直是以農業稅為主體的,要以西方的現代國家標準來衡量明代的農業國家,我覺得不是太恰當。但是它有一個意義,明代所處的世界已經進入到大航海時代。特別是在16世紀初,葡萄牙人已經來到中國的南海,但是中國仍然在原來的道路上繼續行走。所以我在另外一本書中說,如果不和周邊國家進行比較,僅以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身來說,明朝是進步了,但是我們如果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它有一些倒退。
倒退在哪里呢?就是君主制的加強。但是明朝君主制的加強有些不一樣的特點,在前期是(以)皇帝的事必躬親來表現國家的控制力,中后期是以皇帝的垂拱而治來表現這種統治模式。我稱之為“以內制外,內外相制”。什么叫做“以內制外”?建立一種龐大的宦官機制,對外廷的文官和武官進行強有力的制約。但不是單方面的,外庭同樣對內庭進行制約,所以我說,第一是“以內制外,內外相制”。第二(是)建立龐大的監察系統,由六科十三道這些低品官構成,所以它的另外一個特點是“以下制上,上下相維”,以小官來制約大官,大官同樣管小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明太祖自己所說的,五府六部相互“頡頏”,事皆朝廷總之。這是明朝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也是它的一個基本特點。所有的衙門都是相互制衡的,明朝沒有任何一個機構、任何一個個人的權力,可以達到威脅皇權的程度。所以我在這本書里剖析內閣、司禮監乃至皇帝本身,都有種種的制約。
黃阿明:就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問題,我來談一下我的看法。
《萬歷十五年》應該是(黃仁宇)晚年比較學術的一本著作。他在這本書里強調了中國傳統社會缺乏數目字的管理,是以現代化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來看待中國古代時期。我個人覺得黃仁宇,一個以研究明代財政經濟起家的人,講中國古代在明清時期缺乏數目字管理,好像是有點不應該的。因為我們很清楚,在明代中期和中后期的時候,隨著一條鞭法改革的展開,以及在全國推行以后,特別是明代中期出現的貨幣白銀化問題以后,到了16世紀末17世紀初,我們已經能夠在國家層面進行從上到下的財政會計的預算。所以在萬歷九年完成土地清丈以后,萬歷十一年就出版了《萬歷會計錄》,這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中國古代王朝國家時代的第一本國家層面出版的全國財政預算書。所以,這應該是中國數目字管理的開端。到了清代,出現了大量編制的不同時期的賦役全書,賦役全書其實不僅僅是賦役征收的依據,同時也是全國賦役財政征收的預算數,當然在實際征收過程中,會用到實征冊這樣的東西。15~16世紀末到17~18世紀,已經有了比較成熟完善的、從上到下的財政領域的精細管理,廣州大學的郭永欽、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申斌,他們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在明代、清代已經能夠編出非常精致、科學的財政管理和預算,以及背后的一套計算程序。
所以,我覺得黃仁宇先生講的數目字,可能他在(20世紀)40年代末離國赴美以后,深感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那么連帶對中國古代的討論,似乎對某些方面的評價并不是太公允。
剛才講到錢穆先生講明代的獨裁和惡化,其實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里還有一個說法,他把中國古代的漢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這么五個王朝的制度做過比較,首先,他認為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從中央到地方設計最合理的時代是漢代,這個是一個平民社會,中央跟地方的關系結構非常緊密和銜接;其次,他認為明代的制度是中央和地方都合理,但上下是斷裂的,所以他說這是一個夾心餅干或者三明治的狀態。
講到明代的制度獨裁,我經常會提到,中國古代的王朝國家中,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唐朝是存在時間最長的——289年,之后是明朝——277年,如果認為清朝結束于1912年,那么大概是260年吧?如果將其算到1840年,那么其存在時間還要短。那么,這樣一個王朝,你說它專制、獨裁,說其中央體制跟地方體制出現這樣一個斷裂,為什么這個王朝能夠存在這么長時間?這是我們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想它能夠存在這么長時間,一定有它合理的地方,這個合理的地方跟它的制度設計是分不開的。我們還注意到一個問題,剛才方老師講到——他的概括我覺得還是非常精當的——“內外相制,內外相維”。
我們在讀明代的史籍跟官方的文獻,包括很多官員的奏折里,通常講的是內官和外官,很少講地方官和中央官。實際上在洪武九年,朱元璋宣布廢除行中書省,改成承宣布政使司。在朱元璋的設計中,改變了秦到宋的中央與地方的制度結構,在那個時候,如果說它是一個近乎垂直的一種管理體制,到了元代,甚至行中書省的時候,其實已經有了一點改變體制結構,因為行中書省是從中央派出官員到地方,形成這樣的監理和管轄。到了明代就更加清楚,京師的中央官和在外地任職的官員,是內官和外官的關系,這兩者就是:京官屬于皇帝,皇帝來統轄;而外官也屬于皇帝統轄。它其實有點像人的兩只手,一只手歸皇帝的左邊,一只手歸皇帝的右邊。其實并不是中央統轄地方的關系,而是兩者都屬于皇帝直接統轄。所以地方的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司,其實不是向中央對口的機構去負責,而是直接向皇帝負責,只有都司衙門才會向五軍都督府負責,其他兩個部門都不向中央任何一個部門負責,只是在業務上有所往來。所以我覺得剛才方老師的“內外相制,內外相維”講得非常精當,其實就是明代再度進行設計的一個體制。

《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
這種情況跟過去的漢唐宋是不一樣的,因此在錢穆、黃仁宇那里,他們觀察到中央和地方的制度結構好像是斷裂的,其實根本就不是斷裂的。從理論上來說,其實根本就沒有想要建立成中央領導地方這樣一個機構和制度體制、這樣一個體系。它其實不是垂直的,應該是平行的,所以我們一般在明代是稱內官跟外官的關系。
我在讀書的時候,發現一個現象,即有很多學者在討論明代的官員考核的時候,第一,有不少的研究其實概念并沒有搞清楚,但是論文和研究成果出來了。因為概念不清楚,所以在討論某些問題的時候,往往是討論不清楚的,這是一個現象。第二,關于明代考核制度的框架性的描述,發表了相當多的論述,這些論述往往使用的文獻,主要來自《實錄》《明史·職官志》,包括《明會典》這樣的史料,使我們沒有辦法更加深入地了解明代的考核制度到底是怎么運行和怎么運作的。因為依據剛才我所講的《明會典》,包括《明史·職官志》,其實多數只能看到這個制度的框架問題。在我開始認認真真地去展開更廣泛的閱讀,去收集有關明代的官員考核的制度,才慢慢地搞清楚什么是“考滿”,什么是“考察”。大概經過一年半的準備以后,有將近四五十萬字的資料,我在2017年就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當時就叫“明代官員考核與官僚政治”。差不多到了2022年,我完成了這項研究,后來就把它出版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澄清吏治:明代文官考核與官僚政治》。一開始我沒有設定主標題——“澄清吏治”,澄清吏治能實現嗎?葉文憲老師也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說這算是明朝自己的一個理想,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周密的考核制度設計,能夠實現整個國家的吏治澄清。
明代之害:宦官與黨爭
宋晨希:剛才提到了明代制度的種種優勢,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明代的制度背離了朱元璋的設計。其次,為什么明代的黨爭會這么興盛,甚至有人說明朝是亡于黨爭的。在明代的(制度)設計中,宦官和黨爭的出現是不是也(讓我們)看到了這套制度的一些缺陷?
方志遠:剛才黃老師也談到,實際上中國歷代會計制度都是很發達的,唐朝是量入制出,明朝有《萬歷會計錄》,到明萬歷以后,清朝出了全套的《賦役全書》。這個數字都非常多,但關鍵是什么?就像錢穆先生說的那樣,制度實際上是分兩個層面的,一個是形成制度化的條文,一個是人的執行。
我覺得黃仁宇談到中國歷史上缺乏數字化統計的說法,有很大程度上是說的后者。因為看地方志,一個很有問題的事,是人口和戶口的關系。可以看一下明朝的戶和口的統計,第一,戶的統計有些變化,但變化不大;第二,只是在戶數的基礎上乘以五就變成了口數,所以明太祖的時候人口是六千多萬,到了萬歷的時候還是六千多萬,它幾乎沒變化。
(20世紀)90年代的電視連續劇《戲說乾隆》,說是乾隆大壽的時候,有衛士、宦官、宮女三人,分別到古玩市場,給皇帝買了三件古董給他做壽。皇帝一看,全是假的,這三位就要去找賣古董的老板討回公道,讓皇帝去管一管怎么這么多假貨,鄭少秋演的乾隆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這有什么假的,現在什么不是假的,我關心的只有兩個假,哪兩個假?第一假皇上,第二假圣旨。”過了30多年,我仍然印象深刻。文學作品揭示了中國古代統治的一個基本特點——皇位的鞏固。在這個前提下,其他的都可以造假,所以明朝、清朝的數字很多都是假的。明朝一邊有給上面看的紅冊,一邊有自己理政的白冊,五花八門的,各種都有。
所以中國歷史研究很有意思,我們記載下來的東西很多未必是確切的。
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制度都是不斷變化的。所謂“漢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但都是在繼承的過程中改變。明太祖在不斷拓展自己的勢力的時候,他就是仿照元朝,打下一個地方,就設某地行中書省,但是他這個行中書省和元朝的行中書省是不一樣的。
元朝的行中書省既管軍隊也管政務,是軍政一體的。但是(隨著)明太祖的統治區不斷推進,(他在)不斷設置行中書省的同時,設立行樞、行府,就是大都督府的分府。所以一開始他的行中書省是軍政分離的。
另外,明太祖(有)非常充沛的精力和對國家事務的關切,他把自己作為整個明朝的家長,把整個明朝作為一個家族進行管理,所以他構建的那一套制度,都是全方位的行政思考。等于他把中書省的事情兼做了,是皇帝兼宰相,這要巨大的精力,即使(是)他,也是力不從心的。
所以他就讓翰林春坊那些低品官幫他看奏疏,寫摘要,提初步的處理意見,實際上內閣的雛形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所以孟森先生《明史講義》就談到:翰林春坊平章奏啟,是內閣的產生的開始,而不是表面現象的殿閣大學士,所以明太祖他已經在改變自己的設想和制度。所謂“垂拱”二字,所謂內閣和司禮監“對柄機要”,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和明太祖的設想是不一樣的。但是基本原則沒有變,“事皆朝廷總之”沒變,各個衙門相互頡頏沒變,但是統治方式變了。皇帝長期不坐朝,與后來的黨爭,齊黨、楚黨、東林黨的發生,有非常直接的關系,因為(皇帝)看出來了,他希望你在斗,他可以對任何一方進行制裁,但是這種斗爭一旦形成一種氣候和市場,任何人(都)收不回來。
所以有一句話叫“玩火者自焚”,挑起一場運動和內斗,最后他沒辦法收場。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萬歷皇帝主動挑斗,(而是)有些事情他故意擱置,而擱置在那里的一個問題,就是國本問題,他遲遲不表態,讓你們去吵,讓你們去斗。
明朝的黨爭和當下的網絡非常相似,已經不管青紅皂白了。面對面的時候他是正常的人,包括明朝那些參加黨爭的,甚至是黨派的領袖,單個拿出來是很了不得的人物,但是一旦陷到這里頭去,他就不是人。所以我也跟很多朋友交流,明朝的決策機制非常緩慢,或者說非常保守和遲鈍,所有的事情都在慣性中運行。在這一點上我不知道黃老師怎么看,我認為是不如清朝,清朝各個皇帝都是理政的,所以他決策反應得快,明朝的決策反應比較慢。
黃阿明:現在很多人詬病明代的宦官對于民間的禍害,包括我們說的東廠西廠,是制度本身的一個缺陷?還是說皇帝有意為之,或者說是一種失控狀態?
方志遠:我談過一個觀點,在央視《國史通鑒》節目中講宋代的時候也說到過。宋代的黨爭,事實上范仲淹和歐陽修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們標榜自己是君子,對方是小人,還寫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朋黨論》,公開為他們的結黨提供理論依據。
2010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發的一篇文章叫《“山人”與晚明政局》,其中就談到一個問題,正德時期,焦芳還有其他人在依附劉瑾的時候,都是偷偷摸摸,(因為)覺得自己在干壞事。但是到天啟年間,大家依附魏忠賢,都覺得是走上了康莊大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君子,對方是小人。而且我們單獨來看宣黨的首領,楚黨的首領,也是很正派的人,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是君子,東林黨才是小人。但是東林黨又覺得他們是小人。所以當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正確的一方,都認為對方是不正確的時候,就沒辦法收場了。

影視中的魏忠賢形象
那收場靠什么?收場還是靠殺人。所以從東林黨上臺,殺閹黨才平息了一陣子,但是后來東林黨自己不爭氣,弄得閹黨又起來了。我在這里交流一個觀點,歷代黨爭中第一代的黨政領袖,往往都是正人君子,比如宋代的王安石跟司馬光,都是君子,但是到第二代就變小人了。明朝也是一樣的,第一代的東林黨,像顧憲成這批人,還有被別人稱為齊黨、浙黨的那一幫人,都是了不起的,但到第二代就變成小人了,就只顧自己的利益了。
我們在歷史書上看到對宦官的抨擊、揭露,很大程度上是帶有偏見的,是士大夫對這些身殘之人的一種歧視,包括對魏忠賢這些人。魏忠賢開始很想拉攏東林黨的那一批君子,比如說趙南星、鄒元標,他對這些人有好感,覺得不錯,但是這些人歧視他,這里一歧視,那邊就仇視。所以有的時候政治局面的惡化,往往是在一種斗氣之中發展起來的。身殘之人沒有生育能力,會有一種極端的自卑,一旦條件成熟,會轉化成一種極端的自尊,就要表現自己的存在。這種殺人的狠毒,制裁的狠毒,可能就超出一般的人,但是天下事哪里都是宦官壞的?
黃老師可能也記得那段話,劉健拼命地說宦官壞。明武宗說了一句話,“天下事哪里都是宦官壞的?譬如文官詩人,好人才三四個,壞人倒有六七個”。劉健聽聞瞠目結舌,確實是這樣的。主要干壞事的還是文化人,然后(才是)宦官。明朝的宦官里有一個好玩的事:少數民族的宦官往往好的多、壞的少,而漢人的宦官我們看到的壞的多、好的少。明朝宦官傳,第一個是鄭和(回族),然后是侯顯(藏族),這些都是好宦官,第一個壞宦官就是王振(漢族)。
宋晨希:您在論文里還提到,明英宗小時候愛玩耍,王振跪下來說您不要玩物喪志。
方志遠:就像黃老師說的,王振哪里就是壞的?實際上我的書里也談到王振的很多好處。包括后來陸容的《菽園雜記》,還說到宣德時期,很多宦官危害地方,但是正統年間沒有,什么原因?大家都認為是明君賢相,但是陸容說(因為)當時掌管內廷的是王振。
還有劉瑾,廖心一老師有兩篇論文,談到劉瑾的改革。我最近和b站做了一個節目,談到明朝的悲劇人物,把魏忠賢的各種記載結合在一起,他是當然的領袖人物。雖然不怎么認識字,但是有擔當,而且看事情看得很準,當時的士大夫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所以我覺得在討論宦官的時候,要把身殘這一點先放在一邊,很多記載實際上對宦官有些歧視。
黃阿明:我想補充一下我對明代宦官的一些看法。其實我非常同意方老師強調的一點。我們今天在講到中國古代的宦官的時候,是帶有一點我們今天的人的歧視,實際上中國古代,也一定有這樣的眼光去看待宦官的。所以我們看到歷代的文人在講到宦官的時候,講刑殘之人,其實就已經在歧視他了。當然明代的宦官跟中國古代此前漢唐的宦官,包括宦官的專政和干權是有些不一樣的。
明代的內閣制運作的時候,殿閣大學士實際上是不能到皇帝的生活區的,所以把公文和奏折傳遞到御前的時候,需要有人作為媒介和中轉,(這)就是司禮監的太監。

明代的宦官是制度性地被納入到國家的決策機制中。這個和此前是不一樣的,過去是竊權,是干政,明代就是屬于皇權的一部分構成,和閣臣一樣,也是皇權的一部分構成。所以我們對于明代的宦官要清楚,它不是干政,這就是它的權力的一部分,它擁有皇權讓渡出來的批紅權,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
方老師是第一個提出明代宦官知識化的研究者,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方老師在之前的訪談和講座也提到,中國歷代從開始出現宦官以后,每一個王朝都是禁止宦官識字的,當然明朝的太祖時期也是有這個規定的,也規定宦者不得干預國家政事,否則斬。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內閣鐵禁牌,但是宣宗皇帝有一個做法,開始在內廷中開設內書堂,從宦官中低級的或者挑選年輕、貌美、機靈、聰明俊秀的進入內書堂訓練,起初是20個名額,后來還不斷增加名額,所以(明代)是中國古代王朝國家中對宦官進行系統教育的第一個王朝。
道理很簡單,文人士大夫也是讀四書五經起家的,這批宦官進入內書堂以后,他們也是讀這一批書的,還有一點,很多來自平常人家的子弟的讀書啟蒙的教師很可能是落第的舉人或者是落第的生員,但是內書堂的教學者是不一樣的,內書堂能夠由次輔和群輔進行教學的。
中國古代的王朝,不管是制度的運作還是制度運作過程中的利弊,什么人看得清楚,其實皇帝比我們要清楚,身在其中,他能看得清楚。那么在皇帝身邊的人,宦官也好,宮女也好,尤其是這批宦官,他能夠很清楚地知道本朝的制度的長短在什么地方,他知道這個制度怎么運作,而其實很多從底層出來的官僚士大夫,不見得在這一塊比宦官要看得多,(因為)宦官可以說是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看這套國家制度是怎么運作的,他看得一清二楚。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的優勢如果是有文化的話,(宦官)就缺健全的身體,如果坐而論道,一起參與國家決策,(宦官)不見得比外朝的士大夫和內閣的人士看問題、處理事務的能力差。
今天會講王瓊和宦官的關系走得比較近,我要試問一句,從三楊以來,明代的官員,不管是內閣、六部,還是都察院,有幾個人跟宦官的關系不密切呢?包括地方的巡撫和方伯,又有幾個沒有(宦官的)支持力量呢?最早一批的應天巡撫周忱,他在江南地區主持賦役經濟制度改革,如果沒有王振的支持,他不可能那么順利。一方面是有內閣三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獲得了王振的支持。所以,這是明代的一個普遍現象。孟森先生在講到宦官的時候,就講明朝的士大夫,如果你想一無所能,那你不用跟宦官去結交,如果你想有所為,不管是在京師還是在地方上,你必須要跟宦官搞好關系,因為這就是明代的政治現實,制度設計就是如此。
天啟年間以魏忠賢為主的閹黨,從后臺走到前臺有個很重要的原因,萬歷末年的東林也好,浙黨也好,楚黨也好,其實能力都不太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才從后臺轉到前臺,操刀加入混戰,來控制局面。
剛才講到宦官外出的問題,這里一方面要考慮到內使監本身的能力和控制宦官的水平,(另一方面)宦官因為長期沒有辦法外出,一旦外出,這是一個機會。因此宦官外出的放縱是難免的,我認為這是個人因素。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一個宦官外出往往都是帶著采辦的任務。隨著明代宮廷內部的財政緊張以后,經常出現以極低的價格來購買價值比較高的產品和商品,以及宦官帶著很少的錢出去買大量的物品和所需品的時候,甚至采用打空白支票的方式。
在文人的角度,這就變成了變相的搶掠,是有這樣的情況,其實是跟明代宮廷中的采辦制度以及宮廷中的財政本身能不能夠很大方地支付貨幣有關系的,再加上宦官個人的放肆,這幾個因素同時考量,我們就會看到一些不受約束的宦官進入社會以后,他所帶來的一些對社會的危害。
到了萬歷年間,萬歷皇帝把宦官放出去進行采礦、采稅,這個其實是非常赤裸裸地與社會爭利,與百姓爭財富。這是比較形象、比較惡意的做法,但是這種情況在明代其實是不多見的。
我覺得對于談論到明代的宦官,應該是屬于制度層面的,就從制度層面來討論;屬于個人層面的,那就從個人層面來討論。我們可以把它放到失范的狀態上去討論,它既不是常態也不是穩態。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