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龔雋︱作為“神圣空間”的佛教文化通史——讀《普陀山佛教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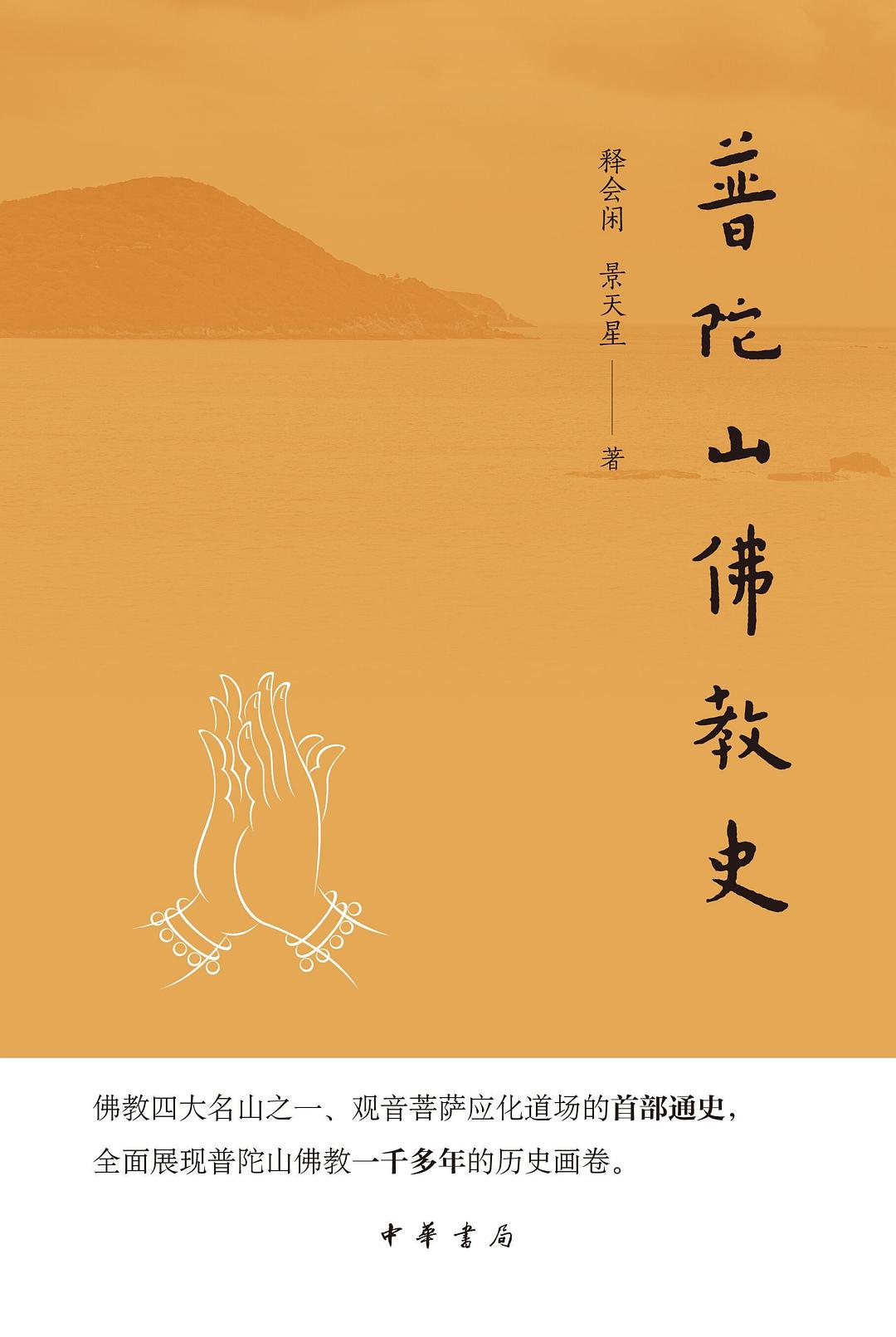
《普陀山佛教史》,釋會(huì)閑 景天星著,中華書局,2024年7月版,489頁,128.00元
釋會(huì)閑法師與景天星先生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一書的出版,不僅為觀音菩薩應(yīng)化的神圣空間——著名的佛教道場(chǎng)普陀山進(jìn)行了詳密的歷史闡述,還為作為“地方性知識(shí)”的佛教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學(xué)術(shù)典范。作為“地方性知識(shí)”的思想或思想史研究,近年來一直就是國際學(xué)界有關(guān)亞洲學(xué)術(shù)史研究的潮流之一。在有關(guān)中國佛教的漢語研究中,以具體地域或道場(chǎng)為中心所開展出的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史著作可謂鳳毛麟角,而這部《普陀山佛教史》可以說是漢語佛學(xué)界為“地方性知識(shí)”的教史之作所提供的一部代表性作品,期待能夠引起學(xué)界的關(guān)注與討論。漢語佛教史的書寫中一向重于宏觀教史,而經(jīng)常化約那些形態(tài)各異而又獨(dú)具特色的地方性佛教法流,該書的出現(xiàn)一方面補(bǔ)充了中國佛教史書寫中的某些疏忽,同時(shí)這種以具體道場(chǎng)為中心的通史之作,也從不同的視角更深入地呈現(xiàn)出中國化佛教歷史進(jìn)程中的復(fù)雜性與豐富多面性。
在中國佛教史中作為具有信仰和生活史意義上的佛教,普陀山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過去有關(guān)普陀山佛教的知識(shí)大多建立在地方史志與一些佛教僧傳和游記等資料當(dāng)中,近代以來中外學(xué)界對(duì)于普陀山,特別是普陀山與觀音信仰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過不少探討,而系統(tǒng)完整地以通史形式來貫通性地論述普陀山佛教歷史之作尚無出現(xiàn),該著可謂首創(chuàng)。本書在較充分地消化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無論在研究方法或是材料的統(tǒng)合運(yùn)用方面,都有自己獨(dú)到的發(fā)明與見地,殊為難得。
我本著學(xué)術(shù)史書寫的角度,從兩個(gè)方面對(duì)本書的意義略加闡明。
一、從文本史到文化史。傳統(tǒng)教史之研究多以文本為中心建立起來,近來西方宗教史的研究特別重視在文本史之外的新文化史研究,注重于宗教生活世界的歷史闡明。如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的《佛教對(duì)中國物質(zhì)文化的影響》(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詹姆斯-本(James A.Benn)的《中國茶:一種宗教與文化史的論述》(Tea in China-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等,都是代表性作品,這些研究推動(dòng)我們對(duì)中國佛教史進(jìn)行更深廣的理解。這部《普陀山佛教史》的書寫,并非如許多一般教史寫作那樣,對(duì)佛教之議題或思想作泛泛之論,而是始終貫穿了一個(gè)重要的主線,即普陀山“神圣空間”的形成與發(fā)展,該書把“神圣空間”作為一個(gè)核心觀念引入佛教史中來進(jìn)行探究,這本身就是對(duì)傳統(tǒng)教史書寫的一種突破。
我們知道,普陀山的聞名與觀音信仰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而有關(guān)觀音信仰的流傳,最初并不是與具體的“神圣空間”,而是經(jīng)由不同宗教經(jīng)典與文本的書寫有關(guān)的。從六朝開始,中國佛教中的觀音信仰而發(fā)展起來,如六朝以來有關(guān)觀音信仰的文獻(xiàn),特別圍繞著《法華經(jīng)》之“普門品”進(jìn)行開展,從其內(nèi)容上來分判的話,大致可以區(qū)分為兩種不同的法流。一是“論釋不同”的義學(xué)發(fā)展,即有關(guān)《普門品》的詮釋歷史;二是作為信仰的事件敘述,即各類中國撰述為主的,重視神異靈驗(yàn)的觀音文書的流通。
這都可以說是文本上的觀音信仰。而古典文本中的觀音信仰,又以思想的闡述為主流。在國內(nèi)一般佛學(xué)史的研究中,比較偏重于有關(guān)觀音義學(xué)史的討論,尤其是生活化的觀音信仰經(jīng)過天臺(tái)大師的觀音闡釋與引申,更趨向于玄學(xué)化的法流。智顗在對(duì)《普門品》的解經(jīng)中,對(duì)中國初期所流傳的觀音信仰都有自家宗義的鮮明抉擇。這表現(xiàn)在他一面保留住觀音信仰的宗教經(jīng)驗(yàn)的合法性,而同時(shí)又要對(duì)此經(jīng)驗(yàn)性的信仰加以玄學(xué)的點(diǎn)化,試圖把這些經(jīng)驗(yàn)轉(zhuǎn)換成為哲學(xué)的議題,在“理”上進(jìn)行論究,這即是智顗在解釋觀音經(jīng)典的活動(dòng)中,把觀音的想象玄學(xué)化而又進(jìn)一步天臺(tái)化的過程。實(shí)際上,作為文化史意義上的佛教來講,《普門品》當(dāng)時(shí)在社會(huì)的盛行,主要表現(xiàn)在日常社會(huì)生活中那類以稱念名號(hào)而獲得體驗(yàn)的觀音信仰,而不是玄學(xué)化了的觀音理論(參考牧田諦亮,《中國仏教史研究》第一,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56年版,第210頁)。唐道宣在《釋迦方志》中就把六朝佛教的這一傾向概括為“稱名念誦,獲其將救”。當(dāng)時(shí)還連帶出現(xiàn)了很多中國撰述的,各種有關(guān)觀音經(jīng)典和靈驗(yàn)一類的文書,最著名的如《高王觀世音經(jīng)》《觀世音三昧經(jīng)》和《觀世音應(yīng)驗(yàn)記》等,這些文書都是以直接宣揚(yáng)觀音靈驗(yàn)為主題而展開的。可以說,初期中國佛教緣《普門品》而產(chǎn)生的觀音想象,大都與這種真摯樸素的稱名實(shí)踐和祈求靈驗(yàn)的宗教操持有密切的關(guān)系。這些內(nèi)容在一般漢語佛教思想史的書寫中,大多為輕描淡寫而一筆帶過。我們不應(yīng)該只停留于有關(guān)觀音的哲學(xué)論究,而忽視觀音信仰的文化史探討。觀音信仰的實(shí)踐都是發(fā)生在具體信仰的“神圣空間”當(dāng)中,于是,把觀音信仰與神圣空間關(guān)聯(lián)起來,進(jìn)行具有文化史意義的研究,理當(dāng)成為中國佛教史,特別是與觀音信仰有關(guān)的佛教歷史中的重要論述。
《普陀山佛教史》的書寫正好完成了從信仰的文本史到信仰圣地的形成史轉(zhuǎn)向,該著對(duì)以普陀山為中心的觀音道場(chǎng)——“神圣空間”的形成,進(jìn)行了細(xì)密地歷史學(xué)探討,明確指明“神圣空間”是指特定場(chǎng)域內(nèi)所賦有的儀式空間,該空間帶有宗教儀式感,具有神圣性,同時(shí)存在于人類日常生產(chǎn)與生活之中。顯然,這些都是宗教文化史,而非以文本為主的哲學(xué)思想史的研究領(lǐng)域。該著作還對(duì)普陀山佛教起源的問題探賾索隱,努力于“傳說”與“歷史”之間進(jìn)行嚴(yán)密的勘辯(如該書第一章佛教傳入普陀山各類歷史傳說的考釋),無疑是一部嚴(yán)肅的佛教文化史著。該書對(duì)普陀山的觀音信仰如何變?yōu)椤笆ホE”進(jìn)行了歷史學(xué)的描述,指出宋代開始了這一神圣化空間的“初步建構(gòu)”,并分別從普陀山“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兩個(gè)方面的“神圣化”給予具體而微地闡明。這些文化史研究的結(jié)論大都在尊重前賢研究的基礎(chǔ)上,而又有孤明先發(fā)之趣。雖然于君方教授的《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一書也曾開辟專章考察了普陀山與觀音信仰的關(guān)系,指出普陀山神圣空間的建立在歷史上經(jīng)歷過不斷建構(gòu)與解構(gòu)、創(chuàng)建與毀滅、建設(shè)與重建等過程,而終于在中國本土形成了中國人所創(chuàng)造的本土化的佛教信仰的神圣空間。但于教授對(duì)于普陀山教史的討論,只重于普陀山與觀音信仰的關(guān)聯(lián),而且限于篇幅也并未能就普陀山佛教的整體歷史脈絡(luò)進(jìn)行細(xì)節(jié)上的論述。而這部《普陀山佛教史》對(duì)于普陀神圣空間的形成史,從普陀山的開山到宋、元、明、清,乃至民國時(shí)期,都有專章予以剖析,循序漸進(jìn),建構(gòu)宏大,在資料方面也能夠盡量做到竭澤而漁,把古今有關(guān)觀音信仰與普陀山佛教、禪宗及社會(huì)歷史等的論述進(jìn)行了整體融合與立體性的探究,可以肯定,該書已經(jīng)成為有關(guān)觀音信仰史和普陀山佛教史方面最新的知識(shí)生產(chǎn)。
二、作為“通史”的地方佛教史。《普陀山佛教史》不只是有關(guān)“地方性”知識(shí)的細(xì)密建構(gòu),同時(shí)它還是通史性的一部論述。雖然對(duì)于一門成熟的學(xué)術(shù)研究來講,通史書寫是基礎(chǔ)性的工作,更深入的研究應(yīng)該進(jìn)入專題性或帶有深刻問題意識(shí)的論述。但是,通史的研究或史觀既是專題研究的基礎(chǔ),同時(shí)也是不同專題研究之后的成果結(jié)晶與升華,一種成熟的通史書寫是相當(dāng)艱難的工作。
對(duì)于不算太成熟的中國佛教研究來說,通史的書寫仍然是一項(xiàng)必要的基礎(chǔ)性工程,我們有學(xué)術(shù)史的經(jīng)驗(yàn)可鑒。當(dāng)近代中國佛教研究要突破傳統(tǒng)宗門史的格局而進(jìn)入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佛教學(xué)形態(tài)的時(shí)候,具有現(xiàn)代性意義的通史書寫就成為中國佛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標(biāo)志。太虛大師在1920年代就稱,晚清到民國初年因?yàn)樾隆八枷胼敼嘀绊憽保瑥亩姑駠饘W(xué)研究突破了傳統(tǒng)宗派佛學(xué)之“拘蔽”而進(jìn)入了“世界佛學(xué)之新時(shí)代”。新時(shí)代的佛學(xué)理念并不一味盲從傳統(tǒng)佛學(xué)有關(guān)教理與教史的模式,而主張融納新知。蔣維喬就發(fā)現(xiàn),這種以新知論究佛法的方式,致使民國佛學(xué)出現(xiàn)了一段“興盛之曙光”,有關(guān)佛教通史的書寫就代表了這一新的佛學(xué)趨勢(shì)。實(shí)際上,新史學(xué)主要綱領(lǐng)由梁?jiǎn)⒊?920年代所提出,而他也幾乎在同時(shí)開始了佛學(xué)史的論述,因而帶動(dòng)了民國佛教史書寫的通史意識(shí)。就近代民國佛學(xué)來講,新佛學(xué)啟蒙最必要的是編撰出與傳統(tǒng)佛學(xué)觀念不同的教史。如何選擇以新知的方式來撰述佛學(xué)通史,可算是一種應(yīng)時(shí)所需的啟蒙了。呂澂在1920年代初就批判了傳統(tǒng)佛學(xué)局限于宗門立場(chǎng),“以各宗為經(jīng)緯的宗史”,無法通觀“佛教全體的歷史”,“不得顯露教史真相”。所以呂澂提倡“一切學(xué)術(shù)之研鉆,莫不以史的尋究為最先”,而他當(dāng)時(shí)所注重的歷史即是一種佛教通史。從他的《佛教研究法》一書關(guān)于教史類所列書目來看,無論是印度或是東亞佛教研究(中、日佛教),都是以具有通史性質(zhì)的著述為主。這一點(diǎn),民國著名佛教史家蔣維喬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認(rèn)為 “我國舊時(shí)的佛教徒,也受印度的影響,不曉得注意歷史,就是偶有撰述,也只限于傳記及編年,要從舊時(shí)典籍尋覓一部有系統(tǒng)的佛教通史,絕對(duì)沒有,學(xué)者不勝遺憾”。可以肯定,民國佛學(xué)界對(duì)于通史之例的呼喚,在當(dāng)時(shí)是具有啟蒙新知的意味。
通史的撰述不僅可以對(duì)整個(gè)佛教的發(fā)展作出條理,而且可以有助于從中去了見佛法興衰的律則,獲得歷史之教益。對(duì)于作為“地方性知識(shí)”的佛教史研究來講,國內(nèi)目前整體還處于起步的階段,如何去具體而又有整體觀念地去闡述不同地域或道場(chǎng)的佛教歷史,確實(shí)需要具有高屋建瓴式的地方佛教通史來統(tǒng)領(lǐng)全局,在通史與專題性研究之間相互激蕩,相輔相成。對(duì)于觀音信仰及其普陀山佛教的研究,正如《普陀山佛教史》“研究述評(píng)”中所說的那樣,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專題性的研究成果,而“實(shí)為一大遺憾”的就是缺乏“通史”或“有明確的斷代史之研究”。我以為該著在以通史為主的書寫中,同樣照顧到了專題性的研究面向,在構(gòu)建普陀山的佛教歷史中,始終以“神圣空間”為中心議題來進(jìn)行闡析,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可謂通專結(jié)合。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普陀山佛教史》不僅是“作為地方知識(shí)”的中國佛教通史研究中具有啟蒙性的讀物,也可以說是相關(guān)研究領(lǐng)域里一部有專業(yè)深度的通史之作。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