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產二次元游戲:本土化與世界化中的“冰山”之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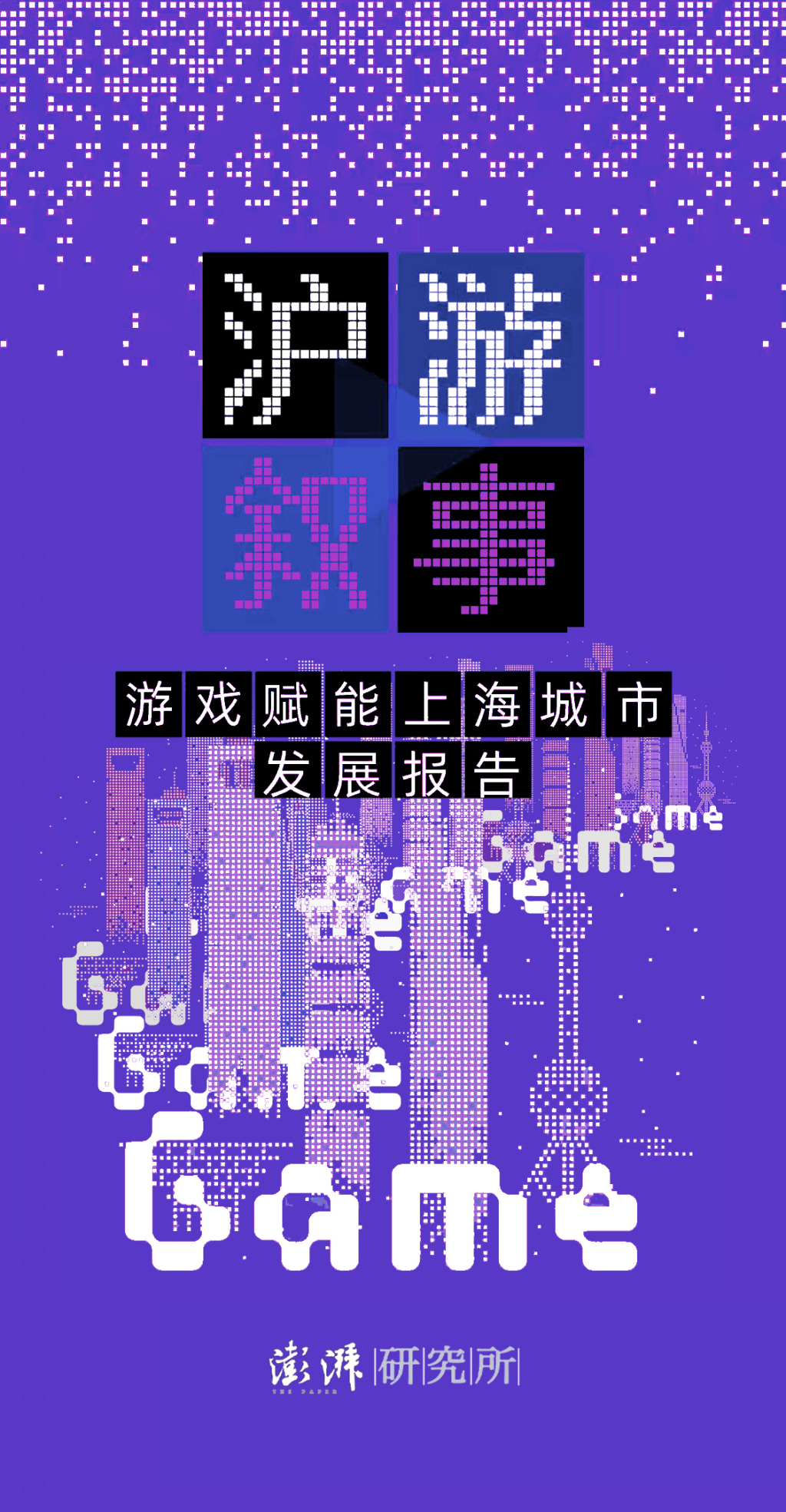
近年來,對中華文化主體性表達的樸素追求在中國玩家群體間日漸高漲。出于相同的文化愿景,以及迎合受眾的商業導向,近年來不少國產二次元游戲確在嘗試滿足玩家們的這部分心理需求。例如《白荊回廊》和《歸龍潮》等作品,都將“國風”“國潮”一類概念作為自身宣發的重點之一。
回顧國產二次元游戲過去十年的歷程,可以明顯看到一條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的發展脈絡。早期作品的內容與付費模式,都從既有的優秀二次元游戲中汲取了充足的養分。最近五年來,隨著相關技術升級,整體工業化程度提高,二次元游戲開發者們也自然而然地萌生了更加獨立且遠大的追求。從圖形技術到視聽風格,從故事立意到角色塑造,包括如今已成潮流的多終端乃至全平臺的全球化市場運營,中國在二次元游戲產業的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其類型發源地。在一定程度上,“國產二游”的類型定義,甚至有掙脫“二次元游戲”概念之束縛的趨勢。
與這一歷史進程相對應的,是中國游戲產業的整體性發展。三十年來單機游戲、網絡游戲與移動端游戲,在高速變遷的中國社會與文化環境中遞進式生長著。三十余年間,“讓中國優秀的游戲作品走向世界”的理想始終深藏在游戲作者與游戲玩家們心中。苦心孤詣的創作、傳播與文化闡釋,為中國電子游戲領域積累了歷經磨難、壯志如初的資深從業者,以及“實踐出真知”式的教訓與經驗。
正是在如此背景之下,當中國電子游戲的產業規模與市場規模達到今時之盛狀,“中國游戲應講中國故事”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具有普遍性的受眾期待,甚至在逐漸變成一種義正辭嚴、不容置疑的評價標準。然而問題在于,所謂“二次元”這一概念,在文化層面是具備高度的多元性與包容性的。例如,盡管受眾在常識上,會憑直覺認為二次元作品天然具有某些日本文化元素與日式審美風格,卻很難篤定地說,日本的二次元作品——包括動漫、游戲與輕小說——在創作層面具有日本文化主體性表達的自覺。
如果我們不得不承認,對全球流行的二次元文化這一問題的思考,暫時無法超越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所提供的思考框架,那么其中異質性文化的多元融合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集體認知中所呈現的“混雜性”,就是難以忽視和回避的“房中大象”。在這樣一種作品類型中,如何辨識本土文化的獨特屬性,民族文化主體性言說的創作自覺與接受反饋能否成為堅實的藝術評價標準,似乎懸而未決,為國產二次元游戲的審美制造了困境。
對此,應重新審視“中國故事”的定義。

著名乙女游戲《戀與制作人》。現在國產游戲除了乙游之外與傳統的“核心二次元”交集并不大,甚至閑魚在統計中將游戲與“二次元”并列。
何為“中國故事”
2024年10月,《黑神話:悟空》的制作人馮驥在中央電視臺訪談節目《面對面》中說:“我覺得‘中國故事’不是中國傳統的、自古以來的故事,(而)是中國人講的故事:我用我的視野,我用我的價值觀來看你,我甚至比你理解的還深刻。”這句話可以被理解為,只要是中國人創作的故事,哪怕題材、人物與情節來自異域,也仍然是“中國故事”——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表達超越了一般的形式與結構,它真正所依附的,是作品所傳遞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觀。
馮驥的這一觀點,也許來自創作實踐的心得。而跨文化研究者經年思考的洞見,也剛巧與之相吻合。比如法國比較文學研究專家達尼埃爾-亨利·巴柔便曾在《形象學研究理論:從文學史到詩學》中寫道:“在言說他者的同時,‘我’又否定了‘他者’,從而言說了自我。”
眾所周知,在日本大眾文化中,諸葛亮的形象廣受推崇。吉川英治根據在日本流傳的三國故事再創作的小說《三國志》,便將諸葛亮作為與曹操并列的兩大主人公之一,受到日本讀者的歡迎。他們不僅喜愛諸葛亮的智慧,更欣賞其忠誠,這顯然與他們的生活和認知方式有關。總的來說,日本民間的諸葛亮形象,與諸葛亮在歷史與《三國演義》中的形象略有不同。比如,在《三國演義》中,意氣風發的青年孔明,出茅廬時曾囑托童子好好治理家產田地,說自己功成身退之后,再回臥龍崗務農。但在日本的某些故事里,諸葛亮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無法達成,卻仍義無反顧地出山輔佐劉備,鞠躬盡瘁,坦然接受星落五丈原的宿命。
主動凋零的櫻花最美,而英雄亦如是——日本創作者寫的雖是外國故事,反映的卻是自身文化中的審美取向與價值觀念。
自這一視角考察中國游戲作品,不外如此。例如《明日方舟》中,玩家所扮演的羅德島勢力,始終致力于消弭爭端、團結各方勢力,以應對事關大地眾生的危機與災難。這雖是發生在光怪陸離的幻想世界中的故事,但它所反映的,是中華文明從“天下大同”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致雅量,是中國人內心深處悲天憫人的文化底色。又如《崩壞:星穹鐵道》中,位于雅利洛-Ⅵ星球的城市“貝洛伯格”的故事。創作者對這座城市的設計,從氣候環境到日常生活,從建筑風格到組織形式等等,都較為明顯地參考了域外文化中的一些特質。但通讀劇情,玩家們可能會發現這仍然是一個中國故事。最典型的例子是這一章節的結尾部分:城市首腦“大守護者”可可利亞為了挽救城市的命運,做出了錯誤選擇,墮入黑暗,最終被玩家勢力聯合繼承人布洛妮婭所擊敗,但為了城市民心的穩定與未來的希望,眾人選擇隱瞞實情,讓民眾認為可可利亞是為了抵抗災難而犧牲的英雄。這樣的情節設置,傳達的是中華文化中“舍小義而全大義”的集體主義精神,以及“民貴君輕”“以民為本”的仁政理念。
這就是“中國人寫的就是中國故事”這句話背后的深層邏輯:當本土文化集體成員書寫異域的故事或風貌時,那創作成果其實無關異域的知識或真相;其所真正言說的,是借相異性以確立身份認同,是以作為社會集體想象物的“異域”“他者”為參照,借之反觀“自我”,定義“自我”。中國游戲和中國故事,其概念得以確立的關鍵,并不在于游戲的內容、風格與故事的情節、人物是否源自中國,而在于其能否借游戲與故事的形式結構,傳遞出中國人的價值觀念。
闡明了這一點,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在“文化融合”“文化出海”等常用詞語中,“文化”一詞的真正定義。

《黑神話·悟空》場景界面
“冰山”之辨——文化的實質與符號
《滬游敘事·上海網絡游戲產業發展報告》中,有一篇題為《文化認同:超越表層的文化符號,游戲還能傳播什么?》的文章,使用“文化冰山”這一理論框架,討論了以《原神》為代表的,暢銷全球的國產原創游戲如何激發當代青年的文化認同并傳播中華文化理念與價值這一問題。“文化冰山”理論認為,文化如同海中冰山,可被明顯看到的是符號與器物,隱藏在海面之下的是理念、審美以及最深層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冰山”式模型并非文化研究者首創,弗洛伊德與海明威便曾分別借之來思考人類心理與文學創作。一方面,在單一社會集體的文化語境下,“文化冰山”可以有效揭示生活層面的日常文化活動與心理層面深邃龐大的集體無意識之間的相關性。另一方面,當問題進入文化產品的跨語際、跨文化傳播時,簡單將文化符號與文化實質之間的關系視為具有整體性的“一座冰山”,又會帶來不少問題。
“文化”一詞,是被高頻使用卻難以被簡述定義的。英國文化研究者麥克·克朗曾說過,應避免將文化描述為一種“剩余變量”,即凡是其他領域不能包括的內容統統解釋為文化現象,這種描述遠遠沒有體現出“文化”的中心意義。在生活中,“文化”一詞的意思也時常靈巧變化,例如,用“文化程度高”和“有文化”形容個體時,前者說的是其受教育水平,后者則往往指的是其閱讀量、知識面以及眼界與修養等等。
研究者的不同著述之中,對“文化”一詞所作定義繁多,至少在百種。英國人類學創始人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認為:“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而言,是指這樣一個復合整體,它包含了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這個看似寬泛的定義卻被認為是“唯一一個能夠為大多數人類學家所正確引用的,也是當其他定義被證明為太麻煩的時候人類學家可以回頭求助的定義。”馬修·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中說:文化是這樣一種過程或東西——“通過閱讀、觀察、思考等手段,得到當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優秀的知識和思想,使我們能做到盡最大可能地接近事物之堅實的可知的規律,從而使我們的行動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亂,使我們能達到比現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這一觀點后來被薩義德總結為:“文化是一個社會的知識和思想精華的貯存庫。”丹尼爾·貝爾則認為,文化在哲學層面為人類的生存處理與意義相關的問題,他說:“文化本身正是為人類生命過程提供闡釋系統,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文化研究的重要開拓者雷蒙·威廉斯將文化的定義總結為三點:文化是指人類的完美理想狀態;文化是人類理智性和想象性作品的記錄;文化是特定的人類日常生活方式。
綜合各種定義,我們可以寬泛地認為,文化的實質是:社會集體成員在特定社會環境中所形成的,令他們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意義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
比如,談及中華傳統文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繁多的文化符號,比如四大發明和二十四節氣。在當今的科技水平下,無論工業或農耕都已不再需要這些具體的技術原理來指導生產。但作為文化符號,它們所指向的是中華民族在探索自然、經驗總結、發明創造以及知識傳承等方面的優秀精神特質。這些文化實質中的價值觀念,仍然驅動著今時我們的工農發展與技術進步,在宏觀上為日常生活賦予意義。
又如,國產游戲《原神》所發布的,以京劇演唱為主題風格的音樂宣傳視頻《神女劈觀》在全球的總播放量達到1.5億次,被視為以電子游戲為載體的文化海外傳播的典型范例。無需多言,傳統戲曲擁有獨特的審美價值,是中國文化主體性標識之一。但藝術審美并非其唯一的文化價值。模塊化、程式化的基礎表演框架,實際上蘊含著一套久經打磨、簡明高效的意指系統,也體現了理性務實的中華民族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符號與文化實質之間的聯系,往往并非直觀,而是抽象的。這也是“文化冰山”理論遭遇的困境之一。事實上,在使用文化符號一詞時,“符號”所代表的并非索緒爾符號學意義上的“符號系統”,而是系統中的“能指”部分——即切實存在的、具有形象或聲音的事物。而“能指”在意義層面指向的抽象概念,也就是“所指”,其與“能指”的關聯是隨機的、約定俗成的,而非先驗的、一成不變的。比方說,隨著用語習慣的變遷,一些字詞的讀音會發生調整,“能指”變化了,與其對應的“所指”卻仍然如初。
在同一社會集體的文化語境下,文化符號與文化實質的意義聯系屬于“常規智慧”,是不言自明的共識,比如提到勾踐就想到堅忍不拔,提到關羽就想到忠義勇敢。但當文化符號進行跨文化傳播時,誤讀與延異的發生幾乎不可避免。例如中國龍的形象,在2013年一次針對美、德、俄、印四國民眾的調查中,被接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具有負面含義,這是本土文化實踐者所難以想象的。再比如,很多海外游戲主播游玩到《黑神話:悟空》的普通結局時,看到天命人戴上緊箍,會興奮地認為這是一場“加冕儀式”,這也是文化隔閡的典型案例。
結語
文化實質與文化符號,在經年累月的跨文化交流與融合中,會自發聯結成一套穩固而開放的意義系統。因此,以自身文化視野與價值觀念講述的異域故事,才可能成為具有言說文化主體性價值的作品。從二次元游戲被引進國內市場,到中國游戲廠商自主研發二次元游戲,所經歷的正是“二次元文化”這一意義系統重組的過程——這既是“本土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世界化”的過程。在信息發達的當今時代,一個文化集體的“自我”所面對的不再是零星幾組與“他者”的關系,而是由“他者”所構成的世界,以及蘊藏其中的盤根錯節的文化與意義網絡。如果嚴守文化符號的“純潔性”,簡單將跨文化交流視為文化主體性的單向宣傳或話語權爭奪,或可在一時帶來不知其詳的擁躉,但對于需長久耕耘的中華文化國際形象打造而言,或許會適得其反。海面上的冰山會隨氣候風蝕、動物活動而變換形態,正如在新媒體時代不斷漂移著的能指。對于特定的社會集體而言,認清文化的實質,在文化交流以多元符號系統衍生并闡釋新的意義,才是文化與文化生產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
[作者李匯川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青少年社科研究工作室首席專家,數字游戲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
--------------
澎湃城市報告,一份有用的政商決策參考。
由澎湃研究所團隊主理,真問題,深研究。用“腳力”做調研,用“腦力”想問題,用“筆力”寫報告。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