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年度閱讀︱張翼:信息超載的時代,如何信而不狂?
相對主義,也就是對于那些不容置疑的傳統規范的解構,曾經被看作是一場大解放。然而,現代性在給予個體以往難以想象的大量選擇與機會的同時,卻也帶來了所謂“選擇之苦”(Qual der wabl)。正如彼得·伯格和安東·澤德瓦爾德在《疑之頌:如何信而不狂》(商務印書館,2012)中所言,選擇已然成為一大重負,使個體以“一種懷舊般的心情回眸過去曾有過的絕對性,或是尋找新的絕對性,以便從現代條件下的多樣選擇之中解脫出來”。從“今天中午吃什么”到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選擇,許多人為了避免在信息超載的情況下疲于決斷,最終投身于各類“原教旨主義”所提供的簡單而不容置疑的答案。他們組成自己的封閉圈子并筑起隔絕信息的壁壘,近乎癲狂般只信仰自己愿意相信之事,此之謂“既信且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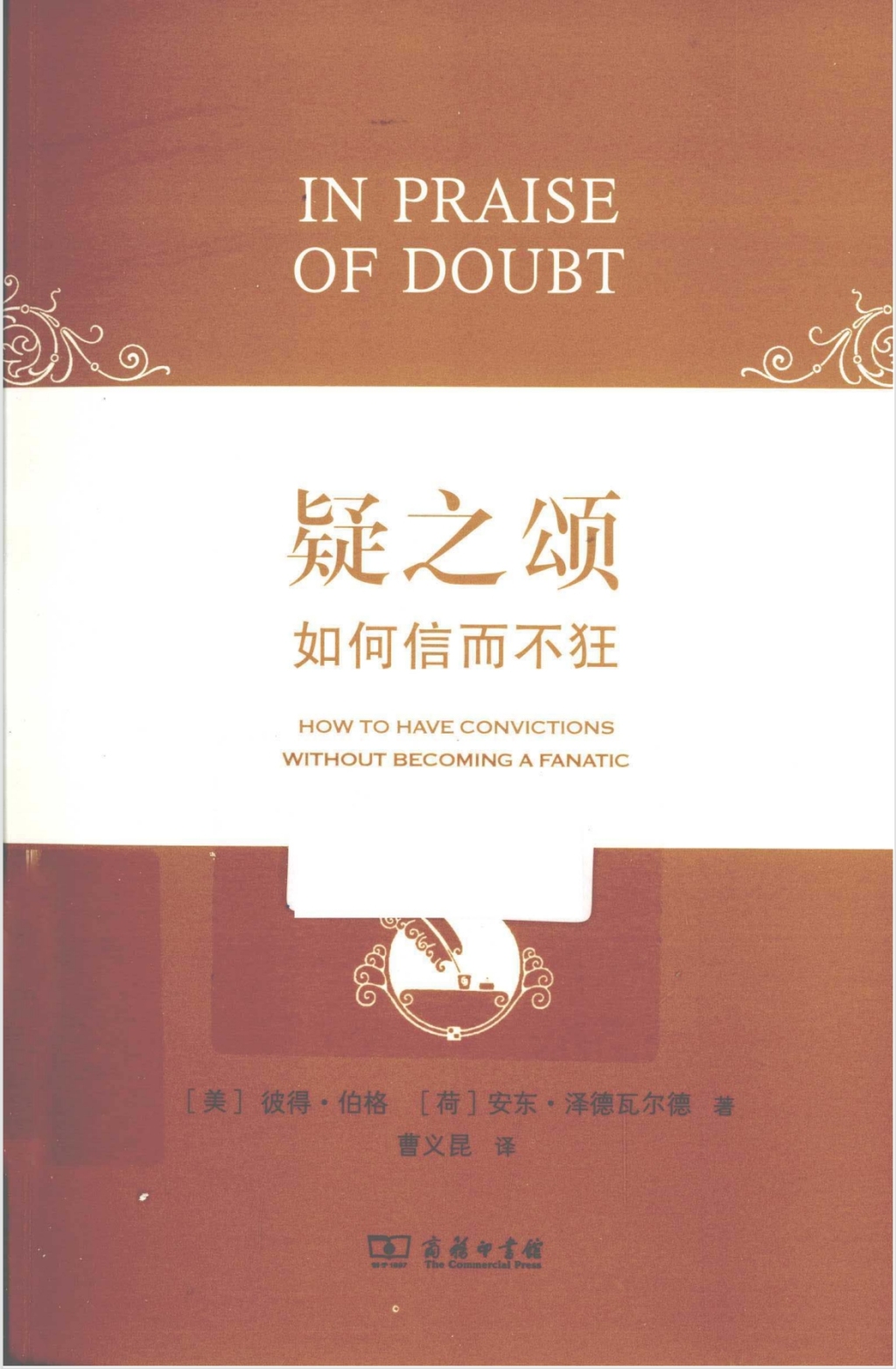
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缺乏理性”來指責這些“狂信者”,因為他們的選擇其實是針對現代性沖擊的反應,正如埃德蒙·柏克德的《法國大革命反思錄》(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所代表的現代保守主義,是針對法國大革命激進主義的反應。他們所拒絕的,恰恰就是現代性中無處不在的“理性的傲慢”。他們回眸過去的愿望,不僅僅是保守或反動者的一廂情愿,甚至在政治光譜的最左側都能找到奇特的共鳴。2024年7月份過世的著名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就在他的許多作品中表達了對于理性主義的懷疑態度。他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中總結了理性主義指導下的大規模社會改造造成災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理性主義在借助官僚體系的工具改造自然和社會時,會傾向于用標準化、目標績效等等“清晰性工具”簡單化社會治理。這種做法實際上忽視了復雜系統中諸多可見或不可見因素的相互作用,就像是那些整齊劃一的人造森林最終會因為缺乏整體生態系統的支持而失敗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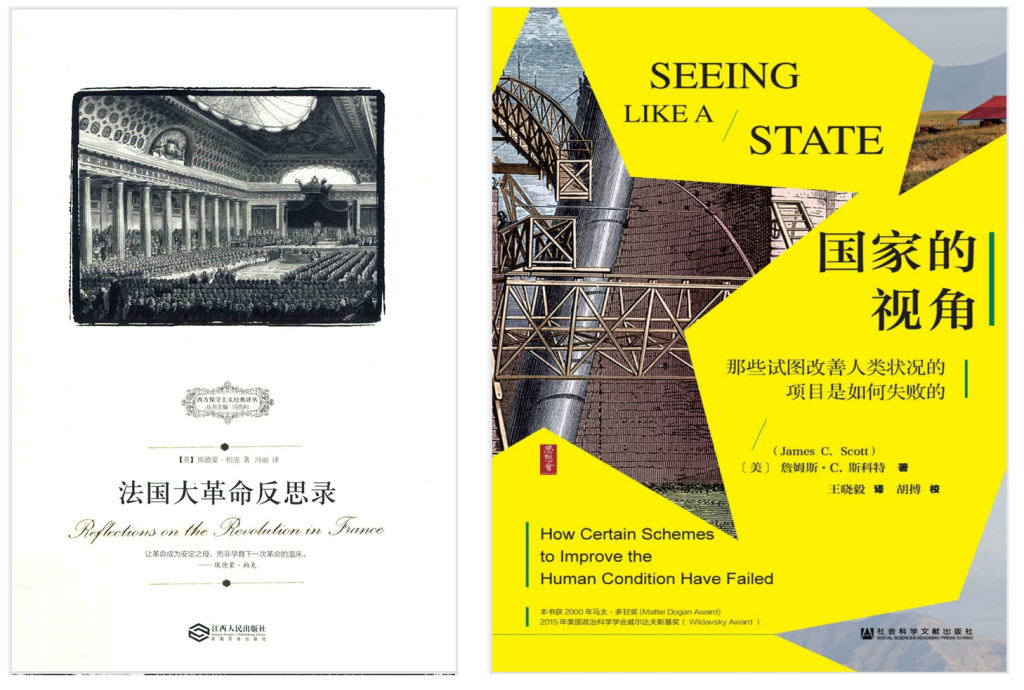
理性主義者總是過高地估計技術進步帶來的控制力,一個生動的例子就來自南美小國智利。伊登·梅迪納的《控制論革命者:阿連德時代智利的技術與政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描述了發生在這個國家的一場失敗的技術烏托邦實驗。控制論技術脫胎于二戰中的軍事技術,并成功運用于企業生產。左派政府阿連德在智利掌權之后就邀請了英國學者斯塔福·比爾,準備在智利推行“Cybernetic項目”。這個項目旨在利用當時最新的計算機技術和控制論建立起對于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和社會管理的實時監控,并施加即時的管理。阿連德的技術狂想很快就讓智利陷入混亂,就客觀原因而言,1970年代計算機技術的不成熟和美國的干預是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更本質的問題在于,在國家這種層面的復雜系統中,有太多非理性的決定因素,這被稱之為“黑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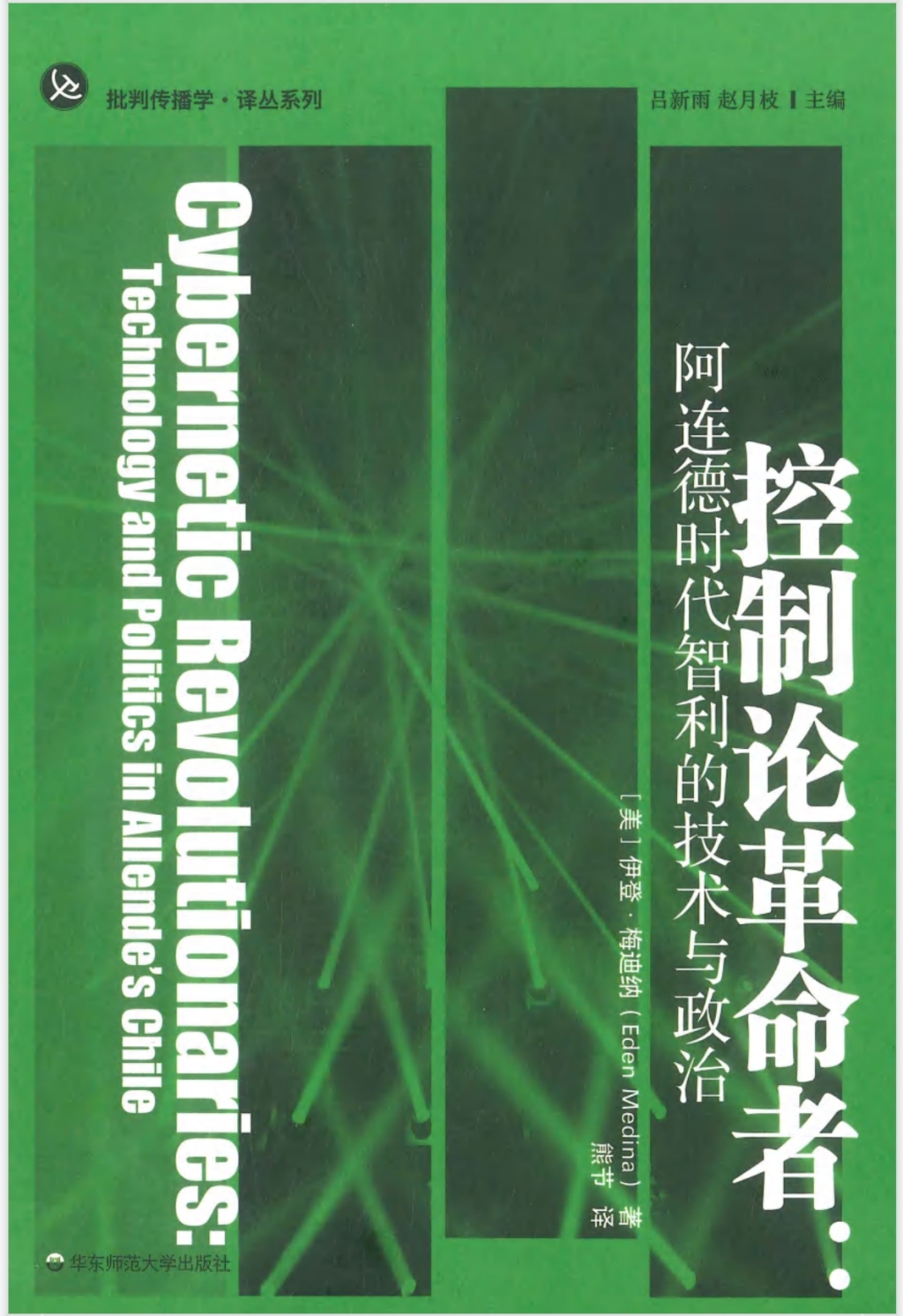
黑箱過程并非意味著混亂和隨機,它是一種不同于理性的知識和決策模式。如果回到斯科特的論述,他將其稱之為“米提斯”(metis)知識。“米提斯”不同于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知識,后者往往是抽象的、普適的,擁有明確的界定并通過邏輯性語言清晰表達。“米提斯”則是具體的,需要語境的,甚至其本身就是模糊而曖昧的、難以言傳的“默會知識”。如果簡單地理解二者的關系,就像是一種語言的語法和現實中我們使用的口語一樣。理性主義者太過重視“語法”的威力而試圖用其糾正我們日常生活中“錯誤百出”的口語表達,但這種做法往往事與愿違,就好像是營養學家雄辯的數據和理論并不能決定一個人的飲食偏好,只有他的妻子在日積月累的生活中才能摸清他喜愛的口味。艾約博在《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就講述了此類“米提斯”知識在夾江造紙工業中的重要性,那些隱藏在社會語境之下的管理技藝在現代主義政權眼中只是“落后的迷信”,但事實證明,國家雄心勃勃的介入最終導致的是嚴重的災難,類似的故事在斯科特的書中可謂不勝枚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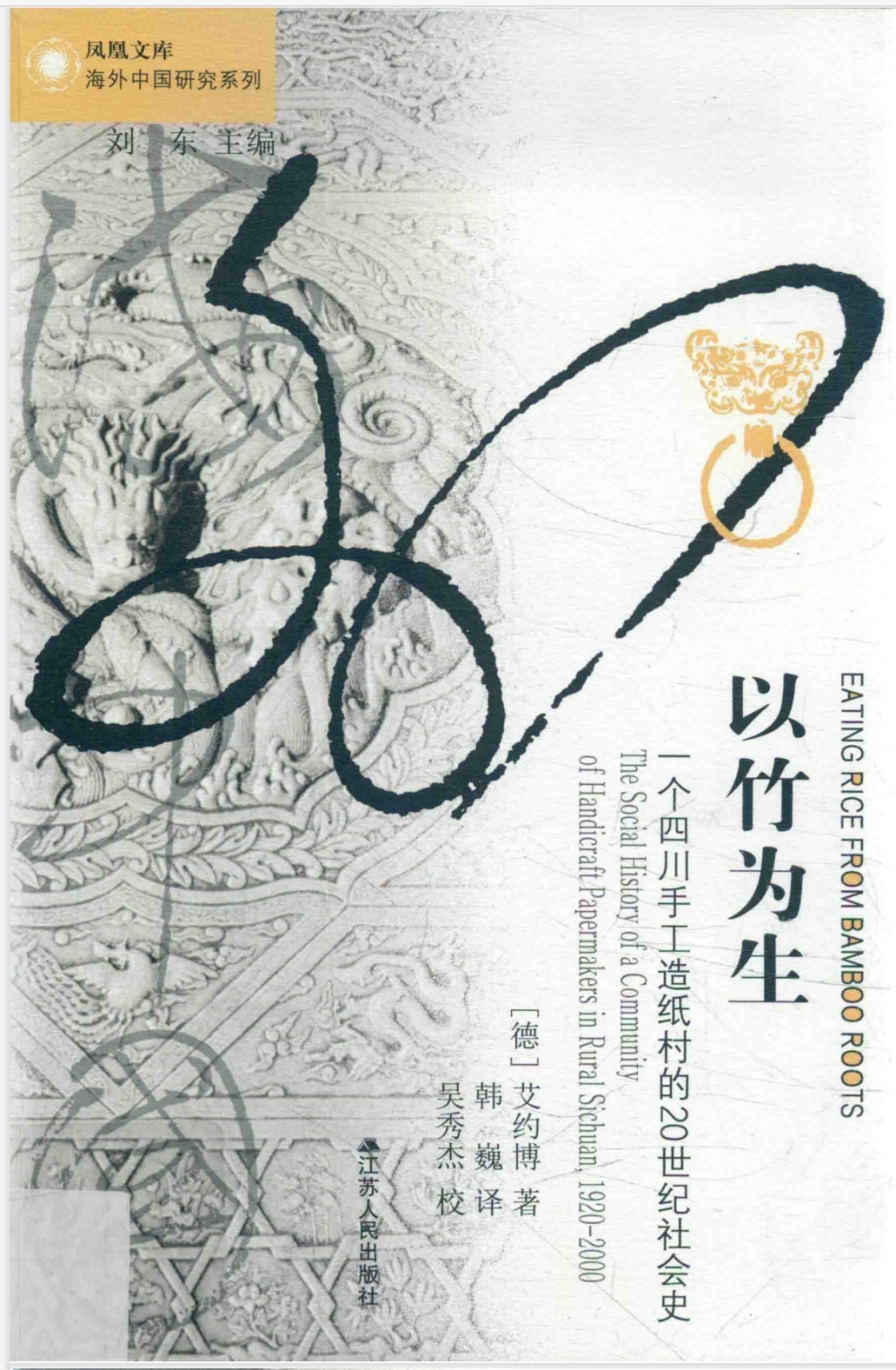
斯科特進一步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傳統和韌性足夠強大,那么或許對于官僚主義的強制就能夠采取比較有效的抵抗。但是在南美這樣社會相對于國家并沒有足夠力量的地帶,類似阿連德智利這樣的烏托邦主義實驗就非常盛行。同樣的例子還包括像巴西利亞這樣的人造城市,斯科特就引用雅各布斯的話說,這是“把視覺秩序等同于功能秩序”,缺乏社區間人與人互動所產生的自發秩序,只會讓這些人造城市充滿令人窒息的“死空間”。然而,在斯科特看來,官僚的理性主義傾向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他在《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2)中,以相當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農業革命對于人類的馴化。即谷物種植技術讓原本敏銳而堅韌的狩獵者變成了瘦弱而順從的農民,而正是后者支撐起整個官僚體制以及文明社會——如果你愿意將其稱之為“文明”的話。那些不愿意接受這類統治的群體,往往如斯科特在《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中所描繪的那樣,逃至贊米亞(Zomia)的深山中,進而被文明社會“發明”為“蠻夷”。那些留下來的,同樣會通過斯科特在《支配與抵抗藝術:潛隱劇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所描繪的雙重話語逃避統治階層的文化霸權,通過“支付恭敬”來保護自己的小團體,直到形勢逼迫他們越界成為公開的反抗者的時刻。這可以看作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弱者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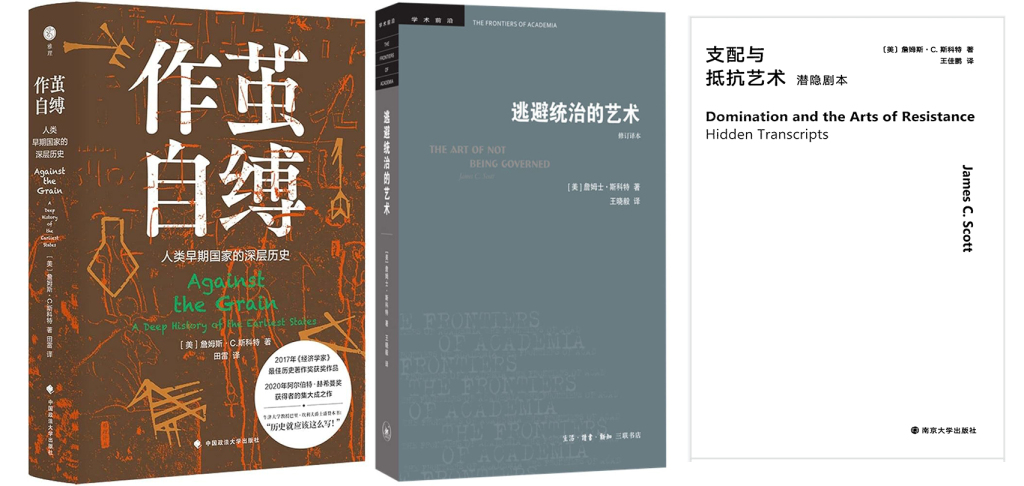
查爾斯·蒂利的《信任與統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從政治類型學和比較學的角度補充了斯科特對于小團體內部話語同統治階層之間的微妙關系。蒂利將共同分擔風險的一群人稱之為“信任團體”。國家為了從這些團體中汲取資源,可以通過強制力、收買或意識形態說服的方式將其排斥、協商或完全整合進體系之中。而那些與國家對抗的團體,也可以通過自我隱藏、尋找作為庇護者的代理人或武裝起來參與掠奪等方式保護自己的資源。彭慕蘭在《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中就有非常有趣的案例,近代魯西北的地主在引進美國棉花后,為了抵抗赤貧階層以“拾荒權”為名進行的掠奪而組織武裝巡邏隊,而在此過程中,地主和佃戶之間的共同利益就構成了人類學家楊懋春在《山東臺頭:一個中國村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中所描繪的鄉村共同體。這種組織方式強化了過去依賴道德經濟維系的弱共同體。高王凌在《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中極具說服力地論證了以“低實收”為主要特點的傳統中國租佃制度如何維系了地主和佃戶之間的微妙權力平衡,揭示了背后的道德經濟運行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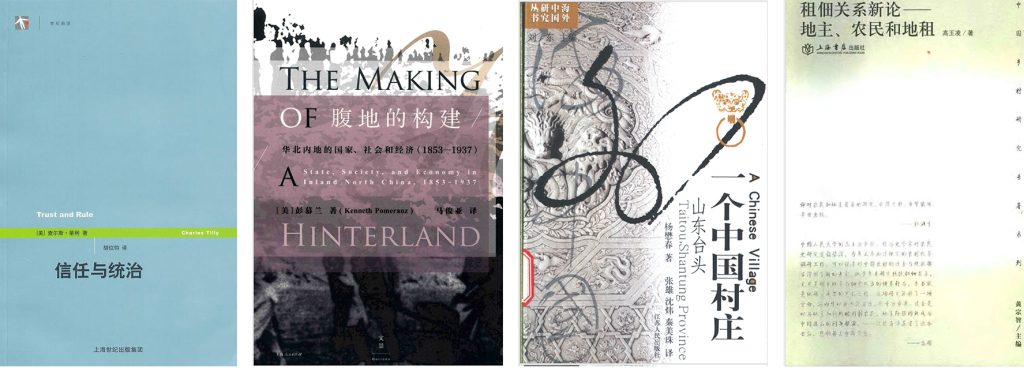
這種共同體和道德經濟不僅是國家權力的目標,同樣也是資本主義試圖瓦解的對象。就最基礎的家庭共同體而言,西爾維婭·費代里奇在《凱列班與女巫:婦女、身體與原始積累》(上海三聯書店,2023)中討論了女性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如何被父權制秩序構建為從屬于勞動力再生產過程的機器的過程,西方近代早期社會中的“獵巫”現象因此有了經濟和社會學意義上的解釋,即通過系統性清除女性中的反抗者而剝奪她們在社會中的組織與行動能力。瓦解共同體的保護以釋放更多的“原子化”的“自由勞動力”是整個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低沉卻刺耳的“低音部”。就算是在“新自由主義”凱旋的21世紀全球化時代,和“自由”截然相悖的各類變種奴隸勞動仍構成全球經濟看不見的“下半截”。凱文·貝爾斯在《用后即棄的人:全球經濟中的新奴隸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就指出了諸如泰國的性奴隸、毛里塔尼亞白摩爾人對黑人的壓迫以及南亞低種姓農民所遭遇的殘酷壓榨,揭示了繁榮的全球化經濟的真正基礎乃是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殘酷剝削。這種剝削是全方位的,是字面意義上的“敲骨吸髓”。斯科特·卡尼在《人體交易》(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中描繪了遍及全球的人體器官市場,包括印度的腎臟村、塞浦路斯的卵子市場、代孕、血液販賣、藥物實驗志愿者(即所謂“職業白老鼠”)等令人觸目驚心的行業內幕。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幾乎所有產業都表現出發達國家“消費”第三世界國家人民身體的共同模式,這樣的場景無疑是殘酷殖民時代的“昨日重現”,就如同馬克弟在《絕對欲望,絕對奇異:日本帝國主義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中信出版集團,2017)中描繪的以“消耗生命”來創造繁榮的偽滿洲國,所呈現出的詭異、血腥、鮮活到令人作嘔的文化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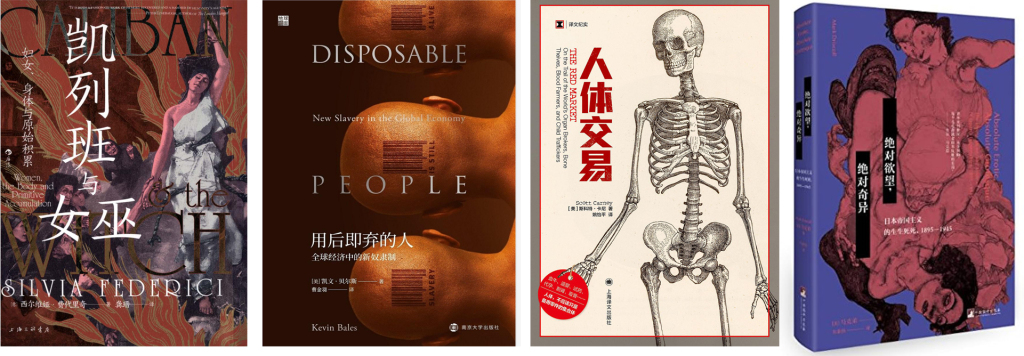
日本帝國的所作所為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在給自己注入了“現代化”的疫苗之后產生的抗體與排異反應的混合。日本盡管一定程度上被承認為列強,但正如真嶋亞有在《“膚色”的憂郁:近代日本的人種體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所描繪的那樣,無論日本人如何用勝利證明自己,卻從來不能真正擺脫低人一等的感覺。因此他們決定用“光鮮的有色人種”作為新的自我定位,用以團結國民和其他殖民地的受壓迫者,共同反抗英美主導的國際體系。為此,日本人在近代民族建構理論中引入了“混合人種說”來增強其帝國的包容性與凝聚力。小熊英二在《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譜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中討論了諸如“日鮮同源”等理論在日本殖民主義理論中的作用。此類理論對于總體戰動員體制極其重要。黑澤文貴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陸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中指出,大正時代日本政治的民主化實際上是最終走向1940年軍國主義體制的重要前提。這種政治路線完全脫離了伊藤之雄在《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所描繪的明治時代日本元老政治帶來的穩定與深謀遠慮,最終為日本的戰敗埋下伏筆。而隨著日本的戰敗和帝國的解體,“混合人種說”也就偃旗息鼓,關于日本乃“單一民族”的神話最終成為如今日本社會的主流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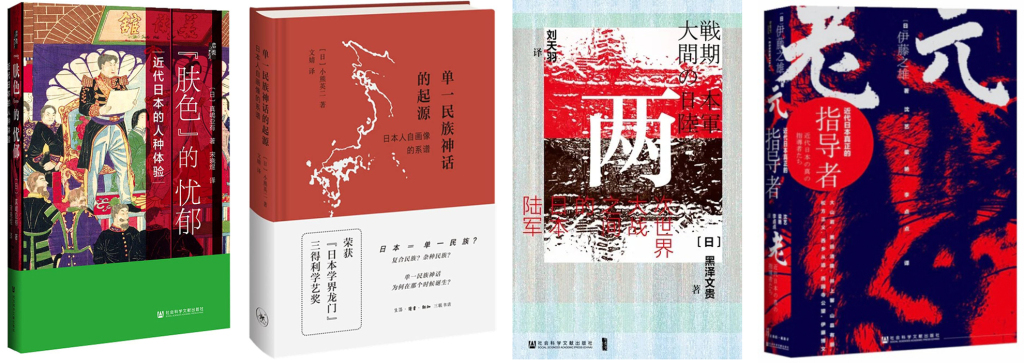
此類民族構建的陣痛與轉型在西方社會同樣漫長而曲折。以美國為例,在獨立戰爭中,就有像本尼迪克特·阿諾德這樣從大陸軍背叛到英國人陣營中的著名案例。納撒尼爾·菲爾布里克的《無畏的雄心:喬治·華盛頓、本尼迪克特·阿諾德與美國革命的命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就講述了這一當時地位和華盛頓不相上下,卻很少被歷史提及的人物。為了塑造美國的新認同,英國就成為最重要的“他者”,于是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就讓位于戰爭的“霍布斯時刻”,馬婭·亞桑諾夫的《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國與大英帝國的東山再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就討論了新生共和國對于親英派的清算與驅逐,而這些逃離美國的人因此散落于世界各地,成為后來英聯邦國家的重要來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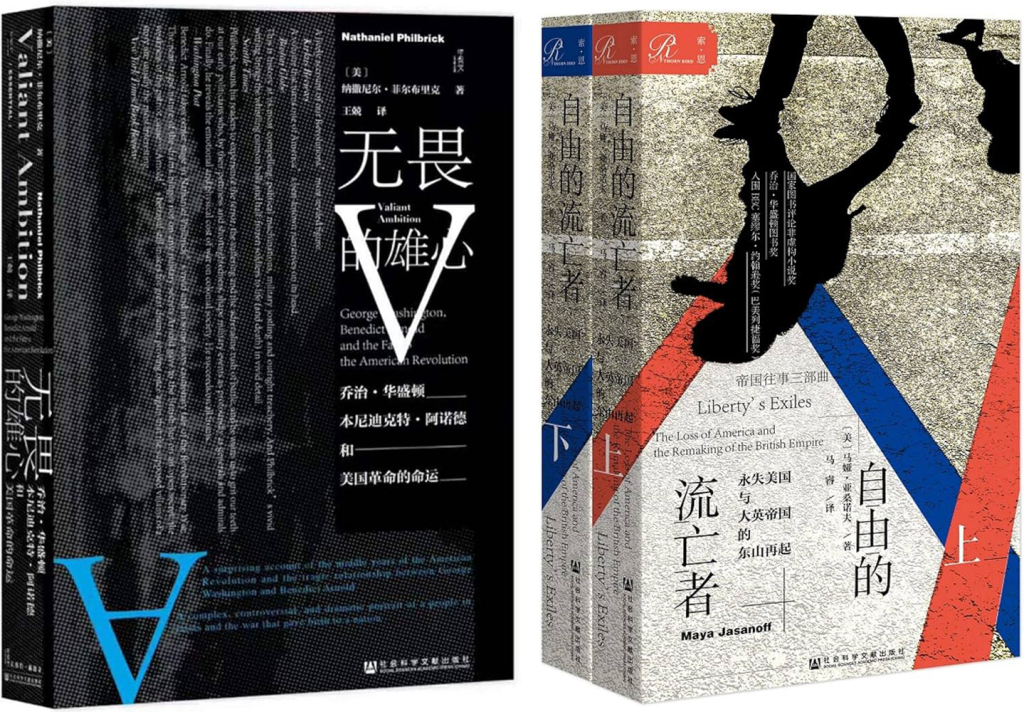
亞桑諾夫的作品讓我們意識到,美國早期的政治文化與如今許多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理念相去甚遠,這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些政治理念本身的歷史性。邁克爾·舒德森盡管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者,但是他的研究卻十分生動地詮釋了美國政治制度與公民社會在不同時代的轉變。在《好公民:美國公共生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中,舒德森強調,美國建國初的公民社會與如今的情況迥然不同。例如在新英格蘭,虔誠的宗教團體在擁有強大自制能力的同時卻對內部成員的個體意見嚴格壓制;在南方的種植園,那些地主鄉紳繼承了英格蘭的等級制度和恭順文化,這都使遲至19世紀的美國選舉都更類似于粗魯的狂歡節和政黨分贓的儀式。美國國父們對于黨派、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警惕則表現為《懲治叛亂法》頒布后針對報刊編輯的迫害,以至于麥迪遜高呼“自由的共和國不會被誹謗擊倒”。即使到了進步主義時代,那些高舉自由主義的城市中產階級,也通過文化水平測試和限制移民的公民權來排斥有色人種的政治權力,這一問題在斯蒂芬·默多克的《智商測試:一段閃光的歷史,一個失色的點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和李漪蓮《亞裔美國的創生:一部歷史》(中信出版集團,2019)有更詳細的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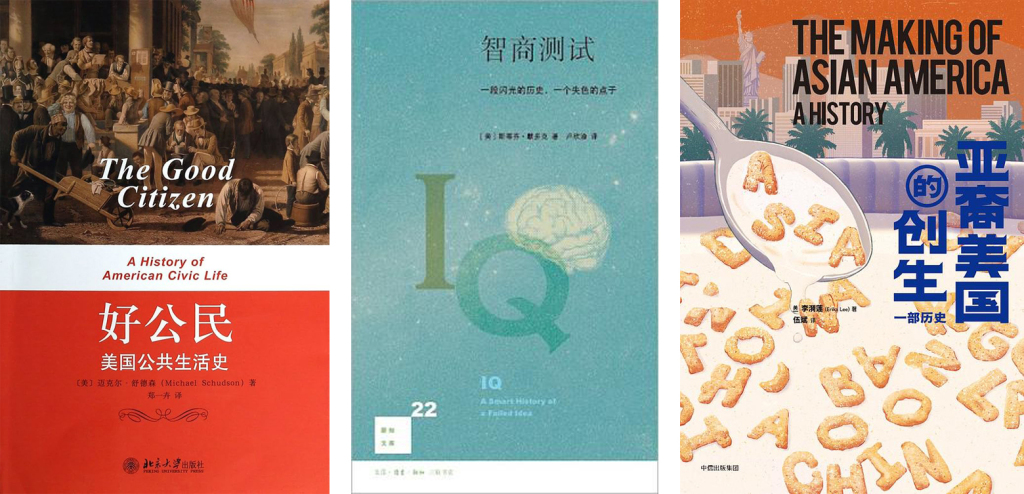
直到二戰之后的民權運動興起,許多如今看來司空見慣的理念才最終成為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的共識。然而,這些共識的形成同樣經歷了漫長的社會博弈,正如舒德森在《知情權的興起:美國政治與透明文化(1945-1975)》(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一書中精彩地指出,“開放不是民主的金科玉律,它只是一種次要的或程序上的道德原則。如果誠實的意思不是不撒謊,而是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那么無論對于誰,都不可能總是最完美的策略”。美國社會實際上是通過諸如商品成分公開運動這樣經濟層面的實踐,以及諸如《國家環境政策法》和《信息自由法》等目標較小但卻幫助公民形塑聯邦政府行為模式的“超級成文法”,才最終讓“讓我們坦誠一切”成為普遍被人接受的原則。盡管媒體始終參與著美國社會的演進,但舒德森在《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和《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華夏出版社,2010)中提醒讀者,新聞作為一個行業,它的根本目的永遠是盈利。美國早期以黨派為主要金主的報紙根本不存在客觀性,充滿了鮮明的個人色彩與政治偏見。后來面向更廣泛讀者存在的報紙,才為了迎合最大多數人的需要,開始標榜“客觀性”,并最終成為新聞行業的一種自律規范。這種自律規范盡管保證了主流媒體的嚴謹性,但也一定程度上通過制造“偽事件”和設置議題來壓制多元性的表達。那些被忽視的聲音,最終就通過類似特朗普這樣的人物使自己的聲音重新被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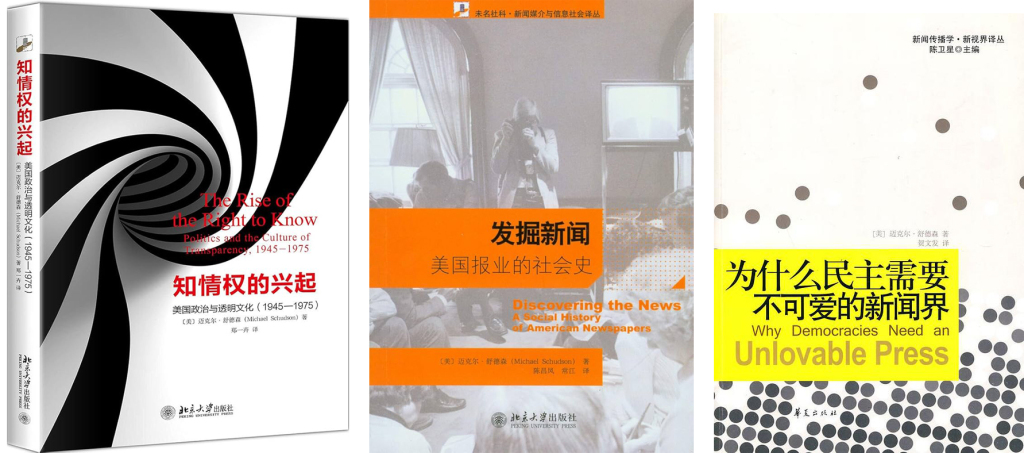
當然,特朗普的出現同樣可以視作美國的在全球秩序中的帝國主義作風倒灌進國內引發的反應。盡管美國在探索太空和新邊疆的努力尚且保存著漢普頓·塞茲在《冰雪王國:美國軍艦珍妮特號的極地遠征》(科學社會文獻出版社,2017)中所描繪的那種可貴的企業家精神。但是諾埃爾·毛雷爾的《帝國陷阱:美國政府如何保護海外商業利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20)和埃倫·R. 沃爾德的《沙特公司:沙特阿拉伯的崛起與沙特阿美石油的上市之路》(中信出版集團,2019)則同樣揭示了美國在維護海外利益中的帝國主義作風,并最終發展為克勞德·德萊斯在《美國國家安全局》(中信出版集團,2019)中所描繪的令美國的敵人和盟友均感不安的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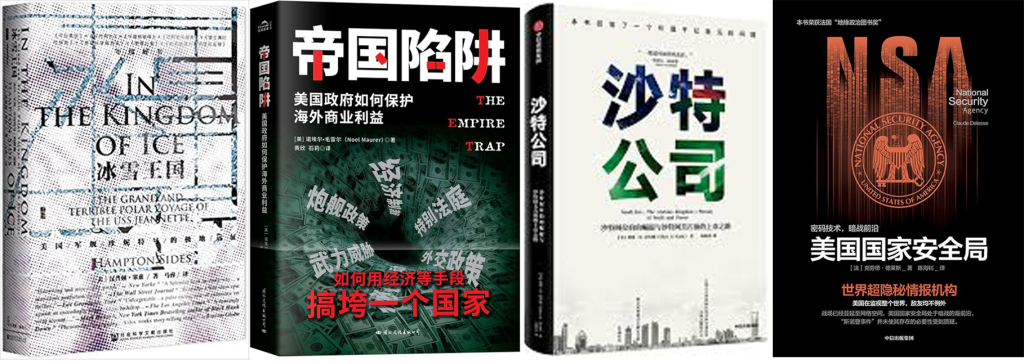
美國的秩序總是夾雜著理想主義和現實政治,正如在西班牙,亞當·霍赫希爾德的《西班牙在我們心中:西班牙內戰中的美國人,1936-193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描繪了無數美國志愿者為了西班牙共和國的事業而英勇作戰的故事;但在斯坦利·G. 佩恩與赫蘇斯·帕拉西奧斯合著的《“愛國的”獨裁者:佛朗哥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中我們同樣看到美國為了冷戰利益而扶植獨裁者佛朗哥的做法。當然,佛朗哥作為邊緣地帶的獨裁者,可以通過審慎的左右逢源安穩統治,但諸如希特勒這種位于主要國際秩序挑戰者地位的獨裁者,他們實際上并無多少選擇。克勞斯·費舍爾的《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譯林出版社,2016)可謂卷帙浩繁,相當清晰而詳盡地梳理了納粹德國興起的歷史脈絡與其內部權力的運行機制。伊迪絲·謝費爾的《阿斯伯格的孩子:自閉癥的由來與納粹統治》(上海三聯書店,2022)則從另一方面討論了納粹德國時代的“診斷式統治”。阿斯伯格以其虔誠的天主教信仰,一方面受到納粹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為從未親自參與安樂死那些自閉癥兒童的行動而逃脫懲罰,它所做的不過是挑出那些無法和“偉大祖國”建立聯系的自閉兒童,并把其中的“棘手病例”交給臭名昭著的耶克爾柳斯醫生,而后者則是安樂死計劃的主要執行者。正如作者所言,阿斯伯格的行為比任何顯要人物更能反映出第三帝國惡行的本質。他既不是堅定的殺手,甚至也不曾直接介入謀殺的過程。他們不具備蓄意謀殺的堅定信念,然而卻是他們使帝國謀殺機制的運作成為可能。這一點同樣適用于卡爾·施米特,貝恩德·呂特爾斯撰寫的《卡爾·施米特在第三帝國:學術是時代精神的強化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描繪了這位曾鼓吹納粹主義的政治學者因為政治斗爭失敗而失勢,但最終卻因此逃脫了審判的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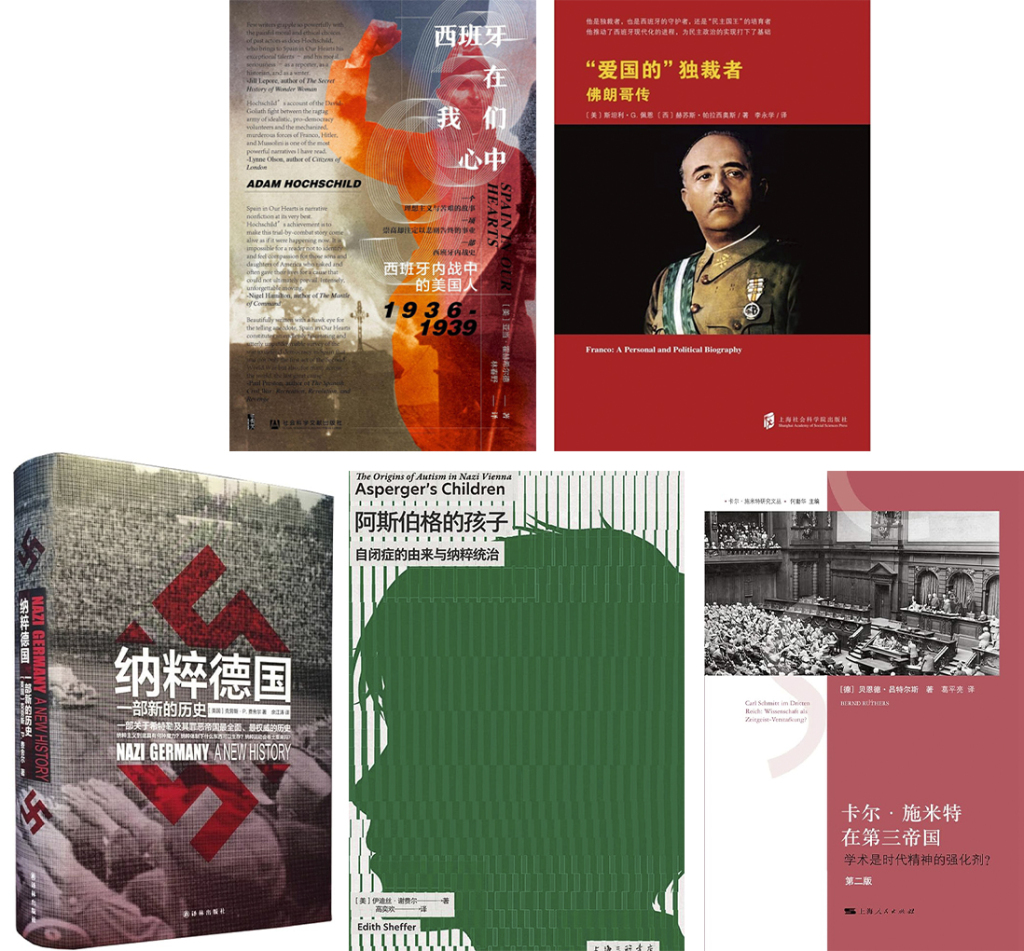
納粹最后的失敗讓這些事實得以大白于天下,并經受歷史學家的審判。但對于正在發生的事,身處其中的我們又該如何鑒別?我想在最后推薦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的《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了分析和檢驗信息重要性的六步法則。①確認自己接觸的到底是什么類型的信息;②檢驗新聞的完整性,避免斷章取義;③了解信息源及其可靠性;、④了解支持論斷的證據;⑤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了解干擾性證據,針鋒相對的觀點和合理的懷疑與反駁;最后⑥判斷這件事對自己的重要性。我想,在信息超載的時代,這些辦法和上述的思考維度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在前途未卜的時刻找到最有前途的路徑。理性雖然并不能指導一切,但確是一劑清醒劑,它讓我們仍有所堅信,但卻避免瘋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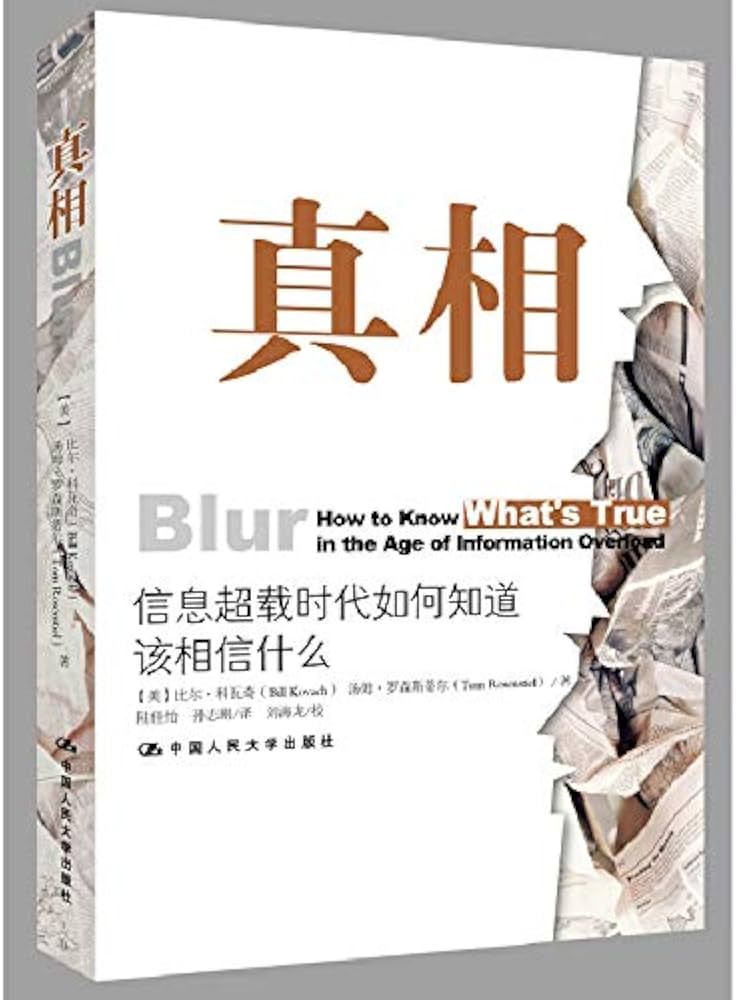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