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為什么大國都在追求技術自主
【編者按】技術競爭已經成為當今時代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政治是主人,技術是仆人。“生于憂患”的邏輯塑造著大國競爭史與世界技術史。本文摘自《大國權力轉移與技術變遷》,黃琪軒著,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9月版。原標題為“大國的技術進步模式與技術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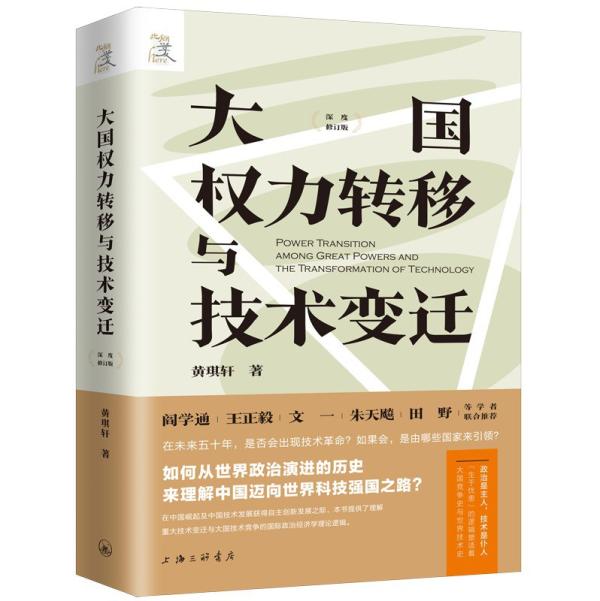
本書通過對大國權力轉移與技術變遷的研究,展示了大國技術進步模式的特殊性。有研究就指出,戰爭是與一國的國際等級相關的活動,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等級中的序列越高,它越可能卷入戰爭。換句話,大國之間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大于小國。即便在二戰后大國之間維持了持久的和平,世界政治日益呈現出“平靖進程”,但大國間的競爭仍在繼續。本書也試圖展示,大國技術進步的模式有著相當大的特殊性,大國更強調技術的自主性、技術的覆蓋面等。
(一)大國技術進步模式不同于小國
……就技術進步而言,國家面臨三種技術發展戰略: 其一,大而全的技術進步模式。這個模式需要該國在各個方面建立自己的科學技術基礎。我們分析的美國、蘇聯以及崛起后的日本都是這一模式。在大國權力轉移時期,這樣的技術進步模式尤其明顯。其二,小而精的模式,即遵循專業分工的模式。這種模式要求科學與技術往專業化的方向發展,要求該國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限的幾個領域。這是典型的小國技術進步模式。這個模式是以北歐小國,如瑞典、瑞士、荷蘭等為代表的。其三,技術依賴模式。即依賴進口技術,再進行本土的技術改進。二戰后,日本曾經有一段時期采納了這一模式。改革開放后,中國也曾積極從西方引進技術。這三種模式明顯體現了:不同等級的國家,技術進步模式有著明顯的分野。我們可以看到,在技術的產業分布上,大國往往強調技術的全面覆蓋性,以降低對他國的技術依賴;而小國則更強調技術的專業分工,更加專注于比較優勢的發揮。大國的技術國際分工程度遠遠不如小國;大國會投資很多違反其比較優勢的技術領域,以確保國家安全。
這種差異并非富裕程度可以解釋。富裕的小國對技術投入的絕對量與相對量也遠遠落后于大國。人均GDP在世界前列的北歐小國,在技術投資上的排名遠遠落后于其經濟排名。從國際數據來看,人均收入相當高的加拿大、瑞典、瑞士、挪威、丹麥、芬蘭、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它們在技術研發中屬于技術研發的中小國家,投資遠遠跟不上其人均收入和國民財富。而大國對技術的投人則可超前于其經濟排名。由于迅速崛起的國際地位,蘇聯在經濟績效并不十分靠前的時候,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投入。
如果一國的國際地位發生變化,其技術選擇也會有相應改變。外來技術并非公共品,領導國常常會通過技術出口限制或者技術轉讓來應對競爭者,扶持支持者。隨著日本的崛起,日本開始著意于擺脫對領導國美國的技術依賴。在政府的資助下,日本科學和技術進步開始覆蓋到廣闊的領域。當前,中國致力于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依托“新型舉國體制”解決“關鍵核心技術”供給問題,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在不斷拓展自身的技術寬度與深度。因此,我們可以說:并不是經濟發展了,該國技術自主性的訴求就會上升。大國和小國對自主創新的強調有很大差別。與小國相比較,大國自主創新的訴求更高。而與其它時期相比,在權力轉移時期,大國隊伍中的領導國與崛起國自主創新的訴求更高。
概括地講,與小國相比較,大國更加強調技術的自主性,其技術涵蓋面更廣泛。不過,盡管大國對技術自主性的訴求系統地高于小國,大國技術自主性的意愿仍然會有波動。有時候,大國出現技術國際主義的浪潮,有時候又出現技術民族主義的返潮。為何有時候大國偏好于通過國際市場購買技術,有時候又轉向自主研發呢?大國的技術進步為何在技術的經濟現實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二者之間轉換呢?
(二)權力轉移影響下的技術觀與發展模式
從國際關系看技術問題有經濟現實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兩種視角。技術的經濟現實主義構造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的主要行為體是享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追求權力最大化。只有如此,它們才能確保在弱肉強食的國際叢林留得生存之地。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為追求國家生存,斗爭永不停歇。國家之間的競爭與沖突盡管可能通過各種辦法來加以應對,但卻難以一勞永逸地消除。長期來看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持續影響各國的政治經濟。在經濟現實主義的視角下,即便是國家間的技術交易也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國家的技術是其國家政治軍事權力的重要支柱:一國的對外經濟戰略可以促使他國行為的改變。如果在技術貿易中,對手取得了更多的相對收益,或者一國過于依賴于對手,那么對國家安全是相當危險的。因此,經濟現實主義者自然會過多考慮相對收益,更加關注擺脫對對手的依賴。從經濟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技術不能依靠貿易,而國家需要掌握自主的技術經濟自由主義則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技術的經濟自由主義往往認為,在一個共同的法律框架下,理性的個人會實現分工。因此根據要素稟賦,有的國家自然集中于生產高技術產品而有的國家則可能集中于生產勞動密集型的低端技術。雙方可以通過國際交換,實現了經濟收益最大化。正是國際技術貿易,帶來了國際的和諧。
我們看到,有時國家強調技術自由主義,重視技術國際主義;而有時國家則強調技術的現實主義,重視技術的民族主義。大國有時愿意通過國際市場購買技術,而有時則強調自主研發。不同的技術觀本身沒有褒貶,它們往往是一定國際權力格局下的產物。本書也試圖展示:國際政治所處的時期有所不同,大國在世界政治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其奉行的技術主義也有所不同。在權力轉移時期,領導國與崛起國雙方會更多考慮技術貿易中的相對收益,會更避免對對方的技術依賴。因此在這一時期,技術的經濟現實主義、技術民族主義更加盛行。由于技術路線的變化,需要國內政治經濟體制做出相應的調整來適應這種變化。因此,在權力轉移時期,大國的技術發展模式,乃至整個發展模式會出現相應的變化來適應國際形勢的變遷。當前,中國政府日益強調“新型舉國體制”、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調“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都離不開變化的國際形勢,即“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技術發展模式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如一些意識形態更傾向于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后發展國家更多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強組織力。而我們對大國技術變遷的研究展示,大國間的權力轉移會導致其技術觀念與發展模式的改變。在大國的權力轉移時期,領導國與崛起國雙方會減少對對方市場與技術的依賴,更加強調獨立自主的發展模式,更加強調國家的干預。如二戰后,美蘇兩國間的權力轉移就促使兩國技術發展模式做出了相應調整。所以我們才看到:此時,即使是以市場經濟著稱的美國,面臨蘇聯的迅速崛起,也形成了一個比較奇特的軍工復合體,而其政府對技術進步的干預也有顯著的擴張。比較明顯的干預方式是對研發的資助與對高端技術產品的采購。當前,不僅中國政府在推進“新型舉國體制”建設,美國也通過《芯片和科學法案》等系列法案與政策,加強了政府對技術進步的介人。2023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被稱為“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就公開質疑“市場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并強調對“政府引導的產業政策與創新政策”的高度認同。因此,大國的技術觀念、技術發展模式,乃至發展模式,尤其是政府干預強度與對外依存度,受到大國權力變遷的顯著影響;而大國權力轉移不僅會影響國內發展模式,還可能會影響到全球化的進程。
我們都知道,全球化受到國內政治的顯著影響。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如果大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是全球化的重要內容的話,那么全球化的拓展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如前面我們所展示的那樣,領導國與崛起國都是全球政治與經濟的重要行為體。在國際政治中,兩國行為舉足輕重。全球化的進程就離不開世界政治的大國合作。但是在權力轉移時期,雙方的這種合作是有困難的。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在蘇聯迅速崛起的時期,領導國美國和崛起國蘇聯各自建立一個封閉的貿易體系,嚴重阻礙了全球化在“全球層面”的推進。而當崛起國蘇聯失去權力增長優勢的時候,全球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進展。從日本崛起時期美日之間日益顯著的貿易摩擦以及迅速崛起的中國面臨美國制造的諸多難題,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在撤退的端倪。時至今日,“中美兩國政府在全球化問題上調換了立場,中國提倡推動全球化,而特朗普政府則采取了反對全球化的政策”。因此,可能的推論是:大國權力轉移會重新塑造大國的技術觀、技術發展模式乃至全球化的進程。當前,面臨去全球化逆潮,中國領導人相繼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與“全球文明倡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崛起的中國在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