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她們不是嘮叨,只是受夠了:不被看見的勞動永遠沒完沒了
母親節那天,我要了一份禮物:房屋清掃服務。具體來說,是清掃衛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戶的費用也合理的話,那就一并清洗。對我來說,這個禮物與其說是打掃屋子,不如說我終于可以擺脫家務責任一次。我不必打電話向多家家政公司詢價,不必研究及比較每家公司的服務質量,不必付款及預約清掃時間。我真正想要的禮物,是擺脫腦中那個老是糾纏著我的情緒勞動。至于家里打掃后干凈如新,那不過是額外的收獲罷了。
我丈夫等著我改變主意,換成一份比房屋清掃服務更“簡單”的禮物,例如他可以上亞馬遜一鍵下單的東西。但我堅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親節前一天終于拿起預約電話,但詢價后覺得太貴了,信誓旦旦地決定自己動手。當然,他還是給了我選擇的機會。他先告訴我房屋清掃服務的高昂費用(因為我負責管控家用開支),接著滿腹狐疑地問我還想不想叫他預約那個服務。
其實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臉書請朋友推薦幾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電話去詢價,體驗一下這件事要是換我來做,勢必得由我來承擔的情緒勞動。我想找家政公司來徹底打掃已經有一陣子了,尤其自從我自由職業的工作開始大幅增多,導致我分身乏術后,這個愿望更強烈了。之所以遲遲沒做,部分原因在于不自己做家務會讓我感到內疚,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不想花心思去處理“請人來打掃”的前置作業。我很清楚事前準備有多累人,所以才會要求丈夫做,把它當成禮物送給我。
結果母親節那天,我收到的禮物是一條項鏈,我丈夫則躲去清掃衛浴,留下我照顧三個孩子,因為那時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亂。
他覺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給我一個干凈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動手清洗。所以當我經過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襯衫、襪子收好,卻絲毫沒注意到他精心打掃的衛浴時,他很失望。我走進衣帽間,被一個擱在地板上的塑料儲物箱絆倒——那個箱子是幾天前他從高架子上拿下來的,因為里面有包裝母親節禮物所需的禮品袋和包裝紙。他取出需要的東西,包好他要送給母親和我的禮物后,就把箱子擱在了地板上,儲物箱就變成礙眼的路障,(至少對我來說)也是看了就生氣的導火線。每次我要把換洗衣服扔進臟衣簍,或是去衣帽間挑衣服來穿時,那個箱子就擋在路中間。幾天下來,那個箱子被推擠、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沒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歸位,我必須從廚房拖一張椅子到衣帽間,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實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為箱子心煩時這么說。
這么明顯的事情。那個箱子就擋在路中間,很礙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舉起來、放回去,不是很簡單嗎?但他偏偏就是繞過箱子,故意忽視它兩天,現在反而怪我沒主動要求他把東西歸位。
“這正是癥結所在。”我眼里泛淚,“我不希望這種事還要我開口要求。”
這就是問題所在。一個顯而易見的簡單任務,對他來說只是舉手之勞,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動完成?為什么非得我開口要求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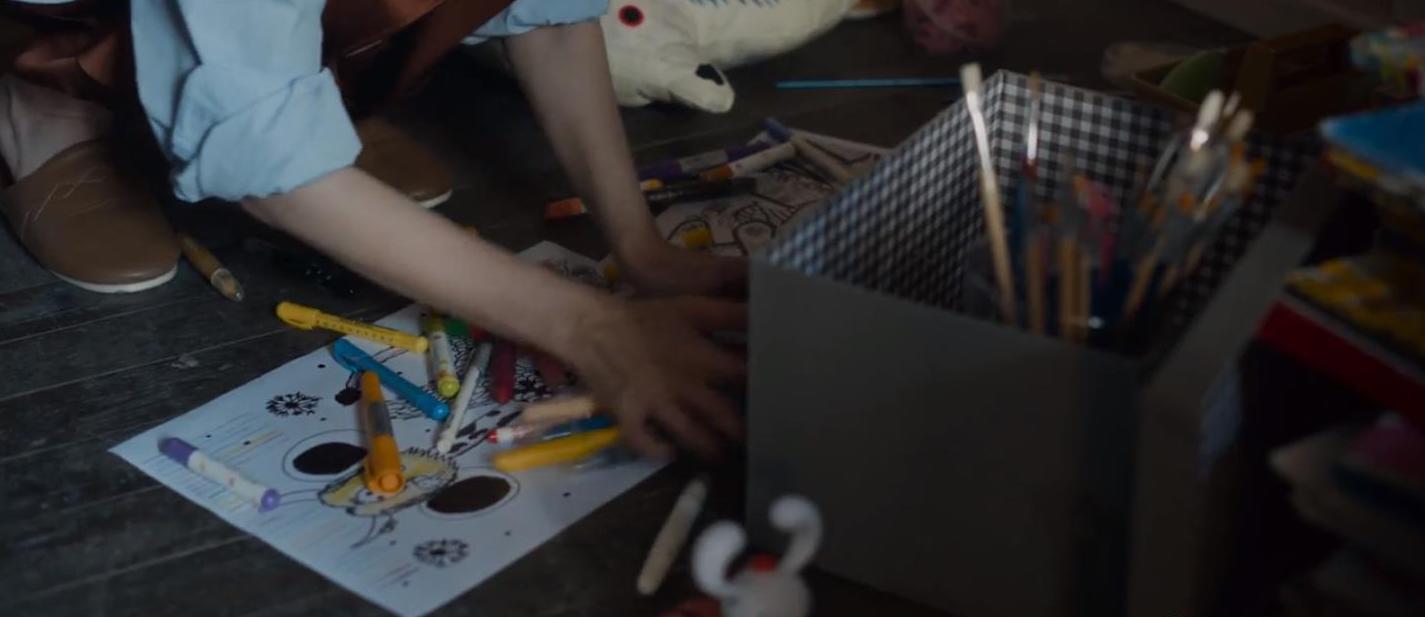
這個問題促使我含淚據理力爭。我想讓他了解,為什么當一個家務管理者,不僅要發現問題、分配家務,還得若無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為什么我會覺得自己承擔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責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負擔。有事情需要處理時,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選擇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別人來做。家里牛奶沒了,我得記在購物清單上,或是讓丈夫去超市購買,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衛浴、廚房或臥室需要打掃時,也只有我注意到。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細節,往往導致一項任務暴增成二十項。我把襪子拿去洗衣間時,注意到有個玩具需要收起來,于是我開始動手整理游戲室,接著我又看到一個擱在一旁的碗沒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順手洗了碗盤……這種無止境的循環令人煩不勝煩。
家務不是唯一令人厭煩的事。我也是負責安排時間表的人,隨時幫大家預約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辦事項。我也知道一切問題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鑰匙扔在了哪里、婚禮何時舉行及著裝規定、家里還有沒有柳橙汁、那件綠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幾號、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我的腦中存放著五花八門的清單,不是因為我愛記這些事情,而是因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會記。沒有人會去看學校的家長聯絡簿,沒有人會去規劃朋友聚餐要帶什么餐點前往。除非你主動要求,否則沒有人會主動幫忙,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然而當你主動要求,并以正確的方式要求時,又會是一種額外的情緒勞動。在許多情況下,當你委托別人做事時,你需要三催四請,別人聽多了還會嫌你嘮叨。有時,這件事根本不值得你一遍又一遍地以懇切的語氣催請對方(而且還要擔心對方嫌你啰唆),所以我會干脆自己做。有好幾個早晨,我幫女兒把鞋子拿到她的跟前,幫她穿上——并不是因為她不會自己穿鞋,而是因為我不想同一件事連續講十幾次,講到我發飆大吼快遲到了,她還沒把鞋子穿上。我希望丈夫打掃院子,但又想維持婚姻和諧時,必須注意自己講話的語氣,以免言語間流露出些許的怨恨,因為要是我不主動提醒,他永遠不會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掃了。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不得不壓抑情緒,只為了讓日子過得更平順,毫無紛爭。或者,我會自己做完所有事情。孩子當然不必做這種選擇,丈夫也不必,那是我的任務,一向如此。
而且無論我做了多少,似乎總有更多在等著我,且那些事情比最終完成的任務還費時,但我周遭的人大多沒注意到。這種感覺對很多女性來說再熟悉不過了。我讀蒂法妮·杜芙(Tiffany Dufu)的《放手》(Drop the Ball)時,看到她講述生完孩子后對丈夫的怨恨,立刻感同身受,跟著氣憤起來。杜芙寫道:“我們在外面都有全職工作,但是回到家,我得更努力。而且氣人的是,他看到的事情,還不及我實際上為維持這個家順利運作所做的一半。換句話說,他不僅做得比我少,還沒意識到我做得比他多!”然而在他的腦海中,他可能認為自己做得已經夠多了。男性大多是這樣想的,因為他們自覺已經比前幾代的男性做得更多了。1965年到2015年間,父親花在家務上的時間增加了一倍多,花在照顧孩子上的時間增加了近兩倍,但這并未帶給我們完全的平等。家庭中的性別差異依然明顯存在。女人在家務及照顧孩子上所花的時間,仍是男人的兩倍。即使在比較公平的兩性關系中,男女雙方平均分配家務及照顧孩子的體力活,感覺起來還是女性做得比較多……她們確實做得比較多,因為我們并沒把這些任務中的情緒勞動也量化計入。通常我們很容易忽略自己“多做”的部分,因為“多做”的部分大多是不被看見的。許多情緒勞動的核心,是為了確保每件事情能順利完成而承擔的精神負荷。對每一件產生有形結果的任務來說,其背后都隱含著無形的心理付出,而這些大多是由女性負責關注、追蹤與執行。
那個母親節迫使我潸然淚下的原因,不單是那個一直擱在地上的礙眼儲物箱,也不是因為丈夫無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禮物,而是經年累月下來我逐漸變成家中唯一的照護者,照顧每件事、每個人,而所付出的勞心勞力完全不被看見。
當我意識到自己無法向丈夫解釋為何如此沮喪時,我終于達到情緒爆發的臨界點,因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緒的源頭了。曾幾何時,落差變得那么大?情緒勞動一直以來不都是我的強項嗎?我難道不是主動選擇照顧我們的家、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朋友和家人嗎?我不是本來就比他更擅長這件事嗎?重新調整我們之間的平衡這件事,難道是我要求太多了嗎?
我不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自省。如果我不把情緒勞動視為分內工作,周遭的人會變成什么樣子?我在意的是結果:那些事情會擱在哪里?誰會撿起來做?如果我放著家務不管,誰會遭殃?如果我不在意我的語氣和舉止對丈夫的影響,我們會吵到什么程度?我這輩子已經習慣了超前思考,預測周遭每個人的需求,并深切地關心他們。情緒勞動是我從小就接受的一項技能訓練。相反地,我丈夫從來沒受過相同訓練,他懂得關心他人,但他并不是體貼入微的照顧者。
然而,當我認為自己不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選,更是最佳人選時,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攬在了自己身上。我比較擅長安撫孩子的脾氣,所以這件事情由我來做。我比較擅長維持屋內整潔,所以我負責絕大多數的打理及任務分派。我是唯一在乎細節的人,所以由我來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但誠如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中所寫的,成為唯一關心這些事情的人,可能導致破壞性和有害的失衡。“每個伴侶都需要負責具體的活動,不然男方很容易覺得他是在幫忙,而不是在做分內的事。”對我丈夫來說,那些歸納在“情緒勞動”那把大傘下的任務,已經變成他在幫我的忙。他所做的情緒勞動,跟精心打理生活或抱持更深的責任感毫無關系。當他不需要我開口就主動完成一項任務,并承擔過程中的精神負擔時,那是在對我展現“美意”,是一種需要稱贊和感激的行為,但同樣的任務由我來做時,卻無法指望同樣的回報。對我來說,情緒勞動變成一個競技場,我的價值與每項任務都交纏在一起。
我感到憤怒,精疲力竭。我不想戰戰兢兢地走在一條微妙的分隔線上,一邊要顧及他的感受,一邊又要清楚傳達我的想法。應對伴侶的情緒,包括預知對方的需求,避免任何不悅,保持心平氣和,是女性從小就被教導要承擔的責任。這個假設的前提是,女性要求男性盡力解決情感糾紛時,男性若是反駁、惱火,甚至憤怒,那些都是“自然”反應,也是可接受的。在賓夕法尼亞西切斯特大學指導“情緒勞動”這個主題并發表相關論文的性別社會學家莉薩·許布納博士(Lisa Huebner)指出:“一般而言,社會中的性別情緒,是在持續強化‘女性在生理上先天就比男性更能夠感覺、表達、管理情緒’這種錯誤觀念。這并不是在否認,有些人由于性格原因,確實比他人更擅長管理情緒。但我認為,我們仍然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這種能力是由性別決定的。與此同時,社會也想盡辦法確保女孩和女人為情緒負責,卻放任男性不管。”

即便是討論情緒勞動的不平衡,討論本身也涉及了情緒勞動。我丈夫雖然個性好,本性善良,但他還是會以一種非常父權的口吻來回應批評。逼他去了解情緒勞動究竟有多累人,就好像是對他做人身攻擊似的。到最后,我不得不在“讓他了解我對情緒勞動的失望有什么好處”“以不會導致我們爭吵的方式來傳達那些想法,究竟要付出多少情緒勞動”這兩件事中進行權衡。兩相權衡后,我通常會覺得“放棄不談”比較省事,并提醒自己,另一半愿意接受我分派給他的任務已經很幸運了。相較于許多女性(包括女性家人和朋友),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已經算好了。我丈夫做很多事情,他每天晚上都會洗碗,也經常做晚飯。我忙著工作時,他負責哄孩子睡覺。只要我開口請他做額外的家務,他都會毫無怨言地完成。有時候期待他做一點家務,好像我太貪心了。畢竟,我丈夫是好人,也支持女權主義,我也看得出來他有心想要理解我的意思,只是他終究還是不明白。他說,他會盡量多做一點打掃工作來幫我分擔家務,也重申只要我開口向他求助就行——但問題就在這里。我不想事無巨細地管理家里所有大事小事,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樣主動積極地面對家務。
喬尼·布魯西(Chaunie Brusie)在Babble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發熱議,文中提到她在家務上缺乏協助,她回想起當時的想法:“如果夫妻倆飯后一起收拾,不是可以更快一起休息放松嗎?如果孩子知道母親不該是唯一的清潔工,那不是更好嗎?把兩人共享的空間視為一種共同責任,不是比較合理嗎?”總而言之,如果所有的情緒勞動不是完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如果她的丈夫(或孩子)能主動注意到家里需要做什么,并主動去做,那不是很好嗎?布魯西是自由職業者,全職作家,年薪六位數(美元),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家人“幫忙”。事實上,她想傳達的重點是,照顧全家的責任根本不該由她一人承擔,但偏偏事實就是如此。她在文中提到,她選擇把飯后的一些雜務分派出去。她不僅要和顏悅色地提出要求,當她第一次分派家務遭拒時,還得把完成任務后一起玩游戲作為獎勵,家人才肯答應。如果她想請家人“幫忙”,就需要以愉悅的口吻提出懇求,即便是“幫忙”清理家人弄亂的東西。“我們把做家務視為‘幫媽媽的忙’,而不是做該做的事。”布魯西寫道,“我希望孩子了解,收拾我們的家很重要。正因為很重要,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然而,當另一半不會主動注意到家里有什么事情該做時(亦即不懂得平均分擔家務的身心勞動時),你很難說服他這樣做。把垃圾拿出去倒確實很好,但真正重要的是,他應該負起“注意何時該倒垃圾”的責任。
不過我試圖向丈夫解釋這點時,他很難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時該倒垃圾”的差別。只要任務完成了,管他是誰要求完成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聽他這樣反問時,我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所以我把導致那一刻混亂的所有掙扎和沮喪寫下來,然后以專文發表在《時尚芭莎》上。我知道有些女性馬上就抓到了我那篇文章想表達的重點,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做這種隱形工作——為了維持整個系統的順利運轉而給輪子上油。我們對于持續擔負起超量的情緒勞動感到沮喪。不過,當那篇《女人不是嘮叨——我們只是受夠了》以驚人的速度被瘋狂轉發時(截至2018年本書撰寫之際,那篇文章已被分享九十六萬兩千次以上),我還是很驚訝。數千名讀者留言及評論,很多女性紛紛分享她們的“母親節時刻”,她們也遭遇過伴侶不明就里的反駁,不知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所思所想。數百萬來自各行各業的婦女紛紛點頭說:“是啊,我也是!”那個聯結時刻令人欣慰,也令人灰心。我不禁納悶:“為什么現在才引起那么大的回響?”
我定義的“情緒勞動”,是結合情緒管理和生活管理,是我們為了讓周遭人感到舒適和快樂所做的沒有酬勞、不被看見的工作。它涵蓋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照護類勞務的相關術語,諸如情緒工作、精神負擔、精神重擔、家庭管理、事務勞動、無形勞動,等等。這些術語分別來看時,看不出是如何交織、火上澆油,終至令人沮喪抓狂的。實際上,這些工作不僅勞心耗神,而且它的負面影響,在我們走出家庭進入世界時仍舊伴隨著我們。朱迪絲·舒勒維茲(Judith Shulevitz)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及母親經歷的情緒勞動,并在文中列出那些工作的高昂成本。她寫道:“不管女人是喜歡操心,還是討厭操心,那都可能分散她對有償工作的注意力,使她在工作上受到干擾,甚至斷送了職業生涯的發展。擔憂及安排事務這種令人分心的苦差事,可能是阻礙女性職場平權的所有因素中,最難以改變的障礙之一。”
舒勒維茲稱這種人為“指定的操心者”(designated worrier),但成為“指定的操心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時間累積及付出心力的。以全職媽媽為例,或許你精心打造了一套系統,好讓每個家人的早晨能夠順利運行,例如你想在墻上掛一個鑰匙鉤。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先“嘮叨”一下,家人才會幫你裝上掛鉤。你需要多次溫和地提醒家人,請他去五金店買掛鉤,不然你就得自己寫在待購清單上,自行采購。你還需要溫和地多次提醒家人:“釘個掛鉤很快,今晚或明天就能完成。”你提出這些建議的同時,還要權衡時間表上有哪些優先要務需處理。然而,無論你講幾次把汽車鑰匙掛起來會有多方便,家人還是會問你:“我的鑰匙哪兒去了?”你心里權衡著到底要直接告訴他鑰匙在哪里,還是再度提起鑰匙掛鉤的事;如果是后者,恐怕又會演變成一場爭論。你總是需要超前一步思考,小心說話的用字遣詞及表達失落的方式。你必須同時克制自己的情緒,也管理對方的情緒。這實在很累人,所以你往往選擇干脆直接告訴他鑰匙在哪里,既省時又省力。
不過事情沒那么簡單,因為在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中,這種加乘式的情緒勞動會變成常態。日積月累下來,你的生活變成一張錯綜復雜的網,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駕馭它。你必須引導其他人在這套精心打造的系統中穿梭,以免他們卡住或陷落。例如,你擠完最后一點牙膏,或是把廁所的衛生紙用完時,你注意到該換新的了;公司同仁指望你規劃下班后的歡樂時光;你腦海中有一份清單,列出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注意及肯定他人的情緒,同時控制自己的;你需要維持事情的順利運作,而且要非常小心。這些勞動都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而且永遠無法將之拋諸腦后。它讓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耗盡無法估量的心神,而且那些心神明明可以用來做其他對我們自身、職業生涯及生活更有利的事,讓我們自己過得更快樂。把這些原本各自存在的用語歸納在“情緒勞動”的大傘下非常合理,因為它們緊密相連。情緒勞動所指的,不僅是關心結果而已,也關心那些被我們的情緒、言語、舉動所影響的人,即使那樣做是犧牲自己以成全他人。
社會指望女人以許多無償的方式,不惜一切代價(包括犧牲自我),讓周遭的人感到舒適。我們創造出一個利他的形象,允許他人的需求凌駕于自我之上。我們成了傾聽者、忠告者、旅行規劃者、行程管理者、居家打掃者、提醒者,也是每個人都可以舒適依靠的無形靠墊(但幾乎沒人考慮這會如何消耗我們的心神)。我們從事情緒勞動時,把周遭的需求擺在自我需求之前。漸漸地,我們在這世上存在的方式,在很多方面開始隱于無形。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們壓抑或調整自己的情緒,從與丈夫和睦相處,阻止孩子亂發脾氣,到避免與母親爭吵,避免街頭騷擾變成人身攻擊。
為了管理他人的情緒和預期,你需要越過重重障礙才能讓人聽到你的心聲,耗盡你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起來的寶貴時間。你必須確保你的響應經過深思熟慮,把他人的情緒也納入考量。當你需要指派任務給別人時,你必須使用正確的語氣,詢問對方的意愿。當你感到不舒服時,你需要克制自己,依舊展現出親和力。如果你想把自己放在最有利的位置,那表示你需要先一步思考對方可能會如何反應。有人說,當你交出完成的任務時,不要同時展現魅力和溫柔的一面,因為你可能被貼上負面的標簽,影響升遷機會。也有人說,走在路上聽到男人對你開黃腔、騷擾你時,不要微笑,緊閉著嘴繼續前進,不然你可能會被跟蹤、攻擊,甚至碰到更慘的遭遇。
當我們的言行不符合既定的權力動態時,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誠如桑德伯格在著作中所述,女性在職場上常避免發表意見,語帶保留,以免被貼上標簽。“怕大家覺得她沒有團隊精神,怕大家覺得她負面或嘮叨,怕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卻被當成單純的發牢騷,怕勇敢說出想法而引起大家關注,怕可能因此遭到攻擊(就是腦海中那個叫我們‘別坐到桌前’的聲音所誘發的恐懼)。”我們在家里,為了獲得迫切需要的“幫忙”且避免爭吵,也要這樣顧全大局,語帶保留。這些持續又傷神的勞動,大多隱于無形。
霍克希爾德在書中提到,航空公司如何要求空乘人員在飛行中營造出溫馨舒適的家庭氛圍,以及她們打卡下班后,那種偽裝會使她們付出什么代價。她們下班后常感到情緒疲乏,很難在工作角色和真實自我之間切換身份。她們之所以難以在內心深處找到真實的自我,或許是因為她們不止在服務業中付出情緒勞動。身為女性,我們必須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營造出同樣的溫馨感。我們不僅在工作中這么做,回到家里或在外面,也必須對親友、同仁、陌生人這么做。女性之所以覺得受夠了,是因為我們意識到這種情緒勞動無法打卡下班,而是隨時隨地非做不可。被要求在生活中時時刻刻都要扮演情緒勞動的主要提供者,我們已經受夠了,因為那實在很累人,很費時,也耽誤了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腦中填滿了家庭瑣事,把不成比例的時間花在造福他人上。我們為了升職所付出的情緒勞動,從注意自己說話的語氣,到聆聽他人的想法并提供意見反饋等,都是男性不必做的。我們必須仔細地權衡在公共場合中如何與陌生男性互動,以確保自身安全。這些必要的情緒勞動類型都是一種征兆,其背后是更大的系統性不平等。那種不平等對女性造成了傷害,尤其是弱勢族群的女性。誠如霍克希爾德所言,男性和女性在情緒工作上的互動方式,是“一種常見的掩飾法,把性別之間的不平等視為人與人之間的虧欠,而且在維持這種現象的表層扮演和深層扮演上都是如此”。在社會上,女性對于任何需要我們的人,總是虧欠著無盡的情緒勞動,除非男性和女性都改變想法,改變他們對于“誰該做這項工作”以及“這項工作的真正價值”所抱持的預期。
每個人都必須改變對情緒勞動的看法,這樣一來,我們才有可能重新獲得情緒勞動這項技能背后的真正價值。沒錯,情緒勞動可能是我們的克星,但也可能成為我們的超能力。我們需要了解這種勞動有其價值,并把它公之于眾,讓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這種關懷和管理情緒的智慧是一種寶貴的技能,是一種密集的解題訓練,還可以獲得同理心的額外效益。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貝克斯校區的傳播藝術與科學副教授米歇爾·拉姆齊博士(Michele Ramsey)表示,情緒勞動往往和解決問題同義。她解釋:“大家對性別的假設是‘男性是問題的解決者,因為女性太情緒化了。’但是在家里和職場中,解決多數問題的人又是誰呢?”身為伺候我丈夫和三個孩子的管家,我非常確定自己知道答案。盡管這些情緒勞動令我們沮喪,但這種照護型的勞動本身就是一種寶貴的技能。我們熟練地顧全大局,宏觀地思考結果,游刃有余地調適意外狀況,用心地投入工作、培養關系、應對偶然的互動。這些技巧是確保我們細心完成精神任務及情緒任務的資產——這里的細心不只專注在任務細節上,也專注在他人身上。情緒勞動在生活中呈現的方式,就像是以維系社會的文明細線編織成一條精致的掛毯。少了情緒勞動,我們活不下去,我們也不該期待情緒勞動消失。
我們應該把情緒勞動變成一種人人都該擁有、人人都應理解的寶貴技能,因為那可以讓我們更熟悉自己的生活。它能使我們更充分地體驗生活,使我們成為最真實、最充實的自己,男女皆然。減輕女性被迫承擔的龐大重擔,同時讓男性進入一個充實的生活新領域是有益的。我們不該只想著“平分”情緒勞動,更應該去了解那些伴隨重擔而來的東西。即使目前女性被迫扛起不平衡的重擔,女性也因為情緒勞動的存在而更長壽、更健康。女性把規劃和深謀遠慮納入生活,關心人際關系的培養與維系,為了讓他人過得舒服而不辭辛勞地付出,她們的伴侶無疑因此受惠了。哈佛大學的研究顯示,已婚男性通常比未婚男性更長壽、更健康。他們的壓力較小,罹患抑郁癥的情況較少,身體也比未婚男性更健康,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妻子對其生活的打理使他們可以更健康地活著。多項研究發現,喪偶及離婚的男性過得不如喪偶及離婚的女性,因為少了伴侶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打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健康、舒適和社交關系都會受到影響。當妻子是家中唯一響應聚會邀約、唯一負責召集家人參加活動、唯一負責維系社交關系穩健發展的人時,失去她也意味著失去了所有人。那也表示,那些人際關系本來就不屬于男性。
女性負責維系男性與親友的關系,也確保伴侶飲食健康、做運動。她們幫男性卸下原本落在他們身上的任務,充當男性的第二個大腦,幫他們記住他們覺得不夠重要而不需要記住的“小事”。然而當男性從來不學習情緒勞動時,他們也錯失掉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大部分。當然,有人代勞肯定過得很舒服,但是如果別人負責處理你生活的一切細節,你的生活便永遠不屬于你自己。目前這種情緒勞動的失衡,導致大家持續以為男人不必建立自己的社交關系,不必密切地關注個人生活的細節,不必從打造個人生活及家庭中尋找意義,這滋長了有毒的男子氣概的恣意發展,在這種環境中,大家依然指望女性以各種方式照顧男性,所以男性永遠不會學習照顧自己,不僅身體上如此,情緒上和精神上也是如此。我們告訴整個社會的男性,他們無法處理情緒勞動,他們需要把一切細節委派給女性處理,他們無法隨機應變,也無法學習這些可以深深改變其生活的技能。我們讓男性對這種依賴他人的人生感到無可奈何,盡管男性擁有那么多的權力和特權。然而,這樣做只是在助長一種對每個人都有害的惡性循環。改變這種現狀不僅不會傷害男性,還可以幫助女性,讓每個人都因此獲得解放。讓大家預期一種更平等分攤的情緒勞動,這并不是在轉移負擔,而是為了鼓勵每個人改善生活。
平衡情緒勞動可以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過更充實,也更真實的生活。負擔減輕的女性可以重新獲得自己的精神空間和時間,在職業生涯上做出理智的抉擇,并從真正平等的立場上,感覺到自己與伴侶的關系更緊密。男性可以以新的方式融入生活,承擔新的角色,擺脫有毒的男子氣概,生活在更緊密相連的環境中,而且不怕幫女性爭取更平等的世界。霍克希爾德指出,我們承認生活中情緒勞動運作的方式,反映了我們在社會變革中的立場。我相信,我們已經準備好打破陳規,邁向新未來。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情緒勞動帶來的阻礙,以便從沮喪中站起來,決定如何好好運用這種深切關懷的技能。情緒勞動不見得會破壞我們的幸福,事實上,它是維系世界的黏著劑。一旦我們意識到它的存在,了解它的利弊,我們就可以掌控它,改變我們使用這些技能的方式,奪回自主權。
我們可以學習如何為孩子樹立更好的平等榜樣,以免他們承襲我們的錯誤模式。我們可以讓男人有機會以新的角色體驗情緒勞動,更充分地體驗如何為人父、為人伴侶,以及成為一個男人。我們可以為無所不在的情緒勞動劃出明確界限,而不是一味地迎合預期。我們可以把情緒勞動視為一種技能,而不是障礙。套用眾議員瑪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的說法,我們可以奪回自己的時間,只在真正有意義的情境中運用情緒勞動的技能,讓每個人(包括我們自己)都覺得世界正在變得更美好。這樣一來,我們不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伴侶和后代的生活。當我們一起消除情緒勞動的不平等時,孩子的未來就被改變了,我們的兒子可以學會恪盡本分,我們的女兒可以學會不必承擔別人的分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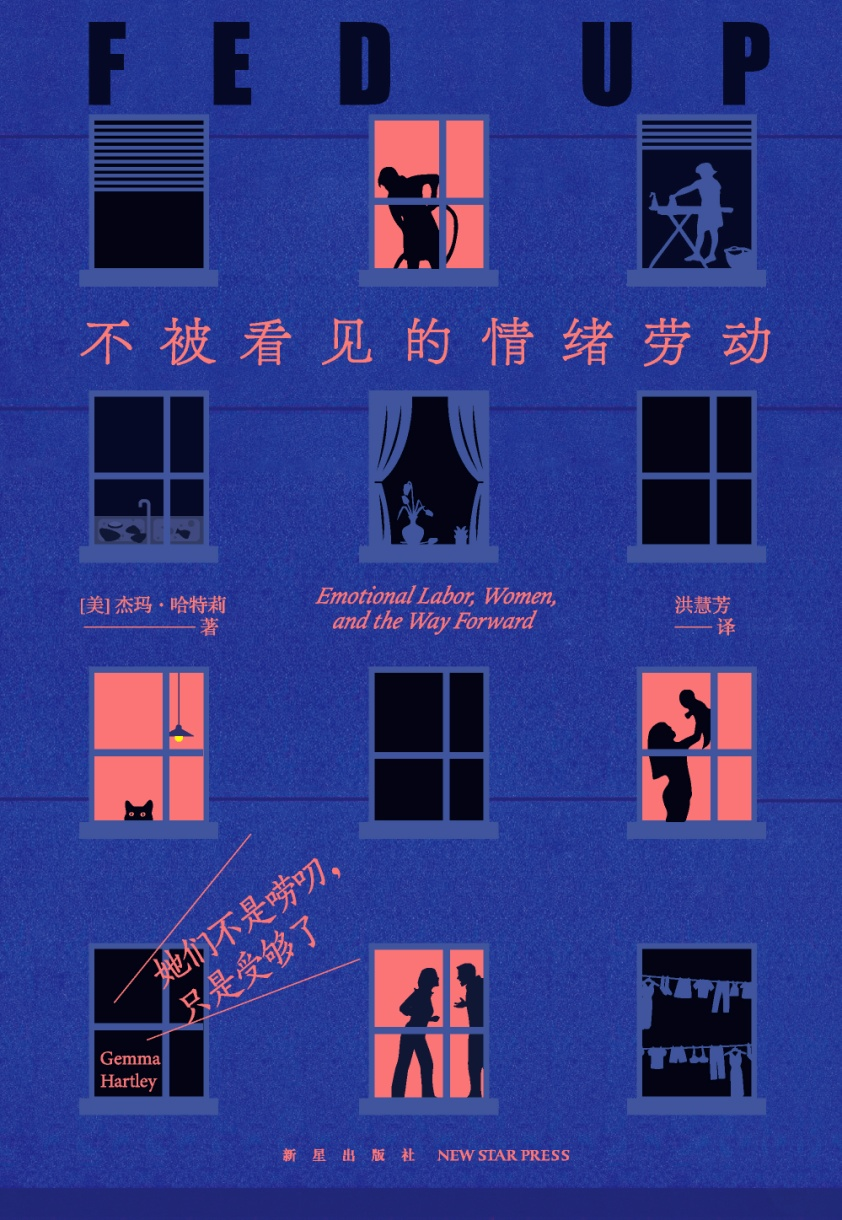
(本文摘自杰瑪·哈特莉著《她們不是嘮叨,只是受夠了:不被看見的情緒勞動》,洪慧芳譯,新星出版社,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