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憶年|劉潤和:河西走廊的那些“年”
【編者按】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不同地域年俗迥異,“年”的背后展現給你的是一部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史詩。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憶年”專題,講述那些年,那座城,那個村莊,那些與年有關的人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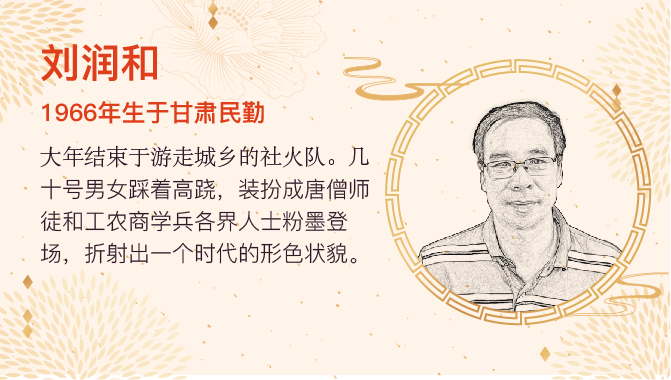
一進臘月,就有了年的氣息。河西走廊吹來的第一縷“年風”,是臘月初八過“臘八節”。《東京夢華錄》記:“十二月初八,諸大寺做浴佛會,并送七寶七味粥與門徒,謂之臘八粥。各家是日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也。”喝臘八粥,又名“灌迷魂湯”。據說喝了它,一年喜怒哀樂該忘的都忘了。
河西走廊屬高寒之地,20世紀70年代,寺廟封門,僧人匿跡,“破四舊”破掉了臘八節,自然不可能有浴佛會,也不會贈送食物。河西物資匱乏,冬天無鮮果生蔬,連干果也緊俏,本來必具七味原料的臘八粥簡化成二、三味,算是艱苦自足,蒙混過節。城里人移風易俗,已沒有了“臘八”的概念。農村舊俗未改,卻無法買到大米,便用麥子、蠶豆或刀豆煮粥,就著咸菜應付節日。
臘八后半月,臘月二十三,小年到了。俗傳司命灶君即日啟程,上天報告各家飲食狀況。灶王爺高興與否,攸關來年生活,各家不敢慢待,送神竭盡全力。晚飯前,要為灶王爺做專用食品“灶卷子”——把發面搟成大圓餅,抹香油,撒胡麻鹽,卷成手腕粗細的圓柱,再橫切為小段,二三公分厚,放進一種叫“鏊”的平底鍋里烙。爐火升騰,香味擠出鏊蓋,撩起饑渴者的食欲。灶卷子出鏊,先擺上灶臺“祭灶”,給灶王爺享用,祈禱“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灶臺上并無神像,灶王爺被熏黑的黃泥墻壁代替,附著蜘蛛網和灰塵,像是給祭獻者的渺茫安慰。
大年一天天臨近,縣城僅有的幾家國營商店年貨陡然緊俏,木制柜臺前擠滿顧客,推推搡搡急著買貨。顧客沒有排隊的概念,誰能擠到柜臺前誰先買了走人。布、肉、煙、酒要憑票購買,有票的急,沒票的更急。營業員被顧客指點著東奔西跑,身心疲憊。算盤噼里啪啦,手中鈔票零亂,一臉的不耐煩。
南街菜社僅賣副食,人少,是小學生購物的去處。他們將攥出了汗的零錢交給售貨員,換回柜臺玻璃下的朝鮮煙、伊拉克蜜棗和南方甘蔗;財力不濟時,買糖精片,一分錢兩粒,叼在嘴角淺嘗輒止;或用幾毛錢買瀏陽造鞭炮,舍不得一次聽完炮響,便拆開連線,化整為零塞進口袋。點一炷衛生香,將單個編炮逐個摸出,拿在手里點燃,扔出去看紙屑炸開,青煙飄散。炮小、火藥少,不傷人,時有男孩引爆口袋或炸傷手指,有驚無險。
一群男孩尾隨頭戴皮帽的殺豬匠,快步走向一座豬圈。豬主人在院子里支好了兩條長凳,上面橫搭一塊門板。一口生鐵大鍋底部柴火熊熊,鍋里冒著水汽。豬匠將裹著屠刀的帆布包放在門板上,和豬主人翻過半人高的豬圈墻,圍捕一頭膘肥體壯的白豬。預感到大限將至,豬來回躲閃,極力逃脫,伴以憤怒的喘息。不過片刻,豬被按上門板,尖利的干嚎直沖云霄。屠刀捅向豬胸,豬掙扎儼然僵尸。豬匠拔了刀,豬主人松開了抓豬腳的手。貌似死去的豬猛然翻下門板,沖過圍觀的小孩,撒著一路鮮血向院場奔去......
宰了豬,主家要請街坊四鄰嘗鮮,淡漠的關系登時活泛。男人互相幫著掃房、清理垃圾,女人聚集起來蒸花饃、炸油馃和油馓,趕制全家過年的新裝,頗有些其樂融融。平日為雞毛蒜皮拌嘴爭吵的兩方,變得友好而親近,讓人詫異莫名,難道是喝了臘八粥的緣故?
大院里支起了大方桌,請“寫家”——回鄉過年的某大學教師寫對聯。“寫家”出身生產隊長,入大學后受教于某書法家,橫豎撇捺均有來路。各家派代表自帶紅紙和墨水,羨慕地看著寫家筆飛墨舞,從住房門聯“抓綱治國展宏圖,斗私批修創大業”寫到土倉帖“五谷豐登”,再寫到牲畜槽頭的“六畜興旺”,圍觀者嘖嘖叫好。“寫家”微笑低語:“就說是生產隊長寫的!”
臘月三十,灶王爺回家,主人照例在鍋臺上燒香獻食,卻不管他在天上說了什么。祭完灶神,拿了黃裱紙,端上肉湯和面饃,到附近的十字路口,面朝先人墳墓的方向燒紙、磕頭,順便給亡故的親友和孤魂野鬼燒足年節費,祝愿逝者在陰間過個好年,免得無事生非。
除夕夜,大小人等聚餐,桌上擺著豬頭和長面,一年一度的饕餮盛宴開場,俗稱“裝倉”。孩子們給老人磕頭賀歲,討得壓歲錢——“年錢”。吃飽喝足,便開始“熬歲”。大人聚在一起諞閑傳、掀牛九、打撲克,小孩等著午夜的炮仗。主婦們在家磨麻籽漿,籮去渣滓煮熟,加蔥姜等料做麻腐餃子,預備初一的美食。
這些司空見慣的場景,每年都在重復。而外地回鄉者帶來的新奇,卻年年有所不同。
縣農具廠請來外地師傅,在縣城十字打鐵水花。十幾個師傅們穿著煉鋼工人服裝,在十字拐角搭起煉鐵棚。風葫蘆吹著炭火,鋼爐里鐵水沸騰。一個師傅用舀出鐵水,倒在覆了鋸末的木板上。另一個師傅端著木板疾步跑向十字中間,將木板上冒著火焰的鐵水和木屑拋向空中,繼而用木板猛擊下落的鐵水。鐵花在空中綻開,黑夜被渲染得五彩繽紛。無數火星像四散的谷穗,向熙熙攘攘的人群落下。圍觀者炸了鍋,驚呼著躲避,猶如慌不擇路的敗軍。如此往復,直到鐵花全部變成鐵渣,眾人才悻悻離去。
看完打鐵花回家,工人大哥點亮了笨重的電石燈,燈嘴冒出銀白火焰。燈下,一伙年輕人圍著在外地讀大學的“說書人”,聽其講述《一雙繡花鞋》:“山城的霧,籠罩在朝天門碼頭......”光焰暗淡,工人大哥往燈肚子里加水,燈光再度明亮。明暗交錯,一雙繡花鞋出現午夜街頭,留下一具無頭尸體飄然而去。電石燈吱吱作響,燈嘴鼓起,電石臭味辛辣嗆人。燈壞了,有人出門找煤油燈。黑燈瞎火,說書人還在說:“曾家巖的燈光通宵未滅,迎來了噴薄而出的紅日......”
鄰居楊姐夫拿出十多塊磁鐵,黑色,長方形,大小各異,厚度不同。他把磁鐵結成長條,再反過來讓其互相排斥。李老二拿出了雷管,說是要在大年初一讓大家聽聽大轟隆。
初一凌晨,郊外地頭巨響如霹靂,雷管驚醒了熬歲的男女老少。孩子們跟著大人,抱了成捆的麥秸和柴草,去地頭“燎天篷”。麥草分成小堆,點火后眾人從火堆上跳來跳去,嘴里念念有詞:“東去東贏了”、“西去西成了”、“牛羊滿圈了”、“百病燎散了”等等。類似越南電影里的巫師作法,只是換成了喜慶的嘲諷。火光、濃煙、爆竹、叫喊此起彼伏,亂糟糟儼然鬧劇的開場。
吃過初一的餃子,大年過去了一半。走親訪友的自行車穿行城鄉之間,車把和后架上捎著油馃和花饃,當做禮物來回交換。招呼客人極簡,一杯開水或茶,一盤花卷足矣。至于陸游詩里所說“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確屬宋朝夢。很少有人家炒菜、上酒,也很少有人喝醉。醉倒在路邊樹溝的經常是三個人:縣文工團的鼓手、運輸公司的老革命和園藝場的馬啞子。
風和日麗,有人用沙竹篾扎骨架,剪舊報紙糊成盾牌形風箏,底部吊著三根長短不一的尾巴。幾個人輪流拉了引線,臉上掛著汗珠,在城郊野地上瘋跑。或許是做風箏技術不行,抑或是風力不濟,風箏飛到一樹高就折頭杵地,孩子們的想象怎么也飛不過藍天。
鄰居楊姐夫用繩子捆好一摞磁鐵,領著幾個小孩在沙地上尋寶。磁鐵粘滿了鋼珠、螺絲、馬蹄鐵,孩子們把這些戰利品收到一個帆布口袋,繼續往下一處奔走。這個場景和《百年孤獨》中拉著磁鐵的布恩地亞一樣,“他拖著兩塊鐵錠,大聲念著墨爾基阿德斯的咒語,一塊一塊地查遍了整個地區,連河底也沒有放過。”布恩地亞最終發掘出了一副十五世紀的盔甲,楊姐夫沒有那么好的運氣,他帶回家的總是一包廢鐵。
初五日后的十天,天氣漸熱,春風吹起沙塵,送走了外來的故鄉人。縣城恢復了日常運轉,店鋪依舊擠著熱情未減的顧客。城鄉簡陋的舞臺上,土洋結合的大小戲曲、夜間的露天電影輪番登場。開場前必須在舞臺口鳴響鞭炮,營造春節的火爆氣氛。觀眾磕著瓜子、嚼著沙棗和麻花,發出半懂不懂的笑聲。灰塵和煙霧籠罩人群頭頂,浮動散不去的空虛。
大年結束于游走城鄉的社火隊。幾十號男女踩著高蹺,裝扮成唐僧師徒和工農商學兵各界人士粉墨登場,在鑼鼓镲鈸的嘲哳中搖頭擺尾,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形色狀貌。
(作者系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