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張治讀《蛋先生的學術生存》|我和“蛋先生”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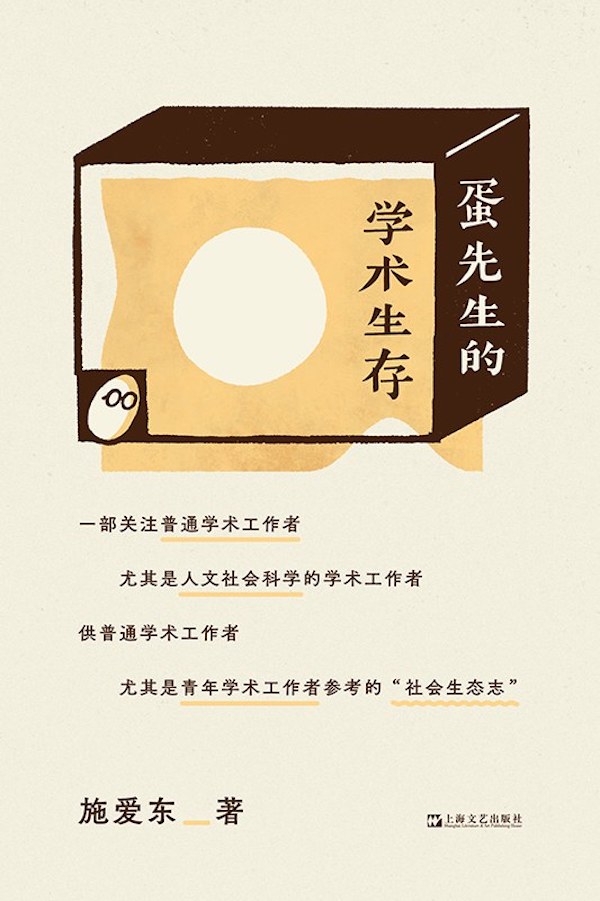
《蛋先生的學術生存》,施愛東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400頁,68.00元
也不知是不是“圍城”的道理無處不在,反正自從我博士畢業,獲得了進入學術界的“敲門磚”“入場券”,就無時無刻不想要離開學術界。據說,好像還真有些人能做到,無非三種情況:其一,自己宣布退出學術界,主動、公開地表示謝絕一切學術活動;其二,比較純粹地消極躺平,另謀生計或是家里有礦,徹底變成“三無”人員(無項目,無論文,無著作);其三,更無可奈何:去世。我仔細揣摩過一番,能說自己是退出學界的,只能是少數有影響力的大佬,人家能那么講話,必然先在學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何況醉翁之意本不在酒,以退為進,也許效果更佳。至于躺平,我也做不到,不僅因為別無生計,而且家里沒礦。第三種情況更不用說了,那本來就是這個時代“無聲無光”的悲劇,誰會愿意拋妻棄子、飲恨吞聲?縱然天堂里沒有體制考核和項目申報,但塵世里還有我買在高點的房貸,需要一直還到我退休后的某年……
這么一想,就是鐵定離不開了。好在我也還很樂于做些什么研究和發表些不上不下的東西,結交一些和我同樣糾結的學界中人,報團取暖,一起自嘲。因此,也還不算特別痛苦。在單位負責一點科研管理的工作,接觸才畢業不久的青年學人機會比較多,也包括平日出差開會遇到的新晉助理教授、副教授,不管前途是否光明,我都覺得他們更加地苦不堪言。名牌高校作為理想的學術界生存場所,現在都在無上限加碼地進行高強度考核。很多青年學人博士畢了業就一邊要應付備課,一邊要拆博士論文拼C刊發表,還要從自己熟悉的那個領域里變出一個新題目來申報項目。如果收獲不多,就是“非升即走”;如果成功了,下一步還有新的困境在前頭等著:原來的題目做到頭了,接下來再寫什么成了難題。回想自己的道路,慶幸早生幾年,在第一處工作單位度過了我從三十到四十歲的光陰。工作頭幾年沒有什么壓力,自己心血來潮,一直搞不在行的翻譯和得罪人的書評,被學科同行譏為不務正業,且沒有屬于自己的代表性成果。后來新領導說不積極申報職稱就要清理冗員時,才發現自己連“核心期刊”是啥都不知道,連國社科項目什么時候申報都弄不清,而拿到的項目,又因為看不懂、理不清財務處報銷經費的大小規則,索性就不報賬,甚至我天真地以為職稱的升遷是單位賜予的,而不是申報的。但那時我還算很快樂,非常清楚自己未來要讀什么書,積累了很多的想法和研究經驗。承蒙師長朋友們關心提攜,算是有了一點成果,一次性升了職稱,換了工作。被新單位給予太多信任,居然要我管理科研,逼不得已,為了服務他人,才算把各種體制里的門道摸個明白。現在雖然沒有了危及生存的壓力,順從于學術研究的尊嚴和讀書育人的志趣,仍會繼續努力,但我也不免時時感到些許的悲哀,體會到青壯年時自己身上那種別有追求的氣概在漸漸消退了。
以上,是我讀民俗學家施愛東老師新書《蛋先生的學術生存》產生很多共鳴的一個原因,雖然這些感受不是此書的主題。在我眼中,這部新書不能算是內封里戲言的“儒林葵花寶典” “學術叢林守則”這種類似“黑幕”文學廣告詞,而應該就是一本民俗學的學術專著。只不過它研究的恰好就是通行言說學術界之崇高與卑下的一種“故事”模本罷了。這原來就是施老師這些年治學的一貫思路。我還清楚記得當年在微博上,他和做當代文學研究的楊早師兄討論,大意是說,當代民間文學應該有個新視野,就是今天的民間在哪里,比如那時候的微博或是豆瓣,就是民間文學創作的“田野”(參看374頁、382-385頁)。當時我和我的同事們關心網絡“謠言”的發生機制、豆瓣書評的“一星運動”、微博上限制字數的學術“清談”,也有樣學樣地將之視為一種類民俗現象。早在《中國龍的故事》里,施老師就曾設立“‘龍圖騰’是學術救亡的知識發明”一章,用社會學、民俗學的眼光考察學術活動某些突出現象背后的通行母題了。其中關于“拿破侖睡獅論”的捏造與流傳,有一句總結非常老辣:“故事都是不可靠的,但都是老百姓喜歡聽的”。假如你還讀過他寫的《故事法則》,肯定知道這一切和此書的中心觀點大有關系:所有的故事套路,都是特定功能相互制約的最優結果。每一則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都是特定語言游戲中的最優玩法。正如《蛋先生的學術生存》甫一問世就常被人們征引的開篇那節文字(第3頁)所說:
傳統學術史多為思想史、發展史或者編年史。當我們借助“發展”和“進步”的眼光來回望一個學科的學術歷程時,我們已經做了許多常規預設,比如:學術發展是在傳統繼承基礎上的學術創新,學術發展是沿著一條從低往高、后出轉精的道路不斷前進的,學者的學術影響力與他的學術貢獻大致成正比,等等。在這些預設之下,成王敗寇,能夠進入學術史大門的永遠只是極少數知名學者,而絕大多數普通學者都被排斥在了學術史的大門之外。
可是,只要我們換一種眼光,參照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思想方式,把學術研究看作一種特殊的行業類別,就會發現,作為“學術工匠”的普通學者,他們的行業習俗以及他們所處的學術生態,一樣應該得到我們的討論。
可知此書關注的是普通學者,不是那些真正有資格進入學術史、思想史的偉大人物。這意味著,你不能把學術界里的蕓蕓眾生自我標榜的那點兒發現或發明,當成是評價他在學術上真正成敗與否的理由,這在每年因國社科獲批項目發榜時刻真實表演著“幾家歡喜幾家愁”的有些人看來,自然都會有些掃興。但我們就此理解了自己在這學術江湖的摸爬滾打、興衰成敗,竟然就如同民間故事里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或是掃灰娘憑借獨特的鞋碼嫁給了王子,或是種了魔豆的杰克打敗了可怕的巨人,雖然沒那么起伏跌宕,卻一樣有著某種可復制搬用的通關套路。也許,認清自己的渺小和普通,比在申報書上寫一萬字強調自己研究的價值、意義、創新性、前沿性更重要吧。
舉個例子,書中拋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大家都知道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卻沒人去做?道理很簡單,“絕大多數學者都只會選擇有經濟利益的課題、有助于獲得學位或晉升職稱的課題、能讓成果得到順利發表的課題、能提升學術聲望的課題;少數學者會選擇那種純粹帶給自己身心愉悅的有趣課題;幾乎沒有學者會為了一幅理想的民俗學藍圖而選擇那些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收益的‘有意義’的課題”(33頁)。比如“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這種題目,“耗時長,見效慢,枯燥無趣”,高成本,低收益,誰也不愿自討苦吃。這令我讀到此處頗感驚訝,因為我見識過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六大卷《民間文學母題索引》(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以為丁乃通、祁連休諸先生開啟山林后必然大有可為呢。如此來看,這種現象恐怕也并非孤立的,想必也常見于其他很多學科領域。
這么一來,什么學術研究的神圣光圈,就都不那么可信了。如同把大到天王老子、下至城隍土地一眾神明的崇拜儀規、典禮法器,都視為一種民間約定俗成的話語和習俗一樣,學術行業的“祖師崇拜、學術趕集、資輩親疏、派系與行規、控制與反抗、順從與革命”云云,不也就是一套某個圈子里的新民俗嘛。作者說,“祖師崇拜”,首先就是一種“半強制性的群體儀式”,其作法的神壇就是“學術機構”,由于共同信仰和儀式將不同代際和存在競爭關系的蕓蕓弟子團結起來。內部存在競爭,但更重要的使命是抱團對外,使這個神壇得以維持下去,維護著在此傳統蔭庇下大家的共同利益。令人神往不已的學術之“薪火相傳”,往往不過就是“世世代代傳香火”的一廂情愿美好祝福。作為擴充學術機構影響的重要手段,學術會議也就首先是一種儀式,用以編織社會關系網絡,進行長幼尊卑排序,很像是武俠小說里的門派大會,確立某種程度團結性和排他性的“圈子”。
門派需要領袖,儀式需要偶像。一代代更替,一代代傳承,也一代代的焦慮和反抗。“圈子”自然有其意義,不見得就是樹立門墻、固步自封、黨同伐異。施老師此書最被人津津樂道、截圖轉發的,可能要數對當下典型的 “師門微信群”各種現象做出的概括了(122頁),他譏之為“丁春秋的弟子群”。但《蛋先生的學術生存》的宗旨并非在于揭露黑幕,我們看到,作為民俗學科富于成就的學者,更是作為這些年關注當代學術生態的知識分子,施老師更在意的,是將這種存在時間不久的門派圈子,區別于具有牢固學術傳統的學派圈子,以及由跨學科學術精英長期互動而形成“無形學院”的流派圈子,最后這種圈子是具有理想意義的學術共同體。對此,我深感贊同。我自己雖然也有師門歸屬(甚至在不少人眼中,我們還算是根柢深厚的大門派),參加師門活動,但從來不喜以贊美自己導師言辭思想為核心話題的圈子生存方式。我引以自豪的是,也結識過好幾位來自不同行業、學科而都有真學問的師友,也形成了幾個不太一樣的日常交流圈子。他們會在我風光的時候來一句冷言冷語的諷刺給我降降溫,也會在我低落的時候給以著實溫暖的鼓勵。拈斷數莖須而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難,會受他們一句話而豁然開朗。雖然不常見面,但時而有微信群里的日常對話,不論晨夕省定,興之所至,不斷涌現各種充滿智慧的戲謔、調侃機鋒,以及深入體己的關懷。不必擔慮自己忍不住分享的新發現會被這些師友搶走先寫論文,也不會因為臧否人物的直白不諱而被別有用心地截圖散播。我想,這應該類似于施老師所說的那種有正面意義的學術圈子了。
除此之外,還有如何宣傳造勢(學術推廣的四種方式,見29頁),如何為自己的學術品格立人設,如何搞理論建設、為自己的學派建立合法性,如何設定學術領域的邊界,乃至如何進行學術寫作,從施老師的專業角度來看,無疑也都是在學術界建立或遵守風俗的手段。他提醒新入行的年輕學者千萬小心頭頂上壓著的學術機制兩座大山——“量化管理機制”和“學術評價機制”,此外還有一座隱形的大山,名為“學術創新機制”,前兩者損害學者個人健康和幸福生活,第三座大山會損害學術發展本身的正常進程(39-40頁)。由此可見,學林的風俗、習俗與種種風氣,不免與學術機制自身存在問題的畸形發展方式有些關系。我們當然知道,學術史大浪淘沙,終會將無價值的學術成果全部淘汰出局。但這并不意味著從事服務工作的管理層有資格來充當裁判乃至行刑人,以一刀切的條條框框來敦促、監督乃至審查、核算學術生產的數量、質量、價值、意義,等等。因此,《蛋先生的學術生存》還有一章專門寫“學科建設”,其實主要涉及的是關乎學術意義上的軟件建設,最可貴的就是一種在合乎學術規范和學科共同體認可前提下進行自由發展的路徑。而這種自由的獲取,除了依靠管理者高度的領導智慧,也需要每一位參與其中的學者的積極行動。三座大山壓迫之下,我們往往都專注于自己論文、著作的炮制,缺少對同行成果的關注和討論(除非是別有用心的原因)。而之所以普遍呼吁減少對每個人學術產出的量化要求,還有一個原因在于學者其實需要互相對話,包括出自真心和實用的互相引用、互相批評。施老師曲終奏雅,在全書的最后環節暢想了各種不同層次學者之間的平等對話,再次申明那種“無形學院”的圈子理想,使我們相信,即便是人文學術,也不可獨坐書齋抱殘守缺,而形式上的團隊建設其實也沒有多少意義。如果沒有優秀學者的杰出成果,沒有年輕學者的研究熱情,沒有眾多學者的平等交流愿望,那么我們看到的學術界,終將還是會辜負“蛋先生”的一片苦心。
我讀后深信,志向遠大的青年學者絕不會將此書當成是“學術界登龍術”的引導習得工具。只要這些早被過來人“看破”的規則成為你知我知的共有知識,只要這些共有知識變成了“看破又說破”的公共知識,就可能出現打破常規、破除舊習的希望。因此,我覺得《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具有《皇帝的新裝》里那個小孩子把大家心知肚明的真相說出來、說清楚的意義。如此,才有可能去除學術界的神圣光環,減少有損害的影響,回歸學術生活所追求的本真目標上去。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