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史語所早期考古人才隊伍的構成及其命運
史語所在1938年1月撤往昆明之前,曾經短期駐留于長沙。在一片兵荒馬亂中,史語所考古組在長沙迎來了有史以來最慘痛的一幕。
從20世紀20年代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培養開始,中國考古專業人才隊伍日漸壯大,到抗戰全面爆發前,具備較高科學發掘水平的專業人員應該在20人左右。這些人員主要分布在史語所考古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質調查所、北平研究院等機構,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史語所考古組。中國有能力從事大規模、高水平科學考古的專家,主要就是史語所考古組的十幾個人。
這十余人是中國的第一代考古學家,但他們的資歷、教育、出身、師承以及派系都有一定的區別,大致可做如下分析:
資歷
屬于第一代的老師輩,對于史語所考古有開創之功者有: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郭寶鈞;資歷較淺、屬于學生輩者包括“十兄弟”中的大多數人,以及劉嶼霞、趙青芳,還有后來出國深造的吳金鼎和夏鼐。
即使同屬于老師輩或者學生輩者,相互之間的關系也很復雜。例如,老師輩中,李濟實際上是梁思永的長輩,因為李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梁啟超的同事,同屬研究院導師。而且李濟發掘的西陰村陶片是梁思永作為碩士學位論文題目來整理的,李濟有指導之力。學生輩諸人中,資歷、水平差別更大。論田野資歷和能力,王湘、石璋如、劉燿參加田野工作最早,次數最多,技術最好。“十兄弟”中的其他人,很多是由這幾位訓練出來的。這些人都是殷墟出身,城子崖出身的吳金鼎是個“異類”。但吳金鼎先后在山東、河南、西南開展考古活動,成就斐然,對于史語所早期考古有極大貢獻,在后輩中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1936年冬,史語所考古組在南京所址前合影,后排左起:董作賓、梁思永、李濟、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尋。前排左起:王湘、石璋如、劉燿、郭寶鈞、李景聃、祁延霈
教育背景
以教育背景而論,可以分為留洋派和本土派。
留洋派包括早期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李濟和梁思永,以及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的吳金鼎和夏鼐。其他人如董作賓、郭寶鈞、“十兄弟”等都可說是本土派。
李濟和梁思永是留學西方學習現代考古學的先驅。李濟本來學習的是體質人類學,兼學了一些考古學知識。但梁思永留學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學習考古學,雖然梁思永只是得了碩士學位,但他在美國學習的時間卻很長,自1923年至1930年,前后達7年之久。而且他得遇祁德(.V.Kir)這樣的大學者受教,有一定機會參加田野實踐,所以他后來成為推進中國田野考古學近代化的最重要人物。吳金鼎和夏鼐去英國學習考古學是受到了李濟、梁思永的直接刺激,而且選擇去當時世界考古學的中心英國留學,表明了中國學術界對世界學術發展潮流的認識。吳金鼎和夏鼐通過這難得的機會,學習到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考古學知識和技能。他們的考古學修養,似乎已經超過了他們的前輩,但戰爭期間有限的實踐并沒有給他們證明的機會。吳金鼎先是改行脫離考古界,更于1948年英年早逝。而更具優勢的夏鼐,則在新中國做出了超越前輩的成就。
本土派雖然都是在國內受的教育,但情況差別很大,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在中國文化中心如北京等地的名牌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如董作賓、高去尋、胡厚宣等畢業于北京大學,吳金鼎、夏鼐、祁延霈等畢業于清華大學,李景聃畢業于南開大學。這些人深受新思想、新知識的影響,屬于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不但接受新事物,還有很強的學習精神和傳播能力。二是在內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者,如郭寶鈞、石璋如、劉燿等一批河南人士,雖然也受到新思想、新知識的影響,但比較間接而微弱,與前者相比,更處于一個學習者的地位。三是只接受過中等教育者,如王湘、劉嶼霞、潘愨等,憑借機遇和勤奮逐漸在田野工作中磨煉出來,成為一方面專家。其中尤其是王湘,考古技術既高,在研究方面亦頗有心得。
本土派和留洋派在史語所考古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明顯不同的。留洋派是現代考古學的引進者,是思想上的先驅,行動上的先導。本土派對科學考古學有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發展之功。兩類人物有相輔相成之關系,但留洋派在科學考古學的興起中起主導作用則是毋庸置疑的。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史語所這少數幾個留洋派考古學家在中國科學考古學史上的地位是如何重要。但是,從這一段史實延伸出去,更有深意的是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說,另外一些具有考古專業知識的人為什么進不了史語所。
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史語所在中國學術文化界的聲望如日中天,待遇和治學環境極好。文化人都以能夠進入史語所工作甚至以能在史語所掛名為榮,成名學者毛遂自薦者不少。如郭紹虞,1936年他寫信給傅斯年,講了自己的眾多成果,想進史語所。但以傅斯年看來,郭紹虞的學問屬于傳統的文史考證和詩話,不是“預流”的學術,故而傅斯年直截了當地說他的學問“不在本所研究范圍之內”,給回絕了。
但胡肇椿的情況與郭紹虞有所不同。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胡肇椿是極少數幾個在國外受到過考古學正規教育的留學生,但以現有資料來看,當時這個在國內頗有影響的考古學者和博物館專家幾乎沒有與李濟領導的史語所考古組以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有過什么交集。
胡肇椿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隨濱田耕作等日本第一代考古學家專門學習考古學數年,1930年回國。他以考古學留學生的身份回國,后來卻沒有得到很好的機會從事本專業。他一生做過多種工作,包括考古學者、大學教授、博物館館長、出版家、翻譯家、官員等。令他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留下姓名的原因是,他從日文本入手,翻譯了大量有關文物考古和歷史的重要學術著作。考古學方面有兩種,一是他做銀行職員時和鄭師許一起翻譯的瑞典考古學家奧斯卡·蒙特留斯《考古學研究法》,這本書可能是從日文本轉譯過來的,因為他留學日本時候的老師濱田耕作的名著《考古學通論》的方法論這一部分就是蒙特留斯的《方法論》。二是他曾經獨自翻譯的英國學者吳理的《考古發掘方法論》。此外,他還翻譯過濱田耕作的《古玉概說》、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等名著,特別是后者,有很大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初,他到黃花考古學院任教,發掘過廣州東郊木塘崗漢墓、西郊大刀山晉墓。后來胡肇椿逐漸轉向博物館研究和教學,先后擔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中山大學博物館學教授等職。
類似胡肇椿這種專業出身而不為史語所見重者,其實不在少數。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有門戶之見,另一方面,與在當時歷史背景之下,史語所的歐美派學者對日本考古學的隔膜以及民族主義意識有關。
地緣和派系
由于不同的出身或者是來源,史語所考古組的學者群體客觀上形成了幾個派系是一個事實。這件事情并無人去討論,但加以探討卻是有意義的。因為這對他們的機遇、命運,以及在歷史關頭的抉擇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語所考古組的人員來源,主要圍繞三個人而形成,那就是創始“三巨頭”: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故而圍繞這三人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三個派別。
首先談一下這三個人之間的關系。傅斯年作為史語所的創建者,對李濟、董作賓有知遇之恩。是傅斯年為二人提供了機會,使得他們能夠功成名就。但這三人之間卻并非絕對的從屬關系,因為史語所的功業是大家共同開創出來的,李濟、董作賓都為史語所名揚天下做出了決定性貢獻。隨著李濟、董作賓學術聲望日隆,在社會上也獲得了相當高的地位,李濟長期擔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三人都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委員,董作賓、李濟還先后代理史語所所長。所以雖然傅斯年在史語所有絕對的權威,實行家長制管理,但這三人之間的關系,在地位上卻大致是平等的。三人合作無間,但也經常為了所務甚至私事爭吵。特別是董作賓,本來創所之初他的地位較低,只是一個比研究員低一等的編輯員,但他有實力又有運氣,對殷墟甲骨文的獨家研究使他成為名重天下的學者,很快在國內外有了很高的聲望,與李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董作賓在與脾氣火暴的傅斯年相處不融洽的情況下,屢次以辭職相威脅,而傅斯年竟然毫無辦法。董作賓在史語所的地位,實際上也就代表了甲骨學在史語所學術體系中的地位,雖然考古發現是史語所業績的重點,但作為一門更有傳統根基的新學問,甲骨學的影響力和影響范圍要大得多。
史語所是一個壁壘森嚴的學術團體,第一代創業者是同志的結合,而第二代進入者,基本上是第一代人及其密友的學生或者親朋故舊。外人除非有很強的奧援,或者機緣巧合,一般不予接納。以考古組為例,大多是傅斯年、董作賓和李濟引進的人員。圍繞三人進入史語所考古組的人員,以李濟最多、最強,其次是董作賓、郭寶鈞等河南籍人士,最次是傅斯年。
李濟延攬的主要是清華和南開時期自己的學生。清華出身者最重要的一個人物當然是梁思永,梁思永因其資格和顯赫的出身,雖然不算李濟的私人關系,但他從事考古事業李濟助力甚多。清華出身者還有吳金鼎,是李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指導的唯一的考古學研究生。吳金鼎在史語所大陸考古時期貢獻極大,是龍山文化的發現者,西南考古的開拓者。另外還有較晚的祁延霈和夏鼐,但夏鼐與傅斯年的關系似乎更為親近。再就是“十兄弟”中的老大李景聃,是李濟任教南開大學時期的學生。
以董作賓為首的河南籍學者,因為在殷墟發掘的地緣關系,數量相當不少。最重要者是郭寶鈞以及石璋如、劉燿、王湘。郭寶鈞和王湘都是南陽人。郭寶鈞是董作賓的小學同學,王湘則是董作賓的表弟,二人自殷墟第一次發掘即參加,資格很老,業務水平和貢獻也很高。劉燿和石璋如則是因為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的協議才以實習生的名義參加殷墟發掘,因為表現突出,又被史語所錄取為研究生,經過長期田野工作,后來成為考古組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河南古跡研究會成立,郭寶鈞成為實際上的負責人,以此機構為據點,招攬了相當多的人員,如他的南陽同鄉尹煥章、趙青芳等。其中也有不少人因為各種原因中途退出。
當然,進入史語所的絕大多數人都與傅斯年有關,但他直接招攬進入考古組的人并不多,后來到20世紀30年代初,胡適任北京大學校長,而傅斯年作為胡適的得力助手參與北大事務,實際控制了北京大學史學系之后,開始實行所謂“拔尖主義”,挑選了不少有潛力的畢業生進入史語所各組,包括考古組,其中有高去尋、胡厚宣等人。
因為這樣一種進入方式,故而第一代與第二代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依附關系,內部等級秩序森嚴,薪資待遇相差很大。管理上實行家長制,業務上實行學徒制。
據1930年史語所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函及備忘錄顯示,各級職員的薪資標準是:專任研究員為400元,編輯員240元,助理員120元或80元,書記25元至30元。像王湘這樣第一線的田野工作人員,1929年10月至12月每月只有10元,到1930年1月至5月,才增長到每個月16元。
這三種來源不同的人,各自有其獨特的性格。他們在史語所的機會和地位很不相同。傅斯年和李濟的人一般有較好的發展機會,如吳金鼎、于道泉等都得到了公費留學的機會。而河南古跡研究會的人員機會稍弱,有一定的獨立意識,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們在1949年歷史巨變關頭的不同選擇。傅斯年和李濟及其追隨者大部分去了臺灣,而河南籍學者除董作賓一人之外,其他全體留在了大陸,包括元老郭寶鈞在內。
社會階層與出身
史語所的考古學家們大多出身不高。稍高一些的,如史語所的領袖傅斯年出身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李濟出身下層官僚地主家庭,父親在清末短暫當過小京官;梁思永的父親梁啟超則是清末民初文化界和政界巨擘。其他人大都出身寒微。董作賓少時曾因家境貧寒一度輟學,與人合伙設館授徒,并兼營書店;郭寶鈞為遺腹子,由祖母、母親撫育成人,以開布店為生,家境十分清寒;石璋如出身農村小地主家庭。其他人大多也是如此。
史語所考古學家們雖然大多出身寒門,但又并非一貧如洗,家庭尚有余力支撐他們接受高等教育以改變命運,大體屬于由社會底層上升而來的新型知識分子,這與羅振玉等老一代金石學家已經有根本區別。清末民初從事金石學研究者大都出身社會上層,有一定經濟實力、社會地位以及閑暇從事玩賞和考據之學,躬身田野是與其身份地位和一貫生活作風不相配的。一般的小知識分子很難有機會和條件從事這種學問。科學考古學的崛起在需要新型知識分子獻身田野的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晉身至少是謀生的機會。民國時期中國一批田野考古學家的出現,與二戰之后西方中產階級崛起帶來考古學的繁榮有相當多的類似之處。考古學家與傳統金石學家們在身份地位上的不同,也在這兩種學問上留下了不同印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它們具有了不同的風格與個性。當然,史語所考古學家這種身份上的高度一致性并非孤立現象,而是與清民之際知識階層結構的普遍轉變密切相關。
但經過千辛萬苦培養出來的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群體,在1938年的長沙,在戰爭壓力下卻面臨解體。這時候,殷墟的工作才剛剛進入正軌,全國性考古活動剛剛起步,大量的材料都沒有整理,中國田野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勢頭戛然而止。
這一幕是在長沙一個有名的飯店“清溪閣”發生的。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把這個掌故敘述出來,是因為它擁有太多的歷史含義,特別是中國考古學和考古人的愛國情和民族恨,都可以從這里找到無須解釋的根源,任何其他辯解與分析,在這活生生的歷史事實面前,都會陷于蒼白無力。民族情懷在中國考古人的血脈中流動,在血與火的民族戰爭中得以永固。
1937年12月12日,南京淪陷,然后發生了大屠殺,舉國陷入震驚與悲憤之中。長沙很快成為日軍下一步進攻的目標,史語所在沒有找到新的搬遷地之前,為了同仁安全決定疏散。個人去留的先決原則是:家鄉沒有淪陷的話,就先回家;家鄉淪陷的話,跟著史語所走,只是地點未定;若不想跟所走,可以自便。決定此一原則之后,就讓各組自行商量。考古組商量的結果是,三個高級委員,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是不能動的,要跟所走,“十兄弟”則各奔東西。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鄉未淪陷,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洛陽人,家鄉還在中國軍隊控制下,也要回家;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鄉未淪陷,但他是考古組的古物管理員,不能走;老四劉燿是河南滑縣人,去延安投奔他的哥哥參加抗戰,后來改名尹達;祁延霈是山東濟南人,家鄉淪陷,去重慶投奔教書的父親,后來也去了延安;王湘是河南南陽人,家鄉沒有淪陷,但他決定跟著長沙的一些大學生去抗戰;老九高去尋,河北保定人,家鄉淪陷,隨所走;老十潘愨,獲派押運古物到重慶,也沒有走。這樣,“十兄弟”只留下了四個,有六個離開了史語所,都是考古組的主力成員。
據石璋如回憶,大家商量好以后,就去了“清溪閣”。參加的人除了“十兄弟”,李、董、梁三先生,還有幾位常年跟隨考古組的技工: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連春。當時大家志氣都很激昂,喝酒比較爽快。大家先說“中華民國萬歲”,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中央研究院萬歲”,第三杯“史語所萬歲”,第四杯是“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是“殷墟發掘團萬歲”,第六杯是“山東古跡研究會萬歲”,第七杯是“河南古跡會萬歲”,第八杯是“李(濟)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賓)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一路喝將下來,滿座大醉。醉后是慘然的離別,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從此之后再未見面。
“十兄弟”中離開的六個人,后來際遇頗為不同。石璋如經過一番漂蕩,幸運地又回到考古組,之后再未離開。尹煥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續從事考古工作,卓有成就。劉燿成為職業的革命家。祁延霈抗戰期間病逝于新疆哈密。李景聃抗戰勝利不久后病逝。王湘則終生脫離了考古。
戰爭期間,史語所和中國其他學術機關一樣,面臨極端嚴重的困難,不僅僅是學術研究,連生存都成了問題。這期間隊伍很不穩定,除了上述人員之外,考古組的骨干人物,如吳金鼎、郭寶鈞以及胡厚宣,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離開了史語所。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對于中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考古隊伍受到的戰爭摧殘極為悲痛和憤怒。在1940年夏即已編竣、歷盡艱辛在1947年3月才得以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報》(即原來的《田野考古學報》)第二冊的《前言》中,李濟悲憤地寫道:
試看這個統計:六篇報告的作者,已死了兩位,改業的又有兩位;只有石璋如、高去尋兩君抱殘守闕到了現在,但他們的健康,已被戰事折磨了大半。至于去世的,是祁延霈君和李景聃君,本期附有二君的傳略。這種損失在將來的和會上是否可以列入賠償的要求?假如可以列入,賠償可以抵補這種損失么?不過無論麥克阿瑟將軍所主持的盟軍總部對于此類損失作何打算,我們仍希望負責計算中國在戰爭中文化損失的主持人不要忘了這一項的道義的和法律的意義。
......
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復,在最近的將來是一點希望沒有,但考古組的工作卻不能不繼續。田野工作人員從此在屋內讀讀書,除寫作未完成的報告外,再多寫點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也許對考古學可以有更新的貢獻。
麥克阿瑟等人也許并不在意中國考古學的這點損失,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考古人造成的傷害,就像他們給全體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一樣,是永遠不會被輕易抹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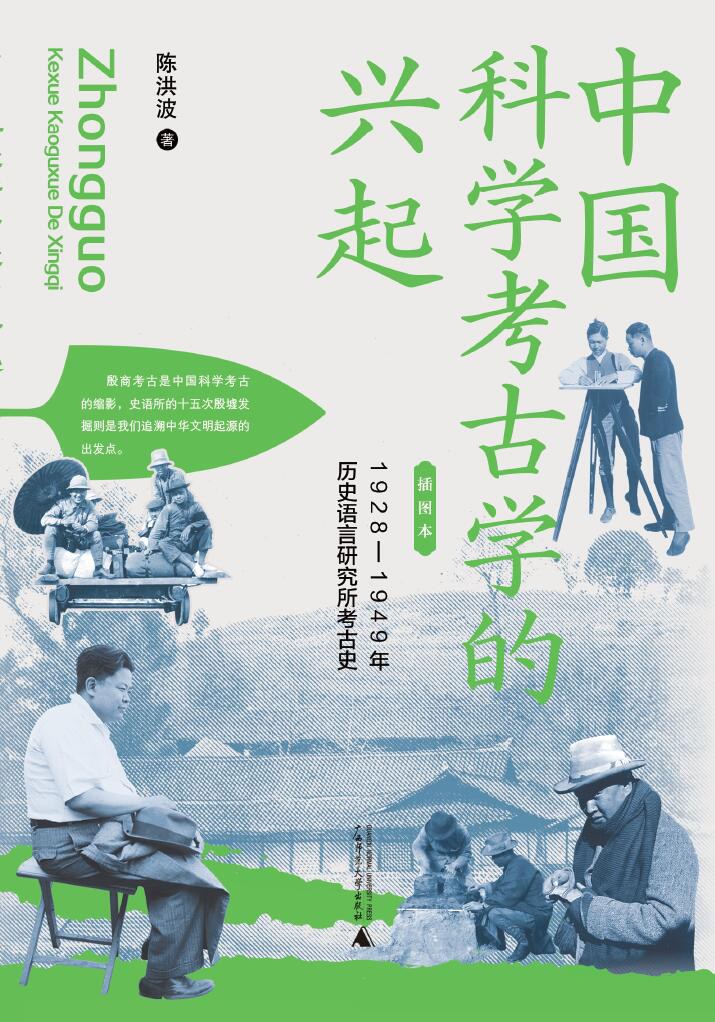
(本文摘自陳洪波著《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1928-194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