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書評丨成也大戰略,敗也大戰略 ——評《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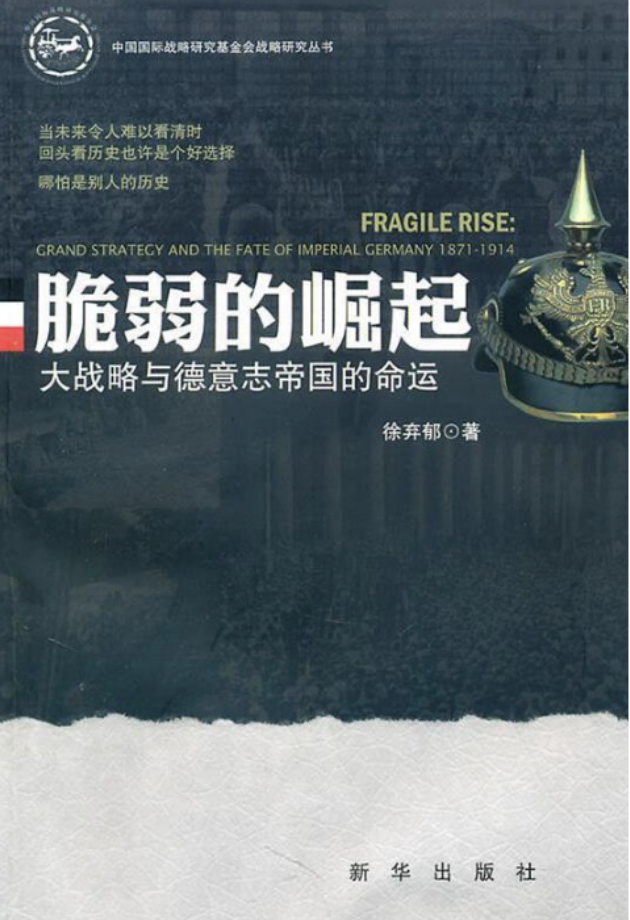
一、導言
史學界圍繞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Kaiserreich,后文簡稱“德國”)興衰的研究汗牛充棟,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原國防大學教授徐棄郁大校的著作《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分析了從德國統一到一戰爆發期間大戰略如何決定帝國命運。
本書時間跨度大,涉及事件多,涵蓋領域廣,但總體圍繞“大戰略”(Grand Strategy)展開。李德·哈特(Liddell Hart)認為大戰略是國家為實現其目標而最有效地發揮國家全部力量(包括外交力量和軍事力量)的藝術。[①]本書的核心邏輯與之相仿:外交戰略和軍事戰略組成大戰略,而大戰略的成敗是決定德國興衰的最主要因素。該邏輯在本書中體現于以下三個維度:
第一,大戰略組成部分的相對地位。外交戰略和軍事戰略相對于彼此的重要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帝國初創時期,以老毛奇戰爭思想為代表的軍事戰略占據主導;帝國前半期,以俾斯麥同盟體系為代表的外交戰略占據主導;帝國后半期,以威廉二世新路線和世界政策為代表的外交戰略占據主導;一戰前夕,以提爾皮茨海軍思想和“施利芬計劃”為代表的軍事戰略占據主導。
第二,大戰略組成部分的內在聯系。外交戰略和軍事戰略并非互不隸屬的官僚部門之間彼此割裂的政策,本質上其實是帝國內政府和軍隊關系(后文簡稱“政軍關系”)在不同領域的展現。政軍關系協調,則大戰略穩固;政軍關系割裂,則大戰略崩潰。
第三,大戰略組成部分的行文布局。本書以外交戰略為主線,軍事戰略為副線,兩條線索相交于政軍關系。
二、大戰略之德俄關系:俾斯麥同盟體系支軸新說
俾斯麥同盟體系是國際關系史上最為龐大和復雜的外交體系之一,傳統觀點將德奧同盟視為其基石,但難以厘清各條約之間的內在聯系。作者極富創見地將德俄關系作為俾斯麥同盟體系的支軸,將各條約相間錯置于支軸兩端,使德俄關系在“敵”與“友”兩個極端之間不斷小幅調整,且主動權始終在德國,因此俾斯麥同盟體系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體系。傳統歷史敘述“…條約形成,標志著…確立”,將之視為一種政治結果,作者指出:條約是“因”而非“果”,是調整體系的杠桿而非記錄歷史的工具,是政治進程的開始而非政治進程的結束。
這一見解的精妙之處貫穿全書。在俾斯麥同盟體系的前期,德奧同盟和三國同盟帶有反俄色彩,三皇同盟拉攏俄國,看似前后矛盾,實則相反相成,使三國戰略互動以一種穩定、均衡的方式進行,俄奧雙方皆依賴德國與對方維持一種不親不疏、亦敵亦友的曖昧狀態,[②]德國得以恃此而執三邊關系之牛耳。作者認為1883年至1885年間是俾斯麥同盟體系的巔峰:面對保加利亞危機對三皇同盟的沖擊,俾斯麥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再保險條約》穩住俄國,一方面以兩次《地中海協定》促成看似與德國無關的反俄同盟,二者在黑海海峽和保加利亞問題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承諾,以對沖戰略抵消了國際變局對德俄關系的沖擊,重新支撐起了德國的大戰略。而威廉二世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放棄了德俄關系的支軸地位,放棄了動態平衡的體系設計,觸發了德國外交和安全環境不斷惡化的正反饋機制,從側面證明了作者的創見對俾斯麥同盟體系的強大解釋力。
三、大戰略之政軍關系:從協調到割裂
部分德國史著作主要聚焦俾斯麥同盟體系、英德海軍競賽、殖民政策和“施利芬計劃”等議題,而作者把握住了“政軍關系”這一大戰略的核心脈絡,將上述議題有機整合于統一的理論框架。根據德意志帝國的制度設計,陸軍部、總參謀部和軍官團三大軍事機關互不隸屬,各自繞開以宰相為首的文官政府而直接聽命于德皇,[③]一方面延續了普魯士時代“士兵國王”的傳統,一方面埋下了德國決策體制中政軍相互割裂乃至對立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滿足于將帝國大戰略失敗簡單歸因于政軍體制的內生性問題,而是通過對比老毛奇和施利芬兩任總參謀長,以小見大透視了德國政軍關系的蛻變過程。
“德國統一三杰”之二——宰相俾斯麥(1862年上臺,1890年謝幕)和總參謀長老毛奇(1858年受命,1888年卸任)被視為德國政界和軍界的靈魂人物。在決定德意志統一的三場王朝戰爭中,無論是俾斯麥縱橫捭闔、折沖樽俎的高超手腕,還是老毛奇的運籌帷幄、料敵機先的耀眼戰績,皆堪稱經典,而且彼此配合得當,渾然一體。他預言了德國兩線作戰的未來,建議德國采取“西守東攻”即修筑阿爾薩斯-洛林要塞抵御法國并準備從東普魯士突出部進攻俄國的戰略,[④]這樣既不枉費俾斯麥簽訂《法蘭克福條約》時力主割地的心血,也能配合俾斯麥以德俄關系為支軸的同盟體系。他還把有限的勝利作為目標,強調以戰場優勢為外交談判增加籌碼。19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俾斯麥外交戰略和老毛奇軍事戰略基本確立,互為補充,二者都貫徹了保守主義的思想,都體現了“適度”、“平衡”和“協調”的原則。正如作者所言,二人親密共事的三十年間,文官政府基本掌握武裝力量,外交系統和軍隊系統保持協調,大戰略有效運行。 “施利芬計劃”的出臺則象征著政軍關系的破裂。在行軍路線上,施利芬不顧英國參戰的風險令大軍取道比利時,但德國本身就是比利時中立的保證國;在戰線選擇上,施利芬從未和奧匈總參謀長溝通,無視《德奧同盟條約》中“締約國一方遭到俄國的進攻,他方應以全部兵力援助,并不得單獨媾和”的條款;在戰爭哲學上,軍人施利芬自絕于政治且引以為傲,基于距離、兵力和火力等軍事參數進行單向的、靜態的運算制定戰爭計劃,將前輩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警惕政治因素帶來的戰爭迷霧”[⑤]等忠告拋諸腦后。諷刺的是,普魯士總參謀部先驅卡爾·馮·格羅爾曼(Karl von Grolman)百年前就曾道:“花幾年時間蹲在參謀辦公室里制定一個詳盡的作戰計劃不過是軍事領域的文學創作。”[⑥]一戰前夕,德軍在大戰略上已完全脫軌,政軍關系徹底決裂,以致七月危機中宰相霍爾維格試圖讓奧匈保持克制時,總參謀長小毛奇卻催促盟友總動員,奧匈不禁反問“德國到底誰說了算?”。[⑦]如書所言,大戰略至此宣告終結,德國滑向了自我毀滅的深淵。
四、大戰略之拾遺補缺:海戰思維與帝國命運
在“海權偏執”一章中,本書從地緣環境上分析德國同時發展一流陸海軍的困難,聯系到本書未涵蓋的一戰海上進程,啟發讀者思考:盡管面臨重重阻力,德國依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造艦計劃,但激烈的德英海軍競賽為何最終只換來一次日德蘭海戰的僵局,德國海權之路為何以公海艦隊自沉的悲劇結束?
德意志民族原屬大陸民族,歷史上的生產生活方式缺乏海洋烙印,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核心也是容克土地貴族階級,其戰爭思維發源于深居北德內陸的勃蘭登堡,強調在陸戰中優勢方需主動發起進攻、消滅對手有生力量、占領敵軍陣地和敵國領土,德意志帝國的海戰思維本質上依舊是陸戰思維之延續,[⑧]因此蒂爾皮茨一廂情愿地將公海艦隊(Hochseeflotte)集中于北海嚴防英國皇家海軍(Royal Navy)的進攻。而英國的海戰思維可以追溯到格勞修斯“海洋并非陸地,不可占而有之”的思想,經過馬漢“經濟利益至上論”[⑨]的發展,到了一戰時已將用兵重點放在控制大西洋遠洋航線和貿易據點上,對于北海這種在全球經濟利益鏈中無足輕重的“死海”缺乏興趣。由此可見,德英陸海戰思維的對立創造了世界海戰史上的奇觀——實力如此之強且距離如此之近的世界兩大海軍“靜坐對峙”長達四年之久(除日德蘭海戰)。然而,平局假象下的事實對德國尤為不利,英國的封鎖窒息了德國的海外貿易,拖垮了德國的國民經濟,而被德意志民族寄予厚望的公海艦隊先是淪為岸防部隊,后以斯卡帕灣集體自沉的悲劇謝幕。
五、結語
《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再現了德意志第二帝國近半個世紀的大戰略演變歷程及其對德國命運的深刻影響。為了完成這項研究,作者不僅廣泛收集了俾斯麥給德國駐外大使的信件、外交文件上的批示,比洛、荷爾斯泰因等要人撰寫的外交備忘錄和個人回憶錄,歐洲各國外交部的公文和電報,歐洲皇室間(維多利亞女王致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致尼古拉二世等)的長期通信等第一手史料,還重點參考了A.J.P.泰勒(A.J.P.Taylor)的《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1848-1918)》和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等國際關系史權威著作。此外,作者精通德語,并得到了聯邦德國國防軍中校在德方文獻翻譯上的幫助,因此能夠避開英文轉譯而接觸大量德語資料,增強了文獻的準確性和研究的說服力。
目前國際環境中存在一種將當下中美關系比作一戰前夕德英關系的論調,而耐人尋味的是,這本研究“德國何以走向自我毀滅”的著作恰好由中國學者徐棄郁寫就,并由“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美國學者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作序。徐棄郁大校在本書中運用大戰略解釋了德國的命運沉浮,為中國讀者提供了從本國大戰略視角思考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的途徑,對中國學界突破西方“零和博弈”、“中美必有一戰”等理論桎梏來解釋中國道路具有非凡意義,這是學術爭鳴,也是話語交鋒。
(作者:廖靖博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①] 黃日涵、姚玉斐:《國際關系實用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②] 王開明:《評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對外戰略——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國際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36-143頁。
[③] Münkler, Herfried. “Spiel Mit Dem Feuer: Die ?Politik Der Revolution?ren Infektion“ Im Ersten Weltkrieg.” Osteuropa, vol. 64, no. 2/4,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14, pp. 109–25.
[④] Foley, Robert T. “The Real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3, no. 1,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6, pp. 91–115.
[⑤] 〔德〕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陳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86頁。
[⑥] 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p. 54.
[⑦] Echevarria, Antulio J. “An Infamous Legacy: Schlieffen’s Military Theories Revisited.” Army History, no. 53,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1, pp. 1–8.
[⑧] 〔德〕沃爾夫岡·魏格納:《世界大戰中的海軍戰略》,羅群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8-11頁。
[⑨] 吳征宇:《海權的影響及其限度——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海權思想》,《國際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97-107頁。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