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頂尖青年科學家們在研究什么?
·與會者認為,期刊、排名、引用量等指標所反映出來的“學術影響力”不一定能反映某項科學研究是否卓越,很多研究的重要性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被人們認識。一味地追求用這些簡單指標去評價科學,不僅給青年學者造成巨大的壓力,也不利于科學的健康發展和做出關鍵突破。
在科學研究領域,有人“厚積薄發”,也有人“趕早不趕晚”。隨著科學工具的發展和科學專業化的加深,很多研究者年紀輕輕就已經做出重要的科學突破,發頂刊、當教授、帶團隊……成為科學探索的新銳力量。
2024年10月25日,世界頂尖科學家青年科學家大會在上海舉行。會上,9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30歲出頭的杰出青年科學家向觀眾介紹了他們的研究成果,主題包括對行星、人體、大腦等不同尺度結構規律的探索,觀測和應用量子現象以及太陽能新材料、生物資源回收利用等能源可持續議題,從理論到應用不一而足。
在隨后的小組討論環節,與會的青年科學家與年長的同行們一起探討了對科學創新、學術自由和激勵機制以及跨學科合作等問題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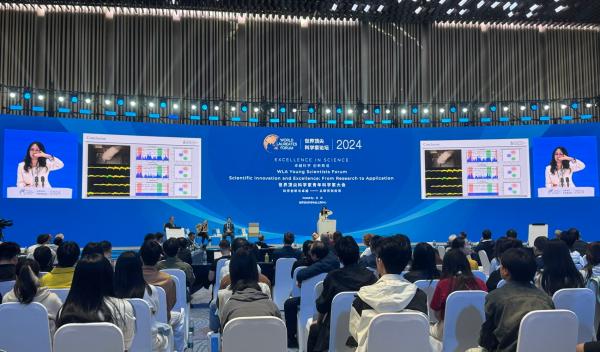
青年科學家在大會現場介紹研究成果。澎湃新聞記者 季敬杰 攝
青年科學人的研究:從星辰到大地,從生物系統到量子世界
“對我來說,研究是由好奇心驅使的。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常常盯著星空,想象其中正在發生的一切。”當被問及為何從事科學研究時,目前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太陽系研究所工作的青年天體物理學家喬安娜·徳拉茲科夫斯卡(Joanna Dr??kowska)回答。
她的研究試圖解答行星是如何形成的。在古典行星形成理論中,像太陽這樣的恒星形成后,剩余的氣體和塵埃會圍繞它形成一個旋轉的“原行星盤”(protoplanetary disk),并在其中通過不斷碰撞和吸附形成更大的“星子”(planetesimals),并最終形成具有引力的行星內核,然后通過吸積氣體成為行星。
通過先進的數學建模以及對比來自太陽系以外星系的新證據,徳拉茲科夫斯卡的團隊發現由塵埃所形成的一種厘米級固體顆粒“卵石”(pebble)扮演了關鍵角色。行星并非由塵埃均勻演化而來,而是通過卵石、星子和塵埃的吸積逐步形成,這些過程中的位置等特點決定了行星的形態。這一新范式對古典理論作出了修正。
如同宇宙一般,人體也是多層次的復雜系統。隨著組學技術(omics technology)的發展,人們已經能夠一定程度上對人體中的基因、蛋白質等分子的特性進行全面分析。然而這些分子具體在人體空間中如何分布,則是一個更難解答的問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鄧彥翔開發了兩項全新的空間組學技術 Spatial-CUT&Tag 和 Spatial-ATAC-seq,通過結合機械工程、大數據分析和生物化學等技術,首次實現了在空間和全基因組水平上觀察組織發育的表觀遺傳機制,對人們理解疾病等生物過程提供了有力工具。
“我是個訓練有素的工程師,所以我對技術問題很感興趣。但同時我也想用這些技術來解決一些具有挑戰性的生物學問題,造福人類健康。”他說。
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科學探索的深入,這樣的跨學科研究已經是新一代研究者工作的新常態。在對神經系統的研究中,香港科技大學的王怡雯成功建立了一個人工智能(AI)模型,能夠根據大腦上游區域(神經活動起始區域)的神經信號來預測下游區域(其它響應區域,如運動皮層)信號。她和合作者訓練小鼠去根據聲音按壓杠桿,并記錄它們在學習過程中的神經活動,再用所得數據去訓練AI模型。
在傳統方法中,獲取準確的大腦下游信號需要通過植入電極等方式來完成,受到倫理和技術的限制。通過AI模擬,研究者就能夠通過行為結果去預測大腦信號,對腦損傷康復、腦機接口等領域意義重大。
“大腦如何產生不同的行為,我們又是如何學習并且與環境進行互動,這些都是我感興趣的話題。”王怡雯說,“這其實是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之間共通的問題,而我正好在這個交叉領域工作。”
面對未知的科學領域,研究者們需要使出渾身解數“鋪路修橋”,創造新的觀察、測量和分析工具,比如在面對神秘的量子世界時。科學家們發現,光子、電子等微觀粒子彼此相互作用時,會陷入一種“量子糾纏”狀態——它們的位置、動量、自旋等物理性質相互關聯,即便相距很遠都能夠“心有靈犀”,彼此感應。
“就像一男一女在跳探戈一樣,相互配合改變自己的舞步。”來自英國赫瑞-瓦特大學的梅胡爾·馬利克(Mehul Malik)形象地解釋道。
這樣的“舞蹈”能同時反映男女兩個舞者的位置信息,處于多個可能的狀態,即“量子疊加態”(superposition)。利用這個特性,人們就能夠構建比計算機比特包含更多信息且能進一步糾纏通信的“量子比特”(qubits),使建造運算速度更快的量子計算機成為可能。
理論上,包含超過兩個“舞者”的“舞蹈”就能包含更多的信息,這就是高維量子位(qudits)。構建這樣的單位計算量更大,信息噪聲更多,更難實現。馬利克所領導的實驗室致力于通過結合大數據建模、實驗驗證等方式,不斷推進高維量子技術的發展。
要“看”到這些微觀世界種種奇妙現象的細節,就需要更有效的觀測工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塞爾希奧·卡瓦霍(Sergio Carbajo)設計了一種光子“錄像”系統,能夠觀測到處于量子糾纏狀態的光子。而浙江大學的宮曉春則開發了國際首個阿秒團簇復合測量系統。阿秒相當于10的負18次方秒,以其為單位的脈沖激光能夠幫助科學家以“慢鏡頭”觀察電子電離過程等現象。
除了上天、入微的科學探索之外,青年科學家在更加“接地氣”的材料、能源領域也頗有建樹。年僅29歲的浙江大學教授薛晶晶主導開發了一種新型鈣鈦礦光伏材料。通過在無機結構中混合有機部分,這種材料展現出了優越的性能。香港科技大學的曾超華教授則領導了多個研究項目,致力于提升有機垃圾等生物資源降解和回收利用的效率,以及優化循環路徑。
青年科學人關心的:創新、自由與合作
在小組討論環節中,主辦方向與會的青年科學家們提出7個主題,內容涵蓋科學創新、科學的社會影響、跨學科合作、與社會各界的溝通、研究與創業以及科學共識等內容。

青年科學家們正在分組討論科學創新、學科合作等話題。澎湃新聞記者 季敬杰 攝
對于科學創新,在場的青年科學家們認為,跨學科合作是創新的源泉之一。而“科學家通常在沉默中工作”,他們的研究通常窄而深,缺乏更宏觀的視角,有時候意識不到其它領域正在發生什么。不同學科使用的術語、思維方式也存在差別,不同專業的人常常難以溝通。此外,有些科學家也缺乏溝通的技巧,不善于尋找“隊友”。這對合作創新造成了阻礙。
“有時候在會上不跟人搭訕,不是因為我刻薄,而是因為我是個I(內向型)人。”薛晶晶說,“就算開得了口,找到合適的合作者也并不容易。”
對此,與會者們認為,為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創造更多交流的機會,以及學習一些溝通與合作的知識,或許能起到幫助。
有人表示,目前“發表至上”的科學成果評價體系也在很多方面阻礙科學創新。比如一項軟件發明,可能相關的論文會獲得一定的認可,但軟件本身卻無人問津。
與會者認為,期刊、排名、引用量等指標所反映出來的“學術影響力”不一定能反映某項科學研究是否卓越,很多研究的重要性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被人們認識。一味地追求用這些簡單指標去評價科學,不僅給青年學者造成巨大的壓力,也不利于科學的健康發展和做出關鍵突破。
“這種帶來科學進步的關鍵性突破,實際上應該是由好奇心、追求樂趣和自由的動機所驅動的。”一位進行總結發言的青年科學家表示。
一位年長的科學家提到,很多“頂刊”手握判斷科學研究好壞的“生殺大權”,其中還有很多非學術的行政因素參與,是不合理的。
目前的科學評價體系對某些研究,如應用研究,更加“偏愛”,導致很多基礎研究創新得不到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對于青年研究者來說,這不僅限制了他們的研究自由,還會導致一些好的科研想法無法付諸實踐。對此,與會者們一致認為,為青年學者和基礎研究設立專門的資助機構是一項行之有效的辦法,在歐洲等地區已有一些成功案例。
對此,科學家有責任向社會各界說明基礎研究的重要性。然而有人表示,科學家與政府、媒體和大眾的溝通并不十分通暢,主要原因是科學的語言常常難以“翻譯”成普通的語言。對此,設立更加暢通的溝通渠道,加強與媒體的聯系以及從事科普工作,都是可能的解決途徑。
而對于科學家創業的話題,很多青年學者表示對其“又愛又恨”。一方面,創業帶來的經濟回報能夠提升科學家的生活水平,助其安心科研,甚至成為科研的資金。而另一方面,大部分科學家不僅可能因不熟悉商業世界而遭遇失敗,還可能會因為創業而擱置科研。
“創業成功了就財富自由了,但如果失敗,那很可能連科研也做不了了。”一位青年科學家說。
最后,與會者們還討論了國際間科學合作的障礙。某些國家對跨國研究合作進行限制,極大損害了學術自由和創新。一位與不同國家的研究機構有著合作關系的研究者表示,這些限制造成極大的不便,也不利于青年學者的成長。
“我相信在場的人都強烈同意科學應當是開放的,而不應該被視為國家的‘秘密’而被‘國家化’(nationalize)。這違反了科學進步背后的所有原則。”會議主持人、美國紐約科學院院長兼首席執行官杜寧德(Nicholas B. Dirks)說,“我們的討論就是科學家愿意合作的證言,是我們對建立全球科學共同體的堅定承諾。”
該論壇是2024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的分論壇之一。據悉,本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由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WLA)主辦,鵬瑞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自2018年創設至今,論壇已成功舉辦6屆,與會諾貝爾獎得主累計超過250人次,中國兩院院士超過150人次,全球杰出青年科學家超過750人次,已成為連接世界頂尖科學家的重要紐帶和促進國際科學界高端對話的重要平臺。與論壇伴生的“頂科協獎”對標世界最高學術水平,截至今年已評選出三屆共9位杰出科學家。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