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和張新穎共讀中國新詩:在詩里找到了現代的自我
在學校,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最有代表性的兩門課是 “沈從文精讀”和“中國新詩”。與“中國新詩”課緊密相聯的一些文字,如今集結成了《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一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近日,張新穎攜新書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青年詩人王子瓜一同做客思南讀書會,編輯胡曦露擔任主持,這三位恰好都曾是“中國新詩”這門課的學生。

從左至右:胡曦露、張新穎、金理、王子瓜
在張新穎看來,大學文學教育如果沒有現代漢語詩歌的課程,是不完整的。“幾乎每一個綜合性大學都有中文系,可是真正有現代詩歌教育課程的學校并不多,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張新穎說,這也是他開設“中國新詩”課程的一大出發點。開課的時候,他給自己和學生都提了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一個詩人,我也不準備寫詩,也不是一個研究詩的人那我要不要讀新詩?”他希望和學生們共同去了解新詩,思考新詩和自己可能會有怎樣的關系。
《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并非課程講稿,而是基于中國新詩具體問題所寫的文章合集,其中提到的詩歌從20世紀橫跨至今,囊括了馮至、穆旦、卞之琳、海子、崔健等詩人及其詩歌的故事。書中的第一篇文章解讀了馮至《十四行集》第二十七首,“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體,讓遠方的光、遠方的黑夜和些遠方的草木的榮謝,還有個奔向無窮的心意,都保留一些在這面旗上。”張新穎在文章里寫到,這首詩讓他聯想到魯迅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在金理看來,這個聯想是敏銳和準確的。“他完整地回到了魯迅當時寫這篇文章的語境當中,而完整地理解這句話,有助于我們去把握馮至那首詩,”金理指出,今天很多人在讀魯迅的這句話時,關注的往往是“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而忽略了魯迅馬上把遠方的世界往內拉回到自己最具體、切身的生命經驗上面,忽略了什么是“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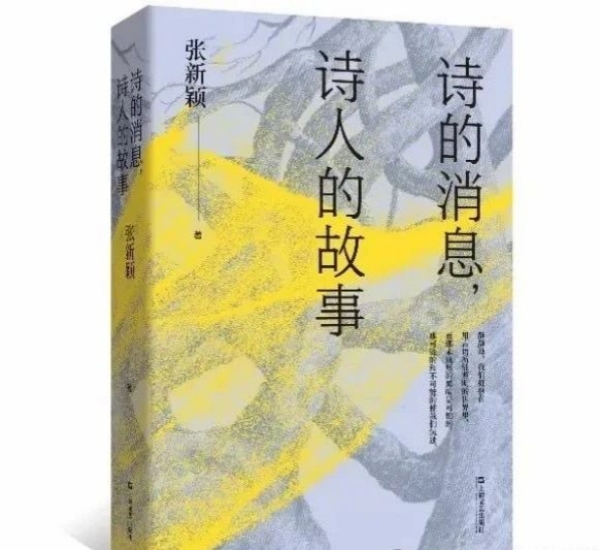
《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
“重讀張老師這篇文章時,我就在想什么叫‘有關’,”金理說,這讓他聯想到蘇珊·桑塔格在《關于他人的痛苦》中對于伍爾夫的批評,她認為伍爾夫對于人類戰爭的反思是勇敢的,但其中有太多濫情的感傷,很容易成為我們觀看別人痛苦的時候,宣布自我清白的一種安慰劑。“在桑塔格看來,這恰恰不是‘關于’,而是把‘關于’的動作給終止了,在這個動作終止的背后是一個不為所動的主體,”金理認為,如今,很多人讀書的入口都是自己熟悉的經驗,無法去領受他陌生的經驗,需要重新關注“有關”的意義,“一方面你要有巨大領受吞吐的能力,另一方面你要尊重很多經驗根本沒有辦法去觸及,不可能被理性所穿透。當你在這樣想的時候,它也讓你的經驗處于更新的狀態當中。”
王子瓜回憶,十年前在復旦上“中國新詩”這門課,讓他對于詩歌有了新的感受。例如張新穎分析沈尹默的《秋夜》,從看似簡單的詩當中,看到了現代世界和傳統世界的分離,現代人自然觀的改變等等。馮至的詩歌中所謂“把住”的沖動,也反映了現代世界誕生后,中國人如何試圖去認識這個世界、把握看似混亂的現實。王子瓜認為,這些解讀讓他意識到,早期中國新詩還有豐富的資源可以去探索。
在《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中,張新穎不僅剖析了詩歌,也講述了詩人們的人生軌跡,在這些詩人的故事里,今天的人也能讀出很多共鳴。例如,書中關于穆旦有飽滿的線索,有詩歌的解讀,也有他在芝加哥大學、西南聯大的求學,甚至在中國遠征軍的經歷。胡曦露認為,穆旦的《詩八首》中蘊含著一個“豐富而且危險”的現代自我,這也讓當下的很多人在讀穆旦詩歌時感受到強烈的共鳴。王子瓜也指出,在張新穎的解讀里,能看到穆旦心中現代人的沖突,還有對現代精神的把握,例如穆旦寫“自由的天空中純凈的電子”,將現代科學的東西融入詩歌,又寫下“盛著小小的宇宙,閃著光亮”,讓人感受到某些看不見的東西。”
張新穎認為,如果馮至的詩是中年人或老年人的詩,那么穆旦的詩就是年輕人的詩,因為穆旦捕捉到了年輕人“從表面到內里的不平靜”,人在不知所措的年紀被多重力量撕扯的動蕩狀態,正是這種獨屬于現代詩的沖突感受使其有了區別于古典詩歌的意義與價值。在他看來, 這個時代的人之所以要讀新詩,是因為它就是這個時代的詩,描述了當下的生活,這與古典詩歌和我們的關系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現代詩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系,”張新穎說,它并不高高在上,但是要讀懂它需要一些學習,在進入一首詩之前,所能做的或許是先擱置判斷,多讀一些,慢慢地進入詩的世界。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