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荒草地:村里的“快樂酒徒”,變老了|鏡相

封面圖源:視覺中國
作者 | 抱布
編輯 | 柳逸
(澎湃新聞·鏡相工作室首發獨家非虛構作品,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夕陽照在一片田壟上,是雞蛋黃的一抹。雞蛋黃投射在我家門口那塊菜園子地上,園子里種滿各式冬季蔬菜。在園的另一邊,則是長滿半人高蒿草的荒草地,在寒風中特有一種荒涼意味。兩塊地的交接處,野草的枝干伸到了我菜園子里來,有許多被母親折枝除掉了。于是草與菜各自生長,遙相呼應,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片風景。
荒草地與我家的菜園子中間,原有一堵石灰石堆成的矮墻,作為兩塊地的區隔界限。農民對土地所屬權的觀念非常強烈,一旦確定了是自家的地,就做些明顯的區隔,以免日后不清不楚而起爭議。
界限這邊是我家的地,界限外那邊是鄰家的地。

荒草地(作者供圖)
二十年前,這兩塊地是反著長的。因家庭生活兵荒馬亂,沒人打理,我家的地常荒著,長滿草橛子。石灰墻外鄰居家的那塊地卻是充滿生機的,一年里總是地盡其用,在春天種上了黃豆,在夏天里收豆翻地,在秋天種上了紅薯。
打理那地的,是鄰居家的一個女人時嬸,她常常一邊澆地或除草,一邊和我們拉著家常。
后來不知是哪一家在石灰墻邊插種上了一溜“臭花”苗,此花因散發難以名狀之氣味而得名。其實“臭花”有個雅名,叫五色梅,這種植物很賤霸,極快地就長成了一道天然植物籬笆,把那石灰墻形成的界限進一步加強了。
五色梅一年四季都開花,花瓣不止一種顏色,呈細喇叭狀,被我們這些孩子一瓣瓣揪下來,頭尾相接做成一條手鏈。
時嬸常常一邊澆地除草,一邊和對面的我家祖母拉著家常。等到祖母走了,她便時常地問著我的話。雖然我才十三四歲,但是已經能少年老成地應和大人的話。
這樣過了三五年,漸漸地,在五色梅籬笆的兩塊地之間就很少發生對話了。
因為時嬸害病走了,那塊春天種黃豆、秋天植紅薯的地從此無人打理。時嬸的三個女兒早早輟學出城打工去了,這一家里就剩下她的丈夫,一個五十開外的大叔,大家都叫他烏力。
我們的鄰居烏力是個神奇的人,他長得高大強壯,愛喝酒,愿意結交些三教九流的朋友。當烏力坐在客廳里與父親喝酒的時候,總能給我們帶來許多新的信息。“只是出不去,要有文化出得去,城里遍地是黃金,只消低頭揀。”有時他把這些話用一種略夸張而自黑的方式說出來,常惹得我們大笑。
也就是說,烏力是一個樂觀而具幽默感的酒徒。這樣的人,在村人眼中多少是不正經的,比如他描述自己和時嬸新婚時的情形:“那還用說的,我可是從頭發頂親到了腳趾頭!”惹得眾人大笑。
男人如此地在外面稀罕自己的女人,在村里雖稱不上驚世駭俗,也是極其少見。然而烏力從不像個安分守己的農民那樣活著。
他不僅言談上大膽,行動上也特立獨行。時嬸嫁給烏力后接連生了三個女兒,生完第三個時,追結扎的公家人來到了烏力的家,讓夫婦兩人到鎮上去做結扎手術。根據當時的政策,如果不配合就要受到懲罰,比如被搬去家里的家具等用品。烏力當時的家里并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但他還是毅然地做了決定,讓時嬸到鎮上去結扎。
人們也有勸的,“再躲躲,說不定下一個就是了呢。”“那點家私值多少錢呢?”可烏力并不那么認為。女兒怎么了?也一樣養。夫妻二人隨后到鎮上去做了結扎。等到他們回來,人們不再說什么,可是肚子里還在嘀咕著。
烏力很愛自己的三個女兒,叫她們“阿崽”。這是一種對孩子寵溺的稱謂,相當于都市中“寶貝”的稱呼。這三個女兒很快長大,個個都出落得婷婷裊裊。尤其是大女兒大美,身子纖細,面容甜美,聲音清韻。只可惜只讀完小學,便跟著村里打工的隊伍到特區去了。去后不久,便開始給家里寄錢回來。到了后來,大美成了烏力的驕傲,每次酒后總要在別人面前夸耀一番。
我父親的行動常常是落寞而散漫的,因此不知道是烏力尋著了父親,還是父親尋著了烏力,總之兩個人混在一起喝酒的時候有點多。
烏力與父親每喝酒,必定要做點好吃的。他的廚藝無疑是出色的,炒菜的架勢如同他的性格本身,揮揮灑灑。他尤其喜歡炒豬大腸下酒,大腸先用鹽腌起來,再用手抓一遍,翻過來,反復地沖洗。等鍋里的油燒得滾燙,烏力把洗凈切好的大腸一揚手撒進鍋中,一頓翻炒,再淋上生粉水,撒入胡椒粉,香味一出來就起鍋。“活要干凈,火候要到,配料要足,別人炒的豬大腸我從來不沾!”
有時到了半夜,父親依然沒有回家。我睡得半迷糊,被臥室外間白色的燈光刺醒,同時聽到父親與烏力兩人大聲說話的聲音。父親與烏力一邊斟著酒,一邊剝蛋吃。見我過來,烏力遞給我一個蛋。剝開一看,里面的蛋黃還有些流溢,深黃一坨,沒有熟透,我猶豫著不敢下嘴。“蛋要八分熟才好吃,營養高。”烏力的話是極其渲染性的,我終于戒除了不敢吃的心理,一邊聽烏力講著許多軼事。
原來大美在城里打工的工廠車間里表現不錯,很快就做上了主管,工資升了不少。烏力還有意無意透露出開小轎車的廠長兒子追大美的訊息。父親是古板的,他聽著烏力說這些,并不發議論。我是有極大興趣地張耳聽,不時還要問幾句。父親便呵斥:“還不快去睡!”

第二天,我看見時嬸一個人在對面的地里鋤草,耕種。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烏力已經不愿意出來種地了。“種地窮一世。”他說。
烏力家在村里先富了起來,最鮮明的標志,就是蓋起了一棟兩層高的白色瓷磚樓房。房子封頂的那一天,我放學經過,見幾乎全村的勞力都聚在了烏力家,篩沙子的篩沙子,活水泥的活水泥,擔磚頭的擔磚頭,一個個滿頭大汗地為烏力家的新房子出力。烏力在一旁端茶遞水,臉黑而紅著,一邊又聊到了大美。蓋房的錢自然是她寄回的。
新房子建起來以后,烏力家的二女兒和小女兒也跟著大美出城打工了。嶄新的房子里只剩烏力與時嬸兩人居住。
烏力家新房子的外墻貼滿白色瓷片,在一片灰撲撲的農村房子中,格外引人矚目。從村外回來的人,遠遠地在村口望一眼,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這棟白房子。烏力與時嬸住在一樓,進門左手邊第一間房子,他們還在房間里裝上了電話機。
我們家沒有裝電話機,彼時外出打工的母親常把電話打到烏力家。每有電話來,時嬸便扯開嗓子朝我家叫喊。我聽到喊聲,匆匆跑去,進門的那一刻卻有些猶豫,好像一個鄉下人進入一個新房子是一個突兀的存在。我徑直走到烏力和時嬸的臥室里,聽完電話就飛快地跑了出去。
他們家二樓在我看來更是一個夢幻,那地板鋪著锃亮的瓷磚,墻壁刷得雪白,貼滿各色明星海報。每間房的門口,都掛著一幕珠簾,珠子輕輕搖曳,如同大美姐妹三人般爛漫。二樓平時是不對外開放的,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我才得以到那宮殿般的地方坐坐。大美從桌上寶氣的水果托盤里抓起一把白鴿糖果遞過來,氣若吐蘭地問我:“你媽媽什么時候回來?”我便感到被關注的緊張與榮耀。
烏力家的新年熱熱鬧鬧的。打工的青年們來串門,坐在二樓的紅沙發上,觀看著CD機里傳唱出各類新年賀歲歌,一片喜樂洋洋。有時候播放最新出的港產武打片子,那是和過去的戰爭片大不相同的解構狂歡美學,尤其令年輕人著迷。
某一年的春節,烏力家異常熱鬧。我隱隱約約聽得時嬸給大美姐介紹了一個鄰鎮的青年,定了年初四那天相看。左鄰右舍都在議論著這個事兒,不知是哪位有福的后生。
然而到了初四那天傍晚,烏力醉醺醺地來到我家。
他在廳里與父親閑聊,一邊訴說著剛剛與時嬸大吵一架的情形。烏力剝開一粒花生,拋物線一樣送進嘴,眼卻盯著我家開著的電視機屏幕道:“這女人真正是頭發長,見識短,它老母個×,她說那男的愿意上門哇!”
“那不正好么?”父親斟了茶回應他。
烏力把花生粒在嘴里咬得“咯嘣”響,然后抿一口茶,道:“沒用的!美崽出去這幾年剛有點出息,你說這又弄回來。沒用的。”
“時姐也是為以后打算,總得老了有個依靠。”父親勸解道。
“不用靠,靠啥靠得住!我看得很淡,老了兩眼一閉、兩腿一伸就是了。”
想不到“兩腿一伸”先走的那個不是烏力,卻是時嬸。
正在他們的日子越過越好的時候,時嬸卻被診斷出得了尿毒癥。那時得尿毒癥對于一個農村家庭的人來說就相當判了死刑。
時嬸走時,女兒們一個哭得兩眼紅腫如桃。烏力卻靜默地,沒怎么哭,也不跟人說話。電話機旁的那張屬于他和時嬸的床鋪被剝去了帳幔和被單,顯得凌亂不堪。那一切都隨著舊人化作了一縷白煙。烏力怔怔地望著這一切,仿佛一個久睡的人沒有醒轉過來。大美紅著眼睛,走到二樓抱來了一床新的被褥,幫烏力把床鋪重新整理了一番。
大美第一次發現,強壯高大的父親矮了許多,坐在床邊就像一堵小山。
時嬸走后的第七天,一個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三個女兒都要離家,再不走就要丟了城里的工作。大美因為與生俱來的責任感,便多請了兩天假留下來陪著烏力。烏力卻對她說:“做你的事去,不用管我。”“阿爸跟我到城里去住一段吧”
就這樣,烏力跟著大美來到了城里,為了陪父親,大美特地從廠里的宿舍搬了出來,在外面租了一個小房子。
在烏力日后的敘述中,那次進城變成一次“進城奇遇記”。他描述大美帶著他游覽世界之窗、逛地王大廈時的情形,那世界的奇觀以微縮的形式來到眼前帶給他的驚詫,那站在近百層的高樓大廈下感到的目眩神暈。烏力沒有描述的是另一面。他看著大美每天早早出去,很晚才回來。這時的大美早已從以前上班的玩具廠離職,和曾經開著轎車追求的富家公子也似乎沒有了什么聯系。據說是對方的家庭不滿她的學歷。這時的大美在一家香港人開的貿易公司里上班,只有排到調休時,才有時間帶烏力到處去轉轉。
在城里待了半年后,烏力終于因為無法忍受城市的枯燥無味,再次回到了村里。從那以后,他開始一個人住在這棟白色的房子里度日。
他偶爾還找父親喝酒,喝多了,開始說著另一套話:“阿美真是實心眼,讓她回老家來找個人家,竟不肯。”那時的大美應該已快到三十歲,在村里人看來是老姑娘了。時嬸走了以后,兩個小女兒反而很快地談了戀愛,早早地走入了婚姻。只有大美還遲遲沒有動靜。烏力有點鬧不清這個大女兒的想法。
去了城里半年的烏力,似乎從失去時嬸的打擊中慢慢恢復了過來,再次變回過去那個樂觀的酒徒,但似乎又與從前的他不一樣。當他把花生剝開,拋物線一樣扔進嘴里的時候,目光常常盯著前面的電視屏幕。屏幕上有時候正放著古裝劇,更多的時候是一些美食節目,甚至是動畫片。當看到節目上的廚師在烹煮一道宮爆雞丁時,他便對人說,今晚特碼出“蛇”,蛇吃雞嘛。這類節目在那幾年的收視率奇高,觀眾們如烏力一樣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想象能力,從平常無奇的現象中發現某種隱秘的關聯。一道家常菜可能隱藏著某個特碼,在動畫片里貓追老鼠的游戲也能被解讀一番。

烏力留在房間的時間越來越長了。在過去那間他和妻子居住的有電話機的一樓臥室里,做了一道暗色窗簾,拉上以后常常分不清白天黑夜。烏力有時候坐在屏幕前直到深夜,第二天醒來已是正午,在夢與醒之間尋到廚房里弄點吃的,找一點酒,很快又縮進了那房間里。
我偶爾從他家經過,能聽見里面傳出“沙沙”響的電視聲。
極少數的日子里,他像個穴居動物一樣走出那間大,迷蒙著雙眼在村里晃一晃。有時候晃到我們家,與父親聊完再次猜錯的特碼,便是罵著娘。最后,他聊到了自己的失眠。
父親勸他把重新把那些屋前屋后的田地種起來,荒著可惜了。
但烏力否定了這建議。
“人生短短幾十年,還要像阿時一樣做到死么?不值當啊。”頓了頓,又說:“我反正也是斷子絕孫的命,做那么多來干什么?不值當。有吃吃,有喝喝!”說完端起手中的酒杯飲盡了那酒,呵呵一笑。
后來,烏力從外頭帶回一個比他年輕些的女人,據說是個寡婦。他恢復了一點過去的揮灑,從不見天日般的臥室里出來的時候多了,每天一大早騎著摩托出去鎮街上買菜。有時還和別人說到那女人如何稀罕著他。
大美姐妹自然很快知道了烏力帶女人回家的事,意見一致地表達了反對。因為她們每月打到父親賬上的錢用得很快,從而感到了可驚的壓力。在大美的追問下,烏力才透露那女人有一個正在讀高中的兒子,每個星期去學校的時候要給的伙食費正是烏力這里掏的。
有兩個月,女兒們沒有再打錢過來。
烏力和那寡婦便常常鎖在臥室里,電視機的聲音重新沙沙響了起來。有時候,烏力看中的特碼和女人的意見不一致時,兩人還會吵幾句。有一次我從窗下過,聽到一兩聲我不該聽到的聲響,紅著臉快快走了開去。
寡婦到后來還是走了。在那之后,烏力又不間斷地帶回過一些女人,都像露水夫妻一樣,過一段日子就斷了往來。根據烏力酒醉后的描述,他和那些不知從哪兒來的女人們不是抱睡在一起,就是爬起來看電視猜特碼。他出來活動的時候,還是和以前一樣高談闊論,但身體比以前肥胖多了,談到激動處,臉色漲紅,像只龐大的發情動物。
自從烏力開始帶女人回家,父親和他的交往就少了,大美姐妹也極少回家。過了兩年,大美回到家鄉,和一個離異帶著孩子的男人結了婚。
十多年過去,烏力再也帶不動女人了。他依然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屋后的耕地長滿了野草,甚至種了幾棵大的桉樹。桉樹生長速度很瘋狂,不幾年便遮天蔽地,到了秋冬,搖一地的碎葉和種子。有時候到某個地方去,不得不穿過那幾地時,便沾滿一身草橛子。一個冬天的夜里,烏力醉醺醺地回來,桉樹刮起了一陣風,把不知什么東西撞得咚咚響。烏力在屋角小解時不禁打了個寒噤。“阿時,你回就回,可不要嚇我。”他后來聲稱,確信自己在那一刻見到了死去多年的妻子。

村里的屋子和貓(作者供圖)
春節我回到村里,在路上碰見了烏力,幾乎快認不出這個當年談笑風生的老酒鬼了。他的身子明顯地矮縮了下去,像一堆泥裹在灰撲撲的大衣里。也許是長期不見光的緣故,眉毛和頭發竟也有些花白。盡管如此,他還能踩著電動摩托出去買菜。
他已經不住一樓那間臥室了,連電視機都淘汰了,搬進了過去女兒居住的二樓。大美回家探親時,給烏力買了一部華為手機,他很快就注冊了自己的微信號,取名快意人生,頭像是一張戴著墨鏡、脖頸處掛著粗黃金項鏈的男人。快意人生常常給父親的微信分享各種各樣的視頻,我有時候幫父親清理手機信息,無意中點開那些視頻,馬上便傳來一陣煽情的音樂和少婦舞蹈,還有一些是勸世良言類的視頻。
快意人生在村里的大群也異常地活躍,村里大部分的人已經住進了城里,但在這個虛擬的微信群中,大家似乎又重新找回了鄉音和過去的親昵。哪家娶親建房有好事了,便在群里發個電子喜帖。每當這時候,快意人生便熱絡地同人攀談起來。他有時也會把那些視頻發到群里。母親節那天,群里有人發了兩個視頻,婦女們曬兒女的禮物。村里人過節也與時俱進了。烏力也來湊熱鬧,他自拍了一個視頻傳上去,在那個視頻里,人們看見一個光著半個身子的老漢,將鏡頭從自己那張大臉開始推移,將整個屋內移了一圈,最后落在墻上的一張靜穆的遺照上——一“你們是不知,今日是母親節咩?”
群里沒有任何回應,都認為他發錯了信息。
烏力有些瘋瘋癲癲起來。他有時帶著貌似歡樂的情緒,甚至有幾分醉意,在群里說些著三不著四的話。“人生嘛,最重要是快樂。祝大家人生幸福。”有時又突然怨懟一番。
一次,群里有個年輕人不會說話,接了一句“有國家養真好”,暗指烏力領低保的事。烏力馬上反擊一通:“你們呢?哪一個不是國家養的嗎?”
他說開了頭,滔滔不絕起來。“噢喲,講起來我慚愧呢,沒生得兒子呢。你們呢,養得大把阿仔,賺得大把錢,好像認為低保沒啥意思呢。你知不知,我日日打針呢......”
因為患了通風,烏力的雙腿走路一瘸一瘸的,經常進出醫院,自稱和醫生護士都已經混得熟了。打幾天針,舒服一些,他出來繼續喝酒。那天他再次坐上我家酒桌的時候,電話響了起來,是大美那一如既往的擔憂和囑咐。烏力哄著電話那邊說:“好咯,阿崽。喝不多,喝不多。”
一天,村干部把生態林的補償方案發到了微信群,引來了一波議論。部分早期出城的村人不太滿意現有的分配補償方案。
烏力聽了,開始大發牢騷:“祖國的山河是你家的么?可不要亂講!說到土地,村里誰有我清?村口大塘都被整去了,你們如今過意得去么?生產隊分田哪一家又沒分到?年輕人有幾個知?如今你們有了錢就看不起烏力。補償款開會怎就沒有通知我?我不是這個村的不成?我以上說的可不是什么好話,大家好自為之。祝大家平安,每一家平安。”
烏力七十多歲,他現在說話常常以一個過來人的語氣自居了。
荒草地上的一棵桉樹不知什么時候被雷打了枝頭,枯萎下去。因為這塊地多年沒有耕種,父親曾試圖說下這塊地,借過來一起種上青菜。這個提議卻遭到了烏力弟弟的強烈反對,甚至跑來大鬧了一通。人人都知道,現在農村的土地又開始值錢了。近兩年,村里的土地進行了新一輪的確權,并在確權后給每家發了新的田證。烏力家的那些地自然也在確權之內。
春節時,烏力的三個女兒帶著大大小小的孩子回到村里來看望她們的父親。荒草地上的一棵桉樹不知什么時候被雷打了枝頭,枯萎下去。大美帶著六歲的兒子回來村里,央人把荒草地上枯萎的桉樹鋸斷,視野一下開闊許多。幾只蜜蜂在草叢中鉆來鉆去,在人間的某一個春天里,烏力卻老了許多。大美回城前還說,要把這些地翻整出來,做孩子周末研學體驗的實驗田。
烏力柱著一根拐,坐在屋門口,瞇起眼望著女兒汽車離去時揚起的一陣煙霧。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本文人物烏力、大美均為化名。)

鏡相欄目此前發布【銘刻“小地方”長期主題征稿】,本篇獨家作品為此次征稿的優秀作品,征稿持續進行中,歡迎各位優秀非虛構寫作者的加入,征稿詳情見海報或【點擊此處】跳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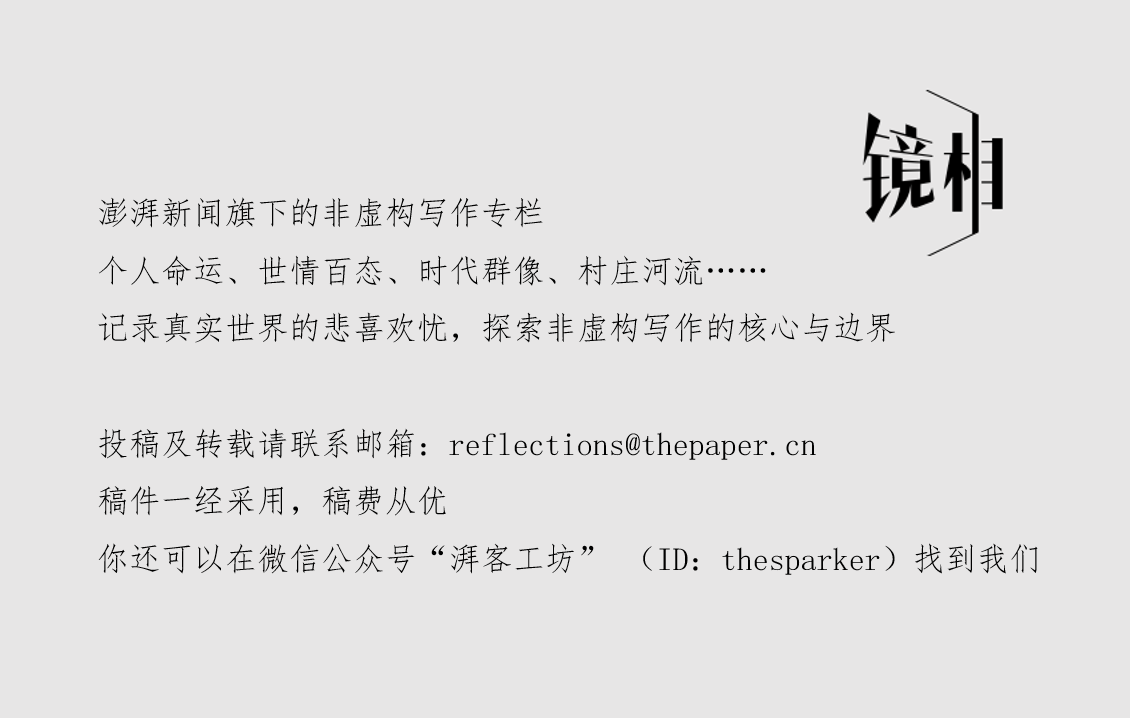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