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蔡炯昊評《上海漂移》|人文主義規劃師的都市漫游與跨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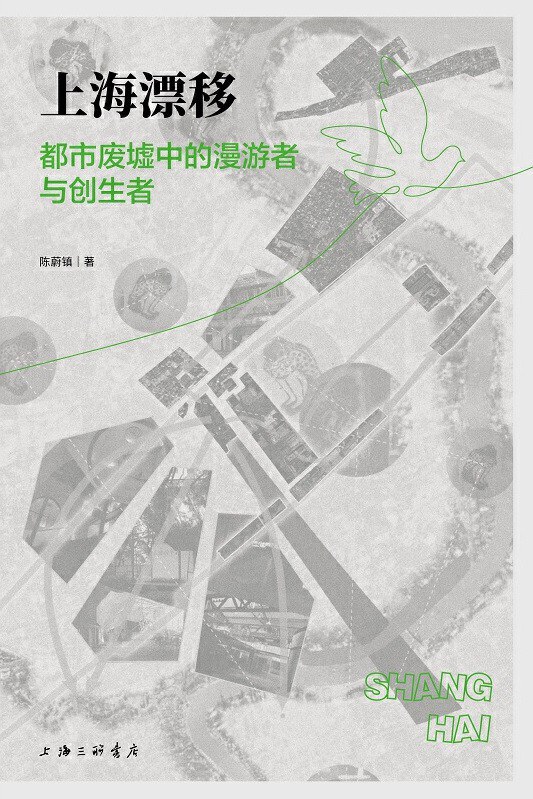
《上海漂移 : 都市廢墟中的漫游者與創生者》,陳蔚鎮著,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3月出版,189頁,67.00元
“城市就像地質學上層次復雜的巖石,不同時期的殘余物消失其中”——王澍:《時間停滯的城市》
一、上海:兩種懷舊
小說《繁花》開篇,金宇澄借阿寶和蓓蒂之眼,描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上海西南部前法租界的一角:“兩個人從假三層爬上屋頂,瓦片溫熱,眼里是半個盧灣區,前面香山路,東面復興公園,東面偏北,看見祖父獨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蘭路尼古拉斯東正教堂,三十年代俄僑建立,據說是紀念蘇維埃處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打雷閃電階段,陰森可懼,太陽底下,比較養眼。”彼時的上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摩登都市文化,被伴隨新社會而來的革命文化海洋滌蕩干凈,茅盾筆下讓吳老太爺驚懼的“LIGHT HEAT POWER”已經消逝。那個年代的夏夜顯得靜謐,西區的街道上,聽得見黃浦江上的汽笛:“東南風一勁,聽見黃浦江船鳴,圓號寬廣的嗡嗡聲,撫慰少年人胸懷。”這是小說中人物的感官,也是作者帶著懷舊之眼描述的記憶景象,上海租界的老洋房、已經大雜院化的石庫門房子,屋頂瓦片如魚鱗;早期的新式公寓和舊時代的教堂屋頂,如城市中的島嶼,構成天際線的焦點。記憶帶著懷舊的濾鏡,也許有不真切的地方,即時性的記錄為我們提供了另外的佐證。1957年五一勞動節前后,沈從文南下出差至上海,在家信中,他用速寫畫的形式描繪了從賓館窗口看到的蘇州河外白渡橋附近,這個城市仍然不乏熱鬧,但變得“十分規矩又極勤勉”,清晨的外白渡橋上“走著紅旗隊伍”,“??船還在做夢,在大海中飄動。原來是紅旗的海,歌聲的海,鑼鼓的海”。上海從紙醉金迷的消費性都會,變成了紅旗海洋中的生產型城市,熱烈但有序。
數十年后,上海再度開始喧囂,城市化以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助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狂飆猛進,近三十年來,作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都市,上海的城市結構和空間肌理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過程中,來自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規劃師、建筑師與政府和開發商配合,參與到各種建設項目之中。無數的藍圖被規劃、無數道路網格在城市的邊緣構建新的骨架、無數樓宇在極其短暫的時間中被設計和建造;城市周邊的農田轉眼成為新的建成區域,而老城區中那些舊的企事業單位、居民區被拆遷或更新,無數人曾經成長或生活的區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李歐梵在九十年代中期研究上海近代都市文化,并在學術界和文化屆掀起一股對舊上海的懷舊熱時,可能意想不到三十年后,九十年代的上海本身成為了懷舊對象,成為了文化記憶和想象的來源,譬如2023年底熱播的電視劇版《繁花》中,九十年代的上海疊印了同時代香港和三十年代舊上海的雙重意象,亦真亦幻。這樣的懷舊符號,能夠引起人們的想象與共情,然而可能掩蔽城市變遷背后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九十年代市場化的繁榮意象與三十年代的記憶無縫對接。另一方面,集體化時代的工廠、工人新村,則成為另一種懷舊的對象,并且在城市改造的過程中被重新“遺產化”“景觀化”。
二、廢墟漫游
時至今日,似乎需要有新的研究回溯這三十年來城市化所帶來的變遷及其背后記憶與情感所系之處。《上海漂移:都市廢墟中的漫游者與創生者》就是這樣一本引人入勝之作。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幾十年來,有關上海的研究與書寫在不同學科中可謂汗牛充棟。文學的、歷史學的、社會學的、建筑學的、城市規劃的研究令人眼花繚亂,甚至綜合性的 “上海學”也已蔚為大觀,那么這樣一本由規劃學者所撰寫的新著,究竟能帶給讀者哪些新知和思考呢?本書的作者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陳蔚鎮,多年來和她的團隊一道致力于規劃實踐與研究,撰寫過不少專業論著。但這本新著與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作者說:“本書呈現了一種上海城市研究書寫的可能,有別于城市歷史研究以及城市社會學或范式的城市規劃研究,也許可稱之為人文主義城市研究。”在這里,“人文主義”意味著什么?我認為是在城市研究中持續的反思以及對多樣性的理解和堅持。正如歷史學家羅新所言:“唯多樣性可通往真理與自由,甚至可以說,多樣性本身就是真理與自由。”
近代以來,眾多城市規劃師采取自上而下的視角,從空中俯瞰城市,在大尺度的地圖上勾勒功能主義主導下呈現規整幾何形態的“光輝城市”,試圖打造現代主義的烏托邦。然而,事與愿違,這樣的城市往往只在圖紙上整齊劃一、光鮮亮麗,當人們進入其中的時候,體驗就不那么好了。文化研究者馬歇爾·伯曼曾經評論巴西的現代主義新首都巴西利亞,認為它是“世界上最沉悶無趣的城市之一”。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所導致的不良后果,已經被從簡·雅各布斯到詹姆斯·斯科特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了深入而犀利的批評,不少反思在此后的城市規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踐。
不過,當上海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進入新一輪快速城市建設的時候,上述反思尚未引起太多響應,畢竟曾經的“東方巴黎”,已經沉寂太久,人們心目中現代化的象征就是摩天大樓與高架路網,一切都顯得時不我待。城市化的狂飆猛進,造了無數光線靚麗的風景,摩天大樓以“超現代主義”的形態出現在新規劃的城市空間之中。其得失利弊,仍然聚訟紛紜。自上而下的視角中,生活在其中的人消逝了,與人們情感相系、血肉相連的場所消逝了、隱身了。在急速變遷的過程中,還沒來得及被重新規劃和建設的空間,暫時淪為廢墟。事實上,正如作者在書中寫到的:“1990-2020年,上海近二分之一的城市空間改弦更張。如果以人類正式的、功能性的活動退出作為廢墟空間的界定,據不完全的統計,上海外環內大約有1000多處廢墟,包含工業廢墟、廢棄花園、舊里以及舊村。”(第4頁)
本書關注的焦點是通常人們所說的廢墟,而且是晚近形成的廢墟。通過對晚近廢墟的探索和思考來打撈上海城市變遷背后常常被大寫歷史所壓抑的那些記憶與情感則是作者的真正意圖。在書中,“廢墟,不是浪漫主義或美學意義上的廢墟。廢墟,或者廢墟探索,只是……傳奇……的隱喻。”(第2頁)作者反思此前在城市規劃專業領域的寫作“常被綁縛于一種學理的或機械的定式”,不過“當廢墟成為寫作焦點后一切都變了。”(第3頁)
作為一本“人文主義”視角的著作,作者的對話對象既包括曾經在這座城市中成長生活的普通居民,又涵蓋了世界上不同時代、國家的建筑師、城市文化研究者和理論家:瓦爾特·本雅明、居伊·德波、列斐伏爾、大衛·哈維、劉易斯·芒福德、凱文·林奇、藤森照信、王澍等名字不時出現在引文之中,“各類有趣的都市研究,來自于哲學、文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或城市科學領域,它們在都市廢墟這樣的邊緣地帶中互相應和,認出彼此。”(第3-4頁)構成“意象蒙太奇”的一個片段,讓讀者目不暇接地穿梭于具體空間情境與精微細膩的理論思辨之間。作為專業的城市規劃師,作者本來是城市空間的“創生者”,應該更習慣于在辦公室中俯瞰藍圖與模型,但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Flaneur)才是作者的精神同道:“他們都是在城市中漂泊、沉溺于思想的人們。他們面對的是現代性的速朽、易逝與新奇帶來的無根與茫然,作為渺小的個體,他們能做的是踟躕流連于都市,穿破裹縛世界的物質與景象的迷霧,在歷史的多層地表下撿拾時空的碎片,找尋被凝固的時間價值。”(第2頁)標題中“漂移”(dérive)一詞意指:“一種穿過各種各樣周圍環境的快速旅行的方法或技巧,一種完全不同于經典的旅游或散步的幽默嬉戲的情境建構行為。”(37頁)。居伊·德波和他的伙伴們,上世紀六十年代巴黎的一群情境主義者“除了在當時的巴黎行將消失的街頭巷尾游走,還去探索了城市隧道、廢棄房屋等被人們以往的地點。這是他們反抗景象化的基礎實踐。”(37頁)事實上,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追隨作者的探索的足跡和文采斐然的詞句,上海城市空間仿佛“一席流動的盛宴”,讀者也在心理層面獲得“漂移”的體驗。
三、人文主義的規劃研究
全書共分七章,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主題,又不斷通過參與式觀察的個案“深描”和理論反思牽引讀者的思緒。在第一章“可見而不可及的城市”中,作者開篇即拋出了一系列意象蒙太奇:2021年5月10日,作者與研究團隊——“都市工作室”,“潛入”正在更新改造的張園片區,以一組集體寫作的文字速寫的形式描述了他們看到的情形。在這里,作者和團隊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專業人士,而化身為都市游蕩者,在“上海初夏的炎熱中,一切顯得嶄新而焦躁”,于是他們“迷失”在都市廢墟之中。在直觀描述之后,作者才開始學理剖析,回溯了上海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的城市空間變遷過程,從政策、經濟因素和欲望、懷舊觀念的虛實兩條脈絡梳理今日都市景觀的成因以及背后的邏輯。政策轉變與經濟發展帶來的資本浪潮重塑了上海城市的空間肌理,一方面使得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以前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區域為中心的部分空間中“上海摩登”意象成為集體懷舊的對象,并被打造為光鮮亮麗的懷舊性消費空間:“懷舊的對象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表征著‘摩登、繁華、現代性’的都市意象”(10頁);另一方面則使大量工廠、普通里弄居民區在改造和拆遷過程中逐漸落寞,甚至淪為廢墟。被保護性更新的空間成為都市中新的網紅打卡地,哪怕是保留了固有的建筑肌理和局部的原真性的案例,作為生活容器的面向已經不復存在。歷史街區的博物館化固然意味著物理層面的歷史場景被保護并呈現給參觀者,但同時也意味著附著在其上的真實生活和記憶已經消散:“懷舊既為了溯歷史之源,也為了發展經濟。”(第11頁)作者兩次探索張園片區的不同體驗,更新過程中的迷失和偶遇,在舊日民居看到的塑料花、巷道中開得正盛的繡球在更新完成后已經消逝在熙攘的打卡游客之中。作者引用文學研究者吳曉東的話頗值玩味:“在某種意義上說,已逝的歷史并非貯存在博物館中,而恰恰是凝聚在無人光顧的廢墟里。”廢墟與博物館構成極具張力的一組概念,博物館意味著大寫的、凝固的屬于所有人的規整歷史;而廢墟意味著游離的、未被重新編碼的空間,指向不斷反芻的、屬于個體的零碎的體驗與記憶。如同顧錚所言:“廢墟的意象越是荒蕪,越是不毛,它所能夠激發的想象力的振幅也許就越大。它因此引起的對于人的聯想也越豐富。因此,廢墟上雖然一無所有,但卻是與可能性相通的。或者說,廢墟就是不可知的可能性本身。”廢墟激發想象與記憶,而博物館則呈現某種確定的知識,知識的背后是特定的權力結構。正如德·塞托所言:“記憶是一種反博物館;位置是不確定的。”
帶著上述反思,作者進入了第二章“廢墟之城-時間之城”。巫鴻曾經梳理了中西文化中廢墟概念差異以及近代以降中國廢墟概念受到西方沖擊后的變化,對此后的廢墟研究者頗具啟發意味。不過,中國城市當中,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伴隨著大拆大建所產生的廢墟則屬于一種此前被關注較少的類型。事實上,在九十年代城市更新發生的當下,就有敏銳的創作者注意到這些廢墟的意義,上海本土攝影師許海峰曾經談及其創作上世紀末上海城市廢墟攝影時的意圖:“我最早的初衷,或者說想的比較清晰的是拍城市更新過程中的短暫廢墟景象。”許海峰注意到這些廢墟的暫時性,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往往是一個過渡形態。

作者援引艾倫·貝格《景觀都市主義》中提出的“廢棄景觀”(drosscape)概念。指出這些景觀形成與近三十年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之中,狀況不一,它們是“城市空間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是城市社會-經濟過程的階段性結果,也是城市增長的必然伴生物。”(25頁)易言之,這些廢墟的空間形態和其中遺存的物件,往往指向業已消逝但并不遙遠的時代:“踏入廢墟,游走在那些上一個生命周期生息尚存的尾聲階段,記憶殘存是重要的,即便那些時間堆疊中的人與景物不過是往昔生活的負累。”(28頁)作者隨即把目光引向豆瓣上頗具影響力的“佛跳墻廢墟探索”小組,小組成立于2018年3月,在不長的時間中已經擁有近四萬成員,分布在海內外各個地區。在這個虛擬的平臺上,成員們分享自身探索廢墟的圖片和文字,交流心得,足跡遍及廢棄廠房、學校、醫院、民居、游樂場、酒店等。作者在這個部分引用了佛跳墻小組成員的探索記錄,為我們呈現了廢墟探索亞文化群體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特征:“身處喧鬧的視覺中心世界,裹挾于圖像或觀念張揚傳播的景象洪流,豆瓣的這個群組是獨特的,他們好像是一群對一切消逝的日常留戀不舍的人,他們在慌亂地和時間賽跑,雖然在席卷都市的時空壓縮中,目睹著物事飛速地被抹掉,會惋惜的人并不太多。”(29-30頁)在第一章中,作者筆下的意象蒙太奇是介于參與觀察者和研究者之間的,描述了一幅有關上海當代城市廢墟的縱覽的、俯瞰的圖景,到了本章,則利用“佛跳墻廢墟探索”小組的材料,進入個體的、零碎的、稍縱即逝的瞬間,在那些有關廢墟的圖文之中,作者有意把界限打破,使得廢墟中那些“迷失”和“懸停”的場景仿佛溢出書外,包裹了廢墟探索的小組成員、作者和讀者。
第三章“穿越景觀的迷霧”中,作者把目光從附近抽回,投到更廣遠的時空脈絡之中。作者回溯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巴黎的以居伊·德波為代表的一群情境主義者的思想和實踐。德波等人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將都市全然“景觀化”(spectacle),街道、建筑、裝飾被包裹為商品,再透過大量復制的圖片傳播和消費。人們看似獲得了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的時間和休閑,事實上則陷入一種被景觀包裹的“異化的閑暇”,圖像在技術化和工業化批量生產,在許多時候“人們喜歡復制品勝于原作”,在毫無深度一元化的消費空間中,城市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被折疊甚至消弭,人們喪失了主體性和感知能力。情境主義者號召大家透過漂移(dérive)反抗景象化的都市空間,進入那些不被注意到的廢棄景觀、背街陋巷中自主探索,從而“保衛城市的混雜性和被多面感受的可能,重申社會生活和城市文化中的勇氣、想象力和游戲。”(39頁)情境主義者在世界各地有著名稱各異的同道,譬如日本建筑學者藤森照信等人倡導的“路上觀察學”,他們嘗試發現和記錄規整城市中一切有趣和奇特的建筑、基礎設施、物件等,繪制獨特的城市地圖。這些“逃離”和“越軌”的實踐都在各自的社會文化中探索了一條反抗景觀社會中沉悶無趣都市的道路。作者認為:“19世紀末巴黎的游蕩者、1960年代的情境主義者和1980年代東京的路上觀察者,以及今天佛跳墻豆瓣社群的小組成員,每個世代,總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踟躕流連于都市,找尋著‘別樣的大陸’。”(63頁)
第四章“上海漂移紀實”,作者再次將注意力收回,聚焦在上海地區廢墟探索的亞文化實踐群體上。在這里,作者從參與“漂移”的“漫游者”轉回作為都市空間“創生者”的研究者身份,對廢墟記錄開展了學術性分析:“我們采集了整個上海地區除去僅有攝影作品的探索記錄之外的232篇廢棄景觀探索記錄,并對其中曾仔細記錄過廢棄景觀探索的40位探索者進行訪談,以此作為漂移紀實主要的分析材料。”(65頁)作者認為在這些記錄和訪談中可以獲取的信息與既有研究中關于廢墟的思考更多聚焦在視覺和審美體驗上有所不同:“平臺記錄、訪談回答所涉及的情緒、想象、思考遠比從審美出發的解釋更豐富。”(68頁)作者試圖在這些記錄中追問廢墟探索者的思想、情緒和意義感。在對個案的分析中,作者發現這些探索者最初的動機也許是好奇或者追求視覺體驗,但隨著探索的深入,追索意義的訴求以及在不斷探索中的短暫“迷失”和持續“尋覓”變得重要起來。因為廢墟空間中一定保持了相當程度上的未知和不確定,所以探索者在失去任何時空和知識上的導覽時,陷入短暫的“迷失”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但也正是這種“迷失”給予了探索者極大的想象空間和滿足感:“從遺留小物件的相關經歷猜測,到對大型設備用途的好奇等,探索從真實的物開始,個人經驗被開啟并建構情境,這顯然不同于陳列館里單一的銘牌解釋式的信息呈現。”(72頁)與博物館解說詞確定性的描述不同,廢墟空間和物件具有多重可能性,激發探索者的想象力和屬于個人的獨特記憶。作者發現,除了想象中空間與物件的歷史之外,探索者往往喚起有關自身“童年”的經驗和記憶,一方面是因為成長經歷中對廠房、宿舍房間和物件的親切感;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探索者面對巨大而沉默的廢墟時獲得了一種類似兒童的視角,獨自面對陌生的、龐大尺度的空間和物件,工廠建筑成為類似童年視角中成人尺度的家具、器物。這樣的多元敘事顯然不太可能在參觀博物館或者更新完成后的建成遺產中獲得,廢墟能夠引導人們尋覓,就顯得具有特別的意義。此外,部分探索者在觀察和記錄的過程中,除了深度體驗、喚醒個人的記憶和情感之外,也會注意和記錄廢墟空間的一些普遍特質和作為“中介”的功能。不同廢墟空間具有不同特質,如擁有大面積露天場地的廢墟往往被居民再利用:種植蔬菜、豢養家禽或者成為社交空間等等。這些觀察和記錄積累到一定數量后,可以成為研究者認知廢墟整體狀況的“數據庫”,而“佛跳墻廢墟探索小組”等類似社群的自發記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廢景演進中的楊浦濱江南段”中,作者開始進入具體的個案分析之中。作為專業的規劃學者,作者對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定海橋和楊浦濱江南段的工業遺址景觀。定海橋呈現的是被城市化進程掃到邊緣的區域:“坐落于上海當下,卻又離散在上海之外,它在物質上的存在和空間上的持續占據,不能阻止它走向時空的廢墟。”(85頁)定海橋有著百年工業化的歷程,不同時代遷入的工業移民擁有漫長的自發建造的傳統。盡管不斷有舊居民遷出,新的外來者遷入,但整個片區仍然保持了自發的活力和看似混亂實則自由多元的狀態。歷次拆遷的浪潮未能波及此處,原本遍布上海多處的生活樣態成為了一個時空的飛地,如果要觀察和懷念早年上海老城區部分區域的生活樣態,這里似乎是一個極佳的窗口。不過,作者的研究團隊中有人發出疑問:“自由難道不是每個人都渴望的嗎?然而,定海橋的原住民不再需要這里了,他們渴望拆遷。”(87頁)是的,雖然五條人的歌詞非常藝術:“農村已科學地長出城市,城市又藝術地長出農村。”但原住民往往與游蕩者和研究者并不共情,生活也遠遠不止藝術與審美。野草般的生機和煙火氣,似乎并不能將生活的逼仄與艱辛簡單地轉化為審美和贊頌的對象,那么城市更新就顯得必要而迫切,只是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樣的更新才是好的?
“從銹帶到秀帶”的楊浦濱江南段與定海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自2016年以來,這片區域的工業遺址被精心規劃更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廢墟逐漸被工業遺址景觀所取代。在這個過程中,廢墟時期的失序被重新建序,混亂的面貌被重新設計的道路、規整的綠化和經過維護更新的部分工業設施和建筑所共同構成的網紅打卡景觀所取代,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在隨后的第六章“空間思辨與情境構建”作者延續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并展現了極具專業素養的反思能力,作者追問:“曾經的過往怎樣才能真正與日常生活共融而內化于未來場所?如何避免借助被淺讀和符號化的歷史信息制造某種視覺消費?如何避免這是一種‘景象生產’?”(105頁)在作者看來,楊浦濱江南段的工業遺址改造與更新,營造了一種在全球語境中能被順滑理解的“銹帶景觀”再生產的案例。但是這種改造所呈現的信息,可能成為“景觀社會”的共謀。更新完成的遺址之中,隨處可見的二維碼和導覽詞固化了場地的意義與歷史敘述,與廢墟不同,在這類景觀中,人們不再迷失和探索,也不再喚起切身的經驗與記憶。而非本地的景觀植物更是吸引游客目光,形成網紅化的打卡視覺焦點。在媒介中生產和傳播的圖片中,更是強化了其全球同質化工業遺址景觀的特質。所謂“秀帶”,秀的恰恰是脫離在地語境的流通性景觀:“從圖像到圖像的傳播和挪用中機械性地固化了地域性景觀的想象,淪為同質化景觀的平庸呈現。此時,與廢棄景觀互為他者的是遙遠的全球工業再生景觀實踐的鏡像。”(116頁)如何避免這種弊端,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做減法:“規劃設計師能做的,是提供人們自我組織敘事的可能性,讓每個個體成為鮮活的主體”(119頁),把空間體驗和記憶還給參與“漂移”的人們,并舉出兩個不錯的設計作品“邊園”和“綠之丘”,這這兩個案例中,人們不會被過密的二維碼信息所包裹,而能夠保持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和隨機性,但場地本身的物質遺存又能成為探索和想象的起點。 沿著這個思路,作者來到了末尾的第七章“廢墟之境”。在本章中,作者再次重申本書的主旨和反思的立場,對“景觀社會”中人們主體性的喪失和建成環境的格式化保持了高度的批判意識。
四、“漂移”與反思的價值
作者在書末再次游走在專業規劃者和普通城市居民的身份之間,她所期待的城市中所具有的多樣性和活力,既需要規劃者的不斷俯身,也需要城市居民的真正覺醒。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城市的每個居民都可以采取自己的方式參與營造和體驗空間的多樣性,并在這個過程中理解何為好的建成環境,進一步思考和理解何為美好生活。
雅克·塔蒂拍攝于1967的電影《玩樂時間》(Play time)中展現了充滿現代主義玻璃方盒子建筑的全新巴黎大都會中機場、大公司看似井井有條實則荒誕無比的官僚制管理方式,使人從屬于機械式的系統。另一方面,在空間上與機場、大公司同構的商場、餐廳、酒吧、新式公寓中,人們看似打破界限:自主游蕩、交流、甚至狂歡,但仍然在觀看與被看中陷入意義不明、面目模糊的虛無之中。人與城市和街道一樣,變得毫無特色,移動變得毫無意義。這讓人很自然想到對現代主義建筑和城市的批判,并且以為在城市規劃和更新改造中賦予街道和建筑可見的多樣性即可走出上述困境。事實上,問題比想象的更為復雜。
當流行的city walk文化將城市行走實踐轉化為網紅地點打卡拍照。移動互聯網的圖像生產與消費主義文化結合,網絡流量直接轉化為現金流量。街道“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現象從實體空間蔓延到虛擬空間,虛實之間的界限被打破,消費主義與景觀社會形成一種牢固的共謀。實體空間中風格不同建筑,無論是古典主義的、裝飾主義的、現代主義的、后現代主義的;街道是寬闊或者狹窄的,都無法阻擋在虛擬世界中被輸出位扁平化的圖像景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居伊·德波所批判的景觀社會,并不一定指向某一類充斥某一類風格的建筑和街道。廢墟本身,也可能淪為消費主義景觀生產的一環,這正是作者在書中反思之后不斷提醒我們的。作者一方面對空間“創生者”也就是專業的規劃設計師提出了期許,同時也高揚“漂移”的意義,呼吁人們:“在呼嘯前行的大都市中,觸摸到時間,度量著空間,體味到慘酷的時空法則,從大都市賜予的‘厭倦與麻木’中醒來。”(129頁)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