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亞當·圖茲談多重危機時代的政經學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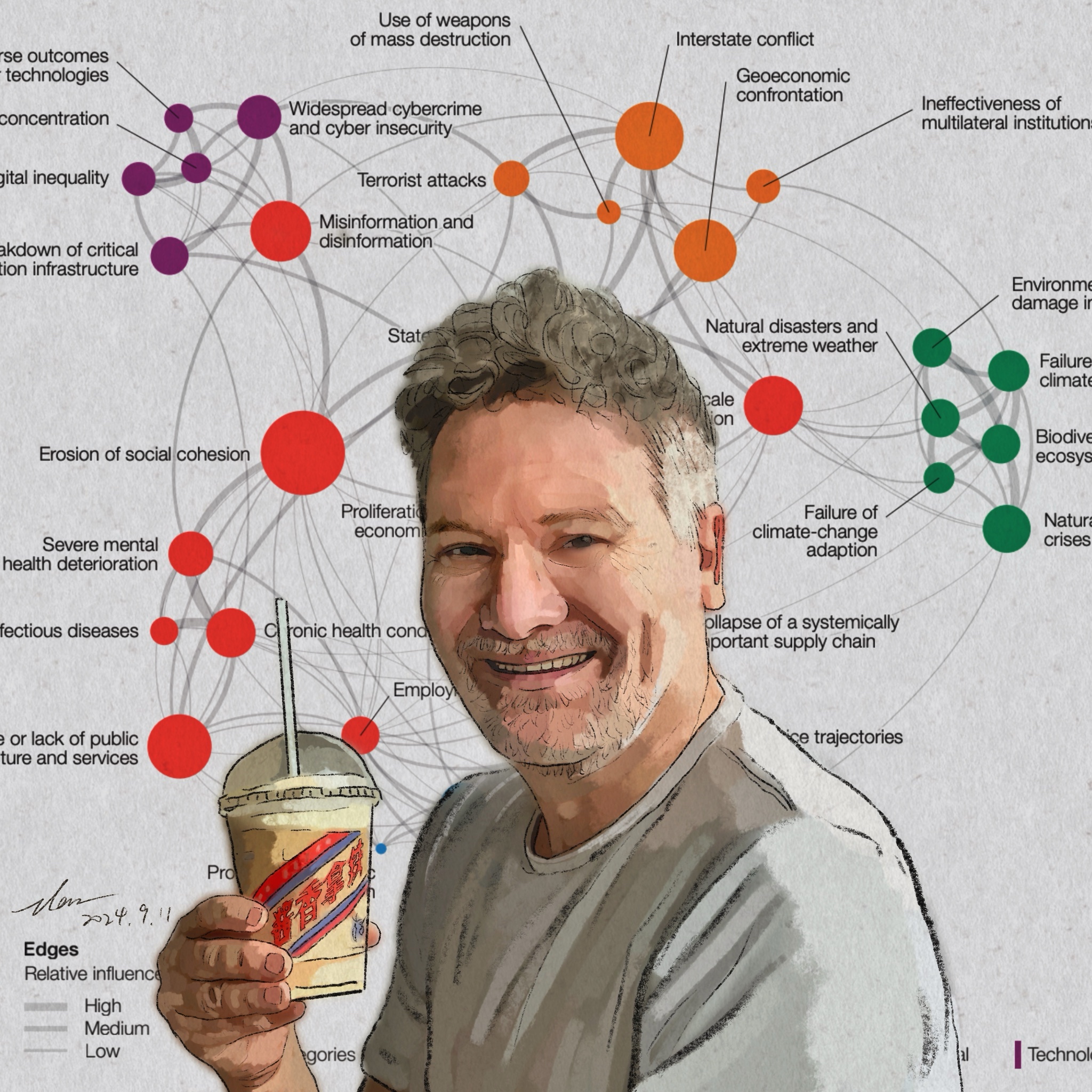
亞當·圖茲(章靜繪)
亞當·圖茲(Adam Tooze)是典型的政學雙棲動物。他長期致力于經濟史研究,尤以危機相關議題為重心。他于2001年出版的處女作《統計與德意志國家,1900-1945:現代經濟知識的形成》(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考察了宏觀經濟知識的誕生,這些知識也推動了他在劍橋任教期間完成的第二本書《毀滅的代價:納粹經濟的形成與崩潰》(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2006)的敘事。2009年,他轉會至耶魯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其間以一戰時期的全球金融體系為主題,撰寫《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 2014),描述了美國經濟與軍事力量重塑世界的過程。
目前,圖茲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兼歐洲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他出版了《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2021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時,他又推出了《停擺:新冠疫情如何撼動世界經濟》(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憑借對危機的研究,圖茲已成為全球決策圈的常客,不僅活躍于達沃斯和對沖基金峰會等場合,還參與拜登內閣的經濟顧問會議。
您能談談《停擺》(2021)和《崩盤》(2018)的關系嗎?——這兩本書、兩場危機、兩次政府對危機的應對之間有何異同,存在怎樣的連續與斷裂?在讀《停擺》時,我注意到許多與《崩盤》的相似之處。什么是新的或不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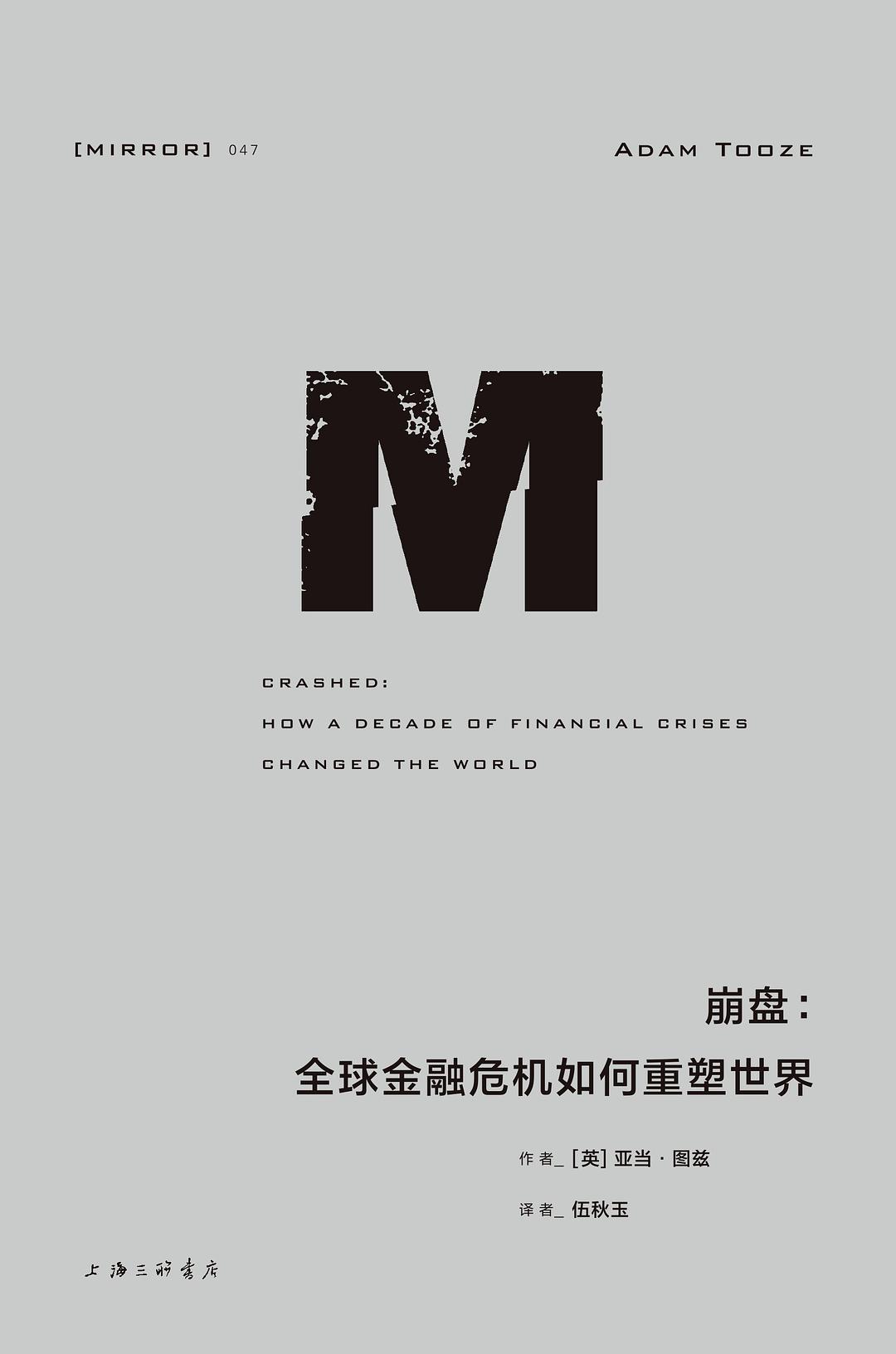
圖茲著《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
亞當·圖茲:《崩盤》的最初設想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十周年的時候,出一部歷史回顧。在2012年啟動這個項目時,仿佛一切都塵埃落定,歷史已重歸平穩——奧巴馬成功連任,德拉吉(Mario Draghi)穩住了歐元區。但沒過多久,危機又起:先是2014年1.0版的烏克蘭危機,接下來是希臘國債危機,然后2015年東亞金融動蕩,再到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于是,原本計劃中的十周年回顧,變成了對持續危機的長達十年的動態記錄。老實說,想在十周年之際完成這本書,確實很困難。就像我們前面聊到的,穩定的前景似乎日漸渺茫,歷史正以有些陌生的方式推進。在勉強完成《崩盤》后,我開始尋找后續的寫作方向,本來考慮寫氣候變化,但疫情的暴發讓我改變了主意,寫了《停擺》。你說得沒有錯:《停擺》是《崩盤》的延續。
從宏觀金融史的角度看,這兩本書主要的實質區別在于:《崩盤》的核心是2008年的私人銀行危機(以及歐元區的后續危機)——政府通過資產負債表將其平息;《停擺》的核心則是美國政府債務(debt)市場,即國債(Treasury)市場危機,時至今日,這依然是過去二十五年里最被低估的金融事件之一,甚至可以說,它比2008年私人銀行危機更危險。原因很簡單,美國國債市場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樞紐。當我們談論以美元為基礎的貨幣體系時,除了貿易,實際上指的就是美國國債市場。美國國債是大額美元儲備愿意投資的“安全資產”。整個美元體系的基礎便是美國政府的債務,這些債務的市場本應流動性充足,卻在2020年幾近崩潰。2020年3月,為穩定國債市場而采取的措施規模比2008年大了一個數量級,這反映了當時風險的嚴峻程度。更令人驚訝的是,這場穩定行動不得不在特朗普政府執政的最后一年、我至今認為仍被嚴重低估的美國國家危機中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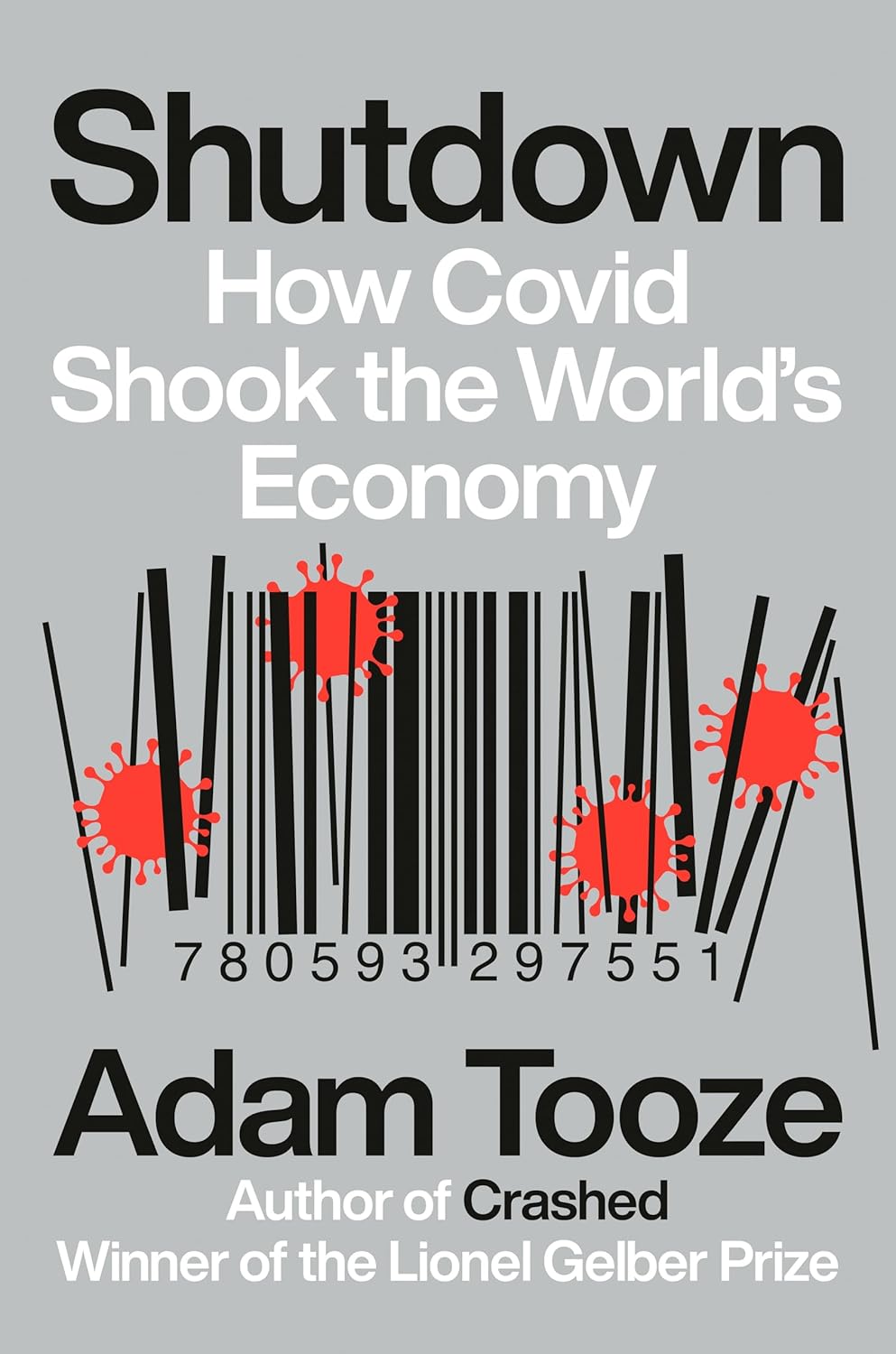
圖茲著《停擺:新冠疫情如何撼動世界經濟》
從風格和結構來看,《停擺》無疑是《崩盤》的續篇。不過,它描述了美國國家危機的升級,這一點在《崩盤》的結尾我僅略有提及。《崩盤》完稿時,特朗普剛剛上臺,因此治理危機尚未成為焦點。而到了《停擺》,美國政府的危機已成為絕對的核心議題。這是兩本書之間的聯系。
這兩本書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寫《崩盤》時,我主要思考的仍是資本主義體系和全球化地緣政治內部產生的危機;而在《停擺》中,我試圖處理我所謂人類世——人與環境互動引發系統性動蕩的時代的第一次全面危機。我認為這是理解疫情的最佳方式。就此而言是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疫情是邁向“多重危機”觀念的鋪路石,從我在《停擺》中對該詞的討論你可以發現,這是一個“本土范疇”(native category),是歐洲官僚和政客喜歡用的術語。
這兩本書和兩場危機還通過一段內嵌的學習歷程緊密聯系在一起。包括我在內的一批人對2008年危機所作的反思,直接影響了2020和2021年應對新冠沖擊的政策反應。這在德國政府,特別是德國財政部長舒爾茨(Olaf Scholz)團隊,以及美國國會民主黨領導層中都有明顯體現。對2008年應對措施局限性的反思,特別是對歐元區失敗原因的深刻總結,極大增強了德國避免重蹈歐元區災難覆轍的決心。在美國,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身邊的關鍵人物也受到類似的啟發,于是他們在2021年推動出臺了真正大規模的第二輪刺激政策。這確實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典型例子。對于作為美國央行的美聯儲,情況也是如此。在技術層面上,如果沒有2008年的經驗,美聯儲在2020年不可能采取那樣的行動。
從某個角度看,我在《停擺》中想表達的是,左翼的診斷——我們需要用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措施來應對氣候變化、疫情沖擊等人類世挑戰——以一種倒錯的方式被政府采納了,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更激進的左翼政治力量,如美國的桑德斯和英國的科爾賓,卻遭遇了決定性的失敗。你可以說,現行體制展示了其吸收系統性批評的能力,即便這些批評并非由體制自身產生。
為什么您認為2020年政府支出和央行干預的規模驗證了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這類經濟學說的核心見解?
亞當·圖茲:讓我們先擱置現代貨幣理論,因為它制造了很多煙霧,卻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火花。新冠危機的應對措施所確證的,正是貨幣凱恩斯主義和功能性財政(functional finance)背后的基本邏輯,而這些理論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便已存在。換句話說,基本的教訓很簡單。在遇到真正危機的極端情況下,最有效的應對方案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你同時進行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和財政支出,并通過印鈔票為其提供資金支持。其實都不必用現代貨幣理論(其關注點是貨幣的起源等問題)來解釋。這就是功能性財政的實踐,早在二戰期間,各主要參戰國——無論是德國還是美國的新政政府——都已采用,并由凱恩斯主義者如阿巴·勒納(Abba Lerner)將其理論化。關鍵就是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合作。任何導致債務市場壓力的債務發行,都會被中央銀行吸收到其資產負債表上。這是西方國家為二戰融資的方式,也是我們為應對新冠疫情融資的方式,它是一種強有力的刺激方法。中國在2008到2009年的時候也做了同樣的事,當時央銀吸收了大量政府債務,以推動經濟刺激。這種做法確實奏效,而且效果顯著,由其促成的經濟復蘇速度之快,在美國史上罕見。
您曾在播客中提到,疫苗是一種維持現狀的技術(status quo technology)。您如何理解不同技術解決方案在應對全球挑戰中的作用?
亞當·圖茲:疫苗就像是黑箱,是一種速效方案。歷數應對當前世界難題的各種技術手段,會發現確實存在一個廣泛的光譜。一端是像人工智能這樣的探索性(speculative)技術,它擁有強大的力量,但我們還不完全清楚它將如何塑造世界。許多人認為它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然后是綠色現代化和能源轉型,在工程技術層面,我們對它們已經有相當充分的理解。綠色電力可以讓我們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但我們得更換汽車類型,改造電力基礎設施,改變發電方式。這些雖然都是重大調整,但主要局限在能源生產等特定領域。
最后是疫苗。轉瞬之間,你從身處險境、時刻脆弱不堪的狀態,變為受保護的狀態。只需簡單的一針,你就可以恢復之前的生活。疫苗侵入性極小,但效果卻極其顯著。相比其他技術解決方案,它們更便宜,開發成本是數十億,而不是數百萬億。總計只需花費幾千億美元,我們就能研發出一個完整的疫苗體系,用以抵御所有已知的人畜共患疾病的病原體。雖然目前資金尚未到位,但技術已經成熟。從許多方面來看,疫苗就是一種維持現狀的技術——它們能讓我們變得安全,而無需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您覺得人工智能有些被炒過頭了,對嗎?
亞當·圖茲:老實說,我也不太確定。我認為人工智能仍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我們正處在類似索洛悖論(Solow Paradox)的情形:人人都在談論它——據說它無處不在——但實際上它還沒有真正開始發揮作用或帶來太多改變。我在各種演講中被問到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問題太多次了,最后我干脆為它做了一個多重危機圖。有太多可能的發展方向。現下我最擔心的是,目前美國股市對人工智能押下了重注,而這基本上是建立在生產力將大幅躍升的假設之上。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白領和重復性勞動市場可能會經歷劇變,這對就業和社會穩定可能是毀滅性的。我們正在目睹的是一場巨大的、杠桿化的金融賭局,賭的是社會動蕩。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可能會見證一次真正的社會變革;如果不順利,投資者會失望,股市可能會暴跌。而在人工智能表現不佳的同時,社會穩定將得以維持,現有的就業結構也會保持不變。因此,這是一個非常模棱兩可的時刻。
我們不禁會認為,對人工智能作為變革性技術的巨大熱情,反映了一種更廣泛的絕境感——當人們開始寄希望于某種單一的技術靈藥來改變世界時,這或許意味著他們對其他形式的變革已經失去信心。不過,這種看法略帶一些推測性。人工智能有可能會兌現其承諾。在股市,尤其是美國股市,大家總是在尋找下一個大熱點、大故事,而現在,人工智能就是那個熱點。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回望過去,您怎么評價“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當然,鑒于這位在任總統目前的聲譽(采訪時正值拜登與特朗普辯論后不久),或許得給它換個名字。
亞當·圖茲:我與“拜登經濟學”的關系有些微妙。我常被認為是靠近權力的人,與政治精英有著不自覺的聯系。但實際上我發現,當一些同事甚至朋友在華盛頓掌權時,我感到非常不自在,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我看來,“拜登經濟學”的核心邏輯一直是一種進步經濟民族主義,我對這種立場感到頗為不適,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義色彩和反華傾向。此外,我也認為它的影響被夸大了。我不相信他們這種規模的投資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大批選民的態度和投票模式,這是不現實的,這種情況顯然也不會發生。因此,興奮地叫囂“拜登經濟學”是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似乎不是天真,就是有些虛偽(cynical)。有些人看起來已經被權力的誘惑俘獲了——能夠接觸白宮確實非常有吸引力。無論是與白宮通話,還是親自拜訪,都是令人激動的經歷。我們在電視和電影中無數次見過白宮,你很難不為之心動。但我認為,這種光環已經模糊了一些人的判斷。
我的感覺是,“拜登經濟學”更像是自由派精英們的一種徒勞嘗試,他們在艱難地打造一個協調一致的全球強權的擬象,而非其現實。我曾在時事簡報里把“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簡稱JETPs)形容為“波將金鴨子”(Potemkin ducks)——它走起來像鴨子,叫起來也像鴨子,但可能不是真的活鴨子。這些政策看著好像有條理,似乎對與中國的地緣經濟競爭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實際上,無論是在南非還是其他地方,其對實際發展的推動作用微乎其微。
拜登的許多國內政策也是如此。它們的初衷是實現漸進式發展,當然公平地說,這屆政府已盡其所能。他們也愿意采取更大規模的行動,無奈缺乏國會多數支持。所以他們只能安于力所能及之事,并讓“拜登宣傳機”開足馬力。這些人都很聰明,很擅長推銷故事。許多媒體也吃這一套。“后新自由主義”是個多漂亮的口號啊。但仔細想想,這些政策在任何實質層面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嗎?我不這么看。實際上,我認為恰恰相反——《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這類措施之所以能通過,正是因為美國的政治經濟格局已經發生變化。綠色能源游說團體已經成為一股重要力量,要求美國也提供補貼。政府便做出回應,給予了補貼。但要說是拜登政府從根本上改變了局面,我覺得是極具誤導性的。如果將美國的補貼與歐洲的相比,許多估算表明,后者規模要大得多,盡管組織得不如美國有序。
再說一遍,依我之見,拜登政府所做的,無非是苦心孤詣地為一個日益混亂的局勢,披上一件自由主義凝聚力(coherence)的外衣。我偶爾會在講座里展示一張照片,是拜登2023年支持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的罷工時站在糾察線上的場景。一位在任美國總統參與罷工?這實在太詭異了,卻反映了當下不尋常的政治動態。

拜登在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的罷工現場
在您2021年出版的《停擺》一書中,中國的形象頗為正面。如今,面對外部環境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國內結構調整持續深化等帶來新挑戰,中國經濟“形有波動、勢仍向好”。我粗略統計了一下,在您過去半年的時事簡報中,您提到與中國有關的話題約二十九次。這趟中國行,您去了大連、北京、上海,見到了許多企業家、官員、知識分子和學生,您的印象如何?為什么中國在當下對您如此重要?
亞當·圖茲:考慮到我的歲數——我是1989年本科畢業的——我個人和職業生涯中最大的遺憾,就是直到很晚才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我成長于冷戰時期的歐洲,很多年里,我的視野一直是狹隘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在完成《毀滅的代價》后的五六年里,我逐漸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無知,特別是我過去未曾理解,二十一世紀初的世界基本趨勢是中國逐漸走向全球舞臺的中心。到寫《滔天洪水》時,我便試圖糾正從前的偏頗。我敢說,這本書是為數不多的以相對平衡的視角處理二十世紀早期全球權力歷史的著作,既關注東亞,也關注西歐,尤其探討了一戰期間和1920年代之后中國的軍閥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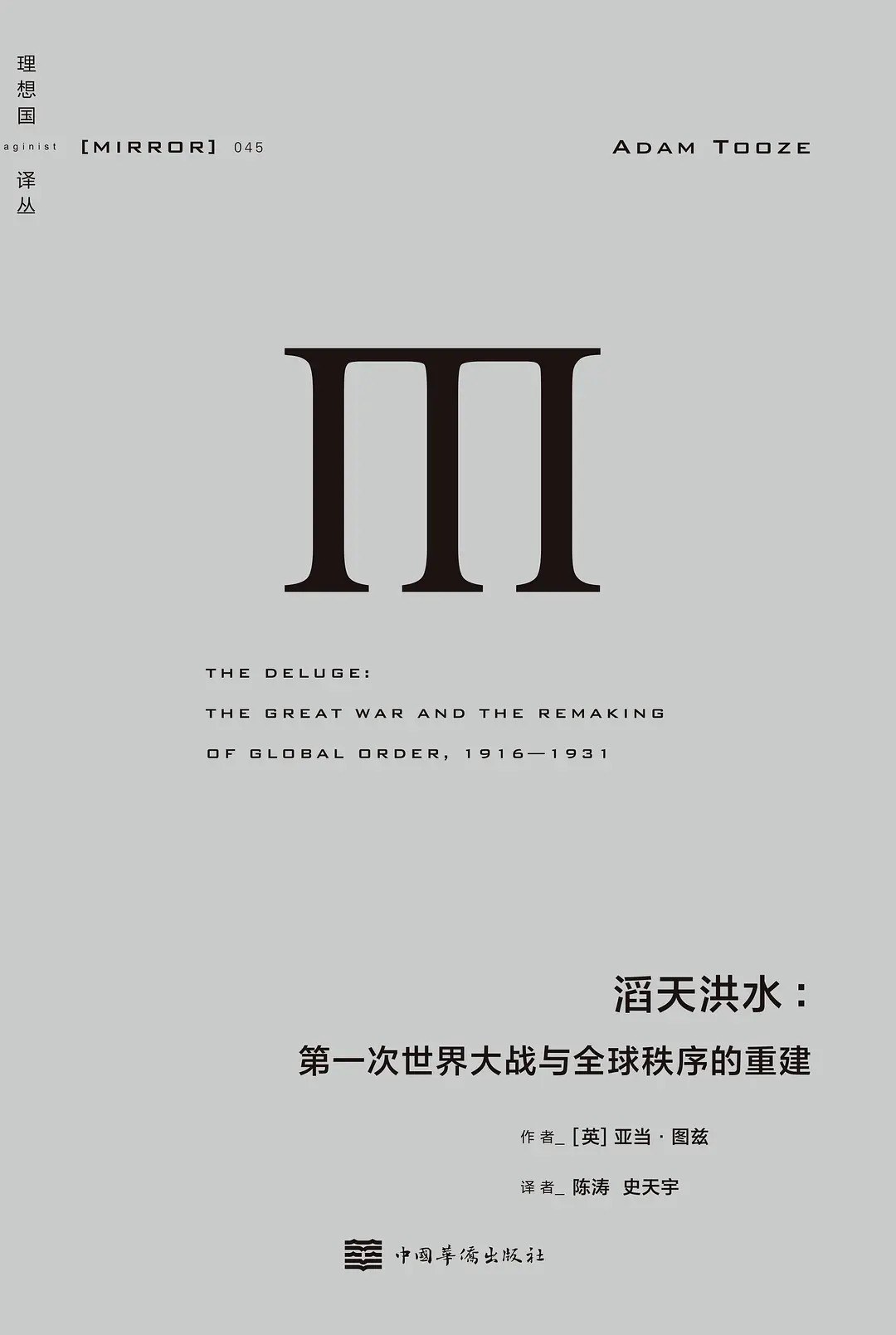
圖茲著《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
從那以后,我開始系統自學,試圖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動態,特別是經濟增長方面,因為幾十年來中國在這一領域一直處于全球領先地位。而我的新課題——氣候變化也讓我必須把中國置于中心。坦白說,我對氣候問題的興趣,部分源于想書寫中國的愿望。當然,我從未認為自己有資格寫一本專門關于中國的書,因為我才剛開始學習中文不久,也并非專業的“中國觀察家”。然而,研究氣候問題使我能夠探討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中心位置。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在我的時事簡報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分量——我每天都在閱讀關于中國的內容。
我在中國訪問期間的見聞是有限的,主要偏重于大學環境,于是年輕人進入就業市場前的焦慮自然成了經常聊到的話題。某些情緒的存在,雖然我之前也有所了解,但直到近距離接觸后才親身感受到,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的視角。一些技術性分析也讓我印象深刻,特別是圍繞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可能和投資信心的討論。過去我僅從理論和書面上研究過這些問題,親眼目睹它們的復雜性,對我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預期,我希望在未來能作進一步更深入的考察。
不過,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綠色能源轉型。這是一場巨大的技術變革,城市環境中新能源車的普及便是其體現。但是,這一轉型非常重要的部分發生在遠離東部沿海地區的地方,因為中國主要的太陽能和風能基地都在西部。在大城市里,我們主要看到的是宏偉的輸電線路,這讓我贊嘆不已,但它們與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大轉型的現實相去甚遠。僅憑上海來判斷綠色能源革命是很困難的——你必須深入源頭,才能真正領會其規模,并全面感受到其影響。
您能再透露些您下一本關于氣候變化的書的內容嗎?除了中國將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還有哪些重點?
亞當·圖茲:這本書追溯了全球氣候政治的演變歷程,起始于科學家首次發現這一問題的早期階段。最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氣候危機被視為一個由西方和蘇聯陣營的排放所引發的問題,它本質上是“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問題,需要北方來處理。換句話說,是“我們造成了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解決它”。接著我們進入了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的氣候政治,以制定《京都議定書》等若干時刻為標志。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這樣的場合,“全球南方”指責“全球北方”說,“你們要負責,你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于是,氣候問題的敘事從北方管控北方內部問題,轉變為南北對抗。
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談判破裂,印度和中國當時直面西方,明確表示“沒得談”。與此同時,中國的排放量也在升高,2006年超過美國,在2011至2013年達到峰值。那幾年,中國部分城市的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轉折點出現在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之后,此時中國的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三成以上,開始積極承擔起應對氣候問題的責任。
從某種角度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勝利的、進步的敘事,中國是這個故事里的英雄。但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這仍意味著巨大的沖擊。對于我的西方左翼進步派讀者,他們似乎依舊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氣候政治中。他們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角度理解氣候政治,認為這是西方進步派與西方惡勢力之間的斗爭,是環保活動家與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這樣的碳排放罪犯的對立。如果你讀美國左翼氣候新聞報道,會發現話題仍然集中在揭露氣候變化否認論、氣候變化懷疑論以及埃克森美孚的惡行。
但如果你去查今天全球最大的二十家企業污染者名單,埃克森美孚排在第五位。誰排在前面?基本上是沙特阿美(Saudi Aramco)、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這些來自新興市場的國有企業,它們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推動了全球增長。重點不在于道德說教,更不在于反過來指責中國。中國的能源消耗是讓數億人擺脫貧困的關鍵。從人均排放來看,中國現在比歐洲高,但遠低于美國。因此,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歷史哲學問題:誰或什么才是推動變革的歷史行動者?
氣候變化可以說是中國取代西方,成為決定性的歷史力量的首個議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的進步派將氣候變化視為對集體理性(rationality)的終極考驗。這正是我之前提到氣候危機時,帶有諷刺意味地稱其為“總體化的最后希望”的原因。現在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如果這個故事有一個好的結局,西方不會是英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成為主導者。這在歷史哲學層面對西方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激進的問題。為什么?因為氣候危機本身就是一個全新的、激進的問題。世界頭號地緣政治強國爭霸賽——造航母和核彈——并不會提出什么新問題。這是個老問題,如今還用如此民族主義的方式討論,未免讓人感到厭倦。超越領先的經濟體是一個集體變革的過程,個體的能動性顯得相對不那么清晰,它更關乎系統的成長。然而,應對氣候變化——目標是在2050或2060年實現凈零排放——需要一種我們前所未見的政治能動性。而這一轉型的主導力量必定是中國。對于這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折,西方尚未做好準備,尤其是在氣候問題上,這是西方進步政治多年來斗爭的重點領域。
這就是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一個關于全球政治中權力與理性中心轉移的故事。
您對“去增長”(degrowth)理論有什么看法?持此論者認為,要真正應對環境問題,僅靠向清潔能源轉型無濟于事,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增長、技術創新從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
亞當·圖茲:他們不可能真的認為技術和投資不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因為這在事實上是與現實相悖的。他們也不可能真的認為GDP增長本身是問題所在,因為GDP衡量了廣泛的事物,其中許多與物質生產關系不大。一個客觀的事實是,近幾十年來,即使考慮到向中國出口的排放,西方仍然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脫碳。因此,在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西方發達經濟體中,GDP與排放的關聯度已經不再緊密。我認為,去增長論的實質,與同GDP相關的技術細節,或對投資和技術變革的立場關系不大——坦率地說,如果是那樣的話,那實在太荒謬了。
我相信,去增長論的核心更多是在向西方精英發出一種道德、情感和文化層面的呼吁。它提醒我們,可能需要放棄某些奢侈的生活方式和服務,比如頻繁的飛行和過度消費。這一觀點得到了排放不平等數據的支持——全球最富裕的百分之十人口,尤其是最頂端的百分之一,其排放量遠遠超過其他人。如果是這樣一種表述的話,我對這一派觀點還有些同情。
但是,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它簡直糟透了。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傾向于綠色增長或綠色現代化的戰略,因為它似乎更有實施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你試圖禁止人們吃肉或限制他們的航班次數,這在短期內根本不可能實現。我們沒有時間浪費在那些不太可能成功的努力上,這些努力可能會讓綠色運動顯得過于高蹈或不切實際,從而帶來意外的負面影響。時不時就有人建議歐洲左派應轉向綠色去增長立場,但這顯然是個選票殺手,注定難以獲得廣泛支持。甚至完全沒有必要涉足那些道德化的爭論,比如是不是首先得非常富裕或享有特權才能主張去增長。這已經是個死胡同,完全沒有必要再去糾纏。
我們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增長與排放的脫鉤。然而,我對我們能否達到去增長倡導者所堅持的那種凈零排放或氣候穩定的水平,并不樂觀。很不幸,我不認為這種設想是可行的。去增長最響亮的呼聲,往往來自歐洲這樣的社會,而這些地方在過去二三十年里幾乎沒有發生過什么變化。當你面對像中國這樣實際經歷了巨大增長的社會,來到上海這樣的城市——一個歐洲從未見過的大規模增長的豐碑——然后說“現在,開始去增長吧”,你不得不質疑自己到底在說什么。現實是,中國的增長相比過去已經自然放緩,所以不用再操這份心了。當前中國更大的關切恰恰是如何穩增長。
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圖茲粉圈”(Tooze fandom)的。您的自我定位是當代史家(contemporary historian),而我有時覺得您更像是在扮演網上通才(online polymath)的角色。您有一眾自稱“圖茲兄弟”(Tooze bros)的男性粉絲,您與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您曾提到,醞釀中的氣候問題之作可能是平生寫的最后一本書,未來或許干脆專注于寫評論。是不是在我們時代,這是一種更合時宜的知識分子安身之法:隨現實而動,而非著書立說?
亞當·圖茲:有些人從職業生涯的起點就立志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從一開始就瞄準了要做一個多面的公眾人物,既寫嚴肅的學術書籍,也經常發表新聞評論。我當初完全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更不認為自己有這個能力。在網絡智識活動發生的早期階段,我是缺席的:不論是寫博客,還是用推特和臉書,我都接觸得很晚,相比之下,我的不少朋友同事早就是這些平臺的常客了。實際上,直到2015年我才在女兒的鼓勵下注冊了推特。自此,打開了一個新天地,我整個人仿佛更新迭代了一樣,變得多產起來,我發現寫作容易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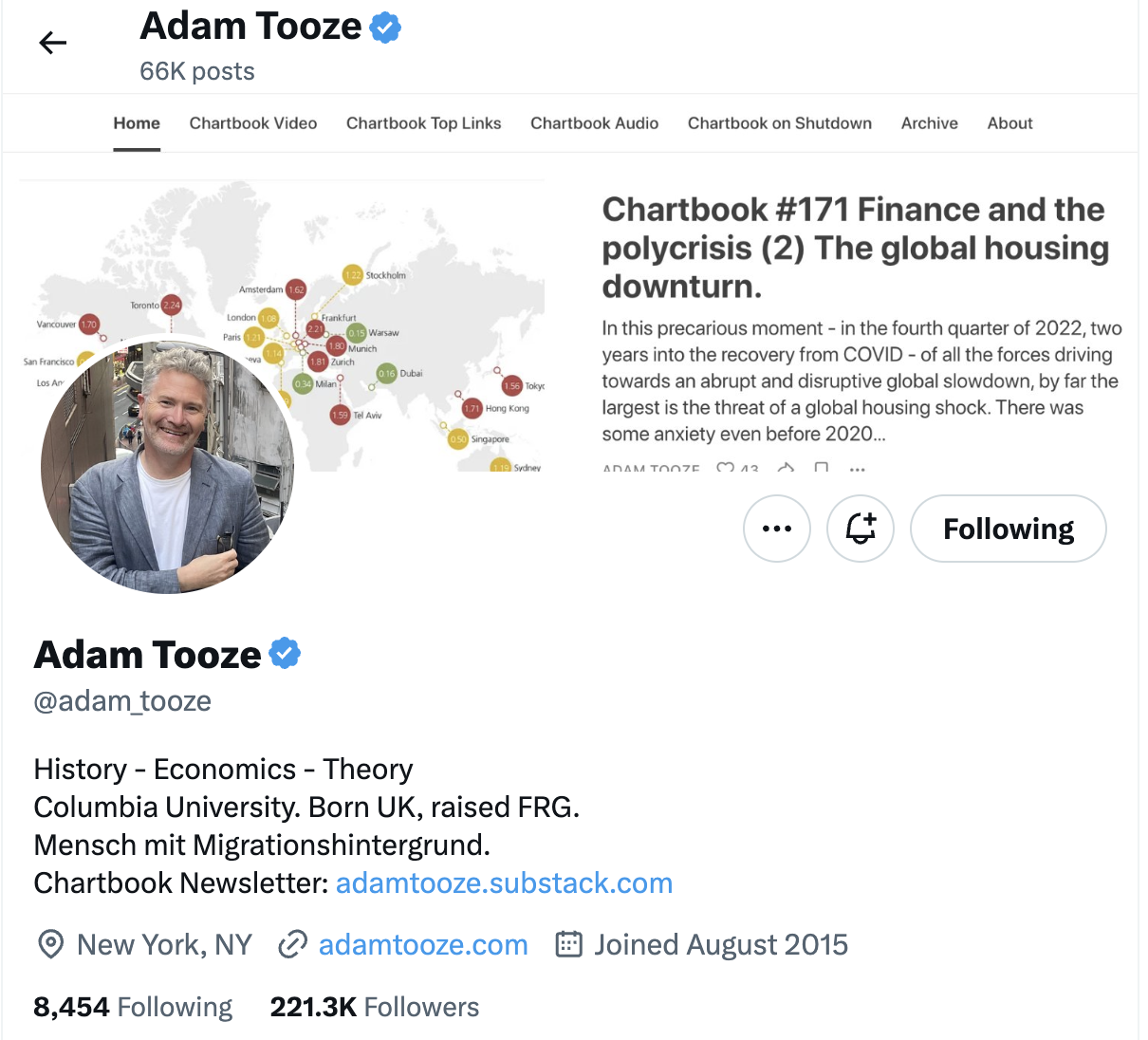
圖茲的X(原“推特”)賬號
最終,在一些人眼中,我竟成了某種榜樣,盡管我不愿輕易承認這一點。我想,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知識分子巨星云集的時代,現在很難說出一個名字,能紅成像當年福柯那批人一樣。但我依然認為,人們——也許尤其是年輕男性,但絕不僅限于他們——仍然希望有人能示范在當今世界的公共空間如何做知識分子,他們在尋找這樣的榜樣。我很驚訝有人把我看成了這樣的人,這并非我的本意。
我父親是一名資深科學家,我們之間的關系非常糟糕。他才華橫溢,學識淵博,但卻出了名的難相處,所以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他未必能帶來積極影響。鑒于我和他之間的緊張關系,如何成為一名杰出的男性知識分子于我而言一直是個挑戰。我想,除了選擇立場、志業和具體行動的政治問題外,重新審視男性氣質、重新思考男性知識分子的角色同樣是一個急迫的問題。
我本人也是數代女性主義者的產物——我的曾祖母、祖母、母親、妻子和女兒都念過大學。捫心自問,我自己隸屬于哪些政治和社會變革的進程,我能想到的有三個:首先是一些實質性的智識議題,比如批判的宏觀金融學(critical macro-finance)、綠色政治經濟學,我和許多同行一起,參與了這些領域新思考方向的形成。其次,我有很強的歐洲身份認同,這種認同感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歐洲統一進程塑造的,對我影響深遠。英國不再是歐盟的一員讓我心碎,但我仍深感自己同這個歐洲一體化進程惺惺相惜。第三大變革當然就是性別——尤其是在美國的語境中:如今,我在一個女性占多數的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在一個女性從業者占多數的專業(歷史學)里工作。于是,男性便有責任重新思考我們在世界上如何立足,重新思考我們渴望成為怎樣的知識分子。我很認真地對待這一責任,尤其是面對那些也許與我有同感的年輕男性。
我盡量在公共場合以開放、誠實、敏感的方式行事。我不在推特上挑起爭端,盡可能不恃強凌弱,努力抑制我過去寫作中那種明顯咄咄逼人的架勢。如果你讀過我早期寫的東西,尤其是評論,你會發現我曾是一個斗爭精神很強的知識分子,我樂于挑起矛盾,制造沖突。我現在不再這樣了。對我來說,無論在公在私,都需要培養一種不同的態度——可能我有些詞不達意,并且在談論這些時感到不自在,甚至尷尬,但這確實是我非常在意并投入大量精力的事情。如果這么做能引發共鳴,并激起任何積極的漣漪,那就再好不過了。
我身處的這個美國學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我堅信,新媒體,尤其是時事簡報這種形式,以及此前的推特、臉書,當然還有中國的微信等社交媒體,為我們提供了公共智識探討和辯論的新途徑。不利用這些平臺是荒謬的。我甚至有點自責,為什么沒有更早參與其中。如今,我必須更明確地問自己,為什么我要寫一本書——這對我來說不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我分明可以通過時事簡報觸及大量讀者。如果說我的目標是對人產生助益(useful),那為什么還要訴諸書呢?答案是有的,我很確定,只是與之前不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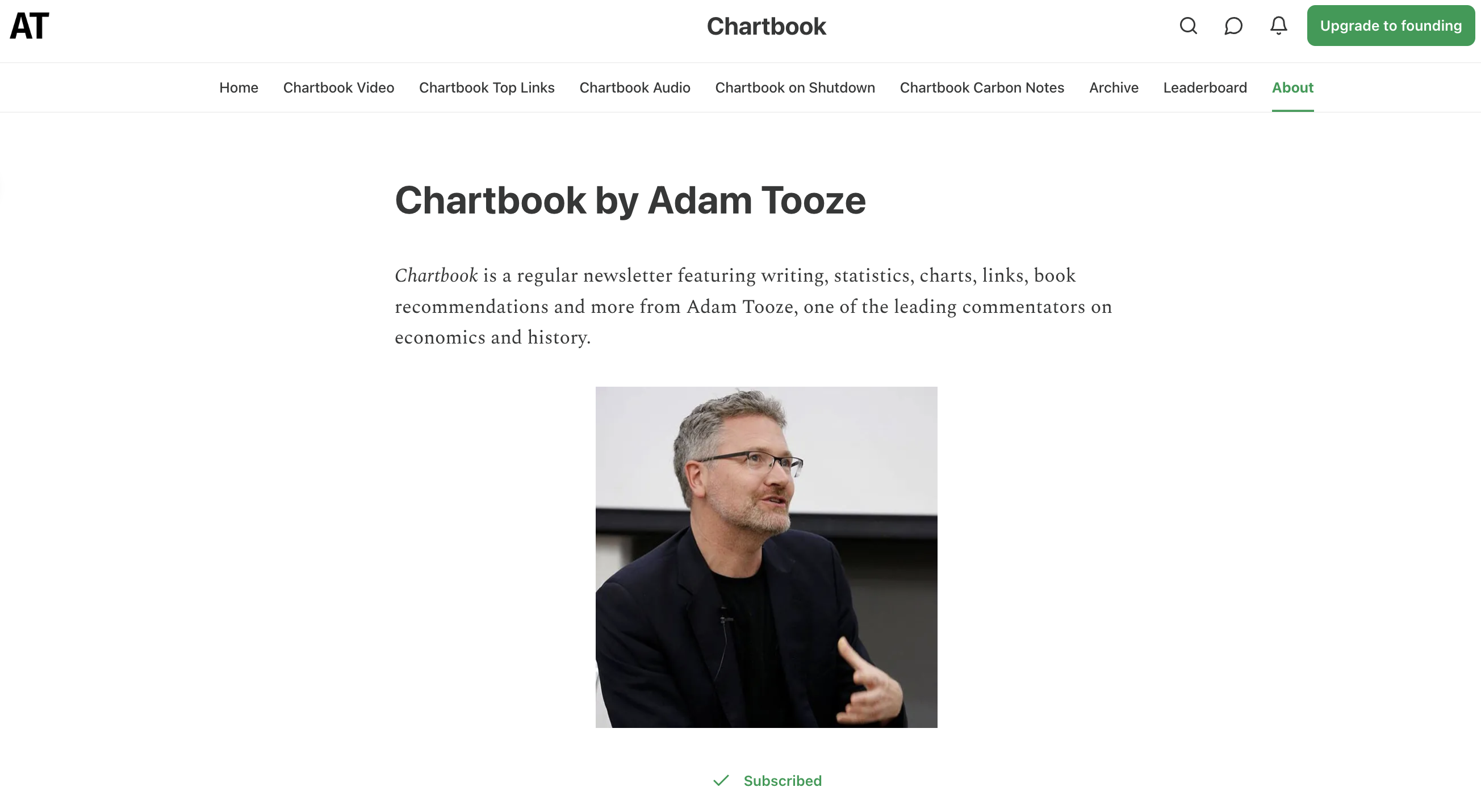
圖茲的時事簡報(adamtooze.substac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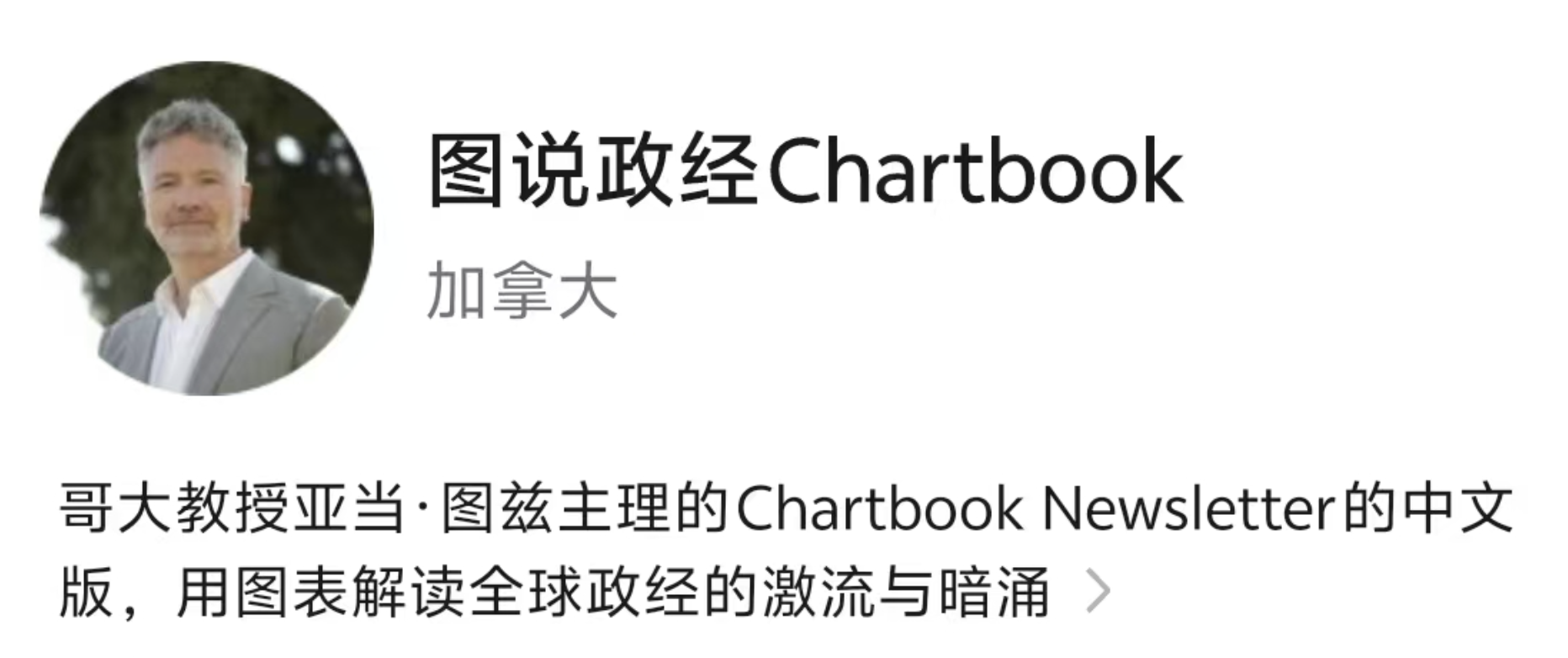
圖茲的微信公眾號
這些問題之所以相關,是因為對我來說,寫書是一個漫長煎熬的過程,耗費心力,因而嚴重影響我的人際關系,它需要在精神極其強大的狀態下才能推進。我過去會一周接受三次精神分析,現在降到兩次。我之所以堅持這樣做,是因為這是一種有生產性的思考和對話方式。在我內心深處,總有一個編織精致的幻想世界的沖動,精神分析把我拉回當下,幫助我直面現實,保持理智。人們常說我的精力充沛,部分原因是我有一種姍姍來遲的感覺,仿佛我年輕時浪費了大量時間,我不想再浪費了。
當下歷史變遷的節奏,真的讓我非常著迷。我隱約覺得,這或許也是引起人們興趣的原因。我的公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一些人自己去做研究,這與“匿名者Q”(QAnon)的動力機制有點類似。“匿名者Q”是最極端的特朗普主義陰謀論,認為美國政府內部存在一個反特朗普的深層政府,它鼓勵其信徒自行開展研究,從而大大促進了陰謀論的自發生成。在我這里似乎有個“自由派版的匿名者Q”在運作,關注我的人經常順著我文章的注釋、材料自己去探索和閱讀。我發的內容并不總有明晰固定的輪廓。我不會向任何人提供一個包裝好的意識形態,比如像安德烈亞斯·馬爾姆(Andreas Malm)那樣主張“生態列寧主義”。我沒有興致,也沒有能力輸送這些標簽。正如我在這個對話里試圖從不同角度解釋的,我認為在與我們的當代現實相遇時,這不是什么正確的立場。
因此,在所謂榜樣示范的意義上,我所做的并不是提供一個簡單明了的模板,而更像是呈現一個謎題。這就好比瑜伽教練對你說的那句玄之又玄的話:“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專注于當下。”試試吧!這太難了。而這正是“置身事中”(in medias res)的啟示——達到全然當下的狀態實在是極困難的。所以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說我處于當下之中時,我把這話當作最高的贊美。
我批判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現實主義時說,他的現實主義是假的,是所謂硬漢行硬事的陳詞濫調。真正的現實主義要難得多,那是藝術家和詩人的領域:如何描述與回應紛繁復雜的現實?我們此刻所在的這家酒店,它背后的政治經濟學是什么?為什么我們在吃這些堅果,而不是別的?這個世界一點都不簡單,這正是它有魅力且吸引人的地方。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會永遠優柔寡斷、猶豫不決,也不是說像“資本主義”這樣的宏大社會力量在建造酒店或供應堅果時沒有起作用,而只是提醒我們,不應該一開始就假設任何事情是簡單的——我們不妨就從酒店建造中的資本主義與堅果供應鏈中的資本主義截然不同這一事實入手。這便是我的時事簡報所要傳遞的信息,它猶如一本剪貼簿,收集了那些我覺得有深度,且能引人思考的事物。在今天的世界,現實主義不是一個公式,它是一個日常挑戰,或許也是一門科學,一項技能,當然,更是一次修行,甚至可能是一種藝術形式。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