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亞洲投資開發銀行:中國式多邊主義路徑的成就、挑戰與對策
自21世紀以來,新興國家已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國際金融機制的不合理性并未得到解決。亞洲擁有全球60%的人口,其經濟總量占據全球的三分之一,然而,由于資金有限,一些國家在鐵路、公路、橋梁、港口、機場和通信等基礎設施方面嚴重不足。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由于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資金有限,無法全面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重要背景之一。
作為區域大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發展體系,并作出建設性貢獻,建立亞投行的倡議使得中國能夠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促進當前國際經濟體系的完善,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出訪印尼時提出了籌建亞投行的重大倡議。2015年12月25日,《亞投行協定》達到規定的生效條件,亞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日至17日,開業儀式暨理事會、董事會成立大會在北京成功舉行,歷時27個月的亞投行籌建歷程順利完成,亞投行正式開業運營,全球迎來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
在全球治理改革背景下,中國式多邊主義應運而生。作為一家為亞洲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的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旨在通過在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富并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其他多邊和雙邊開發機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合作和伙伴關系,應對發展挑戰。作為中國式多邊主義的最佳實踐案例之一,亞投行的建設體現著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變革的思路,即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目前,關鍵問題在于,中國式多邊主義路徑的成效如何?鑒于此,本文將梳理亞投行成立以來的發展成就,對于全球治理的貢獻,當前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一、亞投行成立以來的發展成就與治理效能
亞投行在過去八年的時間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合作伙伴拓展方面,截至2023年12月,亞投行共吸收了52個新成員,成員總數已達到109個,包括93個正式成員和16個尚未核準《亞投行協定》的意向新成員,資本總額達1000億美元。其批準的成員占世界人口的81%,占全球GDP的65%。該銀行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僅次于擁有更多成員的世界銀行。
自2016年成立以來,亞投行在自身治理方面不斷完善,發布并實施了《環境與社會框架》《申訴應對機制》和《信息披露政策》,并制定了《能源部門戰略》《交通投資戰略》和《可持續城市發展戰略》等投融資戰略。截至2022年,亞投行已批準了總額68.1億美元的可持續基礎設施項目融資,較2016年批準的9個項目、總額17億美元大幅增加。目前,亞投行已向35個成員批準了263個投資項目,總計約516億美元,另有74個項目正在籌備中,涵蓋能源、交通、水利、通信、教育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為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能源、運輸、自然災害抵御能力、水務服務、數字基礎設施、性別平等等領域的挑戰提供助力。根據亞投行官網統計,其投資組合中,水利、交通和城市建設等基礎設施項目占比超過50%,能源項目占比最大達22%,其次是運輸和多部門混合投資分別為17%和15%。
除了支持成員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外,亞投行一直在推動綠色發展和融資工具的創新,努力成為亞洲可持續發展融資的領軍機構。作為國際開發性金融俱樂部(IDFC)成員,亞投行遵循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融資的共同原則。為更好地支持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亞投行于2020年9月發布了首個中期發展戰略(2021—2030),明確將綠色基礎設施、促進互聯互通和區域合作、科技驅動基礎設施與動員私營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資作為未來四大投資方向。亞投行承諾到2025年氣候融資項目總額占比達50%、到2030年跨境互聯互通融資項目總額占比25%至30%,以及到2030年動員私人資本相關項目融資占比50%等。2022年6月,亞投行在中國銀行間市場成功發行15億元可持續發展熊貓債。這是可持續發展債券推出后國際多邊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的首單可持續發展債券,為境內外投資人提供了高質量人民幣資產。2022年底,亞投行開展的氣候融資項目占總投資比重已超過56%。在2023第八屆亞投行年會前夕,亞投行表示已兌現了所有新投資項目與《巴黎協定》相關目標完全保持一致的承諾,并提前實現了到2025年氣候融資占比50%的目標。
亞投行的成立和開放,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它符合全球經濟格局的演變趨勢,將有助于使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公平和有效。
第一,亞投行為全球治理帶來新機制。亞投行主導建立的新型合作伙伴關系不僅豐富了全球治理體系層次,而且與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形成了互補共濟的協調發展,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環。亞投行成立后,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密切合作,共同投資項目,并在項目中采用對方標準。亞投行憑借其固有的優勢和獨特性,在提高本地區基礎設施融資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可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使現行多邊體系更具活力,促進多邊機構的共同發展。以東南亞為例,在疫情暴發前,基于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進行“錯位競爭”的邏輯,亞投行對東南亞的項目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然而,疫情暴發后,考慮到亞投行在東南亞基礎設施項目面臨的挑戰以及該地區對經濟復蘇的迫切需求,亞投行靈活應對形勢,將項目投資臨時調整為危機援助。這種轉變彰顯了亞投行的制度韌性和靈活性,有效增強了成員國的危機應對能力,推動了經濟復蘇和建設。這些貢獻充分展現了亞投行的行動力,彰顯了這一區域合作機制的實效性,為成員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第二,亞投行為全球治理帶來新架構。亞投行具有創新的運營模式,已展現出對高標準的承諾,以及強有力的治理和問責制。首先,亞投行合理分配股份與投票權,實繳資本分批繳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副行長兼公司秘書陸書澤表示:“先進國家并不擁有銀行的多數股權,也沒有哪個國家集團主導決策。”他指出,雖然中國是銀行的最大股東,但先進國家(主要來自歐洲)占25%至30%,亞洲新興市場約占50%。其次,亞投行設立非常駐董事會,管理高效。非駐地董事會能夠專注于戰略和政策問題以及成果監測,而管理層則對銀行的決策負責。有效的治理也使得銀行董事會能夠更加專注于指導該機構的戰略方向。最后,投融資效能高,貸款條件合理。土耳其財政和金融部對外經濟關系副總干事艾特金指出,亞洲國際投資銀行將投資與能力建設相結合的務實方法是其作為全球融資機構的優勢之一。共同融資方面,亞投行仍有很大的空間向客戶國家提供貸款,并根據成員的實際履行能力適當調整貸款標準,能使資金盡快進入關鍵領域和特定領域。
第三,亞投行為全球治理帶來新內容。亞投行通過創新實踐有效地將更多的資源引導到基礎設施項目中支持亞洲基礎設施發展,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提供的投資項目,打破了這些國家資金不足的發展瓶頸,以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激發亞洲發展中成員更大的中長期發展潛力,促進可持續發展,推動亞洲和更廣闊世界的經濟增長。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相比,亞投行成立時間較短,但在新興領域,尤其是綠色融資方面已經獲得了認可。亞投行在積極推動氣候投資方面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包括加強專業實踐、強化行動支持和促進專業化運營,為亞洲的綠色復蘇提供了資金和技術支持,構建南北合作與南南合作橋梁,并致力于建立更符合發展需求的綠色金融標準,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
最為重要的是,作為中國多邊主義的生動實踐,亞投行注重協作治理,共建共享共贏。從舊的全球治理體系來看,這些機構的機制設立基本上都是遵循“華盛頓共識”,發展中國家群體話語權嚴重缺失,全球治理結構中利益分配不均衡。近年來出現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逆全球化趨勢,沖擊著國際秩序并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效能。解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矛盾,要靠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邊機制、更加積極的區域合作。亞投行致力于開放的區域主義與可持續發展理念,與發達國家,如英國、德國等建立合作關系,并通過高層對話、人員指派、數據收集等形式進行信息和知識共享,同時在股權和投票權分配上確保中小成員獲得更多權利,并在項目決策和落實中強調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弱勢群體的受益。

二、亞投行所面臨的挑戰
亞投行作為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新策略,已經在諸多領域凸顯治理效能。但由于存在自身不足、發展不均衡、市場競爭、內部分歧以及大國競爭等原因,其未來發展仍面臨制約與挑戰。
(一)自身不足
與世界銀行相比,亞投行資本規模相對較小,融資模式不夠成熟,僅能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合作聯合融資,但基礎設施建設回報周期長,加之亞洲國家資金籌措和還款能力不足,難以吸引私人資本。因此,亞投行需要加強對私人資本的引導,推動金融創新,將更多基礎設施項目轉化為可投資資產,以確保還款來源和實現可持續運營。
(二)發展不均衡
亞投行項目引進的質量以及投融資的方式都會受到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部分投資區域政治社會動蕩,經濟發展不平衡,一體化發展進程緩慢,基礎設施建設無法互聯互通,金融效率與質量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地緣政治問題、不穩定的環境和非經濟因素也影響著外國投資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對于投資需求巨大、風險不確定性高、投資周期長、利率回報低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容易存在償還困境。
(三)市場競爭
基礎設施建設日益成為多邊開發銀行的核心業務,亞投行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及一些國家存在業務競爭。私人資本投資基礎設施的關鍵在于金融創新,然而亞投行在技術、風控和治理方面尚未完善。在亞投行正式運行后,日本把源自公共資金的對亞洲基礎設施的年投資金額比現在增加約三成,通過“亞洲開發銀行”(ADB)這一國際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在內,5年內的總投資額將達到約1100億美元。
(四)內部分歧
亞投行成員內部利益錯綜復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平衡難度加大,可能削弱其內部凝聚力。成員國在投融資條件、對外投資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亞投行面臨協調各方利益和建立有效治理機制的挑戰。
(五)大國競爭
近年來,大國博弈日益集中在全球治理規則變革的較量上。在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后,美國政府采取反對態度,拒絕加入,并試圖阻止其盟友如英國、澳大利亞、韓國等的加入,將其上升到全球戰略和意識形態斗爭的高度。西方社會制造的“中國威脅論”使得一些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產生疑慮或持觀望態度,給項目的推進和亞投行的作用帶來了挑戰。大國競爭背景下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進一步加劇了投資的恐慌,烏克蘭爆發沖突后,亞投行暫停了所有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有關的現有和待處理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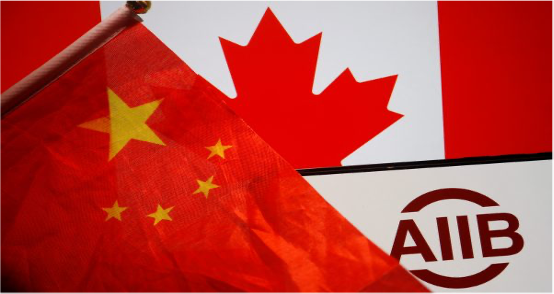
三、亞投行未來的政策努力
首先,在國際合作方面,亞投行應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加強交流合作,學習不同的業務模式和成功經驗,基于自身實際情況優化治理規則和運營標準,以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從而提高其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同時,與商業金融機構的合作也至關重要,可以放大資金杠桿效應,有效調動私人資本的積極性。此外,亞投行還需與各國政府和相關機構深度合作,降低政治風險和市場風險,注重環境和社會敏感問題,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
其次,在政策協調方面,亞投行應加強對外溝通與協調,以增進互信與共識,降低投資風險,兼顧發展中國家和全體成員國的利益,建立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項目評估框架,并與各成員國政府緊密合作,促進項目的順利實施。
再次,在資金調配方面,亞投行應明確投資重點和業務方向,簡化審批流程,通過綜合運用多種融資方式、維持信用評級、調動私人部門、社會資本參與融資等,以吸引更多的資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以提供更靈活的資金支持,保障融資效率。同時,創新運營模式,拓展城市化投資領域,與本地產業相結合,促進產業升級轉型,提高項目還款能力,增強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競爭力。
最后,在風險管控方面,亞投行應積極優化資金配置效率、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完善亞洲債券市場,以提高國際資金融通的效率,分散風險,提高收益。通過加強融資前的風險評估工作,并通過金融衍生產品創新吸引沿線地區的外匯儲備投資,分散風險,提高項目的可持續運營性。針對各國投融資模式,建立完善的資金管理流程,以保障項目的順利實施和可持續發展。
結語
氣候變化加劇、生態環境惡化、可持續發展進程放緩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亞投行2023年年會于埃及沙姆沙依赫召開,主題為“全球挑戰下的可持續增長”。年會開幕式上,亞投行行長金立群發表主旨講話指出,后疫情時代全球面臨的挑戰都更為緊迫,基礎設施融資缺口持續擴大,自然災害與氣候變化威脅也愈加頻繁,多邊開發機構的角色與作用受到廣泛關注。
亞投行的成功依靠各方的團結、合作和協同作用。盡管當下存在一定不足與挑戰,但在各成員國共同的政策努力下,亞投行將成為一個新的平臺,幫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繁榮做出新的貢獻,為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新的力量。
(作者:王翊臣,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區域治理與東南亞國際關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