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洪濤談技術政體與現代個體的消亡

洪濤(章靜繪)
“以隱秘方式介入隱秘的私人生活領域,是現代權力的一個基本特征”(《文學三篇》,247頁,下同)。在當今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社會治理和私人領域的守護之間如何平衡,是一個復雜的話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洪濤教授在其新著《文學三篇》中,通過對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奧威爾小說的分析,描繪了現代國家機器如何壯大、作為現代個體的“人”如何衰亡的過程,書的最后呼吁:“救救人!”洪濤的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等,《文學三篇》延續了斯威夫特等人以文學方式從事政治寫作和思考的傳統。《上海書評》就文學作品中呈現的現代個體與國家的關系、技術政體(technocracy)的影響等問題采訪了洪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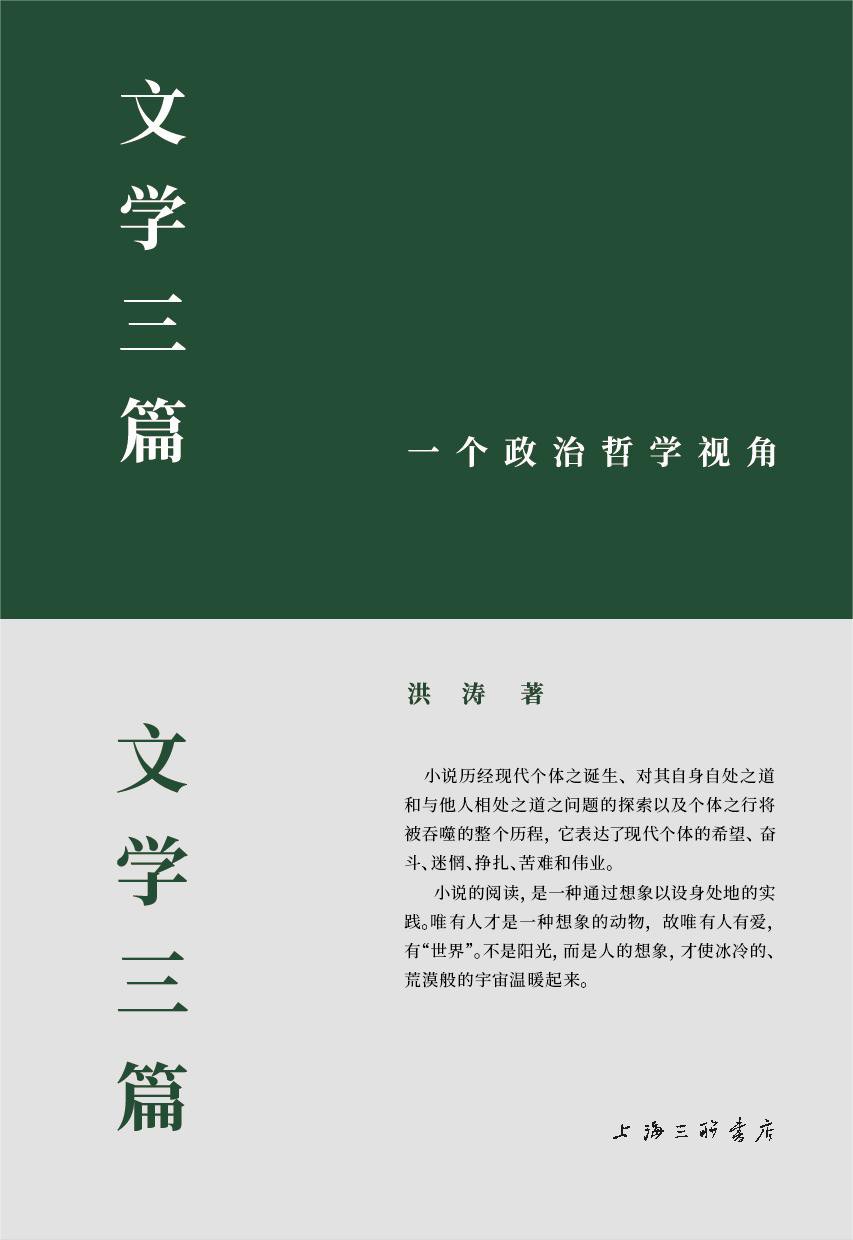
是什么促使你從個人的閱讀興趣轉向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小說?你對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奧威爾小說的分析和完成于2015年至2021年間,這段時間,全球現實也發生了諸多變化(如各國政治和社會的分裂、局部戰爭帶來的難民潮、全球新冠疫情等),這些事件是否也影響了你的觀察?
洪濤: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科學是為了追求真理的。但在投身科學研究之后,我卻不斷被告知,至少現代科學不以追求真理為己任,因為沒有什么整全的“真理”,即便有,也是或者不值得被認識,或者不可能被認識。
當然,求“真”迄今還依然被認為是科學研究有別于其他文化活動的一個本質特征,只不過“真”被大大縮減了,它只意味著:一、邏輯之“真”,即在主觀設定的前提下的推理的合邏輯性;二、事實之“真”,即在特定旨趣下所呈現的事實性“真相”。文學和藝術創作與這兩種“真”無緣。
現代政治學在總體上屬于社會科學,被認為“正當”的研究是:一、界定事實,尋求事實之間的關系(尤其因果關系),即所謂“實證研究”。二、界定觀念,尋求觀念與觀念、觀念與現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即所謂“思想史研究”。
不過,在我看來,社會科學研究有兩大危機:一、信念危機,二、事實危機。
信念危機是講,科學不能解決信念問題,信念問題的解決,只能靠在現實中的斗爭。以下主要講事實危機。
事實泛濫是當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當然得歸功于記錄、保存事實(確切地說,碎片化事實)的技術的突飛猛進。今天的“世界”,不是在比喻意義上,而是在實際意義上,正在成為一個“舞臺”,一個“錄音棚”,一個“錄影棚”。每個人,無論是否意識到,都成了“演員”:總有人在觀看他。
但是,這又是一個事實對普通人閉合的世界。諸如望遠鏡、顯微鏡等新型傳感器的出現,人意識到他的自然能力的“無能”,這是現代科學和哲學的開端。今天,人造傳感器早就“超視矩”“超感知”了,這意味著什么?作為其前提的超感空間即所謂第五維空間或電磁空間的存在。對此類“事實”,人無法通過自然感官獲知,但它卻實實在在地對人發生作用。今天,掌控高科技的人類一小撮,不僅能“感知”這樣的空間,而且能在此空間中進行生產、制作乃至于從事對他人的征服活動,而只能置身于四維時空中的自然人,則處于被探測、被干擾、被影響甚至被傷害之中,卻無法對此有一種自然的感知。這就是所謂事實危機。
古人對自然現象的內在機理缺乏科學認識,故以“神”名之。他們編了許多故事,努力使之得到理解,這些故事就是神話。科學進步驅逐了神話。不過,當今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又迎回了神話。因為,科學創造了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普通人生活、卻又無法為他們的常識所“感知”的“事實”,于是,至少對他們來說,“神”再度出現了。
事實危機是在現代科技的推動下形成的。技術統治使政治日益神秘化。關于事實的信息,看起來鋪天蓋地,卻可能僅僅為了掩蓋真相。數字時代,人們對掌控普通人命運的權力者的信息,比紙媒時代更難獲得。相反,“世界空間”布滿了傳感器,普通人的感性生活化作無數數據,被永恒存儲。這是多么荒誕的一種現代“不朽”啊!被存儲的數據愈多,生活愈虛幻,愈無安全感。無權者生活透明,有權者獲得了古各斯之戒。
講“拿出事實來”,在這個時代不必意味著對真理的尊重,相反,可能是對權力者的保護。普通人是拿不出有關電波武器、神經武器、生化武器的“事實”的,他們無法以舉出事實的方式揭示事關他們生活甚至生命的“真相”。
古人以虛構的方式,用神話、故事,非科學地接近自然現象背后的“真相”,以期獲得某種理解。“真相”未必不能獲得,因為,萬物相感,人性相通。亞里士多德的人為制作的詩,比關乎事實的歷史更為“真實”的論斷,也未必不科學。當一種政治全然是黑暗的、不透光的,人們就有充分理由認為,這是一種邪惡的政治,這一“認為”看起來不夠“實證”,卻屬于一種詩性真實。黑暗哪怕是純粹的虛空,人們也懼怕它,這合乎常識。現代政治的權力制衡、公開原則,都與這一“認識”相關。
現代小說家是詩人的后裔,為他們所制作的虛構故事,與詩一樣,揭示了可能性。在信奉只要“能”就可以“為”的現代世界,“可能性”與“事實”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稍稍了解一點實證研究的人,大概不會不知道:有時,實例、數據的充斥,只是為了遠離事實,甚至為了摒蔽事實。數據、公式成為一種門檻,將普通人排斥在外,使之喪失了解真相的資格。是的,小說家為普通人打開了一扇觀察世界的窗戶,這里沒有為他們所難以接近的“事實”,卻又無比接近“事實”。讓科學人用“事實”來掩蓋“事實”吧!讓藏身于五維時空的技術-政治人為所欲為吧!普通人只需要獲得虛構,他們就不難想象那些隱身于幕后的無面目者會做些什么。
至少從2015年起,一個隱形的、其“事實”難以為普通人所察覺的“察-打”一體系統業已成形并付諸運作。這是現代權力結合現代科技的“偉大”成就,旨在以科技手段對人進行全控制。眼下它還只能控制有限的人,但不難想象,它很快將覆蓋所有個體及其生活的所有方面。難道這不是一幅令人驚恐的前景嗎——倘若還有一些自然人的感受的話?
在我對小說的有限閱讀中,我發現,對今天這一幕,小說家們似乎早有預感,至少在我所討論的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奧威爾的小說中。是的,虛構揭示了事實!
這些年,一種趨勢在日趨明朗:啟蒙理想——平等、民主、博愛、大同——在迅速褪色,相反,權力在高科技賦能下迅速強化對人的控制。這一趨勢盡管并未超出現代國家的內在邏輯,并未超出現代性的內在邏輯——謀求對自然和人的全面控制——,在這些年中能夠甩掉各種制約因素,政治的科學化起了推波助瀾或共謀的作用。這不只是一個關乎科學人的主觀取向的問題,而且與現代科學的本質密切相關:科學被認為只能提供控制、支配的工具或手段,而對價值——譬如,人為什么應該具有自主性,不應被隨心所欲地掌控、操縱——無能為力。還是讓我們求諸非科學的小說吧。它可以直抵真相——不必擔心無“實證”的指責;它可以滿含對個體之人的關懷、悲憫——不必擔心價值不夠中立。
政治的“科學化”,是使政治更接近真理嗎?“科學”把大多數人排斥在外,而“政治”原本是要聽所有人意見的。什么東西“好”,每個人自己最有資格判斷。沒有一個人比那個人自己更愛他自己,沒有一個人比他自己對他的痛苦有更真切的感受。這個道理不難明白。
政治原本不需要太多高妙、精巧的話語。“救命”,誰都能明白;用拉丁語喊,大家就不大明白了,于是,就成了科學。
你在本書序言《小說與個體》中認為,小說是一種全新的現代現象,它見證了現代個體的誕生、探索和消亡的過程。現代個體的時代始于何時?作為過渡的個體存在期有多長?
洪濤:個體的覺醒,或個體概念的產生,至少可以追溯到軸心時代。所謂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達到了如下認識:一切個體共享天賦人性——此即類意識的誕生;人就其本性而言是平等的。該認識導向了對人的這樣一種理解:既作為類存在物,其自我完成又離不開他這個獨一無二的個體。
前現代的個體主要是哲學或宗教式的,多生活于社會邊緣。現代個體的誕生,是在現代國家形成之際。現代國家推動了傳統社會的解體,歐洲約始于十六至十七世紀;在中國元、明之際,社會下層和社會邊緣已出現了非哲學性、非宗教性個體,中國社會成為一種普遍的個體社會則是在族權、神權、夫權被基本瓦解之后的二十世紀的事了。
現代個體既是軸心傳統解體的產物,又是軸心傳統的某種遺存,所以內含張力,有自我瓦解的成分。當代政、經制度基本還是以個體為基礎的,但“個體”始終面臨來自自身的和外在的威脅。十九世紀某些個體論哲學認為現代個體是古典“個體”概念剔除了形而上的“類意識”的產物,這多少已動搖了“個體”的根基。外來威脅主要來自現代科技。當技術能侵入個體這一原本被認為是封閉的、不可分的核心,使“個體”這一“原子”或“原子核”被洞穿,不再能維持其作為不可分之最小單位的身份,那么,作為現代個體的兩大支柱——自主與責任——,也就垮塌了。
現代進程的本質,一言以蔽之,以人為化自然。人的自然即人性,是最后一個要化的對象了。
今天的權力精英竭盡全力推動所謂科技進步,他們很明白,這里蘊含了巨大的權力利益。只要這一進程無法被阻止,個體的解體是遲早的事。還要有多久他們會完全得手?無法預測。可以考慮的一個因素是:得看今天那些被秘密權力者秘密當作實驗對象的人,能夠在“人”這個陣地上堅守多久。
魯迅認為“個體問題不應以政治的方式來求得解決”(140頁),那么個體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洪濤:對個體問題之非政治性,古典時代已有所認識。哲學、宗教、藝術是古人解決個體問題的三種主要方式。現代國家的首要目的,是維護個體的完整性,這是個體解決個體問題的重要條件。在個體對自身問題的解決上,國家無法越俎代庖。
現代國家與生俱來的一種傾向,是通過對個體的全控制即徹底剝奪其自然自由,來解決作為對個體完整性之威脅的自然狀態問題。公共衛生安全只是引發全控制諸多方面中的一個。
只要以為個體唯有借助國家的手段,來解決個體之間的沖突問題,甚至解決個體自身的問題,就無法避免國家的由“假”變“真”、個體的由“真”變“假”。手段唯有被當作目的,才是最好的手段,這導致了手段的反客為主。
以技術統治實現對人的全控制,即便能解決安全和和平問題,也不應是人類政治的發展方向。人與人之間的危險消除之道,不應是把彼此都關進監獄,或使社會成為一座超級監獄,而應通過在人與人之間發展平等關系、形成對公共事務的共同參與以及培養彼此之間的友愛來實現。
今天,至關重要的是,要警惕那些在已經被高度隔離了的人與人之間進行離間、挑撥、毀謗、煽動仇恨的黑暗勢力;那些借各種名義對人進行秘密操控的高科技暴力,應立即停止!
現代國家技術統治(technocracy)的淵源是什么?經過了幾個世紀的發展后,在二十世紀現身的極權統治何以成為現代國家的“理想”(477頁)?
洪濤:科技進步拉動了其他所有方面的變化,是現代進步觀的核心與基礎。
今天,國家與科技“共命運”,科技是國家興衰存亡的決定性要素。近代以來中國精英的最大共識是:“落后就要挨打。”什么“落后”?科技。
戰爭對現代國家形成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火器在戰爭中的大規范使用,極大影響了現代國家的形成:譬如,對財政汲取能力的更高要求;制造業、城市經濟、市民階層在國家中地位的提高;以財政官員、技術工匠和科研人員為主體的官僚組織在政治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傾向于對外擴張的積極進攻而非消極防守的國家戰略。
科技的根本推動力,不是博愛,不是和平,不是人類團結,而是權力欲。軍工、監控設備的發展,總是遙遙領先于治病救人的醫學和藥學。醫療資源的短缺,醫療技術進步的遲緩——舊病依然不治,新癥又層出不窮——,多少揭示了現代科技進步的真相。
現代科技進步要有巨額資金,要有系統配套的教育和科研體系,所以只能掌握在“政—經—文教”精英集團手里。科技首先是為他們賦能的,所以,精英愛科技,崇拜科技。
科技本身不提供科技之被運用的“正當原則”,是“價值中立”的,價值由科技的掌控者決定。然而,現代精英又愛“進步”、反“保守”。當他們拿著高科技對付人時,批評他們“無人性”“傷天害理”,是沒有用的——因為,在他們那里,“人性”“天”“理”隨時代而變,而每個時代的“理”,取決于那個時代的統治精英。所以,他們掌握了“力”,也掌握了“理”。這不難解釋,何以在短短若干年間,社會變成了一個集監視、定位、測量、打擊于一體的傳感空間,一座巨大無外的人間監獄。普通人為生計而奮斗,在不知不覺中——必然地——“闖入”其中,置身于一小撮人的瞄準鏡里,成了靶子。
極權統治的臭名昭著,應該與其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清洗與屠殺有關。當然,這是極權統治的“不成熟”。后來的極權統治未必要以一種明顯的、令人發指的形式表現出來,它完全可以以一種讓人有更大安全感、秩序感的令人喜聞樂見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高科技賦能下的極權統治,應該具有隱身術了。
在現代國家對古典世界崩塌而散落下來的個體進行拼裝的過程中,“某種類型的保守立場出現了,但不管怎么樣,保守離不開個體性”(91頁)。考慮到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變遷和挑戰,如何理解保守主義的現實意義?
洪濤:“保守主義”一詞容易發生誤解。保守主義有政治保守主義、禮俗(道德)保守主義、宗教保守主義、文化(哲學)保守主義等不同類型。政治保守主義通常反對將尊重無差別地給予每一個人,認為應該基于人的德性,故而在政治上主張賢能制,即主張實際上的貴族制或寡頭制(既然出身有權、有錢家庭的人總體顯得更賢能)。禮俗(道德)保守主義是早期保守主義的常見類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主張禮俗(道德)保守主義一定得同時掌控輿論,否則被反問何以不將纏足、女性幽居等等一起保守下來,就不太好回答。這兩種保守主義通常需要權力加持,也反過來投桃報李:在近二十年來,它們為權力的全控制、為秘密傷害,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口實。
我所講的“保守態度”主要是文化上的,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對文化保守主義可以這樣來界定:主張軸心時代之哲學奠基對一切時代的人的自我理解是普遍有效的。文化保守主義并非主張過去的就好——不同于禮俗(道德)保守主義,而是說,對人的自我理解來說,有永恒、不變的根基性東西,這些東西在過去的某個時代被認識到了。
現代思想的主流是主張一切觀念皆隨社會變遷而嬗變,每一時代的人,得自行建立他們的迥然不同于過去的生活原則,這個想法其實非常激進。尼采式的保守主義是政治性的,在文化上,則是一種激進主義。
“個體”概念的過渡性,與這種對觀念的歷史主義理解有關。所謂“保守態度”,就是意識到“個體”之堅守、之維持有賴于軸心時代哲學突破所奠基的“類意識”,有賴于諸如人、人性之類形而上觀念。沒有“性相近”的想象,阿倫特的以“空間”建構“人性”也是無法想象的。
阿倫特和盧梭都認為“人性”最能見諸未經高度教化的普通民眾、而非教化深厚的上層人士身上(106頁)。現在國內流行文化中常賦予作品中的上層人士更多美德,服務的是需要把自己“代入”這些角色的讀者。這種轉變反映了現在讀者怎樣的變化?
洪濤:國內當代暢銷小說我讀得很少,對其中的精英形象以及當前讀者口味的變化不甚了解。精英被賦予更多美德,是一種社會常態,畢竟精英文化的創造權掌握在他們手里。革命后社會“右”轉是常態,畢竟精英掌控著政、經、文大權,操縱善、惡的評價,他們不大愿意承認他們這些高智商者、斗戰勝者,與被他們抓來斗且必然斗敗的人是平等的,也不算不正常。在右翼(精英匯聚之處)眼里,啟蒙理想是可笑的,出自無能者、弱者對強者的嫉恨。
自古精英有兩種,一種是社會精英,一種是自然精英。社會精英是什么,大家都懂。自然精英,我想是指那些有寬廣視野和開闊心胸、充滿慈悲和仁慈之心的人,他們不會以為憑借某些偶然天賦,或依某些特定社會標準,就可以在殊異個體間,區分出本質上的尊卑、高下,更不會因為斗戰勝人就自以為高人一等或幾等。自然精英不自以為高,所以看不出是精英。
今天的普通民眾不普通,因為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接受了無固定人性、科技進步是人類或歷史的目的、斗戰勝人者是精英之類的現代觀念,也是活到老、規訓到老從而“人性”的自然聲音極弱的專業人才。保持質樸“人性”的普通民眾不好找,這是教育普及的一個成果。在網絡業已覆蓋至最偏遠、偏僻之地區,上至垂老、下至稚子的時代,精英是有足夠的機會來操縱普通民眾的情感、甚至臉色,以給被他們視作敵人的人看的——這樣,被精英視作“廢物”的普通民眾也得到了利用,發揮了斗爭工具的作用——,當然,世界也就再難找到一塊質樸之地,人與人之間的自然善意,大概也成了珍稀之物。現代教育增長了人的理智,敗壞了人的自然情性。
今天,在一些所謂落后地區,還多少能感受到素樸人性的存在。樸野之人沒有智慧到如文明人那樣,派人上網贊美他們還有人性。人性沒什么好贊美的,只要是人,原本都應該有。這是一種稀松平常的自然情感,古今一也,中外一也,卑之無甚高論。孟子講,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在這里無法區分出一個尊卑高下。
作家筆下的普通民眾,多少是有點理想化的,用于反襯文明人的所謂文明。如果說,下層人比上層人士保留了更多的人性,大概是因為他們的斗戰才智不夠高。孔子早已指出,才智與人性走的是兩條不同的道路。道家認為二者是此消彼長的。荀子于先秦思想家中最推崇才智,所以貶低人性最甚,政治上也最主張賢能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有將人性分等的說法,是因為他們所講的“人性”,核心是智慧,智慧可以分等。
現代社會是理智型的,一切社會機制都在使理智見長者脫穎而出,所以精英是智力或理智精英。以理智見長的精英,輕視與愚者共有的人性,并不奇怪。
現代人崇拜才智、崇拜能干、崇拜厲害。在靠才智才能脫穎而出的社會,仁慈、同情、善良,不但無用,而且有害,是弱點和缺陷,被認為是“弱者”才有的特點。
理智人好斗,因為理智擅長區分和對立。霍布斯的那些只要遭遇、就一定要斗個你死我活的自然人,盧梭說其實是理智發達的文明人。現代的理智精英認為,人性是不定的,有階級性,或有文明性,于是,原本“相近”的人性又“相遠”了,可以分敵我、尊卑,可以斗爭了。那些年,有人提倡普遍人性,就受到批判。可見,極“左”是一種非常現代的思潮。
文明人長于理智,處處算計,處處斗,于是,不得不呼喚出凌駕于所有人之上的“利維坦”,以維持斗而不破之局。這也算是一種報應。
在奧威爾看來,自由主義在還沒完成之前便已夭折(417頁)。考慮到這一觀點的背景,你認為這一預言在今天看是否準確?這對我們理解自由主義的未來有何啟示?
洪濤:奧威爾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是英國警察眼里的危險的“左翼分子”。社會主義者不否認自由主義的自由理想——即個體的自主發展——,但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比自由主義能更好地實現這一理想。所以,右翼分子是一慣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當作自由主義來反對的。
奧威爾的預言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首先,今天的技術統治較《一九八四》中所描寫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次,以自主性為核心的啟蒙理想,業已成為一種不再有吸引力的老生常談;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的權力欲。
奧威爾當然不愿相信這是一種必然。預言的目的,往往是為了使所預言者不能成真。但是,推動totalitarianism出現的因素是真實存在的。
我讀了一些當代自由主義者的作品,感到在他們心中有一種失落感。自由主義者認同霍布斯所主張的人性,把自由視作一種斗戰的自由,因為,彼此之間不再有內在關聯的孤立個體,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孤子”,置身于四戰之地成為其本質的處境,當然,自由主義者說:斗戰得符合一個條件——法治。自由主義社會好比一個拳擊臺,法官是裁判。令自由主義者感到尷尬的是——今天,他們已不得不承認——,斗戰勝者,往往是那些懷疑或反對自由主義民主之人,這些人因為這個斗局更有利于他們,以至于他們也擺出認同自由主義民主的架式。
其實,能不能斗戰勝,不只是一個能力問題,也涉及性情和意愿,涉及文化傳統。這個道理,凡有過競技性拳擊訓練經驗的人都不難明白。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自視為“職業拳手”——霍布斯的人性概念是成問題的——,自視為“職業拳手”者也不必具有自由主義者的品格:“兵不厭詐”,對未來可能發動攻擊的對象,長期潛伏、秘密布局、挖坑設陷、策反臥底、埋名隱身,時機一到,秘密發起“自由主義之斗”,勝負當然早已決定。
一個自由社會未必是一座費厄潑賴的拳擊臺,而可能是一個反復上演著虎狼獵食鹿羊的叢林。鹿、羊之類的食草獸被斗怕了,于是呼喚totalitarianism。
所以,自由主義的夭折,totalitarianism的興起,至少有自由主義自身的部分原因:愈主張個體自由,愈不得不迫切呼喚凌駕于個體與集團之上的“利維坦”的降臨。
Totalitarianism是一個共同的現代問題(292頁)。國家理論經歷了從古典到現代的發展,現代國家在治理結構、法治、民主和人權保護等方面發展了更加復雜和多元的機制。這是否意味著人類有能力使現代國家在保障安全和秩序的同時,也更加重視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從而避免滑入的totalitarianism的極端情況?
洪濤:向totalitarianism的發展,可以被視作現代國家與生俱來的一種“基因”,當然,不是全部。
今天,一方面,問題中所說的“等方面”還遠未得到充分落實,另一方面,剛踏入二十一世紀,又出現了一種極富誘惑力的選擇——技術統治。跟建立“更加復雜和多元的機制”相比,技術統治便利得多。前者要有觀念和文化作為基礎,要有政治智慧,要反復試錯,要有機遇和契機。后者只需要通過技術管住即可。霍布斯告訴我們,“自然狀態”的根源是人的自然自由(自然權利),可以推論,鏟除“自然狀態”的最簡單辦法,是人徹底交出其自然自由。霍布斯四百年后,技術進步使人徹底交出自然自由成為可能。不必用一種“更加復雜和多元的機制”,而是以技術對所有人進行全控制,剝奪其自然自由,從而徹底鏟除“自然狀態”的根源。“技術統治”是一條捷徑,所以,誘惑力巨大。
國家能力愈強,權力愈集中,就愈易——應該說是必然——成為圍獵的對象。劫奪國家是一本萬利的事。問題中說“是否意味著人類有能力使現代國家在保障安全和秩序的同時,也更加重視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但是,哪里有“人類”?有的只是試圖劫奪國家的這個集團、那個集團,以及既渴望安全和秩序、又渴望權利和自由不受侵犯的與權力無爭的散沙一般的普通民眾。
普通民眾被明面上的國家之“網”捆住了手腳,暗中的“強者”便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將普通民眾摒棄于治權之外,加劇了“國家”的被劫持狀況,“國家”無異于站在“強者”一邊,成為他們的保護傘,成為他們欺負普通民眾的工具。當然,隱身于“國家”之傘之下的“強者”早與“國家”水乳交合了。這的確沒有超出馬克思的經典論斷:國家是“強者”(統治者)統治“弱者”(被統治者)的工具。
書中說,《一九八四》也可作為一種“愛情”小說來解讀,老大哥在“看”著你是因為老大哥在強勢地“愛”著你。古代僭主們已經意識到,愛欲控制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313頁)。因為愛欲會產生主人意識。現代社會中無性、不婚現象的增加以及愛欲逐漸變淡的趨勢,與技術政體的發展是否有關呢?
洪濤:僭主的愛欲控制,即否定他人的個體性,使他人無法自“是”,使他人成為“他者”,倒不是為了反個體,而是其自身個體性的一種極端伸張。古人視僭主為具有強大愛欲之人,只不過他們不是愛他人,而是要讓所有他人愛自己。
壟斷他人的愛欲,使之唯一地聚焦于某個神、某個人,在古今宗教和政治中都不罕見。控制人的愛欲的方法有:造神運動、掌控名利、操縱輿論、建立恐怖。這些辦法在《一九八四》中都被運用了。
無性、不婚現象的增長,應該有多方面原因。男女平等是其一。現代女性不再將為人妻、為人母作為自己的唯一生活之道。住房、教育愈來愈高的成本,也是原因之一。家庭在現代社會中地位的變化,是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如果以父權制家庭為家庭的本質,那么在現代社會,家庭實際上已經解體了。父權制家庭的首要功能是繁衍后代。今人成家,生育后代大概不是主要——至少不是唯一——目的了。
性、婚姻與技術政體的關系,或許可以通過與現代國家的關系來認識。中國法家早就發現,國與家之間存在競爭關系:國向家爭奪其子女之愛。法家愛國,所以反儒家,反后者所主張的孝道。現代父權制家庭解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爭奪子女之愛的失敗。人首先是國家的個體,而不是家庭的一員。
現代家庭還有兩項職能:一、生、養后代的“經濟”職能;二、夫妻作為友伴的共同生活的職能。生、養既然已經喪失了倫理、教育意義,友伴既然不必以家庭為基本形式,所以,無性、不婚現象的增加就不難理解了。
現代規訓也籍由作用于人的愛欲產生效果。在典型的規訓機構——修道院、軍隊、學校、工廠、監獄——中,愛欲都受到管控。這種管控不但是外在的、身體上的,也是內在的、心理上的。今天已經能夠以高科技手段對人的生理進行遠程干預甚至操縱,則對愛欲的影響更大了。
最后讓我們回到個體的“避風港”——想象性寫作吧。的確有一些人受到卡夫卡的影響,過起白天上班、晚上寫小說的雙面生活。這里不得不提到2020年ChatGPT-3發布后,AI與人類作家的合作也越來越多。你怎么看待這兩種寫作需求?假如你想寫小說的話,你會寫什么樣的故事?
洪濤:我幸好生得早。小時候,一枝筆、一頁紙都彌足珍貴。在我所活著的這半輩子里,紙、筆一直是在這個“與人斗,其樂無窮”的現代世界之外的圣·皮埃爾島,盡管最近十年以來,已經不存在在電波武器等降維打擊之外的“世外桃源”了。
今天,據說已經GhatGPT-3了,據說已經AI了,但我想我已經到了不必趕時髦的年齡了。韋伯告訴我們,在這個現代世界,再怎么追趕時尚,也免不了被拋下永恒向前的列車的命運。
與AI合作是不是在自掘墳墓?有人說,你不掘,別人掘,所以,為了領先,還得掘,而且要掘得更快、更深。我自覺能力有限,做不了很多事。我所想要的,只是一張安靜的書桌,讀、寫我自己想讀、寫的。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