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尋找“精神的框架”
【編者按】
今天我們為何還要重溫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精神?西南聯大研究學者、作家張曼菱在其新作《聆聽:西南聯大訪談錄》和《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商務印書館2024年7月版)中收錄了對聯大師生及相關人物的獨家訪談,如中國社會學學科奠基人費孝通,數學家陳省身,“兩彈一星”功臣朱光亞、王希季,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哲學史家任繼愈等,對西南聯大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如梅貽琦、聞一多、劉文典、鄧稼先等進行解讀,對一些至今爭訟紛紜的話題進行多角度闡述,并努力還原戰時大學的歷史現場和精神實質。本文是《回望》的序“尋找‘精神的框架’”。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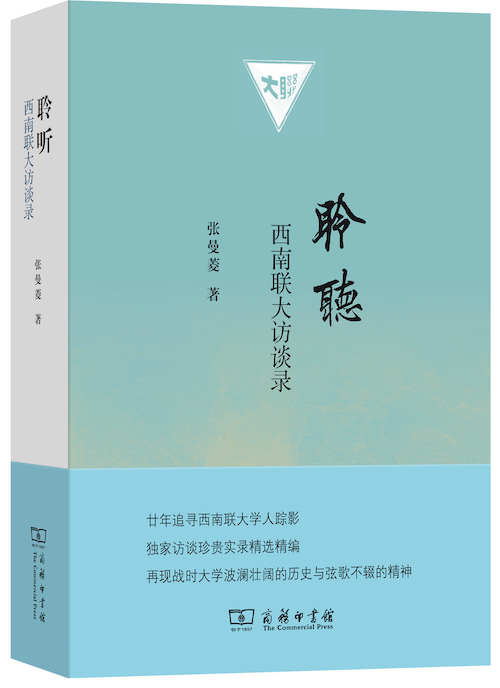
《聆聽:西南聯大訪談錄》書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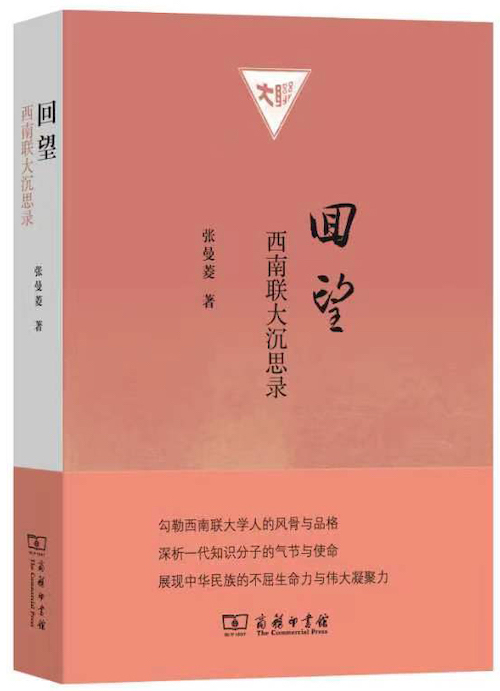
《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書封
陳寅恪說過:“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
戰爭的壓力,使學者們對我們這個民族的獨特歷史文化更加珍視。
這個人群,為什么五千年來打不散,而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亦古亦今的龐大民族呢?
2016年秋,我在成都與馬識途先生晤談。馬老是西南聯大1941級外國語文學系學生,也是當年中共地下黨在西南聯大的支部書記。他說,聞一多曾經想辦一份報紙叫《十一》,合起來就是一個“士”。聞一多想在戰時的艱難環境中提醒和完善“士人”的人格品行。
“士”的稱謂,從西周就有,指那些“王”以下的貴族,他們享受供養,對周王朝負有責任。到東周形成了一個階層,通“六藝”,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質。再后來,“士”形成一系列的歷史與文化。這個傳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將自己看作被賦予大局使命的人。
戰時聞一多舍棄舒適的書齋與藏書出京,喊出:“去吧,去認識我們的祖國!”到師生們的步行中,踐行“飽以五車讀,勞以萬里行”之類的古訓,并重新自省。
朱自清之子朱喬森說:“我父親覺得自己的任務就是保持中國‘弦誦不絕’。弦誦不絕,就是讀書這個傳統不要絕。”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意義重大。
重構“士”的人格框架以及相應的倫理范式,在西南聯大形成了一個普遍的人文趨勢。
羅庸在《鴨池十講》(增訂本,北京出版社,2016年)中也談到“士”的價值觀:“原來士之所以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負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為。”
周作人附逆,學界痛惜其“失節”,稱“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聞一多、羅庸他們,并非如當下很多學者那樣,在抽象領域中來解析一種人格建構,而是在自己的“生存領域”中,在戰火與貧困中,打造理想中“士”的人格。他們是從行動開始的。
羅庸先生在昆明郊區居住時,意外的火災燒光了他的藏書,他面色如常,令同僚們起敬,可以聯系到他在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中寫的“動心忍性希前哲”。
聞一多這樣的“新月派”詩人,回到了傳統,相信其中可以淘濾出精神的金沙。任繼愈在多年后評價:“聞一多研究《詩經》《楚辭》,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區民族民俗的活化石,開辟了學術的新局面。”
聞一多帶著孩子們到小河邊洗臉,坐在草地上玩耍,月明之夜在清輝投射的小院子里講詩。他曾說過“詩化家庭”。那是將親情與文化相溝通,是倫理關系的一種升華。
這是很多有文化素養的父親都做過的事情,而聞一多則將它明確地宣示定義了。
不由回憶起我的父親,他也總是挑選一些田園、思親、懷鄉的古詩帶我們誦讀,避開那些帶有儒家說教氣息的詩歌,而聞一多追究到古詩的終極價值,從屈原之高潔到《春江花月夜》的浪漫。
聞一多講詩時不講“李杜”,卻說《春江花月夜》是“唐詩中最美的詩”,耐人尋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杜甫的思想格局。李白的“長安不見使人愁”,則是他江湖漂泊的牽念。顯然,聞一多追溯的“士”,不是“李杜”這樣的。
推崇《春江花月夜》,是從美學的角度上重新定位“士”的格局,是春天與熱愛,自然之美與人間生活,而與“君主”“朝廷”無涉。
對《詩經》《楚辭》的愛好與深究,表明他要回到先秦諸子的多元化思想領域去溯源,尋找新鮮力量,以振奮抗戰中的學人。這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個源頭。
他在講課中屢次贊美屈原,為自己刻印章“其愚不可及”,直到“最后一次講演”凜然面對槍口,都在昭示一種大無畏的氣概:士可殺,不可辱!
“究竟甚么是文化傳統‘創造的轉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
此書作者林毓生是西南聯大學子殷海光的學生,一位旅美學者。
西南聯大的學人們正是繼承了“守正出新”的文化理念,不斷進行變革與創造。
從大學的格局來看,西南聯大推行一種中西合璧的現代化的教育框架,一方面使用開放式教材,一方面堅持以“中國通史”作為大一學生的必修課。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記載,鄭天挺在昆明辦講座多次以“讀史以明志”為主題。
“九葉”詩人 、哲學系學子鄭敏晚年曾感慨:“我們現在沒有要求所有的文學院學生都念‘中國通史’。丟掉了對歷史的理解,文科好像就沒有一個站腳的地方。”
她說,在西南聯大,課程的設置是非常系統的。它教育學生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告訴學生什么是重要的。
茶館“三劍客”的瀟灑不羈與女生宿舍的雅致詩意相映成趣,而教師之家以“陋室”自況,詩社成員竟往導師家聚餐,共享“得道”之樂。
學生們自辦伙食,“君子近庖廚”,以此為能事。而“倒孔”運動持續發酵,從香港航班上的“飛狗事件”到孔祥熙來校,面對腐敗官僚,學生們不依不饒。
吳宓組織“石社”,自命為“紫鵑”,宣揚“維護大美”的精神。教授的古風與學生的頑皮相映成趣。
劉文典講課時涉及的音韻、訓詁方面的內容頗有獨到之處,當下幾乎失傳。任繼愈的回憶令人耳目一新:“他還講,中國古典文學經常利用漢字象形的特點,引發讀者的想象,從而增強了讀者的想象力。《海賦》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頭亂發在水中出沒,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氣勢。”
一把用舊毛線纏繞多道的刻刀,上面留有壓出的指痕,這是聞一多的妻子為防止他治印磨傷手指而親自做的。妻子的脂粉盒被用作印色盒,有一瓶印油是朱自清先生送來的。
朱自清詩曰:“閉門拼自守窮慳,車馬街頭任往還。”發國難財的人有的是,別人再怎么富貴,但教授們寧肯窮得吃不上飯,也要堅持把學生帶出來,把弦誦不絕的傳統繼承下去。
梅貽琦之子梅祖彥說:“整個戰爭的威脅,對全國人民,至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也是一種激勵。我想,是‘為國家的前途’的觀念,使學生格外地用功,才能培養出這么多人才來。”
當我向李政道問到西南聯大成功的原因時,他說到一個大格局:“西南聯大之所以成功,有好幾個原因。第一是當時的年輕人跟學者的志氣。老師、教授,不光是吳(大猷)先生一個人,也不光是西南聯大,浙大也一樣,那個時候整個學術界所有老師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是有信仰、有志氣的。他們是要做事的,而且他們把他們的經歷都附在上面了。”
他神情沉郁地說:“(師生們)并不認為我們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欺負、遭受大屠殺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是要有前途的。”
美國學者易社強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中幾次提到“傳奇”這個詞,一是表明他對這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敬意:
聯大以壯偉的漫漫長征開始,以數年的剛毅堅卓為之繼,以摻雜著悲劇的成功告終。這無疑是傳奇的材料。
一是表態,要用嚴肅的史學家態度來對待這段歷史:
然而,假如聯大僅僅是一段妙趣橫生的傳奇,那最好由小說家來承擔這個任務。之所以有必要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聯大,是因為它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知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
我贊同這樣的態度,對于一部正在浮出水面的歷史,首先要用歷史的態度來發掘與研究。至于戲劇化的傳播,那只是一種對歷史的消費,屬于另一個范疇。
作為一名西方的自由知識分子,易社強對西南聯大的驚奇心與認同感是并存的。
而我和走近西南聯大歷史的當代學人們,感受到的卻是一種文化傳統的歸屬,在敬仰中有一種熟悉感與親和力。
當年的這批中國知識分子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氣節”“士可殺,不可辱”這樣一些觀念是等同于生命的。
當是時,日本人正在對中國施行“亡國滅種”的戰略,在所占領地區已經用日文代替了中文教育,用血腥手段逼迫中國人對太陽旗敬禮。
與一般戰爭中的掠奪和屠殺不一樣,這是對中國人進行種族與文化的滅絕。
在整個“二戰”中,貧弱中國所面臨的命運不能與其他國家相提并論。文化與種族滅絕的危機籠罩在國人的頭上,這不只是知識分子的感受。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當軍隊在為保衛國土與人民生命浴血奮戰時,學人肩負起自己的使命。
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里,從中國當時的生存危機里,南遷與堅持漫長的辦學,正是這批學人生命中必然的選擇,是一個民族必然的選擇。
其實西南聯大各層人士最重要的共性,涵蓋一切差別的共性,是民族生存與民族抗爭。這是一股融合一切的力量,所以他們可以南遷,可以舍棄小我,可以忍辱負重,而決不可以拋下學業與教育的使命。
易社強的透視還遠未達到這一點。諸如,他提到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是不能涵蓋他們身上的家國意識、民族氣節的;對梅貽琦毫不猶豫選擇南下和預見性轉移物資,他僅從清華與美國的關系來解釋,未免貶低了一個中國教育家的情懷;尤其是他批評中國學者身上的“士大夫情結”,而不懂得這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根本。
他自己也意識到了:
欲理解聯大的淵源,我們至少得回溯到已逝的19世紀;欲理解聯大的遺產,我們得穿越20世紀90年代,進入未知的將來;欲理解聯大的歷史意義,我們要越過中國的疆界,探討更廣闊的跨文化的問題。(同上)
趙元任的二女兒趙新那回憶,當年她非常喜歡昆明,那里有很多熟悉的人,“仿佛是另外一個北平”。這句話非常獨特,帶著童真和智慧。
南遷的人們把北平這個文化都城的靈魂帶到了昆明,進行重構。年少的趙新那所感受的“另外一個北平”,蘊含著新的洗禮與開拓,打造出更加剛健與深沉的氣質。
這本書里的文章寫的時候各自成篇,集中起來,就是對那個時代的學人們的“精神框架”的一種追尋。
聞一多的人格追求、鄧稼先的奉獻精神、任繼愈的“氣節”之說、趙寶煦的教育思想、李政道的家國之念,還有劉文典的風骨與沉浮,皆具有那種涵納民族古今、融匯中西精髓的磊落情懷。
季羨林當年不在西南聯大,抗戰的時候他在德國,一個“局外人”。在《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還有那篇著名文章《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中,他都有歲月風云的梳理與自白。畢生奉獻于青燈黃卷的他,在暮年卻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審判。
《孟子》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季羨林持有的“愧疚”與“不忍”之心,從另一個視角補寫了一代學人的精神框架。
戰爭期間季羨林身在敵國,別有一番深刻的感觸,他說:“當然,‘愛國’這個詞一聽是好的,但也不一定。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德國法西斯侵略別的國家的時候,都高喊愛國主義,但那是假的。愛國主義應該有兩種:一種是真的,被壓迫、被殺害的民族的愛國,是真的;而壓迫別人、殺害別人的愛國主義,是假的。”
所謂“國族情結”,不只是一種親情和根系,也有著“道義”的內容。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