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游戲文化:電子游戲能算是藝術(shù)嗎?未來的藝術(shù)與藝術(shù)的未來
【編者按】
2024年7月29日,在第二十一屆中國國際數(shù)碼互動娛樂展覽會(Chinajoy)中國游戲開發(fā)者大會(CGDC)“游戲音樂主題論壇”上,《滬游敘事·上海網(wǎng)絡(luò)游戲產(chǎn)業(yè)發(fā)展報(bào)告》(以下簡稱《滬游敘事》)進(jìn)行發(fā)布。
《滬游敘事》由澎湃新聞旗下智庫澎湃研究所主編,以詳實(shí)的案例、一線的調(diào)研論證了“上海何以為重鎮(zhèn)”,從產(chǎn)業(yè)縱深、發(fā)展切面、案例特寫以及發(fā)展建議等角度出發(fā),描繪上海網(wǎng)絡(luò)游戲產(chǎn)業(yè)激蕩二十年的發(fā)展圖景。澎湃研究所將陸續(xù)刊發(fā)《滬游敘事》報(bào)告中的文章。本文為“發(fā)展切面”章節(jié)中的第一篇《游戲文化:電子游戲能算是藝術(shù)嗎?未來的藝術(shù)與藝術(shù)的未來》。
二十世紀(jì)后半葉以來,電子游戲的飛速發(fā)展是人類文化歷史上的巨大奇跡,不僅贏得年輕一代的狂熱擁護(hù),還正從電影電視等強(qiáng)大的主流文化產(chǎn)品中搶奪著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根據(jù)數(shù)據(jù)調(diào)研機(jī)構(gòu)Newzoo發(fā)布的報(bào)告,2023年全球游戲產(chǎn)業(yè)市場總值達(dá)到1877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16%。相比之下,2019年全球電影票房為339億美元,就市場規(guī)模而言,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被游戲業(yè)拋在后面。
2003年11月18日,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zhǔn),將電子競技列為第99個正式體育競賽項(xiàng)目。每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數(shù)碼互動娛樂展覽會(Chinajoy)成為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展會,也是數(shù)十萬游戲玩家們的狂歡盛會。

2024年7月26日,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觀眾在體驗(yàn)《崩壞:星穹鐵道》游戲場景。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圖
對于電子游戲這種“另類”文化形態(tài)咄咄逼人的崛起,國內(nèi)外的學(xué)術(shù)界也正在給予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甚至已經(jīng)有人在歡呼“第九藝術(shù)”的誕生。電子游戲能算是藝術(shù)嗎?它在什么意義上可以稱之為藝術(shù)?它與已有的藝術(shù)在哪些方面具有可比性,有哪些獨(dú)特性和潛在的可能性,對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形態(tài)和觀念會帶來什么樣的沖擊?這些都是非常值得人文科學(xué)工作者嚴(yán)肅深入思考的重大課題。
電子游戲的藝術(shù)性:情感的強(qiáng)化與媒介的力量
電子游戲能算是藝術(shù)嗎?英國藝術(shù)批評家喬納森·瓊斯認(rèn)為:“電子游戲創(chuàng)造的世界更像是游樂場,體驗(yàn)是由玩家和程序之間的互動創(chuàng)造的。玩家無法將個人的生活愿景加于游戲,而游戲的創(chuàng)造者也放棄了這一責(zé)任。沒有人‘擁有’游戲,因此沒有藝術(shù)家,因此也沒有藝術(shù)作品。這是游戲與藝術(shù)的本質(zhì)區(qū)別。”[1]像小島秀夫、約翰·卡馬克等游戲業(yè)內(nèi)的著名人士,都對游戲的藝術(shù)性有過很多否定性的言論。游戲最早是不標(biāo)作者的,但是這種情況在后來其實(shí)有很大變化,今天的知名游戲都會強(qiáng)調(diào)是誰開發(fā)的。
瓊斯從傳統(tǒng)的作者性的角度否定了游戲的藝術(shù)性,但是他忽略了現(xiàn)代藝術(shù)、文藝?yán)碚摵蛯?shí)踐的發(fā)展。現(xiàn)代藝術(shù)的重心恰恰是越來越朝讀者、觀眾或是玩家的方向傾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瓊斯對游戲藝術(shù)性的否定,恰恰可以成為對游戲藝術(shù)性的支持,即現(xiàn)代藝術(shù)要掙脫作者的束縛,把選擇權(quán)越來越交給讀者、觀眾和玩家。
例如游戲《仙劍奇?zhèn)b傳》畫面以四十五度斜向繪制,插配活靈活現(xiàn)的角色動畫,描繪出士農(nóng)工商諸如耕種、釣魚、養(yǎng)雞、打鐵、洗衣等民風(fēng)民俗。更時(shí)有松柏仙鶴、漁樵流水,配以絲竹之樂,烘托出古色古香的中國傳統(tǒng)風(fēng)味。與傳統(tǒng)的武俠小說不同,仙劍通過電子游戲獨(dú)有的特點(diǎn),把自身的藝術(shù)性放大。在通過觀看、搜索、打斗、解謎、對話等一系列的操作后,“仙劍迷”們把自我投射在游戲的虛幻角色里,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參與感和認(rèn)同感。
與傳統(tǒng)文學(xué)藝術(shù)相比,電子游戲更注重玩家的體驗(yàn),這種體驗(yàn)不僅是視覺和聽覺的,也不僅僅是語言文字激發(fā)的想象,而是由玩家通過身體性的操作,將多種感官與大腦的活動進(jìn)行整合。游戲研究者格蘭特·塔維諾(Grant Tavinor)認(rèn)為:“電子游戲具有推動藝術(shù)發(fā)展的巨大潛能,就在于它能將觀眾拉進(jìn)虛構(gòu)的世界中,把虛構(gòu)的情感與動作結(jié)合起來。電子游戲是交互性的小說,讓玩家在游戲世界里既成為認(rèn)知的主體,又成為行動的主體,他們因此就能夠?qū)δ莻€虛構(gòu)的世界發(fā)生影響,從而引導(dǎo)他們自身的行動。這也意味著電子游戲中的情感對于藝術(shù)哲學(xué)來說有著更為重大的潛在意義。”[2]
從某種意義上,電子游戲具有不同程度的“角色扮演”意味,過程有點(diǎn)像表演性的戲劇,但玩家不僅是傳統(tǒng)的觀眾,也是舞臺上的演員,而整個游戲空間的廣闊性和自由度又大大超過了傳統(tǒng)的舞臺,讓玩家能在其中盡情發(fā)揮和自我陶醉,體驗(yàn)創(chuàng)造、表演和觀賞的三重快感。
電子游戲?qū)η楦械闹圃旌蛷?qiáng)化,正是其媒介性的體現(xiàn)。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理論,在此基礎(chǔ)上,他認(rèn)為:“大多數(shù)技術(shù)都產(chǎn)生一種放大效應(yīng),該效應(yīng)在感知的分離中是十分明晰的。廣播是聲象的延伸,高保真的照相是視象的延伸。而電視首先是觸覺的延伸,它涉及所有感官的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3]麥克盧漢如果活到今天,他會看到電子游戲?yàn)楦泄俚膹?qiáng)化增添了全新的維度:身體。
早期的電子游戲玩家是用簡單的游戲桿或者鼠標(biāo)鍵盤進(jìn)行操控,身體的動作及其與游戲世界的互動非常有限。在今天,游戲硬件飛速發(fā)展,對玩家身體的開發(fā)和利用也日新月異。從帶有各種力量反饋的新型游戲手柄,到Kinect、WII和Switch的體感控制器,再到六度空間的人體定位、手勢識別和眼球追蹤,現(xiàn)實(shí)玩家的舉手抬足,甚至每個眼神都能被游戲識別感應(yīng),也讓玩家與自己投射的對象產(chǎn)生更大的認(rèn)同、更深的沉浸與更強(qiáng)烈的情感反應(yīng)。
麥克盧漢肯定技術(shù)和媒介的力量,但他也對其濫用保持警惕:“為了放大或增加人體官能的力量,我們放任自己,我們自我異化,這是邪惡的花朵或贅生物。”情感是人類的紐帶,也是所有藝術(shù)的基礎(chǔ)。了解情感在電子游戲中的構(gòu)成方式,因勢利導(dǎo),去粗取精,用而有度,對于推動游戲產(chǎn)業(yè)和文藝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是我又不是我”:電子游戲帶來的視角解放
新的藝術(shù)媒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參與感,也帶來了新的視角。在文學(xué)藝術(shù)中,敘事視角非常重要,它決定了作品的存在方式。同樣,視角在電子游戲中也是一個極為核心的問題。玩家的視角既是客觀視角,又包含了主觀的成分,在傳統(tǒng)的文學(xué)寫作中很難看到。那個“我”既是我,又不是我,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一方面,我站在我以外的地方看見“我”自己,仿佛靈魂出竅;另一方面,我對這個“我”擁有全部的操縱權(quán);這個屏幕上的“我”同我極不相像。游戲中這種奇特的視角及其效應(yīng)充分說明了主體性的脆弱和自相矛盾。
不光有人的視角,還有動物的視角。例如,在冒險(xiǎn)游戲《壞蟲》中,玩家所扮演的是蟑螂,這簡直就是卡夫卡《變形記》的翻版,以更為直觀和體驗(yàn)化的形態(tài)呈現(xiàn),與從動物視角切入人類社會的先鋒文學(xué)實(shí)有異曲同工之妙。玩完這個游戲,你會對危機(jī)四伏的蟑螂以及與此不無關(guān)聯(lián)的人類自己的生活有全新理解。后現(xiàn)代是一個“視界融合”的時(shí)代,我們被各種各樣的眼睛看,我們也用各種各樣的眼睛去看,而電子游戲就是我們在新時(shí)代觀看世界的新的眼睛。
游戲研究者A.L.貝克認(rèn)為:“我們已經(jīng)看到,玩家在玩游戲時(shí)可以有效地了解他們的玩家角色的各個方面(有時(shí)通過受調(diào)節(jié)的交互性再現(xiàn)),而這在傳統(tǒng)的演員與角色的關(guān)系中不會發(fā)生……在其他任何媒體中,都不可能讓觀眾感受到那種將世界作為微風(fēng)、神靈或電子游戲可能使用的任何其他無數(shù)潛在化身 (avatar)對世界采取行動的感覺。”[4]例如在陳星漢的游戲《花》中,玩家可以扮演一股風(fēng),吹過城市,吹過原野,吹過草木花卉,為它們吹進(jìn)生機(jī)。
在電子游戲的發(fā)展過程中,視角變得越來越多樣化。電腦3D技術(shù)的進(jìn)步,使得多重視角成為電子游戲在敘事過程中天然的巨大優(yōu)勢。很多冒險(xiǎn)射擊游戲都允許玩家在游戲過程中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主人公的活動,像FIFA和NBA系列的體育游戲也可以在比賽時(shí)任意地切換攝影機(jī)的角度。可以俯視,也可以四十五度角斜視,還可以用鏡頭追蹤或者鏡頭漫游的方法。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弗·杰姆遜認(rèn)為,視角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藝術(shù)形式的問題,其本質(zhì)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為什么西方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會出現(xiàn)透視法呢?這是和笛卡爾的‘意識即中心’的觀點(diǎn)相聯(lián)系,和西方新興的關(guān)于科學(xué)的觀念相聯(lián)系的,此外還有自然的統(tǒng)一化,以及商業(yè)的興起等等原因。從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透視的出現(xiàn)是和經(jīng)濟(jì)、科學(xué)的發(fā)展,以及空間和人對自己身體的認(rèn)識的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5] 到了現(xiàn)代,西方人不再相信透視是認(rèn)識現(xiàn)實(shí)的惟一方法。現(xiàn)代主義繪畫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達(dá)到的一個目的就是摧毀透視、摧毀畫框帶來的整體性,要沖出的不僅是一種風(fēng)格體裁,而且是一整套意識形態(tài)。
從作者到讀者:媒介的融合與藝術(shù)的共創(chuàng)
什么是藝術(shù)?幾千年來人們對此爭論不休,有一個電子虛擬社交游戲?qū)Υ颂峁┝怂麄兊拇鸢福骸暗诙松薄_@是一個基于網(wǎng)絡(luò)的虛擬世界,其玩家在游戲里叫做“居民”,通過移動的虛擬化身互相交流,參加個人或集體活動,制造可以出售的虛擬物品,甚至可以買賣虛擬的地產(chǎn),從中獲得真實(shí)的金錢。對“第二人生”的居民來說,藝術(shù)就是通過創(chuàng)造可能的人物與可能的世界,讓人們突破真實(shí)世界的束縛,進(jìn)行想象性的自我超越與自我實(shí)現(xiàn)。
這又何嘗不是藝術(shù)的目的呢?但在傳統(tǒng)藝術(shù)中,可能的世界是有限的,自我超越也是有限。更具體地說,就是受到各種藝術(shù)媒體的限制。傳統(tǒng)的文學(xué)作品一旦制作完成,其物理形態(tài)便固定了下來,這是一個一次性的創(chuàng)造過程,而讀者的閱讀過程也不得不呈現(xiàn)出線性的特征。盡管如此,在文學(xué)發(fā)展的過程中,讀者一直是最具推動性的因素,文學(xué)面向讀者的運(yùn)作過程變得越來越明顯,文學(xué)批評中也出現(xiàn)了讀者反映批評、接受美學(xué)、闡釋學(xué)等理論,文學(xué)的重心開始從作者向讀者轉(zhuǎn)移。
有意思的是,這些以讀者為中心的理論的提出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游戲,把游戲視為文本的開放性的原型。接受美學(xué)的代表人物沃爾夫?qū)ひ辽獱栒J(rèn)為:“閱讀總是在選擇中突出對象:或者是多樣化的選擇,這意味著包納游戲的多種可能性,或者它自己開放于各種變化的反動而指向最初假定的角色。”[6] 就文學(xué)史而言,也存在著一個交互性逐漸活躍和不斷被釋放的過程。特別是現(xiàn)代主義出現(xiàn)以后的文學(xué),更多的是一種讀者的創(chuàng)造,作者在文本中留下了很多空白的、游移不定的點(diǎn),閱讀本身也就變成了一種游戲。
法國文學(xué)評論家羅蘭·巴特認(rèn)為有兩種文本,一種是“可讀的文本”(texte lisible),讀者小心翼翼地服從作者的意愿,循規(guī)蹈矩,無所作為;另一種是“可寫的文本”(texte scriptible),讀者在這種文本中玩著無窮指涉的游戲,進(jìn)行自由的創(chuàng)造,在兩者之中,巴特心儀的是具有先鋒性的可寫的文本。[7]如果從一個更大的文化視野來看這些走向,就會發(fā)現(xiàn)可寫的文本找到了全新的載體,并走向了極為廣闊的大眾文化空間,那就是網(wǎng)絡(luò)、游戲和虛擬現(xiàn)實(shí)。在那里,大眾進(jìn)行著前所未有的自由創(chuàng)造的游戲。
一個新的發(fā)展趨勢是,根據(jù)游戲改編的小說和電影不斷涌現(xiàn)。數(shù)碼電影《最終幻想》就是根據(jù)同名游戲改編而成。《銀河飛將》被拍攝成電影,改編而成的系列小說已經(jīng)出了6部。 除了職業(yè)性的創(chuàng)作以外,網(wǎng)絡(luò)上出現(xiàn)了很多網(wǎng)友自己創(chuàng)作的以同名電子游戲?yàn)楸尘暗奈膶W(xué)作品,正在成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中的一大類別,具有網(wǎng)絡(luò)小說“合作化”的特點(diǎn)。
電子游戲與傳統(tǒng)藝術(shù)之間,除了相互改編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相互滲透關(guān)系。在藝術(shù)手法和風(fēng)格技巧上它們也彼此借鑒。例如,在晚近的電影中,越來越出現(xiàn)游戲式的光影效果。在情節(jié)的進(jìn)展上,一些小說和電影也借鑒游戲的練級、生命值、解謎、攻關(guān)等套路,迎合觀眾新的心理需求。這方面表現(xiàn)得最淋漓盡致的是科幻電影《安德的游戲》,節(jié)奏、視覺、調(diào)子、氣氛都給人一種強(qiáng)烈的游戲感。
影視與文學(xué)一旦進(jìn)入游戲,那就不止于簡單的改編,而是開辟了全新的天地。在傳統(tǒng)的藝術(shù)中,讀者和觀眾可以觀看不同的人生,但那多半只是一次性完成。在電子游戲中,玩家不僅僅是觀看,還扮演、體驗(yàn)、創(chuàng)造不同的人生。玩家不僅是讀者和觀眾,也是演員、導(dǎo)演、作者……簡言之,就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就媒介的融合而言,電子游戲?yàn)槲膶W(xué)藝術(shù)增添了新的維度和自由度。
電子游戲的未來:上帝和作者已死,眾生喧嘩
在新一代藝術(shù)的融合中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一種指向:越界。這是一個越界的時(shí)代,人類主體正在變得越來越活躍,越來越具有能動性,越來越不受拘限,而電子游戲就是這一趨向的最新載體。電子游戲結(jié)合了小說、繪畫、音樂、電影等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元素,融技術(shù)、欲望、幻想、現(xiàn)實(shí)、逃避性、參與性、交互性于一爐。從前在其它藝術(shù)中,由于媒介和技術(shù)的限制而受到阻遏的意志和欲望,如今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可以暢通無阻地宣泄出來了。
計(jì)算機(jī)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催生了眾聲喧嘩和主體性空前活躍的新世紀(jì),我們在賽博空間到處可見對無限的可能性的渴望、無止境的選擇、跨歷史的狂歡。這種渴望,一言以蔽之,就是讀者、觀眾、玩家們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尼采說上帝死了,福柯說作者死了。但是讀者還活著,而且他們要做上帝。這是一種古老的欲望,但是也只有今天才為這無數(shù)上帝的誕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
虛擬空間是一個沒有法律,只有游戲規(guī)則的空間,玩家可以為所欲為,宣泄各種欲望,不用擔(dān)心自己會被抓起來。即使失敗了,也還可以去調(diào)一個個存盤文件,或者干脆就重新啟動電腦。這是一場人類扮演上帝的游戲,而交互性就是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里成為上帝的努力:不受限制的視角、穿越時(shí)空的本領(lǐng)、創(chuàng)造毀滅的能力。
隨著虛擬現(xiàn)實(shí)技術(shù)的進(jìn)步,電子游戲中的交互性會不斷地發(fā)展。虛擬現(xiàn)實(shí)是人對超越現(xiàn)實(shí)的渴望,可以說,一切藝術(shù)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虛擬現(xiàn)實(shí)。今天,虛擬現(xiàn)實(shí)有了全新的載體:電子媒介,更清晰直觀,更活色生香,更讓人沉浸其中。與此同時(shí),人工智能也在迅速發(fā)展,計(jì)算機(jī)將能自動創(chuàng)造出具有眾多可能性的交互式情節(jié)。當(dāng)人們所有的幻想都能夠“真實(shí)”地對象化、影像化的時(shí)候,其身份和自我認(rèn)同必將發(fā)生巨大的改變。
另一方面,在虛擬變得越來越真實(shí)的同時(shí),虛擬也越來越成為這個時(shí)代的重要概念:虛擬經(jīng)濟(jì)、虛擬貨幣、虛擬社區(qū)、虛擬購物、虛擬教育……我們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各種形態(tài)的虛擬。虛擬的現(xiàn)實(shí)與現(xiàn)實(shí)的虛擬,這兩種朝向彼此的運(yùn)動能夠最終合流嗎?這其實(shí)也是人類的一個古老的夢想的最新呈現(xiàn):藝術(shù)的生活化與生活的藝術(shù)化。
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中認(rèn)為人的理性和感性存在著永恒的沖突,而游戲可以將這兩者調(diào)和起來:“一言以蔽之,人只有在他是十足意義上的人時(shí)才進(jìn)行游戲,只有在他游戲時(shí),他才完全是人。”[8]席勒所說的游戲是一種美學(xué)的理想,與我們今天的電子游戲看似非常遙遠(yuǎn),骨子里還是有著相通的地方,它們都指向一種自由而又自律的狀態(tài)。我們也完全可以把席勒期許的游戲作為電子游戲未來發(fā)展的理想。
如果藝術(shù)也有制高點(diǎn)的話,文學(xué)和電影都代表過這個制高點(diǎn)。我認(rèn)為,從現(xiàn)在到未來,更具有決定性的至高點(diǎn)是電子游戲。可以這么說:誰掌握了游戲,誰就掌握了人的想象;誰掌握了想象,誰就掌握了未來。
——————————————
[1] 喬納森·瓊斯《對不起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電子游戲不是藝術(shù)》,衛(wèi)報(bào),2012年10月30日
[2] Grant Tavinor, The Art of Video Games, Chichester, Weley-Blackwell, 2009, p. 133.
[3]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0年,第411頁。
[4] A.L. 貝克《作為再現(xiàn)藝術(shù)的電子游戲》,Postgraduate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9, No. 2 (June 2012)
[5] 弗·杰姆遜:《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
[6] 沃爾夫?qū)ひ辽獱枺骸短摌?gòu)與想象——文學(xué)人類學(xué)疆界》,陳定家、汪正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0頁。
[7] 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p4.
[8] 席勒:《席勒文集》第6卷,張佳玨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220頁。
(作者嚴(yán)峰系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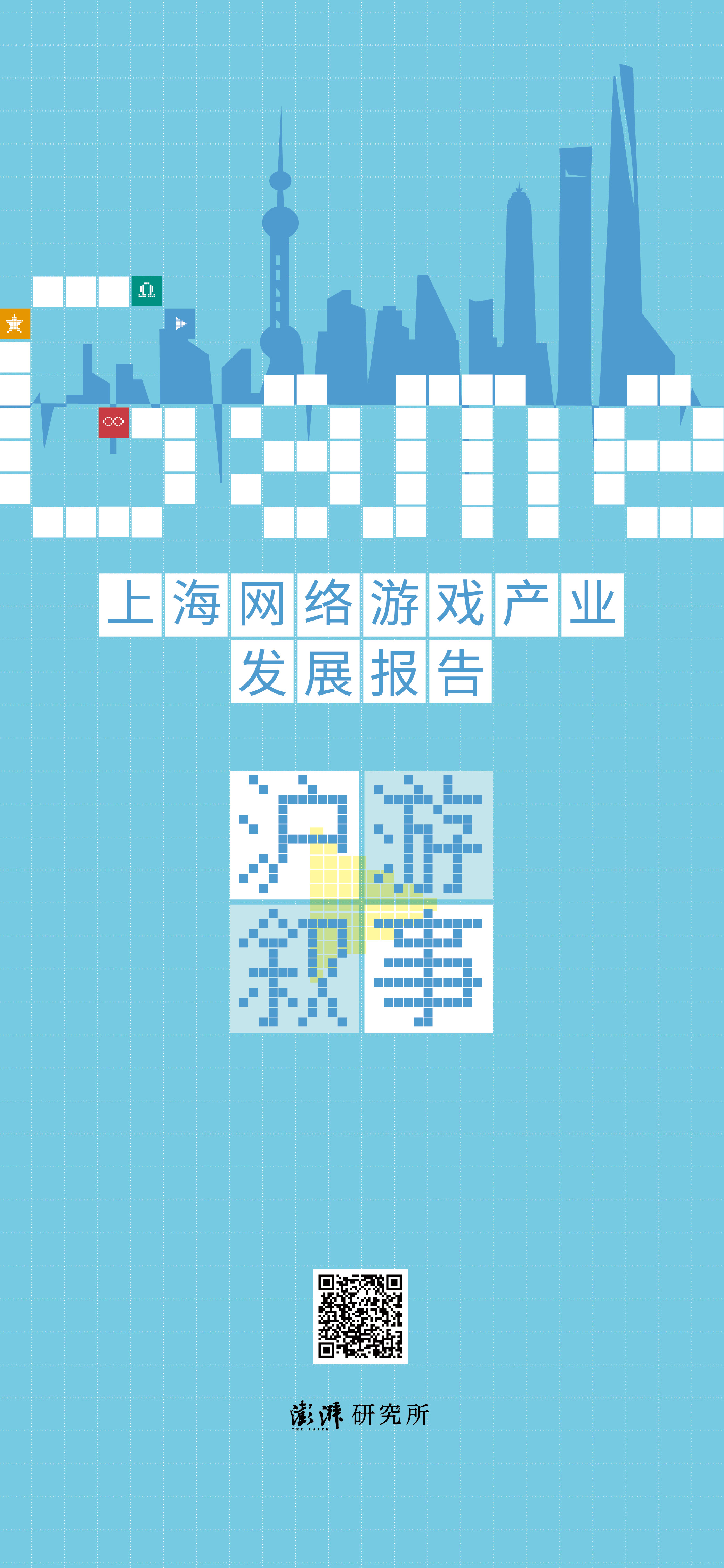
掃碼可見報(bào)告精華內(nèi)容
--------------
澎湃城市報(bào)告,一份有用的政商決策參考。
由澎湃研究所團(tuán)隊(duì)主理,真問題,深研究。用“腳力”做調(diào)研,用“腦力”想問題,用“筆力”寫報(bào)告。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