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22年:宋真宗,品格比能力更可貴
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22年,大宋乾興元年,大遼太平二年。
今年大宋又改年號了,公歷2月4號,也就是農歷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將今年改為乾興元年。“乾興”的意思很明顯:乾坤的“乾”當然就是指皇帝;興,是振作的意思。乾興,就是希望天子能再振乾綱。在當時的情境下,說白了,就是一個簡單的愿望:希望病重的皇帝能夠恢復健康。
真宗皇帝的病確實已經到了最后關頭。他自己心里應該也很清楚。
2月16號,真宗第一次讓12歲的皇太子代替自己,去祭拜宋太宗。一方面,是自己的身體已經不允許出宮做這么大的祭祀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讓太宗皇帝的在天之靈看看自己的好孫兒,是一個可以繼承大統的樣子。
到了3月5號,真宗下了一道命令,他要求大臣們在奏章中,把自己已經用了三年的尊號去掉。這個尊號,我給你念過,一共是22個字: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圣欽眀仁孝皇帝。皇帝和大臣們推讓了半天,最后決定,皇帝只接受一個簡單的稱號:“應天尊道欽明仁孝”這8個字。你聽出來了,這是把原來尊號中的那些過甚其辭的、有道教色彩的字眼去掉了,回到了簡簡單單的儒家圣君的價值觀上來,“應天尊道欽明仁孝”。這可能是為了向上天表達謙虛的意思。人到了最后時刻嘛,沒有那么多妄念了,要追求自己真正能夠得著的歷史定位了。
3月9號,真宗又給朝中的幾個重臣,宰相、樞密使什么的,加封了爵位。這可能是期待他們將來能激發天良,支持皇太子。
3月19號,真宗最后一次接見宰相,交代后事。這個時候,他已經說不出話了。宰相們向他做了最后的效忠保證,他也只能點點頭。
四天之后,宋真宗駕崩,在位26年,享年54周歲。
宋真宗,是我們《文明之旅》節目送走的第一位皇帝。那這一期節目,我們就來送別他,回到1022年,認真地看看這個人留給我們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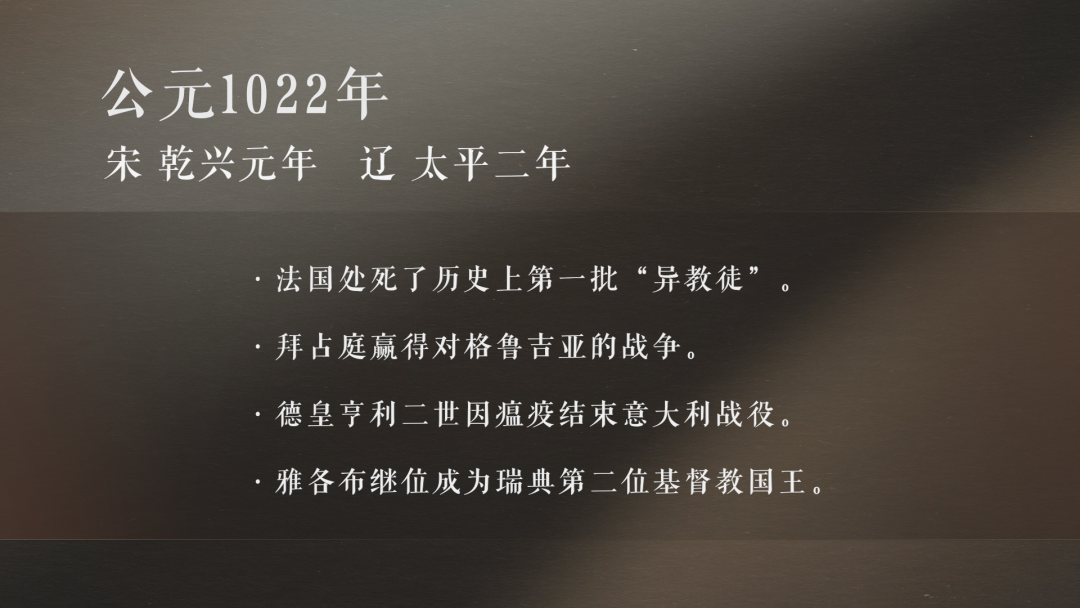
宋真宗的背影
宋真宗這個人,在歷史上的存在感其實不強,評價也不高。
原因很簡單,兩條:第一,因為他封禪泰山、大建道觀,儒家的主流價值觀是不接受的,所以古時候的士大夫不會說他好話;而現代人呢?一聽說,哦——宋真宗啊,他呀,就是那個簽了澶淵之盟的皇帝啊?就是花錢買和平的那位啊?也看不起他。你看,無論用古今哪種價值觀來衡量,他好像都有點硬傷。
但是,咱們今天不能拿這么簡單的結論送別宋真宗。因為,他不需要多我這么一個批判者,我也沒有資格去給這些皇帝排座次。《文明之旅》節目,只是想穿越回歷史現場,伴著古人的步伐一起走,搞清楚我們的文明是怎么一點點地構建起來的。所以,我更在意的,是這些古人為什么那么做,以及,這么做又在我們文明的底座上往上積累了什么。

回到宋真宗,我覺得他至少做對了一件事:認清了在自己這個階段國家面對的首要挑戰。請注意,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很多歷史上的昏君暴君,之所以最后的下場不好,往往并不是因為能力差,而是搞錯了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進錯了考場,拿錯了試卷,最后不管怎么忙活,都是零分。比如秦始皇、王莽、隋煬帝,都是這樣的悲劇。
是的,時代不同,皇帝面對的挑戰是不一樣的。就拿一個王朝開局的前三代君主來說,要解決的問題就各不相同。
一般來說,第一代君主的主要任務就是打天下,什么手段好用就用什么。但是我們知道,解決問題的手段,很快也會變成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第一代君主往往會留下很多衍生問題。比如,漢朝的劉邦為了平衡功臣集團的勢力,就借重自己的老婆呂氏,他一死,呂氏變成呂后,結果就給漢朝帶來了大麻煩。再比如,明朝的朱元璋為了鞏固邊疆,就分封自己的兒子做藩王,結果藩王就給自己的孫子帶來了大麻煩。再比如,清朝順治入關征服中原的時候,要使用吳三桂,但是吳三桂很快就成為康熙皇帝的大麻煩。等等。這些問題都要留給第二代君主來解決了。
對于宋朝來說,太祖趙匡胤至少留下了兩個大難題:一個是軍事上最難啃的骨頭——北漢和幽云十六州的問題,留給了宋太宗;還有,從軍事體制向文治國家的轉變這個超級難題,也沒有完成,也留給了太宗。
等第二代君主把這些問題都解決得七七八八了,這才有機會定下心來完善本朝的治理體系,這就是第三代君主的挑戰。這第三棒其實非常重要。一個朝代能不能活得長,治理體系好不好,往往要看這第三代的表現。比如漢代的文帝景帝,唐朝的高宗,清朝的雍正。這一棒跑好了,后面的接力的選手才有章可循。我們今天要講的宋真宗,也正好處在這個位置上。
剛才我們說,宋真宗至少做對了一件事,就是認清了在自己這個階段國家面對的首要挑戰。那是什么挑戰呢?是北邊大遼的軍事威脅嗎?是國內各個新征服地區的整合嗎?這些當然都是挑戰,但是不是首要挑戰。首要挑戰是:大宋朝沒有了太祖太宗那樣的君主,而且以后再也不會有了。
太祖趙匡胤本質上就是一個軍人,雄才大略,很有人格魅力。太宗趙光義心機深沉,又非常勤奮,他身上雖然有了很多文人氣息,“開卷有益”這個成語就是太宗創造的。但他本質上還是個武人,兩次北伐燕云十六州,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太宗是御駕親征啊,是真上過戰場,真受過箭傷啊。這兩位其實都算是開國皇帝,身上都點創業家的特質。而宋真宗呢?是那種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皇帝,論魅力,比不上太祖,論精力,比不上太宗。說白了,普通孩子一個。
這不是真宗本人的責任,但這就是現實,而且從他開始,大宋朝每一任皇帝,按說都應該是在宮廷里培養出來的。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皇帝不再有軍事統帥出身的權威,既不會有“同袍”和“舊部”,也不會有從底層開始的奮斗經歷,他們所有的權威都只來自于頭上這頂皇冠,屁股底下這把龍椅。你看,到第三代了,皇位本身是越來越鞏固了,但坐上皇位的卻是越來越弱勢的皇帝。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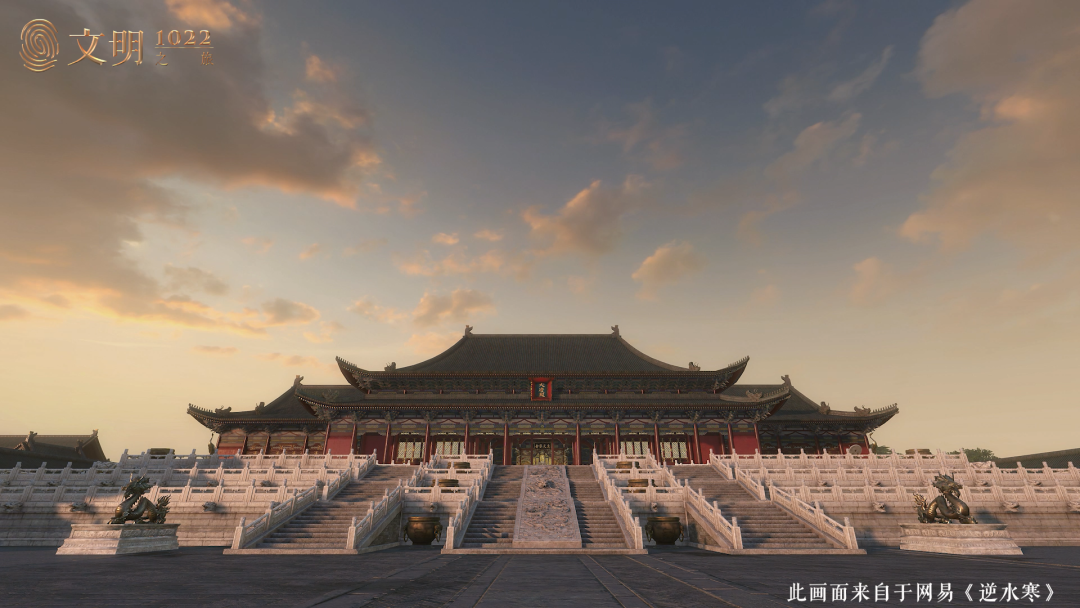
那怎么辦?看了宋真宗的這么多史料,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真宗不僅非常清楚這個挑戰,而且他這一輩子都在想辦法應對這一點。他的策略是一以貫之的。我感受比較深的,是三條:
第一條,就是用好宰相。
我的能力不夠,那我就和不同特點的宰相好好配合,形成組合,來應對不同的問題。
比如,剛開始,他30歲登基,經驗不足,威望也不足,那就用老宰相呂端。呂端去世后,就用自己老師,比自己大20歲的李沆。李沆死了,國家的挑戰變了,正好遼國大兵壓境,那就啟用有決斷力的寇準。覺得寇準性格上有問題,那就用老臣畢士安為寇準撐住大局。澶淵之盟之后,軍事問題不成問題了,國家需要安定,那就用心思細密的行政高手王旦。
你看,整個這個過程,他缺什么,馬上就用什么樣特質的宰相來彌補:我自己也許不行,但是皇帝加上宰相這個組合,可能就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幾次啟用寇準,我們前面的節目都講過這些細節,他從來也不真喜歡寇準,但是,只要需要,他還是馬上啟用。
而且真宗對這些宰相,也基本做到了禮遇和尊重。幾個重要的宰相,都是在崗位上一直干到病重或去世。這樣有始有終的君臣關系非常難得啊。就拿宋朝來說,宋神宗和王安石,算是君臣遇合的典范,但是又怎么樣呢?王安石拜相,第一次不足五年,第二次不足兩年。而宋真宗用王旦當宰相,一口氣用了12年,這可成全了王旦,王旦成了北宋歷史上不間斷做宰相時間最長的人,沒有之一。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真宗用人的風格,一旦需要馬上就用,一旦信任,就放手讓他去干。
第二條,強調“祖宗之法”。
北大歷史系鄧小南老師的名著《祖宗之法》,就是講這個的。什么是祖宗之法?其實無所不包:
是一核心精神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既包括貫徹維系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
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宋朝這么講究祖宗之法的?就是從宋真宗開始的。
你想想看,這是一個很高明的策略啊:既然我的個人權威沒有那么高,那我就借用前人的權威。太祖太宗的權威夠吧?那好,他們定下來的政治框架,我不動,以后的皇帝也不許動。但你意識到沒有?對于后世兒孫來說,宋真宗也是祖宗啊,他可以不動此前的框架,但是他也可以往里加自己的政策啊,兒孫也不準動,他就有了權威了。比如,宋代那個著名的策略“異論相攪”,異論,就是不一樣的觀點,相攪,就是攪合在一起,也就是讓不同的意見在朝堂之上同時并立,所以的人都不敢一意孤行、為非作歹,這個策略就是真宗定下來的。定下來之后,也成為后世的皇帝的“祖宗之法”。你看,講究“祖宗之法”,既保證了政治策略的一致性、延續性和連貫性,也給了真宗本人相當大的自由度和創造空間。
剛才我們講了宋真宗的兩條策略,一條是把具體的事務性工作交給宰相,以彌補自己能力不足的問題;一條是把自己的很多政治策略放在祖宗之法的框架中,一層一層地往上壘,一棒一棒地往下傳,以彌補自己威望不足的問題。
那好了,這都是借力的方法,那他自己干什么呢?
宋真宗的第三條策略:打造自己的新型的權威。
尤其有了王旦做宰相之后,真宗對日常性的政務就基本放手了。當時有官員很識時務,還專門上書說,您這么辛苦,以后應該只管大事,把小事委托給大臣處理得了唄?真宗馬上就表揚,說這個人“識大體”。
確實,要比起勤奮,他跟他爸爸太宗確實比不了。太宗皇帝,登基之后幾乎一天都不休息,連民間丟了一口豬都要管,一般普通人不可能有這樣的精力。但是真宗不管日常事務,他也沒閑著,他去專心打造自己的權威去了。
比如說,他在后宮里面專心寫文章來教化臣民。真宗一生著述非常多啊,他曾經一次性從宮中搬出722卷作品,讓大臣們刻板印刷。722卷,什么概念?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就不到300卷。雖然古人的一卷有多有少,不能完全比較字數,但是你也可想而知,700多卷是一多大的分量。
而且宋真宗還特別在意原創。誰要是說他的文章是別人代筆的,他就老大不高興。據歐陽修記載,有一次,翰林學士楊億夜里在翰林院值班,突然,真宗皇帝要召見他。什么事呢?也沒啥事,又是賜茶,又是問東問西,磨蹭好半天,最后拿出幾箱子文稿來,說你認得我的筆跡吧?你看看,這些文章可都是我自己寫的哦,可不是讓臣下代筆的哦。這幾句話,把楊億嚇得不輕,對啊,皇帝這啥意思啊?可能是有人跟皇帝講了嘛:楊億大筆桿子,在外面吹牛,說皇帝的文章,都是他代筆的。皇帝這是來敲打敲打他啊。
你看,寫文章、搞創作,不僅要當一代圣主,而且要成為理論權威,這是宋真宗的一個努力方向。
當然,我說到這兒,你肯定也明白了:他搞神道設教、東封西祀、偽造天書那些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為了這個。那也是他尋找新的權威資源的一個方向:皇權不夠,神權來湊嘛。搞這些事,當然是他一生的敗筆,這個沒什么可替他辯解的。但是,這也證明了真宗策略的一慣性: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對的首要挑戰,就是要彌補自己能力不足、權威不足的問題。他在這條路上做錯了很多事,但是大方向非常堅定,從來沒有偏離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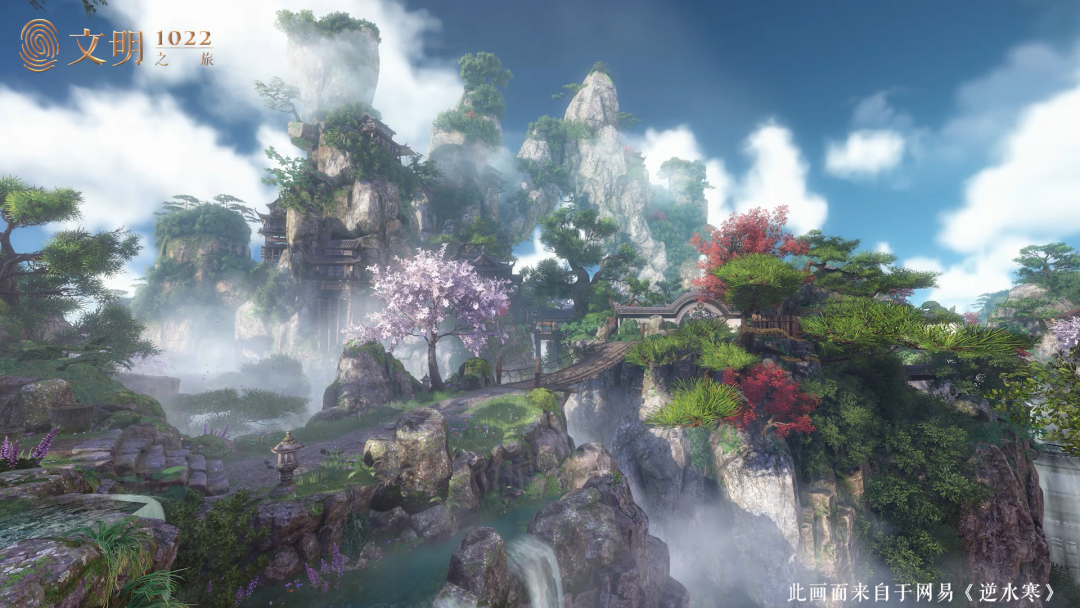
今天我們送別真宗,我自己有一個心得,就是讀書明理,知人論世,不是為了評價別人,更重要的是:我在別人一生的奮斗中能得到什么樣的啟發?我看宋真宗這一輩子,挺佩服他的一點:從年輕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的弱點,也知道彌補的策略。策略既定,就終其一生地堅決執行。
這讓我想起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寫的一首詩,說,“人生天地間,各自有稟賦,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能有這樣的一輩子,已經是一份很難得的善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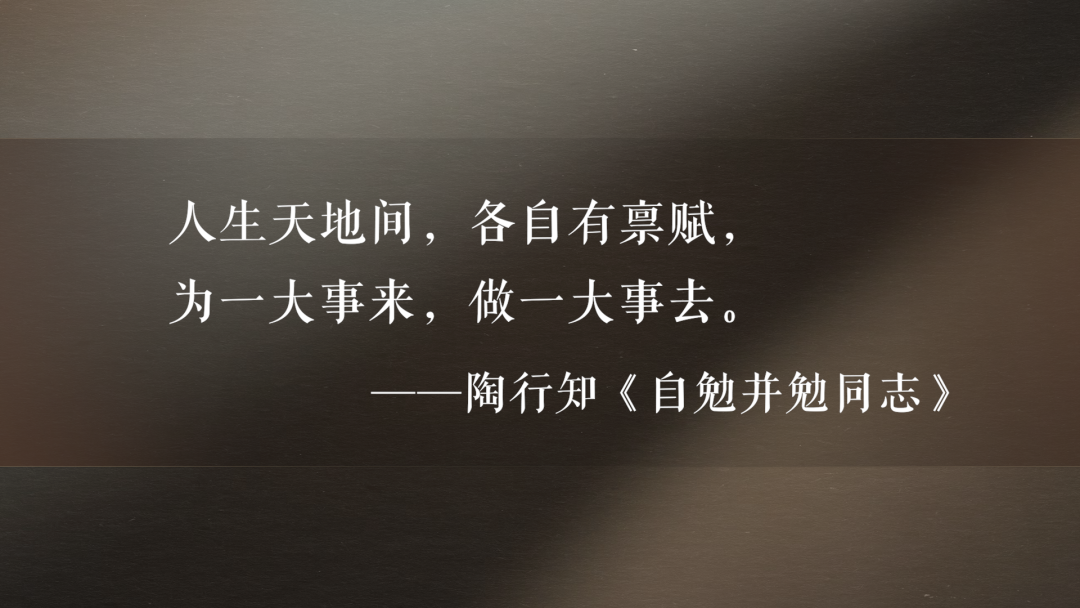
宋真宗的執念
剛才說到真宗皇帝的一個特點:認清自己的使命,然后堅決地按既定策略往前推進。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個挺倔的人,其實不然,宋真宗的性格里面有一種“化骨綿掌”似的東西,他不是靠倔強,而是靠韌性來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目標。
在那么多關于他的史料中,我幾乎沒有看見過他發怒,永遠是一副和顏悅色的樣子。如果臣下真的和他爭執起來了,往往是他當場讓步。但是,如果真是他想辦的事,過不了多久,他又會卷土重來,舊事重提。
這讓我想起一種現代的育兒理念,叫“溫柔的堅定”,對孩子的要求,比如現在去做作業,該上床睡覺了,指令要清晰而堅定,但是態度呢?要溫柔而理性。哎,這個詞,“溫柔的堅定”用來描述宋真宗,真的非常合適。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為劉皇后的謀劃。
咱們就借此機會,介紹一下這位劉氏,今年3月之前的劉皇后,3月之后的劉太后,后面十幾年大宋朝的實際掌舵人。
按照《宋史》的介紹,這位劉氏的祖上是山西太原人,后來舉家遷到了四川。她的爺爺是后晉、后漢時期的禁軍將領,她父親叫劉通,是宋朝的禁軍將領,大概三四品官的樣子。你看,很正常的一份家世嘛。
但是,不好意思,這個《宋史》是元朝人修的,活兒干得很糙,很多事實的考證不太講究。就劉太后的這一段,后來的史學家就看出了很多漏洞。比如前面剛剛介紹了劉太后的家世,緊接著下一段就說,劉太后沒有宗族。前后矛盾得很。倒也不見得是元朝人修《宋史》有意造假,而是因為修得匆忙,不管不顧地把宋朝官方的材料抄進來了,而這些材料有些就是被有意篡改了的。
其實,也用不著后世的歷史學家捉蟲了,同時代的很多人都知道劉氏的底細,當時就留下了很多痕跡。綜合來看,核心的問題就兩點:
第一,劉氏是四川人,家世寒微,而且是個孤女,剛出生,寄養在外祖父家。從少年時代起,劉氏就流落街頭,成了一名搖撥浪鼓賣藝的人。
第二,她后來嫁給了一個叫龔美的銀匠。龔美把她帶到了京城開封,把她轉賣給了當時還是皇子的宋真宗。
好了,現在你明白了:官方為什么要篡改遮掩劉氏的來歷了。出身寒微,而且還是個有夫之婦,這樣的人成了大宋朝的皇后、太后、甚至是最高話事人,按照當時的觀念,確實有點說不過去。
這段故事要是現在的編劇去寫,肯定會寫成一個勵志故事:一個貧家女子,偶遇太子,然后怎么通過一系列宮斗,升級打怪,最后執掌天下。簡直就是一部超級大爽劇。
但是,這個故事更符合歷史原貌的講法應該是這樣的:是宋真宗遇到了這么一位一生看重的女子,于是沖破重重阻力,使盡渾身解數,幾十年如一日地謀劃,成功地把出身寒微的劉氏一路托舉成皇后。當然,劉氏也沒有辜負他,在宋真宗身故之后,劉氏一邊照顧小皇帝宋仁宗,一邊垂簾聽政,主持大局。最后得到的歷史評價居然不錯。有人說嘛,她是“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就是有漢朝呂后和唐朝武則天那樣的政治才能,但是沒像那兩位一樣干壞事。但是,不管劉氏多出色,推動整個故事情節發展的,還是真宗本人。

咱們就一樁一件地擺擺,看看真宗為她做了些什么。
最早,真宗是想直接把劉氏封為貴妃的,但當時的宰相李沆不同意。而且李沆的態度是完全沒商量啊,當著使者的面,把皇帝寫的條子放在蠟燭上給燒了,一邊燒一邊讓使者給真宗帶話:“就說我李沆不同意。”李沆為什么這么堅決?因為真宗還是太子的時候,李沆就是太子班底里的人,對劉氏的來歷應該比較清楚。所以,只用說,“我不同意”就行了。真宗當然知道是為什么——劉氏出身太寒微,當貴妃她不配。
那看來正面強攻是不行了。真宗就等,一直等到1004年,在李沆去世的前夕,他把劉氏冊封為“美人”,這就比貴妃差遠了。按照北宋的制度,美人與貴妃之間,差17個等級,和皇后之間,隔著18個等級。這么低的一個位置,李沆沒有反對。真宗還為劉氏辦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把劉氏的前夫龔美改姓劉,龔美搖身一變成了劉氏的兄弟劉美。這事其實很關鍵。第一,劉氏就不是沒有來歷的人了,好歹有個娘家哥哥啊。第二,劉氏也不是改嫁的有夫之婦了。你們都搞錯了,那只是她娘家哥哥啊。你看,兩個關鍵問題都有了解釋。
接下來是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的事了,真宗的皇后郭氏去世,真宗就動了冊立劉氏為皇后的念頭。但是遭到了王旦、寇準、向敏中等一眾大臣的反對。
好,那就接著繼續鋪墊,還是得在劉氏的家世出身問題上做文章。轉過年,1008年,朝廷突然給劉氏的父親劉通贈了個官職。你看,官職不官職的其實不重要,關鍵是給劉氏編造了一個父親,當然有父親了,順便也就把什么媽媽、爺爺也都編出來了。
到了1009年,把劉氏從美人提升為修儀,這是升了7個級別。
而且此后,真宗還是惦記著替劉氏認一門親。有本宋人的筆記里,就記過這么一個故事。有個開封府的知府叫劉綜。你看,姓劉。真宗有一次召見他,就他暗示:“聽說,你跟后宮是比較近的親屬,我給你安排個官,你看你們是不是該聯系聯系,走動走動?”這個時候,只要劉綜就坡下驢,認了這門親,馬上就是潑天富貴。但是劉綜當時嚇得夠嗆,他立刻用當時的陜西話跟真宗說,“我是河中府人,而且家境貧寒,從來沒有親戚在后宮!”為啥用陜西話說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劉氏是四川人,我是陜西人,八竿子打不著哈。
這段筆記小說的記載,跟正史是對得上的。這個劉綜確實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當的開封知府,我們可以推測,這個時候認親,是有為劉氏立后做準備的意思。果然到了1012年,真宗先是把劉氏從修儀提升為德妃,這是升了8個等級。到這一年年末,真宗看著時機差不多成熟了,終于冊立劉氏為皇后。
其實直到這個時候,阻力還是挺大的。我們《文明之旅》1019年那期講楊億的時候就提到,真宗都已經下旨,要立劉氏為皇后了,希望翰林學士楊億來寫冊立皇后的制書。但楊億就是不同意。如果一定要他來寫,楊億說了,必須“請三代”。什么意思?就是讓劉氏把自己往上數的三代人,也就是父親、爺爺、曾祖父叫什么、哪里人、當過什么官、干過什么事,得交代清楚了。這是啥意思?這是楊億在抗議劉氏偽造履歷啊。
所以,為劉皇后偽造履歷的事情還有一個續集。六年后,也就是1018年,朝廷突然要重新安葬劉皇后的父親劉通。這是要以官方主持的重大儀式,再次確認劉氏的顯赫宗族。造假也要造得板上釘釘。
這就完了嗎?沒有。真宗不僅要把劉氏冊封成皇后,與此同時,他還要進一步鞏固她的位置,給她一個兒子。
正好,后宮里有一個李氏懷孕了,生下了一個男嬰。真宗二話不說,就把孩子變成了劉氏的兒子,讓劉氏負責養育,這就是后來的宋仁宗。那仁宗的親生母親李氏呢?什么名分都沒有給,真宗壓根就不承認這么個妃子。
這個故事后來在民間傳來傳去,變成了“貍貓換太子”,劉皇后就成了故事里的那個偷天換日,搶人孩子,迫害仁宗生母的大壞人“西宮娘娘”。這個當然不符合事實。順便說一句,很多人管劉皇后叫“劉娥”,其實這個名字也是民間傳說里才有的。我們在這里還是嚴謹一點,只能管她叫劉氏、劉皇后、劉太后,不能叫“劉娥”。
這個兒子的歸屬非常關鍵。后來,劉太后之所以能垂簾聽政,最關鍵的是兩個條件,一個是因為她是真宗的皇后,是先帝的正妻;另一個條件呢,是因為母憑子貴,她是仁宗的母親啊,仁宗年齡很小,需要母親的保護和幫助啊,所以劉太后才有了代替兒子處理天子事務的合法性。
說到這兒,你會不會覺得整個事情有點匪夷所思?這個劉氏,哥哥是假的,實際上是前夫;家世是假的,實際上壓根就子虛烏有;兒子也是假的,實際上是別人生的。從頭假到尾。而且,還不是她本人作假,整個戲碼都是真宗皇帝親自導演的。而且這個造假的過程,將近20年之久啊,從劉氏30多歲開始,一直到她50多歲。你聽聽這個歲數,你總不能說這是真宗皇帝被女色迷惑了吧?除了真愛,還有別的解釋嗎?
通過這個過程,你也可以看得出來宋真宗這人性格的一個側面:認定一件事,就持之以恒地努力,不用強,但是也不退縮,遇到阻力,就歇一會兒,換個姿勢,繼續前進,日拱一卒,直到達成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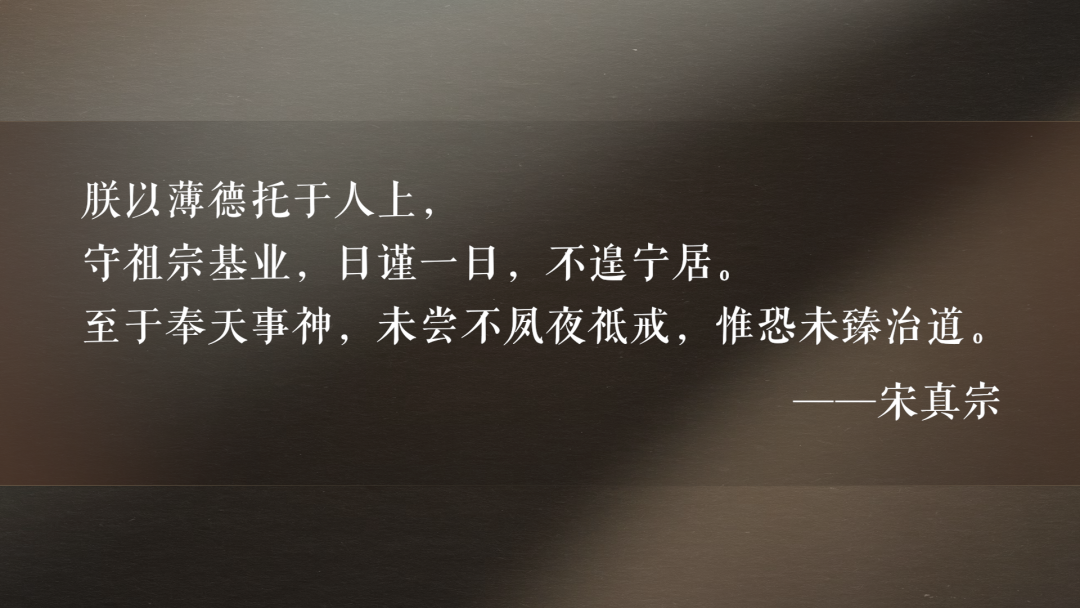
宋真宗的品格
從剛才說的那兩段里,你也聽出來了:真宗皇帝這個人,在個性上的優點,是一旦確定了目標就持之以恒;但是也有一個特別不好的習慣,就是為了目標,不惜造假。為了政治目標,在天書問題上造假;為了私人目標,在劉皇后的身份問題上造假。而且是瞞天過海幾十年,始終如一搞造假。這一點,不符合任何時代的道德標準。所以,沒什么可以替他辯解的。
但是,講了這么多期宋真宗,看了那么多關于他的史料,很不好意思地說一句:我對這個人有感情了。我知道他身上那可貴的溫暖的一面。而且這溫暖的一面,也為皇帝這個抽象身份里面注入了一點新的東西。
皇帝該怎么做,有標準答案嗎?沒有啊。是一代代的、形形色色、活生生的人,坐到了那個位置上,每個人都被儒家的圣君理想牽引,也都被祖宗家法和現實條件限制,更被自己人性中的善惡念頭影響,最后才變成了我們史書中記載的那一個一個的皇帝。每個人人格中閃光點,如果有的話,也都會或多或少地留在這個座位上,讓“皇帝”這個抽象的概念變得更豐滿一點,更具體一點,對后來者投射影響。
說回到宋真宗,他總體來說,是按照儒家的圣君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在關于他的史料里面,有很多體恤民間疾苦、虛心納諫的故事,咱們一概不說了。因為那不是他獨有的品格,其他皇帝很多也能做到。倒是有另外幾個故事,值得我們一起來品一品。

話說有一次,朝廷要給一個將領封官,有關部門報上來的方案,是讓他“領嚴州刺史”。嚴州就是今天杭州附近。請注意,這個“領”是什么意思?是“遙領”,就是名義上是那個地方的刺史,實際上并不去上班。你看,無關緊要的一件事嘛。但是真宗一看,說不行。為啥呢?他說出了一個理由:這個將領平時性格很嚴肅,管理部下也喜歡用嚴刑峻法。你們現在讓他去遙領嚴州的刺史,他難免會多心,覺得朝廷這是諷刺他。何必呢?改一個吧。
你看看,皇帝每天大大小小那么多事,給一個武將封官,而且是封這種沒有實質性的遙領職務,這個信息,一般人可能一眼就溜過去了,但真宗皇帝不僅注意到了這個細節,而且能夠設身處地地體察別人的心理活動,而且也愿意關照這樣的心理活動。你說這是什么品格?是細心?是善良?不僅如此啊,更重要的,是他有這份能夠體察他人的同理心。
這對一個皇帝來說,太難了。皇帝是高居在所有人之上的角色,只有別人探察他的心思的份兒,他有什么必要體察別人的想法?但是宋真宗做到了。
再舉一個例子:朝廷要編修《太宗實錄》,這是個挺大的工程,需要搭一個班子,有人就推薦了前朝宰相李昉的兒子李宗諤。真宗一看就說不行,他不能參與。為啥?真宗說,李昉在太宗時候當過宰相,現在讓他的兒子來參與修這一段的史書,你讓他怎么寫?修史,都是講究秉筆直書的。如果李宗諤遇到什么李昉的問題,為他父親遮掩,這不就影響了《太宗實錄》的信譽嗎?
當然,反過來這也是為李宗諤考慮:你只要參加了編纂,即使你是秉筆直書的,但是因為你是李昉的兒子,后世大家也會覺得你一定遮掩了什么,反而會影響李昉的形象。
真宗的意思很清楚,做一項人事安排,不要讓人陷入這種左右為難,里外不是人的境地。與其讓人尷尬,不如一開始就不讓他參與。你看,這件小事也是在說明真宗皇帝對人的處境的那種細致入微的體察能力。
還有一個例子。它不太符合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觀,但還是值得玩味。
話說,有一個軍官叫馬翰,他報告朝廷說,在開封城里面有一伙賊,他愿意親自出馬去把這些賊捉拿歸案。真宗一聽,就跟宰相們說,這個馬翰我知道。當年我在做開封府尹的時候,就聽說這個馬翰用捉賊的名義搞出了三樁禍害。第一件呢,他天天喊著要捉賊,城里的那些富戶都怕他搞敲詐,所以要經常賄賂他。這是一害。第二呢,他確實也能捉到賊,每次拿到贓款,他都會上報一個數,這個數足以判處盜賊死刑就行了,這筆錢充公,剩下的,他就全部獨吞了。這是第二害。還有,他經常養著十幾個無賴,到處去搞偵查,擾民嘛,這是第三害。
這個分析很到位啊。有意思的是,真宗接下來說,嗨,他干的這些事還沒有敗露,現在也別罷免他。這樣吧,以后在開封城里抓盜賊,就讓開封府去做,別讓馬翰在里面攪合。
這個故事里,可以玩味的地方特別多。
首先,作為一個皇帝,一聽說首都有盜賊,第一反應往往就是要除惡務盡啊,哪怕捉賊的人用的手段過分了一些,那也得先把賊抓了再說。但是真宗知道,只要朝廷急著捉賊,下面就會有人利用這一點謀私利。所謂“興一利”必“有一害”,就是這個意思。他對事情的這兩個面,都洞若觀火。你看,他不是那種自以為掌握了一些簡單的理念就可以治國安邦的人,他明白現實世界的復雜性。
另外,作為一個皇帝,聽說有人貪贓枉法,難道不趕緊把這人抓起來,該判判,該殺殺嗎?不,真宗說,這個人的事兒還沒有暴露,也就是說現在還沒有真憑實據,就不要動他。沒準他還有一層意思:既然公開跟人說這個事,也是想有人把話傳出去,讓馬翰聽到。如果馬翰能及時收手,那未嘗不是給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啊。
作為現代人,真宗皇帝的這個做法,我們未必同意。但是,他作為當時最有權力的人,做事不圖個簡單、直接、痛快,而是能夠從各個角度體察他人、諒解他人。既是一個有洞察力能看穿別人的小九九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愿意與人為善的人。這樣的特征集于一身,而且還是個皇帝,這就更加難得了。
大宋朝的皇帝形形色色,各有缺點,但是,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特征,就是他們身上的戾氣都不重。他們身為皇帝,手里握有最大的暴力機器,但是,在具體施政的過程中,對暴力則是能不用就不用。
這個特點,其實要追溯到宋太祖。趙匡胤雖然是個軍人,打過仗、殺過人、造過反、篡過位,但是他這一輩子,得饒人處且饒人,能講道理就不動手。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問問宰相趙普:你說,這天下什么東西最大。趙普被問懵了,想了半天,太祖又追問:你說,天下什么東西最大?趙普被逼出來了一個答案,他說,“道理最大”。太祖一聽,這個答案太棒了,對,天下道理最大。既然天下道理最大,那權力就不是最大的,皇帝就也要講道理,就不能動不動就亮拳頭。
從趙匡胤到宋真宗,三代皇帝基本都做到了這一條。

今天,我們在公元1022年送別宋真宗。看著他的背影,我特別想說——
你這輩子挺棒的。別的不說,就看20多年前,你寫在即位詔書里的那兩句話:“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你想通過感召天地之間的和善之氣,來延續大宋朝這份美好的基業。你這一任,把大宋朝“召天地之和氣”的執政風格又往前延續了20多年,為下一個時代的圣賢氣象做好了準備,挺棒的。
這里是公元1022年,明年,公元1023年,也是劉太后垂簾聽政、權傾天下的第一年。明年,我們就來好好觀察一下這位劉太后。
明年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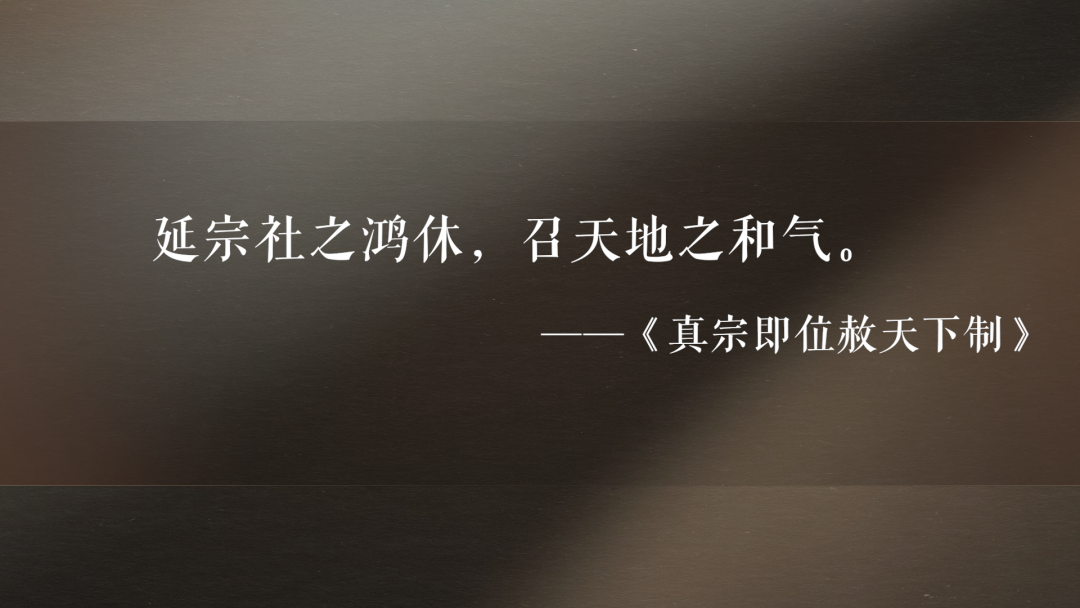
參考文獻: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宋)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中華書局,2017年。
(宋)張舜民撰:《畫墁錄》,中華書局,1991年。
(宋)王偁撰,孫言誠等點校:《東都事略》,齊魯書社,2000年。
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中華書局,1962年。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匯編》,中華書局,1981年。
劉靜貞:《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北宋前期》,稻香出版社,1996年。
張邦煒:《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人民出版社,2003年。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06年。
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中華書局,2010年。
杜樂:《宋真宗朝中后期的“神圣運動”研究——以“天書”和玉皇,圣祖崇拜為切入點》,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劉靜貞:《權威的象征——宋真宗大中祥符時代(1008-1016)探析》,《東吳文史學報》第七號,1989年。
劉靜貞:《從皇后干政到太后攝政——北宋真仁之際女主政治權力試探》,收入鮑家鱗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稻鄉出版社,1991年。
燕永成:《試論劉太后與宋真宗朝史的編修》,《史林》2010年第3期。
王瑞來:《“貍貓換太子”傳說的虛與實——后真宗時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博弈》,《文史哲》2016年第2期。
顧宏義:《誰增“權”字:宋仁宗繼位初年丁謂、王曾政爭發覆》,《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