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錢一棟|政治現實主義:昨天、今天、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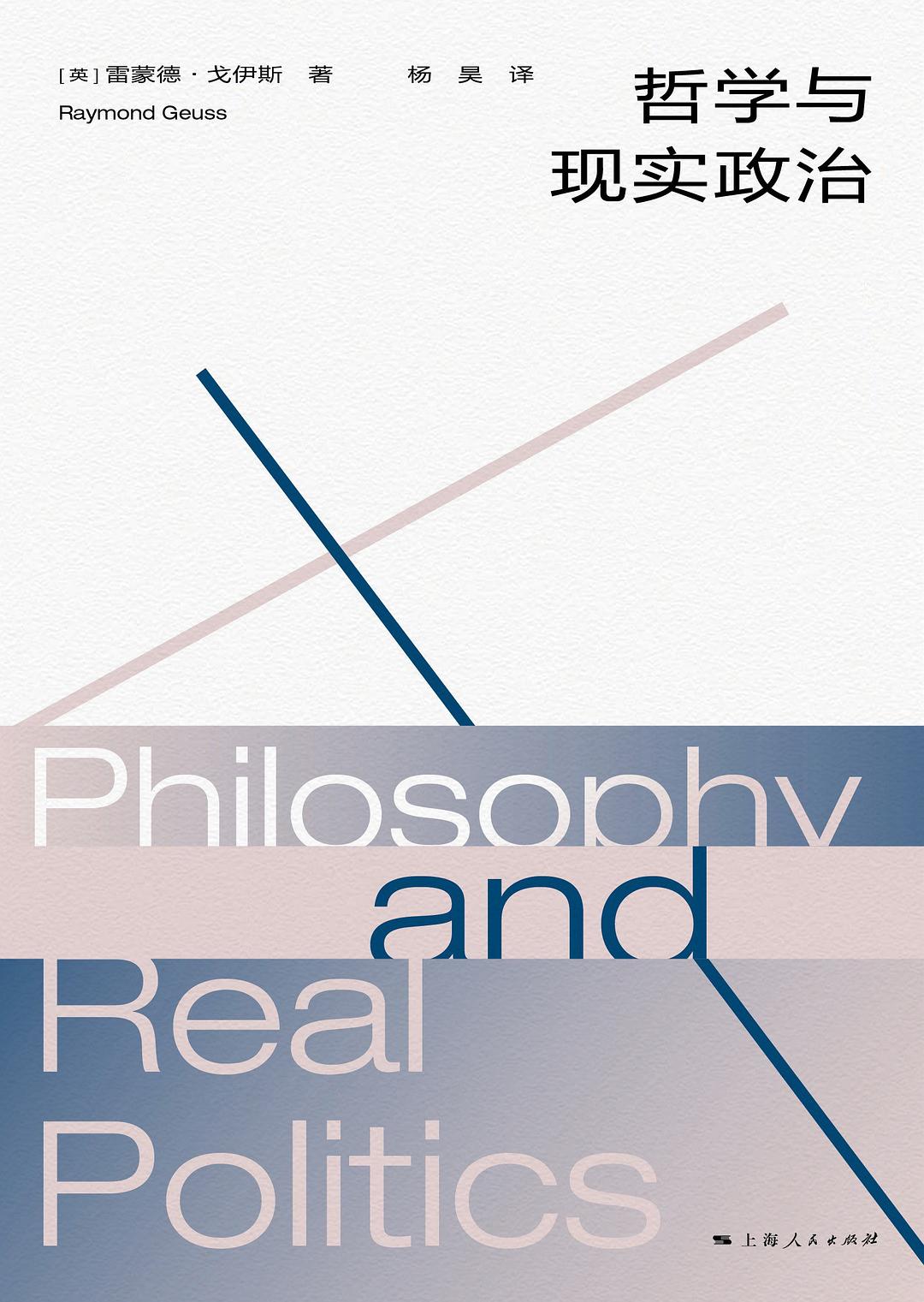
《哲學與現實政治》,[英]雷蒙德·戈伊斯著,楊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158頁,5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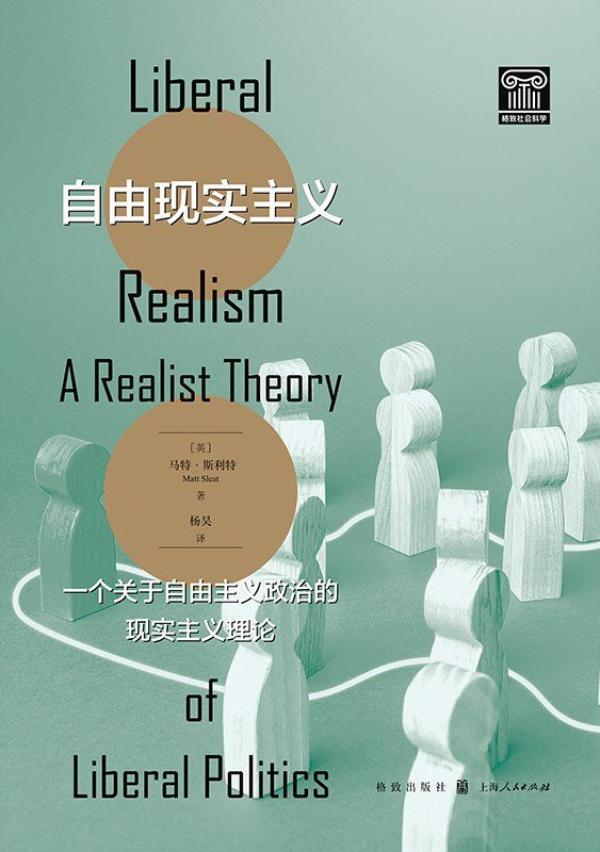
《自由現實主義:一個關于自由主義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英]馬特·斯利特著,楊昊譯,格致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170頁,55.00元
我國學界對政治現實主義(后文多簡稱“現實主義”)的研究起步不算晚,但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只有陳德中等極個別學者專精于此。今年比較特殊,不僅多場學術會議設置了現實主義專題,上海人民出版社也連續出版了兩部現實主義力作:雷蒙德·戈伊斯的《哲學與現實政治》,以及馬特·斯利特的《自由現實主義》,譯者均為中國人民大學楊昊博士。本文將把這兩本書放到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中作介紹和分析。
一、熟悉又陌生的政治現實主義
政治現實主義不算新鮮事物。在思想史上,它與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韋伯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用以標示一系列具有松散相似性的主張,如“在國際關系領域,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家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因素”“政治家應學會作惡”“政治是一種應對沖突的審慎方案”“政治應遵循與私人道德不同的倫理規范”等。在公共話語中,它常指向可行性考量,對立面是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烏托邦幻想。“強權即公理”之類的論調,有時也會披上現實主義外衣。
但當代政治哲學中的政治現實主義并不是從這些思想史脈絡或公共話語中自然生長出來的。相反,它的歷史并不久遠,且一開始便以高度學術化的形態出現。它的首要代表人物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倫理學家伯納德·威廉斯。威廉斯晚年涉足政治理論,留下未竟之作《太初有為》(Bernard William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譯本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里面最重要的文章《政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和道德主義》沒逃過熱衷搜羅各路政治哲學思潮的應奇的法眼,已由他在2011年譯出)。此書的出版是政治現實主義登上學術舞臺的標志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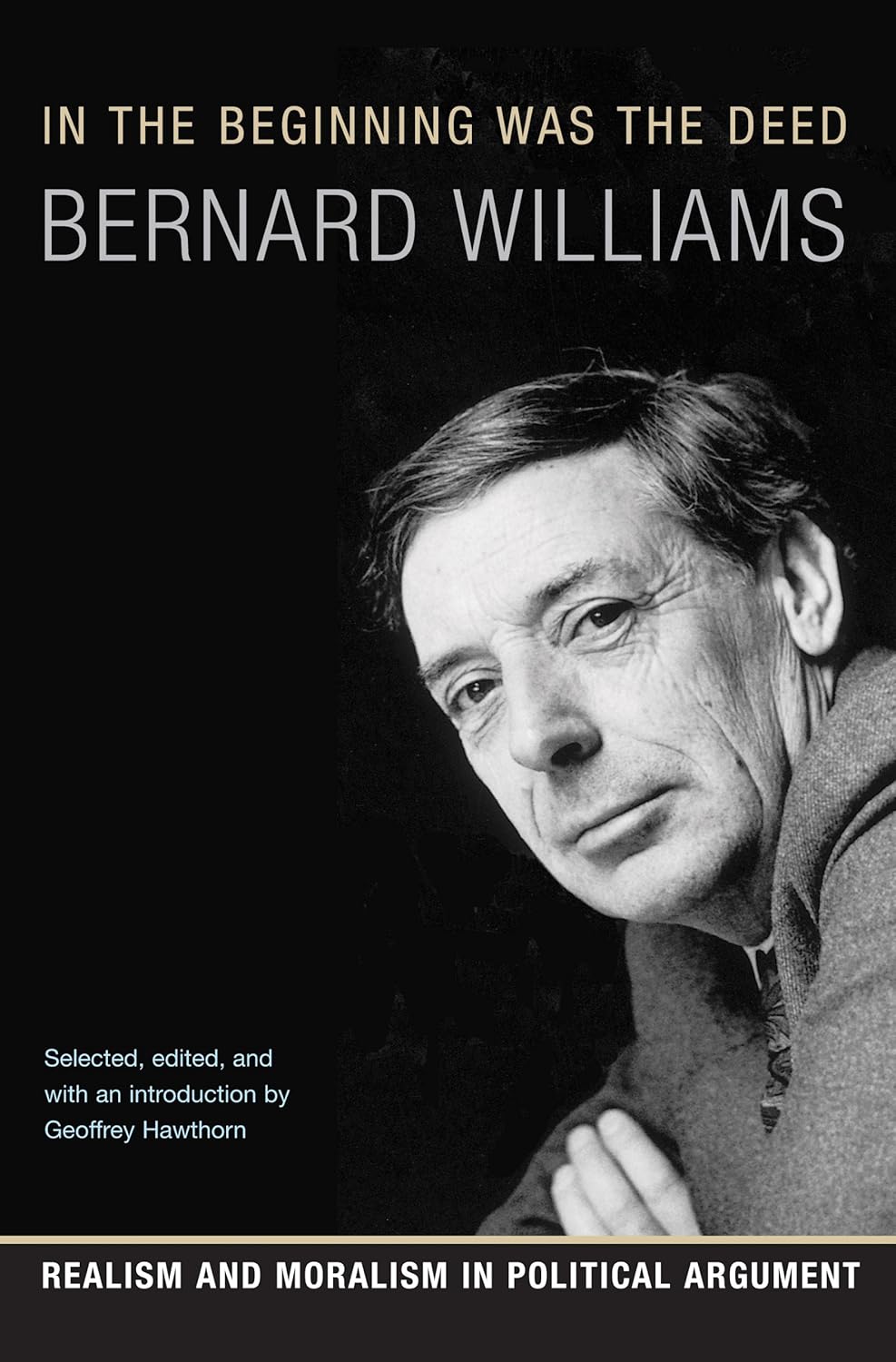
伯納德·威廉斯著《太初有為》
政治現實主義是對當代主流自由主義的批判性回應,后者以羅爾斯和德沃金為代表,高度道德化,致力于圍繞若干核心原則構造規范性理論。從學科看,政治現實主義幾乎從不與國際關系領域大名鼎鼎的現實主義流派對話,更別提雷蒙·阿隆之類的。從地域看,政治現實主義-主流自由主義之爭呈英美對立格局。羅爾斯、德沃金都是美國人,政治現實主義這邊則以英國學者為主,如威廉斯、戈伊斯、邁克爾·弗里登、尚塔爾·墨菲以及年輕一輩的斯利特等。因此,對主流自由主義的一項次要批評是,它是一種高度美國化的地方性理論,特別是與美國獨特的憲法制度聯系緊密(德沃金本人對這一背景作過介紹,參見《哲學與政治:對話羅納德·德沃金》,載[英]布萊恩·麥基:《思想家》,吳蕓菲譯,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366頁;威廉斯與德沃金的思想分歧值得深入挖掘,威廉斯的現實主義用來批評羅爾斯不時讓人覺得牽強,對付德沃金則格外貼切)。現實主義內部有激進派與溫和派之分。前者對規范性理論,特別是對自由主義理論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后者則愿意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接納這些內容。戈伊斯與威廉斯分屬激進派與溫和派,恩佐·羅西和斯利特則是年輕一輩學者中兩派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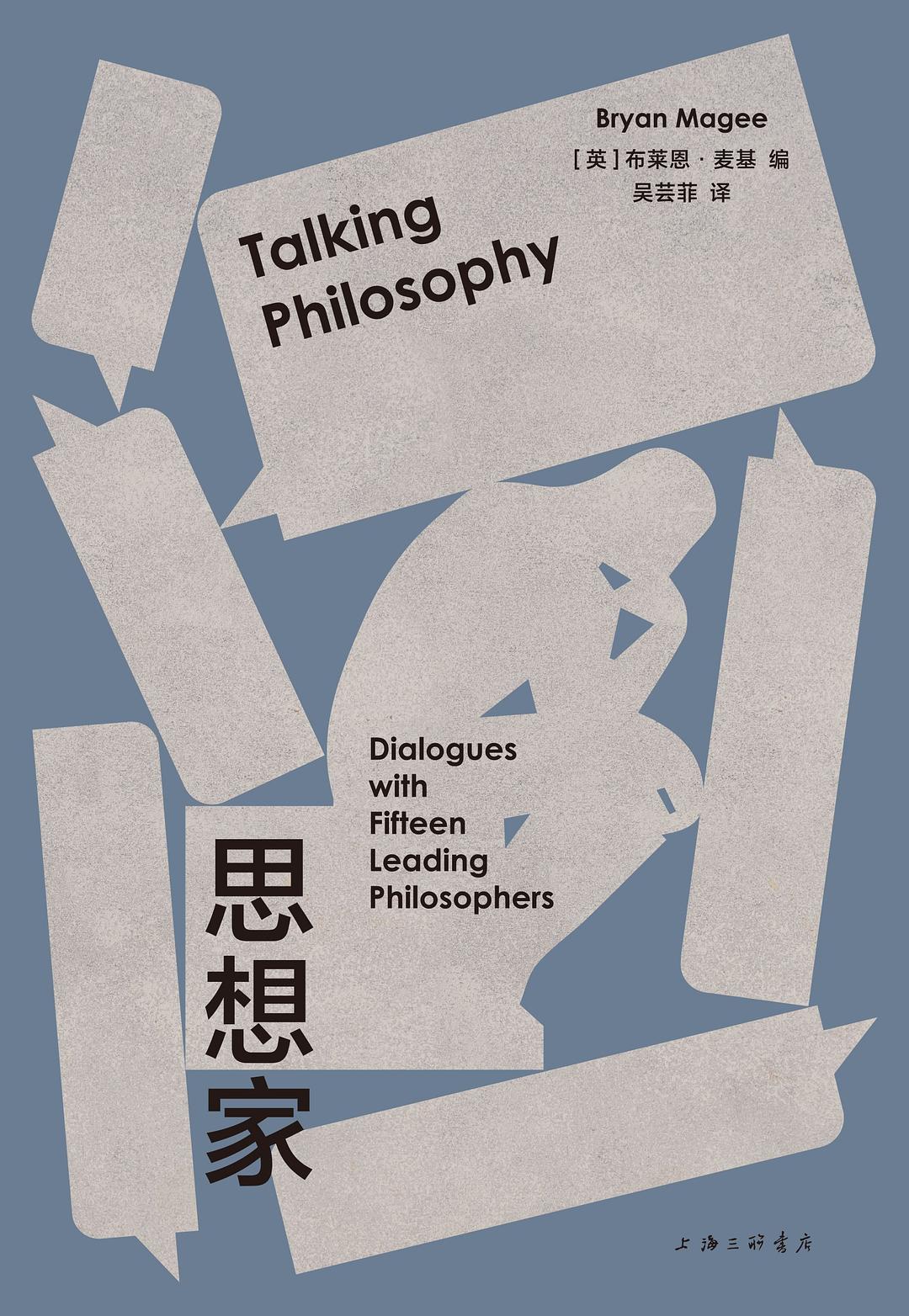
布萊恩·麥基編《思想家》
早些時候,有學者會把現實主義當成理想理論的對立面,視之為非理想理論的另一種說法(如Willian Galston, “Realism in Politic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9, No. 4, 2010),但如今已少有人持這種看法。澄清現實主義和非理想理論的區別有助于我們擺脫對現實主義望文生義的誤解,快速進入當代學術語境。
非理想理論與理想理論相對。兩者的關鍵差異是對可行性問題有不同考量。理想理論不過多考慮實際存在的歷史傳統、社會經濟狀況、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約束條件,抽象地構造理想政治圖景。非理想理論則是在現實條件的約束下,探討切實可行的政治目標和手段。一般認為,兩者是分工合作關系,誰也離不開誰(也有不同觀點,如Amartya Sen, “What Do We Want from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03, No. 5, 2006)。政治現實主義則與政治道德主義相對。道德主義是一種應用倫理學進路,致力于從外在于政治的道德中推導出政治領域的原則、價值、理念等。現實主義者則主張,政治領域有一系列獨特問題,道德哲學幫不上太大忙,同時他們往往對道德哲學本身有諸多疑慮,因此拒絕應用倫理學進路,強調構造政治規范性要從對政治的理解,而非從外在于政治的道德起步。這不是說他們持非道德或反道德立場,例如威廉斯并不介意給政治規范性標準貼上道德標簽,只要承認這種道德標準內生于政治領域即可。(2018年,《倫理》[Ethics]雜志發表喬納森·梅納德[Jonathan Leader Maynard]與阿列克西·沃斯尼普[Alex Worsnip]合寫文章《存在具有政治特色的規范性嗎?》[Is There a Distinctively Political Normativity?]。受此文激發,最近幾年學界對政治現實主義是否以及能否主張非道德的政治規范性作了大量討論。)
政治現實主義的大部分內容屬于元規范層面,抽象地分析政治規范性和道德、審慎規范性,以及和人性、歷史、權力等事實因素的復雜關系。它也有規范性層面的主張,但談得非常稀薄,可以容納各種實質立場。例如威廉斯主要談正當性,并認為歷史語境不同,正當政體的形態也多有不同;自由主義絕非永恒普遍的最佳政體,它只是在現代語境下最說得通(make sense)。威廉斯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正當性+現代性=自由主義。
總體來看,政治現實主義是一種元理論立場,致力于對政治哲學的主題、目標、方法等作通盤反思。戈伊斯的書是這方面的代表。但現實主義也可以進入實質理論層面。例如可以基于現實主義洞見,去重新理解自由主義。斯利特的書便是在做這種研究。下面我們進入這兩本書。
二、輕浮的戈伊斯
戈伊斯出版于2008年的這本《哲學與現實政治》地位崇高,是政治現實主義的第二經典。它與第一經典——威廉斯的《太初有為》——共同設定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基本立場。但我對戈伊斯一直印象欠佳,覺得他雖然能說幾句漂亮的刻薄話,但給不出嚴肅周密的論證。讀完《哲學與現實政治》后,這一印象甚至更牢固了。這很難算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更像是一個自認為看破社會真相的大學男生,把上政治哲學導論課時在朋友圈隆重發表的若干高論——政治不會按哲學家的想法運行;權力是政治的核心;主流政治哲學充其量就是些意識形態——集合成書。有朋友提到,中國讀者很容易被戈伊斯吸引。這大概是因為戈伊斯的觀點與我們的知識背景高度親和。這不見得是好事。相反,這意味著讀戈伊斯可能會強化我們的固有偏見,特別是助長對規范性理論的非常粗鄙的輕視。
寫到這里,本文也有些戈伊斯化了:批評的話說了很多,但沒提供相應的論證。好在塞繆爾·弗里曼寫過一篇書評(Samuel Freeman,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Review], Ethics, Vol. 120, No. 1, 2009),說了我想說的所有話。這篇書評介紹了《哲學與現實政治》的主旨和正面立場,澄清了戈伊斯對當代規范性政治哲學特別是羅爾斯的理論的粗糙誤解,并圍繞道德直覺問題對戈伊斯作了批評。戈伊斯有個著名的說法:“倫理往往只是死去的政治。”(Guess, Poli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2)他批評羅爾斯等人從道德直覺出發構造理論,但從不去思考這些直覺有否被權力關系污染,因此受意識形態操控而不自知。弗里曼反駁道,對于權力關系如何污染了我們的道德直覺,戈伊斯缺少有力的說明。同時,鑒于戈伊斯自己也訴諸道德直覺(意識形態批判家往往容易忽視這一點),他還需要解釋下如何區分可靠與不可靠的直覺。在此,他所青睞的歷史方法派不上太大用處。我們可以借用威廉斯的一句話來總結戈伊斯的理論病癥:“激進的批評家有時逼問這樣的問題,只是他們往往自己掉進了忿忿不平的循環圈里:他們指斥某種虛假意識,(后來表明)是因為這種意識不接受他們自己的那套意識形態。”([英]B.威廉斯:《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陳嘉映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124頁)
戈伊斯的書寫得很簡略,弗里曼的書評也不算長。讀者如想一探究竟,半天時間也能看出個七七八八。晚近的一些研究推進了戈伊斯的立場,可用來回應弗里曼的批評。例如羅西最近幾年連續撰文解釋,意識形態批判不必訴諸道德,這是一種認識層面(epistemic)而非道德層面的批判,僅致力于揭穿權力關系如何污染了政治正當性敘事,從而使人產生錯誤的正當性信念(Enzo Rossi, “Being Realistic and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Constellations, Vol. 26, No. 4, 2019; idem, “Ideology Critique without Mor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7, No. 4, 2023)。這一路徑確實避開了意識形態批判對批判者本人道德立場的反噬。但將意識形態批判限縮為認識層面的批判多少有些像斷臂求生,不見得是高招。
三、混亂的斯利特
(一)主題和結構
威廉斯與戈伊斯的書出版后,政治現實主義的研究推進并不明顯,闡釋、辨析類文獻占發表的多數。斯利特出版于2013年的這本《自由現實主義:一個關于自由主義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則較為獨特:它嘗試提出一些新觀點,且進入了實質理論層面,而非繼續作元理論層面的空談。如此書副標題所示,作者的寫作意圖是為自由主義政治提供一個現實主義解釋(參見[英]馬特·斯利特:《自由現實主義:一個關于自由主義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楊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頁)。全書共分七章,前三章、第四章、后三章分別構成相對獨立的論證板塊。
前兩章依次解釋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視角下的政治圖景,作者稱之為“共識圖景”和“沖突圖景”。在此基礎上,第三章解釋現實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挑戰,核心要義是“共識圖景”無法應對現實政治中普遍存在且難以消除的分歧與沖突(粗略言之,政治分歧發生在特定主義內部,如不同自由主義流派之間的爭論便屬于政治分歧,政治沖突發生在不同主義之間,觀點間的差異程度更深,參見53頁,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用詞頗為隨便,如124頁)。
在第四章,作者考察了兩種非主流的自由主義方案:施克萊的恐懼的自由主義,以及約翰·格雷等人的權宜之計自由主義。它們都富有現實主義精神,降低了對共識的要求。但作者認為其所追求的單薄共識依然不現實。
最后三章是正面立論。作者先是通過批評威廉斯,強化了對政治現象的現實主義描述,然后解釋接受這種沖突現實對自由主義意味著什么,自由現實主義是一套什么樣的理論。
乍看之下,此書論證結構挺清楚,但它只是在最抽象的層面還算清楚。最后三章的關系事實上已有些混亂。至于每章內部,則稍細致點摳論證線索便會發現寫作不夠緊實。作者概括提煉能力平平,無法保證章節主題、理論命題的清晰性和區分度,不少內容翻來覆去、交叉重疊,甚至前后矛盾。關于這點,這里沒法展開證明。好在此類問題遍布全書,讀者不難自己求證,且后文也會提到一些。此處要展開討論的是核心概念的含糊性。澄清這些概念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全書主題。
首先是自由主義。作者主要批評的并非不加限定的自由主義,而是當代康德式自由主義(26、85頁,更準確地講是康德式自由主義的最新代表——政治自由主義,作者基本沒提《正義論》、諾齊克與德沃金)。即便是康德式自由主義,他也只批評其對政治的理解不切實際。對其道德關切——尊重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作者多有認同(81頁)。此書的基本意圖便是將這種道德關切與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解結合起來,構造一種自由現實主義。
但作者提到自由主義時極少加限定詞。由此而來的最大問題是,對康德式自由主義和一般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的混淆貫穿全書。作者確實提到,除了康德式自由主義,還有基于功利主義的、洛克式的、鮑桑葵式的自由主義(26頁)。但這一澄清更像草率的免責聲明,他常常寫著寫著就忘了。有時我們很難判斷他筆下的自由主義是真的不用加限定詞,還是省略了“康德式”這一限定。例如他說:“……訴諸共識是當代自由主義理論所青睞的用以表現對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尊重的策略。……因此,為了終究能夠成為一種自由主義理論,自由現實主義將不得不找尋在不訴諸共識的前提下,回應那些同樣的道德關切的方式。”(80-81頁,翻譯有修改,下同)作者將自由主義和這一道德關切相綁定的表述還有不少。但熟悉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這種關切帶有強烈的康德印記(作者有時也會提這一點,如27-28頁,這反而更讓人惱火:錯也錯得不清晰)。不少自由主義流派并不把這一關切放在首位,如基于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權宜之計自由主義(因此第四章有暗換主題的嫌疑)。還有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是,只有自由主義才能表達這一道德關切嗎?但作者對諸如此類的問題都缺乏敏感。
另一個引發混亂的核心概念是“政治圖景”(vision of the political)。此概念在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作者沒有專門解釋其含義。結合相關論述可知,所謂政治圖景,是對政治的概念化構造,基本是政治概念的另一個說法。例如作者說:
現實主義呈現了一種與當代自由主義存在深刻差異的政治圖景。在最根本的層面,自由主義強調政治共識、一致意見與和諧,現實主義則強調政治沖突、分歧與不一致。(第3頁)
現實主義通過提供一種政治圖景來挑戰自由主義,這種政治圖景削弱了根據共識、一致意見或者說普遍認可來思考政治的說服力或者說恰切性。現實主義政治圖景通過將政治概念化為一種發生在普遍、持久且無法消除的政治分歧和沖突的環境中的活動來挑戰自由主義。(69頁)
問題在于,政治這個詞含義豐富、外延寬廣,許多概念化方案在語言層面都說得過去。不同的理論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化方案,我們無法脫離具體的理論規劃來評判概念用法的好壞,后者取決于理論家想拿這個概念干什么,干得怎么樣。意識不到這一點會陷入無聊乃至愚蠢的語詞之爭,把很簡單的一詞多義現象當成深刻的理論分歧。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讀者腦海中大概率會浮現出這樣一種反駁:自由主義政治圖景是一種規范性圖景,現實主義政治圖景則是描述性圖景,兩者并不矛盾,可以在非理想理論層面調和。這一反駁并不完全成立,但指出了有待作者回應的關鍵問題:所謂政治圖景,究竟指向描述性還是規范性政治概念,是在解釋政治實際上是怎么回事,還是在講理想的政治是什么樣的?作者只在第75頁援引他人觀點時,才頗為隨意地用過一次“政治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圖景”,大部分表述則給人以描述性的暗示。也因此,中譯本將“vision”翻譯成“愿景”,在許多上下文中讀來都挺怪異。談現實主義時更是如此,如第二章的標題“現實主義政治愿景:沖突、強制和政治的環境”。但這主要是作者而非譯者的問題。
作者提到,自由主義政治圖景源于尊重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這一規范性承諾。“因此,自由主義者總是會面臨一個重要問題,即我們如何協調個人自由和共同生活在單一政治權威之下這一顯而易見的需求。”(21頁)作者認為,自由主義者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是訴諸共識,政治正當性以全體公民的同意為條件。據此,服從政治權威便是在服從自己的意志,自由和權威的矛盾于是消解了。既然共識圖景是解決規范性難題的方案,它也應該被理解為一種規范性圖景,現實中存在最好,不存在也不妨礙其成立。“簡言之,自由主義想象出了一種非壓迫的或者說非暴政的政治形式。”(同前)——它是“想象”出來的,是規范性思考的構造物,而非對現實政治的描述。
接下來的問題是,所謂共識,是事實上的共識,還是假設的共識。須注意,訴諸實然共識不是說現實中已經存在共識。相反,這是提出了一種極為嚴苛的規范性條件:只有當所有受治者事實上都認可國家時,國家才有正當性。那么,自由主義檢驗政治正當性的標準是實然還是假然共識呢?這一關鍵問題留到下一小節討論。
初看之下,現實主義政治圖景的性質要清楚許多。作者反復強調,分歧、沖突是政治領域根深蒂固的事實,據此,“政治是這樣一種活動:它發生在極端分歧、不一致與不和諧的環境中,但又促成或促進穩定性和秩序”(第2頁)。以提供這種政治圖景為己任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是在理解政治”,“這種理解不會排除提出規范性政治方案的可能性,但它確實要求,任何這類提議都得以在描述和說明的層面盡可能準確的政治圖景為基礎”(第7頁),“現實主義……沒有明確的政治方案”,“現實主義不是……政治意識形態”(第9頁)。
從這些表述來看,現實主義政治圖景應該是描述性的。但作者又強調,“(按現實主義者的觀點)盡管對政治問題的回應不需要符合正義、公平或平等之類的,但它確實必須是正當的,不然就不能算作政治,而只是單純的支配”(45頁)。據此,現實主義政治圖景又非單純的描述性圖景,而是側重描述性,兼有稀薄的規范性。這種稀薄的規范性可以兼容自由主義,視之為對正當政治的具體回答。當然作者強調,自由主義無法原封不動地與沖突圖景相結合。它要“以在描述和說明的層面盡可能準確的政治圖景為基礎”,因此必須放棄共識圖景。后者不是有待實現的理想,而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由此帶來的難題是,如何在放棄共識圖景的同時,找到激發自由主義道德關切的方式,使之終究還是一種自由主義(82頁)。這是最后一章要回答的問題。
(二)三個對手
上文提到,此書有三個相對獨立的論證板塊。在每個板塊,作者都給自己安排了對手:主流自由主義者(羅爾斯等)、有現實主義色彩的非主流自由主義者(施克萊、格雷等)、不夠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者(威廉斯)。與這些對手的交鋒是此書前五章的基本內容。本小節將依次分析作者對三者的批評是否成立。
1. 主流自由主義者
如前所述,作者認為政治分歧和沖突不可避免,自由主義追求共識圖景不切實際。自由主義這邊的現成回應是,實然共識確實不現實,但自由主義只追求假然共識。作者承認這一點。他說:“當然,幾乎沒有自由主義哲學認為政治是根據所有人確實都接受的原則進行的,但卻常常堅持認為,可以期待所有人都合乎情理地接受這些原則(或者說根據所有人都有望合乎情理地接受的理由得到證成)。”(71頁)
如德沃金所言,假然契約不是真正的契約,它壓根不是契約(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51)。假然共識也不是真正的共識,它無法像所有公民的實際同意那樣證成政治正當性(這里不進一步討論同意理論是否真的能證成政治正當性,也不辨析契約論與同意理論、同意與共識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這不是說假然共識必定無法證成正當性,而是說真正有證成力的是達成共識的理由,而非假然共識本身。這不是說事實上有多少人接受自由主義完全不重要。相反,這非常重要。擴大共識、縮小分歧是自由主義者特別是羅爾斯極為關心的事情。但這種共識必須是合理共識。這一規范性限定使它與實然共識拉開了距離。因此圍繞共識圖景做文章很難傷到自由主義。作者回應這一反駁的策略是區分正義和正當性,將假然共識說成是自由主義證成正義而非正當性的方法,并隱晦地主張,只有所有受治者的實際贊同才能確立起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正當性(參見71-72、79-80頁)。于是他又可以繞回共識圖景來批評自由主義的正當性論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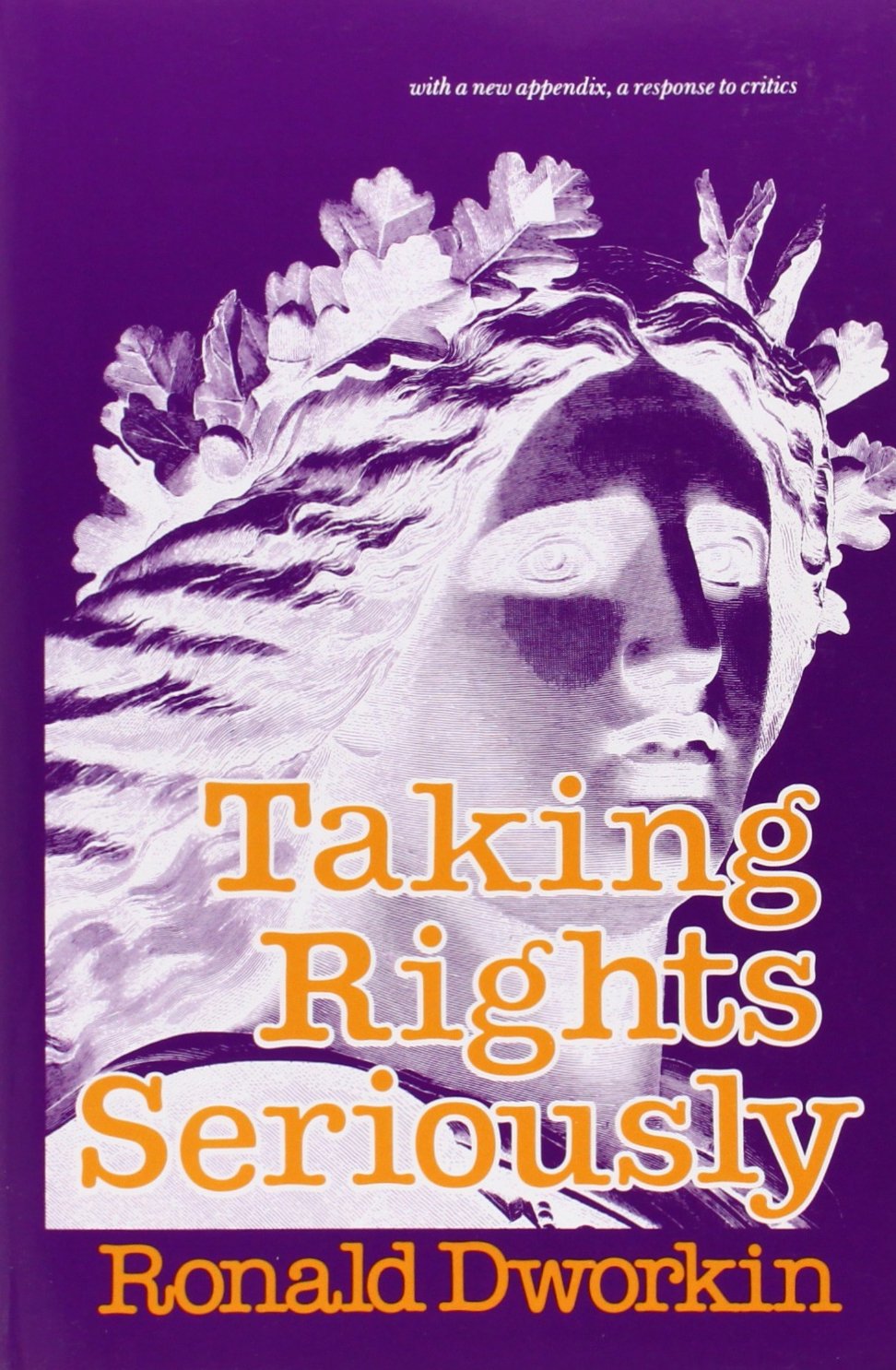
德沃金著《認真對待權利》
突兀而又隱晦地引入正義與正當性的不同論證方式,似乎只是作者挽救共識圖景批判的倉促無奈之舉。這套說法不僅與作者別處的論述相矛盾,也不符合羅爾斯等人的實際觀點。在此書第一章澄清自由主義的正當性觀念時,斯利特并未明確區分正義和正當性,且承認兩者都基于假然共識(如34頁)。在其他文章中,他同樣承認,自由主義者訴諸假然共識來證成正當性(Sleat, “Justice and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Liberal Thought: A Critique,” Social Theory & Practice, Vol. 41, No.2, 2015)。這本就是一個常識。例如在羅爾斯那里,當國家根據通過假然共識檢驗的憲法行使權力時,它便具有正當性(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7)。
除了認為假然共識和正當性之間存在張力,作者對自由主義還有另外三項批評:政治自由主義既試圖避開道德分歧,又訴諸某種道德價值,因此是自我挫敗的;即便存在抽象的自由主義共識,落到具體層面也還是會有分歧;即便自由主義的規范論證確實成立,事實層面的分歧也不會消失,而自由主義沒告訴我們該如何應對后者。這些批評或老套,或瑣碎,且主次不明、邏輯關系不清,顯得非常混亂。
混亂的另一個表現是,作者其實還提出了另外兩項批評,但被他塞進了第一和第四項批評之中。首先是對盧梭式公意觀念的警惕:所謂假然共識,容易淪為雅各賓式暴政的說辭。這個批評指向政治科學乃至知人論世層面,非常重要,但缺乏理論深度。且自由主義在這方面歷史記錄良好,不容易被指控。
其次,作者質問道,既然自由主義者承認宗教、道德問題上存在合理分歧,為何不承認政治分歧和沖突也合乎情理?此處作者將政治與道德、宗教并列顯然有欠考慮。羅爾斯等人無論怎么強調政治領域的獨立性,也不會把道德和政治徹底分開。寬厚起見,我們不去計較這些糟糕的表述,盡可能善意地解讀這些話。可以認為,作者實際想表達的就是對政治自由主義的“不對稱性批評”(asymmetry objection):政治自由主義一方面承認整全性觀念層面的合理分歧無法消除,另一方面又主張可以就正義、正當性問題達成合理共識,如何解釋這種不對稱性呢?這個批評非常重要——事實上是此書的核心所在,第三小節詳述——但并不新鮮,沃爾德倫、桑德爾等人早就提過。作者能把這樣一個經典批評表述得如此笨拙倒是很讓人驚奇(他后來發展了這方面的論證:Sleat, “A Defense of the Radical Version of the Asymmetry Objection to Political Liberalism,” Croat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4, No. 40, 2014)。
2. 非主流自由主義者
處理完主流自由主義,作者又瞄準了第二個敵人:“如果現實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挑戰僅對準其康德式變體,那么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去支持一種不同的、沒沾上現實主義所拒絕的那些理論特征的(自由主義)版本。”(85頁,作者寫過一篇同主題論文:Sleat, “Liberal Realism: A Liberal Response to the Realist Critiqu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73, No.3, 2011)于是此書第四章討論起了施克萊的恐懼的自由主義,以及格雷等人的權宜之計自由主義。
恐懼的自由主義視殘忍為首惡。殘忍引發恐懼,恐懼則是“邪惡生長的根本道德環境”([美]朱迪絲·N. 施克萊:《平常的惡》,錢一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64頁),確保免于恐懼的自由于是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權宜之計自由主義把政治視為一種審慎的妥協,追求的是在共同的政治框架下和平共處。相比主流自由主義,這兩種自由主義依賴的共識更稀薄,更具現實感。作者的批評很簡單:不是所有成員都接受這類觀點。例如人們有時會認為,為了其他重要價值,可以犧牲和平(98頁)。這種批評又會面臨基于假然共識的反駁。這里的關鍵在于,作者以不存在實然共識來批評他人,但幾乎沒有哪種理論會去追求不打一點折扣的實然共識。這不只是因為不可能,更是因為不合理。總歸會有一些人的意見可以被合理忽略,不作任何限定的同意本身缺乏規范性力量。甚至連同意理論的最大代表洛克,也不認為僅憑同意便能確立起正當政治權威。他對同意的討論是在自然法的背景下進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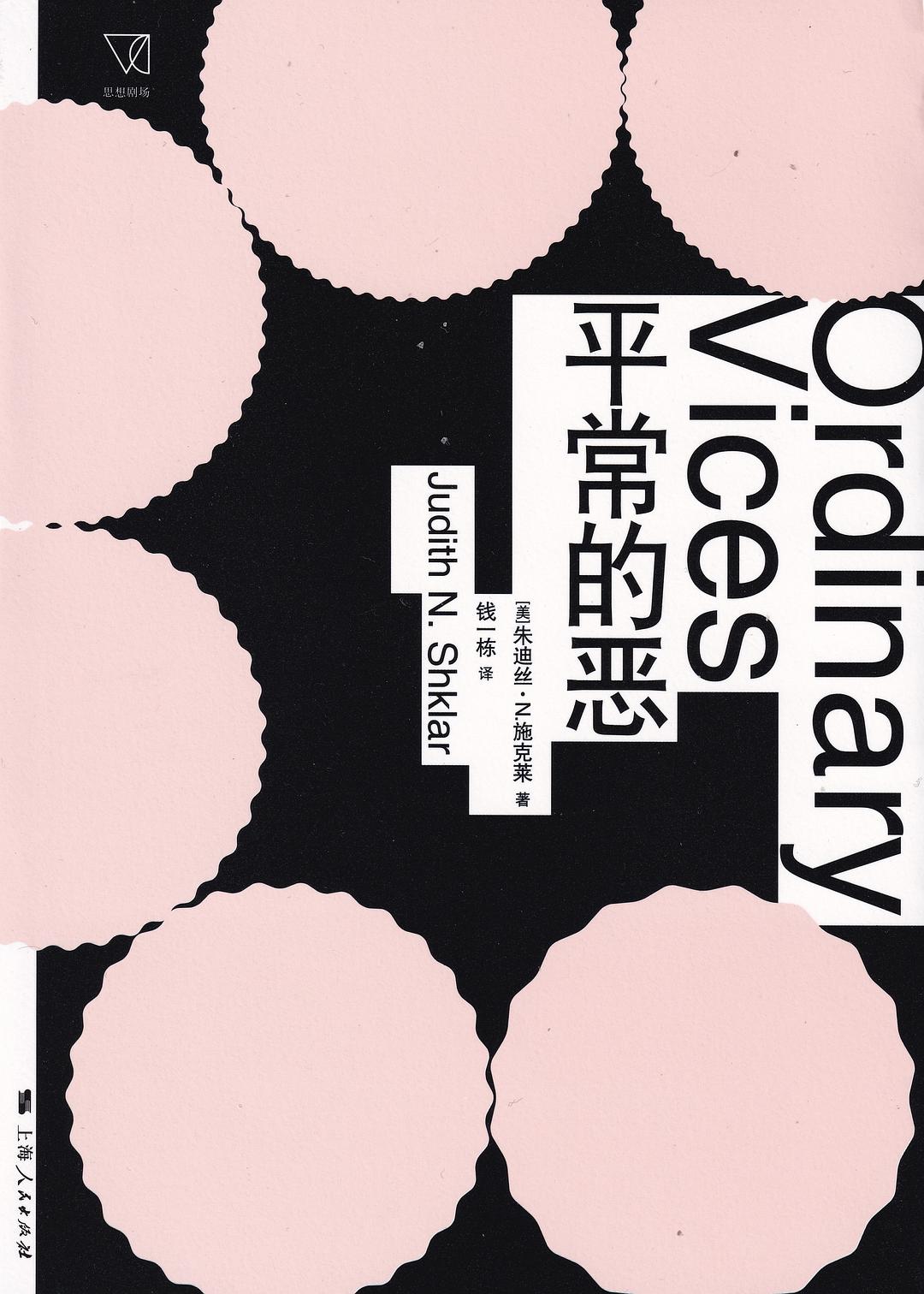
施克萊著《平常的惡》
作者對施克萊、權宜之計的處理還有別的一些問題。限于篇幅,這里只談我熟悉的施克萊。拋開細碎的文本解讀瑕疵,作者最大的問題在于,基本只根據《恐懼的自由主義》這篇文章來解讀施克萊,出現在他筆下的因此是一個最俗套的施克萊形象:有著慘痛政治記憶的流亡者、反烏托邦、懷疑主義、不抱幻想、視殘忍為首惡、恐懼的自由主義……這些閃亮的思想碎片拼貼出了一個典型的冷戰自由主義者,施克萊的一切思考似乎都圍繞著如何避免政治權力帶來的恐懼展開。但只要稍微翻下施克萊的其他作品,特別是《烏托邦之后》和《不正義的多重面孔》,我們便會發現施克萊的形象要復雜得多。
一個可能的回應是,作者不關心施克萊本人,只關心一種有待檢討的理論選項。談恐懼的自由主義是因為它可以被塞進這個選項,而非它是施克萊提出來的。但這會導致作者錯失他本應了解的理論資源。例如,蓋塔基于和作者相似的理論關切,將施克萊解釋為一個激進主義者(Giunia Gatta, Rethink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 Century: The Skeptical Radicalism of Judith Shklar, Routledge Press, 2018)。共識的欺騙性,政治的派系性、爭勝性,都被她妥帖地安置進了施克萊的自由主義之中。這表明,我們能從施克萊那里挖掘出更強的自由現實主義版本。
3. 威廉斯
此書最后一個對手是威廉斯。作者不走尋常路,認為威廉斯的理論并非發展自由現實主義的最佳起點。原因在于,“威廉斯的理論中有若干方面不夠現實主義”。其中最關鍵的是威廉斯對政治和成功支配的區分:“在威廉斯看來……任何單純通過使用權力維持的強制關系都是不正當的,因此是非政治的。政治是正當的強制關系……在許多方面,成功的支配都是政治的對立面……”而在作者看來,任何政治秩序,哪怕是正當政治秩序,都少不了成功的支配。因此,“這一區分最好不要被理解為‘政治不同于成功的支配’,而要被理解為‘政治不能僅僅是成功的支配’”(107頁)。
這些話說得不清不楚,能挑出不少毛病,但我們不難理解作者想表達什么意思。他無非想說,威廉斯認為政治和支配是互斥關系,有支配則無政治,而他自己主張兩者是包含關系,有支配不一定有政治,有政治則必有支配。他和威廉斯都能接受的一點是,政治包含強制。按作者的論述,在威廉斯那里,強制分正當和不正當兩種,政治屬于前者,支配是后者。
作者對威廉斯的這一解讀有文本證據嗎?檢索《太初有為》全書,威廉斯談及政治與支配之關系的只有兩處,使用“支配”(名詞或動詞)的總計有六處(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pp. 5, 7, 27, 63, 71, 142,威廉斯還在126、138頁用了“dominant”一詞,但只是在日常意義上使用,談的話題也和此處的討論無關)。用名詞的幾處表述兩兩重復,合并同類項后總計只有四處。仔細閱讀這四處表述可以發現,在威廉斯筆下,支配確實以非常負面的形象出現,可以支持——但無法坐實——互斥解讀。無法坐實的原因在于,威廉斯的表述似乎也允許我們將支配解讀為和強制類似的單純事實,而非添加了評價性判斷的事實,亦即不正當的強制。
威廉斯的政治概念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對政治和支配的區分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亞氏區分了政治關系和主奴關系:“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轄的則為奴隸。”(《政治學》,1225b)考慮到主人(dominus)和支配(domination)之間的詞源關系,支配和政治確實可以被概念化為兩種不同的權力形式。威廉斯筆下的政治概念似乎遵從了這一邏輯。他不斷通過與主奴關系的對比來澄清政治的含義,后者特指解決秩序、安全等首要政治問題的可接受的方案。因此威廉斯所謂的政治,并非泛指日常語言中一切可被稱為政治的活動,而是特指滿足基本正當性要求的政治。(但威廉斯明確說自己并不試圖定義政治的概念。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p. 12. 這意味著他不會去糾纏“到底什么是政治”,而只是根據自己的理論需要對政治作了特定的概念化處理。但包括斯利特在內的許多現實主義者都被他帶入了無聊的語詞之爭。)這種政治概念也可以支持——但依舊無法坐實——對政治和支配的互斥解讀。
我們姑且接受互斥解讀,繼續檢討作者的論證。根據互斥解讀,支配是不正當的強制形式(作者也接受這一支配概念,120頁)。斯利特不同于威廉斯之處在于,他認為政治必然包含支配。這個觀點似乎平平無奇,誰都知道古往今來的政治包含無數不正當的強制。威廉斯也不會否認這一點,他只是把支配和上段所說的特定意義上的政治概念,而非一切政治概念對立起來。斯利特在批評威廉斯時用的又是何種政治概念呢?這里存在一個兩難:如果用的是寬泛意義上的政治概念,他和威廉斯之間便不存在實質分歧;如果用的是威廉斯那種蘊含正當性的政治概念,則主張政治必然包含支配似乎會陷入自相矛盾。是把正當政治解釋為程度性概念,還是有別的概念化策略?無論如何,作者必須給出一個和威廉斯的政治概念既足夠相似(否則無法產生實際分歧)又非完全相同(否則政治在概念上無法容納支配)的政治概念。這不是就概念論概念。作者實際要論證的是,基于對政治現實主義各項關鍵設定的綜合考量,能容納支配的政治概念比威廉斯的政治概念更可取。
對于這類深層問題,斯利特一如既往缺乏敏感,我們只能根據相關表述推測其觀點。斯利特寫道:“任何政治統治,哪怕那種統治已經被恰當地正當化,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成功的支配……”(107頁)據此,斯利特確實認為,即便取正當政治概念,支配也不可避免。為什么呢?答案藏在120頁的幾句話里:
在對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問題存在根本性分歧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預見,任何政治聯合體中都會有一些……拒絕承認其正當性的人。……盡管從異議者的視角來看,政治秩序和這些人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不正當的強制關系……但這是一種政治關系。……某些人全盤拒絕或部分拒絕(所在政治體的)政治框架,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國家就是不正當的,也不意味著國家在面對這些人時不正當。真相是,如果其提供正當性敘事被相當部分(substantial proportion)公民接受了,這一框架就是對政治問題的正當回答。
為了理清作者這段乍看大有深意的話,我們先引入一個區分:認為正當和真的正當。我認為這是個陶瓷杯,摸了才發現是塑料的;異議者認為身處其中的政治秩序不正當,但根據最可靠的正當性標準(這里不需要明確是哪種標準,只要不同于“隨便哪個受治者認為不正當,它便真的不正當”即可),它是正當的。這里的關鍵是,正當性話語談論的是政治秩序的品質,而人對這一品質的判斷可能是錯的。從引文中作了強調標記的兩句話來看,作者應該也接受這一區分。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又根據何種標準來判斷正當性呢?答案藏在這句話里:“如果其提供正當性敘事被相當部分公民接受了,這一框架就是對政治問題的正當回答。”也就是說,雖然不是隨便哪個人認為正當,政治框架便正當,但如果相當部分公民這樣認為,那政治框架就真的具有正當性。據此,所謂正當性,就是政治框架獲得相當部分公民接受的能力。這種正當性觀念雖然保留了“認為正當”和“真的正當”之間的內在聯系,但它不同于個人主觀主義的正當性觀念,不會把兩者簡單等同起來。
這里主要有兩個問題。首先,這種正當性觀念也許適用于社會科學,但在哲學層面毫無說服力(參見[美]A. 約翰·西蒙斯:《證成性與正當性》,毛興貴、朱佳峰譯,朱佳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50頁)。其次,既然作者承認異議者眼中的支配不是真正的支配,又何談“政治必然包含支配”?剝離各種混亂的理論闡釋后,我們發現作者只表達了這樣一個平平無奇的經驗觀察:政治體的正當性敘事通常訴諸主流價值觀,但任何社會中都會有一些受治者不接受主流價值觀,不承認身處其中的政治框架的正當性,認為自己被支配了。如果這就是作者想教給我們的東西,那么不僅威廉斯不需要回爐重修,任何有常識的人都不需要聽他專門講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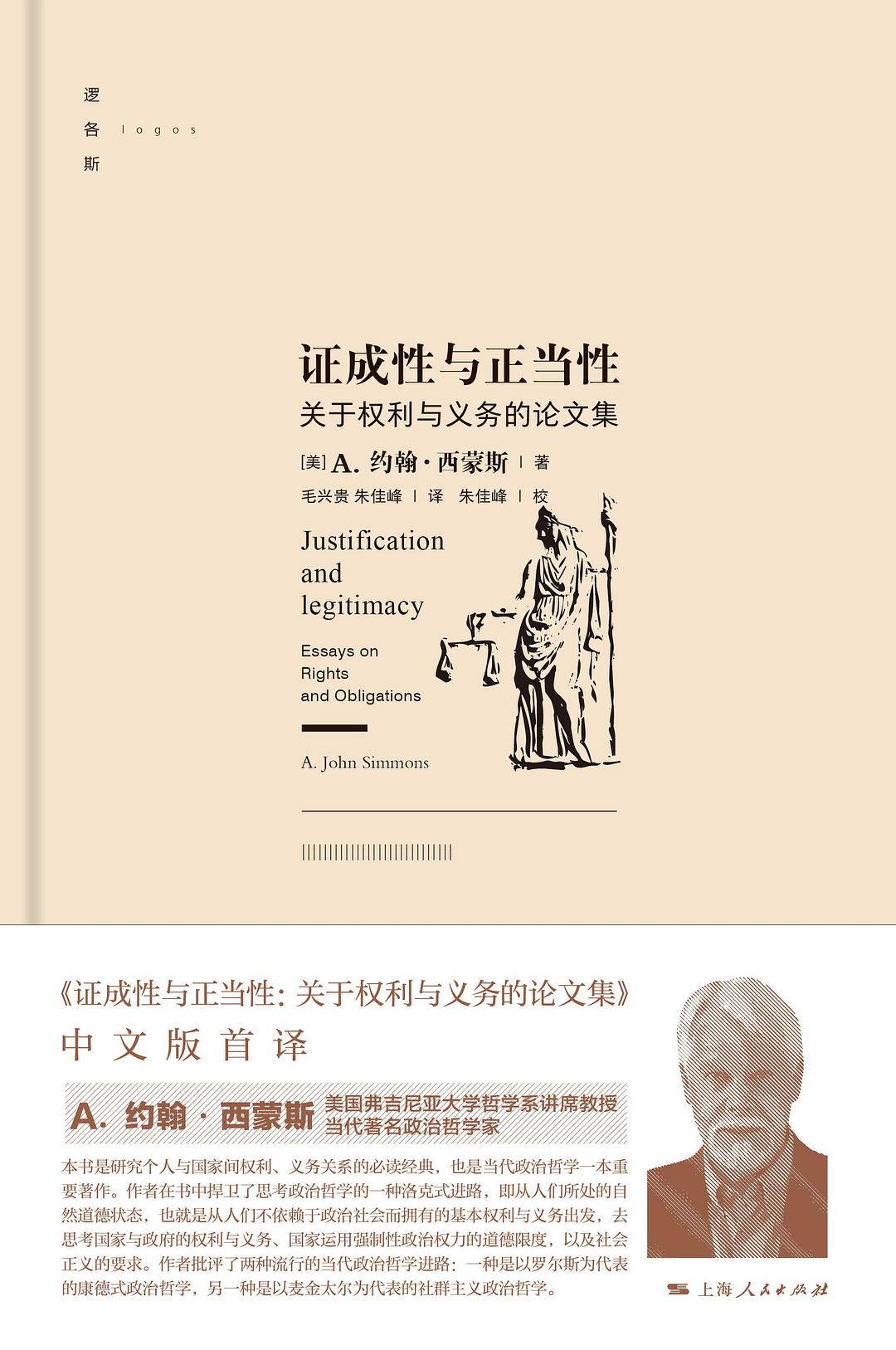
約翰·西蒙斯著《證成性與正當性》
(三)自由現實主義
批評完威廉斯,作者在最后兩章正面闡述其自由現實主義。這像是政治自由主義的激進版本。具體言之,政治自由主義者不僅主張整全性觀念之間存在合理分歧,而且一定程度上接受不對稱性批評,承認在自由社會中會出現多個而非只有一個合乎情理的政治觀念,公民們會就何種政治觀念最合理發生分歧。只是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這個問題并不嚴重:根據自由平等、公平合作等基礎理念,以及一些程序設定,公民們可以合理地接受自己并不認同的政治觀念。斯利特沒有糾纏政治自由主義者的這一自我辯護,而是去挑戰其深層設定。他指出,羅爾斯從一開始便將爭論限制在了自由主義家族內部。他的激進性則表現在拒絕這種限定,將合理分歧的范圍繼續擴大,認為自由主義者(準確講是會接受自由主義的人,它的外延比自由主義者大,Political Liberalism, p. xxxvii)和反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分歧(是的,作者用的是“分歧”而非“沖突”)也合乎情理(126頁;這里潛藏著一個問題:作者對沖突根源的分析顯然只適用于現代社會,但他一直強調沖突圖景是永恒普遍的)。
如何擴大合理分歧的范圍呢?作者的論證策略藏在這句話里:“盡管羅爾斯試圖將關于正義的合理分歧的范圍限縮在那些持有合理觀念——亦即符合相互性(reciprocity)的觀念——的人之間,但沒啥好理由能解釋為何那些(判斷的)負擔不能就自由主義者與非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沖突的起源和性質作出同樣有說服力的說明。”(126頁)簡言之,作者認為應該擱置相互性標準,僅根據判斷的負擔來解釋分歧的合情理性,使之去道德化、高度認識論化,最終使得自由主義與非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也可以被解釋為合理分歧。這一推理的成敗取決于作者能否在相互性、合情理性以及自由主義這三個概念之間建立起他想要的關系。德雷本認為,羅爾斯所謂的合理,就是指贊同自由主義政治觀念(Burton Dreben, “On Rawls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in Samuel Freem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26)。作者沒有德雷本這么直接。雖然講得不清不楚,但他顯然是想將相互性與自由主義聯系起來,然后通過切斷相互性與合情理性之間的聯系,使贊成非自由主義立場也變得合理。自由主義于是成了“一種植根于可爭議且有爭議的規范性價值的派系性政治立場”(128頁)。這些論證推進得太快且太亂了,不僅對羅爾斯的解讀并不準確,對羅爾斯的批評更是充滿奇思妙想。但作者保持了戰略定力,沒去理會(沒注意到?)各種可能的質疑,徑直走向了自己想要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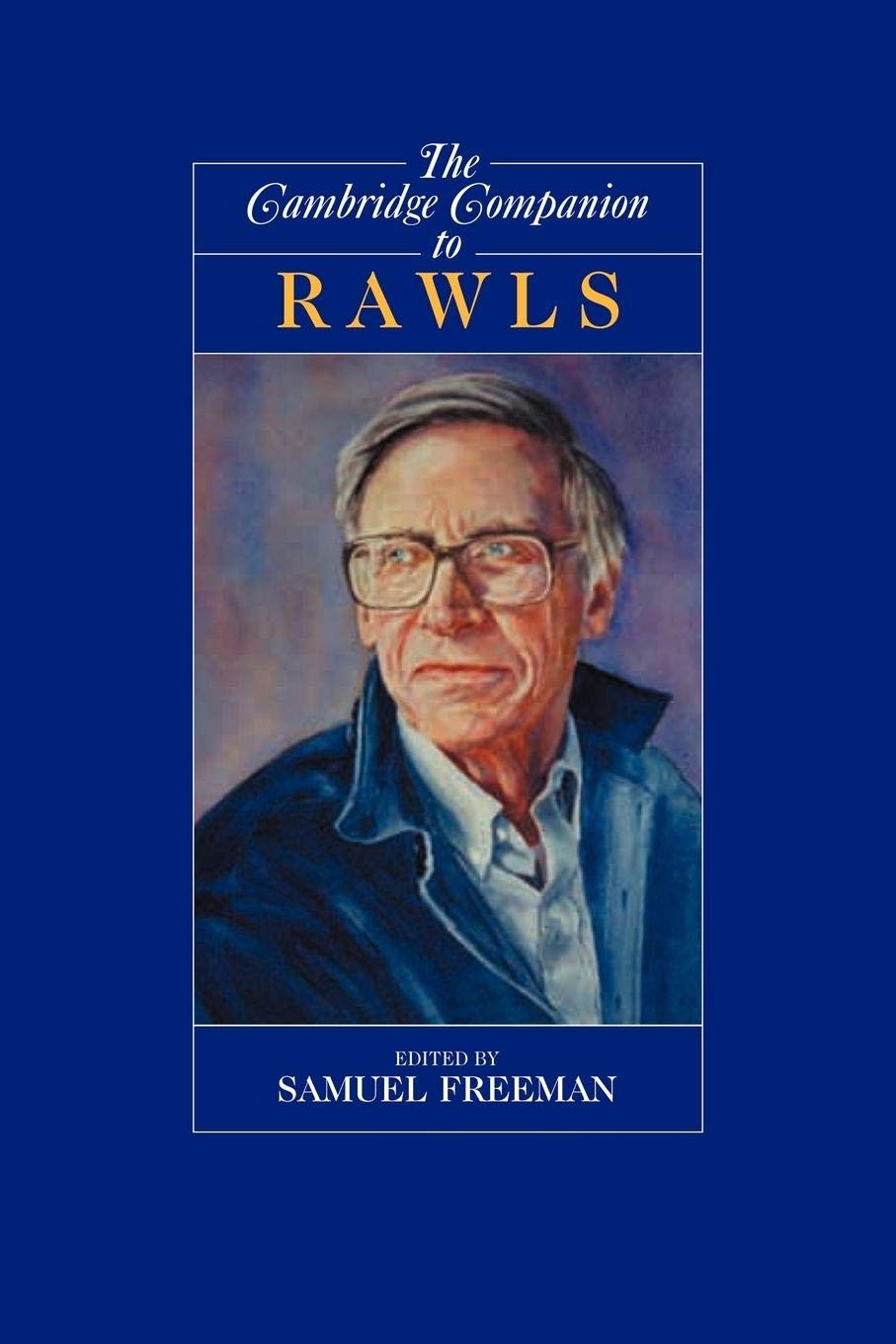
《劍橋羅爾斯指南》
緊接著,作者追隨卡爾·施密特,指控自由主義者試圖去政治化,不承認自己的派系性,表面中立,實則賦予自己特權地位,按自己的立場設定政治辯論的合理范圍。結果是在自由主義邏輯內部自說自話,無法和敵對觀點有效對話(133-134頁)。批評完后,作者給出了自己的修正方案。他參照尚塔爾·墨菲的爭勝主義理論,主張必須認識到自由主義國家中存在對手(即主張不同版本的自由主義政治框架的人)和敵人(即反對自由主義政治框架的人),意識到自由主義的派系性,并積極為自由主義而戰。同時他強調,對于那些反對自由主義的人,自由主義國家必須以符合自由主義精神的方式進行統治。在此,他援引了斯蒂芬·馬塞多的“溫和霸權”概念,要求自由主義者在誠實承認強制不可避免的前提下,盡可能踐行自己的道德承諾。
以上便是自由現實主義的基本內容。斯利特大概認為它既指出了政治自由主義的缺陷(忽視反自由主義立場的合情理性),又給出了修復方案(承認敵人存在,將自由主義作為戰斗信條,以溫和霸權進行統治)。但在我看來,這套理論的問題遠比政治自由主義嚴重。它會陷入心理和認識論層面的雙重困境:既然作者認為自由主義者和反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合乎情理,自由主義不見得比其他政治主張更合理,自由主義者又如何能夠、為何還要全心全意信奉自由主義立場,愿意為此而戰?從自由主義轉變為一種不知怎么說、怎么做才好的懷疑論立場似乎還更合理些。
作者沒把心理困境當回事。他基于對政治的競爭性理解,要求自由主義者堅定信念、牢記使命、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就好像人的心理可以按理論家的需要隨意塑造,既承認自由主義是“一種植根于可爭議且有爭議的規范性價值的派系性政治立場”,又能像容不得異端的衛道士那樣去捍衛自由主義。對于認識論困境,他算是有所回應。他認為,我們的認識論立場深深植根于整全性道德理論,“因此從政治上講,試圖以支持特定認識論立場的哲學論證來為自由主義政治奠基,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自由現實主義……將認識論分歧……當成政治需要去處理的不一致的其中一方面”(130頁)。細究起來,這里又有層層疊疊的問題。但鑒于作者只寫了一段話,似乎就想給個說法草草了事,本文也不多糾纏了。只提一點:這里的認識論困境不涉及復雜而有爭議的認識論立場。引發困境的就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悖論式要求:要求人堅定地相信一個自己認為可能不合理的信念。
以上種種問題也影響了作者對正當性觀念的處理。作者既不認為自由主義價值觀是社會共識,也不追求更稀薄的共識。相反,他主張自由主義國家的正當性就是要訴諸自由主義價值觀來證成。基于作者給出的合理分歧圖景,這種證成只會淪為自由主義者的自說自話。作者不否認這一點。他大方地接受了與這種自說自話證成觀相配套的相對主義正當性觀念。具體言之,作者承認,正當性不能建立在純粹的力量優勢上,而必須訴諸理由。但他不過多限制理由的類型,只要求這些理由是相當一部分公民所接受的。他寫道:“證明和維持正當性的關鍵在于,至少在最重要的社會成員、社會群體中,它們的統治可以訴諸共享的價值、目的和目標得到證成。”(145頁)據此,在自由主義國家,正當性話語就要訴諸自由主義價值觀。這種正當性是相對主義的,亦即只是相對于接受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人而言的。在其他人眼中,自由主義政治框架不具有正當性,國家只是一個支配者,而非正當統治者——作者承認這種看法合乎情理(147頁)。
這一正當性觀念會引出許多問題。首先是和作者批評威廉斯時表達的觀點不一致。他當時說:“某些人全盤拒絕或部分拒絕(所在政治體的)政治框架,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國家就是不正當的,也不意味著國家在面對這些人時不正當。”而此處作者的相對主義立場只能被解讀為“國家在面對這些人時就是不正當的”。其次,基于前文提到的心理和認識論困境,在作者設想的合理多元社會中,許多自由主義者可能會轉化為懷疑論者。因此這種正當性證成高度不穩定,容易喪失基本盤。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既然激進的政治分歧合乎情理,為何非得選擇自由主義的,而非別的正當性觀念,或干脆不談正當性呢?作者承認自由主義國家的正當性不會被反自由主義者接受,但恰恰是這些人最強烈地要求自由主義國家證明其正當性,正當性話語的基本功能就是向反對者證成國家施加強制的權力。如此一來,作者談正當性還有什么意義呢?即便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種正當性話語也沒有太大意義。畢竟作者也承認正當性是要訴諸理由的,而他推薦的那類理由會被很簡單的反思活動摧毀。事實上,基于作者的激進分歧圖景,堅持自由主義還不如隔幾年來一次政體形式抽簽更合理。
無論是批評威廉斯的正當性觀念,還是陳述自己的正當性觀念,作者的種種糟糕表現大多源于同一個毛病:他的頭腦無法全程緊繃,時不時會混淆事實權威和正當權威,分不清對正當性信念的描述和正當性證成。——若是直接問起來,那誰都知道這些區分,但抽象地知道并不意味著能在具體材料中準確辨明兩者,或能對此一直保持敏感。斯利特也許會說,自己只是拒斥描述性與規范性的簡單兩分。但我并未發現他在這方面有任何嚴肅的論證,只看到了大量毫無深度的混淆。
(四)總結
總體而言,斯利特此書論證潦草,且缺乏原創性。前面的內容都可證明其潦草,這里簡單談下原創性問題。此書最核心的觀點都來自沃爾德倫。所謂沖突圖景,基本是沃爾德倫的“政治的環境”的翻版;對沖突根源的解釋,也幾乎照搬了沃爾德倫對羅爾斯的不對稱性批評。至于自由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則是借墨菲和馬塞多的概念搭建起來的。作者真正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似乎只剩下對他人作品的曲解誤讀了。
此外我挺想說一句:雖然所有現實主義者都把羅爾斯當成最大的靶子,但羅爾斯在許多方面都挺像現實主義者。既然作者認為威廉斯的理論并非發展自由現實主義的最佳起點,那么老老實實接著沃爾德倫對羅爾斯的批評做下去也不失為一個合理的選擇。此書幾乎就在這樣做了,但由于作者把太多精力放在了東拼西湊、強作新論上,這一論證主線被淹沒在了枝枝蔓蔓中,長得歪歪扭扭纖細柔弱。
四、回到威廉斯
戈伊斯和斯利特一老一新,一激進一溫和,既是兩代現實主義學人的代表,也是兩路現實主義思想的主要倡導者。再加上威廉斯和恩佐·羅西,本文勉強算是勾勒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大致模樣。總體來看,直到現在,現實主義依然是個雜亂的理論家族,且除了威廉斯,找不出第二位頂尖理論家。而威廉斯的現實主義確實是“威廉斯的”現實主義,彰顯出濃郁的個人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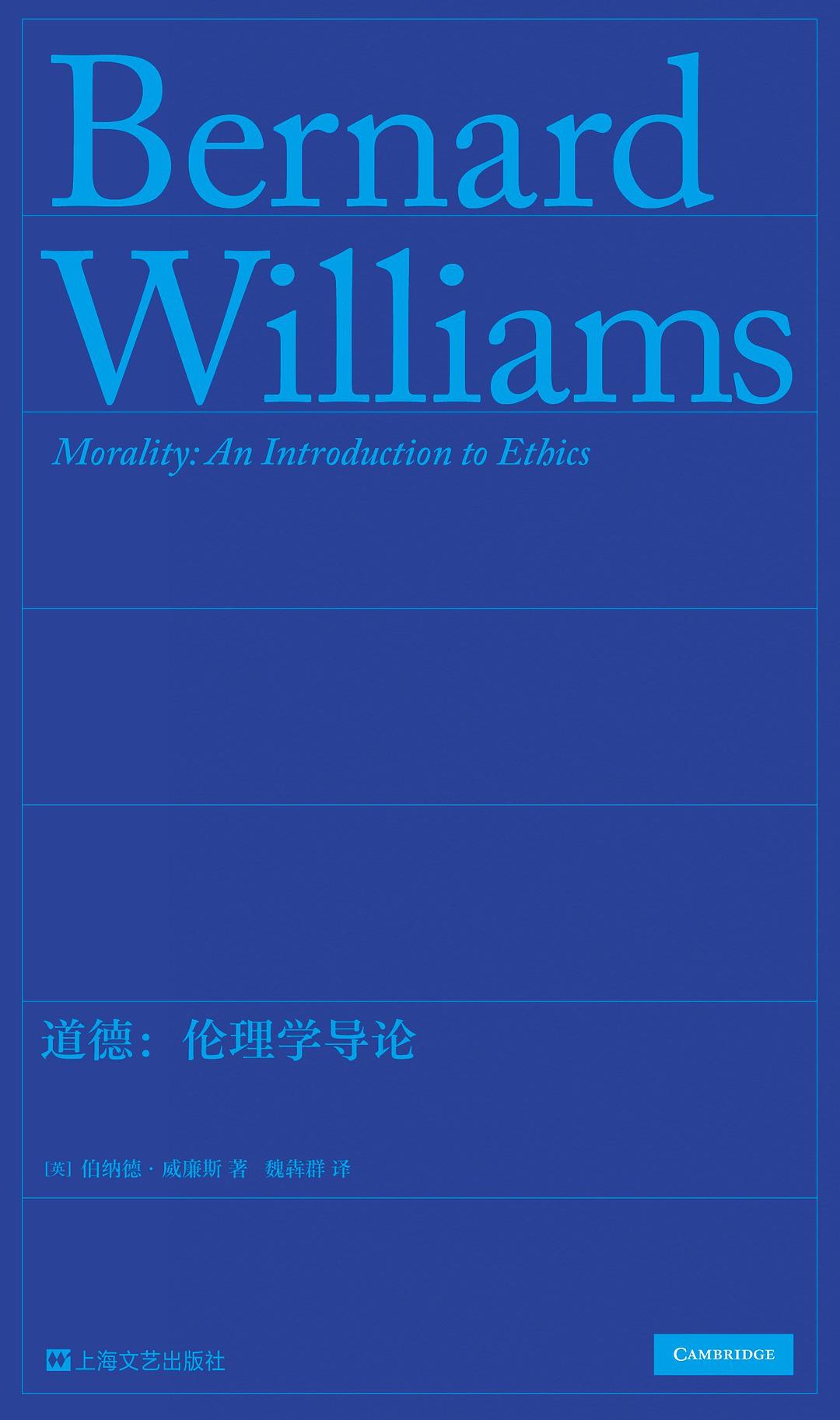
伯納德·威廉斯著《道德:倫理學導論》
在其第一本專著《道德:倫理學導論》的開篇,威廉斯留下了一句名言:“當代的道德哲學找到了一種原創的方式來繼續令人感到無聊,即它根本不討論任何道德問題。”([英]伯納德·威廉斯:《道德:倫理學導論》,魏犇群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第x頁)他提倡政治現實主義,也是因為在他看來當代政治哲學不怎么討論真正的政治問題。無論在倫理學還是政治哲學研究中,威廉斯都拒斥自欺式的體系化理論,強迫理論去和真實的經驗對話,并主張哲學離不開歷史。這種獨特的路數,使威廉斯成了一個思想扳道工:也許他的每個重要觀點都是錯的,但為了證明他的錯誤,我們將跟隨他走上很長一段路,見到原本發現不了的風景。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