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游蕩在美國:真實(shí)唐人街,定格在昨日|鏡相

宰也街(攝影/丁海笑; 海報(bào)設(shè)計(jì)/白浪)
作者 | 丁海笑
編輯 | 吳筱慧
編者按:
惠特曼、菲茨杰拉德、伍迪·艾倫……一代又一代藝術(shù)家都曾為紐約這座炫目的城市心醉神迷。加繆在1947年還這樣寫道,“這么多個(gè)月過去了,我對(duì)紐約依然一無所知,我是置身在此地的瘋子中間,還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中間……”
從曼哈頓唐人街到時(shí)代廣場,從百老匯到布魯克林大橋,本文作者丁海笑以背包客視角打量著紐約的過去與現(xiàn)在,或置身于嘈雜的地鐵,或漫步于令人狼狽的雨中,不斷審視一張張流動(dòng)的面孔,同時(shí)試圖記錄下21世紀(jì)初的紐約圖卷。
當(dāng)通過流動(dòng)的透鏡看紐約,我們能夠看到什么?海笑說,他在這里找尋到了安東尼·波登筆下那個(gè)流動(dòng)、熱烈、不羈的紐約。
(澎湃新聞·鏡相工作室首發(fā)獨(dú)家非虛構(gòu)作品,如需轉(zhuǎn)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tái)聯(lián)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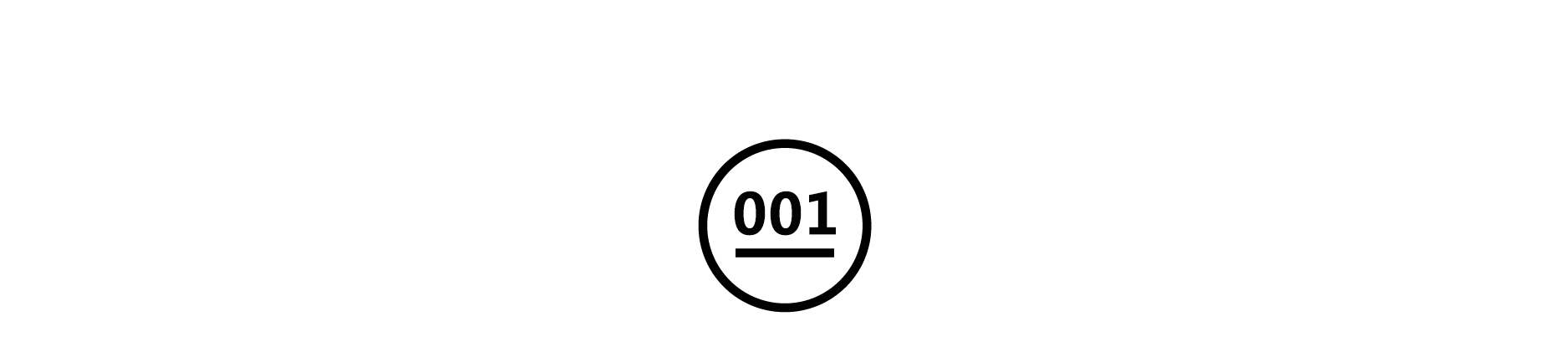
移民之殤
早在移民到來以前,曼哈頓的居民是島上的美洲原住民。島上過去遍布著山丘與河流,原住民對(duì)他們的島嶼傾注了很多名字,其中的一個(gè)就叫做“山丘之島”。1626年5月24日,荷蘭人從美洲原住民的手中買下了曼哈頓,后來的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這是一筆欺詐的交易,因?yàn)樵谠∶窨磥恚瑳]有人能夠買走祖先之地。而持有另一種立場的學(xué)者則把它歸咎于印第安人缺乏契約精神。隨著城市人口增長,曼哈頓島的山地與河流逐漸被填平。
曼哈頓擁有不同的移民社區(qū),各族群像拼圖一樣地分布著,宛如樹木的切面。下東區(qū)的唐人街(華埠)、小意大利、小德國是紐約最老的移民社區(qū)之一,也曾是猶太人的生活中心,數(shù)座猶太教堂就夾在中餐館和雜貨鋪之間。
離開紐約的前一天,我參加了菲爾的“下東區(qū)移民”City Walk。下東區(qū)是菲爾妻子的外祖父母生活過的地方,他們是波蘭裔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來到紐約,當(dāng)時(shí)的波蘭尚在俄羅斯帝國的統(tǒng)治之下。幾乎在一夜之間,紐約的櫻花全開了,分散在各個(gè)公園與街道,映襯著新古典主義的建筑,讓紐約忽然充滿了生氣。
City Walk從Rogers Partners大街的一座Loft公寓開始,這里離蘇豪區(qū)不遠(yuǎn),過去也是曼哈頓的紡織工廠,所有房間皆有著明亮的大櫥窗,一樓用以展示,樓上是車間和倉庫,曼哈頓的制造業(yè)逐漸外遷后,紡織工廠紛紛搬到了新澤西等地,廉價(jià)的廠房被藝術(shù)家租下來,改成藝?yán)群凸ぷ魇摇八囆g(shù)家喜歡落地窗”,也誕生了Loft這一住宅概念。隨著房租的持續(xù)上漲,這些Loft后來又變成了咖啡館、精品公寓和商業(yè)辦公室。
下東區(qū)唐人街活像一塊香港或者南洋的飛地,臉孔更多元化,卻又更雜亂無序。時(shí)光仿佛在此停滯了,這里的華人活在過去,像是一塊塊活化石,不再富有朝氣。街上所呈現(xiàn)的是好萊塢電影里的東方形象——一對(duì)阿公阿婆站在大街上用福建話唇槍舌劍,他們可能來自某個(gè)貧窮的閩北小鎮(zhèn),我同時(shí)想到外婆的家庭,也是這樣吵個(gè)不休。
菲爾站在宰也街的中國戲院前面,向我們繪聲繪色地講述著斧頭幫的故事。宰也街被稱為“血角”,這里曾是紐約最血腥的角落,生存空間受到擠壓的兩撥華人幫派在這條街上相互仇殺。當(dāng)年的故事已經(jīng)成為半神話,失去了歷史的真實(shí)性,那些唐人街的傳奇人物只留下了一串奇怪的拼音。

宰也街
老菲爾對(duì)唐人街知之甚少,且明顯帶著成見,但他卻表現(xiàn)得自信十足,透著一股西方人的傲慢。他區(qū)別不出西邊的老廣東和東邊的新福州,更不知道在皇后區(qū)還有一座更大的華埠——法拉盛,那里聚居著“新大陸人”。1930年后,后起的移民逐漸從下東區(qū)轉(zhuǎn)移到皇后區(qū),如今法拉盛的華埠已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曼哈頓的華埠,被稱作新唐人街。
曼哈頓大橋穿過唐人街,路過時(shí)我想到年少時(shí)聽過的一首老歌——張洪量的《情定日落橋》,標(biāo)題中的“日落橋”正是眼前的這座。“游客們?nèi)加肯虿剪斂肆执髽颍鴽]有人來走曼哈頓大橋,這座吊橋通地鐵,走在上面體驗(yàn)并不好,附近也比較亂。”菲爾說道。


曼哈頓唐人街
美國號(hào)稱“種族熔爐”,這種族群的抗?fàn)幣c融合持續(xù)了上百年,時(shí)至今日也未能完成。無論是非洲人、愛爾蘭人、猶太人,還是東歐人、意大利人、中國人……因?yàn)椴煌睦碛蓙淼郊~約,過程中難免被驅(qū)逐、排擠,都有一段血淚史。美國一度頒布過排華法案,也同樣地打壓過愛爾蘭人,歷史總在重復(fù),這在菲爾看來是一種不斷修正錯(cuò)誤的過程。
曼哈頓唐人街的前身是一個(gè)被叫做“五點(diǎn)區(qū)”(Five Points)的貧民窟,電影《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講的就是這里的愛爾蘭移民故事。美國的愛爾蘭裔人數(shù)眾多,占到美國人口的約六分之一,愛爾蘭節(jié)日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s Day)這一天整個(gè)美國都會(huì)變成綠色的海洋。“如今,美國的愛爾蘭人比愛爾蘭的愛爾蘭人還多。”
關(guān)于愛爾蘭人遠(yuǎn)渡新大陸的原因眾多,菲爾向我們提供了其中的一種:愛爾蘭移民的歷史可追溯至歐洲移民拓殖時(shí)期 ,大規(guī)模移民潮則始于1840年左右。當(dāng)美洲的土豆作物傳入愛爾蘭島之后,帶來愛爾蘭人口的爆炸式增長,1801年,愛爾蘭被英國吞并,1845年,馬鈴薯青枯病席卷歐洲,在愛爾蘭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數(shù)百萬人餓死或背井離鄉(xiāng)。
“橫渡大西洋至少需要兩周時(shí)間,路上就會(huì)死很多人,這些去美國的船被稱為‘棺材船’,甲板下面幾乎都滿載貨物,為了賺錢,船主將船上塞滿了人,只提供給他們勉強(qiáng)維生的食物。”
“最初來到美國的愛爾蘭人大多沒怎么受過教育,除了農(nóng)業(yè)之外沒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且大多是天主教徒……”這些愛爾蘭人在美國飽受歧視,他們被冠以“野蠻”、“酗酒”、“罪犯”等標(biāo)簽而遭到排擠,只能做一些底層的體力工作。
小意大利與唐人街毗鄰,它在19世紀(jì)末形成規(guī)模。早期的移民主要來自意大利南部,比如西西里島和那不勒斯。“在19世紀(jì)初期,一群意大利的年輕人來美國,等他們攢到足夠的錢后,回到村莊接濟(jì)他們的家人,村莊的人們會(huì)稱呼他們?yōu)樘焓梗驗(yàn)闆]有他們的支持,村莊將無法維系下去。隨著年輕人長大、結(jié)婚,他們中的有些人決定留在紐約,于是我們奇跡般地有了‘小意大利’……”
“當(dāng)意大利統(tǒng)一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島爆發(fā)了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蕭條,在1880年至1924年期間出現(xiàn)意大利移民大潮……到了1924年,美國通過了《移民法令》,于是關(guān)閉了意大利、希臘和東歐移民的大門——我們定期就會(huì)這樣做一次……”

小意大利
小意大利與唐人街一帶曾存在一個(gè)龐大的猶太社區(qū),美國是猶太人第二多的國度,而絕大多數(shù)的猶太人都生活在紐約。猶太人的社區(qū)遍布紐約各處,許多大廈的基石上就刻著希伯來文,一些地方還能見到星條旗和以色列的六芒星旗同時(shí)飄揚(yáng)的場景。
前一個(gè)周末是猶太人的普珥節(jié)(Purim),我恰好路過布魯克林的一處猶太社區(qū),大街上燈火通明,猶太人盛裝打扮,如同參加化裝舞會(huì)。普珥節(jié)與猶太人反抗波斯帝國的屠猶計(jì)劃有關(guān),慶祝的方式是施舍與饋贈(zèng),因此許多小孩會(huì)扮成小丑來向過往的路人要錢。人們行色匆匆,步伐快得跟跑步似的,我仿佛來到耶路撒冷的某處街區(qū)。

猶太人的普珥節(jié)
一位德國姑娘對(duì)菲爾講解的猶太歷史尤為感興趣,而且她的英文出奇的好,只有她能全程跟得上菲爾,菲爾雖是一位志愿者,但也可以隨時(shí)轉(zhuǎn)換成一名布道者,不經(jīng)意間他已帶著我們?nèi)チ税柕吕锲娼知q太會(huì)堂、加尼那猶太教會(huì)堂和卡茨熟食店——電影《當(dāng)哈利遇到莎莉》的取景地,現(xiàn)在是紐約最網(wǎng)紅的餐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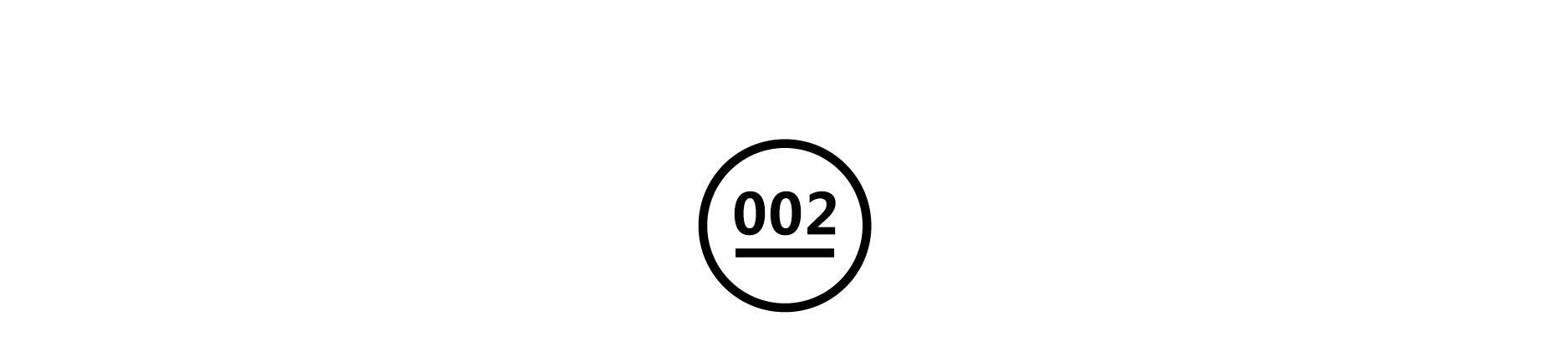
“你是哪里人?”
我們的最后一站是果園街的廉租公寓博物館(Tenement Museum),這里被認(rèn)為是美國移民故事的佐證,聚集了下東區(qū)最多的City walk旅行團(tuán)。果園街97號(hào)建于1863年,這里曾居住過超過20個(gè)國家的數(shù)以千計(jì)的移民,果園街103號(hào)建于1888年,這里也陸續(xù)住過上萬名移民,歷史學(xué)家通過公寓里的一些日常物件與文件碎片,構(gòu)建出百年間不同微小移民家庭的歷史,他們是德國人、非洲人、愛爾蘭人、俄國人、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華人……
紐約在一位旅居英國的朋友眼中是:“倫敦翻版,只是少了幾百年的歷史。”紐約的歷史不長但足夠豐富,這里的歷史學(xué)家著迷于微觀歷史的研究,大到一條街,小到一間餐館甚至一座路樁都能成為研究課題。
曼哈頓下東區(qū)更像是美國夢的一條樣板街,不同族群、宗教、語言、習(xí)俗的移民聚居于此,最終自發(fā)地形成一種共通的美國價(jià)值,聽上去就很世界大同。但這種價(jià)值正在面臨著自我瓦解,族群問題只是被街區(qū)化了,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平權(quán)運(yùn)動(dòng)在美國正走向極端。

下東區(qū)著名的猶太貝果店Russ & Daughters
近年來,身份政治已經(jīng)滲透到美國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主黨執(zhí)政的紐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yùn)動(dòng)愈演愈烈,非洲裔美國人一躍成為第一族群。就連“黑人”一詞也變成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提法,正在逐漸地被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
在大多數(shù)的美國博物館,非洲裔美國人專柜通常會(huì)占據(jù)其最主要的位置,就連最倡導(dǎo)“藝術(shù)自由”的大都會(huì)藝術(shù)博物館也處處充斥著政治立場。2020年,古根海姆博物館通過了一項(xiàng)糾正其體制內(nèi)種族主義傾向的計(jì)劃,到我去的時(shí)候,博物館已經(jīng)整改完畢,負(fù)責(zé)安保的雇員幾乎全部被替換成了黑人,持續(xù)半年的主題展是一個(gè)叫做“Going Dark”(走向黑暗)的展覽,除了一個(gè)面積不大的常駐展廳用以展出愛德華·馬奈、保羅·高更、馬列維奇、巴勃羅·畢加索等名家名作,其余大部分藝術(shù)展品均來自黑人藝術(shù)家。我在場館里能明顯地感受到逆向歧視,那是一種難以名狀的不公平感。

MoMA(紐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
黑人教堂雖然在名義上對(duì)不同族裔開放,但由于頻發(fā)的黑人教堂遇襲案,教會(huì)成員對(duì)一切非我族類都充滿警覺。我曾誤闖過一間芝加哥的黑人教堂,保安將我攔在了門外,他嚼著口香糖,擺出一副嫌棄的表情,朝我揚(yáng)了揚(yáng)頭,我會(huì)意地解釋了一番,但直到我參觀完道謝離開,他嘴里都沒有吐出寶貴的一字。芝加哥有幾家開在白人社區(qū)里的黑人酒吧,里面從雇員到顧客全是黑人,跟種族隔離時(shí)期的黑人酒吧不同,這里是將白人隔絕在外。
毋庸置疑,美國社會(huì)針對(duì)黑人的種族歧視依然存在,而對(duì)亞裔的仇恨也在逐年加劇。亞裔美國人被視作“永遠(yuǎn)的外來者”(Forever Aliens),“外來者”一詞在英文中本身就帶有歧視屬性,被定義在黑白種族關(guān)系之外。脫口秀演員Brian Kim是一位在紐約長大的韓裔美國人,他曾分享過每次當(dāng)他路過時(shí)代廣場的時(shí)候,總是會(huì)被人問道:“你是哪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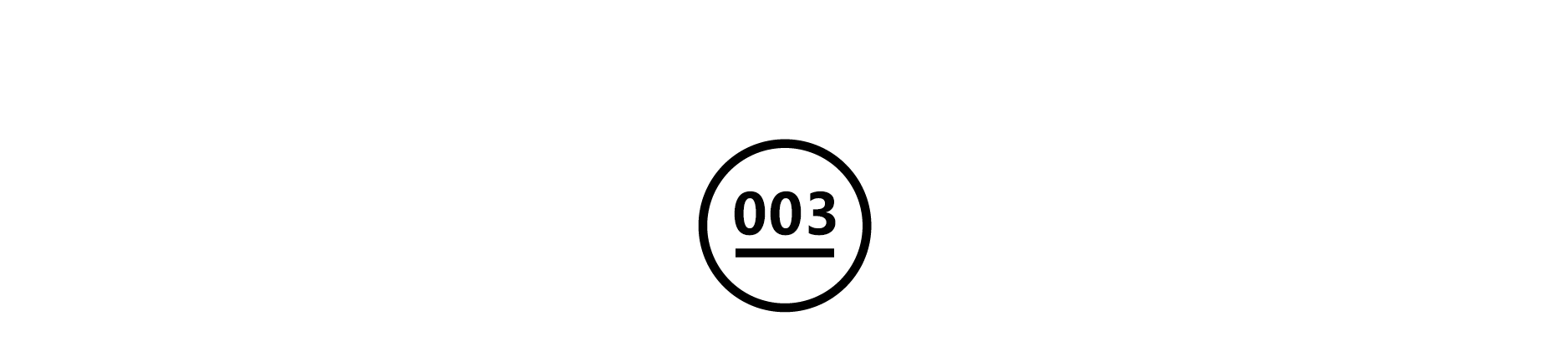
美國背包客
本世紀(jì)初的巔峰時(shí)期,全美共有136家國際旅舍(Hostelling International)——那也是菲爾們的“好老日”(Good old days),疫情加速了它的關(guān)店潮,現(xiàn)在僅存14家。菲爾們的志愿精神源自對(duì)全球背包客浪潮的緬懷,曾經(jīng)世界的各個(gè)角落,都少不了美國背包客的身影。不知道從什么時(shí)候開始,美國青年越來越少地踏出國門,甚至在北美旅行也極少碰到背包旅行的美國年輕人,唯一一次是在火車上,一位來自中西部的小伙子說他正在過間隔年,在一家醫(yī)院里做義工,忙得根本沒有時(shí)間旅行。
雖然有諸多原因?qū)е耑世代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熱衷于背包旅行,但經(jīng)濟(jì)壓力絕對(duì)是主要原因之一。飛漲的物價(jià)讓美國國內(nèi)旅行的成本與日俱增——在芝加哥車站樞紐的Hudson News零售店買一瓶500毫升可樂稅后要5美元(約合人民幣36元),紐約青旅的一張12人間床位平季的價(jià)格是每晚74美元(約合人民幣536元),旺季則不低于每晚100美元(約合人民幣725元),這還是在享受非營利組織免稅的基礎(chǔ)上。
疫情之后,即便是像紐約國際旅舍這樣一家異常火爆的青旅,仍然在勉強(qiáng)地經(jīng)營著,甚至剛從倒閉危機(jī)里緩過來。旅舍的住客有一半來自中南美洲,他們到紐約的感覺就像是過來朝圣,我碰到一群哥倫比亞的青少年,十七八歲的年齡,個(gè)頭都不太高,其中一位蓬蓬頭的哥倫比亞少年在談到紐約時(shí)情緒有些激動(dòng):“我不敢相信這里的人可以在夜晚出門,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國家也能像這樣……”雖然紐約的治安已經(jīng)飽受詬病,但對(duì)于一位在哥倫比亞長大的孩子來說,從未感覺到如此安全,他說自己所在的家鄉(xiāng)非常混亂,他甚至不敢在大白天一個(gè)人上街。
國際旅舍也有許多年過花甲的背包客,其中一位韓國老太已經(jīng)80多歲了,稱自己背包旅行了40年,去過兩百多個(gè)國家。她佝僂著身子,走起路來顫顫巍巍的,口齒也不太清晰,難以想象她是如何到達(dá)這里的。她對(duì)紐約的食物無比失望,跟我要了一些老干媽香菇油辣椒,吃完以后贊不絕口,一定要我告訴她在哪里才能買到。
在旅舍的歡迎派對(duì)上我認(rèn)識(shí)了一位印度博主,叫做斯芬克斯,和開羅的獅身人面像同名,他與法老之間唯一的關(guān)聯(lián)可能就是都剃了光頭。斯芬克斯給人的印象是超級(jí)熱情,且無比自信,他主動(dòng)加了每個(gè)人的聯(lián)系方式,然后建了一個(gè)群,邀請大家第二天從布魯克林大橋徒步去丹波,我其實(shí)已經(jīng)去過一趟大橋了,但沒有走到丹波,于是就跟著一塊去了。

丹波和布魯克林大橋
人都是斯芬克斯組織的,只招到了清一色的男性,斯芬克斯對(duì)自己的目的也不避諱,就是讓大家為他的Instagram新拍一組照。從旅舍出發(fā)之后,印度人便自動(dòng)進(jìn)入了指揮官的角色,不僅路線得聽他安排,就連大小便也得統(tǒng)一行動(dòng)——“上橋之前,我得保證所有人都上完了廁所。”
美國的公共廁所極少,游客找?guī)H為麻煩,你得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到餐飲店的最里面,期望那里沒有密碼鎖或者由柜臺(tái)遙控的開關(guān),也得同時(shí)提防沒有保安過來把你趕走。斯芬克斯有一種找?guī)男嵊X,他總能通過自己的同胞打聽到附近的廁所,再佯裝那里的顧客或者附近的鄰居,從服務(wù)員那里套到廁所的密碼。為了不打草驚蛇,我們被安排輪流進(jìn)入一家小店,上完出來后跟每個(gè)人擊掌慶祝,臉上掛著一副做壞事的表情。
斯芬克斯四十歲左右,在他身上有著部分上個(gè)時(shí)代背包客的氣質(zhì)。他一邊出差一邊旅行,去過不少地方,也來過兩次紐約,留下了他的光頭與世界各國地標(biāo)的合影,效果就像AI生成的一樣。他喜歡三不五時(shí)地提到中國,也習(xí)慣在氣勢上壓一壓我,譬如他會(huì)向所有人科普:“印度人口在去年已經(jīng)超越了中國。”他還強(qiáng)烈安利中國的一加手機(jī),并稱它的拍照功能無與倫比:“在印度,有一半人用中國手機(jī),另一半人用其他手機(jī)。”可惜在紐約,沒有人會(huì)關(guān)心龍象之爭。
我想在丹波看日落,斯芬克斯卻一直催促著我們趕路,我剛架好機(jī)位,他便從遠(yuǎn)處朝我揚(yáng)手,頭也同步地朝外昂,意思是快跟上,我只能示意讓他先走,他又朝我昂了昂頭,表示會(huì)意。
“你在哪?怎么回事?”第二天一大早,斯芬克斯就追著問我照片,睡眼惺忪的我火氣正大,說我正在出門,我不得不爬起來往外走,沒想到又在電梯撞見他,他抓著我索要照片,語氣像是我的老板。
日本的諒子也是我在歡迎派對(duì)上認(rèn)識(shí)的,旅舍的東亞面孔很少,她一進(jìn)來就找我說話。她在加州的一所大學(xué)里做交換生,研究的是國際關(guān)系,我們聊得不錯(cuò),感覺有挺多的共同話題。她在后來的Pub Tour中不辭而別,被熱情好勝的丹麥小伙拉森叫走了,走之前她留了我的聯(lián)系方式,推薦我一定要去聯(lián)合國總部看一看。
在紐約總是感到時(shí)間不夠用,我拼命地按著快門,想記錄下21世紀(jì)初紐約的圖卷,怕它會(huì)轉(zhuǎn)瞬即逝。我改簽了車票,決定在紐約多待幾日,繼續(xù)輾轉(zhuǎn)于不同的線路,往返在曼哈頓與布魯克林,有時(shí)也盡享歡樂,卻很難交到朋友,所幸在紐約根本不需要朋友,有太多可以忙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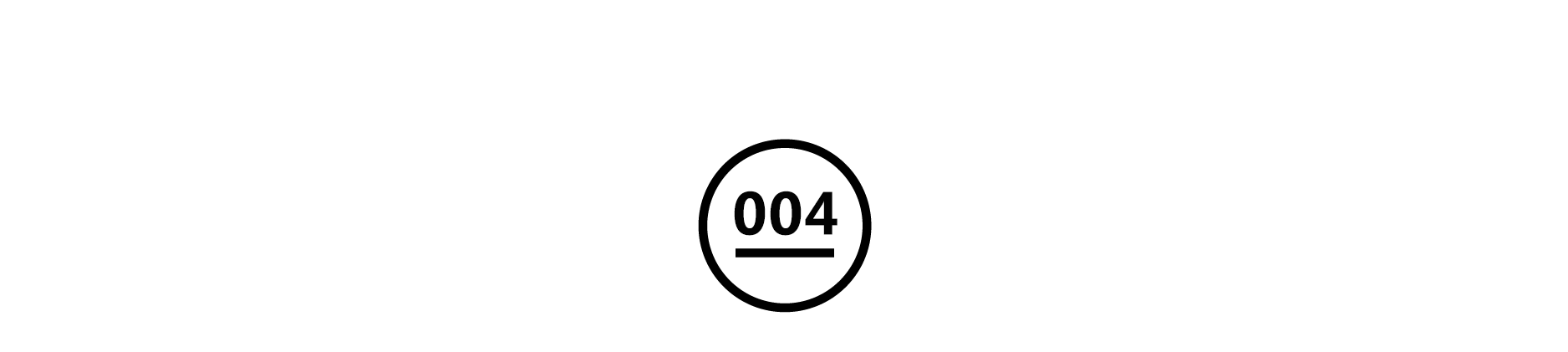
紐約的一個(gè)雨天
那天清晨從BASEMENT回到曼哈頓,通宵未眠,想接著再去“哈林區(qū)City Walk”,無奈在床上睡著了,瞇了有兩三個(gè)小時(shí),收到了諒子的信息:“其實(shí)我今晚要走了,如果我們能再見的話,我會(huì)很開心。我為那天的突然離開感到抱歉,如果你今天有空的話,給我聯(lián)系,我們在什么地方見見。”日本人總是很客氣。
諒子在中午有個(gè)佛教討論會(huì),我正好想去湊個(gè)熱鬧,結(jié)束后已是下午三點(diǎn),我提議去古根海姆博物館逛逛,今天是免費(fèi)開放夜,而諒子對(duì)看展有些興致索然,她說最后一天了,還沒嘗過紐約的精釀啤酒呢。
美國是精釀啤酒文化的一大發(fā)源地,僅在紐約就有300多個(gè)啤酒廠牌,我從西海岸一路喝到東海岸,品嘗過無數(shù)的精釀啤酒廠,逐一記錄下不同地方的小氣候、口感及精釀文化差異。從下午就開始喝酒,這個(gè)計(jì)劃聽上去很瘋狂,但當(dāng)我們到了布魯克林才發(fā)現(xiàn),縱然外面大雨滂沱,各個(gè)啤酒屋都已經(jīng)座無虛席了。
一路上雨下得很大,雨水沖刷著這座老舊的城市,讓我想起羅馬大雨中那只被沖掉的鞋子。紐約一半是雨天,一半是晴天,紐約的天氣帶火了伍迪艾倫的《紐約的一個(gè)雨天》,成為來紐約必看的城市漫游指南,因?yàn)榭倳?huì)碰上一兩次下雨嘛。雨越來越大,鞋子完全濕透了,我倆像是踩在水塘中跳舞。

紐約的下雨天
EBBS啤酒屋是我挑的,據(jù)說是布魯克林最火的精釀啤酒屋之一,啤酒屋的一面墻上掛著“布魯克林第一IPA”的張貼,沽酒客擠滿了整座空間,連過道上也站滿了人,氛圍很燃,音樂越大聲,人們彼此說話就越熱絡(luò),吧員也手忙腳亂的,我們要了IPA和皮爾森,找了個(gè)靠墻的角落碰杯。
啤酒是美式文化的代表之一,酒吧、啤酒與男人的畫面被反復(fù)地投影在電影銀幕上,這種黃金液體也隨著好萊塢文化的擴(kuò)張而走向全球。我到美國還是第一次嘗試在白天喝酒,但沒過多長時(shí)間,我就又破了記錄,從一大早就開始跟人干威士忌。
第二家啤酒屋我讓諒子來選,她挑了布魯克林啤酒廠——紐約精釀的鼻祖之一,歷史悠久。當(dāng)我們走出EBBS,雨逐漸變小了。“如果不喜歡紐約的天氣,只需要等一等,沒多久就會(huì)變天了。”我想起了老菲爾的話。布魯克林啤酒廠離東河不遠(yuǎn),河畔的風(fēng)很大,雨傘不斷地被吹歪,我們在幾個(gè)街區(qū)之間差點(diǎn)迷路。
布魯克林啤酒廠已成為紐約旅游通票的一處景點(diǎn),這里的精釀啤酒中規(guī)中矩,唯一有意思的是角落里有一臺(tái)可以玩任天堂游戲的街機(jī)。我們接著去了Other Half——同樣號(hào)稱“布魯克林最佳”,里面正在舉辦婚禮,把整個(gè)啤酒屋都包了下來,我們只好去下一家叫做Talea的酒館。
路過一家貝果店時(shí),我買了一個(gè)煙熏三文魚貝果,貝果被稱為紐約人的早餐,最初也是由猶太人傳入紐約的。一個(gè)櫥窗邊的白人男子對(duì)我們說了些亞裔歧視的用語,諒子在我們走出貝果店后才告訴我,我原本有些憤慨,但轉(zhuǎn)念一想,也許這就是美國旅途之始朋友所說的“扔掉濾鏡”吧。
布魯克林已逐漸淪為了中產(chǎn)社區(qū),隨著房租上漲,屬于布魯克林風(fēng)、亞文化的酒吧也在不斷外移,許多已經(jīng)從威廉斯堡搬到了布什維克——布魯克林與皇后區(qū)的交界處,那里多了些老布魯克林的氣息,少了通貨膨脹的網(wǎng)紅店、板著臉的服務(wù)員和一些裝腔作勢的文青。我們從威廉斯堡一路喝到了布什維克,體驗(yàn)不同“地層”的精釀工坊,幾乎覆蓋了整個(gè)紐約精釀史。
諒子的故鄉(xiāng)是北海道的札幌,札幌最有名的物產(chǎn)就是“札幌啤酒”(SAPPORO),許多外國人可能不知道札幌市,但幾乎都聽過“札幌啤酒”。 在札幌人人喝酒,諒子說她從來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感覺。十幾年前在亞美尼亞,我碰到過一個(gè)環(huán)球旅行的札幌人,她當(dāng)時(shí)在倫敦大學(xué)念歷史地理學(xué)博士,每到一處,就會(huì)喝掉當(dāng)?shù)厮衅放频钠【疲吹贸鏊钦娴膼酆染疲袼薜谋淅镅b滿了她買的酒,每天不喝一口就睡不著覺。
最后我們?nèi)チ瞬际簿S克附近的一家古董酒吧,是我在去BASEMENT的路上無意間發(fā)現(xiàn)的,這里的消費(fèi)便宜到不像是在紐約,只收現(xiàn)金,沒有小費(fèi)。酒吧仿佛是美劇《瑞克和莫蒂》的外星人狂歡派對(duì),全是穿著“奇裝異服”的皇后區(qū)怪人,有來自中世紀(jì)的巫師,有高更的大溪地少女,還有把自己裝扮成動(dòng)物的人。這里的舞曲更加自由無國界,是酒吧,也是跳蚤市場、占卜攤……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皇后區(qū)是美國本土族裔最多元的地區(qū),古董酒吧的賓客幾乎都是外來者,來自阿根廷、黎巴嫩或者某個(gè)加勒比海上的小島,有的人可能才剛蹲完移民監(jiān)(用來比喻等待獲得美國身份的過程)出來,我卻在這里找尋到了安東尼·波登筆下那個(gè)流動(dòng)、熱烈、不羈的紐約。我們是里面唯一的東亞面孔,他們見到我們也很高興,我們在一群沒有故鄉(xiāng)的人中間彼此取暖。
凌晨兩點(diǎn),我們踏上了地鐵L線,夜班車要統(tǒng)一繞到百老匯交匯車站,再從那里換乘A線回曼哈頓,剛好路過高街車站,諒子說沒去過布魯克林大橋,于是我們即興地決定跳下車,往大橋方向走去。路上要穿過一些黑布隆冬的隧道和公園,一個(gè)行人都沒有,路邊的櫻花卻在黑暗中開了,預(yù)示著紐約的春天已提前到來。
當(dāng)我第二次來到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眼前是曼哈頓的璀璨夜景,身后是簡的旋轉(zhuǎn)木馬,空無一人的置景讓人產(chǎn)生了不真實(shí)感,像墜入19世紀(jì)的巴黎。曼哈頓所有的大樓都在夜空中點(diǎn)亮了,諒子問我:“難道紐約人也像東京人那樣通宵工作嗎?”后來我問了菲爾,他比我更熟悉大樓的事情:“那些不是在寫字樓上班的人,因?yàn)榍鍧嵑途S修工作只能在晚上進(jìn)行,工人會(huì)把每層樓的燈都打開,走的時(shí)候無意或者故意留燈,這樣做一點(diǎn)都不環(huán)保。”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簡的旋轉(zhuǎn)木馬
“我從沒想過我會(huì)有機(jī)會(huì)來到美國。”諒子感嘆道。她出生在一個(gè)普通家庭,父母的工作一直不穩(wěn)定,從出生后便不停地搬家,從最西邊的九州到最東邊的北海道,搬過十幾次家。因?yàn)楣ぷ鲏毫Γ徸拥母赣H患上了抑郁癥,開始沉迷于一些旁門外道,整個(gè)家庭后來一直在靠母親支撐著。“我都不知道我的父親現(xiàn)在在哪……”諒子的語氣里透露著絕望的悲傷。
從上世紀(jì)90年代開始,日本經(jīng)濟(jì)經(jīng)歷了失落的三十年,疫情之后,日本經(jīng)濟(jì)的衰退加劇,跌出了全球第三的座次。日元的貶值使得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赴海外就業(yè),在加拿大旅行時(shí),我碰到了大量日籍的外勞,在當(dāng)?shù)刈鏊緳C(jī)、廚師甚至保潔工作,這是我過去十幾年旅行中極少碰到過的事情。
諒子在凌晨四點(diǎn)過打車去機(jī)場,飛往洛杉磯。我又在紐約晃蕩了幾日,坐跨夜的火車前往印第安納的布魯明頓,見了一對(duì)十年未見的老友,我們從早上就開始喝酒,在森林里燃起篝火,度過了幾個(gè)不眠之夜,仿佛昨日重現(xiàn)。原來最后只有我在流浪,他們從未散落天涯。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澎湃號(hào)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