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醫學與人生:生命、健康、疾苦與醫學職業的選擇
讓我們從100年前一場演講說起。1923年2月,北京大學張君勱教授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題為《人生觀》的演講,提出了科學與人生觀的復調敘事,強調科學并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他指出,如果我們僅僅追求科學技術,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科學為論理(邏輯)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于直覺;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是綜合的;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與自由意志相關聯;科學起于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則起于人格的單一性。
我們今天在討論醫學的時候也會發現,醫學就像張君勱教授講的,不光關乎科學技術,也關乎我們的人性或者說人生觀。醫學是人學,是人文牽引的科學,人性滋養的技術。醫學的價值關切是人生觀、價值觀的具體化,包涵生死觀、苦難觀、疾苦觀、健康觀、救療觀。我最近新出的《反彈琵琶:醫學的現代性批判》一書回答了關于醫學的哲學悖論,為什么今天我們的醫生做得越多,老百姓的抱怨也越多。這背后包含了醫學的一個隱喻,醫學是雙頭鷹、雙翅鳥,而沒有人文滋養的醫學科學是單翅鳥,沒有人性溫度的醫療技術是無花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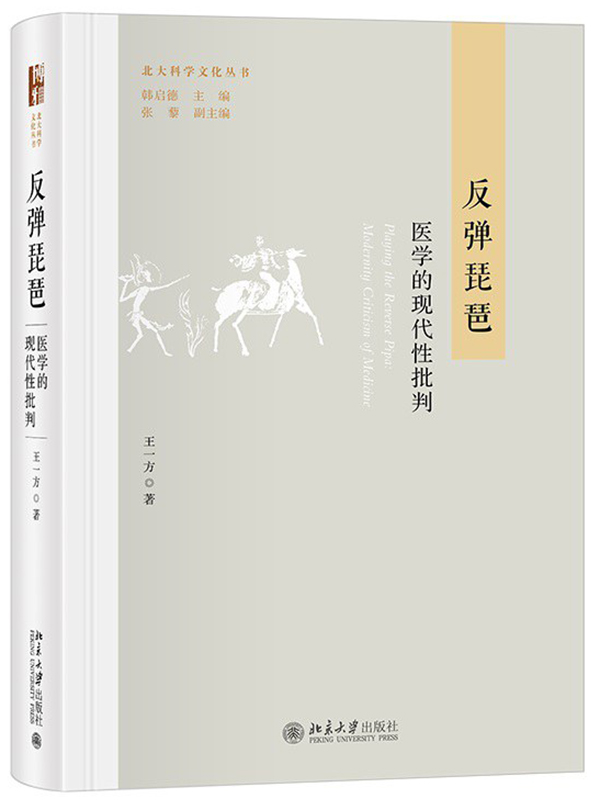
《反彈琵琶:醫學的現代性批判》書封
美國醫學倫理學者佩里格雷諾(Edmund D. Pellegrino)曾經有個經典的論述,醫學是科學中最人文,人文中最科學的學問。醫學關涉最基本的人類價值,即利他和純粹。醫學的一端是科學和技術,另一端是苦難中的人類需求。醫學決策聯系技術和道德命題,因此,醫學既要客觀,又要充滿同情。他的結論是,是否學醫取決于是否具有一種品質,那就是對于人類痛苦不可遏制的敏感。
在西方的STM(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科學、技術和醫學)分類體系中,醫學和科學技術是并列關系,而不是從屬關系。這是因為科學和技術追求的是有知、有理(客觀、實驗、實證、還原)、有用、有效、有利(效益最大化),而醫學有著更豐富的價值半徑,除了上述幾點之外,還要有德、有情、有根、有靈,其中包含了科學性、人文性、社會性的統一,追求的是生命價值的最大化。
100多年前逝世的特魯多醫生的墓碑上刻著三句話:有時,去治愈;常常,去緩解;總是,去撫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他通過自己醫生行醫的體驗告訴我們的是,通過診斷、治療使得軀體的疾病痊愈的概率是不大的,醫生更多的時候是要去安慰、疏解患者心理上的沮喪和憂傷,這是無法用科學去證明的,往往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作為醫生要明白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醫生無法包治百病,但可以情暖百家,撫慰百心,安頓百魂。現在我們對醫學的理解越來越立體和全面,一個好醫生應該從身、心、社、靈四個方面來面對患者,而不僅僅是找到一種藥或者做一個手術。
從醫學哲學的角度來看待生命、健康和疾病,背后有很多大概率和小概率的問題。哪一個生命、健康、疾病,我的還是我們的,個體的還是集體的,個性的還是公共的,是我們要思辨的問題。從個體來看,每個人的疾病都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有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所以我們今天對待生命、健康和疾病,其實有各種各樣的選擇。小到感冒,有個人一個禮拜就好了,有的人卻會遷延到一兩個月,所以現在的醫學追求精準治療,也就是建立在更高層面上的一對一的個性化的分析。現代的健康愿景追求全民、全要素,全流程,全方位的健康,有點像今天的奧林匹克運動要更高更快更強更健康。對于這種現象,傳統的中醫有一種反思,八卦里面有一卦叫飛龍在天,有一卦叫亢龍有悔,事實上人的身體在40歲達到峰值之后,慢慢就會往下走,所以這個時候不要求每個指標都處在最佳狀態,平平常常就行了,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崇尚平人。
疾病與疾苦也不一樣。疾病(Disease)是依據具體病因、特別的癥狀,實驗室及各種現代醫療儀器探測出來的陽性指征所做出的偏離正常(健康)態的臨床判定。疾苦(Suffering)則是疾病個體訴說的痛苦經歷和身心體驗,包含著社會文化投射。“一千個患者就有一千個胃病,一千個頭痛……”、“一千個醫生,就有一千個妙手回春”。生命也是有序和無常的共存,人生常態是生、老、病、死,也有沒有病只有生、老、死的壽終正寢,或是只有生、病、死的未老先逝。同樣的,死亡也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無疾而終,有死于衰老,有不可預期的死亡,比如心臟猝死,也有可預期的緩慢的死亡,比如阿茲海默病……
學醫的動機也存在個體和公共的差異,是否學醫則是個性化的選擇。報考醫學專業的一般考量是就業機會、社會地位、職業收入等等,但個體的動機每個人都不一樣。比如協和醫院婦產科的老主任林巧稚,她因為在考場上救人未能完成答卷,卻被協和破格錄取。著名的婦產科專家譚先杰,他學醫的動機是因為他11歲時母親離世,死于卵巢癌,他因此發愿要成為一流的婦科腫瘤專家,去拯救更多像母親那樣的女性患者。
前面講到,醫學有著多元的訴求,一方面要追求醫學的真相,發現生命的真理,創造療效,同時還要還原神圣,洞察真諦,創造更高的價值。所以每一個投身醫學或者說獻身醫學的人,心中都要有兩個詞,一個是崇高,一個是神圣,否則的話很難往前走。因為成為一個好醫生,不僅需要很高的學歷,還需要跟人打交道的閱歷,跟病人打交道的情感和情商,關懷病人的氣質和氣場,需要長期堅持的情懷和定力。醫學是一個職業群,今天協和醫院有將近90個亞專科。本科階段學的是基礎醫學,碩士博士階段才會進入二級分科。醫學的成才周期是比較長的,按照吳英凱院士的說法,需要十五年才能達到一個高級專科醫生的水平。
醫學的最大問題來自職業社會屬性帶來的巨大的責任和壓力,醫生是社會精英,也是道德承重墻。醫生的神圣光環,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帶來社會的過度期許,尤其是過分道德化的期許。醫生與患者共情,給予患者關懷,自己也需要他人的共情與關懷。渴望更多的理解與支撐。職場是競技場,白色巨塔之中,同行之間龍爭虎斗,難免遭逢不公,產生職業受挫與職業迷茫。醫生崗位不僅需要專業知識與技能,還需要豐富的閱歷與強大的心理素質,譬如,如何保守分享到的他人隱私,接觸異性身體私密部位的本能聯想,直面殘酷的身心苦難,生死轉圜的心理刺激與自我平復。患者的遭遇常常會喚起自己的個人經歷和感受……面對這些挑戰需要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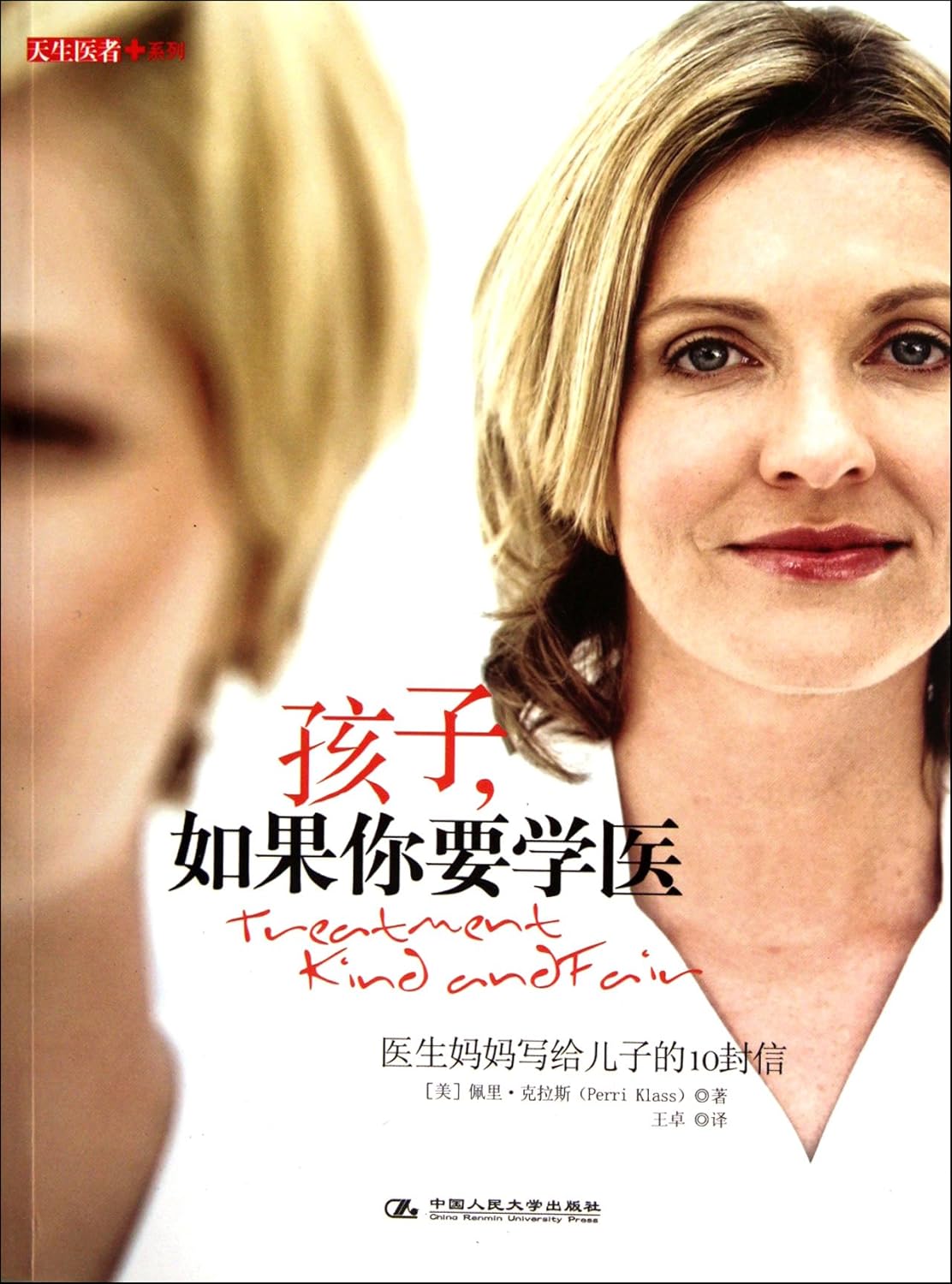
《孩子,你如果要學醫》書封
我推薦大家讀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佩麗·克拉斯(Perri Klass)是一個兒科大夫,也是一名醫生作家,畢業于哈佛醫學院,現任紐約大學小兒科和新聞系雙聘教授,曾出版過三部小說、兩本短篇故事集和兩本醫學散文。她給她的兒子寫了十封信,集結起來就成為了《孩子,你如果要學醫》這本書。她在書里說,在公眾眼里,醫生的形象是高收入、擁有尊貴的社會地位,在關鍵時刻救人于危難之中,擁有起死回生的高超醫術,這些都是表面現象,還要看到背后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醫患關系惡化,包括醫療事故的多發(根據國際上的統計,誤診誤治的比例高達30%,因為很多疾病早期無法識別,等到可以識別的時候已經錯過了窗口),讓立志從醫的年輕人有了更多的思考和顧慮。克拉斯就在寫給兒子的信中說,如果選擇學醫,要掂量一下自己身上有沒有八大稟賦:1、樂于跟人打交道,而非只是生物科學與理化技術的紙上談兵;2、臨床體檢(觸摸身體)總是第一位的,而非五光十色的理化生物檢驗;3、臨床擇科永遠是一個難題,每一個科室都有自己的酸甜苦澀;4、獨特的臨床經驗與共識、指南的困惑、沖突難以排解;5、診療總是不完美,醫者跟醫療差錯總是狹路相逢,越憂心,越冒頭;6、保護患者隱私的意識必須時刻警醒,不可輕慢;7、遭遇患者瀕死的非常時刻,醫者必須全力以赴,逝者為尊,逝者為先;8、工作奉獻與生活閑暇,家庭照料難以兩全,總是顧此失彼。
和消防員一樣,醫生也是逆行者。在價值多元的時代依然追求利他的職業價值,明白利他即利己,助人即助己的道理。在一個漠視生命信仰的時代依然保持堅定的職業信仰。在一個缺少普愛價值的時代依然在診療中保持職業關愛的溫暖,并不懈地傳遞著人間大愛。在一個誠信、規范稀少的時代依然保持質樸、純粹的醫患信任。在一個崇尚任性的時代依然保持敬畏悲憫之心……
另外,現代醫學中有一個新詞,叫做職業倦怠,或者共情耗竭。因為醫學是高強度的,尤其是在住院醫師階段,時間壓力巨大,需要在短期內接診超量的患者。診斷治療中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療效常常不可重復。由于誤診、誤治的普遍性,醫護害怕發生醫療差錯/事故,因而謹小慎微。頻繁的疾苦敘事刺激,帶來醫護共情麻木,關懷遲鈍。當遭逢不治之癥(死亡降臨)時,職業銳氣受挫,感到無力與無奈。患者對于現代新技術寄予太高調期待,醫護難以滿足(做得越多,抱怨越多)。職業奉獻得不到回報,醫學人文的無功利性,導致利他情懷受挫。大眾傳播語境下醫學知識普及化,帶來患者對于醫護權威性的懷疑。
今年3月,韓國因醫學院擴招激起醫生罷工辭職潮,引發社會大震蕩。這個事件也必然會輻射到中國的醫學教育領域。在中國,當下醫學生淘汰率問題十分突出。在2024年中國醫學發展大會上,王辰院士指出,當下醫學生的淘汰率問題十分突出。2020年-2023年國家執業醫師與助理醫師考試通過率不到60%,2019年-2021年臨床醫學本科畢業生有30%根本不當醫生。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目前我國醫學教育總體招生規模較大,但整體層次偏低。過去20年(2002-2021),普通高等學校醫學專業招生人數從23萬增至125萬,醫學專業研究生招生數也從1.7萬猛增至14萬。由于培養模式多元和招生規模過大等原因,各校醫學生培養質量良莠不齊。對此,王辰提出“醫學專業招生要適量、限量、減量。”醫學教育是精英教育,強調這一點并非是醫學界自視甚高,而是因為醫學關乎人類生命和健康這樣的終極利益,只有高素質的人從醫,才能保障生命的圓滿。教育部網站發布的“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8780號建議的答復”中稱,“醫學教育的本質是精英教育。”
在美國,醫學教育一直是精英教育,只在研究生階段開設,不在本科階段開設;精英教育的理念是要保持一定的淘汰率。盡管醫學院的學生都是成績優秀的,但整個醫學教育體系還一直保持淘汰機制,確保留下來的都是最適合的。美國醫學教育制度中,要想做臨床醫生,必須先有MD(Doctor of Medicine),但要想做學術型的醫生,還要在MD的基礎上讀 PhD(Doctor of Philosophy)。多數情況下是以4+4的8年MD為主:4年的本科學習,畢業后進入醫學院進行4年學習。如果是MD+PhD的話,需要在4年MD的基礎上增加4-5年。美國波士頓凌晨發車的公交車里乘客不多,但大多數是哈佛醫學院的實習醫生/住院醫生。他們必須在早7點前趕到醫院,溫習病歷,準備查房與手術。協和沿襲百年的住院醫師制度源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要求住院醫生24小時值班。在杜克大學,無論你的本科成績多優秀,如果要申請進入醫學院學習,必須先完成約500個小時的義工服務,以證明你有照護他者、弱者的意愿與能力。如果沒有義工服務經歷,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醫療服務中有一個3C/2H原理:Cure,治療,由醫生主導,護士配合;Care,照顧,由護士主導,醫生協同;Call,回應訴求,由醫護共同承擔,甚至輻射逝后環節。醫學要給人希望(Hope),其次才是療愈(Healing)。醫學比其他自然科學都要更復雜,這是由四個百年未變的特征決定的,即永恒的不確定性、生命的多樣性、疾病轉歸的復雜性以及醫患的主-客間性。威廉·奧斯勒醫生曾經說過,醫學是崇高的使命,而非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醫學是一門不確定性的科學和可能性的藝術。醫學是一輩子在學習,一輩子在付出,一輩子在收獲,一輩子在反思,這是奧斯勒給年輕醫生的忠告。生命/健康無常,它是一個謎局,一個灰箱,真相無法大白。人類不可能全知、全能、全善,人生路迢迢,也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不等式與萬花筒。
(本文整理自北大博雅講壇第600期,經王一方教授審定后刊發)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