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讀︱張洪彬:這些書讀來深受啟發(fā)
本文原題《2018年讀過的最受啟發(fā)的歷史著作》,現(xiàn)題為編者所擬。
1.鄧野:《巴黎和會(huì)與北京政府的內(nèi)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zhí)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4年。
五四運(yùn)動(dòng)(狹義的和廣義的)作為一個(gè)已經(jīng)紅了半個(gè)多世紀(jì)的史學(xué)命題,相關(guān)研究文獻(xiàn)用“汗牛充棟”來形容可能并非虛夸。且不說每十年、每五年甚至每年產(chǎn)生的大量陳詞濫調(diào)讓人望而生厭,即便是諸多學(xué)術(shù)期刊中的相關(guān)研究論文也已經(jīng)讓人很難有讀下去的欲望。可以說,關(guān)于五四運(yùn)動(dòng)的闡發(fā)已經(jīng)嚴(yán)重過剩而淪為低水平重復(fù)建設(shè)的典型案例了。但是你真要問問,中國與歐戰(zhàn)和巴黎和會(huì)的糾葛是怎么一回事,中日“二十一條”與歐戰(zhàn)什么關(guān)系,“北洋軍閥”是怎樣“賣國”的,國人對巴黎和會(huì)有怎樣的期待,巴黎和會(huì)為什么不支持中國的訴求,北京的學(xué)生是怎樣獲悉巴黎的交涉進(jìn)展的,所謂皖系、直系、研究系以及廣州政府等政治勢力如何對待外交交涉和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大部分的人(即便是近代史從業(yè)者)是講不清楚的,很不幸的是,筆者也是其中一員。拜讀鄧野先生所著《巴黎和會(huì)與北京政府的內(nèi)外博弈》,許多疑惑獲得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閱讀過程中甚至找到了欲罷不能又不忍一口氣讀完的美妙感受。

第二,內(nèi)外兼治已是不易,何況袁世凱死后的中國政治利益、實(shí)力和合法性都高度分化,你方唱罷我登場,頭面人物走馬燈地?fù)Q而且對內(nèi)政外交確實(shí)發(fā)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這就成了對北洋時(shí)期開展史學(xué)研究的一大難點(diǎn)。如想把這段歷史講清楚,對作者的復(fù)線敘事技巧的要求是極高的,而此書的復(fù)線敘事是相當(dāng)成功的,值得治史者反復(fù)揣摩。
第三,該書完全擺脫了愛國/賣國這類道德評價(jià)標(biāo)簽,“用利益解剖政治”,設(shè)身處地去理解歷史人物、政治勢力的處境和利害得失,于是我們在所謂“北洋政府”內(nèi)部看到了“文治總統(tǒng)”徐世昌與安福國會(huì)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于是我們看到了怕背上“賣國賊”罵名而一心甩鍋的代理總理龔心湛、外交總長陸徵祥,于是我們看到了南方政客熱心鼓勵(lì)北洋治下各地的罷課罷市,唯恐天下不亂,同時(shí)卻竭力抑制自己治下的罷課罷市運(yùn)動(dòng),稱號(hào)召抵制日貨的學(xué)生為“匪徒”“亂民”。
第四,作者對歷史人物的性格和動(dòng)機(jī)的揣測非常精彩,印象最深的是沒有槍桿子的文治總統(tǒng)徐世昌在1919年6月面臨內(nèi)外兩個(gè)和會(huì)都破產(chǎn)的被動(dòng)局面如何以退為進(jìn),通過引咎辭職換來挽留和支持,從而換來政治主動(dòng),即要挽留他繼續(xù)擔(dān)任總統(tǒng),必須支持簽署對德和約,必須支持重開南北會(huì)議。作者認(rèn)為,徐世昌的辭職是一個(gè)精心策劃的政治謀略。對徐世昌的動(dòng)機(jī)的揣摩主要出自作者的洞察和分析,作者做出判斷的根據(jù)之一是徐世昌當(dāng)天日記中對辭職一事只字不提。表面上看來這樣的判斷太過大膽,似乎不夠嚴(yán)謹(jǐn),但是加上作者對徐世昌性格的分析,這種判斷是令人信服的。所謂“世事洞明皆學(xué)問,人情練達(dá)即文章”,在證據(jù)鏈斷裂的地方,史家對人情世故的洞察是分得出高下的。
2.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
許多治史者的共同夢想是把具體的人事變遷放到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來理解,從而既可以很好地解釋具體的歷史變遷,又可以觀照廣闊的歷史畫卷。越來越多人體會(huì)到,如果不能從全球貿(mào)易體系的角度來看則很難理解馬戛爾尼使華、鴉片戰(zhàn)爭以及近代中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果不了解蘇俄和日本的近代史則很難理解近代中國的許多關(guān)鍵轉(zhuǎn)折;1945年后的中國史如果不放置到冷戰(zhàn)的大格局下來看更是根本無法理解。
然而,這一理想對許多人來說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幾個(gè):第一,這一方面要求治史者對中國史的論題、材料、研究現(xiàn)狀有很好的把握,同時(shí)要求治史者有相當(dāng)程度的世界史、外國史的功底,而世界史、外國史并不是一個(gè)有待學(xué)習(xí)的固定的知識(shí)存量,而是一個(gè)不斷推陳出新的領(lǐng)域,因此對世界史和外國史的了解并不是靠幾本教材或名著可以解決的,所以要把中國放置到“合適”的世界史背景中去,對世界史功底的要求其實(shí)是相當(dāng)高的。第二,即便是聚焦于中國相關(guān)的世界史和外國史,外語學(xué)習(xí)和資料搜集的經(jīng)濟(jì)成本和時(shí)間成本也是相當(dāng)高昂的。歐美許多名校培養(yǎng)博士生,往往有形形色色的基金資助學(xué)生到研究對象的國度去學(xué)習(xí)語言、搜集資料,類似于此的基金在中國仍是相當(dāng)匱乏的,外語學(xué)習(xí)和資料搜集受限嚴(yán)重,要獲得本國之外的資料信息是相當(dāng)困難的,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只是部分緩解了這個(gè)困境。但沈志華教授同時(shí)克服了如上困境。出身高干家庭的他對共和國史不僅有興趣,而且有體驗(yàn);依靠經(jīng)商所得搜集到的大量蘇聯(lián)檔案使他有充分的一手俄文材料;早年教育背景使他具備俄文閱讀能力;長期的中蘇關(guān)系史研究、冷戰(zhàn)史研究使他能夠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觀照中國。這些優(yōu)勢使得他能把中國歷史放置到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理解。

3.傅高義:《共產(chǎn)主義下的廣州:一個(gè)省會(huì)的規(guī)劃與政治(1949-1968)》,高申鵬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史家未必是時(shí)代最卓越的人士,生活閱歷也未必豐富,研究的對象卻通常是時(shí)代的弄潮兒,有人自然會(huì)質(zhì)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此誠為史家需要時(shí)時(shí)自問的問題。不過,好在歷史學(xué)往往是研究死人的,歷史人物生前來不及看見的歷史結(jié)果和影響,后世的史家可以看到,歷史人物生前看不到的他人日記、書信、檔案等材料,后世的史家可以看到。借助這些信息優(yōu)勢,后世的史家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bǔ)與研究對象的段位差距。后世史家相對于研究對象還有一個(gè)優(yōu)勢,就是可以做一個(gè)冷眼旁觀的人,而不用帶入太多情緒、偏見、立場和利害得失,這使得后世史家能更持平地考慮多重因素,從而能較好地解釋歷史因果。近代史研究者卻往往不占有這些優(yōu)勢,尤其是研究非常近的歷史,塵埃尚未落定,沒有人說得清事情會(huì)朝哪一個(gè)方向發(fā)展,而且研究者本身的命運(yùn)和得失往往還在近代史的影響之下,很難獲得一個(gè)合理的觀察距離,這使得許多近代史著作很容易被時(shí)間淘汰,經(jīng)過相當(dāng)長一段時(shí)間仍然被認(rèn)為有閱讀價(jià)值的則堪稱經(jīng)典,比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李劍農(nóng)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再如傅高義的《共產(chǎn)主義下的廣州:一個(gè)省會(huì)的規(guī)劃與政治(1949-1968)》。

4.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杜蒲、李玉玲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這本書與傅高義《共產(chǎn)主義下的廣州》情況很相似。該書初版于1977年,毛澤東去世才幾個(gè)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990、1992年出版的中譯本均譯自1986年的英文第二版。英文第三版出版于1990年版,中譯本由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出版,題為:《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者也是美國學(xué)者,在毛澤東時(shí)代寫作該書時(shí)無法到中國大陸搜集資料,依靠的材料主要是公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和《人民日報(bào)》等官方材料。在原始文獻(xiàn)極度匱乏的狀況下,邁斯納寫作了這本名著,此后又于1986、1999年兩次修訂出版。該書面世距今已經(jīng)40年,仍然是理解毛澤東時(shí)代不能繞過的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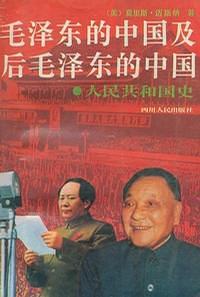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