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粵語簡史
【編者按】
方言是一種語言的地方分支。廣東省內(nèi)的方言,按其語言特點(diǎn)可歸納為三個(gè)大類:粵方言、閩方言和客方言。據(jù)學(xué)者的初步研究,認(rèn)為粵方言的分化與古代的楚語有關(guān),閩方言的分化則與吳語有關(guān)。這些方言中,從流行范圍和使用人數(shù)來說,粵方言都占據(jù)首位。粵方言又稱為廣州方言,傳統(tǒng)上叫做“廣府話”或“省城話”。外省人又把它叫做“廣東話”,其實(shí)這種叫法是不確切的。
對粵方言的演變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翻翻《廣東的方言》(李新魁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修訂重版)第二章“廣東方言的‘老大哥’——粵方言”,本文摘自其中第二節(jié)“粵語簡史”。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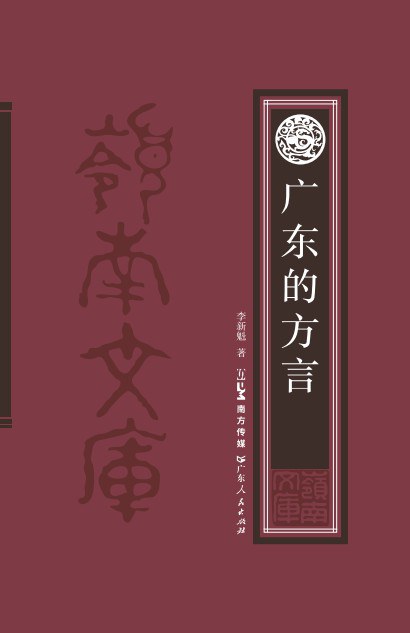
《廣東的方言》書封
漢語的各種方言,都是從古代漢語分化出來的。它們的共同來源,是古代漢族人民使用的語言。當(dāng)然,在我國的古代社會中,既有共同語存在,也有各地區(qū)使用的復(fù)雜的方言存在。現(xiàn)代各地的漢語方言,有的當(dāng)然是古代漢語共同語直接的分化,有的則可能是某一地區(qū)方言的繁衍。但推究其源頭,都是來自古代漢語。
現(xiàn)代每一種方言都有它們各自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有它們自己從古代漢語分化出來的演變過程。漢語各方言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有長有短,分化的年代也各不相同,但是,它們的歷史基礎(chǔ)是繼承了古代漢語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體現(xiàn)在語言質(zhì)素上就是有著比較一致的語法構(gòu)造和基本詞匯,方言的差別主要是表現(xiàn)在語音方面。而各個(gè)方言彼此之間以及與共同語之間相當(dāng)嚴(yán)整的語音對應(yīng)規(guī)律又表明了相當(dāng)密切的近親關(guān)系和方言發(fā)展的穩(wěn)固性。
……
粵方言這個(gè)流行于嶺南地區(qū)的重要方言,是如何從古代漢語分化出來的?分化之后又如何發(fā)展?什么時(shí)候形成接近于現(xiàn)代粵方言的樣子?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一、廣東粵語地區(qū)的先民
廣東僻處嶺外,與歷史上漢族聚居的中原地區(qū)(黃河流域一帶)相距較遠(yuǎn)。明末、清初的廣東詩人陳恭尹《春感》一詩所說的“石羊城下越王宮,天盡東南浪拍空”和《九日登鎮(zhèn)海樓》中的詩句:“五嶺北來峰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正是廣東這種僻居南海之濱的寫照。由于廣東遠(yuǎn)隔中原,又是炎日與瘴癘彌漫之地,在古代成為許多朝代統(tǒng)治者貶謫犯罪官吏之所。秦代以前,居住在廣東和廣西地區(qū)的,基本上是少數(shù)民族。這些民族在西周時(shí)被統(tǒng)稱為“蠻夷”,春秋戰(zhàn)國以后則稱為“越”(與“粵”相通)。越族的種類很多,所以被稱為“百越”。它分布的地域很廣,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以至四川、云南、貴州等地,都有越人的種族。《漢書·地理志》臣瓚注云:“自交趾至?xí)甙饲Ю铮僭诫s處,各有種姓。”《呂氏春秋·恃君》也說:“揚(yáng)、漢之南,百越之際。”可知古代在長江以南及沿海地區(qū),都是越人的聚居之地。
廣東的越族,古稱為“南越”,它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的哪些民族?一般認(rèn)為,它大概包括后代的壯族、黎族和疍家等。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說:“廣東傜(瑤)、僮(壯)二種,傜乃荊蠻,僮則舊越人也。”瑤族一般認(rèn)為原來住于湖南、貴州一帶,后來才遷入廣東。黎族即隋、唐時(shí)代居于廣東的俚人。它也是百越的一支(有人認(rèn)為屬于駱越)。總之,上古時(shí)期,廣東的中南部地區(qū)(也就是現(xiàn)代流行粵方言的地區(qū)如南海以至高要一帶),居住的主要是壯人和黎人。《隋書·南蠻傳》說:“南蠻雜類,與華人錯(cuò)居,曰疍、曰獽、曰俚、曰僚、曰,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這些壯族和黎族人散居于廣東省的廣大地區(qū),當(dāng)然也有住于廣西各地的。后來,他們有的接受漢人的文化,逐漸漢化了,有的則遷移至偏僻的山區(qū)。但他們的語言在居住過的地方仍留下一些痕跡。屈大均《廣東新語》說:“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包某、番某……”(卷十一)這個(gè)“那”原來就是壯語的詞,本指“田地”;“南”則在壯語、黎語中指“水”或“河”。這些地名保留下來,顯示這些地區(qū)原曾居住過壯人或黎人,如廣東臺山有那扶、化州有那霧(今稱那務(wù))、陽江有那龍,廣西靈山有那靈、欽州有那彭,等等。壯族和黎族人的語言屬于漢藏語系中的壯侗語族。
上古時(shí)期,廣東和廣西的絕大部分地區(qū),大概沒有漢語的方言存在。居民使用的是少數(shù)民族語言。這種情況,直至中古唐宋之際的偏遠(yuǎn)地區(qū)仍是如此。如《高州府志》卷六在談及電白縣時(shí)說:“唐宋以前,僮(壯)傜(瑤)雜處,語多難辨。”說的正是這種情況。漢魏時(shí)代以后,廣東出現(xiàn)了苗、瑤、僚、畬各個(gè)少數(shù)民族,它們是后代才從長江流域及其他地區(qū)移入的。一直到明、清時(shí)期,廣東一些僻遠(yuǎn)的縣份,仍然居住著這些稱為瑤、黎、僚、畬等的少數(shù)民族居民。
……
四、唐宋時(shí)代——粵語“自立門戶”
唐代之時(shí),粵方言又有了發(fā)展。在這個(gè)時(shí)期,廣州及附近地區(qū)已經(jīng)主要地為漢族居民所占住,一部分先住民族已經(jīng)漢化了,另一部分則被迫遷移至偏僻的山區(qū)或廣西等地。當(dāng)然,離廣州稍遠(yuǎn)的許多縣份甚至廣州附近,仍有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居民。如唐時(shí)廣州周圍還有不少瑤人聚居著。《南齊書·州郡志》“廣州”條說:“雖民戶不多,而俚僚猥雜。”《南史·夷貊傳》說:“廣州諸山并俚僚,種類繁熾。”《陳書·杜僧明傳》也說:“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南江督護(hù),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并為安興所啟,請與俱行,頻征俚僚有功。”《隋書·薛世雄傳》說:“隋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可知南北朝至唐時(shí),廣州及附近所居之俚、僚族人仍甚多,他們“多次為亂”,故有“討平”之舉。這些少數(shù)民族居民,使用的當(dāng)然是民族語言。《高州府志》卷六說:“(電白縣)唐宋以前,僮(壯)傜(瑤)雜處,語多難辨。”除僚(獠)、壯、瑤等族居民之外,現(xiàn)代海南島上的黎族先民俚人,也聚居于廣東大陸地區(qū)。如《太平御覽》卷七八五引《南州異物志》說:“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郁林、合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shù)千里。”這里所說的高涼郡,是指現(xiàn)在廣東的茂名、高州、電白、化州、陽江、恩平一帶。這些地方在隋唐時(shí)還是居住著大量的黎族人民。他們后來才進(jìn)一步經(jīng)由瓊州海峽遷入海南島。當(dāng)然,黎族人從大陸移入海南,并不自隋、唐時(shí)始。在戰(zhàn)國以至秦、漢之時(shí),黎人已經(jīng)陸續(xù)進(jìn)入海南。俚族在六朝時(shí)出現(xiàn)了一個(gè)杰出的女政治家冼夫人,她就是嶺南地區(qū)高涼郡人,生于梁武帝普通年間,到隋文帝仁壽初年去世。史稱她的家族“世為南越首領(lǐng),跨居山洞部落十余萬家”(《隋書·譙國夫人傳》)。她與漢族人馮寶結(jié)婚,在輔助隋朝統(tǒng)一嶺南地區(qū)、和輯廣東各地少數(shù)民族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北史·譙國夫人冼氏傳》說她善于“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可知當(dāng)時(shí)嶺南的少數(shù)民族居民還很多。僚族是隋唐時(shí)代經(jīng)常活躍于廣東各地的一個(gè)民族,有人認(rèn)為它也是廣東的先住民族,屬古百越的一支(見嚴(yán)英俊《古代僚族略述》一文,載《民族史論文選:1951—1983》下冊,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86年版),其族源與壯族比較接近。隋唐時(shí),僚族人還遍布于廣東各地,《隋書·地理志》說:“俚僚貴銅鼓,嶺南二十五郡,處處有之。”這些僚人及壯人、俚人都操本民族的語言。唐代,佛家六祖惠能是廣東新州(今新興)人,《壇經(jīng)》描述他去見弘忍和尚時(shí),“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fù)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yuǎn)來禮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師遂責(zé)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這里所說的“獦獠”,即指僚人。可知新興一帶還有許多僚族人民。唐宋時(shí)人把語音不正稱為“僚”,大概是惠能的話中帶有濃重的南方民族的口音,所以弘忍和尚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僚人(有人說惠能是穿著僚族的服裝)。唐時(shí)被貶到廣東的韓愈,他在《送區(qū)冊序》一文中說:“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縣廓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余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唐時(shí)粵北的陽山縣,還是少數(shù)民族的聚居地區(qū)。他們的語言與漢人尚不相通。唐代作家柳宗元到湖南南部永州做刺史,他對湖南、廣東、廣西各地的語言情況也作過如下的描述:“居蠻夷中……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舌啅噪,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jié)M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與蕭翰林俛書》)柳宗元所描述的楚(湖南)、越(廣東)之間的語言,似乎還是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由此可知,操粵語的,恐怕主要還是在廣州城附近一帶。
但是,唐代之時(shí),北方的漢語畢竟對廣東的語言有更進(jìn)一步的影響,特別是在唐人張九齡開辟了大庾嶺新路、方便了南北的交通之后。張氏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云:“初,嶺廢東路,人苦峻極……載則不容軌,運(yùn)則系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國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fù)妻載,勞亦久矣。”大庾嶺新路的開通,大大便利了海內(nèi)外的交往。北人入粵者日益增多,由隋至唐天寶年間,廣東人口增加了1.6倍,這就大大改變了廣州一帶的城市面貌。元人陳大震所撰的《大德南海志》(殘本)說:“廣州為嶺南一都會,戶口視他郡為最;漢而后,州縣沿革不同,戶口增減亦各不一,大抵建安東晉永嘉之際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廣者眾,由是風(fēng)俗革變,人民繁庶。至宋,承平日久,生聚愈盛,自王師滅宋平廣以前,兵革之間,或罹鋒鏑,或被驅(qū)掠,或死于寇盜,或轉(zhuǎn)徙于他所,不可勝計(jì)。”唐代之時(shí),廣東確曾出現(xiàn)了一度相當(dāng)繁榮的景象,南來的中原漢人很多。唐代入粵者,起先以聚居于粵北始興、南雄一帶為重點(diǎn)。唐玄宗天寶年間(742年至756年),韶州、連州分別有3萬多戶人家,戶口數(shù)不比廣州少許多。中唐以后,外來居民逐漸以廣州附近一帶為移居目標(biāo),廣州日見繁榮,人口不斷增多。特別是到了在廣州地區(qū)建立了南漢王朝之后,廣州地區(qū)經(jīng)濟(jì)有較大的發(fā)展,人民生活較為安定,出現(xiàn)了相當(dāng)繁榮的局面。比如說,唐開元時(shí)廣州的戶口數(shù)是64250戶,到了元和年間,增至74099戶。到了南漢之時(shí),戶口數(shù)已增加到170263戶(據(jù)《文獻(xiàn)通考》)了。直至宋代,使用粵方言的中心地區(qū)廣州一帶,人口仍在不斷增加。由于珠江三角洲土地的開墾,外地人的移入,使得廣州周圍各地的戶數(shù)大增。當(dāng)然,這一時(shí)期廣東人口的不斷增加,不止限于粵語區(qū)。其他方言區(qū)也有同樣的情形。就廣東全省來說,據(jù)田方等人主編的《中國移民史略》一書的統(tǒng)計(jì),謂“從整個(gè)廣東地區(qū)來看,自6世紀(jì)末至14世紀(jì)后期的800年間,由于全國經(jīng)濟(jì)的逐漸發(fā)展,漢族人民的陸續(xù)南下,海外交通和貿(mào)易的不斷擴(kuò)大,使廣東的人戶繼續(xù)增加,尤以宋代增加最速,而元代則反而略減,大概由于受戰(zhàn)爭破壞影響。各朝廣東人戶占全國比重是:隋占1.5%、唐占2.2%、宋占3.5%、元占4.1%。總計(jì)由隋至元,廣東的人口由131280戶,增至548759戶,共約增加3倍,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全國人口增加的速度(0.5倍)”。這樣,就造成了元人陳大震在《大德南海志》中所說的“廣為海濱鄒魯,詩書文物之盛,不減中州”的局面。必須著重指出的是:唐宋之時(shí),廣州的海運(yùn)事業(yè)有了更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廣州成為我國南方一個(gè)出入口的重要海港。一方面有不少我國人經(jīng)由此地前往東南亞、印度、波斯各國;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外國人經(jīng)由海道來到廣州進(jìn)入我國。進(jìn)出口的貨物甚為繁富。唐代詩人杜甫的《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說:“番禺親賢領(lǐng),籌運(yùn)神功操。大夫出盧宋(指盧奐和宋璟),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當(dāng)時(shí)珠江上停泊的“胡舶”竟有千艘之多。《新唐書·王鍔傳》描述當(dāng)時(shí)廣州進(jìn)出口貨物之盛也說:“日十余艘,載皆犀、象、珠璣,與商賈雜出于境。”《唐大和尚東征記》也說:“(珠)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shù)。”據(jù)史書記述,唐時(shí)的廣州城人口約30萬,而流動人口竟達(dá)80萬。外來的“蕃人”有12萬人。此外,唐宋統(tǒng)治者把貶謫到廣東作為對犯罪官吏的懲罰,一些文人被貶來廣東,他們?nèi)牖浺院螅d辦教育,傳授中原文化,特別是傳授中原地區(qū)漢語的讀書音。這與秦漢時(shí)的大移民以罪犯和贅婿、戍卒為主的情況不同。歐陽修《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說:“是時(shí)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yuǎn),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嶺南者,往往有子孫,或當(dāng)時(shí)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唐人孔戣就曾在南海(廣州)建立“廣思館”收留那些“宦粵子孫之流落者”。又如南漢時(shí),河南人劉浚“以中原亂離相繼,避來嶺表,依崇龜。乾寧中,崇龜死,遂流寓廣州”(見《南漢書·諸臣傳二》)。南漢時(shí)的周杰,也因“嶺南稍安……攜家南徙”。這些名臣、仕宦、學(xué)者入粵以后,帶來了中原漢語書面語的讀音,這就促使粵方言所接受的漢語語音更加規(guī)范化,進(jìn)一步形成一支既有相對獨(dú)立的語音體系和詞匯系統(tǒng)以及語法結(jié)構(gòu)的方言,又是與中原漢語共同語的語音有較為嚴(yán)整的語音對應(yīng)規(guī)律(如現(xiàn)代粵語語音與宋初《廣韻》音系的對應(yīng)規(guī)律一樣)的方言。總之,唐代是粵方言日趨成熟的歷史時(shí)期。
唐末,粵方言的發(fā)展曾經(jīng)穩(wěn)定了一個(gè)時(shí)期,停止接受中原漢語的同化。到了宋代,它便朝著與中原漢語距離越來越大的方向發(fā)展,它已經(jīng)“自立門戶”了。當(dāng)然,這種與中原漢語的差異,并不自宋代始。當(dāng)中原漢語傳播到廣州地區(qū),與當(dāng)?shù)氐恼Z言發(fā)生融合以后,一方面是粵語表現(xiàn)為與中原漢語特點(diǎn)相同的過程;另一方面,由于融合中吸收了楚、吳等地的方言以及當(dāng)?shù)孛褡逭Z言的某些特點(diǎn),也表現(xiàn)了與中原漢語互有差異的過程。但是,當(dāng)粵語已經(jīng)形成了具有自己的某些語言特點(diǎn)、但又大體上同于漢語的一支有一定流通范圍的方言之后,甚至對這種同化產(chǎn)生抗拒的作用,而按著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向前發(fā)展。這時(shí),它從原來的“求同”(受中原漢語的影響、接受它的同化)轉(zhuǎn)而向“求異”(自身的演變)的方向變化了。宋代之時(shí),粵語正是處于這樣的歷史轉(zhuǎn)變時(shí)期。因此,宋人在談到廣東的語言狀況時(shí),都覺得它與中原漢語大不相同。如宋代周去非在他的《嶺外代答》卷三中談到欽州(也屬粵方言區(qū))的語言情況時(shí)說:“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雜為音聲,殊不可曉,謂之蔞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于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獠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疍人,以舟為室,泛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顯然,當(dāng)時(shí)的廣東、廣西之音已有它突出的特點(diǎn),所以周去非在描述疍家話時(shí)用它來作比較。這個(gè)廣東、廣西之音(流行于兩省區(qū)的粵方言)的情況如何呢?他說:“余又嘗令譯者以禮部韻(按:指《禮部韻略》)按交趾語,字字有異。”可知當(dāng)時(shí)的粵語語音,距離中原漢語的讀書音,已經(jīng)有相當(dāng)大的差異了。
宋代的粵方言,大概已與現(xiàn)代的粵方言相去無幾。它所用的語音和詞匯,可能已奠定現(xiàn)代粵語的基礎(chǔ)。宋人吳處厚《青箱雜記》說:“嶺南呼村市為墟。”說的正是現(xiàn)代粵語所用的詞;宋人黃徹《蛩溪詩話》卷十:“東坡‘倦看澀勒暗蠻村’,蓋嶺南竹名。”粵語稱有刺之竹木為“勒”,也與蘇東坡所寫正同。又如《通俗編》引《水東日記》說:“廣東人相傳:宋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精地理之學(xué),名傾一時(shí)。……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這表明在宋代時(shí),廣州人已把“厲”字念為與“賴”字相近的讀音,這也與現(xiàn)代的粵語相同。總之,唐宋之時(shí),粵方言已經(jīng)形成為一支與中原漢語或北方話很有差異的方言,它的面貌,已經(jīng)距現(xiàn)代的粵語不遠(yuǎn)。唐宋時(shí)人,已經(jīng)感覺到粵方言與北方方言的巨大差異。這就意味著粵方言已經(jīng)從北方的中原漢語分化出來而成為一支重要的方言,它已經(jīng)“自立門戶”了。
五、從元明清至現(xiàn)代——由“步入壯年”到“老之將至”
宋代以后,粵方言繼續(xù)發(fā)展,它與北方話的距離越來越大。到了明代,粵語已與現(xiàn)代的粵語大體相同。明清以來粵語區(qū)各縣所修的縣志,其中談及“方言”的情況,可以說已與現(xiàn)代粵方言相當(dāng)一致。如屈大均作于清初的《廣東新語》,其中的“土言”部分所列舉的粵方言語詞,已與現(xiàn)代粵方言的說法相當(dāng)一致。如說:“廣州謂平人曰佬……謂平人之妻曰夫娘……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謂子曰崽……玄孫曰塞,息訛為塞也……廣州謂母曰妳,亦曰媽……亦曰毑,凡雌物皆曰毑……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游手者曰散仔,……大奴曰大獠(案,即‘佬’),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xì)仔,小婢媵曰妹仔……巫曰師公、師婆……廣州謂橫恣者曰蠻……海外諸夷曰番鬼……廣州謂美曰靚,顛者曰廢,無直曰硬頸……角勝曰斗……飲食曰吃……謂淫曰姣,姣音豪……謂聰明曰乖……問何如曰點(diǎn)樣……走曰趯……罵人曰鬧……謂港曰涌……音沖,凡池沼皆曰塘……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也……小舟曰艇,泅水曰游……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鵝春,曰雞春、鴨春……數(shù)蕉子曰幾梳”,等等。這些方言的詞語或音讀,北方人聽起來已很不好懂。所以明人孫蕡的《廣州歌》說:“廣南富庶天下聞,四時(shí)風(fēng)氣長如春……閩姬越女顏如花,蠻歌野曲聲咿啞。”這里所說的“蠻歌野曲”是指當(dāng)?shù)氐拿耖g歌曲,外地人聽來不知所云,所以用“聲咿啞”來描述它。明人陸容的《菽園雜記》也說:“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雖圣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每笑之……”陸氏說閩、粵人“音韻多謬”,是因?yàn)槊鞔畷r(shí),這兩種方言的讀音與北方話相差較遠(yuǎn),所以才有這種說法。清人趙翼《檐曝雜記》說:“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zhèn)安、太平等府……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趙翼認(rèn)為廣東(主要是指廣州地區(qū))的方言主要是在讀音上與北方話有別,“不可了了”,這說明粵方言的讀音是外地人所聽不懂的。明清時(shí)期的粵語,與現(xiàn)代粵語大體相同,還可以從下述明清時(shí)人的描述中得到證明。明人袁子讓在《字學(xué)元元》中的“方語呼音之謬”一節(jié)中說:“粵音以人為寅,以銀為壬,此喻日互相混也。”現(xiàn)代確是如此。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四說:“廣人呼啼為臺。”也與現(xiàn)代粵音相近。清人方本恭《等子述》云:“粵人以雙為松,亦以松為雙,是呼江攝如通攝,通攝如江攝也。”此外,清人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記一些粵語詞的讀音,也與現(xiàn)代的說法相同。如說“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雨點(diǎn)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粵俗呼泥腿曰‘濫仔’……呼使女曰‘美仔’(案,即‘妹仔’),呼十歲內(nèi)男女曰‘顋門仔’(案,即‘細(xì)蚊仔’)……”,“粵人呼荸薺曰馬蹄”,等等,都與現(xiàn)代粵語相同。足以證明明清時(shí)代的粵語與現(xiàn)代粵語已無甚區(qū)別了。這就說明,粵方言發(fā)展到此一時(shí)期,已經(jīng)“進(jìn)入壯年”,并且向“老年”期邁進(jìn)。現(xiàn)代的粵語由于受漢語共同語的影響,正發(fā)生向共同語靠攏的過程。隨著這數(shù)十年來共同語——國語或普通話的大力推廣,各地的方言開始出現(xiàn)“日漸消磨”的過程。方言中大量地吸收共同語的詞語,在語音上也有向共同語靠近,即以共同語的讀音來規(guī)范方言的某些字音的趨向,這就使粵方言逐漸進(jìn)入“老年”。當(dāng)然,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期里,方言仍將強(qiáng)固地存在,繼續(xù)服務(wù)于嶺南這一特定的語言社會,粵方言仍將發(fā)揮它的交際作用。……
總結(jié)以上所述的粵語形成和發(fā)展的簡單歷史,可以看到:在先秦時(shí)代,粵方言區(qū)開始處于接受漢語傳播的階段,起初主要是接受楚方言的影響。秦漢以后,經(jīng)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粵方言區(qū)也是處于接受漢語的傳播以及與當(dāng)?shù)孛褡逭Z言融合的階段。在這八九百年的時(shí)間中,粵語從剛萌芽發(fā)展到成熟,從以接受楚方言的傳播、影響為主轉(zhuǎn)為以接受中原漢語為主,終于走上“自立門戶”、形成一支重要的漢語方言的道路。隋唐之際,粵語更進(jìn)一步接受了中原漢語書面語讀書音更為重要的影響。宋代以后,粵語在成熟、鞏固之后,便朝著與中原漢語差異日益增大的道路變化了。這是因?yàn)樗环矫胬^續(xù)融入當(dāng)?shù)厣贁?shù)民族語言的詞語或吸收它們在語音或語法上的特點(diǎn);另一方面也按著與中原漢語不同的自身語言內(nèi)部發(fā)展規(guī)律向前發(fā)展,這就造成了與中原漢語更大的差異。而在宋、元時(shí)代,粵語的面貌已與現(xiàn)代粵語相去不遠(yuǎn),它已基本上“定型”化而步入“壯年”了。從明清至現(xiàn)代,粵方言的變化已經(jīng)不大。而由于現(xiàn)代漢語共同語的不斷推廣,粵方言就走上方言特點(diǎn)“日漸消磨”的道路。它,已經(jīng)“老之將至”了。這就是粵方言從產(chǎn)生、形成到發(fā)展的簡單歷史。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