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喀里多尼亞危機(jī):“后帝國時代”的法國如何自我解套?
2024年5月中旬,因?yàn)檫x舉制度改革引發(fā)爭議,法國的海外領(lǐng)地新喀里多尼亞爆發(fā)三十多年來最嚴(yán)重的暴亂,造成至少9人死亡(包括兩名憲兵)。事態(tài)之嚴(yán)重,曾迫使總統(tǒng)馬克龍親自飛赴當(dāng)?shù)亍皽缁稹保手Z通過政治協(xié)商和對話來化解緊張局勢。雖然到五月底,當(dāng)?shù)厥聭B(tài)逐漸平息,緊急狀態(tài)也得以解除,但這只是一種“脆弱的平靜”。到了六月中下旬,多名獨(dú)立運(yùn)動領(lǐng)導(dǎo)人因?yàn)樯嫦庸膭颖﹣y而被捕,并被押解到法國本土拘留,此舉頗有“秋后算賬”的意味,在島內(nèi)再度激化了局勢,騷亂勢頭死灰復(fù)燃。

當(dāng)?shù)貢r間2024年5月18日,法屬新喀里多尼亞持續(xù)騷亂,民眾走過設(shè)置的路障的街道。
從更廣泛意義上說,新喀里多尼亞的未來何去何從,如今再度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自1988年“馬提尼翁協(xié)議”(Accords de Matignon)和1998年“努美阿協(xié)議”(Accord de Nouméa)所確立的和平自決框架,仿佛一個被不斷壓縮的彈簧,在走到最后、將要一錘定音的時候,面臨著激烈反彈。
來自太平洋上的遙遠(yuǎn)警報聲,提醒人們法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歐陸國家,它繼承了殖民時代的眾多遺產(chǎn),這些遺產(chǎn)并沒有因?yàn)?0世紀(jì)后半葉的“去殖民化”運(yùn)動、尤其是阿爾及利亞問題的解決而一夜歸零。它給法國帶來了豐厚收益,同時也持續(xù)地造就了法國所面臨的“后帝國時代”獨(dú)特困境。
新喀里多尼亞的亂局,事實(shí)上并不是孤例,今年以來,法國的其他海外領(lǐng)地如瓜德魯普、馬約特等地也先后出現(xiàn)局勢動蕩。在前者,由于犯罪泛濫,當(dāng)局被迫在首府針對未成年人實(shí)施宵禁;在后者,由于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導(dǎo)致治安惡化,法國已多次采取“清場”行動,但效果始終有限,同樣對族群沖突局面束手無策。
然而,我們也不必用隔岸觀火的心態(tài),嘲笑這個老牌殖民帝國的窘困,因?yàn)轭愃茊栴}事實(shí)上存在于所有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昔日帝國繼承者之中。只不過有些國家意識到這種“帝國之后”的難題,或主動、或被動地發(fā)揮“統(tǒng)治的技藝”,尋求走出困境的最佳方案,有些國家仍然沉醉在開疆拓土、“人滾地留”的舊日帝國迷夢之中。這種好大喜功的迷夢固然可以憑借武力一時得逞,但假以時日,恐怕會遭遇更加猛烈的反噬。相比之下,將問題擺在桌面上談,或許短期之內(nèi)火藥味十足,但長期來看才有和平轉(zhuǎn)軌、自我解套的希望。

當(dāng)?shù)貢r間2024年5月16日,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停車場里被燒毀的汽車。
新喀里多尼亞:歷史背景與現(xiàn)實(shí)出路
法國人往往自稱為“六邊形國家”,這指的是從大西洋到地中海、從英吉利海峽到阿爾卑斯山、從比利牛斯山到萊茵河之間的六邊形區(qū)域。但事實(shí)上,除了這個“本土法國”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海外法國”,包括瓜德魯普、馬提尼克、法屬圭亞那、留尼汪、馬約特、圣巴泰勒米、圣馬丁、克利珀頓、瓦利斯和富圖納、圣皮埃爾和密克隆、法屬波利尼西亞、新喀里多尼亞、法屬南部和南極領(lǐng)地等一共13處海外領(lǐng)土。因此確切說來,法國不僅僅是一個“歐陸國家”,也是一個“全球國家”,在非洲、美洲、大洋洲和南極洲均有立足之地,并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戰(zhàn)略利益(例如在法屬波利尼西亞進(jìn)行核試驗(yàn))和經(jīng)濟(jì)利益(例如各地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
在所有這些海外領(lǐng)土中,位于大洋洲的新喀里多尼亞島屬距離法國本土最遠(yuǎn)之列(約16740公里)。1774年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發(fā)現(xiàn)該島,并以蘇格蘭的拉丁語名稱“喀里多尼亞”來為此地命名。1853年,新喀里多尼亞成為法國殖民地。從同一時期起,來自英法意等國的歐洲人開始向此地殖民,其中除大批罪犯之外,也包括在國內(nèi)生計無著的下層民眾、以及因宗教原因背井離鄉(xiāng)的少數(shù)派群體等。
新喀里多尼亞分為南部省、北部省和洛亞蒂群島省,首府為努美阿(Nouméa)。目前島上人口約27萬,其原住民(美拉尼西亞人的一個分支)被稱為卡納克人(kanak)——資深足球迷可能還記得1998年為法國捧回大力神杯的那屆功勛球員中,有個一頭小辮、球風(fēng)彪悍的卡倫布(Christian Karembeu),這便是卡納克族群能夠被世界所矚目的為數(shù)不多的高光人物之一。
在新喀里多尼亞的總?cè)丝谥校{克人約占四成,但在北部省和洛亞蒂群島省占據(jù)顯著優(yōu)勢。這種人口分布也同時伴隨著地域和觀念上的分裂態(tài)勢:細(xì)長如蠶的新喀里多尼亞島被攔腰一分為二:歐洲移民占據(jù)主體、經(jīng)濟(jì)上更加富庶的南部省(包括首府努美阿在內(nèi))傾向留在法國版圖內(nèi),而卡納克人聚居、經(jīng)濟(jì)上處于更不利境況的北部省和群島省則傾向獨(dú)立。
卡納克人與歐洲移民的沖突,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一個歷史遺留難題:在19世紀(jì)中期歐洲人開始向新喀里多尼亞大規(guī)模移民之后不久,卡納克人就曾經(jīng)因?yàn)椴粷M歐洲移民侵吞土地、濫征勞力,于1878年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起義,兩方都蒙受了慘重傷亡。一戰(zhàn)期間的1917年,新喀里多尼亞又爆發(fā)一系列規(guī)模較小的騷亂。而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其中不乏1968年學(xué)運(yùn)影響的因素),卡納克人的獨(dú)立意識再度高漲,出現(xiàn)了“紅頭巾”和“1878年團(tuán)體”等分離主義組織。這些組織逐漸匯聚,于1979年建立了“獨(dú)立陣線”。而幾乎與此同時,忠于法國的移民群體也建立了“喀里多尼亞留在共和國聯(lián)盟”(RPCR)。兩大陣營進(jìn)入成建制對抗的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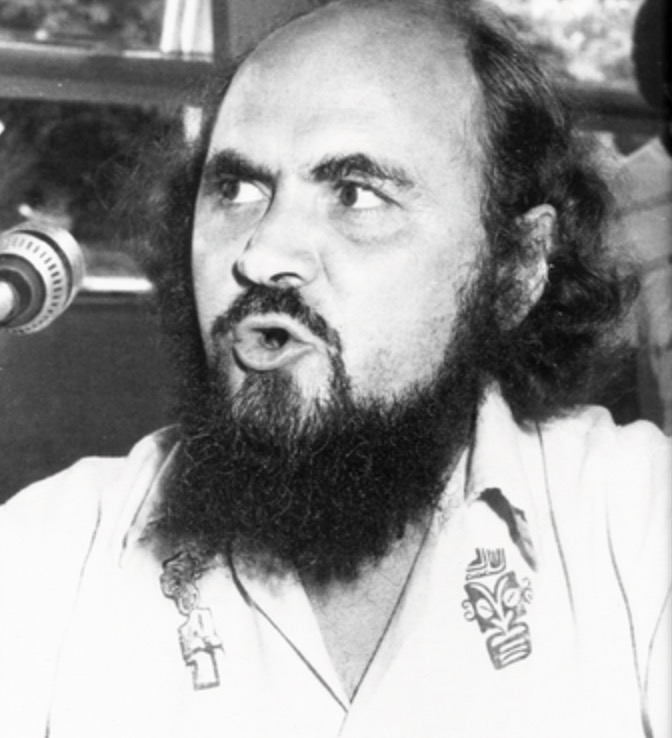
德克萊爾克(Pierre Declercq)
1981年,卡納克獨(dú)立運(yùn)動領(lǐng)導(dǎo)人之一德克萊爾克(Pierre Declercq)遇刺身亡,拉開了一段動蕩時期的序幕。1984年,“獨(dú)立陣線”解散,并重組為“卡納克與社會主義全國解放陣線”(FLNKS),其路線進(jìn)一步激進(jìn)化。在1984到1988年間,新喀里多尼亞爆發(fā)了一連串沖突事件,獨(dú)派和統(tǒng)派各自建立了民兵和媒體,彼此動用暴力手段,互有人員傷亡,多名獨(dú)派領(lǐng)袖及其家人在沖突中喪生,整個新喀里多尼亞陷入“準(zhǔn)內(nèi)戰(zhàn)”的局面。
為了走出困境,當(dāng)時的法國社會黨政府在總理法比尤斯和新喀里多尼亞事務(wù)部長皮薩尼(Edgard Pisani)的推動下,提出了“法比尤斯-皮薩尼地位”作為解決方案,試圖賦予新喀里多尼亞更多自治權(quán)。但在1986年的法國議會選舉中,右派獲得多數(shù),這不僅導(dǎo)致在國內(nèi)政治中出現(xiàn)了著名的“左右共治”,也連帶影響到海外政策。隨后上臺的希拉克總理的態(tài)度變得強(qiáng)硬,新提出的“龐斯一號地位”在此前“法比尤斯-皮薩尼地位”基礎(chǔ)上有所降級,而且計劃將隨后進(jìn)行的地方公投門檻限定在僅居住三年即獲得投票資格(FLNKS要求僅卡納克人有投票權(quán))。在這一背景下,法國政府于1987年9月在新喀里多尼亞舉行自決公投,但FLNKS予以抵制。最終,這場公投以高達(dá)98.3%的贊成比例留在法國,但由于獨(dú)派的抵制,導(dǎo)致缺乏實(shí)質(zhì)意義。
1987年公投之后,右派政府放軟身段,提出了“龐斯二號地位”,對地方行政機(jī)構(gòu)進(jìn)行改革,加大自治力度。但獨(dú)派對此并不買賬,與此同時,首府郊區(qū)一名卡納克少年被憲兵開槍打死,再度激化了局勢。1988年四五月間,暴力沖突達(dá)到了頂點(diǎn):4月22日,獨(dú)派分子攻擊了烏維亞島(Ouvéa)的憲兵隊(duì),導(dǎo)致四名憲兵死亡,27人被扣作人質(zhì)。獨(dú)派提出廢除地區(qū)選舉結(jié)果、從島上撤出憲兵隊(duì)等訴求,雙方未能達(dá)成一致,5月5日,法國當(dāng)局發(fā)動強(qiáng)攻,19名獨(dú)派分子喪生,憲警方面也有兩人死亡。
烏維亞島的悲劇正好發(fā)生在1988年大選期間,它不僅讓統(tǒng)獨(dú)雙方看到了暴力的可怕前景,而且也促使連任的密特朗總統(tǒng)盡快采取行動。與此同時,由于議會選舉中重新獲得多數(shù),社會黨政府?dāng)[脫了“左右共治”,贏得了更大的轉(zhuǎn)圜余地。6月26日,統(tǒng)獨(dú)兩派和法國政府簽署了“馬提尼翁協(xié)議”,并由8月19日的“烏蒂諾協(xié)議”加以補(bǔ)充,隨后由同年11月的全法范圍公投所批準(zhǔn)。相關(guān)協(xié)議旨在在不同族群之間公平分配權(quán)力,擴(kuò)大自治權(quán),推行減輕不平等的經(jīng)濟(jì)政策來促進(jìn)就業(yè)和改善基礎(chǔ)設(shè)施,并在十年后組織公投。
作為雙方妥協(xié)的產(chǎn)物,“馬提尼翁協(xié)議”結(jié)束了持續(xù)多年的混亂和暴力局面(包括對立族群和憲警在內(nèi),整個1980年代的暴力沖突導(dǎo)致近百人死亡)。然而,它作為妥協(xié)方案,注定無法讓每一方都心滿意足。盡管在公投中,無論是在全法還是喀島范圍,協(xié)議都獲得多數(shù)贊成,但在統(tǒng)派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南部省,高達(dá)67%的選民投票反對;而在獨(dú)立派這一邊,這場妥協(xié)也令激進(jìn)分子甚為不滿。協(xié)議簽署還不到一年,在獨(dú)立運(yùn)動中享有卓著聲譽(yù)、曾一度出任卡納克臨時獨(dú)立政府領(lǐng)導(dǎo)人的蒂比奧( Jean-Marie Tjibaou)就被一名激進(jìn)獨(dú)立分子刺殺身亡。當(dāng)對立雙方領(lǐng)導(dǎo)人審時度勢、秉持理性,找到一條制度性解決出路、將局勢從全面內(nèi)戰(zhàn)邊緣拉回來之后,當(dāng)事人卻以自己的生命獻(xiàn)祭,成為這段混亂年代的一出悲劇。
三次公投,以及……第四次?
在1988年“馬蒂尼翁協(xié)議”的框架下,喀島對立雙方經(jīng)過多年談判,于1998年簽署“努美阿協(xié)議”。據(jù)此,法國政府在當(dāng)?shù)乇A魢馈踩⑺痉ê拓泿蓬I(lǐng)域等主權(quán)職能,而將除此以外的其他管理職能移交給地方政府,而且這種權(quán)力轉(zhuǎn)移是“不可逆”的,換句話說,中央政府不能隨心所欲地收回已經(jīng)轉(zhuǎn)讓給這個萬里之外島嶼的權(quán)能,如果要采取“倒退”措施,必須同時經(jīng)過公投批準(zhǔn)和修憲程序。
“努美阿協(xié)議”確立了公投“三步走”的框架,規(guī)定在2014年到2018年間舉行第一次公投,就“是否希望新喀里多尼亞實(shí)現(xiàn)完全主權(quán)并獨(dú)立”來向選民征求意見,如果第一次公投的結(jié)果是否定的,隨后還可以舉行第二次公投;倘若仍然被否決,那么將舉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公投,來決定這個島嶼的最終命運(yùn)。
2018年11月4日,新喀里多尼亞舉行第一次獨(dú)立公投,結(jié)果顯示反對票比例占到56.67%;在2020年10月4日的第二次公投中,反對票比例略有下降,但仍占53.3%,獨(dú)立動議再度被否決;2021年12月21日的第三次公投中,獨(dú)派予以抵制,理由是新冠疫情仍然肆虐,卡納克族群需要更多時間來哀悼親人,但統(tǒng)派則認(rèn)為是前者已經(jīng)預(yù)見到這一次公投很可能仍將以失敗告終,因此使出緩兵之計。由于抵制因素的存在,此次公投導(dǎo)致贊成獨(dú)立的比例僅有3.5%,反對票則高達(dá)96.5%,幾乎是1987年自決公投的翻版。

當(dāng)?shù)貢r間2018年10月30日,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市民身穿傳統(tǒng)服裝,要求新喀里多尼亞脫離法國獨(dú)立。
根據(jù)“馬提尼翁協(xié)議”和“努美阿協(xié)議”,新喀里多尼亞實(shí)行“特別選民團(tuán)體”制度。具體而言,在全國性的總統(tǒng)和議會選舉以及歐洲議會選舉中,當(dāng)?shù)厮械某赡赀x民均可投票,在這一點(diǎn)上與法國本土并無二致,但在事關(guān)本地的省級選舉中,只有卡納克人和1998年時已經(jīng)定居在當(dāng)?shù)氐臍W洲移民(及其子女)有權(quán)投票。
按照原本設(shè)想,在“努美阿協(xié)議”之后,統(tǒng)獨(dú)雙方應(yīng)當(dāng)和中央政府一道,協(xié)商出未來制度演進(jìn)的方向,但雙方在這一問題上始終無法達(dá)成一致,于是“努美阿協(xié)議”所規(guī)定的“特別選民團(tuán)體”制度便一直維持下來。但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問題愈發(fā)嚴(yán)重,當(dāng)年被排斥在“特別選民團(tuán)體”門檻之外的歐洲移民,在當(dāng)?shù)厣疃嗄陼r間,卻一直未能獲得對本地事務(wù)的發(fā)言權(quán)。根據(jù)法國官方2023年的統(tǒng)計,有42596名選民有權(quán)在全國性選舉中投票,卻無權(quán)在地方性選舉中發(fā)聲,這部分人大約占到當(dāng)?shù)爻赡旯竦?0%之多。
面對這種顯著的失衡現(xiàn)象,喀島統(tǒng)派和法國政府認(rèn)為選舉資格標(biāo)準(zhǔn)必須進(jìn)行修改,于是政府提出一項(xiàng)憲法修正案,計劃將出生在喀島或者已經(jīng)在當(dāng)?shù)厣畛^十年,并且已在全國性選舉名單登記在冊的移民納入到選民團(tuán)體中,這意味著將在原有的“特別選民團(tuán)體”中增加大約2.5萬名新選民。
相關(guān)憲法修正案于4月2日得到參議院批準(zhǔn),5月15日又在國民議會(眾議院)通過。馬克龍?jiān)媱澰?月中旬召開議會兩院全會,完成全部修憲程序。正是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爆發(fā)了今年5月的大規(guī)模暴力沖突。因?yàn)榭{克人看到,一旦修憲完成,這2.5萬新選民(其中絕大部分傾向留法)匯入全體選民之中,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通過公投實(shí)現(xiàn)獨(dú)立路徑,將會被徹底堵死。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龍為了平息局勢,表示可以動用國家元首權(quán)力發(fā)動公投,這意味著將突破“努美阿協(xié)議”所規(guī)定的“三次公投”框架,將舉行第四次公投來“一錘定音”。然而發(fā)動公投遠(yuǎn)比解散議會、提前大選要來得復(fù)雜,它本身不是簡單地涉及說“是”或者說“否”的問題,涉及統(tǒng)獨(dú)雙方如何完成復(fù)雜的政治博弈,為新的公投劃出共同底線,否則一旦獨(dú)派再度抵制,局面將不可避免地重新陷入到死胡同中。
兩種“帝國”話語
經(jīng)歷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去殖民化運(yùn)動的洗禮之后,在當(dāng)下無論中西語境中,“帝國”似乎都已經(jīng)成了一個惡名昭彰的詞匯,往往同“暴力”、“霸權(quán)”、“奴役”等惡行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人耳熟能詳?shù)牧袑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更讓這個詞帶上某種邪惡氣息。
但在西方語境中,“帝國”本身具有既關(guān)聯(lián)、又分殊的雙重含義。根據(jù)美國學(xué)者克里尚·庫馬爾(Krishan Kumar)的考證,拉丁語中imperium的含義,從羅馬共和向羅馬帝國轉(zhuǎn)折之際發(fā)生了重大改變,并成了“此后混亂的根源”:一方面,它被用于指代羅馬高級官員經(jīng)人民賦權(quán)而掌握的權(quán)力(尤其是在軍事意義上),并由此逐漸演化為在特定地域當(dāng)中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進(jìn)而滲入歐洲各民族的政治語匯當(dāng)中(例如1534年的《最高權(quán)威法令》聲稱“英格蘭就是帝國”,并不意味著亨利八世就此稱帝,而是旨在確立英國國王在宗教領(lǐng)域中的至高權(quán)威,并排除教廷的干涉)。另一方面,imperium從羅馬人民的統(tǒng)治權(quán),轉(zhuǎn)變成皇帝統(tǒng)治的行省或領(lǐng)土,并有了“管轄其生活著不同族群的廣闊領(lǐng)土”的意義,這在羅馬帝國、神圣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都有充分體現(xiàn)。
而在法國語境中,如果提到“帝國”,自然讓人聯(lián)想起近現(xiàn)代歷史上的兩段“帝國時代”:一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侖帝國”,即1802-1814年的第一帝國;二是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效仿其叔父,于1852-1870年間建立的第二帝國。這兩個帝國給后世留下的最顯著特征,就是高度的權(quán)力集中,乃至于達(dá)到“一人之治”。這種獨(dú)裁高度依賴軍事力量,以政變肇始,以兵敗告終。1814年的滑鐵盧戰(zhàn)役和1870年的色當(dāng)戰(zhàn)役,讓兩個帝國的宏圖霸業(yè)隨之灰飛煙滅。
然而,在這種正式命名的帝國之外,法國還具有另一重“帝國”屬性。這種意義的”帝國“同法國的海外征服和擴(kuò)張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具體而言,從16世紀(jì)中期到20世紀(jì)中期這四百年間,法國在海外建立了兩個殖民帝國:從1534年到1763年間為“第一殖民帝國”,這一時期法國的主要擴(kuò)張方向是北美,建立了地域廣大的“新法蘭西”(今天已經(jīng)很難想象,當(dāng)年北美土地上的頭號強(qiáng)權(quán)竟然是法國),并在加勒比海、印度洋和非洲建立了多處殖民地和貿(mào)易據(jù)點(diǎn),然而法國的擴(kuò)張遇到了英國的強(qiáng)力競爭,處處受制于人,并在七年戰(zhàn)爭之后喪失了絕大部分殖民地,1763年《巴黎條約》的簽訂,宣告了“第一殖民帝國”基本歸于失敗。
此后,法國陷入了革命和戰(zhàn)爭的漩渦之中,1803年拿破侖將路易斯安那出售給新生不久的美國,標(biāo)志著法國力量在北美進(jìn)一步退出,而復(fù)辟的波旁王朝也無暇開拓海外。1830年七月王朝的登場,尤其以同年占領(lǐng)阿爾及爾為標(biāo)志,開啟了“第二殖民帝國”。法國的擴(kuò)張重心由此轉(zhuǎn)向了非洲和印度支那,但同時繼續(xù)經(jīng)營前一個殖民帝國所殘存的成果(正是在這一時期,新喀里多尼亞被納入到帝國版圖之內(nèi))。但在二戰(zhàn)后的去殖民化浪潮中,法國曾經(jīng)苦心經(jīng)營的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反過來成了這一體系最大命門所在,1954年奠邊府戰(zhàn)役的失敗導(dǎo)致法國勢力退出中南半島,1962年的《埃維昂協(xié)議》終結(jié)了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同時也標(biāo)志著“第二殖民帝國”的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第二殖民帝國”這一階段,橫亙了七月王朝、第二共和、第二帝國、第三共和、維希體制、第四共和、第五共和等性質(zhì)截然不同的政體。這就造成了一種吊詭現(xiàn)象:不僅像托克維爾這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竟然同時也是一個殖民主義者,而且“帝國”更可以與“共和”并行不悖,甚至在第三共和這樣一個共和制最終決定性地戰(zhàn)勝君主制的時期,政治人物卻毫不避諱地使用“帝國”來指稱法國的海外擴(kuò)張。
帝國:統(tǒng)治的技藝
在庫馬爾看來,就西方世界而言(甚至包括奧斯曼帝國在內(nèi)),羅馬乃是后世所有帝國的源頭和典范。而在這些后繼帝國中,法蘭西帝國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謂最得羅馬的衣缽真?zhèn)鳎阂环矫妫冀K以文明和教化自許為對外擴(kuò)張的使命,在第一殖民帝國時期體現(xiàn)為傳播宗教福音和絕對君權(quán),經(jīng)歷革命洗禮之后則變成世俗化的人權(quán)、自由、平等觀念,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羅馬帝國的自許形成呼應(yīng);與此相關(guān)的另一方面是,如果羅馬的文明使命意味著“羅馬化”的話,那么法國的使命便意味著“法國化”,因此和更加接受差異性的其他帝國(尤其是同時期的英帝國)相比,法帝國對同化理念情有獨(dú)鐘,“盡一切可能將帝國塑造為他們自身”。
在法權(quán)制度上,“同化”意味著打破族群藩籬、開放公民權(quán)、法律在本土和殖民地一體遵行、殖民地代表有權(quán)進(jìn)入全國性議會,等等。這種同化政策有時達(dá)到了相當(dāng)刻板的程度,例如殖民地學(xué)校一律使用法語教學(xué),非洲的孩子們學(xué)習(xí)的是“我們的祖先高盧人”,總督獨(dú)攬殖民地行政大權(quán),并聽命于巴黎,土著族群領(lǐng)袖幾乎沒有什么發(fā)言權(quán)。這種政策和英國在英屬殖民地推行的“間接統(tǒng)治”模式形成了鮮明對照。
然而,這兩種模式事實(shí)上都不免遭遇各自的困境:對于英國模式來說,盡管在殖民地底層不乏空間和彈性,但本地精英在上升通道中很快遇到天花板(最典型者如印度“圣雄”甘地的經(jīng)歷),難免萌生異志;而對于法國模式來說,只要本地精英接受整套法國文化(以法語為媒介),且表現(xiàn)達(dá)到相當(dāng)水準(zhǔn),那么不僅可以獲得公民權(quán),而且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大門是敞開的。1946年的《拉明·蓋耶法》將公民權(quán)賦予所有法國海外領(lǐng)地居民(某種程度上讓人聯(lián)想起公元212年擴(kuò)展羅馬公民權(quán)的《卡拉卡拉法令》)。一個更加著名的例子是,曾提出“黑人性”概念的塞內(nèi)加爾首任總統(tǒng)桑戈?duì)枺↙éopold Sédar Senghor),前半生基本是一份法國精英履歷:他不僅在巴黎接受教育,用法語寫詩,此后還一路出任法國議員及部長。即便成為獨(dú)立后的塞內(nèi)加爾總統(tǒng),他仍然希望塞內(nèi)加爾留在法國版圖內(nèi),卸任后還當(dāng)選了法蘭西學(xué)院院士。
然而,正是在公民權(quán)問題上,新喀里多尼亞對這種同化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在這里,民族原則和民主原則發(fā)生了碰撞。在傳統(tǒng)的帝國語境中,公民權(quán)很大程度上是宗主國施加羈縻的手段之一。然而在新喀里多尼亞,公民權(quán)面臨著一種“反向擴(kuò)展”的困境:獨(dú)派將擴(kuò)大選舉權(quán)看成是“再殖民化”的手段,以合法或暴力手段予以抵制。被剝奪地方性選舉權(quán)(作為完整意義上公民權(quán)的最重要部分)的不是傳統(tǒng)上處于弱勢的土著族群,而是從宗主國輸入當(dāng)?shù)氐囊泼袢后w。但在追求普遍性、均一性的法式政治文化中,剝奪弱勢一方的公民權(quán)尚難以自圓其說,更何況是與原宗主國同文同種的移民群體?自1998年“努美阿協(xié)議”以來,當(dāng)?shù)財?shù)萬移民在20余年間一直被剝奪地方選舉權(quán),無論是移民群體還是中央政府,都認(rèn)為不能再讓這種狀況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才有了此前緊鑼密鼓、只差臨門一腳的修憲進(jìn)程。
為什么新喀里多尼亞的公民權(quán)會面臨這種“反向擴(kuò)展”困境?從具體的制度層面來看,答案顯而易見,為了盡快從暴力漩渦中擺脫出來,1988年“馬提尼翁協(xié)議”和1998年“努美阿協(xié)議”對卡納克人作出了顯著讓步,而代價便是移民群體的權(quán)利暫時受損。而在此后的政治協(xié)商中,卡納克人出于對未來徹底淪為少數(shù)的憂懼,封鎖了逐步擴(kuò)大移民投票權(quán)利的通道。
而從觀念層面上來看,在經(jīng)歷了非殖民化浪潮之后,法國已經(jīng)無法再用此前殖民帝國時期的暴力手段來達(dá)成目的,它寧可“以大事小”,用一種更謹(jǐn)慎的方式來推進(jìn),因?yàn)榇饲暗臅r代潮流和歷史經(jīng)驗(yàn)無不顯示出,這是一片暗潮涌動、充滿風(fēng)險的海域。
就此而言,1998年“努美阿協(xié)議”的序言或許可以作為一個例證,顯示出新喀里多尼亞問題可能具有的開放式結(jié)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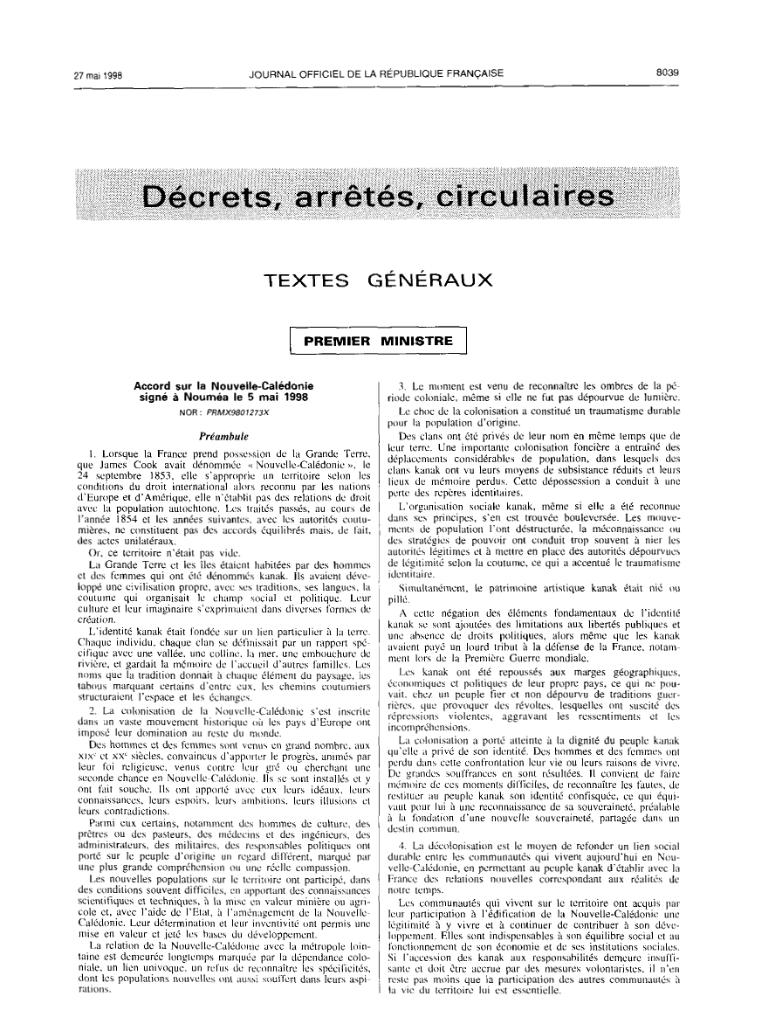
1998年“努美阿協(xié)議”
“努美阿協(xié)議”承認(rèn)了一種“雙重合法性”:一方面,1853年法國將新喀里多尼亞劃歸自己的殖民地,本質(zhì)上是“單方行為”;而卡納克人早已居住在此,并以其傳統(tǒng)、語言和習(xí)俗塑造了自身的文明;另一方面,在19-20世紀(jì)大規(guī)模殖民活動中來到這里的移民,帶來了科學(xué)技術(shù)知識、參與了礦業(yè)和農(nóng)業(yè)發(fā)展,并為將來的發(fā)展打下基礎(chǔ)。這意味著,協(xié)議盡量試圖同時兼顧兩大族群,不抹殺任何一個族群的貢獻(xiàn),以創(chuàng)造“共同命運(yùn)”——這正是協(xié)議所著力強(qiáng)調(diào)的概念。
在這一前提下,協(xié)議承認(rèn)殖民化沖擊給原住民造成了持久的創(chuàng)傷,后者被剝奪土地、流離失所,并導(dǎo)致喪失身份標(biāo)記,其社會組織遭到破壞,藝術(shù)遺產(chǎn)被掠奪,盡管卡納克人為保衛(wèi)法國付出了沉重代價(尤其一戰(zhàn)期間),但其公共自由和政治權(quán)利仍然受到限制,他們在各方面都被邊緣化,這催生了叛亂、鎮(zhèn)壓和怨恨。協(xié)議呼吁“記住這些艱難時期、承認(rèn)錯誤、恢復(fù)卡納克人民被剝奪的身份”,而這意味著——對于跨文化、跨語境的讀者來說或許難以理解——承認(rèn)卡納克人的“主權(quán)”,以此作為確立的一種“新的主權(quán)”的前提,而這種“新的主權(quán)”應(yīng)當(dāng)以分享“共同命運(yùn)”為特征。殖民時代已成為過去,現(xiàn)在是“分享”與“重新平衡”的時代,未來則應(yīng)當(dāng)是在“共同命運(yùn)”中重塑身份的時代。
不難看出,協(xié)議并沒有試圖用一種直截了當(dāng)?shù)姆绞絹頌閺?fù)雜的新喀里多尼亞問題一錘定音,毋寧說它提出了一個開放式的模糊愿景:新喀里多尼亞并不是非獨(dú)立不可,也不是非留在法國不可,當(dāng)務(wù)之急是矯正殖民主義的惡果、承認(rèn)并恢復(fù)卡納克人的身份,在這一基礎(chǔ)上決定未來走向,包括“與法國分享主權(quán)”乃至“通向完全主權(quán)的道路”。換言之,或許終有一天,新喀里多尼亞將會實(shí)現(xiàn)獨(dú)立(但這仍然要通過公投的程序性手段來落實(shí)),而法國也正在為此做好體面退場的準(zhǔn)備,在這種“帝國余暉”中,重要的不再是鎳礦帶來的經(jīng)濟(jì)利益,或者向地球另一端投射力量的戰(zhàn)略格局,而是某種“文明教化”的復(fù)歸——作為當(dāng)初對外殖民擴(kuò)張時所秉持的理念,如今正在反過來映射在昔日殖民者自己的身上。
作為鏡像的新喀里多尼亞問題
相比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沖突(例如1980年代),2024年5月間新喀里多尼亞的局勢其實(shí)并沒有達(dá)到暴力高點(diǎn),但6月下旬以來暴力復(fù)燃,再次顯示出這一局面的難解特性。無論獨(dú)派領(lǐng)袖是否會被定罪以及何時能恢復(fù)自由,都無法掩蓋更大的問題本身:“努美阿協(xié)議”規(guī)定的三次公投,或者馬克龍所允諾的“第四次公投”,都只是程序性解決方案,最終面對的是經(jīng)久不衰的身份政治沖動,而追求自決(甚至獨(dú)立),是每一個位于帝國邊陲、稍具規(guī)模的族群的近乎本能反應(yīng)。更何況,每一代人都無法為下一代人完成“終極立法”,即便下次公投仍然決定留在法國版圖內(nèi),再過二三十年后,新一代卡納克人是否甘心服從于前人投票的束縛,仍將是未定之?dāng)?shù)。這對維持一個“準(zhǔn)帝國”不至于分崩離析的統(tǒng)治技藝,提出了極大的挑戰(zhàn)。
正如西方學(xué)者所不免流露出的某種“西方中心主義”一樣(例如傾向于認(rèn)為一切帝國都沿襲自羅馬),東方人的“帝國”圖景,往往也難以擺脫東方式的窠臼,尤其是秦制的痕跡,它本能地會強(qiáng)調(diào)帝制中“口含天憲、言出法隨”的威權(quán)和專斷一面,但缺乏對多元化及自由的體認(rèn),更容易流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觀念。
作為對照,英國學(xué)者史蒂芬·豪(Stephen Howe)曾指出,“至少部分現(xiàn)代帝國……有很多被人遺忘的可貴品質(zhì)。帝國為臣民提供了穩(wěn)定、安全和法律保障。帝國試圖約束可能使其臣民變得殘忍的族群間的敵意以及宗教間的對立,在鼎盛狀態(tài)下還會嘗試超越這種敵對關(guān)系。統(tǒng)治階層中的貴族,比起后來更加民主的體制中的領(lǐng)導(dǎo)者,更信奉自由、人性和普遍的價值觀。”
以新喀里多尼亞為樣本,回溯法國在“后帝國時代”的成敗得失,顯然并不是為“法國時刻”獻(xiàn)策建言,毋寧說是以此來作為自我審視的鏡像,看自己作為一個想象中的“帝國”,是否更有能力提供穩(wěn)定、安全和法律保障;是更能約束、還是更放縱底層的敵意和對立;是更信奉、還是更敵視自由與人性?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