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貞德:從一則高僧助產的故事談起
唐代(618-907)中葉的王燾(約670-755)在其醫學名著《外臺秘要》中收錄了一則婦女分娩、高僧助產的故事。故事由名為“崔氏”的學者閱讀“巒公”的著作破題,接著便以巒公第一人稱敘述,描述一位名叫慶的男士,因媳婦即將臨盆,憂慮之余,前來求助,不僅要求醫生開“滑胎方”助產,更力邀他一同回家坐鎮。故事原文如下:
《崔氏》:……余因披閱巒公《調氣方》中,見巒公北平陽道慶者,其一妹二女,并皆產死,有兒婦臨月,情用憂慮,入山尋余,請覓滑胎方。余報言少來多游山林,未經料理此事,然當為思量,或應可解。慶停一宿。余輒憶想,畜生之類,緣何不聞有產死者,淫女偷生,賤婢獨產,亦未聞有產死者。此當由無人逼佐,得盡其分理耳。其產死者,多是富貴家,聚居女婦輩,當由兒始轉時覺痛,便相告報,旁人擾擾,令其驚怖,驚怖蓄結,生理不和,和氣一亂,痛切唯甚。旁人見其痛甚,便謂至時,或有約髻者,或有力腹者,或有冷水噀面者,努力強推,兒便暴出,蓄聚之氣,一時奔下不止,便致運絕,更非它緣。至旦,以此意語慶,慶領受無所聞,然猶苦見邀向家,乃更與相隨,停其家十余日。日晡時見報,云:兒婦腹痛,似是產候。余便教屏除床案,遍一房地,布草三四處,懸繩系木作衡,度高下,令得蹲當腋,得憑當衡,下敷慢氈,恐兒落草誤傷之。如此布置訖,令產者入位,語之坐臥任意,為其說方法,各有分理,順之則全,逆之則死,安心氣,勿怖強。此產亦解人語。語訖閉戶,戶外安床,余共慶坐,不令一人得入。時時隔戶問之何似,答言小痛可忍。至一更,令爛煮自死牝雞,取汁作粳米粥,粥熟,急手攪,使渾渾適寒溫,勸令食三升許。至五更將末,便自產。聞兒啼聲,始聽人入。產者自若,安穩不異。云:小小痛來,便放體長吐氣,痛即止。蓋任分和氣之效也。慶問:何故須食雞肉汁粥?答云:牝雞性滑而濡,庶使氣滑故耳。問:何不與肉?答云:氣將下,恐肉不卒消為妨。問:何故與粥?答云:若饑則氣上,氣下則速產,理不欲令氣上故耳。慶以此為產術之妙,所傳之處,無不安也。故知巒公隱思,妙符神理。然則日游反支之類,復何豫哉?但以婦人怯弱,臨產驚遽,若不導以諸法,多恐志氣不安。所以簡諸家方法,備題如左,其間取舍,各任量裁。
這則故事,應當是現存文獻中,描寫婦女生產,最早也最完整的記錄了。其中身懷絕技、成功助產的“巒公”,名為曇巒(476-542),是北魏時代的高僧。據說他年輕時,為尋求長生不老仙方,曾遠赴南方的蕭梁王朝(502-557),企圖拜見著名的道士陶弘景(456-536)。不過,后來經佛教高人指點,決定解脫生死,因此北返之后,便隱居山林,不再尋尋覓覓。盡管如此,由于他“調心練氣,對病識緣”,技術精湛,名滿京城,大概像慶這樣的求助者絡繹不絕,因此干脆寫一本《調氣方》,將一生練氣治病的心得發表示人。

婦人乳兒圖
《調氣方》顯然流傳多時,一百五十年后,唐代的戶部尚書崔知悌,晚年“述職孤城,空莊四絕,尋醫訪道”,便曾接觸曇巒之作,并將上述故事收錄在自己編輯的《崔氏纂要方》中。崔知悌讀了曇巒的助產事跡,甚感佩服,大嘆“巒公隱思,妙符神理!”然而,話鋒一轉,突然發問:“然則日游反支之類,復何豫哉?”既然巒公的調氣方如此有效,又何必回避“日游神”“反支日”之類的鬼神禁忌呢?接著他又自問自答:“但以婦人怯弱,臨產驚遽,若不導以諸法,多恐志氣不安。”實在是因為婦人膽怯懦弱,臨到生產,容易驚懼,假使不教導她們各種方法,恐怕她們情緒不穩!于是崔知悌說,除了曇巒調氣助產的技術之外,他還整理了各家的禁忌說法,收錄在后面,請讀者看完調氣助產的故事之后,再各依所需,選擇采用。
遺憾的是,盡管曇巒洋洋自得,崔知悌大表贊嘆,他二人的著作,不論是《調氣方》或是《崔氏纂要方》,如今都已失傳。我們今日之所以能讀到這則生產故事,必須歸功于王燾。王燾生活在公元七世紀末、八世紀初,約當武則天的時代。他收集自古以來的重要醫藥方書,加以整理、摘要,并且注明征引文獻的原始出處,編成一部《外臺秘要》。《外臺秘要》共四十卷,其中第三十三和三十四卷,收錄了婦女懷孕、產育、保健等相關知識。上述生產故事,便在第三十三卷《產乳序論》之中。而在故事之后,王燾羅列“崔氏年立成圖法”,依照產婦的年紀,說明回避各種鬼神禁忌的方法,應當就是前面崔知悌所說“簡諸家方法,備題如左”的內容。
從以上的生產故事可以得知,這位名叫慶的男士,曾經有三位親人因難產而過世,可見分娩危險,九死一生,充滿難以預估的變數。如今兒媳即將臨盆,慶為了減少風險、掌握生機,決定尋求醫藥專家的協助。而他所拜訪的能人,既不是在市街上掛招牌、貼廣告,為人看病開方的醫生,也不是鄰里之間經驗老到、甚具口碑的產婆,反而是隱居山林卻名滿天下的曇巒。對慶來說,醫學高僧所能提供的,小自滑胎藥方,大至親自出診,應當對婦女生育之事了然于心,具備一套全面性的健康照顧措施。曇巒到了產家,指導布置產房,挪出空間之后,并沒有讓產婦躺下待產,而是在屋梁上“懸繩系木作衡”,以衡木撐住產婦的胳肢窩,讓她以半蹲的姿勢生孩子。一個人半蹲地生產,應該非常辛苦,曇巒卻不讓任何人進去協助,是因為將難產歸咎于“聚居女婦輩”,造成擾攘驚怖,因此標榜由產婦一人自然順生。由崔知悌的評論看來,當時存在的助產知識,除了巒公的調氣法之外,也包括了“日游反支”之類的禁忌。不過,崔知悌認為這類知識之所以聊備一格,純粹是因為“婦人怯弱”,不能不設法安定她們的心神。顯然,在高僧和士大夫這兩位醫學專家的眼中,不論是臨月的產婦,或是助產的女流之輩,都各有問題,沒有男性醫生的幫忙,還真不行呢!
然而,醫學高僧的實際助產經驗恐怕不多,他最初被慶問到關于難產死亡的事情時,所能想起的,竟然是“畜生”“淫女偷生”“賤婢獨產”之類的傳聞,沒有什么親自參與觀察的資料。反倒是他批評助產婦女的文字,透露了兩個歷史事實。第一,助產的主要幫手是女性,而不是男醫生。她們可以支持半蹲的產婦,讓她安心生孩子,而不必掛在衡木上。第二,助產婦女可能采取的方式,包括幫產婦按摩(力腹),可能是減少疼痛,也可能用來協助胎兒往下運行;倘若產婦暈了過去,她們也可能拿冷水潑她(以冷水潠面),好讓她蘇醒。不論如何,這些方法都得不到曇巒的青睞,反而是這名獨自生產的女士,看來挺能領會他的教導,令他頗為嘉許。然而,我們看看這位女士,她形容自己以“放體長吐氣”的方式來消除陣痛,顯然相當熟練與穩健,不禁令人懷疑,她的生產知識恐怕不是到了分娩當下,才現學現賣的,應該是早有準備,另有來源。說不定她在懷孕的過程中,就不斷吸收新知,而她所請教的對象,也可能包括曇巒所批評的那些女性親友或助產人士!
女性雖然具備醫藥知識,卻很少寫作發表,反倒是她的生產經驗,靠男性的記載流傳了下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男士在記錄這個故事的時候,想要傳達的訊息重點,并不在于生產,而在于助產。一位僧人提供絕妙產術,經一位男性士大夫抄錄,兩人還借機對產婦和助產婦分別評論了一番。這些男性醫學專家所在意的,不是女性的生命經驗或知識形態,而是他們自己研發出來的醫學技術,對生育這一件攸關女性生死的大事,能掌握到什么程度,提供哪些幫助。他們的出發點,是保護。不過,由于他們對女性的身體和行為,逐漸發展出一套特定的看法,因此對于女性自己的經驗和知識,有時反而難以接受。于是乎,這一套保護的醫學,就難免流露出管束女性的意味。

北魏家務陶俑
從曇巒的北魏,到崔知悌的唐代,這一百多年間,正是這一套保護與管束并行的醫學逐漸形成的時代。雖然在曇巒之前,中國就已經有不少醫藥方書,針對婦女健康提供各種意見,不過,在五世紀到八世紀之間,卻不斷出現收集、整理、摘錄、分類各種醫藥文獻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男性醫學專家們,透過撰寫各式各樣的醫學著作,對女性的產育功能,從求子、懷孕、安胎、養胎,到分娩、產后保健,一步步發展出應對的措施。這些針對女性而來的醫藥知識和醫學觀點,深深地影響了傳統中國醫學對女性的看法,奠定了幾百年后中醫婦科學在宋代獨立發展的基礎。雖然這些醫書的作者都是男性,但若抽絲剝繭,努力搜尋,我們仍然可以從字里行間,找到女性經驗或女性意見的蛛絲馬跡。
事實上,由于傳統中國的性別分工方式,女性必須負責日常生活中的衛生保健。為人助產,當然需要醫藥知識。但即使是一般婦女守護家人健康,也難免涉及醫療照顧的行為。不論是母親撫育子女,女兒奉養父母,媳婦敬事舅姑,妻子服侍丈夫,甚至是家中女仆幫忙哺乳,充當奶媽,恐怕都各有一套醫藥觀點和知識。女性擔任健康照顧的工作,既符合社會倫理,也滿足自我期許,眾人不但沒有負面意見,偶爾還會加以表揚。有時,一個女人必須照顧的親屬人數超過她所能負荷的程度,她不得不有所取舍,以至于被放棄的親人,或者患病、或者喪生。即使如此,政府法令或社會輿論也未必大加撻伐,反而可能基于同情而予以寬宥。然而,倘若她跨出門庭,協助生產,或嘗試制藥,醫療病患,那么她所面臨的待遇和處境,就吉兇難卜了。有些男性醫書作者將女性研發的藥方收錄下來,有些卻主張女性參與制造藥品會令藥品無效,另有一些則如曇巒和崔知悌,認為女性介入只會帶來煩亂困擾,大可不必。然而,正是因為有男性醫學專家這些品頭論足的文字,我們才知道女性參與生老病死的活動從來不曾間斷。
王燾所收錄的這個故事,生動寫實,仿佛那位半蹲地架在衡木上的女士,就在讀者的眼前似的。然而,這個故事除了告訴我們,古代人是蹲著生孩子之外,其實還透露了許多醫療史上非常重要的性別課題,亦即女性在生育文化和健康照顧的活動中,究竟占據什么地位?又具有哪些形象?事實上,即便是蹲著生孩子這一件事,都已經足以使我們大開眼界,重新思考醫生和病人的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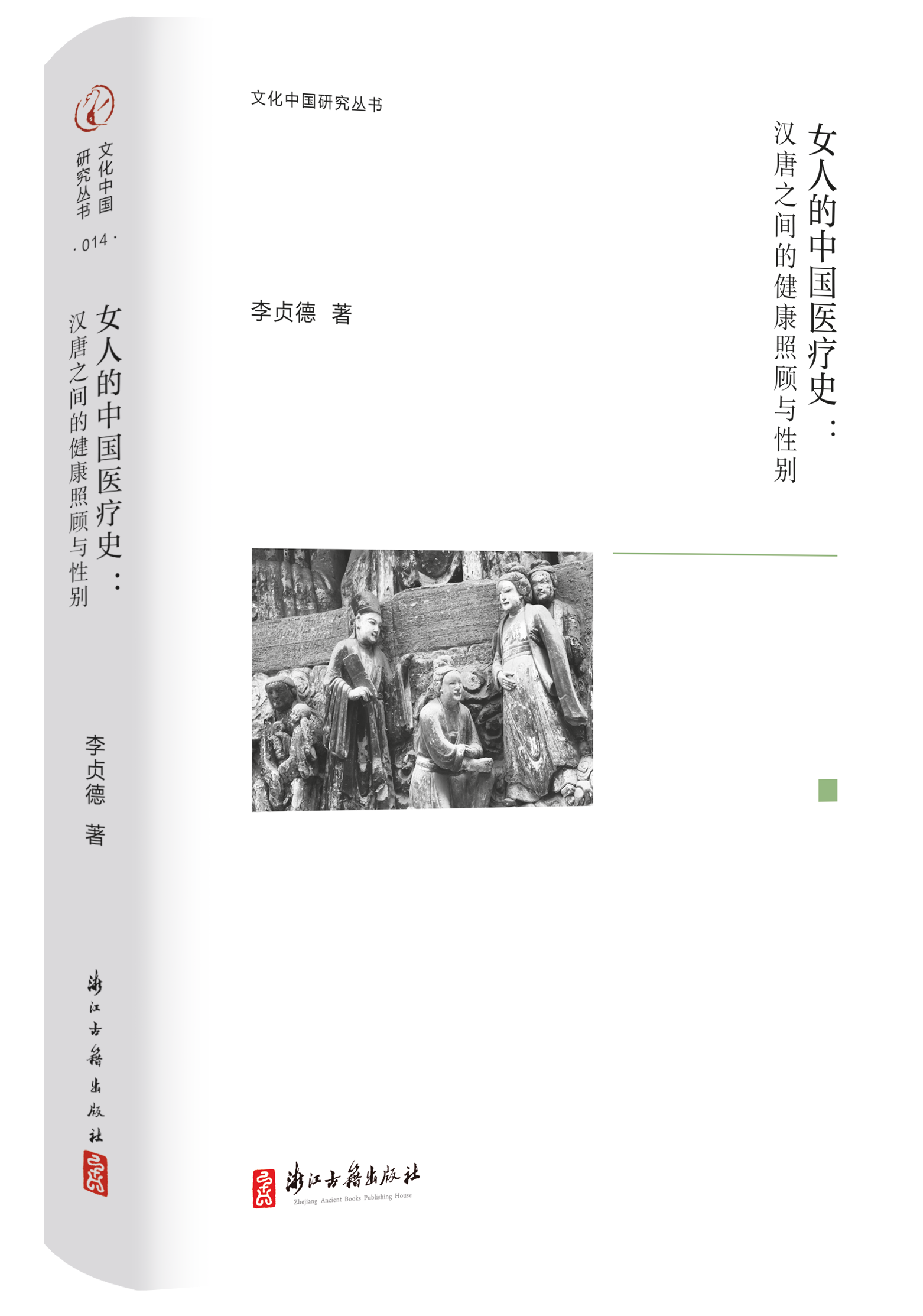
(本文摘自李貞德著《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